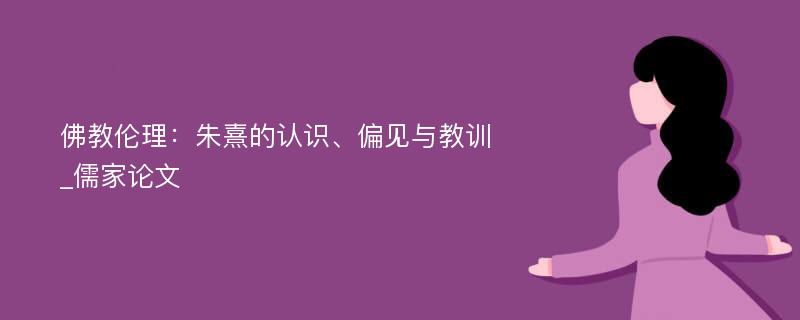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失论文,佛教论文,朱熹论文,伦理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20-08
自从佛教进驻中土,佛教伦理便遭到儒家学者的普遍性批评;然而,或许只有朱熹的批评更系统更深入,只有朱熹的批评更集中地暴露出儒家学者评论佛教伦理的缺点和不足,只有朱熹的批评更能让人把握到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关系的真实信息。
第一,不识天理。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认知能力的评判。在朱熹看来,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诸关系乃天之伦,仁、义、礼、智、信、敬诸德性乃天之德,皆为“天理”。这些“天理”是平常简单的,是日用庸常之道,识之不艰,行之不难,没有任何神秘莫测之相。然而,佛教却不识得此“理”。朱熹说:“圣门所谓闻道,闻只是见闻玩索而自得之之谓;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当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测知,如释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说也。如今更不可别求用力处,只是持敬以穷理而已。……先圣言此,只是说言必忠信,行必笃敬,念念不忘,到处常若见此两事不离心目之间耳。如言见尧于羹,见尧于墙,岂是以我之心还见我心别为一物而在身外耶?无思无为,是心体本然未感于物时事,有此本领,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论之云云也,所云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天理尽见,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运用无非天理之发见,岂待心思路绝而后天理乃见耶?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若使释氏果见天理,则亦何必如此悖乱、殄灭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1](P2836)朱熹认为,“闻”,即见闻玩索而自得之谓,“道”,即君君臣臣父子之谓,没有什么玄妙奇特之处,所以根本用不着在身外另找一个用力的地方,只是持敬穷理即可。换言之,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运用便是天理的发用,所以佛家谓只有折腾得“心思路断”方见得“天理”,实在是不知“天理”为何物、不知“天理”在何处。亦正因为此,佛家不仅不亲履忠、孝、悌诸德,反而舍本求末,花大气力去解释“当孝者应是怎样”、“当悌者应是怎样”等多余问题。朱熹说:“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所以当弟者是如何,自是无缘得如此。……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著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其为说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弩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所以谓之禅机。”[2](P1304)也就是说,在儒学中,事亲即为孝,事兄即为悌,十分简单明白。而在佛教那里,事亲,必须体认得“事亲者”是何物,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仁”;事兄,须体认得“事兄者”是何物,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义”。朱熹批评这是画蛇添足,是禅家言道方式作怪,也就是“禅机”,是离心为二。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不识天理”:一是认为佛教故作高深,将易知易明的“天理”复杂化;二是认为佛教故弄玄虚,对仁、义诸德作毫无必要的求证。所以,朱熹言佛教“不识天理”,即言其不识儒家伦理,不识儒家伦理是平直简易之道。
第二,不守伦理。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实践能力的评判。朱熹认为佛教不仅在认识“天理”上表现低能,在伦理实践上也毫无建树。朱熹说:“释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胫坐也得,叠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将见喜所不当喜,怒所不当怒,为所不当为。他只是直冲去,更不理会理。吾儒必要理会坐之理当如尸,立之理当如斋,如头容便要直。所以释氏无理。”[3](P3490)如果按照佛家的做法,孔子以“理”教人便是多此一举了。朱熹说:“若是如释氏道,只是那坐底视底是,则夫子之教人,也只说视听言动底是便了,何故却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居处、执事、与人交’,止说‘居处、执事、与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着个‘恭、敬、忠’?如‘出门、使民’,也只说个‘出门、使民’便了,何故却说‘如见大宾?如承大祭’?”[3](P3940)孔子之所以在视、听、言、动后面“设置”一个“礼”,就是告诉人们,视、听、言、动不仅仅是动物性行为,还是社会性行为。佛家“不守伦理”还表现在有“克己”而无“复礼”。朱熹说:“克己是大做工夫,复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也。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便至以君臣为父子,父子为君臣,一齐乱了。”[4](P1452)为什么说佛教只有“克己”而无“复礼”呢?因为在儒家学说中,“克己”意味着言谈举止处处皆合规矩准绳,意味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而在佛教的“克己”那里,这些皆是“无”,所以说佛教有“克己”而无“复礼”:“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4](P1454)本来,按照朱熹的理解,“克己”与“复礼”是一,“克己”便能“复礼”,可是由于佛教“克己”与儒家“克己”不同,佛教“克己”仅仅是自修其身、自养其性,置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人伦关系于不顾,视仁、义、礼、智、信、忠、孝、敬诸道德规范为虚妄,自然也就谈不上遵守伦理了。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不守伦理”:一是认为佛教徒言谈举止、情感表现没有规矩,恣意妄为;二是认为佛教将俗世中的人伦秩序、伦理规范、道德责任全部抛弃。所以,朱熹言佛教“不守伦理”,即言其不遵守儒家伦理,不履行道德责任。
第三,自私其身。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目标的评判。任何一种伦理都有其价值目标,朱熹认为,佛教伦理的目标是“自私其身”。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则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纤毫之间,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纤毫造作轻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若夫释氏,则自其因地之初而与此理已背驰矣,乃欲其所见之不差所行之不缪,则岂可得哉?盖其所以为学之本心,正为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己不得一席无理之地以自安:厌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无理之时以自肆也;是以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虽自以为直指人心,而实不识心;虽自以为见性成佛,而实不识性。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5](P3376)在朱熹看来,大宇宙只有一个“理”,这个“理”是万物所以为万物的终极根据。天得此“理”为天,地得此“理”为地,生于天地之间的万物因各分得此“理”而成其“性”,此“理”之成为“法”即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此“理”之成为“纪”即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概言之,万物皆是此“理”流行之结果,故此“理”无处不在,无时不流。儒者识得此“理”,故其心内外精粗不容有纤毫之间隙,而修己治人、垂世立教,也不容有纤毫造作之己私,所以,儒者是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故其参天地赞化育,可以做到无论是大小、明暗之物,皆无轻重厚薄之私。然而,佛家对世界的认识,一开始便与此“理”相悖,所以希望佛教所见不出差错、所行不出谬误是不可能的。佛家所谓为学之本心,正是因为厌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自己得不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正是因为厌恶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自己得不到一息轻松自由之时;所以只有离妻弃子、弃君逃臣、入山捐命,以逃入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足见佛家气量之狭隘、气势之忤逆。因此,佛教根本就没有触摸到“穷天地亘古今之实理”,自然也就不识得心、不识得性了;而昧于天理、殄灭人伦法度而与禽兽为伍也就成为必然。佛家既然以万法为幻,既然不知忠君、孝亲、敬妻、养子是“天理”,而遁迹山林以自修其身、自养其性,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上责任,判其为“自私其身”应该不算冤枉。朱熹说:“佛氏虽无私意,然源头是自私其身,便是有个大私意了。”[4](P1453)不过,朱熹也清楚,这个“自私其身”与私欲私利是不同的:“(佛法)要求清净寂灭超脱世界,是求一身利便。”[3](P3953)可见,朱熹批评佛教“自私其身”,实际上是批评佛教徒自修其身、图一己之便利,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
第四,无缘之慈。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特征的评判。为什么说佛教伦理关怀是“无缘”的?朱熹有他的解释。首先,表现在人兽不分上。在朱熹看来,禽兽虽有灵性,但毕竟与人不同。他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须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存佛性,与自家都一般。”[6](P1891)也就是说,人不仅禀承天之所赐此善此理,并能秉持此善此理,这就是人与物的差别。但众人不识得此差别,所以不能自别于禽兽,故虽为人,而实无以异于禽兽;而君子识得这种差别,并能存得此善此理,从而能自别于禽兽。因此,不能认为所有含灵之物与人一样皆有佛性。否则,必然模糊人与物的界限,从而混人与物为一,继而导致无亲疏厚薄、无君无父。既然人与物不具有共同的天赋,从而不具有共同的成佛根据,而佛教却要广而爱之、等而爱之,故其爱乃是“无缘”之爱。朱熹说:“禅家以父子兄弟相亲爱处为有缘之慈。如虎狼与我非类,我却有爱及他(如以身饲虎,便是无缘之慈,以此为真慈)。”[3](P3953)在朱熹看来,佛教之“慈”分两种,一是有缘之“慈”,一为无缘之“慈”,而以“无缘之慈”为真慈。因而从根本上说,佛教之“慈”是不需要缘由的。朱熹说:“释氏说‘无缘慈’,记得甚处说‘融性起无缘之大慈。’盖佛氏之所谓‘慈’并无缘由,只是无所不爱。若如爱亲之爱,渠便以为有缘,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3](P3953)佛教所谓无缘由之爱,就是无所不爱;而爱亲之爱,佛家认为是有缘之爱,故弃父母而不养:可是遇上饥肠辘辘的老虎,佛教徒却可舍身以饲之。可见,佛教的“无缘之慈”,以“无缘”超越了“有缘”,是一种泛爱、兼爱,而且以此爱为最高追求。其次,表现在等民、物为一上。“爱物”是儒家、佛家共同之理念,但在仁民爱物的秩序和方式上,佛教与儒学有异。朱熹说:“‘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然谓之爱物,则爱之惟均。今观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兽之类是也;有无知之物,草木之类是也。如数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圣人于有知之物其爱之如此。斧斤以时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于市,圣人于无知之物亦爱之如此。如佛之说,谓众生皆有佛性,故专持不杀之戒,似若爱矣。然高宫大室,斩刈林木,则恬不加恤,爱安在哉?窃谓理一而分殊,故圣人各自其分推之,曰亲,曰民,曰物,其分各异,故亲亲、仁民、爱物亦异。佛氏自谓理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一,但借此言),但指血气言之,故混人(亲)、民、物为一,而其他不及察者,反贼害之。此但据其异言之。若吾儒于物,窃恐于有知无知亦不无小异。盖物虽与人异气,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气所生,与无知之物异,恐圣人于此须亦有差等。”[7](P2689)朱熹认为,“爱”于任何物都应该是均平的,不管是有知之物(如禽兽之类),还是无知之物(如草木之类)。对于有知之物,圣人之爱表现为数罟不入洿池、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对于无知之物,圣人之爱表现为依时令入山、未成林之木不伐。同时儒家既有“均爱”,又有差等。佛教谓众生皆有佛性,从而戒杀,看起来爱得深爱得厚,但看看佛教富丽堂皇的高宫大室,足明其砍伐树木之无情,哪还有什么“爱”呢?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家不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何谓“理一分殊”?比如圣人之“爱”,因对象差别而推及之,亲、民、物(包括有知之物和无知之物)四者各异,所以对于四者的“爱”也就有厚薄不同:但佛家只懂得(可能)“理一”的道理,而不知“分殊”的道理,所以仅就“血气所生”的角度看,混“亲”、“民”、“物”为一,而那些非“血气所生”者(如无知之物)则无缘无故地遭到戕害。而儒家的做法是,一方面,于“有知之物”与“无知之物”都有爱,但有等差;另一方面,于“血气所生”之物亦皆有爱,但必须有等差。可见,与儒学相比,佛教奉行“均爱”而不能爱“无知之物”,故为狭隘;佛教奉行“均爱”而无等差,故混亲、民、物为一。概言之,佛教之爱由远而近,由外而内,泛爱万物,次而禽兽,次而他人,次而家庭,次而自己,即“缘”厚者、近者,越可放弃;与此相反,儒家则是先己后人、先人后物,即“缘”薄者、远者,越可放弃。所以,佛教之爱,是“无缘”之爱,是与儒家之爱背道而驰的,既去亲离子,又不关怀社会众生;儒家之爱于父母,是至大至亲,佛家之爱于父母,是非仁非义,与儒家伦理完全反辙。所以说,佛家是“合侧隐底不恻隐,合羞恶底不羞恶,合恭敬底不恭敬。”[8](P177)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为“无缘之慈”:一是认为佛教人兽不分,爱兽甚于爱人;二是认为佛教亲、民、物不分,混亲、民、物为一,从而颠覆人伦秩序。所以,朱熹言佛教为“无缘之慈”,即言其无有血亲意识、人伦意识、等差意识,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伦关系的颠倒。
第五,绝类止善。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后果的评判。为什么说佛教伦理后果是“绝类止善”?朱熹也有他的解释。首先,何以说佛教“绝类”?朱熹认为,判佛教为“绝类”之教,第一是因为佛教主张离家出世,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为幻妄。朱熹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却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为幻妄。”[9](P3117)我们知道,“五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基本关系,社会其他关系的和谐、健康,与“五伦”关系的状况密切关联。而佛教以“五伦”为幻妄,自然是绝灭了“五伦”,也就绝灭了所有人伦关系。第二是因为佛教空幻万物,绝灭义理。朱熹说:“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3](P3932)所以不但不“敬”父母,就是赡养父母也是一句空话:“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奈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佛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3](P3960)连父母都不能养、不能敬,那还有什么义理可言呢?第三是因为佛教主张不婚不育,绝灭人类生殖之源。朱熹说:“(佛教徒)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5](P3377)就是说,佛教徒出家离世,自以为逃入空门,却无异于绝灭人种的繁殖。不过,朱熹认为,佛教并不能绝灭人类生殖之源。他说:“然则彼释迦是空虚之魁,饥能不欲食乎?寒能不假衣乎?能令无生人之所欲者乎?虽欲灭之,终不可得而灭也。”[10](P2015)概言之,朱熹所言佛教“绝类”,是因为佛教所为绝灭了人伦关系、绝灭了人间义理、绝灭了人类繁殖之源。其次,何以言佛教“止善”?朱熹也给予了自己的解释。一是佛家不能理解“元”是万物的始点、“善”的始点,却以万物为幻,以寂灭为乐,从而绝类止善。朱熹说:“‘元者,善之长’底意思,释氏既不识元,绝类离群,以寂灭为乐,反指天地之心为幻妄,将四端苗裔遏绝闭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则要于此发处认取也。”[11](P2217)在儒家思想中,“元”,不是一个简单的始点,而是万物的开端,是善的种子和起点,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易传·文言》)但佛家不识“元”的意蕴,反指天地之心为幻妄,从而遏绝仁、义、礼、智四端之流行。所以朱熹所忧虑者,在于佛家从源头上遏制了善的生长。二是“奉佛替善”。佛教号召众生敬佛拜佛,而且认为这是善行,会得到佛的保佑。但朱熹认为,奉佛不足以为善,反而是将善的标准改变了。朱熹说:“自浮屠氏入中国,善之名便错了。渠把奉佛为善。如修桥道造路,犹有益于人。以斋僧立寺为善,善安在?所谓除浮屠祠庙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于彼,自然孝父母,悌长上,做一好人,便是善。”[3](P3955)何以言佛教改变了善的标准?佛家以尊奉佛法、斋僧立寺为善,而将孝敬父母之行遗忘,如是,佛教“善”之内涵与儒家完全不同。三是“死后治恶”。佛家有所谓地狱说,认为恶者死后统统会进入地狱,接受地狱的惩罚。朱熹认为,如果作恶之人等他死后再来惩罚,非但不能护善,反而会助长恶。朱熹说:“吾友且说尧、舜、三代之世无浮屠氏,乃比屋要封,天下太平。及其后有浮屠,而为恶者满天下。若为恶者必待死然后治之,则生人立君又焉用?”[3](P3955)由于佛家地狱说是针对为恶者而言的,既然犯恶者死后才进入地狱接受惩罚,那么现实社会中立人君还有什么意义?立人君就是教化人为善的,所以“死后治恶”乃是止“善”。基于此,朱熹认为佛家是善恶不分的。他说:“圣人不说死,已死了,更说甚事?圣人只说既生之后,未死之前,须是与他精细理会道理教是。……释氏更不分善恶,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狱。若是个杀人贼,一尊了他,便可生天。”[3](P3944)以对待佛是否尊敬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不管这个人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只要他在佛面前表达恭敬之心,不仅可以赎罪还可以成佛。按照这种“善”的标准,儒家所建构的一套关于“善”的理论体系,就可能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朱熹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12](P370)佛教虽自谓光明,但不知人伦之理,不知父子之亲,不知君臣之义,此乃佛教“止善”之必然结果。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为“绝类止善”:一是认为佛教出世离家而绝灭了人伦物理、佛教主张不婚不育而绝灭了人类繁殖之源;二是认为佛教遏制了善的增长、以奉佛代替行善,完全改变了“善”的意义和方向。所以,朱熹言佛教为“绝类止善”,即言其绝灭人类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劳动力基础,言其改变了“善”的含义和方向。
如上即是朱熹对于佛教伦理的认知和评判之情形。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朱熹的这份认知和评判佛教伦理的实践,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教训与启示呢?
第一,揭示了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差异。在朱熹认知和评判佛教伦理实践中,朱熹揭示了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几种常见性差异,主要有:佛教把人伦物理看得太神秘、太复杂,认为要么深山修行,要么精细考证,方能识得“天理”,而在儒家这里,“天理”乃天之所命,为平直简易之道,所以说在认知上,佛教不识天理;佛教言行举止无拘无束,喜怒无常,置礼于不顾,而在儒家这里,礼制伦理是行为的准则与说话的根据,所以说在实践上,佛教不守伦理;佛教自私其身,只顾小我,漠视社会公共事务,而在儒家这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神圣的责任,所以说在社会责任感上,佛教是没有尽其所能;佛教之爱无亲疏之别,无人、兽、物之别,而在儒家这里,爱不仅有亲疏远近的差异,还有等级的差异,所以说在施爱方式上,佛教是无母无父、无君无臣;佛教绝灭人类繁殖之根,遏制长善之源,而在儒家这里,生殖是人类延续、存活的基础,绝类则意味着人类的毁灭,而“善”只体现为实践中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所以说在表现“善”的方式上,佛教是空疏无实。总之,在朱熹看来,被儒家奉为简易平直之“天理”,佛教却不能认得、不能接受;被儒家奉为社会之经纬、秩序之纲常的礼制伦理,佛教却不践行;被儒家奉为神圣责任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佛教却漠然置之;被儒家奉为施爱方式之“亲亲仁民爱物”,佛教却不分亲疏,彻底颠覆;被儒家奉为植善之象征的博施济众、孝敬父母等具体的善,佛教却以奉佛代之。这样,佛教伦理不能不对儒家伦理构成威胁,不能不给儒家伦理制造麻烦。然而,这种威胁或麻烦,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朱熹思想世界中的威胁和麻烦。而从学术意义上考量,朱熹对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差异的揭示,虽然存在诸多误读之处,但的确暴露了佛教伦理异于儒家伦理的部分,从而为理解和处理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分析资料和结论。但让我们失望的是,朱熹本人并没有根据这种比较和分析,对佛教伦理做积极方向的开掘与引导,而是作出了一系列非常消极的结论。如是,我们的讨论便不得不转向朱熹在对佛教伦理认知和判断中所出现的偏差和失误。
第二,对佛教伦理的片面认知和错误评判。朱熹虽然觉察到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基本差异,但他将这些差别一味放大,致使其于佛教的认知与评判方面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与佛经本义不相合。何出此言?朱熹言佛教“不识天理”,儒家所谓“天理”无非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及其他人伦关系,仁、义、礼、智、信“五德”及其他德性,而《无量寿经》云:“世间兄弟,当相敬爱无相憎嫉,有无相通,无得贪吝,言色常和,莫相违戾。”[13](P274)提倡兄弟敬爱、勿要憎恨,此不可谓“识得天理”?朱熹言佛教“不守伦理”,儒家所谓“伦理”无非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及其他人伦关系,而《杂宝藏经》云:“不听弃老,仰令孝养。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当加大罪。”[14](《杂宝藏经·弃老国》,P21)此是教导人们必须孝敬父母、长辈。《观无量寿经》云:“欲生彼国(西方极乐国土)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读大乘,劝进行者。”[14](《观无量寿》,P226)此是教导人们应怎样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楞严经》云:“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15](P170)此是告诉人们,那些遵守戒律、践行伦理的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会获得奖励。如此,还能说佛教“不守伦理”乎?朱熹言佛教“止善”,朱熹所谓“止善”即是抑止善源、以敬佛代善。而《佛性论》云:“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种公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除五种过失者:一,为令众生离下劣心故。为离慢下品人故。为离虚妄执故。为离诽谤真实法故。为离我执故。……为此五义因缘,佛说佛性生五种公德。一,起正勤心。二,生恭敬事。三,生般若。四,生闍那。五,生大悲。’”[16](P21-23)佛祖提出佛性说是为了“除过生德”,即为了除去五种过失、生出五种公德,而且以财富、地位、寿命、土地等鼓励人们行善,怎能说佛教是助恶扶邪、绝类止善?可见,朱熹关于佛教伦理的一些认知和判断与佛经本义的确是有距离的。
第三,不能理解佛教伦理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佛教伦理亦自有不同于儒家伦理的特质,但朱熹不能理解、不能领悟这些特质。首先,不能理解佛教伦理的逆向性。所谓佛教伦理逆向性,是指佛教伦理不从“顺向”关怀人,而是从“逆向”关怀人。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的基本关怀,但佛教却主张离家出世,躲在深山老林自修其身、自养其性。与儒家伦理关怀比较,佛教伦理似乎显得消极、负面。然而,佛教要求修身养性者,都应努力将自己的德性品行修炼到最高境界,并推布于世,型于万民。再如,佛教言“人生是苦”,并不是否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是说,人生拥有的一切都是常变的、易逝的、短暂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珍惜人生,追求人生的幸福,实现人生的价值。可见,佛教伦理实践上亦是关怀人世、关怀人生的,只不过,它采取的是一种“逆向”方式而已。但朱熹不能认识到这点,他只看到出家离世的视觉缺陷,看不到此现象身后的价值,所以批评佛教伦理消极、空虚。其次,不能理解佛教伦理的自虐性。所谓自虐性是指佛教伦理在教化众生的过程,采取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摩诘经》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而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比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疾何所起因?菩萨疾者,以大悲起。”[17](P124)菩萨与众生是一体,众生乐,菩萨乐;众生苦,菩萨苦;因此,菩萨完全是以一己之生救度众生。《华严经》云:“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14](《华严经》,P80)为了众生远离疾苦、获得安乐,菩萨愿代众生受苦。就是说,佛教信徒完全是甘愿承受所有的罪业,代人受过,承受苦痛,以感化他人。事实上,佛教徒离别父母,是去亲情之乐;不婚不嫁,是去情欲之说;食素不荤,是去食欲之好;……无不是佛教牺牲自我以度脱众生、感动众生的伦理教化之体现。可见,佛教伦理教化是一种牺牲自我的教化,这与儒家伦理以追求事功、成就大业为教化方式是不同的。朱熹不能认识到这点,他只看到佛教徒逃世遁形、逍遥自在的一面,看不到佛教信徒自虐行为的伟大和所内含的巨大感化力,所以批评佛教自私。第三,不能理解佛教伦理的超越性。所谓超越性是指佛教伦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心灵的纯洁和救赎,是精神的升华。佛教谓万物皆有佛性,即谓人人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从而给顽劣者以自新的机会,给善良者以向善的动力,这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伦理情怀,它超越了智愚的差异、身份的偏见、等级的歧视,体现了佛教的大慈大爱。朱熹不能理解这点,反以“亲亲、仁民、爱物”这种狭隘的、等级的、近亲远疏的推爱方式否定佛教“无缘之爱”,朱熹只见“物有佛性”说对等级伦理造成的冲击,而根本无法领悟“物有佛性”内具的肯定人、关怀人的深刻内涵,根本无法领悟佛教平等伦理对儒家血亲伦理所具有的更新意义。佛教认为,万事皆有因果,如有人此生作恶,在来世便会下到地狱遭受惩罚,是谓因果报应。因果论在于警示众生,此生如果行恶,就会下到地狱遭受惩罚,故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由历史经验看,因果报应论对于人类在实际生活中近善远恶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由价值指示看,这个教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人从心灵上确立行善的根据。也就是说,因果报应论实际上是让人们由心灵上了悟行善是一种内在责任,从而确立行善的信念。朱熹不能理解这点,认为这是“死后治恶”,将导致君王教化的废弃。显然,朱熹只看到因果报应论被他夸大了的消极面,而没有看到因果报应论所蕴涵的精神救赎意义。可见,朱熹立足儒家伦理的现实层面,去理解、判断佛教伦理,的确出现了较大的偏失。
第四,需要更新的态度和方法。本来,朱熹能够揭示一些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差异,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他的成就也就仅仅停在这个界面上,没有进一步对佛教伦理的深刻而独特意蕴进行开掘,对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在功能、特性上互补的可能性、程度及其效果进行尝试。非但如此,朱熹对佛教伦理的认知和评判,还表现出态度上的片面性和认识方法上的局限性,以致佛教伦理根本无法真正进入到其思想世界,根本没有成为朱熹伦理思想成分的可能,也就根本没有成为宋代新儒学内容的可能。如果我们并不认为朱熹对佛教伦理的错误认知有其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因为朱熹的错误判断而影响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的融合是思想史上的一次失败,那么,我们又应该从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有宽容的态度。前文已示,佛教伦理被朱熹判为“不识天理、不守伦理、自私其身、无缘之慈、绝类止善”。那么,朱熹对佛教伦理何以作如此片面的评判呢?根本原因在于朱熹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极端否定的态度。这种极端态度就是把儒家伦理视为绝对的、至上的、唯一的伦理,然后用儒家伦理作为审判佛教伦理的准则和根据。而儒家伦理所具有的唯物、排神、实用等特性,与佛教唯心、容神、超越等特性是完全相悖的,这样,佛教伦理进入朱熹思想世界的通道便被彻底堵死,朱熹也就不可能对佛教伦理进行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诠释,也就不可能在价值上对佛教伦理有真正的肯定和容受。因此,如果要对一种宗教有正确的诠释和正确的评判,我们必须拥有宽容的态度。对本案而言,就是不能预设儒家伦理本位主义立场,尤其不能将这种立场绝对化,将佛教伦理置于被动的接受审判的位置,而应让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具有平等对话的机会和权力。其次,要有深入研究、全面把握的专业修养。就是说,有了宽容的心态之后,如何在行动上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准确的研究、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对所研究对象不做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就随便发表结论,那是妄论。就本案而言,就是要对佛教伦理的文本文献做基本性把握,就是要对佛教伦理内容做深入的研究,就是要对佛教伦理的特殊性做精准的透悟。世界上的事物因特殊而丰富多彩,因特殊而有自己的个性并获得存在的根据,所以,对于佛教伦理而言,也应从它的特点去认识、肯定、发挥它的价值,而不是用另一种伦理(儒家伦理)去消解它的特点、否定它的价值。如是,人类所能享用的伦理资源才会不断丰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