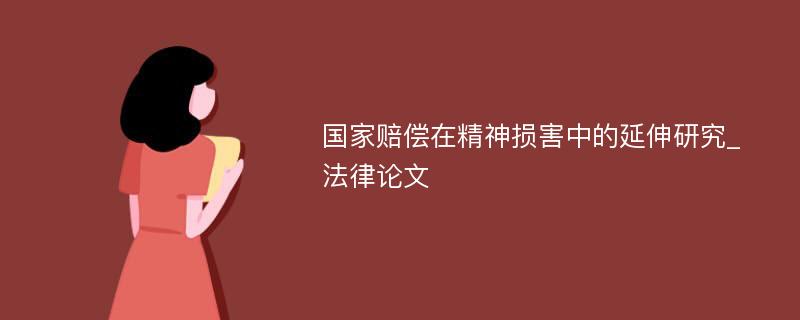
国家赔偿范围拓展至精神损害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赔偿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赋予了作为 司法对象和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因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的不法侵害造成损害时,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对于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在经过几年的具体运作之后,我国第一部国 家赔偿法在具体内容上的确存在一些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可赔范围的狭窄。 国家赔偿范围主要是指能够引起国家赔偿的事项,它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两部分, 我国《国家赔偿法》仅将物质损害确定为赔偿对象。
然而,我们在实践中遇到了如下一些案例。
案例一:1995年6月9日,某市城西区黄河路派出所治安民警丁某和黄某按照上级关于 整顿市容、收容遣返乞丐、流浪人员的统一部署,上街执行任务。一名已被丁某捉住的 流浪儿趁其不备,挣脱丁某双手逃跑,丁某在重新将流浪儿抓住后口出秽言并打了他两 个耳光,路过此地的赵某说:“他还是个孩子,你不要打人嘛。”站在一旁的黄某厉声 说道:“我们正在执行公务,你少管闲事。”赵某不服,与黄某争辩起来,并引起群众 围观,丁某见状十分生气,在黄某的配合下当众强行给赵某拷上手拷,拖入警车带回派 出所。派出所所长韩某在问明情况后感到丁某和黄某行为欠妥,当即下令将赵某释放。 赵某于次日向该派出所的上级机关城西公安分局,以其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人格尊 严受到侮辱为由,要求行政赔偿。(注:参见胡锦光主编:《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案例二:1989年5月,某县乡镇企业局与个体户邱某某签订了承包该县某供销公司的协 议。邱某在承包后,该公司一年后就扭亏为盈。1991年初乡镇企业局以整顿该公司为由 单方面撕毁合同,邱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县法院经审理后作出裁决:“准予原告 正常营业,维持原承包合同关系。”县乡镇企业局在败诉后捏造事实,向某县公安局反 映邱某某有侵吞财产等严重经济问题,1992年3月5日,县公安局将邱某某收审,限制人 身自由达7天,且从未向其出示过任何法律手续,7天之后,县公安局又给邱某某办理了 取保候审手续,在取保候审期间,邱某某多次请求公安局尽快给一个说法,然而公安局 一直置之不理,致邱某某取保候审达两年之久。1995年5月6日,邱某某向县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县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要求赔偿其在公安局收审和取保候 审期间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0万元。(注:参见关保英编著:《行政法案例教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实际上,这两个案例只是从众多类似案例中选取的并非典型的案件,这类案件的起因 都是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采用了违法手段给公民的心理及感情带来 了伤害,原告都有精神赔偿的诉求,但囿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受害人都无从获得赔偿 。
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赔偿范围采用了列举式规定,(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第3、4、15、16条规定。)实际上也就是将法条中没有列举的部分排除在国家赔 偿之外,而精神损害恰恰在排列之列。由于精神损害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受害人心理和 感情的创伤和痛苦,它一般表现为受害人在权利遭受侵害之后所产生的愤怒、绝望、恐 惧、焦虑、不安、屈辱等情绪,这种情绪往往还会影响到受害人的日常工作、生活。精 神损害属于人身权益损害的一个类别,它与其他人身权益一样都应得到法律的一体维护 ,而且精神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一样都是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存在获得法律救济 的现实理由。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对国家机关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在 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但30条的规定没有 现实的应对性手段作为保证,所以这一规定对于受害人而言形同虚设,显然是缺乏力度 的。
国家赔偿范围的界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其宽狭界定不仅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受到监督和约束的重要标志,更是直接关系到有公民的受损权利能 够得到国家法律救济范围的程度,它往往也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
二、国家赔偿范围日益拓展的国际化趋势概览
在当代社会,国家机关,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极其密切,社会各个层面与各级政 府职能部门的关系更是如影随形,在国家干预日益普遍、公共权力的行使剧增、行政自 由裁量权不断扩大的现实下,侵权纠纷大量涌现,同时也正是由于行政权的“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无所不能”,防范与救济公权力对公民权益造成侵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 为各国国家赔偿制度成立并将可赔范围进行不断拓展的理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盟的实质性作用的加强,世贸组织对国际社会超越经济事 务的渗透,全球化时代已现实地逼近,在法律领域,甚至连最具国家主权色彩的公法制 度也渐渐地为适应全球化的冲击而有所反应。
在国家赔偿法制化进程中,作为世界上国家赔偿制度建立较早的西方国家对精神损害 是否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作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
最初如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是将精神损害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的,“法国行政 法院在建立之初,赔偿范围仅限于能以金钱来计算的损害,对于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精 神损害,如对名誉、感情等的侵害,国家不负赔偿责任。”(注:皮纯协、冯军主编: 《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因为按照当时的观点,可 赔偿的损害应是现实的、确定的、可衡量的,作为精神损害则是无形的、主观体验的, 因此,各国法律“最初将国家的赔偿责任局限在物质损害的范围之内,在国家赔偿的初 始阶段,只有物质才是可赔偿的对象,其后逐渐发展到人身非财产损害领域以及有碍生 存的损害领域,最后被适用于精神损害领域。”(注:江必新著:《国家赔偿法原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最早对非财产性损害予以赔偿的国家 是瑞士,它是以民事赔偿方式来体现的。(注:瑞士债务法第35条:由他人之侵权行为 ,对人格关系上受到严重损害者,纵无财产损害之证明,裁判官亦得判定相当金额之赔 偿。)法国于1964年11月24日在公共工程部长诉Letisserand家属案中,认为尽管缺乏物 质损害,儿子的死亡给父亲造成的痛苦是可以作为给父亲赔偿的充分理由的,自此,法 国开始接受并判决死者近亲之感情损害。(注:参见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德国于1973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更是明确地 将精神损害作为了国家赔偿的对象,该法第2条第4款规定:“应予赔偿的损害包括所失 利益以及依据第七条标准发生的非财产损害”,其第7条的规定为:“对于损伤身体的 完整、健康、自由或者严重损害人格等非财产损害,应参照第2条第4款予以金钱赔偿。 ”
今天,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国家赔偿范围的构建上,已经涵盖了精神损害的赔偿, 即精神损害已成为不容争辩的可诉对象和法律救济对象。当代社会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在 民事审判中得以司法支持以外,作为国家赔偿范围之一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得以法 定化,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许多国家关于国家赔偿方式与民法是基本相同的,如日本《 国家赔偿法》第4条就明确规定:除国家赔偿特殊规定外,国家或公共团体的损害赔偿 ,依民法规定,包括对精神赔偿。
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赔偿法》未能包含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实是一重大缺陷。我们 已经有近七年的国家赔偿的法律实践,其间对国外同类法律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完全 可以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身的特点将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拓展至 对精神损害的救济。
三、国家赔偿应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在当今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词汇,将其放在社会运作机制的环境,它主要 是指我们的制度从订立到操作都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应切切实实地关注公民的各项权益 的制度化程度、实现的过程及其受阻时通过什么途径、以何种方式进行救济等实质性的 问题。在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将人作为个人而不是群体对待,这一态度集中反映在对 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上,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忽视甚至侵犯 公民的各项法定权利,其中当然应该包括精神权益。
在我国公民的心目中,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以“为人民服务”为 行为宗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最值得信任与依赖的力量正是各级国家机关,可 以想象,当公民的权益一旦受到源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对其心理上、精 神上造成的打击就是巨大的了,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 ,代表了国家对个人的评价,其对相对人的态度往往会影响到社会对该相对人的态度, 并决定他人对该相对人的评价。事实证明,对受害人不利的评价给其带来的精神痛苦是 大于遭受的物质损失的。我们一再呼吁社会要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实际上公民的人格 尊严同样,甚至更加需要国家赔偿法的认可与保护,因为任何个人面对国家机关所拥有 的权力而言都是脆弱的,法律理应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庇护力量。
一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设计往往要受到诸如国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国家对公民权利 的关注程度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的制约。具体到可赔偿范围,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盖多 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救济制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忽略,虽然在 我国民事赔偿审判实践中已逐步肯定了精神赔偿责任,但作为法律规定来讲仍是非常不 明确的;二是居于国家财力的考虑,认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也刚 刚起步,国家还不富裕,而国家赔偿是要由国库开支的,国库的钱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客观地说这一点是造成现行国家赔偿法限制可赔范围的重要原因。
其实,正由于我国民事赔偿已有了精神赔偿的经验积累,同时在日益加剧的公民权利 意识中,精神损害作为法律救济对象已经较为广泛地为我国公民所接受,所以法律将精 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已经具备了实践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由于我国的国家赔 偿制度是以《国家赔偿法》为主体,一系列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 》、《海关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为助体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我们完 全有可能通过一些调整领域更为狭窄的法律法规的先行规定与实际运作,探索出一条适 合中国的精神损害国家赔偿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经济尚不十分发达、国库尚不十分充盈为理由,从制度上 忽视公民的人格尊严,或者在公民的精神权益在受到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侵害时 已可获得民事赔偿的情况下,在相同权益受到国家机关侵害时无法获得国家赔偿,这对 于形成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极为不利的。为了真正体现公民的权利得到了 国家的尊重与维护,“在法律和社会效益上为防止一切不公平而付出增值的代价是值得 的”。(注:[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页,第262页。)同时就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从最终的目的性上看应当是一致 的,即都是为了弥补当事人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尽管如前所述,我国《国 家赔偿法》第30条对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法侵害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已有所表示 ,但要使国家法律救济得以真正体现必须走精神赔偿的金钱化道路,即要“借物质之手 段达到精神之目的”。
众所周知,权利的实现除了要以法律规定出具体范围以外,至关重要的还必须依赖于 法律救济,“权利与救济不能分割,救济的性质决定权利的性质”。(注:[英]威廉· 韦德著:《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第538页。)人身权益 在我国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的,而宪法权利的最终实现必须要在相应的普通法律 中得以具体化。作为公民人身权益重要内容之一的精神权益也只有在得到具体部门法律 的救济后才是一项真实的权利。我们可以借用英国的一个法律理念来表达我们将精神损 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理由:“不能用国家行为的托词来对付英国国民。”(注:[英] 威廉·韦德著:《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第538页。) 同样,如果在我们的《国家赔偿法》中不能涵盖进精神损害的赔偿,势必会给一些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以执行公务为由恣意侵害公民的人格尊严,这对于我们实现法治化社会的 目标是极为有害的。
“在一个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必要的,它给予公民这样的信心,即法律 值得享有特别的权威,……一个政府通过尊重权利表明,它承认法律的真正权威来自于 这样的事实,即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法律确实代表了正确和公平。”(注:[美]罗纳德 ·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第262页 。)
收稿日期:2002-0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