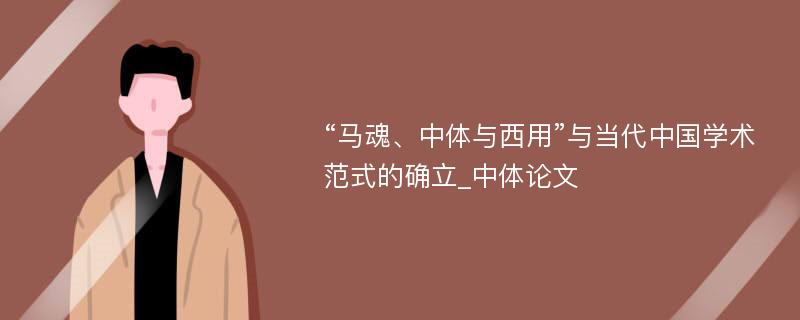
“马魂、中体、西用”与当代中国学术范式之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术论文,中体论文,马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魂、中体、西用”说是方克立先生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及走向,尤其是如何处理中、西、马三种学术文化资源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于2006年提出的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①。“马魂、中体、西用”说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种重要学术理论创新,在客观上为当代中国学界建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马魂、中体、西用”说是方克立先生在继承与反思我国传统文化体用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在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中,体用范畴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本体(主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二是本体(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此二者往往表现为“道体器用”与“器体道用”之异。中国古代学者通常是在“道体器用”的层面来使用体用范畴的,“体”是指恒常不变之精神指导原则,“用”则是指精神指导原则之具体应用。晚清时期“中体西用”论者便继承了传统体用观的此种含义,以中国儒家的“伦常名教”为不变之“体”,以西方现代的“强国之术”为应世之“用”,即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②。方克立先生认为,“中体西用”论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重要偏离在于,割裂了文化之“体”与“用”的统一。传统文化体用观是在一种文化系统内部来区分体用、内外之学,而“中体西用”论者则是在两种(中、西)文化之间来探讨体用关系。方克立先生在否定晚清“中体西用”论之保守意涵的前提下,借鉴了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与“中体西用”类似的“和魂洋才”的表述,引进“魂”的概念来取代原来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而用“体”来专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用“魂”、“体”、“用”三个范畴来表述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三种学术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关于这种“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客观根据和现实可能,方克立先生借用王夫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的思路来加以阐释。中、西、马三“学”作为各自独立的文化系统,本来分别各有其体用,然而,在当代中国,中、西、马三者实际上已成为同一个文化系统中“和而不同”的三种学术文化资源。由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着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故而,西方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观念自然不能成为我们的文化选择,但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学术资源仍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从中、西、马三“学”的关系来说,“中学”或中国文化体现的是民族主体性,它既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对于外来文化而言它又是接受主体,它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那个“形”,由此,“魂”(“道”)、“体”(“形”)、“用”(“器”)三者得以有机地联结、统一起来③。 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说的基本内涵,方克立先生明确指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所谓“魂”,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精神指导原则之重要性。“中学为体”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在此,“中学为体”之“体”,其含义已不再是“中体西用”论者所指的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亦即一种文化系统中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此处之“中学”并非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儒家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④方克立先生指出,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西学为用”是以中国之外所有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作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西用”不仅是对于作为精神指导原则(“魂”)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同时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体”)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来说的。对于精神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便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⑤。 作为“综合创新论”的最新理论形态,“马魂、中体、西用”说突破了传统文化体用观中西对立、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是别出心裁地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表述中、西、马三“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文化方针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方克立先生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马魂、中体、西用”说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觉,同时也在客观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 “范式”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概念。在库恩看来,“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⑥,“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⑦而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就在于是否形成了为该领域的研究者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共同认可并遵守的范式。范式一方面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范围,使研究者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⑧;另一方面又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⑨。事实上,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学术范式的指导,正如梁启超所言:“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⑩基于库恩关于科学范式的理论阐释,可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范式界定如下:所谓学术范式,是指在研究立场、价值取向、学术资源、研究方法、学术话语乃至学术精神等方面为特定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某种自明性预设,它直接影响研究者的基本立场、学术旨趣和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及其社会价值。 学术范式根植于一定的思想文化土壤。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之际,中国这个长期雄踞东方、熠熠生辉的文明古国遭逢所谓“三千年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文化领域也处在频繁的思想变换和激烈的文化碰撞之中,西方文化借着中国积弱屈辱的民族危机和风雨飘摇的政治状态,猛烈地挑战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古典学术传统的现代合理性。一些有识之士以西学为坐标。对中国传统学术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系统整理和深刻反思,这也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步伐,为现代中国学术新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一大批忧国忧民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胡适等在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的基础上,或化西入中,或中西对化,或化中为西,着力打开中国学术界新的知识格局,试图开创现代中国新的学术范式。尤其是随着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格局的形成,如何整合中、西、马三大学科资源,建立现代中国学术新范式,就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不解的情结。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从“全盘西化”到“文化复古主义”,从“马体西用”(11)到“马魂、中体、西用”,每一种文化主张的提出,不仅折射出中国学者关切中国文化命运、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学术范式的可能路径。 “魂、体、用”三元模式涵盖了一个学术范式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维度。其中,“魂”是指特定学术共同体所持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及根本方法,即学术研究之“精神指导原则”;“体”主要是指学术研究主体、学术话语体系及主要学术资源,以此凸显学术研究之“民族主体性”;“用”则是指可资学习、借鉴的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资源及研究方法,亦即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 “马魂”(“马学为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党的旗帜和灵魂,同时也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魂”亦即精神指导原则。哲学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核心地位,更加直接地肩负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铸什么魂”的重要责任。因此,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只有始终不渝地、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是凝固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马学为魂”所强调的就是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即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潜心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与文本的正确解读,同时要深入地了解社会,探求历史规律,把握时代脉搏,尤其是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推出真正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术成果。 “马学为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精神原则、基本方法贯穿于整个学术研究当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处理具体学术问题。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理论立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和抵制宣扬“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复古主义”等错误思潮。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法则,为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方法绝不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照搬、照本宣科、对号入座,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精神实质融入学术研究当中,真正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三是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足国情、立足实践、立足当代,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善于通过理论与学术视角,理性观察生活,深刻洞察社会,提出真知灼见,推出学术精品,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中体”(“中学为体”)主要是指以中国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之主体,以中国文化作为学术研究之根基。建立中国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以此凸显中国学术之民族主体性。 “中体”首先是指以中国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之主体。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度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善于发现并解决这些理论与现实问题,促进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乃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和职责所在。当前,一部分中国学者热衷于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盲目尊崇乃至迷恋西方学说,完全忽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事实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有自己的核心话题与主问题域,只有基于本土的核心话题与主问题域所展开的学术探索,才有可能成为本民族和国家所需要的前沿性学术研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在国际学术界做出独立的贡献,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就需要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逐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进而提出一些为西方学界所无法提出的理论和思想。因此,如何回到“中国问题”,重建“中国立场”,理性找寻自己在世界学术潮流中的定位,乃是构建现代中国学术新范式的核心议题与当务之急。 “中体”同时也意味着以中国文化作为学术研究之根基。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不仅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也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根基,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厚土壤。 “中体”还包括构建中国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在百舸争游、百家争鸣的现代世界学术体系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及其在现代世界对话中的表达能力,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在注重与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对接、广纳世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不能迷失在现代西方学术话语的众声喧哗之中,这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保持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彰显中国学术之民族主体性的基本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认真汲取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中的合理元素,使之成为构建现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源流。正如季羡林所言,中国学术要在全球化的学术境遇中立足并发展,必须以自尊自重的姿态盘点本土文化资源,“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12)。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表述方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用中国的学术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切实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学术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理论自信和影响力。 “西用”(“西学为用”)即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和其他民族思想文化成果中的有益成分。“马学为魂”与“中学为体”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化采取漠视或拒斥之态度,而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本立场,也是“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题中之意。 应当承认,西方包括学术理念、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在内的一整套现代学术体系传入中国之后,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士人皓首穷经的生存模式和以注疏考据为主体的学术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代中国学术范式的总体格局,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范式转型。正如学者杨义所言:“以现代世界人类智慧来激活和展开中国智慧,又用中国智慧来丰富和拓展世界人类智慧,成为学术创新及其现代性的基本思路。”(13)当然,“西学为用”并不意味着对西学的盲目尊崇与全盘吸纳,而是对其中的学术资源进行科学的辨析、梳理与评判,从中吸取合理的内涵。在借鉴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时,有必要将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结合起来,服中国的“水土”,接中国的“地气”。当前,学术界流行的撷取西方学术的只言片语或套用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丰富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当代经验,唯洋是尊、削足适履的学术风气,是与真正意义上的中、西、马融通互补相去甚远的,也是与“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背道而驰的。方克立先生指出:“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你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有没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14),这是“西学为用”的关键所在。 可见,“马魂、中体、西用”说是主张以“兼和”之道融通中、西、马三“学”,彰显马列之魂,融会中西之学,实现综合创新的一种学术范式。其中“马学为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立场、精神原则和根本方法,这也是中、西、马三种学术文化资源整合与融通之基本前提;“中学为体”强调以中国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之主体,以中国文化作为学术研究之根基,同时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挺立民族主体性的客观要求;“西学为用”强调积极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包括研究方法和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三流合一”强调中、西、马的对话互释、交融互补,通过对相关学术资源的梳理与整合,形成新的学术理路,拓展新的学术空间;“综合创新”强调在纵横古今、贯通中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创造转换,最终形成有创新、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马魂、中体、西用”不仅意味着三种思想传统的互释融通,同时包含不同表述系统的话语融合,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新语境中学术发展之必然趋势。“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学术范式,在客观上避免了中、西、马三“学”各执一端、各守一隅的偏颇态度,而是提倡兼容并蓄、和谐共存,强调在多元之中求贯通,在贯通之中求创新,外可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内可以坚持自主性的创新。 “马魂、中体、西用”作为学术范式的建立,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三大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互动与激烈论争中逐渐产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固而逐渐得以确立的,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背景下已日益展现出其独有优势。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建立之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事实上的“舶来品”,是伴随着“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进入并席卷中土的。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道路和方向,同时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分析、解释中国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故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就被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并自觉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他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理解、诠释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在现象与资料的背后探寻事物本质的解释逻辑,把历史和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开创了一套全新的学术话语系统和治学方法,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范式转型与长足发展(15)。 早在1922年,陈独秀就提出,要“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6)。李大钊出版于1924年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史学理论著作,该书系统探讨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学术方法、基本价值等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此外,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现代社会学》以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成果,均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学术范例。在此期间,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也公开承认自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陈衡哲在1924年5月28日曾致信胡适,坦言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并明确表示:“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17)胡适的弟子顾颉刚公开宣称:“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时,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18)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与不可抗拒,以至于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其重要性并用它来从事学术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还强调学术创造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以期“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9)。创刊于1939年,以“学术中国化”和“理论现实化”为办刊宗旨的《理论与现实》在“创刊献辞”中宣称:“‘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20)著名学者潘梓年也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过去的学术运动只是从外国贩运了一些新的、进步的东西到中国来,还没有在中国的土壤中种植、结果,今后应该使学术中国化,亦即“精通现有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21)上述之“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和“唯物辩证法”均是指马克思主义,运用此方法的目的便在于“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要以中国问题(包括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和主体。与此同时,人们还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对于凸显中国学术之民族主体性的特殊意义。梁启超就告诫当时的年轻学者“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22),历史学家陈寅恪更是在应对中西文化碰撞和近代文化转型上坚守其“中国本位”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路径,他明确提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3)于此可见陈寅恪对于保持中国学术之民族主体性的重视程度。 关于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之重要性,学贯中西、博涉诸学的梁启超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现在往后,要把欧美思想,尽量的全部输入,要了解,要消化。”(24)梁启超主张中学、西学并重,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25)更重要的是融合互补、创造转化,“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6)1935年,何炳松、萨孟武、陶希圣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承认:“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27)这代表了当时学者(包括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立场的学者)对西学所持的一种理性态度。1995年,张岱年在为《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28)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参考西方的治学方法”,借助西方理论这一“他山之石”来解释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构建中国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拓展中国学术的创新空间,使现代中国学术展现出波浪千叠、涡流百曲的壮丽学术景观,确实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试图建立现代学术新范式的突出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郭沫若(1892-1978)可谓是“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先驱者。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年幼时期的私塾教育使他熟谙中国传统文化。负笈日本留学的经历则让他博通西方学术文化,这决定了郭沫若在学术之路上注重中、西、马的会通与融合。在撰写于1922年的《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中,郭沫若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唯物史观的认同:“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29)在《论中德文化书》(1923年)中,郭沫若主张要把中国古代传统中“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30),他同时强调:“我们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1)在撰写于1929年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相当系统地考察了中国上古社会的生产力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此书视野开阔,纵横捭阖,读来令人耳目一新。综上所述,不难窥见郭沫若对于“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朦胧的学术自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给他以方向、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中学不仅是他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深厚文化底蕴和重要学术资源;西学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话语则成为其学术研究之参照体系,出现在他的论证逻辑进程当中,或渗入他的相关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在青年郭沫若那里,“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已具雏形。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固,“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逐渐得到确立,一大批学者自觉地走向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学术道路,并坚持秉承“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进行学术探索和理论创新。一些学术大家,诸如范文澜、冯友兰、张岱年、冯契、任继愈、张世英等,以充分的批判意识和创新姿态,在中、西、马融通的治学路径上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学术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张岱年(1909-2004)是当代中国积极探索中、西、马融通的学术路径和自觉遵循“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代表性学者。70多年来,他在学术上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贯通古与今,融合中、西、马,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在哲学理论方面,张岱年青年时代就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兼综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力图创造一个“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32)即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是他践履“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张岱年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融通互补,综合创造,从而开创出一种新的文化(33)。经过方克立先生的深入阐发和大力弘扬,“综合创新论”已成为在当今中国得到广泛认同、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化观。提出“综合创新论”不仅是张岱年本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而且也是方克立先生开创“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的理论先导。 冯契(1915-1995)在中、西、马会通的学术之路上也是一位极具参照意义的典范性人物。作为“现代中国最有智慧、道德人格高尚、学术贡献十分突出的哲学家之一”(34),冯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先后撰写了两部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揭橥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及其近代演变,论证其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以及近代中西哲学合流之趋势。冯契还在融通中、西、马的基础上,以智慧学说的理论探索为主干,以“化理论为方法”(方法论)和“化理论为德性”(价值论)为其两翼,通过会通古今和比较中西以达到新的哲理境界,进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在“智慧学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冯契力图解决知识如何提升为智慧即“转识成智”的问题,旨在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克服科学与人生、知识与智慧的脱节,克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矛盾。总之,冯契运用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会通古今中西,博采众家之长,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最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智慧学说。可以说,冯契是当代中国践行“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而有大成的一个代表性学者。 以上简略的历史考察说明,“马魂、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之后的客观事实,也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交汇之文化境遇下中国学术发展和转型的必然选择。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最为重要的特征,这也为建立现代中国学术新范式提供了时代机遇和可能空间。而20世纪真正卓有成就的学者无不是在跳出孤立、狭隘的专业研究藩篱,步入中、西、马会通的治学通衢上才有所超越和创建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不同文化和思潮之间的相遇与融合。中国学术要在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实现创造转换、综合创新,这也是时代变迁的必然趋势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马魂、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立足中国传统、把握时代脉搏、融摄中西之学,建立现代学术新范式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情怀。 在当代中国,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各种“学术范式”不断翻新,不同文化思潮和学术范式都以不同的声音和方式陈述着自己的合理性,这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各种学术文化资源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也亟待确立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学术研究范式。托马斯·库恩曾坦言:“理论要作为一种范式被接受,它必须优于它的竞争对手。”(35)作为迄今为止处理中、西、马关系最为理性的解释框架,“马魂、中体、西用”说以其正确的政治导向、科学的研究态度、理性的思维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综合体现和高度凝练,理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学术范式。事实上,“马魂、中体、西用”学术范式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独特优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不断增强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自觉,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积极借鉴国外学术文化的有益成果,创建既有民族特色又能与时俱进的学术话语体系,才能真正突破传统,打开局面,凸显问题,彰显特色,将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进而在世界学术对话中获得自己应有的话语权。 注释: ①④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②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③⑤参见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⑥⑦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⑧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1)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 (12)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13)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4)方克立:《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应当承认,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大都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因此其学术研究也更多地是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带有较浓的政治宣传意味,而作为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唯物史观、矛盾论和阶级分析法。 (16)《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17)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2页。 (18)《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7页。 (19)《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20)《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21)潘梓年:《新阶段的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22)《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3页。 (2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84-285页。 (24)梁启超:《道术(哲学)史的做法》,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25)《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26)《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页。 (27)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28)薛德震主编:《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序。 (29)《郭沫若自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30)《郭沫若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 (31)《郭沫若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 (32)《张岱年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 (33)方克立先生曾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文化方针。 (34)《方克立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 (3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标签:中体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范式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