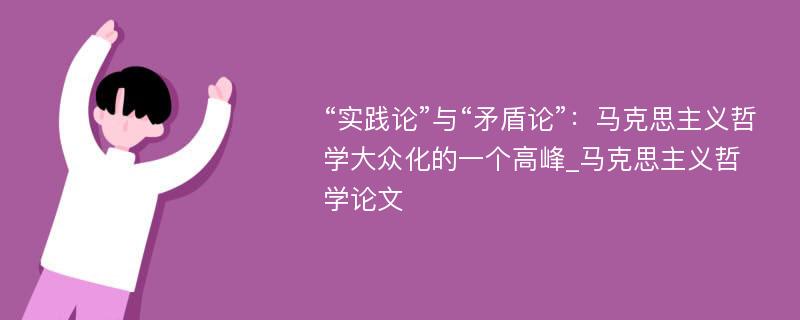
《实践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座高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矛盾论论文,一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高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0)04-0427-05
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论题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对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议题的呼应。其实,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是一时的议题,也不能简单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历时久远、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以及中国经验的相互融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过程,有着独立的品质和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史上的一座高峰,因而,也是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的珍贵标本。
一、“两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路径、新层次和新阶段
“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1938年4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1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时标明“毛泽东主讲”。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中文本正式发表前后,“两论”的俄文本、朝鲜文本、法文本等也相继发表。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两论”被编入第1卷。
由此可见,第一,“两论”实际上在最初文本中是联为一体的,“两论”在思想内容上是融会贯通的。《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针;《矛盾论》接着讲解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重点解说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理论,阐释了认识中国社会特殊国情、处理中国特殊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因此,“两论”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是一座高峰而不是两座“山头”。
第二,毛泽东创作“两论”,并非学问家阐释个人的思想,也非为博取名利而撰写学术论文,而是一方面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向广大革命青年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理论创新与理论普及的时代统一、实践统一。“两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和一个新的时期。
在“两论”面世之前,上世纪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中文版已经在中国出现,李达撰写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创作了《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两论”发表以后,它与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大众哲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议论。
“两论”确实与苏联教科书在理论语句上有相似之处,但不是苏联教科书的重复。因为貌似相似的理论语句里面,“两论”隐含着深刻而具有时代和现实背景的哲学思考。“两论”批判的是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阐释的是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特殊矛盾认识而获得的认识方法和思考理路。“两论”的文本背后有着中国式的经验和中国式的思维方法。
“两论”的理论观点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相同之处,但是,“两论”不同于《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用5个篇章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进行了面面俱到的、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在篇幅上比“两论”庞大得多。“两论”则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以短小精悍的篇幅集中阐释实践认识论和矛盾辩证法思想。对于二者之间区别的原因,许全兴先生有独到分析:“两论”之所以能够超过《社会学大纲》而精彩面世,“不在于李达同志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同志逊色,而在于李达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了中国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做出系统的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1]“两论”与《大众哲学》在行文用语以及理论内容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论”与《大众哲学》的服务对象是不一样的。
《大众哲学》服务于社会青年。艾思奇将当时的社会青年分成了四类:一是阔少,他们习惯的精神食粮应该是“西点”;二是以前“安心埋头开矿”,做着“皇宫里的金色梦”的学生,他们攻读的应该是大学教科书;三是在店铺内、在乡村里谋生的失学者,这些人应该是以《大众哲学》为精神食粮的,是当时的《大众哲学》的服务对象;四是广大吃草根树皮的灾民,他们可能连《大众哲学》这样的干饼都无法消受,或者是没有钱购买,或者是没有阅读中国方块字的能力。结果,《大众哲学》不仅成为第三类青年,即在店铺内与乡村里谋生的失学者的精神食粮,而且也得到广大在读大学生的厚爱和拥护,甚至连一些以“西点”为精神食粮的阔少也成为这块干饼的消费者。其实,《大众哲学》对第四类人群也是有用的。《大众哲学》对这类人群的服务方式不同于前述三类人。《大众哲学》的政治宗旨就是唤醒人民群众变革世界的觉悟,凝聚人民的力量,彻底改变使得人们只有靠吃草根树皮才能生存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大众哲学》的成功。
与《大众哲学》不同,“两论”是为已经投身革命队伍、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干部们写作的。如果说《大众哲学》主要从个体生活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精神,那么,“两论”则立足于中华民族集体利益、集体诉求的视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中国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矛盾的视角和方法。
“两论”的发表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两论”的面世,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与研究的重点由阐释唯物史观转向解说唯物辩证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阐释的是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进程,它主要回答的是“向何处去”的问题。经过三次大的理论论战,唯物史观确立了对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导地位。此后,“怎么办”的问题就成为理论的重点和实践的核心。“两论”阐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的领会和创新,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进入到新境界和新阶段。
综上所述,“两论”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重要的意义。它向人们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仅有着层次的多样性,而且有着阶段的递进性。从层次上看,有面向普通社会大众,也有面向党员干部的;有面向社会青年,也有面向在校大学生的层次。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论内容和不同理论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阐释不能只有一副面孔。从阶段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曾经围绕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和“怎么办”的问题,那么,在现在和平建设年代,则要指导人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如何处理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实现怎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问题。
二、“两论”示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两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在中国大众化的高峰,而且也是释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品格的难得的标本。
“两论”发表以后,它的创新价值和理论宗旨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另一个热点论题。观点是不一样的。按照某些学者理解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两论”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地位,更遑论学术创新,充其量只不过具有战略和策略的意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两论”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如法国学者让·雪斯诺在《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一文中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尤其是给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从列宁的某些指示出发并发展了它,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区别开来;他指出两者同社会实践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并指出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怎样构成一个辩证的循环,‘每一个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他又从列宁的另一些指示出发,拿当时中国的形势中若干事例为依据,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与次要的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复杂的概念分析得一清二楚,极其仔细。”[2]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种形态问题受到哲学界关注。笔者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其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笔者认为,“两论”最根本的理论价值是它示范了作为再生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解决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确立以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人民属性、批判精神和实践取向,所有这些特点都打上了欧洲的烙印,具有欧洲的气派。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民主要指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诞生于欧洲而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变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典型发展的欧洲社会。
“两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中国与英法德三国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全新的社会问题,面对着不同的社会力量。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凝聚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不仅使得人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取得了崭新的结论,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品格。这一点,在毛泽东创作的“两论”中有深刻的体现。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立场高于阶级取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中国没有一个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两论”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策的视野上,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现实的实践世界,其主体自然就不是个人,甚至不是单纯的阶级而是作为各种阶级大联合的团体或者社会。对此,冯友兰先生深有体会:“《实践论》所谓认识,和西方传统所谓认识,其意义不尽相同。西方传统哲学所谓认识,主要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是个人,《实践论》所谓认识,不是就个人说的,其主体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也可能是整个社会。”[3]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于阐释矛盾的特殊性,探讨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形式及其解决方法。“两论”要认识的对象是中国当时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面对的英法德三国资本主义确立以及所暴露出的危机与困境,中国革命当时面临的问题、要解决的任务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论定:“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4]“两论”强调的是对矛盾的特殊性的精确认识和深刻探讨。总体来看,“两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对象、路线、方针和策略的认识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上的表达。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的是中国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有进化的历史观。“两论”则将这种进化的历史观表达为立足于当代实践的中华民族自强乐观的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乐观主义精神打上了当代中国实践的烙印。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全面侵华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深重危机集中呈现的时期,当时人们对中华民族向何处去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见解。正是以“两论”的认识方法为指导,毛泽东独树一帜地指出:对日之战是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是持久战,既是民族革命,也是民主革命。“两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哲学基础。
第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式的实践取向。“两论”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践取向。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实践取向,有人称之为“实用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诞生伊始,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实践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践取向既承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又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精神的精髓。但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践取向不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以及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取向的简单克隆,而是以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为土壤,在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实用理性”两大精神元素作用下,一种新的发育和新的生成。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来自西方的各种哲学体系纷纷亮相。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面前选择以集体的力量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发展而奋勇前行的决心和意志。“两论”的产生与这种选择有必然联系,而不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在文本上的逻辑推演。“两论”的理论创新不是词句上的,也不是命题逻辑推演上的,而是以中国式的实践经验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丰富和推进,以当代的实践诉求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全新诠释和创新。
第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地在社会实践的舞台而不是哲学家的书斋。“两论”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现实路径。哲学的推进并不仅仅是专业哲学家们的任务,换言之,只有专业哲学工作者的努力,哲学向前迈进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对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有很深刻的理解:“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因此,在罗素看来:“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至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就这一方面而论,甚至于纯粹的行动家们有时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6]
毛泽东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工作者,他的“两论”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推进作用却得到海内外的公认。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给予“两论”以专章阐释的文本待遇。“两论”给当今的领导干部以启发:哲学不是远离现实实践的神间圣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时代回响。“真正的哲学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只要做有心人,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就能够拥有哲学发展上的发言权。
三、“两论”是高峰,不能被膜拜为顶峰
我们说,“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一座高峰,但是,“两论”并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道路,不能被膜拜为“顶峰”。
第一,“两论”篇幅较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释仅仅是专题而不是系统的体系。“两论”不仅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大精深的内容,而且对中国当代的实践精神的阐释也不是充分和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需要认真地反思、冷静地梳理和全面地阐释。有学者认为,“两论”在学术层面存有缺陷,这尽管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有一定的警醒价值。出现在战争年代的一部非常有针对性的著述,不能代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完整阐释。
第二,“两论”所立足的实践已经被刷新和超越。在“两论”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也顺利地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富强、中国人民的发展和幸福都还只是“在路上”,在实践中。新的实践必然会给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提供新的经验,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当前,西方政要、学术媒体纷纷热炒“中国模式”一词。它表达了关注着中国发展的人们对“中国式选择”、“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经验”的思考、重视、担忧和期待。中国的学界,有人试图澄清“中国模式”的时间界限和建设性的内涵;有人则担心使用这个词可能造成负面效果。其实,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而言,它提出了一个挑战,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说它是机会,“中国模式”呼唤人们对其意蕴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必然提供了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契机;说它是挑战,“中国模式”考验着人们在哲学思维上的创新能力。面对这样的机遇与挑战,毛泽东当年驾驭哲学理论的气度是值得揣摩和学习的。
第一,哲学创新要有坚定的实践取向。哲学理论本身是哲学家个人表述出来的,但是,它的创新源头在人们的现实实践中。“中国模式”是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的一种概括,书写“中国模式”的人们在实践中创新了一个又一个值得哲学专业工作者揣摩和反思的经验:实践对于真理的最终检验权;三个有利于;一国两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关键是,我们用怎样的哲学理解将这些经验上升为抽象的哲学叙说,这已经不是创作“两论”的毛泽东所能思考和阐释的内容了。但是,毛泽东创作“两论”的精神无疑对于我们有很深的启发:哲学工作者要有关注现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二,哲学创新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实践程序,一个公式化的存在,而是由实践中的问题、解答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实验和解决问题以后的经验总结等串联而成的。很多人之所以不同意使用“中国模式”一词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践的发展,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的实践”并没有完成,而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精神意蕴进行阐释,必须有毛泽东创作“两论”那样对问题的敏锐感觉,要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总之,“两论”是树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道路上的一座高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叙说自己品格的珍贵标本。我们对“两论”要深入学习和揣摩,但不能膜拜。
收稿日期:2010-04-06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矛盾论论文; 实践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