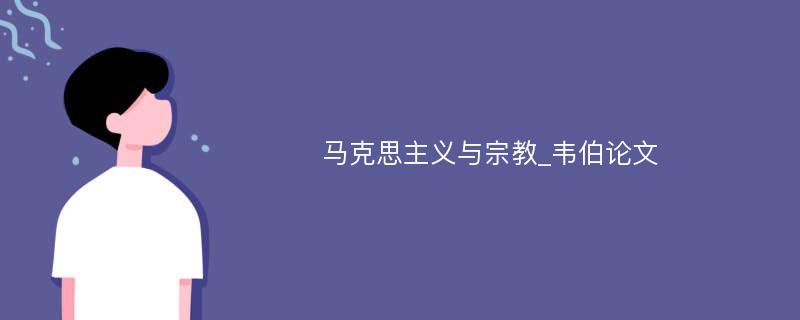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如何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关系怎样?或者应该怎样?在我尝试描绘出一种答案的框架之前,应该提出的显而易见的初步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是某种宗教?当然,大量的评论者断言马克思自己就是一位宗教思想家,并以宗教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当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模糊的,至少在概念上是很复杂的。这里指的是哪种宗教?至少我们想以“宗教”表明什么?同样,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中是否有某种可描述出来的本质或者核心?在一种非常模糊的意义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不存在连续性的话,那二者之间也有一种明显的关联。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毕竟是犹太人,他的犹太身份一定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同样的,马克思深受西欧文化遗产的熏陶,西欧的文化遗产几个世纪以来又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最显明的例子是,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可以被视为一种使基督教新教适应于时代精神的努力。而由于马克思被视为黑格尔的学生,这一思想的渊源就很清楚。 尽管如此,我想挑战的是,过分轻率地、在概念上并不缜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例如,卡尔·波普基于他所谓的“神谕哲学”(oracular philosophy)①,确认了马克思思想的宗教性质。别尔嘉耶夫则告诉我们: 如果共产主义反对所有宗教,这较少是因为共产主义所包含的社会体系,更多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它希望成为一种能适当地替代基督教的宗教,它声称对人类的宗教抱负作出回应,并赋予生活以意义。共产主义认为自身是普适性的,它希望控制所有存在而不仅仅是它的某些方面。② 此外,帕累托运用一种带有上述方法的典型的心理学还原主义,称社会主义为一种“世俗宗教”,一种较低阶级的非理性信仰。最后,熊彼特断然宣称: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首先,它为信徒提供了一套终极目标,这一目标包含生活的意义和用以判定事件和行为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提供了通达那些目标的导向,那些目标包括拯救的计划和对于人类或部分被选择的人类将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的指示。③ 这类判断通常受到政治或宗教的偏见的影响:热衷于基督教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试图取代真正宗教的伪宗教;而反基督教的人则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视为同类,宗教在此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建立在神话之上,是文明进步的敌人。这里顺便提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也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等同起来,他们希望把理想的信仰纳入马克思主义。④ 以上所引用的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偏向于印象性的描述。在罗伯特·塔克的《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中,有着对于熊彼特观点的更加完整的描述和概念上更加严格的描述。塔克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后奥古斯丁基督教之间至少在四个方面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首先是二者都对世界提供一种彻底的解释:“就像中世纪的基督教,马克思的体系承诺提供一种综合的、整全的关于现实的观点,一种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的所有重要知识的组织,一种通过它所有可能的关于重要的东西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或者可被回答的框架或者指引。”⑤其次,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都视经验为历史的,即一个有着开始、中期和结局的故事。再次,对于塔克而言,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基督教中的拯救和救赎,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重生或者人性的思想,都与之高度相似。最后,这两个体系都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理念,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或工作的复合体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是相似的。 塔克的观点几乎完全依赖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因而忽略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任何断裂,甚至发展的可能性,也忽略了马克思拒斥他那个时代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宗教的观点。⑥进言之,塔克的方法几乎等于将任何形式的总体主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这种主义的话)——甚至是任何“主义”——都标定为宗教。但是,只有通过使用更为严格的界定——它一定是规范性的并因而在本质上是有争议的,才能对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的关系给出一种满意的分析——如果有所谓的满意的分析的话。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不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宗教思想家,也不认为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宗教是恰当的。这是因为,基于概念上的混乱,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宗教,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宗教,都是不正当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是因为这种界定往往既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描述,也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清晰内涵。而对于宗教而言,则是因为这种界定通过使宗教屈从于当前流行的世俗化潮流,剥夺了宗教自身的本质上的超验性。当然,这个领域往往为界定问题所困扰,我在讨论中宽泛使用的“宗教”一词指称的是,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及宗教(其模式可能是某种主流的基督教)时所想到的。⑦如果宗教的概念被拓宽了,就像受涂尔干启发的大多数人类学文献一样,那么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就变得过于模糊而毫无用处。然而,应该注意到,即便对事情作最具功能主义色彩的解释,仍然有某些宗教的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⑧现在我们转向一个稍微容易处理一些的问题,即在此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有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宗教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词都可能是对群众运动的描述。这样的话,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几乎任何维持时间相当长的群众运动都会呈现出这些特征。比如,共产党和天主教会都有这样的特质:有着同类的等级组织,对于神圣的典籍有着同样的信仰,对于信条或教义有着同样的偏好,对于异端学说有着同样热切的关注。但是,尽管被视为一种观念和态度的结合体,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清楚地反对与宗教同化。首先,马克思主义被它的一些拥护者视为仅仅是关于社会的科学,一种描述社会如何运作的科学。这一观点在一战以前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的解释,考茨基在其关于伦理学的书的结尾处对此作出了非常到位的表述: 如果没有道德理想,没有对于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深恶痛绝,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其阶级斗争中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一理想并不能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得到任何帮助……当然,在社会主义中,研究者也是战士……因为,例如,在马克思那里,道德理想的作用不时突破科学研究的边界,但是,一有可能,马克思总是毫不犹豫地径直地将其从自己的作品中剔除……科学只是与关于必然性的知识相关。⑨ 根据这种观点(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很多解放神学家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分析的工具,并没有想回答宗教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很难把这种相当肤浅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宗教,如果可以的话,也很容易把涂尔干或者韦伯的分析视为宗教。⑩ 但是,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有更大的野心,而不仅仅是将其界定为一种社会理论。在此,马克思主义的确在变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总体的观点,一种世界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始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广泛地出现在苏联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条中——包含着关于什么东西存在(只能以这种或者另一种形式存在的物质)的形而上学教条。宗教话语的客体并不存在,相信这些客体存在根本就是错误的。在辩证唯物主义中提出的判断不是功能性的,而是本体论的。它们植根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或者法国实证主义传统之中,这些传统把宗教叙述视为错误的或者毫无意义的。这种简单的、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显然与宗教信仰不相容,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恰恰是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描述为宗教的人最铭记于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两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有别于马克思本人的路径。马克思更多地与尼采或者弗洛伊德的观点一致,他将宗教视为一种其意义必须通过某种“系谱”加以解码的症候。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异化和解放的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形式也越来越可信了。(11)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包含这样的观点,即历史有着被冷酷无情地制定出来的目的,历史也有着一个与当前的冲突形成鲜明对比的关于未来和谐的有力构想。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个末世论的维度,这个维度有着强烈的宗教起源。然而,关于世界的观念可以有宗教的起源但其自身却不必是宗教。尽管几乎可以把费尔巴哈算作神学家,但把马克思也视为神学家的话,显然忽视了他对于整个费尔巴哈的方法所作的犀利的批判。说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的立场纯粹是当地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其理论之本质,也是忽略了这一批判。当然,马克思对于宗教异化的解释产生于他那个时代的极端的路德教,恩格斯的观点带有他在伍伯塔尔(Wuppertal)的童年时代经历的严酷的虔诚主义生活的印记,而列宁对于宗教的尖刻的评论整个在实际上屈从于当时俄罗斯东正教之沙皇独裁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都是事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评超越了纯粹的历史偶然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基督教那里承继了一些主题,但在这里和在其他大多数情形中一样,这种继承暗含着被继承者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和在某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但它一直是世俗化的,我们应该按照它自己的范畴来对待它,而不是将它重释为宗教的范畴。 如果马克思主义可以合理地与宗教对立起来,那么这种解释有多大的有效性呢?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思想作出一般性评估之前,通过将其与其他两位伟大的社会学奠基者——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进行比较,进而把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殊之处凸显出来,是有助益的。 马克思与涂尔干的方法有着几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并不奇怪,假定马克思和涂尔干都试图将德国哲学传统与法国的政治以及经典政治经济学综合起来——涂尔干更受其本土的法国实证主义的影响,而马克思则更受其黑格尔背景的影响。涂尔干把历史视为一种渐进式的进化,并且对社会主义颇有同情心。与马克思一样,他敬仰圣西门,寻求一种关于可以应对由资本主义的冲击所带来的问题的社会的解释。涂尔干也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尽管是在一种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并且在应用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公式时显示出比马克思有着更浓厚的决定论色彩。 然而,相同的社会存在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眼中是非常不同的。尽管与马克思一样,涂尔干将宗教的根源锚定于社会结构,但他经常把宗教视为社会整合的资源。马克思有时(确实也经常)也把宗教视为这样的一种资源,但他更兴趣于追溯社会冲突的根源。因此,涂尔干的态度可能看起来更加平淡无味,既没有分析剥削性的经济关系,也没有解释阶级与群体的冲突,而这些在马克思那里都可以找到,因为马克思对于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更感兴趣,而不是探讨作为既定的社会结构。涂尔干没有预见到暴力革命,他认为,现代社会最终能够成功地应对混乱和分裂的问题。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宗教的形式和社会的形式是同一的,而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现实的一种变型,确切地说,是一种畸变。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宗教是一种在不久的将来应被超越的异化的力量,而不是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整合的不变的源头。对于宗教,涂尔干比马克思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把涂尔干视为还原主义者很可能是误导性的。在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受推崇的评论中,他说: 表明宗教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宗教自身限定于用另一种语言来说的社会的物质形式以及它的直接的绝对必要性。我们显然认为社会生活依赖于它的物质基础,并且带有后者的烙印,这是真的,就像个人的精神生活依赖于他的神经系统以及事实上他的整个机体。但是,集体意识不只是某种由它的形态学基础所带来的纯粹的副现象,正如个人的意识不只是神经系统的简单的展现。为了使前者能够出现,要求有一种对于特定意识的自成一体地综合。现在这种综合有一种将整个情感、观念和幻象世界分解开的效果,这些情感、观念和幻象一旦产生,就遵循着它们自身的规律。它们(这些情感、观念和幻象。——译者注)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统一起来,又分裂开,产生繁殖,尽管这些结合并非是作为其基础的现实条件所要求的或者认为是必须的。由此产生的生活甚至有着极大的独立性,它有时沉溺于自我表现,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只是为了自我确证的纯粹的愉悦。我们已经表明,宗教活动和神话思想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形。(12) 涂尔干对于其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大多强调它是一种形式相当粗陋的经济决定论。(13)作为对20世纪的政治事件的回应,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放弃“经济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可能是符合此马克思主义版本的最好的例子,他给予包括宗教在内的上层建筑因素以更多的重视。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经常以新黑格尔主义的形式出现,它突出主体而非结构,从而远离了涂尔干。但另一方面,某些晚近的新结构主义的(同时主要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确与涂尔干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4),比如,普兰查斯把国家视为统一的社会组织的象征性表达。这并不奇怪,因为涂尔干显然对结构主义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大受欢迎,这是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产物,其时的西方社会大体上似乎有着良好的秩序和较多的共识。吊诡的是,涂尔干的方法既能很好地适用于原始社会,也能很好地适用于非常现代的社会,比如在美国,“在信仰中信仰”这种民间宗教的确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合(15),同样的分析有时也可以应用于既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本身。相比之下,在被宗教信仰撕裂以及存在着明显的群体冲突——对于这些情形,马克思主义至少能够提供某种解释,但涂尔干的原则却束手无策——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才最有生命力。 韦伯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另一位更直接的对手,因为一般认为韦伯的作品或多或少直接地针对马克思,并且他通过强调和仔细地研究宗教和一般观念的影响,否定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甚至以一种关于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取而代之。譬如,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韦伯致力于提供一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起源的“反马克思式”(16)的解释。当然,我们应该记住,当韦伯把他的宗教社会学描述为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验性驳斥”时(17),他(像涂尔干一样)所指的历史唯物主义很可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晚年恩格斯的影响下,这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宗教仅仅视为对物质环境的消极反映或者是其影响。(18)如果说马克思在面对这些门徒时曾经愤怒地宣称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那么,任何说马克思与韦伯直接对立的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不一致的地方。与韦伯相比,马克思给宗教提供的细节性分析要少得多。下面将讨论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的评论通常是附带地提出来的,比如,在他关于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在于流动的社会弃儿和奴隶的明确表述中(20),这一观点与韦伯认为早期基督徒是城市工匠和熟练工人的判断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相容的)。当然,韦伯对于各种社会阶层的不同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注,而马克思则倾向于把宗教视为一种较低阶级的现象。更宽泛地说,马克思对于历史进步有着更为自信的观点。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逻辑,一种关于历史发展——其发展在消除了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到顶点,在此顶点,马克思得以更清楚地判定各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这是由于它们代表的是部分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即将占据统治地位、作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韦伯则由于对事实和价值作出新康德主义的原则性的区分,不认为历史有总体性的意义,把自己限定于处理历史行动者之间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观点。 这一差异性的一个结果就是,韦伯比马克思给予宗教更大的自主性。韦伯断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宗教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社会阶层的一种简单的‘功能’,宗教的特质是由社会阶层带来的,或者说宗教代表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或者宗教是对社会阶层的物质或者理想的利益状况的一种反映。”(21)相反,他声称:“不管在特定的情形下宗教伦理受到的社会影响(经济的和政治的决定性的影响)是多么直接和深刻,宗教烙上的主要是源于宗教方面的印记,并且,首先是烙上了它所传报的(来自天使)和许诺的内容的印记。”(22)特别是,通过强调边缘群体对于宗教的需要和对于拯救的意义的寻求,以及突出宗教专业人士在有意识地发展宗教观念中的作用,韦伯试图表明它们远非纯粹表达阶级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韦伯远非反对马克思,而是认同马克思。因此,熊彼特会说,就宗教社会学而言,“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事实和论争,在整体上完美地契合于马克思的体系”(23)。韦伯乐于将不同的宗教观念锚定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就像他把现世的世俗宗教与特权阶级相联系,把救赎宗教(salvation religion)与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联系起来一样。(24)因此,他研究中国与印度的宗教中特别强调财产和生产关系。由于韦伯比马克思更为重视宗教,对于宗教的细节性内容、内在的差异性、各种宗教专家的社会学以及沟通宗教教义和经济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和心理学的变量,他更为兴趣盎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韦伯有时非常接近于把宗教描述为一种异化——这使人想起年轻的马克思;而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的概念则是从席勒那里借用过来的,后者曾经对马克思早期的作品产生过强烈的影响。这种与马克思的亲和性是晚年韦伯的一个更突出的特质:韦伯著作的编者发现,“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一个趋向于马克思的明确的关注点的转移”(25)。但即便在他早期关于新教伦理的作品中——有些人将其作品视为对马克思的有意驳斥,韦伯的立场还是有矛盾的。 当然,(他写道)我的目的不是用一种同样片面的唯心论的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因果性解释去取代一种片面的物质主义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是可能的,但对于历史的真相而言,每一种解释——如果它不是作为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而是作为其结论的话——实现的东西同样是微不足道的。(26) 沟通韦伯和马克思的桥梁是“选择性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这个概念。因此,如卡尔·洛维特所说:“对于韦伯而言,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就是出现一种导向于理性生活行为的一般趋势,这种趋势只是由社会中的资产阶级阶层带来的,这个阶层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教伦理之间搭建起了一种选择性的亲和性。”(27)因为韦伯想表明作为纯粹宗教出现的那些观念的要素,是依据其与其他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利益的亲和性而被筛除或者被选择。韦伯对这一过程的解释非常接近于马克思,马克思也会同意韦伯这样的表述:“在历史的面前观念是不足信的,除非它们指向一种能够促进各种利益的行为的方向。”(28)重要区别在于韦伯赋予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同样的重要性,也在于(韦伯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些精神利益常常根源于特定的宗教观念,而这些宗教观念与社会的经济组织只有极为松散的关联。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涂尔干及韦伯的方法的上述比较,再次表明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他学说隔离开来有多么困难。尽管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留给宗教的空间极为狭窄,最近已有一些努力试图使这一空间变得更有包容性。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最为精巧的捍卫者,最近提出了这一学说的一种“受限的”形式: (这种形式)并不认为精神存在的主要特征是从物质上或者经济上来解释的。它只是要求精神现象既不打断物质的和经济的顺序,也不对该顺序产生如此大的贡献以至于该顺序被认为缺乏任何历史唯物主义都归之于它的那种自主性。(29) 正如很多神学家开始谈及上帝的死亡以及放弃在人世和天堂之间做出区分,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经失去了对于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及严格的唯物主义规划的信心。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至少把下述两个方面结合了起来:其一是宗教社会学——把宗教视为一种依赖于包括阶级冲突在内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因变量;其二是把宗教视为一种“异化”——它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来临而消失。第一个方面是描述性的,第二个方面则是规范性的,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中它们经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两个方面。 在更具描述性的一面,宗教是否真的是一种因变量?暂时撇开定义问题,我们先简略地看看马克思主义在加尔文主义、早期循道宗(Methodism)和千禧年主义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s)这三个领域的解释。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解释在很多方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经典名句。然而,从前面对马克思与韦伯的讨论来看,很难判断他们之间是否有任何基本分歧。更确切地说,如果说存在基本分歧的话,这一分歧似乎取决于较之对历史的因果性不做简单描述的东西。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循道宗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将宗教视为源于社会剥夺——获得相当大支持的例证:教派是既更为虔诚又属于较低阶级的现象的命题有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里,有两个带有典型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观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E.P.汤普森把循道宗解释为对主动性革命行动之失败的补偿,并声称在1790年至1830年之间,“在‘政治的’和世俗的理想遭遇失败的节点就出现了宗教的复兴”。(30)然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怀旧的命题已遭到了来自经验层面的强有力挑战。它遭到了霍布斯邦(Hobsbawm)的直接反驳(31),他认为政治激进主义和宗教的复兴是同时产生的。反之,基尔南(Kiernan)认为循道宗的复兴的主要效果在于通过使其成为既定秩序的一部分来解除叛军的武装。上层阶级,在面对异常的宗教冲动时,“只要一种外部的打击使得由内部的不满所带来的危险得到强调,就会由敌对态度转变为接受的态度。如,雅各宾主义在法国废除了基督教历,却促进英国维多利亚安息日的建立”(32)。在基尔南看来,大约在1800年,基督教新教传统的复兴开始被当局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认为是对于秩序和稳定的一种可能的支持。因此,至少在这种情形中,存在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统治阶级的灌输,宗教成为人民的鸦片并进而成为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支持。因为只要社会被认为存在阶级划分并且宗教被认为是社会稳定的来源,那必然会得出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结论。然而,千禧年主义运动并不能够轻易地融入这一方案。受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启发,像霍布斯邦和沃斯利(Worsley)的分析(33),追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于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经典解释,倾向于把这些运动视为政治革命运动的原型或者先驱。但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千禧年主义运动似乎劝阻其追随者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不是引导他们去进行政治活动。此外,霍布斯邦和沃斯利的方法简单地假定宗教是一种掩盖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并且和恩格斯一样,低估了教义和仪式可能具有的重要性。革命乐观主义使他们以为,这些运动将在使他们潜藏的(政治的)理性得以发挥出来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迅速消失。 所有这些表明:至少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强调宗教所获得的社会或经济利益的强有力支持,为我们理解宗教和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马克思主义的抱负并不止于做出纯粹的描述。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可能会同意把宗教视为高因变量这一朴实的马克思主义描述,但它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对宗教的社会价值、更不用说宗教的真理性问题做出判断。比如,哈勒维(Halevy)关于循道宗是革命的解毒剂的命题,可能会被视为是有利于循道宗的——哈勒维的确是这么看的;又比如,在对千禧年主义运动的研究中,科恩对于这些运动的判断几乎是站在霍布斯邦和沃斯利的对立面,尽管科恩的社会学方法与后者相似。显然,如果宗教总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话,它就可能成为相反的判断。但显然不是这样:宗教也可以成为一种针对统治和剥削的抗议,成为“无情世界的感情”,等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它并不意味着可能有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就像根据其社会功能来判断可能会有好的政治和坏的政治、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一样。因为马克思主义服膺于这样的观点,即所有的宗教——不像所有的政治和所有的文学——都是一种异化,都是社会畸形体的一种征兆。这一观点进而导入某种世俗化的观点,即一种非宗教的因而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的可能性或者必然性。 这一世俗化的概念已经激起了宗教社会学家之间广泛的争论。马克思显然高度认同其中一种较为激进的观点。马克思深受19世纪中期的社会舆论的影响,该舆论认为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冲击下宗教正在消亡,并且理当如此。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已经在19世纪末遭到了攻击,当时的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剧变,正如涂尔干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34)一说到涂尔干,人们就明白世俗化这个概念是充满争议的,因为这个概念的可行性主要依赖于其采用的宽泛的方法和对于宗教所运用的定义。但即便是建立在一个狭义的定义———如宗教包含着信奉超验的存在以及宗教实践包含着参与基督教会组织——之上,实证的证据也绝对不会是片面的:它必须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逐渐流行起来的宗教热——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宗教的复兴以及在苏联发生的宗教崇拜的异乎寻常的反弹——考虑进来。这种实证方法也依赖于宗教之“黄金时代”(通常是指中世纪)的假设。然而,如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在他的经典的书中所指出的,“早就存在于工业化开始之前的那些对宗教冷漠的、异教的和不可知论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公正的对待……有组织的宗教对于人们的控制从来没有这么彻底,以至于没有为与其竞争的信仰体系留下任何空间”(35)。甚至连原始的人类尤其具有宗教信仰这一观点也被当代人类学家所质疑。(36) 从更基本的层面看,宗教的定义展现出其形而上学的选择。比如英格尔(Yinger)(为宗教)所下的定义,使世俗化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而卢克曼(Luckmann)和伯格(Berger)更为精微的方法——处于涂尔干的传统之中——则表明一种新的宗教形式的产生,而不是宗教的彻底消亡。(37)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说世俗化是“与一种反宗教的意识形态工具相比更不科学的概念”(38),这一说法尽管过于极端,但毫无疑问,它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俗化命题的特定版本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宗教的衰退之间有着关联性。因为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创造,正是在工人阶级那里,反宗教(irreligion)才会越来越集中。即便我们能够将多面相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现象作为过去的一个阶段而不予考虑,但这种观点仍然会遭遇两个经验上的困难。第一,大多数西欧工人阶级的反宗教更多的是受资产阶级反教权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的实证主义的影响。第二,工人阶级一开始并没有全部服膺于基督教,因为至少在19世纪的英国,基督教更主要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事务。更一般地说,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出现,正如在马克思时代的境况一样,是一个遥远的期望。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文化的整合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而不是它被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认为是反宗教的)所取代。 从更根本上讲,可能有人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境况的探讨并不够彻底。因为马克思对于生产关系(进而阶级)的中心地位的描绘,可能会引起质疑。种族和(更重要的)性别已逐渐被很多人认为是更为基本的东西。基于这种观点,黑人神学或者女性主义神学的出现将会使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确定无疑地离题了。“所谓彻底”,马克思写道:“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对于帕斯卡(Pascal)来说,宗教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它非常理解人类”。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理解如何呢?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称为基督教的异端,而所谓异端就是以事物的其他方面为代价而选择或者强调它的某一个方面。马克思的学说被视为异端可能是因为它将从19世纪中叶西欧社会所归纳之宗教功能适用于所有社会,以及将宗教的意义化约为对于经济冲突的反映。作为莱茵兰地区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在他的世界观中保留有很强的启蒙理性主义的因素。这使他及其后继者低估了非理性的话语模式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性。但宗教的模式,如同艺术的模式一样,能够激活更理性模式所无法触及的那些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不是针对其无神论,而是针对其对人性的把握不够充分,但这不是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方案忽略了一些被视19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为根深蒂固的个人私利的陈词滥调。相反,批评指向的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潜能的观念太过狭隘,排他性太强以及太缺乏远见。我们可以看看罗杰·伽罗蒂(Roger Garaudy) 在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与他们的过去被隔绝的时候,在如此多的奴隶和士兵活着和死去而其生死又是毫无意义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去谈一种关于人性的普适的方案和一种必须归之于人性之历史的意义呢?如果我不确信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包括在这个新的现实之中并且被保留下来,使人们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复活,我又如何能够使自己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未来的人们将为新的世界而牺牲他们的生命呢?也许我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该观念为未来允诺了一种胜利,而这种胜利很可能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通过使群众的消亡来实现的;也许一些事情是如此发生的,以至于我的全部行动都建立在对死者复生的信仰之上。(39)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着活着的人、胜利者和那些最终获得成功的人讲的,而基督教首先是对着那些失败者、有残疾的人甚至是亡者讲的。最后,假定在共产主义社会宗教会消失是过于轻率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共产主义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明朗的观点,与基督教传统关于在上帝之城中宗教的象征和形象都会消失的观点有着很突出的相似性。因此,基督教在本性上是或者应该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当我们在黑暗中透过玻璃去看时,象征和形象的中介是必须的,尽管(我们)经常易于陷入拟人化的偶像崇拜之中。一旦别人如我们理解我们自己那样理解我们的话,他们的中介作用就会消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反对意见是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将如何运作的解释过于模糊。尽管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角度来看,这种谴责是相当公正的,但是从一种宗教的观点来看,情况则恰好相反。霍克海默让我们注意到了马克思拒斥描述共产主义与犹太人命名上帝之间的相似性。(40)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如犹太人那样有所节制。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主张是这样的:关于意义的基本的问题(“为什么”的问题)能够通过生产关系的重新组织得到解决。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其未来必定超越任何可以马克思主义术语来描述的社会。正如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 所言: 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构造的精神或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负有道德责任的而不是无关道德的权宜之计,是富有精神意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因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构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形象似乎与一个宗教的社会相类似。(41)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过去都使自身制度化,并且保留着对过去的怀旧之情,尽管其过去有着显然的失败。不过,它们的生命力在于作为反抗运动的那种力量之中。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存在的理由,如上所述,在于它在世俗领域的成功。失败则易于导致最终的意志消沉,而对于大多数宗教而言,失败更多的是充当一种有益的(字面上的) 警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性和现实终究是一致的。 [本文译自David McLellan,Marxism and Religion:A Descrip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hristianity,The Macmilian Press,1987。经作者授权发表。] 注释: ①K.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4[th] edn London,1962,Vol.2,p.224. ②N.Berdiaev,Les sources et le sens du communism russe,Paris,1951,p.316. ③J.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4[th] edn,London,1954,p.5. ④See,for example,L.Goldmann,The Hidden God,London,1964,p.90. ⑤R.Tucker,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Cambridge,1961,p.22. ⑥See,K.Marx和F.Engels,"Circular against Kriege",Collected Works(London,1975ff)Vol.6,pp.46ff. ⑦见如霍顿(R.Horton)清晰的讨论,“一种宗教的定义以及它的运用”。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90,1960. ⑧See further,p.170. ⑨K.Kautsky,Ethik a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06,p.141. ⑩近期最为彻底地为马克思进行划界的尝试,可见P.Frostin,Materialismus,Ideologie,Religion,Munich,1978. (11)参见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1978,Vol.1中极为精彩的第一章。 (12)E.Durkheim,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London,1915,pp.423f. (13)See,A.Cuvillier,"Marx et Durkheim",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1948,pp.84ff. (14)See,S.Strawbridge,"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and Durkheim's Account of Religion:An Examination of Some Striking Parallels",Sociological Review,Vol.30,1982,pp.125ff. (15)See,R.Bellah,Beyond Belief,New York,1970. (16)T.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1949,p.505. (17)引自R.Aron,The Main Current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London,1968,Vol.2,p.262. (18)See,K.Lowith,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1980,p.100. (19)K.Marx,F.Engels,Werke,Berlin,1957ff.,Vol.35,p.388. (20)K.Marx,The German Ideology,Moscow,1968,pp.143,188f. (21)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1948,pp.269f. (22)同上,见韦伯对印度宗教的讨论以及这一讨论所呈现出来的与马克思的方案的差异。T.Ling,Karl and Religion,London,1980,ch.6. (23)J.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London,1954,p.11. (24)参见M.Weber,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1968,ch.6. (25)From Max Weber,etc.,p.63. (26)M.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ed.T.Parsons,New York,1958,p.183. (27)K.Lowith,Mar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1980,p.102. (28)From Max Weber,etc.,p.63. (29)G.Cohen,"Restrictive and Inclus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Marx en Perspective,ed.B.Chavance,Paris,1985,p.59. (30)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ndsworth,1968,p.428. (31)参见E.Hobsbawm,"Methodism and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History Today,Vol.8,1952,pp.115ff. (32)V.Kiernan,"Evangel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Past and Present,Vol.1,Feb.1952,p.44. (33)参见E.Hobsbawm,Primitive Rebels,Manchester,1959; P.Worsley,The Trumpet Shall Sound,London,1957. (34)R.Nisbet,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1986,pp.221ff. (35)K.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London,1971,p.173. (36)参见M.Douglas,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London,1973,ch.1. (37)见戈特瓦尔德( N.Gottwald) 的一段简短而睿智的讨论:TheTribes of Jahweh,Maryknoll,1979,p 10. (38)D.Martin,"Towards Eliminating 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Penguin Survey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5,ed.J.Gould,Harmondsworth,1965,p.169.欧洲思想史上关于世俗化的大多讨论的肤浅性,参见H.Blumenberg,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Cambridge,Mass.,1983. (39)R.Garaudy,"Glaube und Revolution",in Marxisten und die SacheJesu,ed.I.Fetscher and M.Machovec,Mainz,1974,p.43.见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探讨:C.Lenhardt,"Anamnesic Solidarity:TheProletariat and its Manes," Telos,Vol.25,1975. (40)See,M.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London,1973,pp.56,262. (41)R.eilbroner,Marxism:For and Against,London,1980,p.167.标签:韦伯论文; 涂尔干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