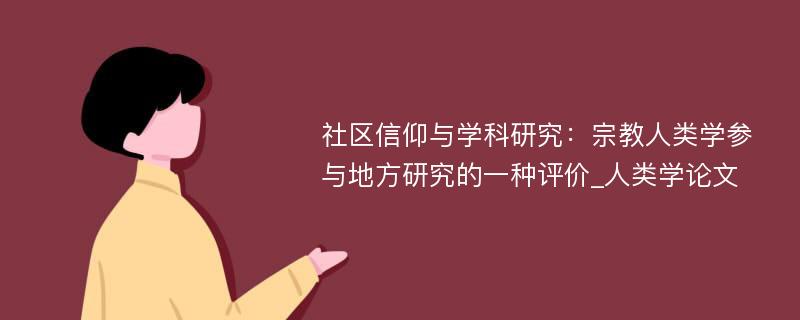
社区信仰与学科进路——宗教人类学介入本土研究的评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人类学论文,本土论文,学科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的分解与综合是现代知识创新的平台,也是诞生新观念的温床。自20世纪40年代以降,西方宗教学研究先贤与人类学研究泰斗,各自寻求学术增长的新空间,形成取向不一、风格各异的宗教人类学学派。①而近30年来,该学科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由“厚古”向“厚今”的转变。② 中国现代学术建设造端于民国初年,迄今为止,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皆有不同的特色。民国以来,大量西方宗教人类学的汉译成果纷纷涌现,以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本土论著也渐次问世;时至20世纪上半叶,宗教还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未能形成专门的宗教人类学研究,更没有自觉从事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建设。③自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学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不乏涉及宗教信仰的层面。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新的西学东渐浪潮,宗教人类学引入国内,国内学人与域外学者竞相译介、推广,至今已推出数量不菲的宗教人类学论著。其中,社区宗教信仰的研究尤为引人关注。褒扬既有的成就,检讨存在的问题,讨论提升的空间,是学科发展必须具备的自觉。本文瞄准大陆地区的社区宗教信仰(主要侧重基督宗教信仰)研究现状,寻求进一步拓展社区信仰研究的空间,匡正学科意识的偏差,提升学科介入社区信仰研究的力度,所论所言,是璞是玉,尚祈学人体察。 一、社区个案研究的前沿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较为关注的领域。其中,人类学更是诸学科中的后起之秀,显示出该学科深厚的创造潜力。当然,真正拥有人类学学科意识,使用其方法,遵循其规范,来从事社区组织、社区制度、社区信仰的专门性研究,恐怕是从21世纪初年开始的。较早者如吕卓红关于川西茶馆的研究,④开创了传统公共领域研究的新路;马威针对中国北方农牧文化交汇处蒙古族继承制向汉人轮伙头制度转换的研究,别有意味;⑤周泓在杨柳青地区关于绅商导引市镇运作的细密讨论,提出了宗族制度更多地表现为血缘宗统归属关系及其认知体系和宗祧伦理体系的结论;⑥石峰针对关中社会“宗族缺失”环境下各类组织的生成和转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组织参与的逻辑转换”现象。⑦人类学田野实践中涌现出的这些论作,显然是近年来社区研究的力作。在当代中国的社区研究中,还有一类田野之作属于宗教人类学的范畴,其鲜活、立体的原创特色,更应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就是宗教人类学的社区信仰研究领域。 宗教人类学兴起的时间不算很短,但瞄准中国大陆社区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宗教信仰的研究历史却并不长。最初常见的著述是在讨论地区性宗教历史发展问题时,间或使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方法,聊补单纯史学或宗教学研究的不足,此一时期的成果抱有突破学科藩篱的诉求,蕴含着鲜活异样的气息。⑧近年来,社区人群的不同信仰诉求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不同社会中的宗教结构不同,同一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宗教价值取向会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宗教内的不同层次的群体也有不同的信仰诉求,由此形成国家、社会(群体)、个人间在宗教信仰与实践诸方面的复杂互动。⑨介入社区信仰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多有海外宗教人类学训练的学术背景,或受到海外相关研究的启发,推进学科发展的意识相当明显;代表性的专著、论文由境内期刊、出版机构陆续推出,亦有部分论作在境外出版机构和权威期刊面世,然后辗转影响内地学人,呈现梯次冲击的学科推进机制。 既然是社区信仰研究,科学而合理地选择社区,是宗教人类学介入本土研究的前提。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区、山区社区、城市社区,几乎都已进入相关学者的视野。学者选取社区的眼光完全依凭宗教人类学的规范要求,注重其历史承续和当下宗教生态的完整性,每项研究力图承载着宗教人类学的关怀,强烈的学科意识,躬身田野调研的努力,使得部分成果的创造性贡献日见其深远。这些代表性成果中,以学术专著为主。此类论著尤其擅长扎实翔实的田野文献调研,既注重社区信仰的当下生态,又兼顾社区信仰历史层面的勾稽连缀,学术视野与田野意识俱可称道。 近几年来,学人较为关注的社区基督教信仰研究成果,主要侧重在对当代社区的研究,它们多数是在境外著名的出版机构诞生的,并最先受到海外学界的褒奖与推崇。这些成果或以中文成书,或以英文面世,其学科反响正在逐步扩大。学术原创性的成色多寡,言人人殊,见仁见智。就笔者所见而言,下列三部论著不可忽视,依照出版时间先后,分别是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0-2005)》(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香港大学曹南来助理教授《构建中国的耶路撒冷:当代温州的基督徒,权力和地方》(斯坦福大学,2010年)⑩、中国人民大学黄剑波副教授《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2年)。上述论著基于人类学特有的视野,分别瞄准了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磨盘山天主教社区、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温州基督教社区以及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吴庄基督教社区。这些社区的文化信仰被纳入锐意求新学人的视野,正是西方宗教人类学开始介入中国本土研究的重要个案,西方本已兴盛的学科在中国开始呈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态势。 上述学人的宗教人类学素养或有差异,但选取研究对象的眼光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康志杰教授慧眼独具,发现了鄂西北谷城县紫金镇磨盘山区内部深藏的天主教社区,自清代中叶迄今,磨盘山深处的各个村落始终盛行信奉天主教传统,二百多年来,世代耕耘生息,以耶稣天主为精神寄托,代代承续,自成一独立不羁的信仰系统。康教授由史切入,追溯信仰源流,梳理脉络起伏;继而关注天主教社区之当代生态,自信徒人口、习俗与礼仪、伦理与治生,以至于信教家族、虔诚信徒等,均有粗描细刻、着墨不等的研究。这是一项关于历代移民自然形成的信教社区的实证研究,兼具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科特色,并参以社会学的调研方法,洵属当今山区信教社区的典型研究。 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人类学的代表性成果,则体现在曹南来关于温州工商界基督教社区的扎实研究,以及黄剑波关于甘肃天水吴庄基督教社区的鲜活论著。所谓“完整意义”这一认定,是基于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学科意识。在选取研究对象和治学理念方面,曹氏声称,其学科视野与通常的社会学研究者介入社区研究迥然不同:“在研究中国宗教复兴的过程中,社会学者往往聚焦于宗教组织与宗教管理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宗教团体与国家和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互动。本文提出的对宗教实践中主体性与地方性的关注,将是与之互补的研究进路。尤其是当一种宗教已经成为大众参与的流行性社会象征空间(而非地方权力结构中一种边缘的存在)时,研究者更应对人们是如何在宗教场所和宗教组织形式之外,体验与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所谓非典型宗教活动情况给予充分的关注……这些关注主要集中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是如何以各自和集体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建构和理解自己的宗教体验与意义的,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宗教资源去获得公共空间、社会权力和资本的。”(11)黄剑波也宣称自己的研究,希望“能从宗教人类学的进路对跨地域/世界宗教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并在对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上贡献一些人类学的见解。”(12)基于此,曹南来注重截取经济发达地区的温州基督教社区中诸类信徒参与政治经济的心灵过程、体验宗教实践的实时画卷,以扎实翔实的田野文献深描这种画卷的宗教色泽,和盘托出信徒们将信仰渗入生命的复杂历程。而黄剑波则追寻那种“理想社区”——“第一,它是一个汉人社区,并且保持较为完整的大姓宗族;第二,它有比较明显的基督教活动及一定的信仰群体;第三,最好还具有多元化的文化和信仰资源。”(13)在这样的视野之下,黄氏根据长时间的田野工作,获取了丰富的民族志文献,给读者展示出吴庄信徒在生活、交往、伦理、习俗等各个层面的信仰介入。依凭这种宗教人类学的学科眼光,选取温州也好、瞄准吴庄也罢,充分展示出研究者敏锐的学科意识。 这些颇具前沿的论著除了拥有匠心独运的学科眼光之外,还以自己的实证研究个案,为宗教人类学如何介入当下中国的社区信仰研究,贡献出一种渐趋成熟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充分体现出人类学学科跻身宗教社区研究的巨大潜力。其内在要素,诸如宗教社区的选择标准、介入社区的超然中性立场、田野工作的规范性操作,民族志研撰的规程、宗教信仰文化内在质素的界定、宗教仪式丰富意义的挖掘,等等。无论是磨盘山社区、温州社区还是吴庄社区,其宗教面相与人类生活的交集,均被清晰详实地展示出来。虽然有的研究者不欲创建一种所谓的“研究模式”,但是,这些位居前沿的论著,无不昭示着宗教人类学已开始形成中国风格的研究范式,尽管这种范式或许被将来更有价值的论著所修饰微调,但它们依然属于这一学科重要的奠基之作,甚至或许称得上是“第一线田野作品”。(14) 二、学科介入的落差 社区宗教信仰是一个虚实结合的问题,“虚”指的是这一问题的精神层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完全是个体或群体的特殊心理活动;“实”指的是特定信仰的个体或社群基于相同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社交、生活、聚会等,既可测量,又可管理。同时,社区宗教信仰又是一个时空兼备的问题,“时”指的是该社区的历史进程由远迄近,聚散离合,逐步形塑,因而构成一个值得研究“理想社区”;“空”则是指它所位居的自然区位,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地域交通等,因而也可以构成一个有特殊研究价值的地理单元。 因应这种虚实结合、时空兼备的特性,研究者选取的侧面各有考虑,也各有可以贡献的观点。于是,21世纪以来,介入社区宗教信仰这一领域的研究力量,就其学科训练背景而言,民族学研究者关注社区居民的民族性交往、民族经济文化的区域化变迁;社会学者讲求社区信教人群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研究;历史学者偏重社区宗教信仰的变迁史研究;人类学者则注重对社区信仰的人群交互作用、信仰与生活交集的研究;心理学者更关注社区群体或个人的心性嬗变与宗教情结。诸如此类,相关学科各有关照侧面,的确会形成多学科渗入的态势。(15)这种现象,既能收到交叉研究的益处,又可偏重专属领域,极有可能形成一种社区信仰研究旨在“协同创新”的学术共同体格局。 问题也就出现在学者们以“跨学科”姿态介入社区宗教信仰的高质量操作层面。傅斯年曾言,“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16)目前,由于从事社区宗教信仰的各学科学者纷纷宣称,其研究进路不仅宗奉本学科脉路,而且积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导致一种几乎所有研究都属于“跨学科”成果。尽管有学人倡导“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成果实在需要两个学科人员互相欣赏与知识互补的前提”,(17)但是毋庸讳言,某些自视为“跨学科”之作,却在实际上呈现尴尬之境——本学科的精深理念与有效方法并未运用到位,而点缀其间的其他学科理论或方法,亦属“东施效颦”,并未真正体会到运用学科的真谛。这种尴尬之境目前在很多研究领域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而各学科“齐抓共管”的社区宗教信仰研究领域则暴露得更为明显,即便是已经引起关注的成功之作,亦多少显露出此种难解之症。 于是,相关学科共同研究社区宗教信仰的学科落差产生了。以人类学和历史学为例,这种“落差”体现在文化人类学者、宗教人类学者既想从本学科出发,来解释社区人群的宗教现象和宗教信仰的深度研究,又关怀社区信仰形成历史中的各种面相,以便更准确地理解现实,研究现状。但就拥有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本身而言,由于其人类学方法训练有年,谙熟规范,相关部分的研究也就做得游刃有余;而追踪历史,这些学人则功力未备,在历史文献蒐集、解读、使用方面均不免显露捉襟见肘的窘境,强行介入其领域,也只能不顾历史文献的合理结构和时境限制,略作点缀。整个研究过程自然会呈现“厚于此,而薄于彼”的学科落差。就历史学者而言,本身的志业学有师承,功底扎实,研治社区宗教信仰时,擅长于历史变迁的综合梳理;但是面对当下,欲呈现社区信仰的实态,却因人类学的训练不足,田野事功勉为其难,东施效颦又不足成事,最终仍堕入另外一种学科落差的窘境。这种“落差”轻微者,表现为本业功夫扎实规范,视野开阔,而非本业的学科在相关知识和方法方面则略嫌牵强。读者因学科差异,虽已觉察其微瑕,然而尚可接受。落差较大者,则轻重失衡,甚或一丑遮蔽其余,不但难言“研究”,更遑论创见。更有某些研究者大胆宣称兼顾二三种以上的学科方法,以关照研究对象的整体情态,在学术训练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虽然勉强成文,然在内行读者看来,却有童牛角马、不伦不类之印象。这是近些年来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热闹非凡、但却隐藏着一种不易化解的浮躁顽症。 根治此类顽症,首重祛除浮躁浮华、妄作标榜之学风。数年来,学界诸君子倡导跨学科风气,教育行政领导亦以跨学科作为学术评价的导向。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也的确需要一种各相关学科介入的必要,但是具体到一项个案研究,在学人相关学科方法和理论并未兼备的情况下,是否一定要标榜跨越学科藩篱,则未必重要,勉强为之,也很容易做成非驴非马、两不沾边的所谓实证研究。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史实重建与当下呈现,便是一种难以融洽接榫的问题。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与历史学背景的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往往会遇到各自尴尬的问题。如下文所述,这类尴尬问题正好显示出典型的学科落差。 人类学研究者主导下的社区宗教信仰个案研究,若追求研究对象的完整实态,便会遇到社区信徒历史来源的求索问题。通常情况下,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宗教信仰问题,如果不是截断众流,总会面对追踪史源的问题。史源问题的解决,需要历史学科的强力介入,但是严谨的学者绝不会贸然踏入。这是由于某个区域狭隘的农村村落、地域有限的城市社区,甚或深藏山林的空寂村庄,其遗存下来的文献资源非常罕见。在“中央史观”一统天下的旧时代,这样局促狭小的一隅角落,实难进入史家文人的视野;国史、地方史和家族史的书写者,更不屑于记载这类毫不起眼的“家长里短”,梳理其百数十年来的脉络谈何容易。幸运者寻觅到一种地方记载或独门秘笈,如获至宝,完全依据此类文献,追踪史源,适足以堕入史家极为忌讳的“孤证不立”的弊端。基督宗教社区研究领域,此类问题更显突出。原因是当今遗存的基督宗教社区很可能是清代乾嘉以后逐步形成的,(18)单独依靠所谓零星片段记载,来重建史实,结果遗漏大量的背景性文献,最终只能是自说自话,社区信仰的历史也只能是作者心目中的历史而已。历史学者主导下的社区个案研究,与人类学者遇到问题正好相反,田野训练的先天不足,极易导致民族志书写欠缺规范,又缺少深入了解信徒社群心智的调研手段,满足于依靠简单的社会调查问卷数据,进行表面性分析;结构性访谈,亦难免形式上追求“结构合理”,而实则难以达到运用人类学解决族群信仰与生活交集的理想境界。 正如学人所见,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将过去和现时勾连起来,为“理解文化观念、经验、社会组织和物质状况的跨时空的关联性互动”,(19)比较理性的做法,倒是不刻意追求面面俱到的研究心态,避开编写“教科书”那种四面兼顾实则容易导致的“四面不顾”,在心态上树立真正的“问题意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发挥研究者本行的学术积累,只有遵循本业至上,才会深入堂奥,个案研究也才能做得精深,学术创见也才有所可能。“跨学科已受制于分的成见,不分科才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探寻本来的意境,重现史事而非创作历史。”(20)如果对“跨学科”作直观性理解,表面上虽可以敷衍外行,但实际上却难逃内行人的法眼,本欲推进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却适得其反。 三、田野工作的提升空间 学人大致都会认同这样一个理念,即田野工作为人类学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着不可替代的活态素材,为训练人类学者提供着动感的反思与成长的场域,为获得中国人类学典型极致的表达谋求着重要空间。(21)不宁唯是,田野工作又是宗教人类学的核心环节,该学科成果质量之低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各个环节是否真正到位。按照黄剑波先生对田野调查工作的体会,田野调查是一种“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循环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比“进得去”和“出得来”要更为细致的对于调查者身份以及对被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尊重和强调,田野作品是一种“多声道的复合叙事”。(22)这一体验是从宏观方面得出来的,若从具体操作而言,尚有细微末节的技术性和理念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既往论著暴露出来的田野调查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遮蔽了宗教人类学解决社区宗教信仰研究的光辉,抑制着这一学科介入中国社区研究的巨大潜力。 首先是如何对人类学田野工作中问卷调查文献的证明限度和解释能力进行恰当定位。问卷调查本属社会学介入社会问题研究的一种典型方式,宗教人类学虽然不排斥使用这种获取研究对象文献的简单方式,但绝对不会将其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主要的原因在于问卷调查是针对整个信徒(或非信徒,详见后)表层信息的调查,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旨在获得整个群体表层数据的田野工作。社会学之推重这种田野方式,与这一学科的“求同属性”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即在于发现社会运作的共性规律和同质现象,然后上升至理论层面;而宗教人类学则偏重“求异属性”,旨在发现异质文明的“相异成分”,它以深入社区人群深层的心智和信仰生成机制、信仰与生活交织程度作为研究的旨归,(23)实质上看,它属于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某些既往宗教人类学论著的田野事功,惟重问卷调查,将其视为研究工作的主体,实际上忽视了这种田野方式在解释宗教信仰方面的局限性——仅能“把握”表象,而不能深入个体心境。就重要性而言,问卷调查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人类学介入社区信仰研究的首选事功。 其次,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质量的提升空间。在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田野工作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上述所提及的三部代表性论著,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方面均有可以称道的地方。当然,包括已经引起反响的论著在内,很多实证性社区信仰研究的成果中,这项最重要的田野工作依然存在尚待提升的空间。具体而言,观察与访谈并非走马观花和简单对话,最为重要的是以掌握核心性、深层次的资讯为根本,这些资讯既包括信徒、非信徒个体宗教情感的生成因素、表达方式,渗入政治、经济、生活、社交、伦理等领域的程度和表现形态,又包括在访谈过程中显露、微露、暗含的爱憎情感、教俗关系认知、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态度立场等细微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通过言谈可以得到,或由面部表情、手语等体态语言表现出来,或由乐于谈论、回避谈论等谈话态度加以合理揣测,这些隐秘资讯的质量和数量完全由访谈者现场把握和体悟,并且及时客观地存留下来。 更深入一步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如能借鉴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话语分析”方法,注重文本表面信息和内层信息,信息内涵和背后含义,则可以使田野工作的质量大大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倡导的“语境”论、“话语分析”已开始为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所借鉴。“话语”(discourse)的运用往往包含特定的价值预设,也往往体现出对于研究对象不同的关照和认知视野,揭示出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面相。(24)在巴赫金(M.M.Bakhtin)看来,作为一种言说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是“活”的,其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25)。对于田野访谈而言,“话语”不单纯是访谈内容的记录,访谈对象言说的声音高低、谈兴低昂、面部表情、动作语言等,都需要访谈者细微观察,将被访对象的口语表达与非语言符号结合起来,既保留其公开的话语记录,又尽量把握其潜在意识、难言之隐,尤其是体会其是否受到从众心理的压力,将单纯语言分析与当时处境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这种获取田野文本取径所带来的研究图景,与往日研究论著习惯于将语言与处境、思想与现实分割处理,仅把访谈内容作为理解和评价其思想的旧有方式有明显区别,从中可以看到过去被忽视的语言与意图、思想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复杂关联。这对于加深研究的深度,拓展社区信仰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创新性和贡献度,当能提升一层,在方法学上,亦不失为一种创新性贡献。 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水准的提升,还包括对社区内各类非信徒人员的细致了解。这是中国社区宗教信仰研究拓展的必然要求。“灯下黑”效应本应在社区调研中设法避免,但是既往论著中,这一方面的田野工作似有若干程度的忽视,不幸变成了田野工作中的“视野死角”,往往整个研究过程,充满了对信徒本身的多角度调研,获取的田野文献也基本不出信徒本身这一范围。其实,深度了解信徒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交范围,不得不需要掌握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周边人脉关系和人际评价。一个信徒在人际交往中若感到孤立、紧张,因自身信教原因而被周边人视为异己,在社群活动中也因其宗教信仰而被有意疏远,那么,信徒对自己的信仰是否坚守,是否执意特立独行,还是尝试改变自己的信仰,这是研究者必须深入观察和访谈才会得到资讯。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伦交际的国家,人际关系和外界评价向来被国人所看重,社区信徒所面临的人际环境不仅他本人会时刻感知并加以应对,作为田野工作的重要一环,研究者似乎不应过分重视信徒个体和群体,非信徒的个体、群体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会从自身体会去评价身边的异类,对异类朋友和邻居也会提供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种“他者”提供的信息或许对我们走出信徒世界来了解信徒,开辟出另外一个视野,以匡正仅仅了解信徒们自身评价的偏差。 再次,社区宗教信仰中各种宗教仪式的深度解读。宗教信仰研究中,宗教仪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大凡传统宗教,总会进行各种仪式,如基督教的祷告、读经、唱诗、讲道、圣餐,以及特定的丧葬礼仪、入教洗礼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仪式,其信徒规模、时间长短,因具体环境差异而有区别。关键是不同类型的仪式上,信徒个体因年龄阅历、学历水平、与会心境、信仰程度、了解本教知识的宽狭、遭逢磨难、灾难疾病、对神祇感悟的不同,当其亲身参与仪式现场后,随着仪式的进行和会众情绪的波澜起伏,其情绪、表情、身心投入等这些需要“特写”,需要深度体会的信息,才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且,这些需要现场观测的资讯中,尤其要注意扑捉那些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人缘不同的信徒个体之间存在若干差异。人类学田野工作需要细致到聚焦、扑捉这些一般访谈所得不到的信息,做一个高明的旁观者,而不是抱着“例行公事”的心态去观察。 宗教仪式是信徒群体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和持久的方式,仪式的象征意义亦是支撑社会价值观的基础。(26)信徒认知宗教的程度、保持信仰的浓烈与否、参悟人生价值的深度等,或许均与宗教仪式不可分割。仪式的空间和环境对参与者而言,也是不可忽视影响因素,它在摄人心脾、凝聚人心方面,会随着仪式规模、环境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参与者来说,仪式的意义具有双重解释,它既有宗教意义又有政治意义、既有神圣意义又有世俗意义。注重文化解释的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的作业而融合起来,变为了同一个世界。”(27)这段话中“一组象征形式的作业”,是值得学人认真参悟的关键点,其中肯定包括了以往我们有所忽视的各类宗教仪式。学人对某一行为或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如将其放在原来的脉络(context)中予以解读,透过对域内与域外宗教生活场景的了解,对日常宗教实践与信仰生活的意义、象征进行多重把握,则可以深化对不同社群间的理解。格尔茨曾对爪哇东部小镇举行的一次葬礼仪式进行了深度观测,收集到大量的民族志素材,他据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文化解释理论,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次社会互动形式。”(28)虽然东西方宗教社会群体存在若干差异,中国本土的基督宗教仪式中,城市信徒与农村信徒在仪式上的表现也各有不同,但是,值得田野工作者细心聚焦的“意义”解读、宗教渗透社会互动的体察工作,仍是提升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重要途径,格尔茨对宗教仪式文化的解释理论对于进一步拓展宗教社区的田野视野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巨变时代社区宗教信仰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协调。所谓“巨变时代”是指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生活变动的步幅较以前大大加快,由大众媒体、互联网和社会人口流动急剧变动等各种显性因素造就的一个变化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身居高山内部的偏远社区、还是处于繁华城市的现代社区,无不感受到这一巨变时代的种种变化,甚且已经参与到这种变化之中。既往论著中,田野工作重心大多以社区宗教信徒中的中年和老年成员作为调研对象,(29)这是由于经历“文革”十年后,最先表达信教愿望的就是这批人员,直到近几年各类宗教人类学作品面世为止,这批中老年信徒在社区中仍旧是铁杆的信仰守望者,难怪他们会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角。 然而,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即连农村社区(包括身居大山内部的村落)也早已被覆盖在大众传媒的笼罩之下,电视媒体的冲击力尤不可忽视。在这种媒体营造的文化环境中,受众随着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变化或许会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家庭内部思想观念固守者往往是中老年这些“欲望”不够强烈的人,相反,年轻一代对新思想、新事物感知能力较强,易于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加之农村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城乡交流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步得到强化,社区人口中年轻信徒的可塑性因素在逐步增加。城市社区也会面临着多歧性变化,年轻一代受到互联网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信仰缺失、生活随意、沉湎游戏甚至放浪思想的人不在少数,社区宗教信仰的整体环境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类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应漠视这种变化,在田野工作中更应关注的是社区个体在这种社会变迁中的不同取向,尤其是对其宗教信仰产生的冲击性反应。 在已经出版的社区宗教信仰论著中,除了专门讨论年轻一代(例如打工者、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等)社群的论著外(30),一般而言,社区宗教信仰的整体性研究和专门的社区个案研究,其田野工作的视野中,大多仍将信徒社群视为一个整体而不加区别。其实,尊奉宗教的感情程度、认知限度、参与活动的次数,中老年信徒与青年信徒本来就有若干差异,包括既已成名的论著在内,很少有研究对这种差异作深度解剖,田野工作过程中,对此不加区分的做法较为普遍。在已经来临的巨变时代,这种差异还会持续,或许有扩大的趋势。笼统的民族志文献不可能呈现差别明显的层次性信仰实态,这是既往研究的严重不足。 四、信息把关人的学科自觉 “把关”的概念由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卢因(Kurt Lewin)最早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他认为,食物从生长到变成餐桌上的佳肴这一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这些把关人决定着食物的去留和品种。1947年,卢因将“把关人”运用于传播学研究,认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通道。(31)怀特(D.M.White)1950年将“把关人”传播理论再度发展,他认为,从新闻事实到稿件见报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决定是否刊出新闻稿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怀特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32)怀特的理论采用个案研究法,聚焦于把关人,将把关行为的内核凸显出来,这是怀特研究的主要价值所在。“把关人”理论在宗教人类学研究中当然值得借鉴。前述田野工作过程中,研究者重视中老年信徒资讯收集,而忽视青年信徒资讯,偏重于对信徒资讯的调研,而漠视对非信徒资讯的收集,等等,均属于研究者作为“把关人”不当的田野行为。 此处引入“把关人”理论的用意,主要是针对既往研究中程度不同存在着研究者超然立场的偏离倾向。换言之,不论是历史学者主导的偏重社区信仰历史研究、社会学者驾驭的社区信徒研究、还是人类学者亲身主持的社区信仰田野工作,其成果必须受到严格的检验。读者若细密冷静地阅读之后,或有这样的感觉:作者在书中的措词行文、调研倾向以及事件评估,总会偏爱信徒一端,而对非信徒、地方政权以及异己存在,不免冷淡很多,两类叙事色调已经形成一定的反差。有学者讨论清季教案中的信徒遭遇问题,通篇之内对教内人士的遭际倾注眷眷同情,而对反教士绅和官员之言行分析并未深入时境,在其文献并不足征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倾向明显折射出“把关人”欠缺了超然中立的“他者”意识,其史学文献功夫之浅陋固不足论,而其人类学的学科意识之淡漠由此可见。即便是研治当下之社区信徒群体者,其调研问卷设计、访谈安排以及读经会的细描浓画等,各种田野作业无一不显示出偏重信徒,而对反教倾向、叛逆情感、疏离宗教信仰、政府介入方式等有意淡化,甚至站在信徒立场,“旁观”那些异己力量的“表演活动”。 以提出文化和宗教解释理论著称的格尔茨,曾经对人类学研究者的“移情”问题有过讨论。他认为,“移情”并不需要研究者变为当事人,当其在一个地方进行田野工作时,他虽然生活在其中,有所体会和感悟,通过自己的体验逐步接近当事人生活的世界,明白当事人所思所想。但是,必须意识到,研究者的观点不可能等同于当事人的看法。人类学者对异质文化和当事人的观点必须保持“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与“经验远离”(experience-distant)的程度差异。前者是要求使用当事人的概念语汇恰当描绘当事人的文化建构,后者则要求使用学术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异质文化。格尔茨这种“移情”理论,是对研究者“中介”身份含义的另类解释。(33)正如罗红光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人类学家“受制于一套严密逻辑和习惯术语,并决定了它的表述结构。用我们的一套术语(系统)再现地表述另一套知识系统的术语,它是一种关于表述的表述。”因此,将会出现“理解之理解”。(34)当学人将社区宗教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就是一个“把关人”,他必须学会“移情”,学会“理解之理解”,时刻对自己的所思所想与研究对象保持一段刻意分割的距离,如此,中介者在情感取向上才会超然姿态。这是一种学科自觉,正如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走进历史,又须做历史的超然者”一样,人类学者也必须做到“进入田野,而又要远离田野”。 这种学科自觉本属极易理解的问题,但是“知易行难”,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总有放松自己学术警觉的时候。一旦这种警觉心理出现真空,其民族志撰写中,田野文献信息的剪裁便会极易出现取舍失衡、情感错位的缺陷,如此一来,作为整个社区信仰研究的“把关人”,自然会产生非理性的厚此薄彼,不自觉的堕入“当事人”一方。而“跟着感觉走”的结果,很可能使该项研究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到质疑,更难以面对后来者严格的学术检验。认真领会“把关人”理论,保持人类学的学科底线,将是创建学科自觉意识的不应绕越的一环。 宗教人类学引入中国后,在宏观理论发展、社区个案研究、特殊社群研究、宗教事件解读等各个领域均已产生丰硕的成果,这是近年来宗教学学科发展较快的一大领域。随着国内学术机构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不断加深,西方学界流行或曾经流行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形貌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拟剧理论、仪式理论以及文化解释理论等,均在我国学人的研究实践中有所借鉴,并以之运用于诸如社区信仰研究等领域,从而涌现出若干有一定影响的论著;中青年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下,纷纷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以期与西方早已卓有建树的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学科实现接轨;西方学界凝练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评价规范亦整体上指导着国内学界同仁的学术实践和教学活动。(35)这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初期的萧规曹随阶段,理应得到理解。 然而,知识生产和智慧创新并非西方学界的专利。本土的社会土壤和精神世界自有与西方世界迥不相同的成分,即如广袤中国的各类社区,其信仰体系、信众生活、信徒结构,总有其独到特殊的异质系统。学人所受训练,尽管借镜西方,但其依托中土文化资源所进发的创造潜力不应被低估。庄孔韶先生尝言:“世界人类学史上连续展示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为了挪用和套用,而仅仅是为了协助我们在新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思想的转换、提升与创新”,(36)赵旭东先生进而提出了“中国意识下的田野工作”的观念。(37)循此而论,学人理应有勇气也有才智敢于以自身的精深研究突破西方的既有框架,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社区宗教信仰研究天地。然而,目前相关学科共同介入产生的学科落差、田野工作的粗糙化现状、研究者“把关人”身份的模糊状态,必然会阻碍着学科超越的步伐,只要学人不尽快摆脱这种乱象,快速走出迷离游移的狭境,我们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尽管宗教的体验可能是虚幻的,但是当下学人对学科现状的感知不应虚幻,而应时刻抱具凛凛警觉,如履薄冰,才会踏上追越世界学科前沿的坦途。 ①参见Bronislaw Malinowski,Magic,Science,and Religion,Kessinger Publishing,2010; A.A.Radcliffe Brown,Structure and Fo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The free Press,1952; E.E.Evans Pritchard,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Claude Levi-Strauss,Claude Levi-Straus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②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③于丽娜、胡晓娟:《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综述》,《宗教社会科学》(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⑤马威:《北方蒙汉边际地区的轮养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⑥周泓:《群团与圈层——杨柳青、绅商与绅神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⑦石峰:《非宗族乡村——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⑧近年来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展开的基督教区域史或社区史研究的成果丰富,代表性论著包括,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年;朱峰:《基督教与海外华人的文化适应:近代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个案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等。 ⑨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第357页。 ⑩Nanlai CAO: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Christians,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1)曹南来:《中国宗教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地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第26页。 (12)黄剑波:《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吴庄基督教的人类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12年,第10页。 (13)同上,第6页。 (14)此措辞用语,见庄孔韶、生龙曲珍:《田野调研:布局、论证、发现、转换与交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5)参见Batson,Daniel,Patricia Schoenrade,and Larry Ventis.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Smart Ninian,Worldviews: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s of Human Beliefs.New York:Scribner,1983. (16)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今本误谬》,载《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 (17)庄孔韶、生龙曲珍:《田野调研:布局、论证、发现、转换与交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8)参见Ryan Dunch,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Joseph Tse-Hei Lee,The Bible and the Gun: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1860-1900.New York:Routledge,2003; Alvyn Austin,Chinals Millions: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1832-1905.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2007. (19)周泓:《魏公村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20)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71页。 (21)刘谦:《“活”在田野——人类学表述与训练的典型场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2)赵旭东等:《“田野回声”五人谈:中国意识与人类学意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3)Clifford Gr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41. (24)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52—153页。 (25)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第2卷,第359页。 (26)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2页。 (27)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86页。 (28)格尔茨:《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第52页。 (29)参见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0-2005)》,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此类论著包括高师宁:《信仰与生活——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香港:道风书社,2006年)、何哲:《城市中的灵宫:一个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教会的发展实录》(香港:明风出版,2009年)、张寿芝:《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和对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周晶:《兰州市基督教青年教会唱诗活动初步调查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等。 (31)Kurt Lewin,"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Human Relations,1947,pp.2-38. (32)D.M.White:"The ‘Gatekeepers':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27(1950). (33)Robert J.Priest:"‘Experience-Near' Theologizing in Diverse Human Contexts",Craig Ott,Harold A..Netland,ed,Globaliz-ing Theology:Belief and Practice in an Era of World Christianity,Baker Publishing Group,2006.p.183. (34)罗红光:《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35)近年来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积极推进此项工作,如2012年7月由普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机构联合举办的宗教社会学教师研修班为该领域的青年教师提供相关课程和培训。 (36)庄孔韶、生龙曲珍:《田野调研:布局、论证、发现、转换与交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37)赵旭东等:《“田野回声”五人谈:中国意识与人类学意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