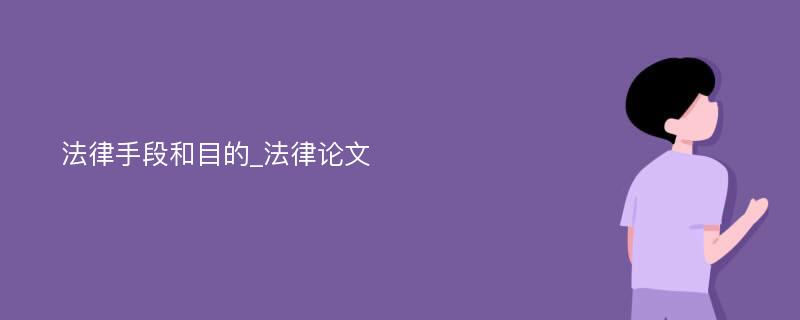
法律手段和法律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法律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106—07
1.法律的目的(Purposes of law)
初看起来富勒与哈特间的论战似乎是围绕法律能否被看成是实现某种目的的行动这个问题来进行的。哈特批评富勒太喜欢目的这个概念,他希望富勒的这种浪漫“能降温为某种令人尊敬的冷静方式”[1](p363)。富勒则反驳哈特“太不重视目的”,并批评他“对待那些有目的的行动安排,就像它们根本没有服务于任何目的一样”[2](P190)。由此两者的分歧似乎就是法律在哪种程度上能被看成是服务于某个目的的。两位杰出的理论家正在认真权衡,在法律中的目的(purpose)应在何种程度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所幸这一问题只是论战本身的产物,哈特从来无意拒绝承认法律可以实现某些目的。法律当然可以,但哈特想强调的是这些目的应该是法律外的。“平等对待妇女和减税是独立的实体目标”在辩论中是道德和政治问题,应由政治家来决定。法律可以是实现这些法律外目的的手段,但这并未把法律本身变成独立的道德实体。因此,以实现这些目标为目的的法律安排是道德中立的,它们有效与否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这就是哈特为什么不断强调:“尽管法律可以对实现终极目标做出贡献,但它本身却不是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原因。”[1](P351)
哈特的观点接近凯尔森(Hans Kelsen)和韦伯(Max Weber)的新康德主义观,即认为法律官员的技术行动就根本而言是技术性的。当政治家的任务是决定努力的目的时,法律人的行动就应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的。法律和道德的根本分立点在于新康德主义对目的和手段的区分。目的的讨论被认为在根本上是道德和政治性的,而在这种讨论中我们无法形成对真正可欲目的的理性一致;相反,对手段的选择则被认为是技术问题。理性被限制在如何选择那些能最好和最有效地实现一个既定目的的手段这样一个范围内。由此,他们的论战就不是关于法律本身是否具有某种目的,而是这个目的的本质(nature)是什么。这些目的是法律外的,还是法律的组成部分?法律本身是充满着这些道德和政治目标(ends),还是是个功能众多却中立的手段,仅被用来实现政治家提出的任意目的(purposes)?
2.内在道德(Internal morality)
在同哈特的论战中,富勒的立场并不暧昧。他不断强调法律不能被用来实现任何意图(purpose),并且他真的被哈特的那个关于制毒人的比喻吓坏了。 富勒坚持认为,法律本身必然存在着某种特质,使它根本不同于毒药制作及其他技术手段。但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富勒并没有完全找到答案。其实,富勒哈特的辩论中心不是关于法律有没有目的性,也不是这些目的的本质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承认法律可以是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两者仅仅区别在:当哈特认为成功工匠的技艺指引标准是道德中立性时, 富勒坚持认为其源于法律的某种“内在道德”(internal morality)。富勒认为,当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时,法律就实现了自身的道德价值;审慎立法者的工作不仅应具有杰出的技术品质,还应在某种程度上被评价为取得了一定的道德成就。
但是富勒并未论述他提出的八项要求与其他技艺规则不同,而应当被理解成道德标准。在回应他的批评者时,他甚至采取迂回策略,承认八项要求中的七项可被看成是纯技术性的。其目的在于促进便宜行事的权宜之计,而非实现道德目的,它们取决于制定规则的技术(the craft of rulemaking)的相关专业背景。① 在富勒称作“管理性指引”的“由上及下关系”的背景下,这七项要求是道德中立的[1](P208—209)。与此不同,在法律范围内,仅在富勒称为自由公民间平行关系(horizontal relations)下,这些要求才有道德意义。然而,这个论证并不支持这八项要求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的观点;相反,恰恰加强了哈特的看法——这些要求本身应是道德中立的。富勒并没有论证法律由于这八项要求而具有了道德性,他提出,因为它们是法律的,所以才是道德的。
3.作为手段的法律(Law as means)
那么,立法的八项标准究竟是道德性的还仅是技术指引性的这一问题真的重要吗?富勒的这个问题——法律是否因为包含了这些要求,从而具有了道德特性,真的重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旦拒绝法律和道德应该分离的法律实证主义教条,在论证法律本身代表了道德价值的时候失败,那我们就只能论证由于法律作为服务道德价值的工具,从而具有了道德意义。
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就赞同这个方案。他试图建立一个实质性的而非程序性的自然法理论,但他的努力并不令人满意。相反,对任何不同意八项要求本质的人而言,菲尼斯的理论正表明了将等待他们的某个理论陷阱。从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对菲尼斯的理论给予认真的回顾。② 菲尼斯的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富勒观点的态度在根本上与哈特的批评一致。菲尼斯明确同意哈特的看法,即认为富勒的八项要求是道德中立的,并且认为它们可以和“恶的目标”(evil aims)共存,并相互作用[3](P293)。但这种一致意见的结论却不同,当哈特认为富勒的要求太多时,菲尼斯却认为富勒在表明法律和道德的内在联系时做的不够。菲尼斯赞同新康德主义对法律实证主义的评论,并在道德和技术间做了严格的区分。这导致他把法律的目的(ends)一分为二,即技术目的和道德目的。技术目的代表了争端的解决、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对这些技术目的(technical ends)的追寻,使法律沦为了技术手段:“律师的执业工具,就是那些手段,这些手段在服务于某个目的时能明确地确立某种技术,是某种技术推理(technical reasoning)模式。这个目的(purpose)就是对于每个争端的不模糊的解决,它是可以以某些方式预测和提供的。”[4](P142)
法律作为实现给定目的的一系列工具而具有的技术层面,表明它的词汇和用语不应单单被看成是对道德训诫的简单翻译。法律不是一组道德训诫和惩罚性强制力的简单叠加[3](P281)。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可预测性和确定性,这要求它需要另一种形式的词汇,如“法律推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推理——而不是道德推理。正如所有的技术推理一样,它关注的是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a particular purpose),即一个可以通过对实现目的手段进行有效安排而得到的确定的事物状态。”[4](P142)
为实现这些技术目的,立法者应当接受菲尼斯所称的“法律之治”(pule of law)的引导,但“法律之治”并不比富勒提出的八项要求包含更多的内容[3](P270—271)。菲尼斯认为,这些要求是技术要求(technical requirements)。与实证主义不同,菲尼斯没有就此罢手,他认为,技术目的应从属于道德目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的技术目标(technical aims)理应是追求一些更高道德目的的手段。法律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法律更应以“公共的善”(common good)为目的;法律不单单具有技术层面,它也有道德层面。菲尼斯强调说,为了更正确地理解法律,应该把这两个方面都加以考虑,并应理解法律的技术层面是依附于道德层面的:“这种对确定性的诉求,对完全一系列的,唯一正确答案的诉求本身,就是服务于一个更广泛的善(a wider good)。它正如其他人类根本的善(all basic human goods)一样,虽然不能简化为一个确定的目标,却更是开放性的善(open-ended good)。”[4](P142)
4.公共的善(The common good)
那么,什么是那个更广泛的善呢?菲尼斯介绍了“公共的善”的传统观念:“一系列的条件,它们允许社会成员为了自身的原因,来实现某些合理的目标,或者来
理性地实现某些价值,而正因为这些价值的原因,他们才有理由在一个社会中彼此合作。”[4](P155) 菲尼斯再一次强调了法律之治(富勒的要求)要从属于公共的善。按照菲尼斯的观点,法律之治“不一定保证公共的善的每个方面,并且有些时候它甚至不能确保公共的善的重要方面”[4](P274)。因此,不应总给法律之治以优先权。他论证说,在法律之治不能完全实现公共的善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地或者有时是大幅度地离开法律之治。他还认为成文宪法不应是“自杀公约”(suicide-pact),在极端的条件下,真正的“治国之才”(statesmanship)是必需的[4](P275)。因为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服务于“更广义的善”,有时候有必要牺牲它们来实现后者。这些论述符合菲尼斯描绘的,由手段、技术目标和道德目标共同组成的等级画面。但如果把它们与菲尼斯对公共的善的定义结合起来,即公共的善作为一系列条件时——这些条件能促使公民追寻那些彼此合作的价值,这个画面就很令人迷惑不解了。如果我们把后者理解成一系列起授权作用的条件,那么法律之治对创设实现它们可欲的相关氛围(the desired climate)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其说法律之治“甚至不能保障公共的善的重要内容”,还不如更恰当地说,法律之治就是公共的善的主旨所在。
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菲尼斯的公共的善的概念广于以上所引含义。在他最近发表的论文中,菲尼斯引入了一个公共的善的概念,它可以更容易地和公共的善应该优于法律之治的观点相协调一致[5](P1—26)。他区分了公共的善的两个观念,即工具性的和非工具性的。前者是我们目前遇到的,由一系列的授权条件构成的善;后者不是公民个人可以自主选择所要追求价值的某种氛围,但它可能和菲尼斯辨明的终极价值之一相近。这些终极价值,即菲尼斯的术语“基本的善”是:生命、娱乐、知识、宗教、友谊、美感(aesthetic experience)和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它们是那些由于自身的原因而被追求的所有价值,而且不应作为追求更深层次目的的手段。
5.先道德决定(Premoral decisions)
如果菲尼斯的法律之治的“技术”所要求的从属性,只能在“公共的善”的非工具性的意义上论证的话,那么问题就是:这个公共的善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那个“更广意义的善”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们中哪个应位于“法律之治”之上?在基本的善中,哪个应处于最优先的地位?友谊、知识、还是宗教?菲尼斯没有提供答案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认为这些基本的善或终极价值本身都是平等的,它们本身就是目的所在(end-in-themselves)。由于价值源于自身, 从而无法相互进行比较,他坚守这个观点。因为他的新康德主义观认为,一个终极目的(例如幸福),会把对目的的道德论争简化为对手段的技术考虑。把实质性的、非工具性的公共的善的概念发展成对某种基本的善的参与,将同这些相互间不具可比性的价值的多样性特征发生冲突。由此,菲尼斯不愿定义一个更具体的公共的善,他认为它们本身应该是公共论辩的结果。但问题是,当这些终极之善被认为相互间不具可比性时,将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这种争论呢?在理想条件下,一个社会应该努力实现这七种基本的善,但不可否认,每个社会,即使是物质富裕的社会,都或早或晚必须决定它们中哪个应具优先性。而等待决定的这些问题表明了我们对公共的善的某种特别概念。
菲尼斯强调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选择是主观而非理性的决定。它们不应像功利主义者那样将幸福作为标准进行评价,而应该按照自身原因来选择,就好像那些不能再降为更深层的目标的价值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最终意义上,个人和集体都无法给出任何理性论据来证明其选择的最终原因,因为这种选择是先道德的。”[4](P148)“在团体的共同生活中,对理性无法衡量和比较的因素(rationally incommensurable factors)的先期初步估量(preliminary commensuration),不是由理性判断完成的,而仅仅是人为的决定(decisions)或选择。”[4](P149) 然而,这些“决定”不能够用“法律之治”的要求来验证。作为单纯的技术标准,这些要求被认为有助于一个更广泛意义的善,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应该做出让步。但这是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意见,例如安全、可预测性和平等价值,就可能在最终意义上因为所谓的公共的善的专横裁决而被牺牲。③
6.菲尼斯的两分法(Finnis' dichotomy)
对菲尼斯理论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这个自然法理论中的内在问题。基于新康德主义的理论预设,这种自然法理论对技术手段和道德目的进行了明确划分。这种二分法对法律实证主义者而言,则是颇具成果的理论预设。他们可以把它作为论证法律和道德应该分离的理论基础,并对那些认为法律和道德在某种程度上相联系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但它也导致了法律被人为地分为技术和道德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又不能有意义地发生联系,除非认为技术层面应从属于道德层面。即使在道德层面上,两分法也导致了危害,公共道德本身要么被看作是手段,要么是目的;若不是手段性的,就是非手段性的。在菲尼斯整个理论中,弥漫着手段和自身目的间的分裂。菲尼斯的这些看法在理论上不能令人满意,且实践结果也更缺乏说服力。尽管法律程序和安排的目的在于实施和保障自由公民间的合作,应该以不可归结于其他任何更深刻理性探讨的对象的名义做出牺牲,但它却成了主观感性偏好的产物。这一系列想法所产生的令人吃惊的结果就是我们应遵守法律[6][P259—281)。原因不是法律确保了安全或确定性(因为它们“仅仅”具有程序性的品质),而是因为法律服务于某种不确定的、广义的善。
显然,富勒的理论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远离了任何关于绝对价值或公共的善的讨论。但从他坚持自然法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这一观点来看,其更容易受到相反的批评——在某种确定的程度上,他过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根本没能证明法律和道德是内在联系的。很明显,这种批评仅仅在同意对目的和手段两分时才适用,它仅建立在富勒以纯技术家身份出现的假设上。也正因为如此,富勒才仅希望能以削弱这种两分法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7.富勒的建议(Fuller' s proposal)
实际上,富勒的反驳意见在其文章《手段和目的》中都可以找到[7](P47—64)。这篇论文为富勒的理论——法律本身体现了一个道德价值,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他能够把法律和道德联系起来,而无须一定遵循法律必须为了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善做出牺牲这样一个观点。以此为据,富勒试图克服技术手段和道德目的间的二分问题。④ 富勒认为,表明目的终极性和手段单一工具性的语言表达完全是误导的。为获得对行为、尤其是对法律体系的更清晰的内在看法,应远离这种区分。富勒论述到,法律不单单是个带来秩序和正义的手段,她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秩序。他援引欧克史特(Oakeshott)的论述来证明自己,自由不是“非经审判不得非法关押之程序”存在的结果,但蕴涵其中[7](P60)。由此,他批评了功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理论对理性的有限认识。富勒认为它们受到的危害来自于以下事实,即低估了在选择手段时自由的参与程度,高估了技术工匠在完成给定目标时的考量能力。“令人好奇的是,尽管从来未明确谁是有能力为实现社会目的设计恰当手段的技术家,但人们似乎认定他们的能力是无限的。”[7](P56) 但正如富勒指出的,即使每个人头脑中有某个确定目标,也会出现最困难的尴尬境地,因为对手段的思考,不单单是纯粹的计算问题。相反,对手段(means)的选择完全影响了对可欲目标的选择。在“目的明确者”(end setter)和“手段专家”(means specialist)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这些看法对反驳哈特和菲尼斯的批评意义重大。由此,这篇论文可能已经变成了论证以下观点的新起点,即具体目标不能被认为是独立于法律安排的,并且由此这些法律安排也不是道德中立的。⑤ 但是富勒在对批评回应时, 仅仅不时地暗示这个手段——目的间的区别。他坚持,“从某个角度看是手段,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是目的,并且目的和手段时时处处存在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2](P196)。然而,这个不严谨的评论显然不足以反驳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富勒对内在和外在道德的区分,似乎又重新引入了道德和技术间的区别。对木匠的比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理解,即他的要求仅仅是对立法者的技术指引。他对自然法仅仅是程序性的坚持也强调了其把法律首先看成是工具,一个实现外在的、由政治家决定的“实体目标”的工具和途径。这就难怪富勒的结论不能完全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如果这个两分法的僵局有脱逃之法的话,它应存在于富勒那些犹豫不决的、制定法律实用主义理论的尝试中。
8.作为手段的行为(Activities as means)
富勒强调法律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1]( P123),她是人的行为, 是一个事业,目的在于“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它的优点在于允许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评价,因为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取得某种程度不同的、或多或少的成功[1](P122),而不是被迫认为法律在此是某种可有可无之物。
但究竟什么是行动呢?富勒认为行动是为了达到更深层的目的的手段,我们通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富勒的。杰瑞米·沃顿(Jeremy Waldron)就区分了两种层次上的工具性:首先,人们要问规则之治是否能作为服务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最佳制度工具;其次,人们要追问为了有效地实现目的,这个工具应有什么特性。他认为富勒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8](P262)。
笔者并不认为这种理解合理并能被接受,因为把行动看成是“手段”未必有意义。洗盘子当然是得到干净盘子的手段,或者生产皮鞋带是得到它的手段,但是看来只有这些简单、普通和例行公事而单纯重复的工作,才能够从它们将带来的具体目标的角度来理解。然而对大多数行动,要确定它们准确的目的的确是件极困难的事。绘画是表达某人内在情感的工具还是检查灯光效果的方式呢,或仅仅为了装饰一面空墙?答案在于你如何理解绘画。与简单重复性的行动不同,绘画不能从它的众多目的来理解,因为它还有别的方式——对目标(goals)的选择和归属本身,取决于先于行动的态度。尽管多数行动的目标可能难于判断,人们仍可以把它看成外在于行为本身。复杂的行为,诸如绘画暗示着,它最终不能被看成相对于更深层目标的手段。同时这种观点也太简单。以写作活动为例,依靠写作来取得额外经费或申请工作,可以从简单的工具性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如何理解论文式的写作呢?多数学生认为应在动笔前把一切都想好,以便真正地开始写作,但这种做法常常以困扰而终结,因为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成功的构思活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写作是表达思想的手段,正是在写作中,人们才找到了他们真正要写些什么。但我们能由此认为写作就是思考的手段吗?写作是思考的工具,但在事先没有要写什么的想法时,你却不能写出任何东西,这样思考又成为写作的途径了。问题在于,你的视角决定写作和思考的因果关系。更多时候两者是统一的,写作就是思考,思考就是写作。也许这就是富勒论述目的和动机时要表达的真正意图。
9.作为目的的行动(Activities as ends)
把写作或绘画等行动简单看成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错误的,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采取相反的态度,认为此类行动本身具有目的。这是菲尼斯的观点,至少就对行动的看法而言如此,通过他的特殊用语,把行动理解成对七种善的参与。绘画,作为对美的体验的参与,应承认它本身具有自己的目标,且再无法追溯至更深层的目标。菲尼斯认为,绘画者如仅为了某些外在目的而画,就失去了绘画本身应具有的意义。这种立场缺乏说服力。菲尼斯认为绘画者仅仅为了绘画而绘画,这表明了可能他自己从未从事过绘画活动,因为对写作的理解同样也适用于绘画。一般而言,绘画的起点是对某个最终结果起引导作用的模糊念头。随着第一稿产生了新问题和新想法,绘画者进而发现下一步行动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和创作灵感。他会以循序渐进和谨慎的方式进行,并在每个步骤中重新调整原来的计划。这并不是无目的,新画稿创作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看成是对某些目的的实现。绘画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持续试错过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可以明显地归纳出一系列的连续问题并加以解决,或可以指出为什么一些相关答案最终是错误的。那些连续出现在画家心中的目标,仅出现在绘画者真正沉浸在绘画中时,它们并非外界“赋予”的,不是和绘画行为脱离的。但是,绘画行为既不能被理解为与任何目的无关,也非纯粹为了自身的原因。
当然,我们可以给菲尼斯一个更宽容的理解。可以认为菲尼斯仅仅意在论证绘画应该看成是实现外在目的(external purposes)的手段,例如幸福、成功或金钱。
我们可以假设行动的内在目的应当和外在目的区分开来,并且仅仅是后者起到了干扰作用。但是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外在目的可能削弱行动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ht)的看法。相反,若有人安排我画一幅肖像画或某种特定风格的画(或者对富勒加以评论),那我就有了对选择完成此目的的众多适当方法的一定限制,由此在剩下的可能性中,我可以寻找能取得最佳效果的安排,并可能由此找到本对我不具可能性的新途径。外部的压力往往加强而非减弱人的创造性。这就是杜威(Dewey)为什么认为实际上对行动而言,目的是绝对必要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严格地说,目的根本上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它们引导着我们的行动,“人们不会因靶子而射击,设立靶子是为了使投掷和射击更有效和更有意义。”[9](P156) 看来这些目标无论是顾客的还是自己确立的并不重要,只要能有效引导行为就可以了。行动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有自己的目的,而在于那些复杂和多样的路径引导着行动,并在其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目的。
10.实践行动(Practical activities)
学者们试图通过强调“制造”和“行动”间区别的方法来拯救菲尼斯的理论。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Techne和Praxis间的区别。他们认为,在以生产产品为目的的行动和结果是其他行为的行动间,存在着重大区别。游戏、交谈、思考或维持友谊就是这类实践性行动。尽管生产性行动永远无法被认为“本身具有目的”,但实践行动在菲尼斯的观点中却被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行动,而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更深刻的目标。与生产性活动相比,这些行动(实践性活动)实际上更难被理解为是工具性或手段性的。然而与生产性活动一样,这种定义为手段的反对意见,并不能表明这些实践行动只能被认为是本身具有目的的(end-in-themselves)行动。各种不同的外在目的加强而非减弱了这些活动的内在价值。生产性活动亦同,把这些行动划分成要么是实现某目的的手段,要么是本身具有目的的行动的做法是没有收获的。因为很多行动同时两者兼具。对行动的分类,仅仅是视角问题。对行动的类型划分的视角决定了从属于某个行动的目的。简言之,从参与者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目的是和行动本身分离的。只存在某个“眼前目的”。正如约汉·杜威所言,“它是人们想要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9](P155),同时这个目的作为手段引导着我们的行动。
这同样也适用于Praxis的主要情景,即道德考量。在此,杜威的“眼前目的”的概念也同样重要,因为不存在“外在且超越性”的目的作为道德思考的现成起点[9](P154),没有人会像柏拉图那样纯粹以善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对不同行动进行选择时,个人不是接受某个“最终目的”的指引,而是被那些最直接的可见结果所引导。对某个特殊行动的选择经常会带来各种不同的结果,而它们依次又会引发新的思考和决断。思考和决断是实验性的、不确定的,它从某个眼前目的转换到另一个。当然人们可以把一个人的道德生活看成是对诚实和正义的终生追求,把道德思考看做是对此目的的追求手段,但这种评价往往是外在的和后发性的,它并未加强我们对某人(如果他正在思考某事)到底做了些什么的理解。这种对行动本身工具性的理解,如同把写作看成是一本书的手段那样,同样远离行动本身的真正过程,同样毫无意义。但把道德思考看成是本身具有目的的做法,也未必令人相信。菲尼斯认为“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本身是基本的善的观点,就轻视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我们并非仅仅为了思考而思考,因为我们面对着不同的行动路线,必须加以选择。
11.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Techne and praxis)若认为道德思考(moral deliberation)是杜威所指的实践行动(praxis)的最高形式,就不能避免这种印象,即它和上面提到的技术活动一样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看来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首先是观念中的目的本身促成了进一步的行动,随之带来新的问题,而新问题又带来进一步的行动,如此反复。它们是不确定的或者具有实验性,从某个目的转换到另一个。“制造”和“行动”(making and doing)的相同之处提出了为什么要坚持Praxis和Techne间的区别这样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这种区别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行为蕴涵着不同的目的—手段关系;他假设技术活动可以独立于其产品,而实践性的活动却蕴涵于其结果之中。
但是这种假设没有根据,不是所有的技术活动都是例行公事,其手段(生产的过程)能看成独立于其目的(产品)。进言之,它构成了某种序列——在一端可以看到例行公事的活动完全依其产品来理解,在另一端会发现一些目的和手段完全不能分开的行动。人们可能质疑有没有行动可以明确地被列为两者之一,回答是多数活动其实是位于两者之间的。写封求职信比写首诗更加例行公事。手工造的桌子和工厂的桌子不同,这种区别准确地说明工厂工人和木匠在上述序列(continuum)中的不同位置。这对实践行动同样适用,这类行动的目的不在于产品而在于其他行动。一方面,目的是相对简单和被赋予的;另一方面,目的仅仅产生在对活动本身的思考。正如技术性活动那样,实践性活动也常处于两者之间。对高回报投资活动的周密计划和安排,尽管不完全是例行公事性的活动,但相对道德思考而言,却是更外在和直接的活动。菲尼斯把长久友谊看成本身有目的的行动的观点,可能是令人仰慕的崇高理想。一旦友谊变成了单方面的事务且没有任何回报,多数人会迅速放弃,但这并没有把友谊变成一个纯粹的计算行为。在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中,对行动和结果进行的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划分是一个渐进的、分层的行动,它取决于我们手上进行的是什么样的特别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行动有手段和目的的明显界限,而实践行动没有这种分别。
12.法律制定(Rulemaking)
由此,比区别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更恰当的方法,是对下列两种行为进行划分,即可以完全按照其目的来描述和理解的行为(比如写求职信),以及那些以不确定方式进行的产生自己的新问题及答案(比如写哲学文章)行为。那么这对使“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行动有什么启示呢?答案显而易见。雇主制定的、针对雇员的命令和指示,应在相对简单的意义上被看成是工具性的,并应当位于序列的一端;另一端是复杂的法律制定行为,比如制定一部完整的环境法,制定行为本身不能仅仅看成是减少污染的手段。进言之,法律起草过程中有种种无法预料的新问题,它们要求对一些法律概念,如责任和财产权,重新进行界定。这些新问题的答案可能又反过来会对其他部门法律产生影响,从而引起与其他部门法相兼容和一致性的问题。
法律制定,正如写作行为,包含并存在于整个序列之中。它可能是个简单但也可能是个复杂的活动;可能是例行公事性的,也可能是创造性的行为。并且多数法律制定行为是位于两者之间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富勒有关木匠技艺的比喻产生了误导的原因。它不是因为木匠技艺的比喻是一个技术工艺,⑥ 而法律制定是实践,原因在于它认为木匠技艺仅仅占了序列的某个特殊位置,但实际上法律制定却占据了全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把富勒指出的管理指导和立法间的区别解释成这个序列提出的术语呢?我们能说管理性指导是日常的例行公事,而立法是更复杂和更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吗?新交通规则的引进可能是更直接和例行公事的工作,而管理指导、尤其是对大型组织而言,并非富勒认为的简单直接的行动,相反却包含了诸如决策等复杂行为。这种行动也可以看成是创造性的和实验性及不确定性的,正如环境立法一样。在一个著名的研究中,社会学者指出人们不应当认为决策行为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即从针对确定良好的问题开始到对问题解决为止。相反,众多的问题、选择和答案在其中产生并以任意的形式相连[10](P1—25)。我们没有理由引入存在于管理行动和法律创制活动间的那种巨大差别。立法行为可以是复杂活动的事实,并不表示我们不能从技术性手段的角度来理解它。某些税法以分散收入和减少空气污染为目标自不待言,但这种不必要的管中窥豹的行为不足为虑,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以实现某些目的的方式来理解立法行为。
对表达某几个确定的价值如确定性、正义或公平的目的和目标而言,以上道理就更真实了。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这些价值的要求来重新建构法律,但这是后事之智,因为仅仅当认为法律是实现某些理想的手段后,我们才能如此。我们仅仅能从外在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正如心理学家可以把游戏行为看成加强感情联系的手段,法社会学者可以通过减小视野——选择某些法律提供服务手段的目的,以求获得特别的内在看法一样。
在这种意义上,富勒的用语“法律是有目的的行动”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法律目的解释为某种有意识的努力,比如为了实现某些定义良好的目的,这种解释对这样一个事实不公平,即法律制定,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例行公事性的,但它也是一个创造性的事业,它由一个问题发展到另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并会连续产生其他同样无法预料的新问题。这种模糊、不确定的方式,即从某个眼前目的转变到另一个目的的方式,可以解释法律需要自身的驱动力,它不能被以手段—目的简单方式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
13.八项要求(The eight requirements)
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两者都既可以是例行公事式的,又可以是创造性的。两种行动的手段—目的关系可以是直截了当的,也可以是复杂的。认为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间的区别不再重要的理论预设,表明了法律中对道德和技术进行划分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赋予富勒的八项要求意义,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是否可以被看成既是道德性的又是技术性的争论。富勒不应没有根据地强调这八项要求是道德标准,关于它们是技术性还是道德性的论证,是多余且误导的,因为它开始于一个对技术行动和实践行动的错误区分,菲尼斯和哈特都被这样一个没有道理的区分误导了。然而也许这个答案还无法说服那些批评者。他们可能继续以某种理由争论道,在富勒所称的外在道德,即法律的实体目标和八项要求间存在着一个区别,虽然不可能把八项要求理解为技术目的,把法律的实体目标理解为道德目的(如同菲尼斯认为的那样),但是在这两种目的间也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即在起草一部反歧视法和确保它的实施间存在区别。
富勒不否定这种观点,他明确指出八项要求已经提出了对“工匠的自尊”的诉求[2](P43)。当然这必须在他关于木匠的比喻意义下来理解,正如必须依靠经验获得的技术规则那样。一旦当我们认识到写作的比喻要优于木匠的比喻时,对八项要求的理解就改变了。如果我们认为法律更接近语言而法律制定更接近写作的话,正如一个时时可有可无但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例行公事化的、充满活力而且变化的事业,那么很清楚,富勒的要求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语言式的引导——从简单的语法规则到对语言风格的要求。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比较,我们应该利用富勒提出的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间的区别。从根本而言,这八项要求应当在最低意义上被认为是谈论法律的必要条件(义务道德),还是应被看成是某种理想——从未实现但却为法律所渴望(愿望道德)?富勒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他认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包含着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两个方面[2](P42);另一方面他总结道,“法律的内在道德注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愿望的道德而非义务道德”[2](P43)。如果我们在写作比喻的条件下理解八项要求,那么在最低意义上它们可以被比作语法规则(没有它,写作是不能被理解的行为),而在更广意义上可以是对雄辩和优美文字的指导。
这个比喻说明了我们对这八项要求是以最有限、还是最广泛的意义来理解,不仅取决于立法者的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同时也取决于特定的法律制定行为本身在这个序列中占据的位置。如果仅仅是对雇员制定一些简单规则或是改变限定高速公路的最高时速的规则,我们可以在最低意义上使用对普遍性的要求,即要求规则应以普遍方式颁布。但如果某人要改革税法,同样的要求可以看作是最广意义上的——把这些规则适用于普遍阶层,不涉及不相关的差别,不涉及不合适的具体对象。正是如此,富勒把义务道德和愿望道德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序列,“谈及两种道德,我建议画一个代表上升等级的图表,位于底部的出发点是对于社会生活明显而根本性的条件,顶端终结于人的最高奋斗而追求的人的至善。”[9](P27)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富勒的序列和我所假设的、存在于例行公事和创造性行为间的序列是平行并列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富勒认为,在法律的背景下他的要求有种道德意义,而这种道德意义正是管理性指导缺失的。他可能认为后者是例行公事的行为,但实际上这些引导可以被理解为简单的公理(maxims)。富勒的观点表明,他的八项要求的确同时既是对语法规则又是对语言风格的指引。它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它在那个序列中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富勒对哈特的回答中包含了对法律和管理性指导背景分析,而不是包含了对八项要求的道德本质有利的详细论述。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着手进行的工作。
14.风格和实体问题(Stytle and substance)
如果工作性质能决定富勒的八项要求应该被看成是义务道德还是愿望道德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来继续保留对这些要求的特殊用词——内在道德,从而与法律的外在道德区分开来。富勒经常焦虑地强调这种区别。例如,在处理上面提到的对普遍性的要求时,他坚持规则的普遍性和法律不应该包含具体确定的适用对象,或它应该以一般阶层为适用对象没有任何关系。后一个要求是公平的原则,也是法律外在道德的一部分,然而这个对规则应具普遍性的简单要求,属于法律的内在道德[9](P47)。这是个人为的界限。前一个对法律应具有一般性的要求,可以认为是最低意义上的语法规则,或在最广泛意义上对语言风格的要求。以最低意义而言,它仅仅要求规则应充
分具有普遍性,以便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规则;而对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对普遍性的要求是和公正原则相同的。如果采用了广泛的意义,比如愿望道德,它就和“外在道德”的那些原则非常的接近。越是认为这些要求的范围广,就越难在内在和外在要求之间确定一个界限。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和富勒的想法一致的,因为实质上他也认识到存在着一个“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相交的、尚未确定的界限”[9](P79)。对实体内容的错误而言,写作风格起到了预警系统的作用,法律亦同。在富勒的例子中,南非的种族法在缺乏明确性时,也表明了它同样在道德上有问题。
因此,哈特的那个关于制毒人的比喻是部分正确的,它仅适用于那些的确被看成例行公事的、仅靠语法规则来创设的活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律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更确切地说,作为创造性活动,法律的重要在于它竖起了那些能让我们更好射击的靶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的确是在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探求着自我。这种睿智也允许我们看到,就目前它追求实现一个预先设定的共同的善而言,法律不仅有道德价值,而且还是重要的手段。通过它能发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公共的善。这就是富勒为什么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道德被法律改变了的原因[11](P1)。正如其他创造性活动,法律不仅仅在满足旧的需要,而且也开启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之一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以它为基础,道德价值的讨论才能得以进行。如果用道德代替法律,正如菲尼斯所言,结果将是没有任何理性的方式能确定我们所追寻的公共的善的某个特定概念。因此不应当坚持富勒的观点,我们应当把这些要求看成是可被信赖的引导,它指引我们走向人的致善;如果没有法律的帮助,对它的追求就可能远远处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
收稿日期:2004—12—04
注释:
① 这样一个要求例外,即官员的行动和颁布的规则间应具一致性。
② 对菲尼斯理论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The Disintegration of Natural Law Theory:From Aquinas to Finnis,Leiden:Brill,1998.本文第三、四、五节部分来源于该书第五章。
③ 自由和平等不在菲尼斯所称的“基本的善”中,而是通常被看做由从属性的法律之治来实现的价值。
④ 富勒把这种两分法应归因于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但是很显然它也是新康德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⑤ 此句为译者所加。
⑥ 这个观点由J.Mootz提出。J.Mootz Natural Law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egal Rhetoric,in:Willem J.Witteveen and Wibren van der Burg,Rediscovering Fuller:Essays on Implicit Law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Amsterdam U.P.,1999,Volume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