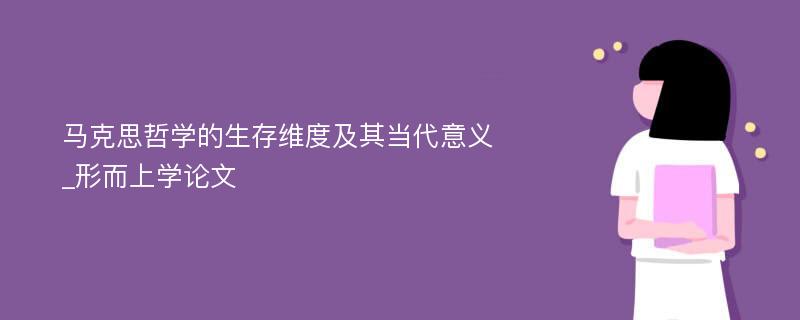
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维度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 (2000)02—0002—07
我们已经来到新世纪的入口处。但时间上的新世纪并不等于历史上的新世纪。历史上的新世纪仍在艰难的生成之中,因为人类在告别了传统信仰从而也失落了传统生活意义之后,新的信仰和新的意义仍付阙如,尽管人们每天都能感触到新奇的东西并使感官得到新的刺激和享乐,——这却只能表明人们被无止境的欲望和由它所牵引的智力所左右,心灵却依然被放逐。失却了心灵,欲望和智力甚至真的可以把人变成某种“高级”动物或者不伦不类的存在物,有关的生物实验已经毫不含糊地确证了这一点。人的生存的目的性问题仍然晦暗不明,它远未被人们自己解决。为了从根本上遏制住人的欲望和智力这匹脱缰的野马,一些学者极力呼吁强化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希冀在“超验”这一维度中恢复人的自持和自足,并从而使人在经验的尘世中不再追逐声色犬马,在科学技术的开发中也不要再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这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也有违于哲学的当代走向。如同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人类已经进入“后形而上学”、“后宗教”时代,且必定还要向前走。只不过这个前进“方向”作为人的生命向度,不应当外在于人,相反,应当是人在更本真更充分意义上的存在。但是问题就在于,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当代哲学由此而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它不能确诊并疗救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症结,如果不能承诺人的本真的生存,它就可能真的“终结”。这就如同面对斯芬克思之谜:答不出来,你就要被吃掉;答得出来,那魔獐就死掉。而正是着眼于当代人的生存问题,我们发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及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一
令我们颇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欧洲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和全球)问题,尽管有巨大的差别,但在人类生存困境这一根本点上,却又是相通的。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不再是(或从来不真正是)纯粹而崇高的“普遍理性”,而是愈来愈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在观念的“王国”中,居支配地位的虽然依旧是和宗教神学互为补充互相支持的玄虚的哲学“形而上学”,但却正在遭到另一种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的哲学的猛烈冲击。于是,满怀自由民主思想和抱负的青年马克思得以以这样的信念开始其哲学探索:“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453。)哲学要承担起这个任务, 就必须有能力进入现实的人类生活,也就是切入普遍异化的现实的“前提”之中。哲学形而上学缺少这个能力,它向人展示的是恒定的“纯真”“纯善”,这虽然能给人生以希望和某种信念支撑,却同时起着掩饰和安慰人的苦难生活的作用,而无从把人带出生活困境。那么,以反“形而上学”面目出现的“感性”哲学又如何呢?表面上看,这种哲学直接地向人自身和人的现实生活敞开,但凭借直接的“感性直观”,人们所看到的却只能是一种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自在的存在,它看不到被人的活动所中介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性存在即“属人”的存在,亦不可能了解“感性”自身的属人性质。正因为人及其世界的“属人”性进入不了这种感性哲学的视域,所以,马克思认为它和“形而上学”一样的“抽象”。“形而上学”和感性哲学表面上互相反对,因为前者的视界是超验的,后者的视界是经验的,但是为什么都产生同一问题,即都与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相脱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为什么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克思发现,这两种哲学其实有着同一种实体性思维方式,实体性思维方式认为复杂多样的现象是同一实体变化不居的属性,都不真实,唯有独立自足的实体真实。“实体”赖以存在的条件、关系和环境都被舍像掉了,“实体”成为一无所凭的赤裸裸的纯粹存在者。这正是把人生存的现世抽象化——纯化同时也是简化——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人在本质上必定是一种既定的或现成的单一主体,他先天地生、独立不倚,实际上是超然世外的,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现实性。如果说“人”是以“理性”或“感性”为根据的,那么,“理性”或“感性”作为人的根据或规定者同样是无待的绝对的本体,也不具有在世的现实性。至于人实际上在世生存的“世界”则要么被视为附属的或派生的东西,如同费希特式的“自我”创设出来藉以证明自己的“非我”;要么被视为另一种自在的实体,只是在直观和审美意义上与人发生关系。这样,不仅人本身成为完全能动而又不可究诘的谜,而且,恰恰是由人们并不满意的生活所构成的现实存在成了上述哲学的盲点。而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现实存在就是“现世”存在即存在于人与周围世界的具体关系中。他据此认为费尔巴哈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P22、38。 )可见,要使哲学真正进入人的现实生活,就必须彻底摒弃实体性思维方式,在人与世界实质性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人与世界。正是由于马克思用关系性思维方式取代了实体性思维方式,所以他对“人”的探究便转向对人的“生存”的探究:人不是独化自生的超世存在者,而是在世生存的存在者;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实体,而是复杂的矛盾的网络。因而,具体而多样的“在世生存”才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状态。人怎样生存,他就是怎样的人。人的在世生存本身就是现实的并因而具有受动性。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批判和扬弃的动因与力量,也必定蕴含在人的现实生存之中。这样,马克思实际上确立了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并使传统的“人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对“人自身”的“实体—属性”式研究转变为对人的生存的“实证—批判”(或“描述—规范”)式研究。 人的“生存”(Existence)由此在哲学中获得自觉表达并导致了哲学的自批判自超越的辩证思维及精神气质的产生。
以哲学生存论维度观照人的现实生存,我认为马克思探究并解答了下述三大问题:
(1)关于人的“生存”。人的生存就是人现实地在世生存。 马克思曾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他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前一句表明“自然”既是外部世界的规定,又是人的规定,所以人与外部世界具有同一性;后一句表明人又是自我规定的,因而人是不同于“自在”存在的“自为”存在。然而,上述前后两句话并不是指称两种分立的事实,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定是对象性存在物,即人与外部自然互为对象、互相作用;而人作为属人的存在物的自我规定正是通过人有意识地作用于外部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而实现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生命机能在对象上的表现,也是人对这一表现过程及其结果的体验和享有。因此,具有感性客观性的人的在世生存既不等于思想观念,也决不同于非人的实存,它就是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中建构并为人感受着生存意义的实际生活过程,或者说就是世界人化和人世界化的过程。诚然,人的异化生存也具有“铁一般”的现实性,但铁一般的既成事实正是丧失现实性即经历着“抽象化”的“现实”,它的属人的性质正在被抽掉、淘空而物态化。所以,人的异化生存的“现实”本身又是“非现实”的。这从反面说明人的现实的在世生存总是由于其内在否定机制(实践)而走向某种新的可能,从而呈现为自否定自超越的过程性。这也说明,人的现实的真理是可能,现实只有不断地扬弃自身才不致于停滞或退化为毫无生气的非人的实存。
(2)关于人的“生存方式”。 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它是人在世生存的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形式。人的生存方式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人凭什么生存?第二,人怎样生存?马克思认为,人不能直接依靠外部自然为生,而只能依靠人们有选择地变革外部自然的“生产”为生。原初意义上的“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所以它是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展开的生命创生活动。“生产”蕴涵着并分化出“交往”而又与之互为中介,由此形成人们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性生产方式。但生产方式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人的生存的基础,因为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其生命取向的生存,它必然以人的自我意识和族类意识为起点和坐标,对自己的活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和规范,从而使人的生存赋有人文意蕴和伦常秩序,成为社会性文化性生存;这才有了人之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这一生存共同体,人在现实性上才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越是向前追溯,我们越能发现人的生产和交往中渗透着各种信念、道德等意识因素,所以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P15。)这说明, 人的最基本的生存信念和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生存的基础。而在这时是并没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二分的。只是到后来,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关系开始主宰一切、经济利益成为主导价值、工具理性肆意扩张、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包括生产在内的经济活动才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和发展机制,而“思想、观念、意识”则“上升”为“意识形态”并为特定的经济利益和秩序进行掩饰和辩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们生存共同体的“社会”才空前地分裂开来,人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独立和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同时也反转来成为资本和商品的附庸。人的“生存”这才具有了空前严重的物化和异化的性质:人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盲目,以至于人成了他们社会合力的玩偶,成了他所从事的职业的符号,成了他不可支配的对立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的。“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P48。 )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发生的异化。
(3)关于人的生存的“实然”与“应然”。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现有的实际的生存方式与他们应有的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不是互相外在的,相反,它们互相贯通互相转化,因为人的生存本来就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自我生成和自我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to be ”的自我发展,即“to be”并且表现为“to live”和“to create”。 (注:参见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4,P20。 )而这正是对人的“生存”(existence)的丰富意蕴的揭示。 正因为人的现实生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实现而又孕育着人的新的本质力量,所以,人的现实生存自身就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本性与能力。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生存运动的理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一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P31。)以此观之,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生存决非“偶然的”“反常的”现象,而是人的社会历史性生存的必经阶段。所以,异化也不可能是人的“绝境”;从主观方面看,异化来自于人的生存活动又为人自己给出“异化”这一否定性价值评价,就说明人能够意识到并力图改变自己的异化处境。人对异化的感觉本身就催促着人去克服异化。作为“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的人化的“感觉”——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是最难以被异化的,它因而总是充当着人反抗异化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内在的动力。从客观方面看,通过异化劳动创造的巨大文明成果恰恰为异化的克服提供了历史前提。一旦联合起来的个人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他们就将自主地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创造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P486。)
可见,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开启的新的生存视界不仅使人的生存向人自身敞开,而且实际上导致哲学因获得生存论维度而发生范式转换:哲学从非生存论哲学转变为生存论哲学,并在扬弃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同时,拯救了哲学的形上维度。因为哲学不再由人的生存之外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者”(“上帝”、“精神”或“物质”)并藉以绳度和决定人生的一切;而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去开掘和阐释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和人的生活要素的一切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意义,包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的意义。实际上,立足“形而上学”难以解读人的现实生存,立足人的现实生存却可以使形而上学发生“现象学还原”:“形而上学”中的“实体”是抽象化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自我意识”是抽象化了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绝对精神”则不过是抽象化了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因此,与其说“形而上学”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根据,不如说人的现实生活是形而上学的根据。形而上学作为生存论哲学的“前身”不过是人生存的“属人”向度的抽象或异在表达。当然,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表达形式既是必然的,又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而马克思以类属性和普遍的社会性来说明人的现实的本真的“生存”之并非“现成地直接呈现”在人面前的自在存在,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生存论哲学的形上维度。
二
从以上论述可知,马克思依据其关系性思维方式发现了人在世生存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因而从根本上说明了为种种意识形态所遮蔽、所颠倒的人的生活世界的实情,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生存异化的症结并给出了救治之方。站在21世纪的入口处解读19世纪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我们自然也会产生时间的跨度感。已经走出20世纪的人的生存能力比其在19世纪不知高出了多少倍,而生存问题的复杂性也远不在同一层次上。例如,生态危机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是马克思的时代未曾面临的;人的心灵的孤独感漂泊感荒谬感及精神疾病亦非马克思的时代普遍而重大的生存问题;生物工程和计算机对人的身心及生存所带来的改变和冲击更是既让人振奋又让人困惑莫名。这些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多少现成的答案。而要求马克思为我们活在今天的人预备下一切解危济困的“锦囊妙计”,也只能证明我们作为马克思后人的无能乃至退化。我们必须自己拯救自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已经过时,恰恰相反,它在充斥着纷繁而喧嚣的各种话语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它所具有的“思”的品质:指向事物根本的穿透力。就认识和解除当代人类生存困境而言,我以为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它为我们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辩证生存观, 即从人的生存活动自身的矛盾及其螺旋式展开理解并批判地对待人的生存的基准和思路。人在世生存的一切问题可以说都源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表明了人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自我肯定,只有把自己作为手段才能成为目的,只有使自己对象化才能使对象人化。因而,一般说来,人的生命历程在走向人化、自由和进步的同时必定伴随物化、苦难和牺牲;人类社会现象总是具有对立、悖反、双刃效应,人的选择也因而往往处在两难之中。人的对象性活动决定了人要活着就要自找“麻烦”,因为有“麻烦”而感伤失望,或者想通过取消人的活动的对象性而一劳永逸地消除所有的“麻烦”,那就是不懂或不敢正视人的生存实情。但是,这并非说人在生存活动中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收益只是八斤半两,人类永远不会有实质的进步。其实,人的生存活动所具有的以对象为中介而自生成自相关的循环结构,不是封闭而是开放式的。人固然首先要依赖对象并将生命力量贯注于其中,从而与对象互相作用互相改造,但最终则会换来对象对自己的适应和自己生命力量的提升。如果说正是人的活动使人的在世生存陷入困境,那只不过说明这种活动未能成功地建构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从而使人的生存的开放式循环出现缺环而难以为继。不管造成人的生存困境的具体原因有多少,就人是活动的自觉主体而言,人显然应当批判地反省和调整自己活动的取向和方式,努力在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采取辩证的观点和批判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和处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它让我们充分重视人的生存条件, 特别是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这些人的生存的“前提”。人的在世生存的现实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生存的条件性,包括人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由自己创造的社会条件。而既然人的生存直接依赖于自己的活动及其对自然条件的利用和改变,人当然更应当重视社会条件尤其是人的社会性的生存能力的提高。人的生存条件不仅制约着人的生存,而且支撑着人的生存;在世生存的人只有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人从自然中的解放和人的社会解放。因而重视生存条件既是要求我们客观地看待生存的受动性、有限性,同时也是为了现实地而非抽象地发挥人的能动性,按照人生存的价值必要性和条件允许的可能性来推进人的生活。马克思之所以在人的生存能力中特别重视人的“生产能力”,就是因为人的生活消费及其质量直接决定于人的生产的性质和水平。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前提,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只会有贫穷和普遍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要为争取生活必需品而斗争。反之,只有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地域性的个人才会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人们也才能最大限度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身。所以,马克思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P68。)。当然,建立共产主义的意义不止于经济, 它是全面地重构人的生存的前提,为人的生存创设新的游戏规则,从而能够使人按照自己自觉自由的“本性”来生存。可见,重视人的生存条件,尤其是人的生产能力、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是对人的生存进行“前提”反思的结果。我们今天探讨生存问题在理论上最为需要的,也正是对当代人类生存方式进行“前提”性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指出:“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被消灭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P497。)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就是变革构成中国人生存障碍的那些“过于狭隘”的“前提”吗?
(3 )它的社会视域仍然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涵盖当代人类生活,其思想资质仍然具有透视当代人类生存问题的能力。今天,整个世界越来越具有互依性和一体性,虽然并非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所说人类历史将完成于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但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的确正在形成。其实,马克思早就看到了世界市场的前景,也早已充分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应当说,资本“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P393。)这样一种“文明作用”,对于那些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度的进步来说,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也要充分地注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资本”对于人的社会生活是推动者,也是破坏者;它唤呼出了巨大的生产力,而又使之成为制造人与人分裂和人与自然对立的手段。今天,由市场经济所引发或助长的人的物欲横流、狭隘自私、生存斗争、精神迷惘、心灵空虚比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严重得多了,正因为如此,诸如毒品泛滥,邪教横行才成为世界性现象。马克思当时所痛感的人类“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问题,仍然有待于当今人类“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并非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远未成为一个共生共荣的和谐的“生存共同体”;而应当是批判和尽可能地限制导致人类分裂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大力发展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文化产业,改变人的狭隘自私的物欲取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摸索出真正可行的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亦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此而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探索“第三条道路”,都是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可贵的努力。而以计算机为依托的“因特网”的普及,对于打破各种人为的封锁,开发人们的文化生活和公共生活空间,无疑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重新解读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维度和思想时,我们也早就注意到在马克思身后出现的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注:西方存在主义(包括“生存哲学”)各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基尔凯郭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与萨特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差异,海德格尔甚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属于“存在主义”。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它们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思想倾向进行评析。)。产生并兴盛于20世纪前、中期的西方存在主义,由于出自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尤其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因后果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和反应,所以更加鲜明地表现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反映了生命个体在世生存的无助和无奈;同时也力求通过对人的生存情态和内心世界的深入剖析和开掘,显示个体生存的新的可能并确立个体生存的意义。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和探究更为内在也更具现代性,所以它的确更为接近我们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和马克思的思想比较,应当说也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合理性。它的某些论述是对马克思某一观点的具体推进,有些看法则与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互相确证的关系。但是,马克思的生存哲学思想和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的理解在逻辑起点上就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揭示和解释也各有其特点和侧重;在某些方面两者可以互补,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就有可能构成对立。如果说,前者更为重视人生存的客观的社会的方面,后者则更为重视人生存的主观的个体的方面;前者认为人虽然在社会中会发生异化,但也只是在社会中才有自由,后者认为人在社会中往往被“平均化”,成为个性消失的“常人”;前者重视的是人生存的生产能力和社会规则,后者重视的则是人生存的自我选择的主观体验;前者重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后者重视的则是人生的差异、偶然和不确定性;前者看重人的感性,但同样重视理性,后者则质疑理性,信任并推重非理性;前者充分肯定工业和科技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和解放作用,后者则尖锐批评科技和现代化作为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前者对人类有一种最基本的信任,这个信任来自于人的生存的实践批判性,后者却因为人类的利己本能而对人深深地怀疑失望,要么就在感伤和浪漫之间徘徊;前者对人类有一个进步的基本信念,并指出了人走出动物式“生存斗争”状态的道路,后者则对人类的前途感到迷茫,也只能让人的心灵在信仰的维度中得到安慰。当然,这种比较并不全面,因为双方自身也有前后期的变化,并且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对人生存的理解和识见也必定打上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因此,它们必定具有互补和互斥之处,据此并不能判定孰优孰劣。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生存论思想在总体上还是比存在主义高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显赫一时的地位在六十年代被结构主义所取代,就说明了它只是从个体和主观方面看待人的生存的思想局限,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因为它重蹈了我们前面所批评的实体性思维方式的覆辙。而我们认为,结构主义和作为其批判者的“解构主义”也仍然是在寻找继续推进生存论哲学的切入点,并且其理论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当代西方人的生存问题之中。因此,认真地研究西方的存在主义及其后来的各种西方哲学并批判地汲取其一切合理的因素,也是我们在今天开掘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思想的需要,更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存哲学所不容忽视的理论课题。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