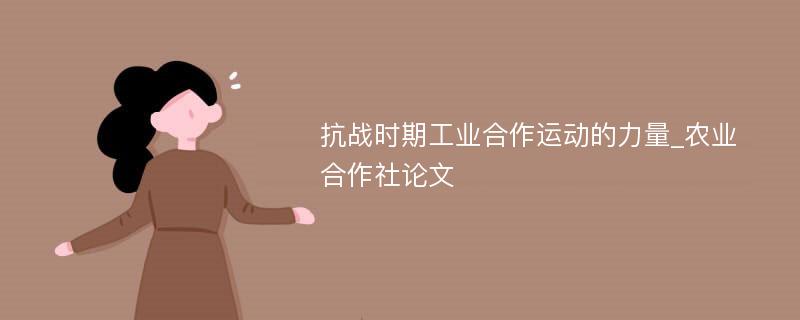
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力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合运动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抗战时期工合运动的缘起、组织结构、工业品类、重要成就和管理精神,论述了国际友人对工合运动的贡献、国民党当局对工合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及工合运动在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状况,系统展现了工合运动的历史概貌及其巨大力量。
关键词 工合运动 缘起 组织 力量
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但战争也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中国到处都显示出了反抗日本的力量,工合运动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工合创办人之一斯诺明确说:“到1938年时,中国如果不是沦为一个只有农业和牧业的国家,那么,我们也不会想到要创办工合。”
一
工合的创始人路易·艾黎、尼姆·威尔斯和埃德加·斯诺,为了增强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决定把逃到后方的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便发动工合运动。这一运动得到宋庆龄、周恩来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和鼓励。卡尔大使写了介绍函,将工业合作的计划介绍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看到这个计划也表示赞助工合,国民政府行政院拨款50000万元,作为推广工合的经费。1938年7月艾黎被任为工业协会技术顾问,他迅速集合了一批有才干的年青人,建立起机构,设在汉口,后迁至重庆,以合作专家卢广绵为总干事,孔祥熙为工协理事长[①a]。
工合是一种生产救国团体。按照他们拟定的计划,工合分三道经济防线,第一道为最大的单位,设于中国的西部、西南部和西北部,每个合作社都利用较大的机器,雇佣多数工人从事生产。第二道防线,设在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组织单位较大,利用半手工半机械从事生产,发展轻工业。第三道防线,设在战区,组织单位最小,利用比较容易移动的工具或机械,活动于战区之间,以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为主,也称为游击式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有两种特殊的功用,即:1.能够供给军队或游击队所急需的物品;2.成为各种经济组织的中心,将制造品供给农村民众,以防止接敌区变为日本货物的市场。他们设想,以第二种组织为主体,在全国建立3万个工业生产合作社。
工合是很吸引人的。从1938年8月第一个合作社在陕西宝鸡成立,半年时间就建立起西北、西南、川、康、云南5个办事处,成立了197个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社员达6000人以上,贷款120万元,合作社的门类有50多种。到1940年6月,工合区域已遍及16个省份,在陕、甘、晋、豫、鄂5省成立了14个事务所,3个指导站,组织合作社361个,社员4528人;在湘桂黔3省,成立事务所13个,指导站2个,合作社187个,社员2201人;在赣、粤、闽、浙、皖5省,成立事务所20个,指导站3个,合作社299个,社员3690人;在川、康两省,成立事务所15个,指导站5个,合作社467个,社员6378人;在云南,成立事务所3个,合作社40个,社员475人。在全国广大地区,都可见到有三角形的工合标志。据斯诺考察:“到了1940年10月初,工合在16个省建立了2300个小工厂,有7个工合分部对这些小厂进行技术指导。从游击区到敌人的后方和中国的极西,从蒙古高原到云南高地,都分布了这些小工厂。首先建立起来的是手工业、纺织、印刷和交通运输合作社,后来又办起了小铁矿、铸造场、煤矿、金矿、简陋的机器厂、面粉厂、造纸厂、制糖厂、煤油厂、化学品厂、玻璃厂、出版社和电器厂,以及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车和帐篷的小工厂。有25万人依靠在合作社里劳动为生。此外有4万人在家里从事劳动替工合制作毯子,供中国士兵使用。”[①b]艾黎1941年7月到香港时所描述的工合状况,在工合发展的数目上和斯诺所讲的稍有出入,减少了100个,在区域上则扩大了两个省份。艾黎说,工合事业全国现分布及于川、康、云、贵、湘、桂、赣、闽、粤、浙、皖、陕、甘、青、宁、晋、豫、鄂等18省,共有事务所及指导站80余所,合作社2200余所,社员总数约5万人,连同工人雇员,及各级工作人员,共有20余万人。各区现有资金总数约1000万元,每月之生产总值已达2000余万元。这两者相比较,数目字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了工合组织的惊人发展,大约一个星期以25所的速率出现着。到1943年年底,全国工合组织约3000个。这个数字距原计划3万个的目标甚远,但已显示出它的力量。各种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作坊和工厂,大体可分以下几类:
1.纺织染工业——有织布、纺纱、麻织、丝织、毛织、毛巾、毛编织、毛纺、线毯、缝衣、织袜、针织、织带、漂染、毛毡、棉线、丝线、刺绣等项。
2.机电工业类——有机械、铁器、织布机、铜器、五金等项。
3.矿冶工业类——包括翻砂、钨铁、炼铁、铸锅、铁矿、煤矿、锡砂、采钨、淘金、硝磺等项。
4.化学工业类——包括造纸、制糖、中药材、烛皂、油墨、油漆、酒精、松脂、卫生材料、西药品、硝酸、榨油、代汽油、制革、电池、火柴等项。
5.陶瓷工业类——包括陶器、瓷器、玻璃、砖瓦、石灰、耐火砖等。
6.食品工业类——包括糕饼、面粉、碾米、糖果、酿造、罐头、制盐、豆粉等。
7.交通工具类——包括造船、运输车等项。
8.其他工业——有印刷、笔墨、度量衡、藤竹器、木器、建筑、木炭、卷烟、雨具、伐木、弹花、油蒌、牙刷、蚊帐、制绳、染纸、油纸、药棉、布鞋、油灯、油漆、布、轧花、锯木、服装、麻鞋、粉笔、制帽、织席、纽扣、棕器、皮箱等项[②b]。
工合生产合计大小业务140余种,其中纺织染工业约占二分之一,化学工业次之,约占七分之一,冶矿工业约占十五分之一,食品工业约占二十分之一,杂项工业中的鞋袜服装等约占十分之一。总的比例是,以较小工业为主体,日常必需品占四分之一以上,规模较大的矿冶机电等工业不过十分之一。
工合组织所以有了这样突出的成绩,是因为它聚集了1000多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经济学家、科学家、会计员、各种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共同推动着这一事业。它把失业工人、流亡难民、荣誉军人以及抗战家属组织起来,利用当地原料,进行加工制造,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来满足军用和民用之需要。这不仅使农产品获得销路,也使工业引发了农业,促进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互发展,既稳定了社会,也充实了国防经济力量。
组织工业合作社的手续既简便又严格,依法定有7人即可向工协会办事处接洽,经工协会负责人分别考核,认为确可以从事于某一种工业者,即由工协会领导。在开成立会、选举经理负责人之后,即进行缮成业务计划书,内容包括该社组成,每月需若干原料?可出品若干?能得多少利益;开办时需购若干工具?经工协会技术、合作、会计3股审查,始进行贷款,按各合作社的性质及需要决定数目,年息8厘,分长短两期。贷款成立,即需取保,并向当地政府立案,工协会也派指导员赴该合作社协助一切。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生产单位才算圆满成立。工合赚得的利益分给社员,大伙都是合作社的主人,也都是股东,自己管理自己,社员都具有健全的独立精神。
二
工合协会的基金来自各方面的捐助和政府银行的贷款。1939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美国主教何明华为主席,斯诺、艾黎、普律德和港澳爱国人士钟秉锋、郑铁如、何东及国府要员宋子文等20多人为委员。陈翰笙任秘书,陈乙明为会计。他们在国外开展募捐活动,以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纽约、伦敦、马尼拉、香港也都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或称工合促进社。纽约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①c]。工合曾得到美、英、新西兰等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捐款。据1940年10月出版的《实业通讯》记载,菲律宾华侨捐助法币215000元,英国伦敦中英合作事业促进会主席白尼斯募集英金10万镑,爪哇巨商华侨林氏捐助10万元,美国救济中国平民顾问委员会及美国基金团各捐法币2万元,继又捐助法币25000元,总共收到海外援助基金38万元又10万镑。国民政府中、中、交、农4行的投资为,贷东南区100万元,重庆中国银行贷四川工合200万元,陕西金城银行及甘肃省银行、甘肃中国银行及农本局工合金库等贷西北区工合款数为2935000元,广东省行贷粤省工合200万元,工合基金总数达到3000余万元。
国际热心人士的捐款,截至1940年已有500万之谱。本来指定这批款项的2/3用于敌后游击区,特别是敌后根据地,但许多捐款都被国民党方面扣留,没有运到敌后。国民党内的CC派头子陈果夫和陈立夫把工合运动当成一种威胁,起初以为工合成不了事,未曾料到工合竟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组织,因此大为不快,说工协总部安插了赤色分子,说艾黎、斯诺也是赤色分子。孔祥熙为改变工合性质,掌握工合领导权,把所谓簿记员和会计员塞进工合,许多工合组织很快就形成反差极大的两批工作人员,一批是真正做工作的,另一批却是拼命喝酒、制造政治谣言、向陈立夫和戴笠打报告的。“工合”中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到逮捕甚至杀害,如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就先后有18个“工合”妇女工作人员被捕,被关进西安集中营。因为国民党内顽固分子极力破坏工合,一些地区的工合为了生存曾付出了血的代价。工合所走的路也是一条充满崎岖的路。它是在斗争中前进的,现按1939年工合所划分的4个区域,分述于后:
(一)工合西北办事处。该处工作区域为陕、甘、宁、青、绥5省,下辖15个工合分部,即西安、南郑、凤翔、天水、兰州、沔县、双石铺、陇县、宝鸡、榆林、安康、韩城、耀县等。截止1940年底,共有524个社,社员10245人,贷款为304万元,每月平均生产总值为724万9千余元,参加工作的雇员,工人共有113407人,其中包括技师706人,雇工76298人,雇员8402人,练习生30000人。1941年,工合西北区又与陕西省动员指挥总部合作成立陕西省动员实验县,划定洵邑、淳化、商南、韩城、耀县为实验县,在这几个县中,推行生产有关前方将士需要的工业产品,及当地民众日常应用品,并加生产工具的制造。
凡具有工合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人们的生产观念也发生变化。
西北地区的工合是最活跃的,其贡献也最大,所生产的产品,占全部工合产品的半数。在西北,宝鸡和汉中之间的工合,特别兴盛,出现了几座工合城。
宝鸡那时是陇海路西端的终点站,从山西、河南逃来的难民很多,从武汉撤退到西北地区的工人,也多集中于此。卢广绵和流落到武汉的一位上海技工夏威,由武汉经西安到达宝鸡后,住在一个鸡鸣的小客店中。他们见难民们在小土坡上搭着席棚,安下灶,居住着,但生活没有着落,许多人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办法。人口增加的很多,市场商品又极度缺乏。卢感触很多,夜不能寐,思索着如何在这里组织工业合作社。次晨,在客栈两旁看见十几个河南来的打铁工人,各自独立地在打铁,制造农具。卢广绵便启发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团结起来合作,“如果你们能够集中起来合制、合卖、合做饭,那么工合协会可以解决你们当前的最大困难”。铁匠们立即表达了愿意合作的心愿,成立起铁器合作社,这就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成的第一个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联合盖房,协力工作,工协对其制品加以改良,使其不仅能制造农具,还可以供给军事需要[①d]。卢每一天从早到晚,在难民们面前演讲,在大街小巷里贴上标语:“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难民的伙伴”、“开发西北富源”、“努力生产”等等,这样一来,访问者都蜂拥到鸡鸣小客店来了,卢应接不暇,不到两个星期,织袜合作社、制皂合作社、炼铁合作社、药棉合作社、印刷合作社等,相继成立。由于宝鸡县县长王丰瑞全力支持,东北救亡总会的一些青年人(主要是东北大学学生)的积极帮助,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诚给工业合作贷款5万元,金城银行周作民也同意贷款,西北工合因此获得了发展的良好机会。不到两个月,已成立80多个合作社。不到一年,许多作坊和工厂已能制造鞋、帆布袋、衣服、机具、肥皂、颜料、电器用品、粮食、军装、帆布床、帐篷、毯子等。合作社有自己的商店、批发部和零售部,出售200多种不同的货物。还有自己的学校和训练班,以及它自己的装着本地仅有的淋浴设备的俱乐部。宝鸡遂成为工合运动的发祥地。
宝鸡各种合作社生产的产品通过商店出售,营业额很大,平均每天零售5000元,批发生意更大。1940年斯诺在该地小住时,军队方面就买了10万元的药水纱布和2.4万元的布匹,随后又订制了25万条羊毛毯子,3万磅绷 带,3万磅药水棉花,几千件大衣和担架。
双石铺的工合,特别繁荣,有50多个合作社,该城中有一条路改名为工合路,开办了工合小学、托儿所、保健所,还有一个技术训练学校。保健所,即工合医院,规模不大,仅有6张床位,是该城仅有的一所医院。医师唐文和是一位教会学校出身的青年。这所医院曾给几千名工合工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几百个乡下人种牛痘、打预防伤寒和预防霍乱的针。在该城附近有一家合作社机器厂,主要从事纺织机器的制造,曾为其他合作社制造了许多机器,也制造过盒子炮和步枪,一个月内造了7万颗手榴弹。后来,国民政府禁止它制造军器,工厂的机器被运到南方去了。该工合分部还包括一些煤矿、运输、皮厂、羊毛织物厂和一家造纸厂。造纸厂是当时最大的一个。
工合汉中分部在中共党员李华春的领导下,颇有声势。李是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生,时年27岁。他和他的职员18个人,包括会计人员、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依照合作办法,同住在一个宽大的宅子里。这些人的工资很微薄,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有自豪感,精神昂扬,以全力指导着这一地区的工作。成立不到6个月,就组成了51个合作社,制造棉布、绸、皮件、墨水、纸张、肥皂、蜡烛、机器、机器零件、玻璃、编织物、衣着、化装品,以及足够摆满一家百货公司的零星杂货。汉水两岸用原始办法从流沙中淘金的人们,多数也组成了合作社,共有467个。1940年,金子在重庆卖500元一两,当时由于中国银元跌价,使淘金工作获利甚丰。
工合总是将社员的利益、生活状况、生存条件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汉中附近有一个以江浙工程合作社命名的小木厂,社员只有7人,都来自江浙。他们的借款股本共2400元,经营了5个月,每个月都做1000元的生意。当时到苏联去的西北公路上,需要中俄文路标牌子,他们愉快地承担了建造任务,感到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斯诺曾考察过江浙工程合作社,记录下这个工合的状况:
社员们共同住在一个清洁的宿舍里,床是双层的,隔壁一间是俱乐部,它把读书和娱乐的设备合在一起,有一个合作书籍的小图书馆,和一个该区合作报纸的订存册子。一天的工件表和社中的规程一同陈列在显著地位,墙上挂着通常的劝勉性质的标语:
工业合作社是真正工人的工厂!
工业合作社是抵制日货的方法!
清洁就是卫生,康健才可做更好的工作!
工业合作社是民主主义的实行!
在我们的社会上,只有做工的才得吃饭![①e]
这些标语表达了工合的精神和工合的职责。
上述三个城市的工合是很出色的。其实,每个地方的工合,都按照自己所处的情势的特殊条件,在工合道路上猛进。譬如青海、甘肃的北部和陕西的北部,是羊毛的出产地,工合在这几个地区就发展毛纺工业。全国军用军毯也大都由这些地区的工合来承制。榆林毛纺织业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该地是塞上汉蒙贸易的一大中心,茶、马、羊毛、皮革等交易很盛,特别是羊毛贸易。但毛纺织业一直很落后,仍停滞在数世纪以前的原始状态中。1939年8月,工业合作社榆林事务所成立,榆林工人开始贷款组社,很快成立3个毛织合作社,1个皮革工业合作社,2个制鞋合作社。3个毛织合作社共有毛编织机16部,每日可织军毯6000余条,这就部分地改变了以往落后的生产状态,榆林和外界的贸易也增强了。当时西北区工合承制百万余条军毯,全国工合协会便和贸易委员会商妥,将贸易委员会设在榆林的专卖处所收买的羊毛,转售工合协会,榆林工合事务所收发当地汇集收买的羊毛,运送至西安交货取款,于是巨量的塞外羊毛,一批一批地在骆驼的背上,从蒙古沙漠,搬到西安的毛织厂里[②e]。
因为工合的建立,科学技术也得到推广,譬如工业合作研究所兰州分所,从骨中提取阿摩尼亚和磷酸盐,制造制刷和制钮用的净骨。硝及制革的方法也有了很大改善。工合国际协会捐款在西北建立的机器社,制造了许多改良的机器,特别是军毯社所用的梳毛机和纺织机,来帮助其他工合的技术改进。梳毛机是引用水力或木炭引擎发动的,纺织、压光和漂染的方法,改进的很多,所制出的军毯,非常精美。
工合西北办事处的显著特点是设立供销机构,组成合作社联合会,互相帮助,解决疑难问题。他们制造的许多东西已代替了舶来品,如干电池、电筒都能自己制造。
西北工业合作协会设立了妇女工作部,伦敦经济学校毕业的任珠明为主任。她认为,把逃难到大后方的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可以成为国家的一宗资产。她和她的助手共5位姑娘活跃在陕甘两省的广大土地上,办起了17所小学,招聘义务教师,除了教儿童识字以外,还教数学、地理、简易卫生学、战争发展、自由歌曲和合作原理。通过儿童获得妇女的信任,又通过妇女取得社会的信任。她们组建了两个妇女训练学校,教会1000多位妇女运用改良纺车和布机的方法,吸引了6000多名妇女参加到21个合作社中。她们还办了一所高级的训练学校,教授妇女关于纺织业技术方面的知识和组织合作社的方法。甘肃省为军队制造军毯、纺毛的工作,就是该妇女部组织荣誉军人、日军俘虏和农村妇女们担任的。
西北工业合作协会与工合联合会还组成合作金库,把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储积在金库里。西北工合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获得了全国的称赞。
(二)工合西南区办事处。该办事处设在湖南邵阳,所辖的范围是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后来该办事处又划为湘桂和滇黔两个办事处。自从原在上海电力公司任职的赖福裕领导着工业合作委员会的技术班来到湖南西部查勘该地原料时起,湖南的工合就开始了。这一地区的合作社组织分两大类,一类是合作场,是规模较大的组织,如火柴合作场、玻璃合作场、造纸合作场、紫棉合作场等。其中,火柴合作场系租用前长沙和丰火柴公司机器,工人约有六七十人。另一类组织是合作社,规模较小,分城市组和乡村组两种。城市组所制造的是各种日用品,象毛笔、自来墨水笔、纺织、印刷、草鞋、缝纫、手巾、布袜、皮件、皮革、干电池、洋蜡、肥皂等。乡村组设立于乡镇,大都从事纺织和缝纫等工作。除此之外,办事处还做了三件事情:1.组织妇女手工业训练班,先在邵阳举办织布、织巾两组,训练3个月。后又开办荣誉合作社,以救济失业妇女;2.在邵阳创办小规模的托儿所一间,代各合作社妇女抚育幼童;3.组织各合作单位成立合作社联合社,以期增强生产力量,规定每一联合社包含17个合作社[①f]。
西南区办事处自从划分为湘桂和滇黔两个办事处后,在桂林、柳州、全县、新化、贵阳、昆明、大理等15个地区建立了事务所。湘桂区的合作社最多时有300个,滇黔区有100多个。
(三)工合东南区办事处。该办事处设在江西赣县,所辖范围包括江西、浙江、安徽、福建和广东5省。在办事处之下,又设许多分办事处。如江西雩都、宁都等地都有办事处。浙江、安徽地区在金华、丽水、衢县、临海、嵊县、浙西、屯溪、经县、潜山、立煌等县,推动棉纺织、造纸、水产、榨糖、樟脑油、煤铁、榨油、丝织、麻纺织、制革等工业。广东省工合在曲江、南雄、始兴、乐昌、连县、罗定、德庆等18县,成立事务所。闽省工合在旅菲侨胞援助下,在连城、邵武、德化、建阳、上杭、永春、龙岩等地组织7个事务所。东南区工合在1939—1940年间共有28个事务所,组织的工合最多时有700多个单位,社员8000多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颇多贡献。如韶关的机器社制造了不少农具和碾米机、磨面机、印刷机,使许多工业合作社由手工业生产转为机器生产。
(四)川康区和云南区办事处。该办事处成立较晚,但重庆、荣昌、成都等地的工合运动一出现,就颇引人注目,发展很快。在重庆成立的有紫棉制造、印刷、五金等合作社。万县有志中肥皂工业合作社,盘溪有代汽油工业合作社。荣昌县工合成立仅6个月,就有53个合作社,制造麻布衣,从事印刷业务等。成都的工合组织,因为有金陵大学一些教授和学生的协助,发展更为顺利,如工合织物合作社能接受150万条羊毛毯的大批定货。成都及附近各村,1940年约有5000多妇女在纺羊毛。当地工合的职工,每天能出产1200条毯子。成都附近的一个合作机器厂,有150个工人,主要从事布机和纺锤的制造,以满足羊毛工业的需求。
三
工合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是很不容易的,但经过艰苦努力,还是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工合运动,颇有声势。1939年3月,西北工合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曹菊如任主任,黎雪任技术股长,努力推动工合运动。在边区各地先后开设纺织、榨油、造纸、肥皂、缝衣、鞋子、植物油、运输、木工、煤矿等工业合作社数十处,并计划将原有的137处生产合作社一律改称工业合作社,直隶全国工协西北办事处。延安工合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因为工合很注意技术的改进,所以各类工合产量都在不断增加。如安寨振华造纸工业合作社过去因原料缺乏,产量日出只两千余张。工合后,为适应边区的实际需要,特大量购置稻杆、麦杆草、破布、糜草、小米杆以及山上的野草等造纸原料。在技术方面,对碾浆、选料、拣料、提浆、拟纸、晒纸等,悉心改良。不仅出品质量提高,每日产量也增至1万余张。安寨王家河纺织工业合作社,是1939年7月成立的,有纺织机3部,每人可产纱2斤,每人每日可织袜8双至一打,每天每人能织布一丈左右。1939年9月,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斯诺、全国工业合作协会委员孟用潜到延安视察工合运动,对边区工合取得的成绩,备加赞许。孟说,边区一地,工合数目已占全国总数六分之一,为工业合作服务之人员亦最多,惟贷款一项,边区占全国四百分之一。斯诺答应在国际委员会的捐款下拨款帮助边区工合发展。1939年底,在国民党压力下,重庆方面断绝拨给管理经费,边区工合事业面临危机。此时边区政府给以大量资助,国际工合拨出马尼拉华侨的捐款10万,也由西北工协转来,出现的紧急情况才得以度过。
1940年1月中旬,艾黎来到延安考察。1939年他已曾来过一次,前后两次都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其推进工合,予以极大鼓励。此次艾黎参观了工合延安事务所所属的化学、制纸、鞋袜、油灯工业合作社,然后讲道:“时只一年边区工业大大发展,所有成品如肥皂、毛巾、布匹等较诸外面机器工业出品品质尤为精良。”继之谈到此后边区工业合作事业发展的方向与前途:
边区矿产丰富,如煤、铁、石油极应开采,他如三边之毛产亦丰,毛织工业亦急需建立,虽边区经济困难,但有优良的政治环境,应继续努力,前途大有希望。工业合作事业在全国其他各地正蓬勃发展,但仍时时受有某些方面的阻碍。事实证明,一年来工合在全国各地曾组织了大批的伤兵与难民参加了工业生产,建立了1400处小型工厂,部分地供给了抗战需要,支持了长期抗战。现在,敌货仍在某些地区充斥,一方面抗战,一方面又大量购买敌货,这真是矛盾的事。目前中国应大量从事小型工厂的建立。[①g]
艾黎对根据地的赞扬,对国民党政府的尖锐批评,对中国的热爱溢于言表。
在晋东南,首先在阳城成立了事务所。1940年,又在晋城成立了事务所。同年10月,这两个事务所合并,孟用潜为主任。这一地区的合作社发展到44个,贷款20万元,培养技术工人约500多个。工合的种类有:造纸6个,纺织5个,煤窑5个,印刷2个,军服2个,肥皂5个,制鞋4个,运输1个,造丝2个,磨面4个,食品1个。工合曾供给军队15万双鞋,纸厂每天出纸56000张,每月出纸280万张,解决了阳城、晋城、济源一带的用纸问题,毛巾肥皂也能保证自给。1941年9月底,鞠抗捷率领工合协会晋东南事务所一行16人,进入太岳根据地内。年底,在沁县、沁源组织30个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与工业有关的运销合作社。首先发展纺织业,再发展造纸、肥皂等化学工业[①h]。后又派东复到太行区辽县开展工作,组织了21个合作社,有200多个工人。工合在晋东南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太行工商管理局和冀南银行给予了很多赞助。
在苏浙皖地区,江西有遂川工合事务所,安徽有茂林事务所,曾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受到叶挺的称赞。
工合在全国各区成立了5个培黎纪念学校,其使命在训练青年以工业技术和组织能力。
根据地的工合运动,所以得到发展,在北方是因八路军的保护,在南方是因新四军的保护,而全部经费是由海外华侨和美国人士的供给。寄给延安的捐款,是由陈翰笙通过廖承志经由上海银行转去的。延安方面经手收款的是李富春,每转去一笔钱,都会收到李富春签收的回条[②h]。工合是在征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才坚持下来的。
和晋东南相连接而属于河南省的几个县,以及河南西部的几个县,为济源、孟津、禹县、洛阳、鲁山等地,到1941年时,也组织了130多个合作社,社员2000余人,每月产值约40万元。
纵观各地工合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先有后,有起有落,甚至遭到破坏和摧残。在历史的动荡的痛苦的进程中,工合运动应该说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表现出了神奇的力量,但是就是这样的组织,也触动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神经,使其未能顺利地发展,距离它要达到的目标相差很远。
注释:
①a 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99页。
①b 斯诺:《我在旧中国三十年》,第113—114页。
②b 千家驹:《抗战以来的经济》,1941年8月20日《华商报》。
①c 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①d 徐盈:《巩固工业经济国防线》,1938年12月14日《大公报》。
①e 《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第180—181页。
②e 《榆林的毛织工业》,1941年11月7日《华商报》。
①f 何俊:《一年来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东方杂志》,第18号第34页。
①g 《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
①h 杜直先:《工合在太岳》,1942年1月17日《新华日报》。
②h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