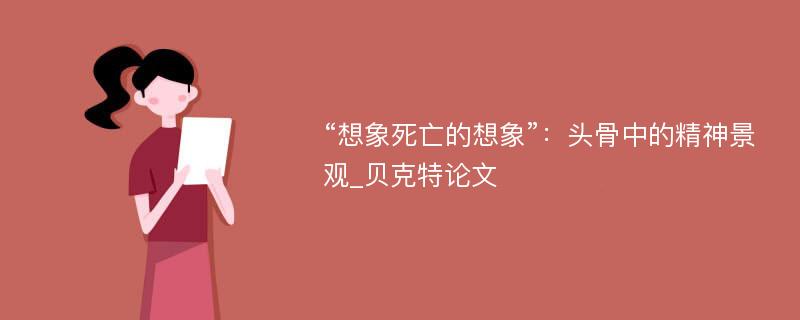
《想象死亡的想象》:头盖骨里的心灵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头盖骨论文,景观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萨缪尔·贝克特(Samnel Beckett)是20世纪举世瞩目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他所有的作品都重复着一些同样的主题,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普鲁斯特特征的变形者。贝克特通过形式的相互渗透和媒介的戏仿对连贯的主题进行变形,变形的方式因作品不同而异。用A.阿尔瓦雷兹(A.Alvarez)的话说,他的全集“就像一块大理石——洁白而光滑,但一个区域与其它区域接合处的色泽纹理却精细复杂”。①我们注意到,在贝克特的散文体作品中,用第一人称叙事自我毁灭式地追求确定性止于小说《是如何》(How It Is,1961)。从1961年起,贝克特开始写一些更短的小说,或称为“文本”。其中有《想象死亡的想象》(Imagination Dead Imagine,1965)、《够了》(Enough,1966)、《迷失的人》(The Lost Ones,1966)、《乒》(Ping,1966)、《无意义的文本》(Texts for Nothing,1966)、《无》(Lessness,1969),等等。除了《够了》,所有这些短篇文本都使用第三人称,那种自己给自己讲述过去生活的声音现在变成一种咕哝,一种《无意义的文本》中所谓的“记忆和梦幻的轻声细语”。“仿佛作为叙事者的贝克特已经摈弃了他早期发现自我时的那种自命不凡,那时他以第一人称单数显耀地介入到自己的虚构故事中。”②相反,现在的贝克特以第三人称的传统手法取代了第一人称,为我们奉献了一系列叙事的意符。
贝克特称他这些短小的晚期小说或散文虚构故事为“残片”(residua)。它们由被遗弃的更大的作品演变而来,发展了一种极简主义艺术。这些文本类似剧本的舞台说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但其结构却是精雕细刻的。它们长度上的缺陷因密度上空前的浓缩而得到补偿。然而,贝克特晚期的作品过度地暗示了寓言因素,以至于这些因素让人什么都想象不到。从泛指意义过程发展到意义,贝克特后期小说的意义不断膨胀,在日益广阔的同时也愈发微弱。那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些文本呢?本文把《想象死亡的想象》作为分析的对象,通过贝克特典型的边界隐喻,来展示他以语言和叙事的美学文本侵入到内心边界的冒险旅程和他描绘的心灵景观。
《想象死亡的想象》只有1500字长,可谓“小说的残片”或“空间旅行的幻想曲”。③它创造了一个高和直径三英尺的白色的圆形建筑物。这个小型穹顶矗立在一片平坦的白色旷野中。在贝克特看来,在一片白色的包围下几乎看不见的这一白色圆形建筑物是天地之间剩下的全部东西。从外面看,这个球体像头盖骨一般坚实:“敲击吧,到处盈满硬实,在想象中它发出的声音就像骨头的响声。”④实际上它是中空的。包围在这个圆形建筑物/头盖骨中的是一对男女的白色裸体,他们以子宫中婴儿的姿势背对背、头对着屁股地躺着。光在白与黑、温度在热与冷之间起伏波动,从炙热的白色到冰冷的黑色,中间经历了各种灰度和热度变化。这是一幅终极的世界景象。《终局》(Endgame,1957)的头盖骨房间外的原子弹爆炸后,那种荒凉景象已经沦为“这一陷于白色空间之中的微小垂死的球体,这是想象力在犹如一片空白星系空间里内心始终不忘的最后一个形象”。⑤它沉默而空虚、冷漠而无特色,是丧失个性的意识的内心景观。但倘若把圆形建筑物/头盖骨看作内在与外在之间的边界线,我们就可以和贝克特一起窥视精神的微观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边界线上自我与他者、理性与荒诞尚未分离。
该文本始于许多法国小说的主人公所处的困境:“哪儿都没有生命的迹象,你说的。”看不见的叙事者以巨大的信心用“呸,没什么了不起的,想象力还没死”抛弃了他们唯我论的失败主义。再度出现从无限中获得实质性进步、赢得更多阵地的期望。叙事者声称,需要一切就是一种强劲的想象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以数学家的精确在头脑中建构起它关于人类存在的图像。几何学理论用在这里为胚胎中的男女标定位置、测量尺寸,用时间把现象记录到秒,同时计算温度变化,进行科学实验。为了给他的图像的可靠性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贝克特借用科技语言:直径、直角、半圆、数字和字母层出不穷。然而,从一开始另一种应该是死亡主体的想象的语言就不协调地侵入到伪科学的词语当中。因此,在光与热的升降之间也会插入“长短不等的停顿,从瞬间到在某个时候,其他的地方本来会是一段永恒”。实测时间在经验时间面前畏缩不前。数学的确定性被用来建构不确定之物,建构“一个仍在抵制持久混乱的世界”。“渴望的诗性语言暴露了毫无希望的主体支持虚假知识的偏见。”⑥随着怀疑逐渐深入,贝克特将他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运用置于更加荒唐的背景下:“从看得到的表面判断,两个身体不胖不瘦,不大不小,似乎完整无缺,状态甚佳。”叙事始于客观陈述,止于自我戏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性的形式开始干扰圆形建筑物/头盖骨的形象。光与热的波动作为永恒和无限的表现形式开始影响感觉者。视察已非轻易所能为之,因为记忆歪曲了他的反应。静止与运动之间的反差“对于为相反情况而震惊并且仍然记忆犹新的人来说,一开始就觉得十分突出”。习惯作为我们“一种麻木的不可侵犯性的保证”抹除了过去。最后,痛苦的人性的形象让观察者难以承受。起初稳如磐石的圆形建筑物/头盖骨及其占据者在最后一句难忘而短暂的美的语言中化为泡影。幻觉的吸引力势不可挡,诗性取代了逻辑,怀疑驱散了科学的确定性。感觉者否定了他对现实的认知,成了自己缺陷的牺牲品。开头几行对进步那么自信的展望再度证明不过是循环而已。恰如文本的标题,叙事又回到它的开端。叙事的自我戏仿最终破坏了它反面乌托邦的筹划,悬置于乌托邦与反面乌托邦之间。
整个叙事还有一种精雕细作的美,每个白色的肉体躺在白色的半圆中,时隐时现,冷热、黑白交替。他们未动但镜子显示他们在呼吸,双目圆睁,“一眨不眨地瞪着”,但只有一次两眼目光交汇,“大约十秒钟”。他们控制着不哆嗦却“大汗淋漓而且冷若冰霜”。贝克特使用的降格陈述简直令人震惊,“两个肉体似乎完整无缺,状态甚佳”。即便不能牵强附会地认为这是交媾的性形象,把他们想象为一对夫妻却顺理成章,他们以一种非拥抱和非睡眠的姿势搂在一起。贝克特把他们想象得太成功了,想象力死亡了似乎也能想象到他们之间没有爱。然而,在这个文本中我们同样感到贝克特所有作品里总是包含着的那种奇特而矛盾的乐观主义调子,也看到他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毫无结果的尴尬处境”。“三部曲”中那些爬行的人物终于来到他们的憩息地,唯有呼吸和眼球的运动在泄露他们持续的心灵生活。“贝克特的想象力企图生产人类存在的现实的拟像。”⑦这是一种在圆形建筑物中原原本本地现实的心灵的内心景观,一种头盖骨景观。《想象死亡的想象》必须经历的那种光与热的波动也是我们的心灵必须经受的昼夜、寒暑、意识与无意识、生与死的交替运动。
贝克特的科学的叙事者就圆形建筑物、它周围的环境和它的内容提供了透过望远镜和在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景象。从远处看到的圆形建筑物与对内部躯体的近距离的观察展现的是外部视野与内在景观之间的对比,贝克特还结合客观视域和主观视域的对比、表面现实和内心现实的对立,迫使读者透过他(叙事者)的眼睛观看并体悟只有内在视域才是唯一有效的参照系:“经历完满虚空中的缺席之后又奇迹般地被重新发现,它已不再是原样,这是从这一视角看,但又没有别的视角。外在地看,一切一如既往……但是,进来吧……”穹顶内这对男女的姿势恰似两个莫菲背对背地绑在两个不同的摇椅上,然后命令他们相互注视。但他们无法相互感知,只是被叙事者和读者所观看,而在这里眼睛或视觉/想象等同于内心世界。在《电影》(Film,1967)的介绍性文字当中贝克特写道:“在逃离外部感知时寻找非存在,结果在自我感知的无法逃避性中崩溃……寻找感知者不是外部性的而是自我,这一点直到电影的结尾才明了”。⑧《想象死亡的想象》也发生了感知者和被感知者之间的同样的混淆,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认为其中“研究者的眼睛接受的是从根本上讲对他的对象产生一种病态兴趣的东西。他怎么看反映他的性格,而且可想而知,他所看到的在他身上产生了‘颤栗’,旋即又被掩盖起来”。⑨根据布莱恩·芬尼(Brian Finney)的解读,颤栗马上流向读者:“倘使说两个作为其环境的典型的受害者被迫面对关于人生存在的真理而感到痛苦,那么也可以说读者兼观察者面对同样的真理时一定同样是痛苦的。”⑩
贝克特终生都在寻找呈现精神现实的文学手段。从他早期小说《普通女人的梦》(A Drean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1992),我们便可以发现努力栖息于陌生之地对他来说是情有可原和理所当然的:
心灵阴暗而寂静,像个病室,像个烛光里的停尸房,挤满了幽灵;心灵最终是它自己的避难所……;心灵一下子获得暂时解救,不再是坐卧不安的身体的一个附属物,理解之光倏然陨灭。心灵坚硬而痛苦的盖子封闭了,心灵中突然一片昏暗;不是睡眠,还不是,也不是梦魇,大汗淋漓,惊恐万分,而是一种清醒的大脑以外的昏暗,身份不明的天使穿梭往来;他身上唯有坟墓和子宫的暗影,这里正是他的死亡的和未出生的幽灵出没的地方。……在暗影中,在隧道中,心灵驶向子宫坟墓,然后是真实的思想和真实的生活。……在隧道中他是一阵阴郁的无端的思绪……(11)
显然,对贝克特而言,艺术家心灵的微观世界是用语言在头颅的图像中传达的;头盖骨是“心灵的盖子”。心灵必须从外在世界的意象中获得滋养。换而言之,通过再现可见的事物,以外界客体作为想象的跳板,揭示不可见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关于莫菲心灵三个区域划分的概念,光明与黑暗对立运动的意象,《终局》中头盖骨似的背景,“三部曲”中子宫/坟墓的意象,《出自一件被抛弃的作品》(Froman Abandoned Work,1958)对白色的迷恋以及《够了》中那对男女,现在都在《想象死亡的想象》中融于一炉,使贝克特能够探索感觉、存在、写作活动等一些他最关注的东西。《想象死亡的想象》应该算是莫菲心灵的第三地带,那是“形式的涌流”,“这里只有混乱和纯粹混乱的形式”。(12)在混乱的精神区域,惯常的时空遭到破坏,结果一个生命周期的两个端点合二为一,时间停滞。同样,在《想象死亡的想象》中生与死融于一体,圆形建筑物中的两个人不是胎儿就是垂死的躯体,或者可能既是胎儿又是垂死的躯体。这种胎儿木乃伊在出生前白热化的沉静和死后冰冷的黑暗之间摇摆。由于这两种状态同时存在,在两者之间流动就构成了人生的炼狱。通常在贝克特的作品中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状态,如黑暗与光明、陆地与大海的意象,就是心灵的微观世界的特征。(13)
在《想象死亡的想象》中白色的穹顶是唯一的物质现实,也许它是一个巨大的眼球,也许是一个心灵世界。如果被感知就是存在,那么被想象,即在心灵之眼中被看见,也是存在。当然,除了暗示一只巨大的眼睛和一个头盖骨,白色的圆形建筑物也代表两个胎盘中的人物居住的子宫或者坟墓。劳伦斯·哈维(Lawrence Harvey)注意到在贝克特的诗歌中,子宫和坟墓都成了转变想象力的意象。(14)圆形建筑物可能只是想象力的建构,证明想象力并没有死。因此,《想象死亡的想象》可能是贝克特想用书面形式证明:《无法称呼的人》(The Vnnamable,1953)之后所遭遇的小说创作的瓶颈并未阻断他的想象力。我们再次面对典型的贝克特讲故事者的悖论,即虽然无可表达,也没有表达手段,却千方百计地叙述一个故事。不过这次失败的艺术家也许成功了。
叙事者总是强调圆形建筑物只存在于心灵之中。这是因为贝克特发展了叔本华的观点,即如果想象死亡,那么外在世界便消失,留下唯有内在的残留物。(15)一切“消失”之后,仍然存在的就只有叙事者和读者的内心世界,而通过一种想象的行为我们必须一道用虚无来建构起一个新的外在世界。《想象死亡的想象》暗示我们省略四样东西——岛屿、水面、苍天、绿地。但为了给想象力提供可把握的东西,它还必须提供其它的事物、其它的名词:“空虚、沉默、炎热、洁白”和“地面、墙面、穹顶、肉体”。自然世界由四种成分来象征;圆形建筑物中的人为世界由四种物体和四种特性构成。
当贝克特想促使人们注意他作品里的超现实主义部分时,他使用了一个特殊的词:死亡的想象。布勒东的标语——精神自动性、痉挛的美——强调超现实主义癫痫病似的一面:灵感让人觉得陌生,变得不由自主。布勒东为僭越生与死的边界而心醉神迷,喜欢想象水晶的自发生长,海底石珊瑚的香味:“这里无生命的东西毗连有生命的东西,其密切程度使想象力对表面充满矿物质的形式发挥充分的联想,并沿着矿脉复制如下过程,即如何辨认我们从石化的山泉取下的鸟巢或一串葡萄。”(16)贝克特也以死亡想象的形式对被矿化的人类形象精雕细刻并乐此不疲,在他笔下,人类僵死的感觉断断续续地出现“极其微小的颤抖,旋即又被平息下来”。
“贝克特通过显示想象力对事物产生的影响来激活它们……他能独辟蹊径地创造不确定的、临时的、可溶解的事物。”(17)但是死的想象与活的想象有多种不同。“活的想象制造的形象是在物质世界有指称物的形象,是负载着可理解的意义的形象。对比起来,死的想象不具备点燃意义的力量。可以把死的想象当作淘尽了所有燃素的象征物,它看起来往往异常奇特,但要寻找奇迹定会无果而终。”(18)在1937年给埃泽尔·考恩(Axel Kaun)的信中,贝克特勾勒了一套反象征主义艺术的理论,这是在“想象”一词夸大的意义上走向扼杀“想象”重要的第一步。象征主义作为一场艺术运动本意是要抵制话语的、散文的东西,以趋向沉默。但贝克特发现象征的手法阻碍象征主义者实现其目的,即实现马拉美渴望的一页白纸。真正沉默的艺术是撕开词语的表面向词语深处窥探,破除象征,摆脱象征要求清晰的呼声。贝克特的论文《普鲁斯特》(Proust,1931)显示了他得益于象征主义手法,但他也从普鲁斯特那里学到了某种对象征物的反感,厌恶意义过剩,而这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一直是一个反主题。长期以来,人们注意到贝克特的小说处处沿着自传的边缘而行,也许他的目的不在于回忆青春而是要使其去象征化、非审美化,把它调和成音乐或一批卵石收藏起来。对于贝克特来说,必须把象征变成“自动象征主义”。(19)“必须让它(象征)的触角把攥着的世界松开,代之以攫住分离中的事物,捍卫孤立中的事物。”(20)同时淘汰了模仿和象征的小说似乎弃绝一切精神慰藉。“贝克特自娱的主要方式是锤炼文本反映自身内容缺失、中心缺场的过程。”(21)
在这一过程中,贝克特用一种内心经验进行创作,把他心灵的经验从他一度描述为“无理数的子宫”(22)的虚无变成了词语的存在,使这种虚空的经验表现为一种想象力和直觉的创造力的源泉,凭借这种力量他深入到未出生和死亡的世界。贝克特特别专注于濒死状态、死前状态和出生前状态。正如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指出的那样,这表明贝克特使自己置身于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的一个边界。古代世界处处是精神,现代世界处处是物质。贝克特的意识代表那种模棱两可的阶段,它寻找物质是为了不使精神混同于物质,是为了找到一种方式好把生活看作是在固体性和非物质力量之间保持的共存关系。(23)
窥探贝克特构筑的古代和现代世界的边界,我们发现一处别有洞天的内心景观,那是死亡或枯竭的想象为我们提供的。《想象死亡的想象》表明,古代和现代世界之间那种物质与精神的边界是一种不生不死的状态,动与静、生与死难以分辨;而动态和静态之间的边界点最容易唤起人们的想象和联想,并具有最丰富的内涵和最多样的变化的可能。《想象死亡的想象》效法瓦特的建议,证明虚无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说得煞有介事:语言想象出什么来的同时又创造了虚无。贝克特在词语的物质性表面打洞,企图看到它后面的虚无。结果,他穿越了内部与外部之间本无厚度的边界。贝克特就是用这种词语填充来省略真实世界和想象力死亡造成空虚的空间,即心灵的微观世界。
对于伊瑟尔而言,贝克特的文本指出了意识和想象之间的鸿沟:“一个阻断它自身的意识,一个只能做圆周循环运动的想象力——这些都是一场我们不再知道是否要结束或开始的游戏的最后残存物。这些残存物也只不过是将自身强加到语言之上的动态的空洞;只有那消耗自身的语言才能给想象以清晰的表述。”(24)那个鸿沟需要无穷尽的认知沟通而被体验到,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死亡的想象”是贝克特刻画心灵的微观世界或头盖骨内部的美学或文本原则。我们甚至应该说:“贝克特矢志创作突出‘想象力’问题的文学作品,标志着他为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所做出的主要贡献。”(25)心灵的微观世界一直是贝克特作品描绘的领域,如果说在《莫菲》(Murphy,1938)中白色的圆形建筑物还只是被客观地描写,那么直到《乒》里作为叙事的背景它已经反复多次地出现,《想象死亡的想象》因此在贝克特的后期小说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它使我们得以窥探头盖骨里面的景观,它再现了死亡的想象的虚无,发展了一种能够呈现虚空图像这一悖论的语言,再现了一种摹仿坠入想象的风格。
注释:
①⑤A.Alvarez,Samuel Beckett,New York:The Viking Press,Inc.,1973,p.123,p.126.
②⑥Katharine Worth,Beckett the Shape Changer,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p.75,p.76.
③Hugh Kenner,A Reader's Guide to Samuel Becket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73,p.178.
④Samuel Beckett, Six Residua, London:John Calder (Publishers) Ltd.,1978,p.35 .后文所引《想象死亡的想象》的内容均来自该书,不再逐一注出。
⑦John Richard 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Beijin: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859.
⑧Samuel Beckett,Cascando and Other Short Dramatic Pieces,New York:Grove Press, 1968,p.75.
⑨John E.Grant,"Imagination Dead?" in James Joyce Quarterly,8 (Summer 1971),pp.340—341.
⑩Brian Finney,"A Reading of Samuel Beckett’s Imagination Dead Imagine,"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17 (April 1971),p.70.
(11)Samuel Beckett,A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Dublin:Black Cat Press,1992,pp.38—40.
(12)(22)Samuel Beckett,Murphy,London:Pan Books Ltd,1963,pp.65—66.
(13)Lawrence Harvey,Samuel Beckett:Poet and Criti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32.
(14)Melvin J.Friedman ed.,Samuel Beckett Now,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84.
(15)G..C.Bernard,Samuel Beckett:A New Approach,New York:Dodd,Mead &Go.,1970,p.80.
(16)(18)(20)(21)Daniel Albright,Beckett and Aesthe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p.13,p.13,p.13.
(17)Bruce Stewart ed.,Beckett and Beyond,Buckinghamshire:Colin Smythe Limited,1999,p.148.
(19)Samuel Beckett,Proust,New York:Grove Press,1957,p.60.
(23)Paul Davies,Beckett and Eros:Death of Humani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33—38.
(24)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家定、汪正龙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25)Ed Jewinski,"Beckett's Company,Poststructuralism,and Mimetalogique," in Lance St,John Butler ed.,Rethinking Becket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p.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