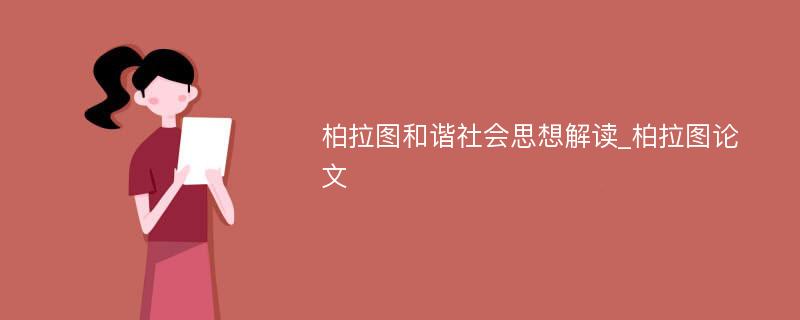
柏拉图的和谐社会思想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2)02-0090-06
一、柏拉图和谐社会思想的产生
柏拉图的和谐社会思想与雅典帝国由盛趋衰息息相关,公元前431-前404年爆发的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惨败而告终。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使希腊各城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陷入全面而深重的危机之中。各城邦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使希腊城邦普遍遭到破坏,城邦颓危败落,各城邦内部由于土地和财富的集中,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城邦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诸多社会弊端日益暴露,社会内外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奴隶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亦愈演愈烈,政治动荡不安,原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优良的道德传统不复存在,城邦社会精神生活解体,种种邪恶行为充斥着整个社会。伯罗奔尼撒战争标志着雅典的奴隶民主政体从繁荣的顶峰开始走向衰落瓦解。在此情况下,柏拉图以其哲人的睿智和思想家深邃的目光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他针对城邦奴隶制面临的深重危机,为了挽救濒临衰亡的奴隶民主制,以理念论为核心,以“正义”为原则,以斯巴达的君主政体和古埃及的种姓制度为样本,融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哲学为一体,设计了一个公平正义、各尽其职、各得其所、稳定和谐的理想城邦国家。
早期希腊以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学家,从自己的哲学出发,或多或少地论述了和谐问题,这些哲学巨人多视角对和谐问题的追问与反思,为柏拉图系统地研究和谐社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应该说,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概念的是毕达哥拉斯,他将数视为万物的本原,认为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源自于数,宇宙万物的和谐即为数的和谐,提出数的和谐观点。毕达哥拉斯在研究数,特别是在音乐的研究中,发现数的一定比例和关系产生和谐,天体之间的和谐也如此,得出了“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1(P133),“一切都是和谐的”[1](P36)结论。宇宙中和谐无处不在,整个宇宙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和谐是普遍的、一般的、必然的、绝对的。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和谐”思想扩展运用于考察人伦社会和灵魂现象,提出美德、友谊、爱情和灵魂等都是和谐的思想。赫拉克利特向毕达哥拉斯提出了挑战,他以“永恒活火”的动态思维方式超越了毕达哥拉斯仅对数量作抽象静止规定的静态思维方式,用“对立和谐观”扬弃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和谐的深层秘密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对立和斗争,事物总是由其内部的对立和斗争向它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实现统一与和谐,真实的必然的和谐是由于这种内在对立和斗争造成的。这样,赫拉克利特在深刻的层面直接指向了和谐的本质。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哲学从自然哲学的尽头,转向对“善”、对“自我”、对“人”和“社会”的探询。苏格拉底的和谐思想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他个人的命运是同雅典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了城邦追求善的理想,尽管他的城邦是以死刑成全了他的理想追求。他从生活实践、道德方面提出他的“理论”主张:“认识你自己”。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能仅仅以为他有感觉和欲望,而在于人有灵魂,能够追求善。他的“认识你自己”开辟了一条重理性、寻求普遍性知识之路,就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道德的本性,从而确立一种普遍而又稳定的道德体系,只有这样的道德体系才能确保和谐的社会秩序。
二、正义是缔造和谐社会的总原则
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寻正义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现的首要价值一样。”[2](P1)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第一次系统而深入地诠释了正义问题,《理想国》的副标题是“论正义”,围绕着正义这一核心问题,柏拉图以其整全的思维方式详尽地探讨了城邦政制、财产制度、婚姻、家庭、哲学王、教育、文艺、宗教、伦理道德、男女平等、法律、城邦和谐等诸多社会领域,提出了很多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在柏拉图的视野里,正义是理想城邦的立国之基,是统摄个人德性的最高伦理范畴,也是缔造和谐城邦社会的总原则。柏拉图将正义分为个人的正义和城邦国家的正义,二者都符合正义的理念,是密切相连的。由于在国家存在的东西在每个人的灵魂里都存在着,而且数目是相同的,城邦的品质和习性都来自个人的品质和习性,通过探讨个人的正义去追寻城邦国家的正义是柏拉图诠释正义问题的基本路径。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包括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理智用于思考和推理,为整个灵魂而谋划,在三部分中起统帅作用,激情是理智的辅助者,欲望是满足和快乐的伙伴,其本性是贪婪,欲望必须受到理智和激情的监管与控制。如果个人的灵魂这三部分“各做各的事”而互不干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部秩序井然,彼此和谐相处,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人,他不会去做邪恶之事,他会以自己正义的行为参与实现城邦国家的正义。相反,如果个人的灵魂这三部分彼此争斗,相互干扰与混淆,那么这个人的灵魂就“不正义”,他就会做出种种邪恶的事,从而破坏城邦国家的正义。与之相应,城邦国家应具有智慧、勇敢、节制三种美德,何谓“智慧”?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把智慧解释为整体秩序的创造者,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智慧理解为“考虑整个国家大事”的治国知识,体现在军人护卫者身上的勇敢主要是指一种通过法律和教育培养而形成的理智信念,节制是指对某些快乐和欲望的调控,是做自己的主人,节制是面向城邦国家的全体公民并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和谐。由上观之,柏拉图是基于哲学层面,从整体上来解释城邦国家的美德问题,智慧的整体性要求奠定了正义的哲学基础,整体性正义成为正义的内在必然要求,也就是说,正义的指向必然是智慧、勇敢、节制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与和谐,正义就是智慧者智慧,勇敢者勇敢,节制者节制,正义的终极秘密就是通过彼此限定、节制所达致的整体和谐。因此,正义成为最能使国家“善”的德性。作为建立城邦国家总原则的正义,它是指“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3](P154),也就是每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这样便有了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国家正义,国家有了正义,建立了稳定正常的秩序,社会也就和谐稳定了。反之,违背这条总原则,就“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就是“不正义”,社会也就不和谐了,这对城邦国家是最大的危害。
三、实现和谐社会何以可能
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在于其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三种人的和谐相处,一个正义的国家就是一个和谐的国家,就是一个善的理想的国家。问题是如何使一个理想的国家成为现实?和谐社会何以可能实现?就此,柏拉图设计了实现和谐社会的路径。
(一)通过社会分工实现和谐社会
柏拉图以人的自然“禀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严格的社会分工体系。社会分工是城邦国家产生、发展的自然基础。他认为,城邦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城邦国家的起源是为了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足需要的结果。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3](P58)。城邦首先是起源于满足人们衣食住等基本的生存需要,由于人的生存需要是多方面的,单靠个人有限的力量是无法办到的,因而需要大家相互帮助,城邦必定要有社会分工,将个人的产品提供出来,于是就有了农夫、瓦工、纺织工、木工、鞋匠、铁匠等生产劳动者。他强调,每个人应根据他的天性专搞一行,这样每种产品都生产得又多又好,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求。从经济层面看,社会分工直接地提高了城邦的劳动生产率,丰富的物质产品不但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还产生了大量的可以用来交换的剩余产品,进而有了市场和商贸的产生和发展。从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分工直接或天然合理地将城邦的社会等级划分出来了。柏拉图认为,随着社会成员需求层次的提高,城邦由一个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低水平城邦逐渐发展为“一个繁荣城邦”。在繁荣城邦里,不仅要有基本的生存必需品,还要有较为高档的生活消费产品及奶妈、理发师、厨师等提供的生活服务;不仅要有生产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还要有一批城邦文化人创作文化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随着从事非生产人口的增多,城邦之间势必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而导致“战争”,城邦的一个新型阶层护卫者(军人)由此产生了,随后有了城邦的最高层次的“统治者”。这样柏拉图就将城邦国家里的社会成员划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或治国者;第二等级是军人护卫者,他们是统治者的助手,执行统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级是农、工劳动者和商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等被统治者。他强调必须按照人的天性安排社会成员的职业,极少数的统治者要运用他独具的智慧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全局事务进行整体的谋划安排,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条件;护卫者的天职是秉承勇敢的德性,承担卫国的重任,抵抗和驱逐入侵之敌,保卫城邦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与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对内执行执法和警察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任务,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军事保障;生产者要发扬节制的美德,运用他们的特定的“技艺”创造物质财富,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为了证明这种社会等级的合法性,柏拉图还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善意的”故事:社会成员原本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白银使他们成为是护国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铜铁使他们成为生产者。一般说来,一个人属于哪一个等级,他的子女就属于哪一个等级,但也有例外情况发生,尽管父子天赋相承,但难免有金父生银子或银父生金子等互生情况出现。受其“圣人政体”思想影响,柏拉图特别提醒人们应注意天赋的混杂和等级的变化,要知道后代的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并要求统治者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他们放到与他们本性相对应的位置上去,切实保护好同族的纯洁性,以保证理想城邦国家的永世长存。
(二)在哲学王的治理下实现和谐社会
柏拉图精心设计的“理想国”怎样才能实现?他认为关键在于要有“哲学王”来治理城邦:“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4](P214-215)。他首次提出的“哲学王”不是说哲学家一定就是国王,这里可以宽泛的理解为集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要么是真正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要么是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真正掌握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哲学王能够成为理想的统治者是因为哲学王自身具有优秀的品质学识,具有其他阶层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一,哲学王是掌握了理念论哲学的城邦领袖。他从理念论出发,认为由于哲学王是以其理性思维方式直接注视可知的理念世界,因而只有哲学家才能真正懂得治国之道。因为唯有获得真正知识的哲学王才能认识事物的本性,才能够区分出一个正义的人和正义本身。掌握了真正的治国知识,面对纷纭复杂的城邦现象,哲学王就具有透过事物的流变去把握其本质的能力,凭借哲学王高超的知识,提炼出城邦的理念,为现实城邦的发展提供目标,引领城邦国家前进的方向,制定治国的措施,使人们永远按照城邦的本来面貌建设城邦,“使城邦最本质的东西世世代代熔铸在城邦的文化之中,内化为公民内心的道德准绳,成为公民行动的指南”[5](P194)。其二,哲学王具有卓越的品质和禀赋,能使人们保持完美品质,实现社会和谐。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认为人不会有意去做坏事,人作恶是无知使然,如果真正掌握了善的真知,人就会有善的美德。哲学王具有卓越的禀赋,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热爱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等美德,是德行最完善的人,哲学王心怀并关注事物的原型,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哲学王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国家培养和造就的“蜂王”,是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有神授的灵感,人格高洁,他已经掌握了正义、美、善的理念,他有能力理应为城邦公民培养美德指点迷津,帮助城邦公民改造品行,促使城邦公民的灵魂得到升华,治理出团结而不是内乱的公民集体,给城邦国家公民带来整体幸福。其三,哲学王能克服现存政体的弊端,实现正义的政体。他认为在正义国家中,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并认为现存城邦的政体、管理模式和理念都是坏的,一切都是恶的和非正义的。城邦的出路在于使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使国王成为哲学家。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关注和热爱真理,对一切存在进行无情的质疑、反思和批判,渴望得到知识的全部。只有哲学王才能帮助人们区分知识与意见、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美与丑,也只有哲学王才能依据他所拥有的理念拯救城邦的危机,哲学王既是城邦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城邦最完善的护卫者,哲学王肩负着领导、改造和完善国家的神圣使命。柏拉图相信,由哲学王来领导城邦就可以实现理想国家的全部制度,引领城邦国家走上正义的道路。
(三)教育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造就“哲学王”和城邦统治人才的必由之途是教育,因为掌握理念哲学的统治者(哲学王)治理城邦,帮助“囚徒们”实现灵魂转向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详尽地讨论了教育问题,他甚至将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统治者)的教化手段,才能重新塑造人性,培养出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柏拉图系统设计了一套理想的教育体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一是使举国之人,皆能敬神孝亲爱友,培养好的公民;二是造就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他将教育分为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两类,初级教育的对象是城邦公民,在于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高级教育的对象是城邦统治者和护卫者,在于培养他们在城邦政治统治的位置上为公民服务。依照他的课程设计,所有十岁以上有公民身份的孩子都要接受初级教育,学习音乐和体育,学到十七八岁。音乐用以陶冶心灵,通过音乐的熏陶来达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属于知。体育用以培养健全的体魄和刚强的意志,属于动。音乐和体育都是用来改善心灵的,训练好的运动员如果没有心灵的改善,那就与野兽无异。柏拉图十分强调对孩子进行美德教育。他在《法律篇》中以雅典来客的口吻说出如下一番话: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获得金钱或强壮的体格,或者甚至某种不受理智和正义引导的知识才能的训练。倘若一个人接受过如此这般的完全训练,他会被认为没有受过教育,是粗鲁的和无教养的。反之,柏拉图心中真正的公民教育“是从童年起所接受的一种美德教育,这种训练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的渴望,这个完善的公民懂得怎样依照正义的要求去进行统治和被统治”[6](P27),通过初级教育,用城邦制定的道德和法律来教育他们,消除父母不良习惯对他们的影响。从20-30岁的公民中选拔少数优秀青年接受高级教育,学习算术、几何学、天文学、谐音学等数理科学知识,以培养他们的理智。然后再从30-35岁的公民中挑选合适的人完整地学习辩证法,以培养他们把握哲学理念的理性能力,这是为未来的统治者开设的课程,它是最高等级的学习科目,是最高等级的真正的知识。经过层层严格筛选的候选统治者在35-50岁年龄段,还须参加社会公务,积累社会工作经验,丰富社会阅历,这样的社会实践考验需要15年,此时已是50岁以上的年长者,其中只有社会实践和哲学研究两方面都最优秀者才能成为城邦统治的“哲学王”。柏拉图特别申明,每个公民不管他们的出身和性别如何都应接受教育。如果公民从小就受到好的教育,就会成为明智的公民;如果军人受到好的教育,就会成为勇敢的士兵;如果统治者受到好的教育,就会成为有智慧的统治者。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相处,到达理想的社会状态。
(四)通过改革政体实现和谐社会
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城邦的长治久安,柏拉图还对当时的各种政体加以分类考察,比较其优劣并提出改革方案。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是由哲学王执政的国家,即“圣人政体”。然而,“圣人政体”因血统的混杂和统治者在生育子女上的失误而成为一种理想。在他看来,现实中存在的荣誉制、寡头制、平民制、僭主制四种类型的政体都是有缺陷的政体。圣人政体的内在原则是智慧,其他几种政体分别是荣誉、财富、自由和专制。由于这四种政体的顺序是根据偏离国家正义的程度而不是根据时间顺序划分的,因此,它们在对国家正义的偏离上,使它们向坏的方向演化,一个比一个严重,到了僭主政制,国家不正义达到极点。于是历史成为一部不断恶化、坠落的历史。不断恶化的政体更进一步反衬了柏拉图王政理想国的伟大、纯洁、美好和至善。为了实现社会和谐,防止统治集团两极分化与腐败,柏拉图主张废除统治阶层的私有财产和家庭,实行公有制度。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统治者和护国者不应有任何经济利益,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都集中在同一双手中对政治的纯洁和效率都是致命的。因为统治者的灵魂早已从神那里获得了神圣的金银属性,如果再与人间的金银混在一起,统治者阶层的灵魂就会受到玷污。所以,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的私有财产,实行集体食住制。至于第三等级,柏拉图主张他们拥有自己适度的财产,防止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困,这样整个国家既不太富也不太贫,疆域大小适中,就能够保持和谐统一。在婚姻、家庭、妇女问题上,柏拉图主张废除固定的婚姻关系和性关系,而代之以按国家的规定定期地、有节制地交配,在统治阶层废除家庭,实行公妻制。这一则利于优生,二则利于城邦的统一、内部的和谐,再则利于人们无私奉献和忠诚效国精神的培养。通过废除小家,全城邦就融合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五)通过德性和法律兼治实现和谐社会
目前学界几乎普遍把德治视同于人治,将德治、法治对立起来,以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只讲德治,只重视道德王国建设,轻视法治以至于不谈法律及法治,仅仅是到了晚年的《法篇》中才论及并重视法治及法律[7](P91),但是,如果我们以德治、法治对立的视野来解释柏拉图的治国方略,那么他的治国理念就已经被我们深度误读了。事实上,作为伟大哲学家和深刻思想家的柏拉图“从未对他的信念作过任何突然的改变”[7](P97),他对德治、法治思想认识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柏拉图认为法的本性有其道德基础,法治的原则在于全部美德。“德治”和“法治”并非绝对对立,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法中有德,德中有法,“德治”与“法治”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法治需以德治为基础,德治需以法治为补充与保障,两者相得益彰。在《理想国》中,他在主张实行贤人政制、以德治国、道德兴邦的同时,并没有因此否定“法治”,认为法的规范性、确定性、国家强制性有助于道德实现,在其德性治国的思想中包含有法治思想。在罗素看来“‘正义’这个名词在法律上仍然被人们使用着的那种意义……是更有似于柏拉图的观念的”[8](P154),而卡西尔直接指明正义“这个概念使柏拉图成为法治思想的奠基人和第一个捍卫者”[9](P80),“节制”的实质是指“一种守法的意向,或一种尊重国家制度和愿望使自己服从国家法律的精神”[7](P105),“勇敢”则被柏拉图诠释为“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4](P149)。在《理想国》中,尽管柏拉图赋予了智慧多种含义,但从社会管理层面看,总的来讲,智慧是对城邦事务管理本质的深刻洞察与整体把握,在《法篇》中,“智慧”这一内涵丰富的词汇便被具体化为法律,也许甚至可以说冻结成法律[7](P105),他甚至将日常生活中的音乐和健身术等制定为法律,认为“这些法律都对……公民的身体和心灵抱有好感”[4](P120),在教育思想中他提出应将德育、法律教育渗透在孩子的游戏、音乐、体育中,让孩子们成为品德端正的守法公民,促使他们健康成长。在《法篇》中,柏拉图深刻认识到法律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要让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从人类的主子,而要服从法律”[7](P97),因为人类的本性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因此人类须有法律和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甚至强调“在一切科学中,最能使人完善并且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法律科学”[10](P151)。在推崇法治的同时,柏拉图也给“德治”极高的地位。柏拉图将公民“守法”的法治和“公民道德修养”的德治结合起来,在他看来,依照美德的顺序,我们就会知道立法的最高原则,因为立法必须关心美德,关心人类灵魂的卓越。只要具备了美德,人们热切关心的其他好处必会随之具备。如果人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形成良好的品德,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相反,人们能自觉遵守道德并形成行为习惯,然后再制定和执行法律就不难了。“法治”下的德性(节制、自由、公正等)伦理视野是柏拉图治国理政的突出特征。在《法篇》中,柏拉图在节制、自由、平等、公正等一系列德性伦理范式中描绘他的法治国家蓝图,作为“法治”内在的伦理精神,这一系列德性伦理折射出柏拉图构建其“第二好的理想国”的德性思维方式。将德性精神渗透到法律之中,以德性思维方式的视角展开其“法治”范式的构建过程,这样才能弥补“写在纸上”法律条文的缺欠与不足。好的法律,需要有较高道德素质的人去执行,才能把遵守法律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自觉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节制、自由、平等、公正等德性范式是城邦实现法律化,并最终成为社会走向和谐有序的公民道德基础。总之,与其说从《国家篇》到《政治家篇》和《法篇》,柏拉图实现了从“德治”到“法治”的转变,不如说是柏拉图从更宏大的视野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相互融合与渗透,他在对智慧、节制、勇敢、正义等核心范畴的深刻诠释中,彰显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和谐、政治有序化的德治理念,还有自由、理性、秩序、民主等法治观念。我们看到,知识、美德、智慧等道德范式的真谛和法治的根本尺度、基本精神、价值取向在柏拉图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彼此贯通,相互协调,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法”、“兼治”成为柏拉图构建和谐社会并重的重要手段。
标签:柏拉图论文; 理想国论文; 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法律论文; 哲学史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