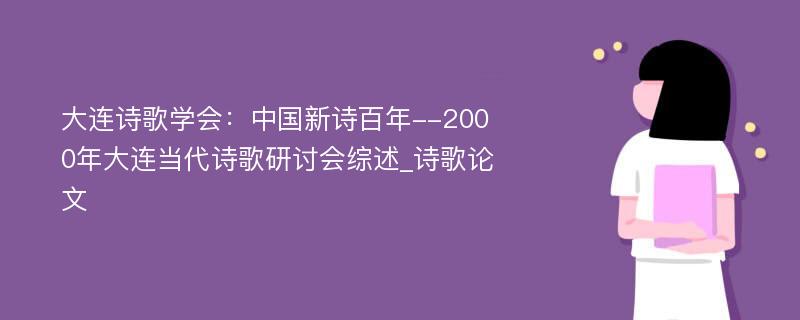
大连诗会:中国新诗百年绝响——大连#183;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连论文,绝响论文,新诗论文,中国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最后一周70多名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学者聚会于滨城大连,全面回顾中国诗歌百年进程,遥想诗歌未来,把一股强劲的诗性暖意注入了中国北方的料峭寒风。12月25日至27日,由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收获》、《作家》、《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山花》及作家山版社、《文学报》、《大连日报》周刊部第9家文化单位和企业联合主为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自1980年南宁诗会起,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诗歌走过了波澜壮阔的进程,它曾以敏锐、颤动的神经,启动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大潮,影响了几代人的心路历程。20年后,关注中国当代诗歌的各路精英聚会大连,使本次诗会堪称世纪末中国诗界的绝响。他们围绕着百年来中国诗歌的文学史贡献、诗与文化传统及全社会的关系、国际化背景下汉语诗歌的姿态与特性及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诗,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但可能更深入地发生在诗人内心,并潜在地影响人的灵魂。基于对我们的内心和灵魂的关注,文化周刊的最后一期拿出3个版面关注本次诗会。我们希望与大家一起以诗的方式来告别20世纪。
诗歌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虽然面临危机,但在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深处,她依然顽强地滋长着,弥漫着,渗透着,这种生命力产生了巨大的召唤作用,使严冬的萧条最终无法抗拒春意盎然的勃发生机。在这种意义上,世纪末举行的这次大连诗会,不仅真正构成了中国新诗的百年绝响,而且也堪称中国诗歌在新世纪发展的一个建设性开端。鲜明而突出的历史性和开创性特征,将把这次近20年来仅见的文学盛会及其具体收获载入史册,铭记悠远。
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着有关中国百年尤其是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诗歌语言的嬗变、诗歌理论的建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互动、诗歌与文化传统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贡献及地位评估、国际化背景下汉语诗歌的姿态与特性、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和多种可能等等,全面、深入地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对于中国现当代诗歌创作达到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在诗歌表现形式的创造、诗歌语言的本体意义的拓展和深化、诗歌艺术的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及其对民族文化、世界文学和人性共融的特殊价值等方面的突破性和历史性的贡献,以及对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启示,与会者都予以了全面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质疑。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评价
这是一个既有基本共识又体现出争议性的问题。首先发言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应当重视20世纪的中国诗歌传统,这一传统是经过“五四”而主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和建立的,当代诗歌的传统也由此而来(李欧梵的发言请见今日本刊D2版)。相比之下,北京大学谢冕教授的看法更为明确而乐观,他把百年诗史概括为从诗界革命开始,经“五四”新诗运动、革命新诗、新诗潮到后新诗潮等几个主要标志性时期,肯定新诗的发展是成功的。对于谢冕先生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先生认为,不仅要摆脱诗歌标准的“惟一”观,而且,以所谓的“多数”、“少数”定标准的观念也应当摆脱。她进一步质疑说,是否确实需要或能够用新诗完全代替旧诗(传统)的精神?并强调指出,将中国的汉语(语言)精髓注入新诗之中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新诗应当包容旧诗所达到的文化境界水平及经典性(郑敏的发言摘要请见今日本刊D2版)。《新文学史料》主编、著名诗人牛汉先生认为,只能说新诗已经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非完全取代了旧诗。新旧之间并不是纯粹相克的取代关系。这也是对“五四”式思维的一种反思。对于以上质疑,谢冕先生补充说,自己虽持乐观态度,但也是看不清前景;至于新旧关系问题,坚信只有新诗才是20世纪的中国诗歌,但新诗对旧诗也不是完全的替代,新旧之间的联系当然不能简单割断。
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从迄今已有的文学史书等方式这一角度发表了对当代诗歌遭遇的文学史评价的看法。他说,20世纪基本上是小说的时代,文学史书写基本上围绕或依据“核心概念”编码,如“改造国民性”等等,但这种方式对于诗歌的文学史书写则非常困难。因此,小说成为20世纪文学史书写中的主导性叙述内容,诗歌只能处于“次席”的历史和文化境地。北京大学副教授、诗人臧棣紧接着评论说,现在的文学史体制对诗歌写作造成了一种压迫感,进入文学史似乎是诗人的潜在目标,这种“文学史焦虑”对诗歌写作会构成某种威胁。诗人曲有源则明确指出,“文学史焦虑”其实是由批评家对诗歌的普遍性“失语”所造成的,其中暴露的也是批评家的尴尬。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对当代诗歌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他认为当代诗歌给各种文艺门类都注入了开创性精神因式,对此,文学史必须予以极度的重视。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陈超也认为当代诗歌迄今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恰当评价,而实质上诗歌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最大。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则指出,文学史写作受到体制性的规约,它是有限的,这也就证明了学院体制及其需求应当与创作实际进行最大程度沟通的重要性。
二、关于诗歌语言和汉语诗性的重新建构
这是一个主要突出诗歌语言特性的根本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新诗创作的历史和现状都说明了重建汉语诗性精神传统既是整个百年中国诗歌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语言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汉语诗歌对此的责任义不容辞,并且首先也与它自身及其发展直接相关。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认为,语言(活动)本身是一种“伦理行为”,诗人也是一种“伦理学的主体”,必须承担和履行自己的语言责任,投身于诗歌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种伦理责任的承诺,从此无可回避语言的挑战。对此,著名诗评家唐晓渡先生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语言伦理与承担语言伦理责任不是一回事,应当有所区别。诗人应当采取价值居中的姿态,先验的伦理意识可能会导致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无助于诗歌语言或汉语诗性的建立和表达。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诗人张枣则将中国诗歌的“汉语性”与现代性相沟通,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当代觉悟,那么这在中国诗歌中,将通过汉语的(诗性)内涵和特征来获得实现。在这种意义上,诗歌语言的建构也就必然地与现代性的获得同步并发生内在的密切联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任洪渊先生则主要从文学史上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方面论述汉语发展的生命力,他认为汉语具有“天赋的自由特性”,写作就是对汉语精神的展示,而世纪之交的当下,正是重新由诗人(主体)向世界展示汉语的时代,即中国诗歌语言重新建构的时代。著名旅法诗人宋琳的见解也是独出心裁,他说因为有“原始寂静”的存在,“倾听”便成为人的“内在要求”,这种“倾听”的欲求促成了诗歌(语言)的出现,因此可以说“语言生于沉默”,其中就含有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内容和生命本质因素。当代诗歌的语言建构应该关注汉语的内在诗性。徐敬亚提出的又是另一个尖锐而现实的问题,即汉语的世界境遇面临着“大民族、小语种”的事实挑战,所以中国诗歌语言的建构便不仅是属于汉语(诗人)自身的问题,而且也必须同时考虑更为广泛的世界范围的普遍性问题。这个话题自始至终都展开得相当丰富,有一点是可以完全肯定的,诗歌语言决不仅或主要是形式范畴内的问题。
三、关于诗歌的创作主体(诗人)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永骏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是“个人性”的行为,只有获得“个”的自觉,(诗人)才能找到“他者”的存在,而且这种行为并不是被“集体意识”所浸透的,而是“个人性”的自身认同的行为。在他看来,创作主体(诗人)在诗歌活动中的“个体自觉”意识是最首要的前提和条件。(是永骏的发言请见今日本刊D2版)。批评家谢有顺也强调了诗人主体因素在新诗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指出要从“内部”来探求诗人各种体验的主要原因(谢有顺的发言请见今日本刊D2版)。郑敏先生同样专门提出了“诗人的素质”问题。在徐敬亚和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等人的发言中,都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诗人及诗歌创作中的“真诚”问题,他们认为,真诚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要的;真诚与否,完全取决于诗人的良知和道德。在这一话题上,全体与会者的反响和共鸣最为一致。
四、关于读者问题和对诗歌创作的批评
读者远离诗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这也构成了当代诗歌几乎难以克服的一种困境现状。究其原因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从“私人化写作”和“审美公共空间”的关系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私人化”写作的极端表现是封闭了自我,隔绝了读者,甚至连批评家也只能面对“陌生化”的文本束手无策,因此,他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具有“审美的公共空间”意识,诗人要实行自我制约,其中既有文本调整的问题,还有心理调整的必要,批评家则需要“细读文本”,消除“陌生化”,促使读者进入或介入诗歌阅读领域,共同建立和拓展诗歌的审美公共空间。
北京师大教授王一川先生强调的是“泛诗”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纯粹的诗歌创作和阅读的严峻挑战。著名诗人钟鸣的看法是,诗歌写作含有“对话”的性质,但在对话者间存在着隐秘关系,语言、多元文化、时空对象等的限制,使诗歌的阅读显得困难重重,诗人能够做的只是努力增强诗歌的“激发”作用。批评家张柠是从网络角度探讨相关问题的,鉴于网络读者的庞大数量,他呼吁诗人们充分“亲近”网络,使诗歌成为网上读物。在研讨会上发言和其他的与会者还有张笑天、杨匡汉、董秀玉、芒克、李陀、叶兆言、程永新、宗仁发、蔡翔、林建法、张胜友、何锐、麦城、西川、孙绍振、南帆、王小妮、陈仲义、杨克、于坚、孟明、柏桦、沈奇、素素、朱文颖等。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会议不仅是多年来难得的一次具有高质量学术文化内涵的诗歌和文学研讨会,而且也是一次充满严肃理性精神、展示健康人文心态和表现丰富的诗歌、诗艺、诗学及诗人个性特色的文化会议,它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诗歌、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未来、面对世界的希望和自信。
2000诗歌意见
(中国·大连)
1.公元2000年12月24日至27日,由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收获》文学杂志社、《作家》杂志社、《上海文学》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作家出版社、《山花》月刊社、《文学报》社、《大连日报》周刊部等9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大连举行。7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和批评家在理解、友善的气氛中进行了近年来少有的自由的对话、交流。
与会者希望:从大连发出的诗歌“世纪绝响”,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从而对新世纪的诗歌实践提供建设性的推进。
2.1980年“南宁诗会”引发的诗歌争论,如今已成为历史。中国诗歌在近20年的艺术变革中获得了新生。而且,它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各门类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这情景与“五四”时期新诗的文体试验对当时新文学诸文体所产生的影响十分相似。新诗,在艺术变革中一直充当着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角色。
3.艺术思想的解放,促使中国新诗迅疾完成“多元共生”对于单一模式的取代。拥有巨大包容性的中国当代诗歌,使大多数诗人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创作,并习惯于这种各自独立的、互有差异的从容秩序。
4.中国诗歌目前仍处于危机和困境中。大连诗会充分关注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诗人生存、作品传播、批评互动等环节中发生的新的难度。
在此复杂背景下,诗人应以潜心的、非功利的、独创性的智慧,为矫正和提醒当代文明的偏执,坚持自身的使命。
5.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中国当代诗人应珍惜和体认百年来忧患和苦难所提供的精神资源,不断拓展当下经验,在创作中注重原创性和生命质感。
与会者深切感到:汉语的丰富表现力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进一步展现母语的魅力,是每一位中国诗人的职责。
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
2000年12月27日于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