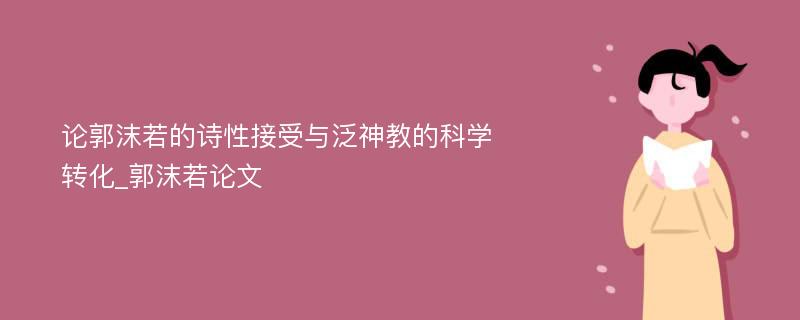
论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诗性接受和科学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泛神论论文,的诗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接受的主体性看郭沫若对泛神论的接受
郭沫若早期对泛神论思想的接受,早已成为郭沫若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有研究者已提出“什么是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应当“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点首先加以研究的”“顶顶重要的问题”。(注:见陈永志《郭沫若思想整体观》,第23页。)这样提出问题并努力加以解答,无疑体现了对接受主体的主体性即自主的能动性的高度重视。
所谓接受的主体性,是接受活动中的基本性质,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十分普遍简单的事实,即接受主体对象事物和信息的接受是一个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由于主体的选择,理解甚至改造而打上了主体的主观烙印的活动。在接受中,主体的目的、“前理解”、能力和气质等主观因素,都要直接影响其对信息的选择、理解和阐释,并把接受的成果在相关的活动中加以运用和表现。经过这样的接受过程,信息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其间必定有取舍、有变形、有重心偏移、有结构重组,以至引伸转换。
郭沫若对各种泛神论思想和观念的接受,正是这种具有强烈主动性和高度能动性的接受。他曾经说过:“哲学中的泛神论确是以理智为父,以感情为母的宁馨儿。不满足那upnolsterer (室内装饰)所镶逗出的死的宇宙观的哲学家,他自然会趋向于泛神论,他自会把宇宙全体从新看作过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机体。”(注:《文艺论集》,第212页。)在“五四”时期血气方刚、英姿踔厉的郭沫若,是以诗人的角色站在时代潮头的。在这个社会亟需变动、人生亟需活力的时代,他要用自己的诗歌去拨动年青一代的心弦,点燃年青一代的心灯,煽起使凤凰更生的烈焰。基于此,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眼于使现实理想化即“青年化”的极富革命实践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极富革命思想性的诗人。他从中外古今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吸取固有的或他所以为的泛神思想与观念,使他为之动心忘情的那个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都无处不在的“神”,正是一种生生不已的动态、气势,一种永葆青春的生命,一种昂扬奋发的进取意志,一种能启迪心志,鼓舞热情的精神。到他明确提出“永远青年化”的主张时,还在呼唤这个“神”,要求全中国的青年“尽量发挥我们人性中所具有的神性”。郭沫若本来就是一个偏于主观表现型的诗人,是一个曾声言要当“自然的父亲”的诗人,他在接受从孔子、庄子、王阳明到斯宾诺莎、歌德、泰戈尔等人的泛神观念时,其主体性也就特别鲜明。质言之,郭沫若对泛神论思想和观念的接受,乃是作为一个青春型诗人即诗性主体的接受,是一种诗意化即诗性的接受。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中曾说:“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意体现。”无疑指明了这种诗性接受的特征。郭沫若对泛神论这种诗性接受之所以可能,一是诸种泛神论观念本来就具有诗性思维的内涵,二是经过郭沫若接受内化的泛神观念更实现了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运动、进化和创造的生命精神。也正是由于诗性主体所持有的这种主体性,初期的泛神论观念才在科学思想的作用下发生了向“感应”论诗学的理论转化。
二、泛神论的诗性思维与诗性接受的意向谋合
所谓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接受中即是:“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注:《文艺论集》,第290页。)这段写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的话,表达了郭沫若泛神论观念的下述内涵:
第一,“泛神便是无神。”这就是不承认那个作为万物本源、先于万物存在而创生了万物的神,通过对神的泛化而消除了它的独尊和至圣的地位,于是神所具有的运动,创生的本性和功能也就泛化为万物自身的本性和功能。
第二,“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只是神的表现。”这就是说,无论外在客观世界还是内在主观世界,都是神的表现,即都以神为其存在的基础和本源,都赋有神的本性。这就为人与自然之间、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和融洽找到了本体上的根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以这种泛在因而也共有的神性而达到本质上的同一。
第三,“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重心转到“我”,以神为共同中介而沟通的“我”和“自然”,在这里转换成“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因而人能从自然中观照到我,用自然来表现我。把这个转换改变一下位置,说“我就是自然的表现”,也未尝不可(比如“我是一只天狗”之类)。但是,作为一个主观表现倾向特别强烈的诗人,郭沫若更倾心于把“我”的神性泛化到自然万物,通过自然来表现自我,这正好是他对泛神论进行诗性接受的必然选择和阐化。宗白华曾经这样描述他和郭沫若同样崇仰的泛神论者歌德:“当他纵身于宇宙生命的大海时,他的小我扩张而为大我,他自己就是自然,就是世界,与万物为一体。”(注:《宗白华全集》(2),第8页。)这不正好活脱脱一个早年郭沫若的形象吗?
除了上述内涵之外,还有一层也十分重要,那就是其中所表达的“神性表现”的观念。在郭沫若看来,自然和人都是神的表现,因而“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即我的“神性”的表现。这种神性表现观,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形神”说和“意象”说。在这里,形神不二,意象难分。这里的形和象对于神和意来说,在这里,形神不二,意象难分。这里的形和象对于神和意来说,是透明的;这里的神和意对于形和象来说,则如盐在水,有味无痕。在郭沫若的“神性表现”观念中,泛在的神不是作为内核藏文于物内,而是透过万物的形色声气得到显现,能为人所感知、观照的东西。
这种泛神观念在哲学上的真理性,不是我们在这里的讨论现象,我们的兴趣在于这种泛神观念在思维上的诗性特征,因为这正是郭沫若之所以倾心于它的主要原因。
人类学家对原始思维的“五渗性”的揭示,已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原始的思维尚不能把自我与外物区别开来,正如列维——布留尔所说:“这个思维不仅想象着客体,而且还体验着它。”(注:《原始思维》,第429页。),在原始人的心目中, 自然万物与人是互相渗透融合在一起的一片混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同人一样的生命体。意大利十八世纪文化哲学家维柯所说的“诗性玄学”和“诗性逻辑”,就是对原始思维的互渗性的一种阐释。他指出:“最初的诗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实事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他提请人们注意,“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这里所说的“以己度物的方式”,说明“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注:《新科学》,第180-181页。) 人类童年时期的这种思维方式先是在神话传说中,后来则是在诗歌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维标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揭示了诗的起源,把它看成诗性思维的产物。
这种诗性思维之所以是“诗性”的,是因为它正好体现了文学表现人性并通过人性观照宇宙本体这一本质特征。古往今来的文学之所以是“诗”,具有诗性和诗意,就因为它以类生命的形式观照和表现着人性及其生成的过程与成果。无论文学具体描写何物,归根结底都以活生生的人性意蕴为灵魂。在原始的互渗性思维中,万物皆具人性,都表现出人的感觉和情欲。人在自然万物中所观照到的正是他当时所体验到的自身的感觉和情欲。后来人逐步知道把自己同自然区分开来,但这种隐喻式的诗性思维和由此引起的体验,却一直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延续下来。在近代以来的“移情”说、“直觉即表现”说、象征主义的“应和”说、以及“生命符号”、“感情符号”说中,这种诗性思维作为一种独具生命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依然以不同的阐释方式和衍生形态存在着。应当说,正是人与自然在本体上的内在联系和人对生命整体体验的追求赋予这种思维方式以无限的生命力,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始终保持着用文学艺术从世界的诗性去观照并呵护人性的意愿和热情。
在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到处出现的那个“我”,就是诗人心目中的“神”的表现,这个“神”被诗人称为“人性中的神性”,实际上就是他所理解和体验着的人性尺度。由泛神观念所驱动,这个“我”泛化为万事万物的神即魂魄。
郭沫若早年从对孔子、庄子和王阳明(应当说还有那个写了《离骚》、《九歌》和《天问》的屈原)的生命精神的独特理解而孕育的泛神观念,在斯宾诺莎、歌德、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中得到印证和鼓舞,并通过他们的思想如生活实践融贯为更加充沛的心灵体验。何况,这种观念固有的诗性思维特征,本来就催生过庄子、歌德、泰戈尔等人的诗性创造。难怪郭沫若要由衷地赞成宗白华说的“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为适宜”的观点,因为正是在它的指引下和启迪下,诗人直接地就能以诗性的思维从万事万物中感悟人生,观照人生,从而表现人生。这种观念也因此而一直活跃在诗人郭沫若的心中,什么时候他作为诗性主体的诗性高扬起来,什么时候泛神观念也就激扬着他的灵感。在《屈原》的独白“雷电颂”中,他通过屈原的口赞美着“这宇宙中的博大的诗”,呼唤着雷和电那如火的神性,简直《凤凰涅槃》的再现。可以说,正是这种泛神观念的诗性思维,成全了诗人郭沫若和他的那些真正的诗。
三、 泛神论的生命内涵与诗性接受主体生命精神的价值合拍
人们熟知表达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在本世纪之初的中国所激起的热情。古老衰败的中国需要灌注和激发新的活力,以便革固鼎新,重焕青春。郭沫若真切而强烈地感悟到时代的要求,明确地意识到“要把动的文化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注:《文艺论集》,第15页。)这种“动的文化精神”在他们诗歌中得到最鲜明的表达,其中的《凤凰涅槃》所表达的在烈火中“更生”的思想,更体现诗人根本的价值追求。动是必需的,但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推动进化、创造和更生的前提,他呼唤“青年化”的诗歌,就是鼓吹这种更生,推动这种更生的。正是出于这种价值追求,他才特别倾向于他心目中的泛神论,这实际上是在各种泛神论思想和观念所具有的运动和进化的因子共同启发下被诗人自己所强化了的一种极富青春活力的生命精神。这种追求进化和更的活力,乃是郭沫若的“我的神”的生命内涵。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中,郭沫若这样阐释孔子的思想:“本体含有一切,在不断地进化着。然而本体这种向‘善’的进化,在孔子的意思,不是神的意识之发露,而是神之本性,即本体之必然性。”又说孔子“认本体论在无意识进化,这一点又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异趣。我觉得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他认为人类有很多缺陷,如想使人性完成向上,第一步当学‘神’之‘日新’。……这样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注:转引自陈永志《郭沫若思想整体观》第38页。)显然,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向‘善’的进化”和“日新”就是“神”的本性,也是这“神”之美的所在。他之欣赏于歌德的,也正是这种生生不息、不断更新,“于积极进取的动态中以求生之充实”的精神。这种进化观张扬到极致,就是对“革命”的渴求。在《宇宙革命的狂歌》中他唱道:“宇宙中的何等的一大革命哟!/新陈代射都是革命底过程,/暑往寒来都是革命的表现,/风霆雷雨都是革命底先锋,/朝霞晚红都是革命底旗霖,海水永远奏着革命底欢歌,火山永远举着革命的烽火……”泛神观念在这里衍生出泛革命的观念,诗人的“革命”之“神”在宇宙万物中处处表现出来,无不成为“革命”的化身。这正如他后来所说:“宇宙的内部整个是一个不息的斗争,而斗争的轨迹便是进化。”“我们的生活便是本着宇宙的运行的促进人类的进化。”(注:《文艺论集续集》,第78页。)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急需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去推动社会的改造和进步。与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不同的是,郭沫若更多地洋溢着青春的理想和热情,而且葆有对中国古代固有生命精神的特殊理解和信念,因此,他在同别人一样看到黑暗和腐败的中国的同时,还把它看成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葱俊的姑娘”;在别人倾注全力对旧中国的现实进行解剖的时候,他却倾其全部热情呼唤着凤凰更生的烈火。这种对“动”的倾心,对“进化”的向往,对“革命”的憧憬,必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与叔本华、尼采等的生命哲学合拍。郭沫若说“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与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的表象”的观点何其相似。在郭沫若那“天狗”式的狂放中,无疑有尼采式“超人”的影子。
显然,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进化追求和革命意向,正是郭沫若泛神观念中的“神”所具有的特殊生命内涵,也是他所呼唤的“人性中的神性”的价值核心。这种凌励超迈、昂扬奋飞的生命精神,与那个时代的生命哲学(及其美学)实际上合着拍子,相互激扬,成了郭沫若诗歌中最动人心魄,也最具特色的主调。正是诗人对泛神论的诗性接受,使他的诗中出现的自然万物乃至宇宙整体的形象都到处洋溢着他所憧憬瓣青年时代的“新鲜”、“甘美”、“光华”和“欢爱”,鼓荡着充沛的力,迸射出耀眼的光。正是“进化”的神,“日新”的神,“革命”的神,造就了郭沫若火山爆发般的诗情,造就了他火山爆发似的诗。从这种诗性接受的主体特征出发,也就不难理解“物活论”和“泛神论”何以渗透进郭沫若思想和诗歌中的缘故。
四、郭沫若泛神论观念与宗白华活力论美学的诗心相印
宗白华是发现郭沫若这匹诗坛千里马的伯乐。“知音实难哉”!宗白华之所以能发现郭沫若,郭沫若之所以能被宗白华发现,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们在诗学观念上难得的心心相印。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诗性接受,使其诗学观念与宗白华不约而同地彼此耦合。无论是宗白华的诗作还是理论著述中,都明显地看得见郭沫若那孕育于泛神论的诗心。
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概括:从审美特性论的角度可称之为“同情”论美学,因为他主张美感的动机和功能都在于“同情”,即沟通、融洽感觉情绪使之达于和谐一致;从美本质论的角度可称之为“活力”论美学,因为他认为美的根源就在于无处不在的活力这一生命特征。这位最早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诗人,倾心追求和张扬的就是“少年”的精神,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才与热烈呼唤“青年化”的郭沫若同气相求。
《艺术》是宗白华写于1920年的一首小诗,以最精致而且明白的方式表达了这位未来美学家当时的诗学观念。诗中写道:“你想要了解‘光’么?你可曾同那林中透射的斜阳共舞?你可曾同共昏初现的月光齐颤?你要了解‘春’么?你的心琴可有那蝴蝶的翩翩情致?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的一缕温馨?……”这不就是郭沫若《女神》序诗的先声吗?宗白华认为,“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注:《宗白华全集》(1),第308页-309页。)他通过罗丹的雕刻和歌德的人生认定了这种美学观念。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中他写道:“我自己自幼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是相信创造的活力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也是自然的内在的真实。”“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生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美’的源泉。”“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注:《宗白华全集》(1),第310页。)正是由于这种无往而不在的活力,才有艺术生活的“同情”,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艺术之间的共鸣。宗白华认为:“艺术的起源,就是由人类社会‘同情心’的向外扩张到大宇宙的自然里去。”“因为自然中也有生命,有精神,有情绪感觉意志,和我们的心理一样。”(注:《宗白华全集》(1 ),第317页-319页。)正是泛在的活力、生命和精神使这种同情有了可能,而这种同情又更加激发了人生的活力,使之不断地向上向前去作不倦的追求。宗白华终身赞赏的表现于歌德的创作和人生的“浮士德精神”,乃是他所说的“艺术生活”的典范。在歌德身上,为宗白华所欣赏的是其生命中“激越的动”。他说,歌德的生活“是以动为主体,个体生命的动,热烈地要求着与自然造物主的动相接触,相融洽。”“歌德生平最好的诗,都涵蓄着这大宇宙潜在的音乐,宇宙的气息,宇宙的神韵,往往包含在他一首小小的诗里。”(注:《宗白华全集》(2)。)宗白华的这些思想,与郭沫若孕育于泛神论的诗心,不是正好侔合无异的吗?
在比较中国和西方文化时,宗白华曾提出西方文化主“进取”,而东方文化则主“静观”。为此,郭沫若曾专门致书宗白华加以讨论。在这篇《论中德文化书》中,郭沫若明确指出“中国的固有精神当为动态面非静观”,他甚至把老子的“无为”说也用‘生而不有,为而不持’的积极精神”加以阐释。这种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征的不同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却最终消弥在对“动”的“进取”生命的共同追求之中。当时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宗白华主要从西方文化吸取“进取”精神来鼓舞启迪中国的“少年”化,郭沫若则同时也在中国固有的周秦文化中也看到了这种精神,并要把它引入世界的潮流而发扬光大,使他自己所宣扬的生命精神能接上民族的源头。使他们得以诗心相印的,则是他们共有的那颗生机勃发、热气腾腾的“少年”心。
我们不是专门作郭沫若宗白华美学比较论,但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泛神论思想的接受确实是诗性的;他从自己的诗心出发去接受它,又用它启迪、激发、深化自己的诗心。
五、从泛神观念到“感应”诗学的科学性理论转化
如果说郭沫若最初的诗学观念主要是建立在他对种种泛神论思想和观念的诗性接受之上,那末经过岁月的凝炼和对自己创作经验的反思,这种泛神论诗学就逐渐为“感应”诗学所代替,并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形态。
郭沫若的“感应”诗学是他1925年到大夏大学讲授文学概念时构想的。在《创造十年续篇》中,他对自己“悬想的文艺科学”所作的概述,应当说是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一笔宝贵的遗产,它在美学方法论、审美本体论和审美特性论上的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郭沫若认为:“文艺论的总论也应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而“这种细胞成分”“不外是由于外在条件所激起的情绪,与情绪所必具的波动,即节奏。”“情绪的波动具有感染性。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由其本身的节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样的反射。”他把这个作家情绪节奏表现于作品并感染读者的过程称为“文艺的感应过程”。(注:《沫若文集》第7卷,第202页。)对这种“感应”,郭沫若后来在《论节奏》中以“节奏互相转变”作了进一步的单释,并且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为便加以描述。
郭沫若的“感应”诗学,无疑是对中国先秦时已经发端的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用近代科学对这一古老的美学观念进阐释,从作为文艺“细胞”的节奏及其相互转变的作用方式揭示了“感应”的根源。可惜的是,这个中国现代美学进程中十分具有建设意义的理论建树,还来不及作进一步的阐释和深化,就淹没在文艺革命化的潮流之中,并很快就被革命的文艺政治学所消解。直到80年代中期,人们才又开始重视“感应”说对于认识审美本体及其特性的意义。笔者专门论述“感应论”审美观的《感应与生成》一书,即是在包括郭沫若、宗白华等前辈开拓者的思想遗产启示下写成的。在这本书中,笔者就是把郭沫若所说的“节奏互相转变”当作对“感应”的具体描述来理解,并由此提出“节律感应”这一重要范畴来的。
从泛神论到节奏互相转变的感应论,郭沫若的诗学观念虽然科学化了,但泛神观念的基本精神依然存在。过去由泛在的“神”造成的人与自然相互表现和共感呼应,现在则以“节奏”及其感染性为根源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之所以能够互相沟通、互相感应,其间的中介不再是那个泛在的“神”,而是泛在的“节奏”。正是基于此,郭沫若才提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观点,其间感情得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就是感应。这个感应过程,也就是发生感情感染的过程。
在郭沫若的感应说中,具有感染性的节奏取代了泛神观念中的“神”,这正是感应说本身走向科学化的关键一步。中国古代的感应论很快便畸化为“天人感应”的神学政治观,甚至堕落为巫术神使。无独有偶,西方的感应说也一度仅为神学家所青睐。当人们未能对事物感应这种最原始的相互作用方式作出科学的解释时,便自然会因其神乎其神而把它诉之于神灵。后来的“物活论”和“泛神论”,也无非是对世界普遍存在的活力的一种解释。当郭沫若把“节奏互相转变”视为感应时,他实际上是用前者来对后者进行了科学的证明,他因此把泛神观念中的“神”科学化了。
为什么说“节奏”是对泛神观念中的“神”的科学化呢?
首称,节奏作为事物运动的基本特征和表现,乃是普遍的存在。自然事物的运动有节奏,人的生理、心理和意识活动,特别是作为这一切的综合整体表现的情感,更是具有节奏。整个宇宙在运动中,也有它的节奏,而且是其他一切节奏的本原性节奏。节奏就像泛神论中的那个万物俱有的神一样,也是一种泛在。只是它不再象神那么隐秘,而常在物的形式上现身上。
其次,节奏作为事物运动的特征,本身就表现了活力,造成了动势,具有生命式类生命的性质。而这正是世界运动、进化、创造、革命的基础。中国古代的“气”和“气韵”,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事物的动态特征的,而节奏正是气和气韵的基本因素。这种联系已为郭沫若所感悟,他解释谢菊的“气韵生动”时就说:“动”就是动的精神,“生”就是有生命,“气韵”就是有节奏。(注:《文艺论集》,第154页。) 试着郭沫若的诗歌,那磅礴澎湃之气也好,那盘桓缠绵之气也好,无不表现为特定的节奏——由语言的节奏、形象的节奏交汇而成的情感节奏。正是这种节奏所具有的感染力,才使人与物、人与人彼此感应共鸣。
再次,由于节奏既是一种普遍的“泛”在,又具有自身的动力性,因此可以作为事物相互作用的中介,不仅由于节奏的相互转变而相互感应,而且彼此映照和象征,使每一形式都能在感应中映照出他物乃至整个宇宙。正是由于节奏的泛在性,形式才有了这种映照万象而超越个体局限性成为宇宙生命和人性精神象征的表现功能。
用这种感应论返观郭沫若在泛神论作用下所创作的那些诗歌,不是可以得到更科学的也更真切的解释吗?不仅诗歌,就是他盛年时期创作的那些历史剧,不是也以更复杂的形象体系应征着他的“感应”说吗?郭沫若自己也曾用节奏来解释“画中有诗”的原因,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艺术要有‘节奏’,可以说是艺术的生命。”(注:《文艺论集》,第95页。)
泛神观念在感应论中的科学化,使郭沫若达到了对“文艺科学”的独特感悟,这也不能不归功于当初他接受泛神观念时所具有的强烈的诗性主体性。
标签:郭沫若论文; 泛神论论文; 宗白华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科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文艺论文; 人性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