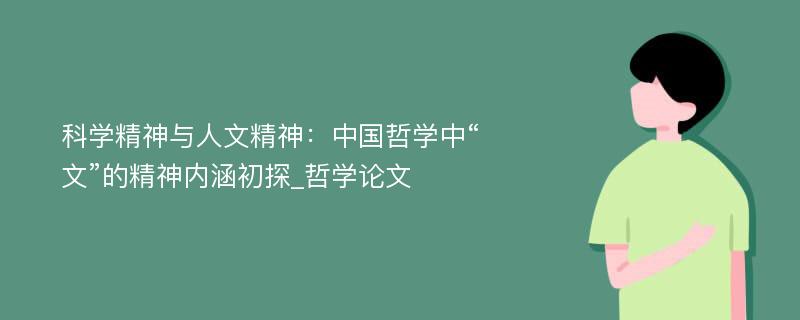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哲学中“文”的精神内涵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中国论文,人文精神论文,内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中的“人文”与“科学”
“人文”意义,一直是人文学者所关注的。首先“文”这个辞,殷商甲骨文已出现,《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西周时,“文”已结合“德”作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周书·谧法》曾经对“文”作一定义式的说明:“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至春秋战国时,更是哲学探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就道家哲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郭店《老子》、竹简《文子》与《黄帝四经》中,找出这一探究的发展线索(注:参考拙著《先秦老子后学之学术流派发展与哲学问题探究——从出土简帛道家资料谈起》,发表于师大国文系举办先秦儒道会议,2002.5.25-26。)。这样一种“文”的探究,更多的是关注“文”本源意义与人文制度之规画的哲学探究,“文”并不完全以“人”为中心主体,“文”更多的是建立在作为存在物的存在,及其所确立的互动与关系上,换言之,“人”是“物”中的类别之一,“人”最终,也在于能够与“物”通,如此才是与“道”、“自然”合而为一。但是就儒家的发展趋向而言,“文”所指的是《诗·大雅·江汉》之“文德”,“文”与礼乐之制有一种联系。“人文”一辞也在这一脉络下,与“天文”对举,《周易·贲卦·彖传》:“《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但是“人文”一辞,并未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原因可能在于儒者之“文”自是一种“人文”,因此无须多举出一“人文”。
就中国古典哲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人文”并没有与“科学”对举,如果我们回归“文”的出现,则“文”包含所谓的人文与自然。“科学”若就它在中国的发展而言,它所指的是天文历数,乃至道教所发展的丹药,及其后发展的火药,但这一类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实际上为原始意义之“文”所涵括。
“科学”这一辞的出现,对中国而言,应是晚近的事。但是它在西方的起源,却是相当的早。Science一辞所指的,最早就与系统性的学科探究有关,它包含对于人、社会、政治、道德、数学、修辞等的探究。西方近代哲学的兴起,有一主轴即是探索哲学的精确而且稳固之基础,希望哲学如同数学般精确,甚至将伦理学以几何学的方式处理。但也几乎在稍后,已然兴起非数学、科学式的思考,“哲学”已然以一种反本质优先论、非理性探究之方式兴起,以一种相对于“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方式,崛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逻辑思维的探究方式。但是这样的一种探究,直至20世纪中叶,终究是摆脱不了纪元前希腊哲学所立下的典范思考——Logos中心论,只不过在这一思维中,尝试加入了时间的变动与持续。
对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精神内涵,在历史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文”与“科学”的差异,这一种差异不在于探讨的对象所涵括的种类,而在于思维的方式,即“Logos”与“文”的差异。Logos关注的是“存在”与“存在物”的问题,“文”关注的是呈现“关系”的图象,是“物之运行”或“伦常之行”的问题。
“文”之为中国哲学表征及其内涵
“文”,就文字的意义而言,是表现一种“交错之画”,若就其作为一种文彩、纹饰而言,它赋予素材一种丰富性;在文化的使用意义上,它作为“天文”——“人文”对举而言,“文”其实质是表现为一种“图象性”,这种图象性,并不以显示单一个体的方式呈现,而是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之图谱。这种图谱、图象,从其实质内涵而言,它是关系结构的图象,个体是在这图象中被定位、被安置,或者说个体彼此之关系,构作了这一图象。“文”作为“图象”,实质上是“关系”之表达,或说显现“关系”之结构,这从《周书·谧法》对于“文”的定义使用,除了“文”具有周人的时代意义——“德”之外,从其形式结构中,可以发现就是“关系”之表达。
“文”作为“关系”之表达,或者可以说就是“行”的表达,是一种涵括时间中之变化的整体表现,在“天文”与“人文”对举的《周易·贲卦·彖传》中,“文”的实质内涵,就是涵括“变、化”的时间因素,或说“行”。“行”包含自然物或天体之“运行”与作为“实践”之“行”,这在老子、孔子所确立的哲学典范中,可以找到诠释与说明。
《老子》19章提出“文不足”的问题,以此而开展关于“道”与“德”的论述,并赋予新的诠释,在这一新的诠释,“自然”成为新的哲学观念,开启了魏晋“自然”与“名教”,及当代“人文”与“自然”的对话。“自然”作为老子哲学精神的表征,即在于阐释“道”之周行而不殆的“运行”,这种“运行”的确立,展现了老子对于“文”的诠释,主张真正的“文”不是特别突出“人”的问题之哲学说明,而是将“人”视为“物”的方式,这在竹简《文子》对于“德”、“仁”、“义”、“礼”的诠释中可以发现。
相应于老子,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明确说出“从周文”的方向,对于“文”的理解、诠释,周初即确立为“德”,“德”作为“文”的实质内容,其展现是藉由礼乐制度,与宗法制度中大宗、小宗的完善所确立,这种确立,实际上就是对于人所处之境的“伦常关系”之规范,以及因此规范应有的行为、态度。“文”在孔子的诠释中,是作为“伦常之行”的关系图象,这种关系图象的核心在《论语》中并没有清楚开展出“人”与“天”之关系图象的论述,而是罕言“性”与“天道”。虽则如此,但是确也曾透露蛛丝马迹,即:人之“伦常之行”不脱离“天命”之旨。《论语·为政》记载着孔子生命历程的自述,可以发现“文”作为伦常之行的关系图象,是有周折的,是涵括对于“自然”的领会。“知天命”这种领会,若穷究其本质,其实保留了《尚书·周书·泰誓》中“天必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维之路,这一种思路是将“天”的关系图象内容,诠释为“民”的关系图象的表征,说为“天”,其实就是“群体之人”为其实质内容。“人”因此在生命中被赋予“自然”的精神,对于“人之伦常之行”的图象确立,即领会了“自然”,展现了“文”。
老子、孔子之后,战国儒、道哲学的探究,也分别依循其各自的哲学典范,开展出对于图象基质的不同诠释,《老子》中已指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至《庄子》内篇,则更是指出“气”是让“人”与“物”可化为一、通于“道”的基质,但是其“物之运行”的关系图象也转化为“情”。换言之,作为“物之运行”的关系图象,在基质中已然存在这一图象的因子——“气”,但是对于“物之运行”的关系结构图象则是以“情”作为说明。儒家则是提出一组观念——“性—心”作为“伦常之行”的基质,而对于关系结构的图象内涵则以“情”作说明。换言之,“情”才是这一“伦常之行”之为关系结构图象的实质内涵。(注:参考拙著《〈性情论〉与〈性自命出〉中关于情的哲学探索》,发表于上海大学与台湾楚文化共同举办“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7.27-30。)
老子之后学的传承,不论是文子、或庄子,不可避免的必然关心“人”的问题,因此对于“人”的进一步哲学处理,是必然而且必要的。《庄子》内篇中除了指出“气”之为“物”与“人”的共同存在基质,也是“人”与“道”可通为一的可能。对于人间世的不可逃脱,庄子也是明确体认到的,因此对于人间世不可免的伦常之行,庄子指出“情”,但是这一种“情”是回应“物之运行”的“情”,而不是人之为个体的情绪、情感之“情”,《德充符》中惠子与庄子的一段对话,即明确指出“情”的实质内涵,是指向其作为关系图象的内涵的必要,是就结构去说的关系内涵,而不是就个体而言的关系内涵。这一关系结构之内涵,也就是“道”的展现,《齐物论》、《大宗师》中即明确指出“道”是“有情”的。“情”其实就是“关系之实”的呈显。
孔子后学,在传世文献中最为人所关注的是孟子、荀子,其对于“心”、“性”的哲学说明,已为后代哲学研究者所知悉,但是对于“情”的关注,虽然在传世文献中已有,但是却因后世对于善、恶之价值的关注,以及“情”作为喜、怒、哀、乐之“情”的表达,忽略了“情”在“伦常之行”的关系结构图象中的重要性。换言之,“情”由于被划归为个体人基质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情”最本源的存在方式是在关系中呈现,或说关系之德行的呈现,其实质内涵即是:以“情”作为此一关系结构之实质内涵。从出土文献论述“性”、“情”的哲学作品——郭店简《性自命出》或题为《性情论》的上博简,“情”有其喜、怒、哀、乐之“气”,此“情”是一类似基质的方式蕴涵在“性”中,即“喜怒哀乐之气,性也”。“性”与“情”的关系是“情”出于“性”,另外在“伦常之行”的图象中,“情”也是礼、乐的兴作的本源,所谓“礼作于情”,关于“乐”,《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乐在先秦就是一种文化、制度的体现。“情”作为伦常之行的图象结构之内涵,事实上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大戴礼记·礼三本第四十二》:‘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佚兴;其下,复情以归太一。”虽然这是论述“礼”在“人情”与“节文”关系互动中的呈显,但也关涉到“情”在关系结构图象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关系结构图象中,作为“人”与“自然”联系的关键所在。
标签:哲学论文; 人文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科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科学精神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