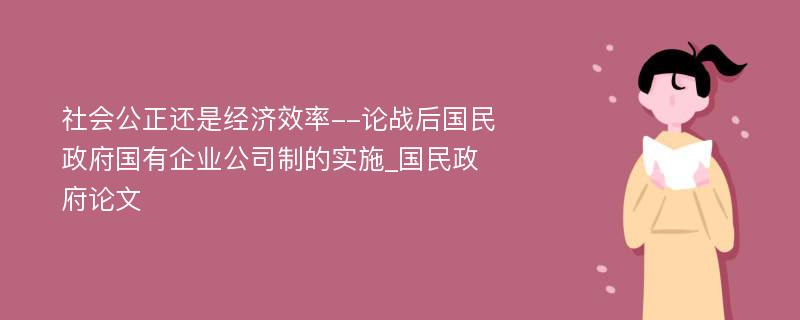
社会正义抑或经济效率——论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公司制的推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论战论文,正义论文,效率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大规模地推行了公司制度。这一工作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贯穿整个战后时期;不但是一种制度的变迁,更多地涉及一些基本社会价值判断与选择,因而在当时曾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近年来的学术界已有个别论著涉及该问题,如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①、陆仰渊的《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②、周春平和尹荣的《论近代中国公司制演变过程》③、(日)川井伸一的《中纺公司と国民政府の统制——国有企业の自立的经营方针とえの挫折》④以及拙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⑤,等等。这些论著或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加以叙述或在重大事件梳理中有所捎带,虽然均有重要学术贡献,但对国民政府推行公司制度的深层因素语焉不详,对推行过程的整体状况没有梳理,更不谈评估推行结果及分析相关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原始档案、文献为基础,尝试对该问题作一次相对全面的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战后国民政府在国营生产事业中努力推行公司制度,这是在对战前、战时相关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展开的。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民政府早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国营事业公司化改造的问题。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第163次政治会议通过了由孙科草拟,经胡汉民、蒋介石等人审查的《建设大纲草案》。该案强调国有产业经营的成败“非但为民生主义实施成败之所关,实亦全国经济技能之生死所系”,但受旧官僚政治余毒的影响以及经营指导思想的局限,即“革命时期不能以经济原则为唯一标准”,国有产业大多经营不善;方案提出,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速革新,其中关键是“在可能范围内应尽量采用公司管理制”⑥。抗战之前的国民政府因受各方面影响,既无财力对国营事业展开大规模投资,也无暇顾及其管理制度改革问题,上述设想几乎落空,真正按照公司制度组织运作的国营事业寥寥无几。⑦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大了对经济事业的直接投资力度,国统区国营企业由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到1942年,占后方工厂总数17%的国营企业,控制了后方工业资本总额的70%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托拉斯性质的国有大型企业。此类企业的发展,对支持抗日战争作了很大贡献。但国营经济事业的大发展也带来了种种问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有二:
其一,经营效率低下。据经济部1942年统计,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后方水电、冶炼、机器制造企业平均利润率为-5.3%。⑨据侯继明研究,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中,28%的企业亏损,25%的企业利润率低于5%,换言之,50%以上的企业“营运结果几无利润可言”。⑩
其二,经营无序。一方面,在抗战的名义下,国营企业不断突破既设界限(重工业),将投资触角深入到一向被归属于民营范围的轻工业系统,在纺织、面粉、商业贸易等行业取得长足进展,不断挤压民营事业的生存空间。同时,借助政府权力行垄断之便,享受土地、资金、信贷、税收、贸易、进口设备等大量优惠条件,与民营企业展开极不公平的竞争。更有甚者,大批政府官员假借“国营”名义,牟取私人利益,使官僚资本主义“长足发展”,“价愈平愈高”、“货物愈统制则愈缺乏”。(11)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国营事业的各种批评日渐激烈,关于其未来制度改革的讨论也异常热烈,其间最为引人注目者有以下三点:其一,对国营事业经营宗旨的认识发生了普遍性转变,由过去单纯强调其公益性而“不以营利为目的”,转而重视其经济效益,强调以效率为先。其二,推行公司制度,以此实行政企分开,重建管理制度。其三,对国营公司制度建设提出了许多原则性意见,主张国营公司应为“独立法人”,政府必须赋予其“相当独立的地位”,应实行董事会制、总经理制,应与普通商业公司“享有同等权利,尽同等义务”,应特别重视员工福利待遇的保障,“俾得安心从公”。(12)
此类主张,因篇幅所限,庶不能一一列举。受此影响,国民政府的相关理念与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以提高经营效率为中心推行公司制度,成为构建新的管理制度的核心指导思想。这可以从其抗战胜利前后所出台的关于战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政策与计划中反映出来。例如,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规定,“国营与民营工业,均应力求增进工作效率,采用最新技术,减低出品成本,与提高品质标准,以求巩固事业之基础,达到迎头赶上之目的”(13);1944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的《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规定,公私合办之事业“应采公司制度”,政府除依法行使行政监督权外,对其业务及人事之管理,“应以股东地位行使之”;国营事业除邮政电信、兵工厂、铸币厂、主要铁路、大规模水力发电厂等外,其他凡具有商业性质者,无论独营或与民资外资合办,“均与同类民营事业之权利义务同一待遇”(14);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规定,国营工矿交通事业的经营可以是“全由国库拨资建设经营”,也可以“组织国营公司兼招民股或外股经营”,但都必须“力求效率之提高,成本之减低,一切管理经营标准可以作为全国之表率”。(15)特别是1945年11月,由蒋介石核准并签发行政院执行的电文《确立战后我国经济事业制度》,更是突出地反映了此种转变趋势。该文把实现政企分开作为构建战后国营事业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国营事业应采公司组织,由政府选任董事,组织董事会,政府对董事会应予以指导监督外,不直接干预。其各层业务公司经理,由董事会提请政府任用之,免职时亦同”,并要求相关部门依照一般企业管理办法,重新确定国营事业人事、财务与物料管理制度。(16)
上述种种,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国营事业中推行公司制度奠定了基础。
关于战后国民政府在国营事业中推行公司制度的过程,目前的学术界仅做了颇为宽泛的简单描述。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该项工作经历了时间界限虽不十分清晰但工作重点却各有侧重的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有大公司初创时期,时间大致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中。
如前所述,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即提出了国营事业中推行公司制度的问题,并做了相应的规范设计。据此,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后,一方面对沦陷区日伪产业展开大规模接收,一方面以公司制为基础,对其进行重组和改造。
资源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各部门中接收的敌伪产业最多。据统计,至1946年底,它在全国各地共接收292个单位,包括了电力、钢铁、煤矿、机械、化工、水泥、电工、石油、制糖、造纸等行业,价值战前法币约13亿元。(17)早在接收之初,该会即确定:“接办之事业要化零为整,集中人才财力,全力经营”,“接办事业组织与管理,要以企业化为准绳,尽可能采公司组织”。(18)依据这一原则,该会到1946年共组建了各种公司近30家(19),且多为大型乃至特大型。例如,它以日伪产业为基础组建的冀北电力公司,下辖北平、天津、唐山三分公司,“供电范围遍及平津唐地区”;以接收之日伪机器产业为基础并整合其原有之昆明机器厂,成立了中央机器有限公司,辖上海、沈阳、云南、天津4家分厂,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营业所;以接收的日伪石油产业为基础,并合并其原有之石油产业,组建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下辖甘青分公司、四川和台湾2个油矿勘探处、高雄和锦州2个炼油厂,另与招商局合资经营中国油轮公司,在中国沿海和沿江各大城市均设立营业所与储油所,成为“一个统筹经营全石油事业的托拉斯”(20);它将接收的台湾地区的48个单位改造为石油、铝业、铜业、电力、水泥、机械造船、制糖、制碱、肥料、造纸等“十大公司”,其中制糖公司拥有糖厂35所、酒精厂15所、蔗田10万公顷,以及规模可观的专用铁路,资产总值1.2亿美元(21),生产能力不但能满足岛内需要,还可远销大陆及日本、东南亚市场。
其他部门也以接收企业为基础组建了一批国有大公司。经济部将日伪在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纺织企业共114家,合并组建了著名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其纺绽、线绽和织布机的数量,分别占全国同类设备总数的39.2%、70.7%和60.9%(22),资产总值近1.5亿美元(23),不但是国内纺织业的巨无霸,在亚洲乃至国际市场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财政部的中国盐业公司、经济部的中华烟草公司和中国蚕丝公司、农林部的中华水产公司等等,也均位列同行业之前茅。
总之,到1946年中,公司制度已在国营事业中得到很大范围的推广,特别是深入到电力、钢铁、化工、矿产等重工业领域,其意义则尤为值得注意。但问题也不少。国民政府长期把国营事业视为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因而相关法律特别是《公司法》没有对国营公司制度作出规范。各部门在组建国营公司时,大多参照战前颁布的《公司法》或战时颁布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其中各行其是、自相矛盾之处很多;有的仅有公司之名,自我性质界定模糊,内部治理设置不完备,甚者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第二个阶段是以有限公司为基础的完善规范时期,时间大致在从新《公司法》推行到1947年底。
1946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颁行新《公司法》。新法对旧法作了许多修订,例如,它对公司设立的程序进行了更严格的规范,强调“非在中央主管官署登记后不得成立”,未经登记而以公司名称经营业务者,除罚金外“并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称”;对政府作为股东而在公司中的地位、权利及其行使方式作了规范;新增了“有限公司”的内容,规定“有限公司之股东,应有二人以上十人以下”;要求凡公司章程有与新法抵触者必须限期改正,特别是依《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创立的公司,应于新法施行后六个月内依法修正并“呈报中央主管官署备案”(24)。此类修订,迫使已有或即将创立的国营公司不得不有所遵循和调整。
依据新法,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公司制度的实行与完善,其中,又以资源委员会为最。该会利用自身机构改革(25)和新《公司法》推行的机会,进一步突出企业化和公司化的经管方针。其负责人钱昌照指出:本会最重要的方针“为走上企业化的大道”,要“组织各种总公司或总管理处等机构”并予以充分的自由(26);翁文灏也强调:资源委员会的经营管理既要重视精神,“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更要重视组织,“重大事业悉设公司,或为有限公司,或为股份有限公司,因事制宜,依法办理”(27),特别是仍然保留厂矿组织形式的国营独资事业,也必须在一定时期内改为有限公司,以期尽量求其企业化。(28)翁文灏还亲自为其手订“工作应注重之方向”,要求其所办重大事业从速“采用公司组织”,以企业精神“图事业发展”。(29)为此,该会拟定颁行了《资源委员会附属事业组织原则》和《资源委员会附属事业设立须知》。前者规定,规模大且具有永久性之事业应“采公司组织”,公司应设董事会、监察人及总经理(或经理);后者规定,采取公司组织者“应分别拟具公司章程、董事会组织规程暨公司组织规程,呈会核定”。(30)同年9月,该会颁行的新“组织法”也规定,其所属各项事业得吸收地方或人民资本,“采用公司方式共同经营之”(31)。
按照上述要求,资源委员会以接收日伪企业为基础,新组建了一批大型国营公司。其中仅东北地区就有鞍山钢铁、本溪煤铁、东北金属矿业、辽宁水泥等“九大公司”(32)。据统计,到1947年底,该会所属96家企业中(不包括各单位附属厂矿),采取公司组织者52家,总数已经过半。(33)
同时,依据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对上述公司特别是依照《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设立者,进行规范和改造。在股东方面,普遍进行了调整,由过去的单一股东,增加到两个及其以上,达到了有限公司股东数量的规定;在规章制度方面,普遍按照统一格式制订并公布了公司章程(其中仅1947年就有16家),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股东及资本构成、董事监察人及职员设置的数量和选任方法、财务决算及盈亏分配方法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所属公司中普遍设立了董事会。截至1947年初,完成此项工作的附属单位已达到25家,且均系大型公司。
诸如此类的变化,其意义不容忽视。
第三阶段是向股份有限公司改进时期,时间大致在1948年间。
进入1948年后,国民政府继续推动创设新的国营公司和改造旧的国营厂矿,并有一定进展。(34)但受时局影响,其工作重心(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已不在此,而是配合国营生产事业的民营化计划,对国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该项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47年2月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此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全面升级,国民政府又着手币制改革问题,并先后在1948年3月26日的国务会议上和8月19日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决定将中国纺织建设、国营招商局、台湾糖业等公司改组为股份公司,发行股票,部分划充货币发行准备,部分发售民营。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上述改制工作均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于11月初宣告结束。有关这一改制的过程,笔者曾有专题研究(35),此不赘述。
进入1949年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解体,公司制度的推行工作也终止了。
1946年颁布的新《公司法》开篇即强调了公司的营利性质,规定“本法所称公司,谓以营利为目的,依照本法组织登记成立之社团法人”(36)。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准在国营事业中推行公司制度,表明其经营宗旨已经在抗战胜利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它也推动了国营事业独立法人主体地位的形成。实行公司制后的国营事业,自主权有了明显提高。从这个时期公布的一系列公司章程来看,大部分都明确界定了董事会在其中的核心决策权力,比如总经理等重要行政人员的遴选、营业发展计划的拟定、财务预决算的编制等。特别是在那些有地方政府或民间资本参与的公司中,董事会更是被赋予了许多最后裁决权,例如,在该会与台湾省政府合办的电力、肥料、碱业、糖业、水泥、造纸等公司中,董事会有权任免公司总经理及协理,有权核定公司年终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财产目录、盈亏分配方案,有权确定股东红利、董监酬劳、员工奖金及福利金的分配方案,等等。(37)各事业间彼此大锅饭的局面开始打破,相互交易“采用商业原则”,买卖价格,“悉采市价,不打折扣”。(38)各事业的发展积极性也因此而有所提高,例如,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与美国飞歌公司签订了经销合约;台湾肥料公司为增产氮肥,从联合国救济总署争取到氮肥机器拨赠,价值美金40万元;台湾电力公司向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借贷美金200万元,用于购买急需的电气器材;台湾糖业公司则利用加拿大贷款,向其订购万余吨生产资料,等等。(39)
公司制的推行也有利于推动公私营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建构。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新《公司法》下,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是地位相同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其所有税款运费等负担,皆与其他民营事业统一待遇”,不享有特殊权利。(40)另一方面,与《公司法》修订相同步,国民政府陆续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使国营公营事业与民营事业在平等条件下均衡发展”(41)。例如,在税收方面,此间颁布的诸多相关法律,都明确规定甚至是强调了国营事业的缴税义务:1946年4月公布的《所得税法》规定,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合伙、独资及其他组织形式之营利事业,均须依法“课征分类所得税”(42),这其中自然包括国营事业(43);同时公布的《印花税法》修正条文规定:“国营事业及地方公营事业所有之契约主要账簿及凭证,均应依本法交纳印花税”(44);1947年6月公布的《特种营业税法施行细则》规定:凡公营银行、信托、保险及其他有竞争性之国营事业都属于“特种营业税课征范围”,而所谓竞争性之营业,系指除邮政、电信、兵工、造币、铁路、水力发电以外“与同类民营事业并存竞争营业者而言”。(45)不仅如此,它还明显地加强了对国营事业的税负征收。国民政府曾以行政院的名义接连训令有关部会及各省市政府,严加督责所属公营事业机构,“切实奉行税法,按时纳税”(46),并要求主管征收机关及时做好对此类事业营业稽查,以确保税收足额到位。(47)此类措施的推行,使国营事业的特权受到削弱。
上述两种积极趋势的出现,正是国民政府推行公司制度的基本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民政府的上述工作又是不彻底和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具体表现有三:
其一,真正实行公司制度的范围有限,主要集中在国营工矿生产领域,其中又以资源委员会所属事业为主;而历史更为悠久、资产更为庞大的铁路、公路、航运等国营交通事业以及军工企业等则鲜有涉及。至于向股份有限公司改进的事业,在全部国营公司中更是极少数;而在这极少数公司中,所拟出让民间的股份就更少了。
其二,对已经实行公司制度的企业,采用种种措施继续保持掌控,其突出表现就是改制过程中,大多数国营事业选择了“有限公司”的形式。张忠民曾指出,新《公司法》关于有限公司的规定,“十分有利于国有企业实行和采用公司组织”,既可以满足其注册为“具有法人地位,负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同时又可以因为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而使其“避免成为公众性的公司”(48),此言极为切题。因此,新法颁布后,各国营事业大多以有限公司模式进行象征性改造。例如,资源委员会在改组中大多是以其原有独资经营的企业为主,各自提取少数资金投入对方,组成新的公司;同时,将其本部中高层领导人纷纷派往各公司担任董、监事,甚至是董事长,以确保“对公司进行政策性的领导”(49)。
资源委员会的骨干企业实际上控制在极少数高层领导手中。在此情况下,董事会之设立就更具有象征意义了。吴兆洪曾回忆说:“这样的董事会事实上可有可无。”(50)
其三,与其主体地位构建相同步,国民政府的其他诸多政策则在不断瓦解着此类公司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其中既有无序的临时性举措,也有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就前者来说,自新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国营事业也深陷其中。它们既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战争物资的生产与运输,承担各种军政摊派,又要经常充当政府平抑物价的工具,使得许多单位入不敷出,“支持备极艰苦”(51)。就后者来说,最典型者莫过于《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该法虽明确了国营事业的企业化、自主性的经营理念,并做出了许多相应规范;但在加强监管的名义下,也赋予政府全面干预之权力,包括其组设兴废、业务政策、人事考免、资金筹划、营销策略等等。(52)显然,据此而行,即使实行了公司制度,国营事业也不可能拥有完全市场意义上的自主权。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验的不足、环境的动荡、政治体制的不良等,但在笔者看来,思想理论上的根本性分歧,是重中之重的因素。从表面上看,抗战胜利前后,朝野各界对国营事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形成了一致性意见,即以提高效率为中心,推行公司制度。但事实上自始至终都伴有不同的声音:或认为关系国民生机之大事业“绝非公司之类所可胜任”,以公司制度之推行来解决国营事业之问题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53);或主张国营事业“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单纯强调其“盈利多多益善”是错误的,将会牺牲“有关国家整个利益的民营事业”,“便利少数特权阶级”(54)。
两种不同的声音,看起来争论的是一些制度层面变革的问题,即,要不要推行民营化、要不要推行公司制等,然而事实上却是关于基本价值判定与实现方式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平如何实现、国营事业经营中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孰先孰后,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既想利用公司制度改善国营事业经营不良的局面,又担心因此而失去对其控制,进而失掉对社会正义的保障。尽管这些国营事业被更多地用于支撑专制政权而不是保障大众民生。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它在推行公司制度的过程中,对“有限公司”这种形式青睐有加;在实施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计划中,采取大量的保留性措施,以利于其继续控制经营(55);而在实际的公司运营中,既强调效率的提高,但也不时地被警告“不应太计较成本”(56)。
显然,将抗战胜利后国有大公司的涌现,单纯地视为“近代以来中国公司制度发展演进的自然逻辑结果”,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在笔者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国民政府的主观努力;而这种主观上的努力,主要是基于对国营事业社会职能的认识及其经营理念的重大转变。正是这种转变对于国营事业从以局厂为基本组织形式、政企紧密一体的传统经营体制,向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的现代企业组织转变,具有不可小觑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环境的复杂性、利益的多元性,决定了价值评判标准的多样性,也决定了长期以来围绕国营事业经营宗旨的争论(亦即以公益为主抑或以效率为先),仍然延续到战后时期。国民政府在推行公司制度过程中,因此而政策谨慎、保守甚至是自我矛盾,既没有解决国营事业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没有对政治统治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社会正义的保障更无从谈起。
注释:
①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陆仰渊:《中纺公司的建立及其性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③周春平、尹荣:《论近代中国公司制演变过程》,《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
④[日]川井伸一:《中纺公司と国民政府の统制——国有企业の自立的经营方针とえの挫折》,姬田光义编:《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年》,日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
⑤拙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
⑥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0年版,第377~380页。
⑦(17)(35)(55)拙作《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42~174、390、429~522、515~518页。
⑧参见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后方工业概况总表(一)》,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22页。
⑨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7页。
⑩转引自侯继明《1937年至194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九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
(11)(13)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第80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版,第101~102、351~352页。
(12)杨华日:《确立我国国营事业制度的几个要件》,《经济建设季刊》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1945年,第157~159页。
(14)(16)周开庆编:《经济问题资料汇编》,台湾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3、82页。
(15)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年版,第424~436页。
(18)(19)(33)资源委员会编印:《复员以来资源委员会工作述要》(1948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28(2)-48。
(20)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1932~1949)——事实与评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80、183页。
(21)《台糖公司资产》,1948年9月12日《申报》。
(22)张西超:《中国工业现势》,《新中华》复刊第六卷第四期,1948年2月,第7~11页。
(23)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7页,1948年。1美元约等于战前法币2.57元(作者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
(24)(36)《公司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卷第五期,1946年5月。
(25)1946年5月,国民党改组政府,资源委员会从经济部划出,直隶行政院,负责创办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重要矿业、动力事业及政府指定的其他重要工矿电业。
(26)《钱主任委员训词》,《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卷第六期,1946年6月,第55~56页。
(27)《本翁委员长在本会第一届委员会议开会辞全文》,《资源委员会公报》1947年8月第十三卷第二期。
(28)(51)《资源委员会事业概况》,《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二卷第六期,1947年6月。
(29)《翁委员长手订:本会工作应注重之方向》,《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三卷第二期,1947年8月。
(30)《资源委员会附属事业设立须知》,《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46年7月。
(31)《资源委员会组织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一卷第四五期合刊,1946年11月。
(32)《东北区各事业接办单位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一卷第四五期合刊,1946年11月。
(34)例如,在此期间,该会新增设了上海通用机器、济南电力、巴县电力、鄂南煤矿、福州电力、贵州水泥、中福煤矿等公司,并将中央无线电、有线电、电磁、电工等器材厂及第一区特种矿产管理处等单位改组为有限公司。
(37)《台湾电力有限公司章程》、《台湾肥料有限公司章程》、《台湾碱业有限公司章程》、《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章程》、《台湾水泥有限公司章程》、《台湾纸业有限公司章程》,《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二卷第五期,1947年5月,第36~37、64~65、68~71页,第十三卷第一期,1947年7月,第53~54页。
(38)《业务会议要案汇志》,《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五卷第一期,1948年7月。
(39)《事业消息》,《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一卷第一期,1946年7月,第十四卷第二期,1948年2月,第十四卷第五期,1948年5月,第十五卷第三期,1948年9月。
(40)《翁部长在二中全会经济报告全文》,《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卷第三四期合刊,1946年4月。
(41)《资源委员会训令》,《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四卷第六期,1948年6月。
(42)《所得税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卷第五期,1946年5月。
(43)1948年4月国民政府修订公布的《所得税法》规定:凡公司、合伙、独资及其他组织营利事业之所得,均须依法课征分类所得税,而所谓营利事业,包括“各级政府所办公营事业,政府与人民合办事业,及其它团体所办营利事业”。参见《所得税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四卷第五期,1948年5月。
(44)《修正印花税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条文及税率表》,《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卷第五期,1948年5月。
(45)《特种营业税法施行细则》,《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7年7月。
(49)《资源委员会训令》,《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7年7月,第66~67页,第十四卷第六期,1948年6月。
(47)《三十七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办法》,《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四卷第三期,1948年3月。
(48)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49)(5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52)《国营事业管理法》,《申报》1949年1月1日。
(53)《关于国营公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资源委员会档案28(2)-395。
(54)《行政院通知》(1947年6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44-26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56)《事业消息》,《资源委员会公报》第十二卷第一期,194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