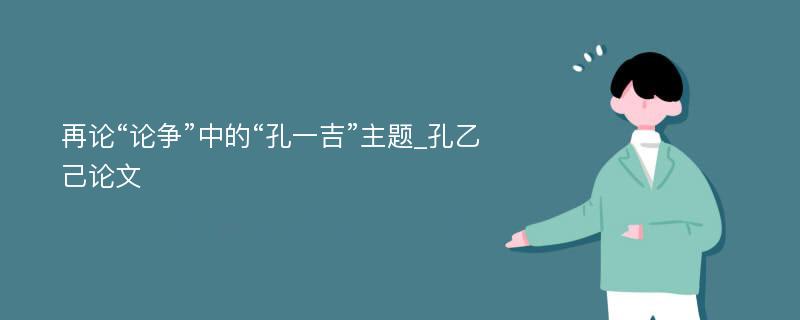
争鸣篇 《孔乙己》主题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题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乙己》是鲁迅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小说发表70多年来,人们针对“孔乙己”人物形象及其主题的探讨与研究从未间断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见解。有持“凉薄”说的(他们大抵都以鲁迅曾和孙伏园的谈话为依据);有持“反封建”说的;有持“等级观念”说的;有持“批判封建教育、科举制度、整个封建社会制度”说的;有持“兼有”说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如何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及《孔乙己》一文的主题,成了孔乙己研究者渴盼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和《孔乙己》一文的主题作出新的判断。
首先,我们从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语言心理机制入手,掌握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语言折射的意义。先把小说中人物孔乙己的话分两部分来考察,以此获得人物语言的浅表性内涵。
A.皆平常人语。
“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充耳不闻别人的议论,以简洁明快、要言不烦的话语来摆脱自己尴尬、难堪与困窘的处境;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反问得当,落意准确,毫无优柔寡断、犹豫难决之状;
“你读过书么?”恳切中透出关切;
“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认真而又不乏机智和友好;
“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热心、恳切,富有耐心,嘉誉之辞里满含着一层善意;
“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吗?”惊喜之情溢于言表,内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话语直接而无遮饰,憨而见真;
“温一碗酒。”平实简单;
“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短暂的犹豫之后,便从容应对,句句得理;
“不要取笑!”干净而又坚决,话语中透出几分愠怒;
“跌断,跌……跌……”变“打断”为“跌断”,最后连“断”也不忍承认,颇有几分自尊。
以上,我们照录了孔乙己的话。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初步认识:孔乙己的话没有什么出格之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很符合“当时体”的。①从话语的形式看,句式活泼多样。既有长句,也有短句。像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和疑问句及其特殊形式在其中都有所见。②从话语的内容看,他的应对表达都有一定的实际内容,言之有序,没有诘屈聱牙,半通不通的语言现象。③从话语的表达效果看,孔乙己的话应该为人们所能接受,但由于人微言轻,效果并不见佳。他的话一次也没有使自己摆脱尴尬的处境,冲出哄笑的氛围。④从话语的交谈对象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大人,有小孩;有短衣帮,也有长衫主顾等。⑤从话语的指向性看,既有主动攀谈,也有被动应答……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乙己话语不失明白晓畅的特点。
B.教人半懂不懂的话。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当别人问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之际,他说话时,则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了。
当孩子眼睛都望着他碟子里的茴香豆时,他说:“多乎哉?不多也。”
上述所引,便是孔乙己说话“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确证了。但我们不妨也对上面的句子作点比较分析。①从话语的形式看,这些句子都是弃白话而用文言。②从话语的内容看,都明确而具体地表达了说话人的意思。③从表达效果上看,往往引起人们的哄笑而结束。④从交谈对象看,仍具有广泛性。⑤从话语的指向性来看,这类话语大致都是在被动应对的窘状下进行的。
孔乙己说话,为什么出现从“皆平常语”转而为“教人半懂不懂”的怪现象呢?这是一个往往令人忽视的问题。
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我们知道:一切“痛苦的”“不幸的”经验,往往是被人们“潜抑”着,压在心里底层。但它越是被压抑,越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冲破“潜抑”的途径,是乘意识不备时,借助意识中出现的有关联的因素,把自己“化装”成类似的因素,然后把自己的“潜能”转移出去,从而达到潜意识自我表现的目的和愿望。由于借助“转移”“化装”的手法,所以,潜意识因素的“溜”出,必然会连带阻止意识界中其他有关因素,致使那些熟悉的,甚至到了舌尖上的事情被挡了回去——也就是说,迫使意识反而把不该被压抑的因素压制下去。
从孔乙己话语形式转变的显性因素来看,主要是人们对他的挖苦、讥讽和嘲弄引起的。人们何以如此呢?我以为,这得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他原来也读过书,这该是他一生的辉煌与骄傲了,这似乎也成了孔乙己骄人的地方。但终未进学,却是一块很大的暗影。这就造成了孔乙己性格的二重性:一方面自以为饱读诗书,腹藏经纶;另一方面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处处遭到嘲讽。他的孤独、狼狈和困窘,没有促使他反省,反而加深了他对诗书的渴望。这种渴望越强烈,他的痛苦也就越深重:他的伤痕、伤疤;他抄书时人与书俱去;他因偷书被何家吊着打;最后被丁举人打折了腿,我以为多多少少都是与书有关。孔乙己对书这样执迷与牵挂,这样“皓首穷经”,用意何在呢?仍想进学,书中没有答案;从孔乙己的言行来看,大概是早绝了这番雄心与壮志了。那他这样嗜书如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以为孔乙己是把诗书当成了自己的避难所,是用以炫耀和护身的。这就构成了孔乙己读书致用的潜在内涵了。
人们说他“偷书”,他非要美其名曰“窃书”。偷者,口语词也。既然是口语词,那么老妪能解,说出来岂不令人汗颜吗?孔乙己巧以“窃”易之,足见他读书的实用价值了。进而言之,它不是护了身,遮了丑吗?当别人问他何以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此时,令他平日足以炫耀的荣光也委落如尘土;但他的潜意识里却要为这种荣光而挣扎而奋斗,所以,“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在众小孩围住孔乙己要茴香豆吃的场面中,孔乙己穷形尽相之际仍忘不了用圣者贤人的话语来为自己救驾,实在有点滑稽可笑。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孔乙己“教人半懂不懂”的话是由潜意识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半懂不懂”绝非是因为语意含混所致,只不过是取文言的形式罢了。
古书为他带来了些什么呢?伤痕见多了,肉体的伤害更重了。他本以为古书能给自己挣来面子与身价,最终却不过一场梦幻而已。人们的哄笑,大概就因为这些了。
其次,我们不妨把《孔乙己》一文的时代背景和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联系起来考察,进一步蠡窥鲁迅写作《孔乙己》的真正动因。
“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围绕着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的《新青年》同人围绕以白话代替文言,以白话文学代替旧文学的问题,讨论争辩了近两年,形成“五四”前期文学革命的主导思潮:白话文学观。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为“正宗”。不久,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1918年5月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针对白话文运动,守旧派人物开始站出来咒骂和抵抗。当时,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诬蔑恐吓。以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他并且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来影射诋毁攻击新文学倡导者,嘲讽白话文。在这一时期,作为文学革命主将之一的鲁迅自然不甘沉默,他和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等人一道撰文猛烈反击。他为此写了一系列杂文讽刺和打击守旧派。鲁迅在《现在的屠杀者》(1919年5月发表)一文中曾对林纾就白话文的指责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并且还指出:“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在这场白话文与文言文对垒中,鲁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文言作了挑战。他是当时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人。
鲁迅的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茅盾语),他的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都有所触及,难道独独忽略了文学革命中白话文与文言文斗争一页?这在鲁迅这样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以为鲁迅设置孔乙己这个人物,主要的立足点还是在艺术地再现白话文与文言文激烈斗争情景上。这是作者的初衷。这篇作品写于1918年冬,1919年3月写就附记,4月发表,而这期间又正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由此可见,这一情景不可能不影响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作者当时的附记中看到:作者的用意是“单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作者并且还指出,发表这篇小说之际,正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可见作者对守旧派对白话文的攻击已颇愠怒了。虽然鲁迅不主张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但我以为,作者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解剖与批驳则是很自然的事了。他的这种思想,直到1925年在《答KS君》一文里仍可寻得到:他将章士钊的“旁加密圈”,自视名句的“得意之笔”加以分析,指出章的字句和声调都陋弱可哂。“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我以为,这就是《孔乙己》一文的最好注脚了。从作者叙述语言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作者的深意的:孔乙己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这“半懂不懂的”一语,实在是作者站在白话文的立场来审视孔乙己语言特点的。用鲁迅的话来说:“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由此可见,孔乙己的“气绝”,不正是“文言文的气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