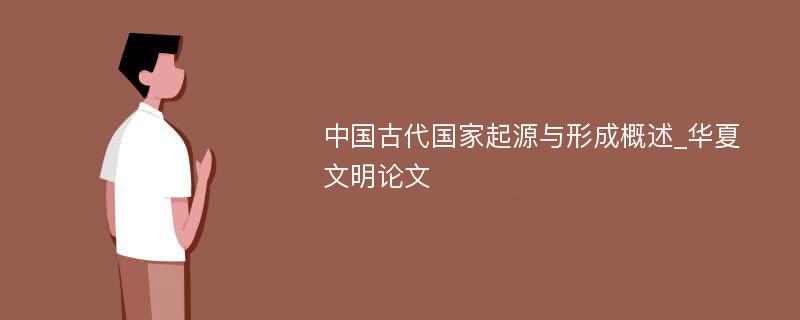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起源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5-0116-04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瞩目的重大学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就已有所涉及了。建国以后,也陆续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真正蔚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则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受到国际学术界有关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热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考古发掘工作的推动。自7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界不断传出与中国古代文明暨国家起源有关的重大发现的消息,这极大地鼓舞了学者重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及国家起源的热情。尤其最近这二三十年,结合新的考古发现,有关论著不断涌现,包括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许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应当说,讨论的成果是丰硕的,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然而,尽管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讨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我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亦即国家状态,以及我国古代国家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却并没有在学者中取得广泛共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有资料发现还不是十分充分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学者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及对待这些理论的不同思想方法所致。此外,学者对待资料的不同态度与使用方法,也加重了有关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理论上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如何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上面。长期以来,我们用于指导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的理论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应当说,这部著作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里面提出的有关国家的概念、国家产生的基本途径、国家形成的标志等理论,在原则上均不成问题,均应是我们研究的指南。但是这种指南,仅仅意味着拿它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用它作理论向导,而不是从它上面摘取现成的答案。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据以分析古代国家起源与国家形成标志的例证,主要是古代希腊、古罗马和古日耳曼人的国家。这三个国家产生的背景同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古国的产生实有着很大差异。这在恩格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反杜林论》中已有很好的说明。我们的一些学者未曾区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国家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往往拿了恩格斯据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归纳出的国家形成的标志及其产生的具体途径作尺子,去衡量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这种做法,自然要与坚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的学者的意见发生冲突。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走的也是如同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形成所经历的那样一种军事民主制的道路,古代中国的国家形式也是如同古希腊罗马那样一些奴隶制城邦,就在学者中引起过不少争议。而如今在学术界引起更广泛争论的对于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即“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的理解问题,看来也与是否承认古希腊罗马同古代中国两种国家形式的差异有关。根据实际,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夏、商、周三代,氏族组织并没有被打破,地域组织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理论分歧的第二个表现,是如何对待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理论。人类学、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科学。过去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许,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人类学研究有了不少新的进展,其中一些理论传播并影响到中国。这些理论主要是美国人类学者塞维斯(E.Service)等人提出的酋邦理论与其人类进化新说,以及荷兰人类学者克列逊(H.Claessen)等人提出的有关“早期国家”的理论。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很高的热情介绍并率先使用这些理论,这无疑与他们认为这些理论适应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有关。他们的做法立即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但不同意见亦随之而产生。其中争议主要发生在对酋邦理论的不同认识上。所谓酋邦是对前国家社会形态的一种概括,有人认为这个理论“十分有利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十分有利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十分有利于近几十年来中国相关领域新的重大发现,尤其是考古学上发现的解释”[1](P153),有人则认为“酋邦制只是通过一些特定的民族和地区考察后归纳提出来的”,“从多线进化的观点看,很难认为古代诸文明古国都是通过酋邦这种形式由史前走向文明的”[2](P13),有人甚至说它根本不符合中国考古的情况。看来,这里涉及到酋邦理论到底是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问题。此外,从一些学者对酋邦理论的批评看,还有一个这种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社会进化暨国家产生的学说相互对立,还是可以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与完善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些现代人类学理论的理解,在赞成这些理论的学者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分歧。例如,对于所谓酋邦,到底应理解为一种不平等的氏族结构,还是应理解为“部落联盟”,抑或“部落联合体”,就是一个尚需加以澄清的问题。而对所谓“早期国家”,国内一些学者也存在着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理解。至少对中国早期国家的解释,国内不少学者与西方学者的说法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个也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理论,讲如何从考古学角度观察文明的产生。这个理论本身在学者中并没有太多的争议,但学者在使用这个理论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不少分歧。这个理论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者克拉克洪(C.Kluckhohn)和英国考古学者格林·丹尼尔(G.Daniel)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他们主张通过考古发现的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等所谓文明要素来探知某个古代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认为一个社会只要发现有了这些文明要素中的两项,即可判定它进入了文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社会。国内学者引用这个理论时,又或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为文明要素加进了青铜器一项内容,将这几项合称为文明的“三要素”或“四要素”。也有称之为文明的“物化表现”的。应当说,这个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可取的,并且也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然而学者同样运用这个理论,甚至同样进行这几项文明要素的举证,却仍然为我国何时进入文明争论不休。有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距今五六千年的,有说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已进入了文明的,也有说夏代甚或夏代以后才进入文明的。看来,问题还出在学者对这几种文明要素发展水平把握的尺度不一样上。如同夏鼐在他那篇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讲话[3]中所说的,有人认为文明这个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对于这种性质的“文明”,他认为只是指“文明的起源”,其时间段应划入新石器时代,而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用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的文明,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文明时代。夏鼐所说的“用低标准来衡量”的文明,指的是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文明因素,如萌芽状态的文字、小件青铜器、普通规模的城邑、一般贵族的宫室或墓葬等,用它们来比较夏或商时期的大型宫殿或都城、青铜礼器以及甲金文字,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学者在资料处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文献资料及使之与考古资料相互结合的态度上。不正确的态度来自两个极端,一是过分怀疑文献资料,主张单纯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二是主张对文献资料全部拿来,反对或轻视对文献资料进行时代、真伪及文字训诂的处理,在未有这些处理的情况下便急于去使文献与考古资料“对号入座”。这两种态度所造成的对研究工作的不利影响,已使学术界感到有必要大力提倡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提倡历史工作者与考古工作者的相互理解与密切配合。近年有关机构主持召开的以“历史与考古的整合”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即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关切。
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其早期形态,同样也是十分关注的。他们一致认为古代中国是人类社会少数几个已知的原生的早期文明或原始国家之一。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克列逊等人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列早期国家的21个实例中,就有古代中国的殷商和周朝。克列逊认为,在这21个实例中,只有6个可以看作是处于过渡形态(指向成熟国家的过渡)的早期国家。这里面也包含了中国;而在这6个过渡形态的早期国家中,又只有两个国家后来达到了成熟国家的水平,其中也有中国[4]。此可见古代中国在当代人类学者心目中的位置。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际学术界十分重视古代中国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知识,却不甚了了。多数外国学者谈到中国的文明,只是从殷商开始,不包括夏,更不包括夏以前的历史。有关夏的考古发掘及其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相对应的情况,他们所知甚少,不少人受过去国内个别疑古学者的影响,仍坚持认为夏只是传说中的朝代,没注意到有关夏的一些传说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或部分印证。而就其所描述的他们认为已进入国家状态的商周社会的具体内容看,这些学者对我国早期国家的认识仍相对简单,一些描述不仅显得空泛,而且有的明显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实际相违背。如上所述,克列逊将中国商周社会认作是处于过渡状态的早期国家,可是按照他给出的处于过渡状态的早期国家的特征,如所谓“贸易与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官吏任命制度占据主要地位”、“土地私有制度显得越来越重要”、“取得固定薪水的职员占绝大多数”、“税收体制发展已臻完善”等[5]来衡量商周社会,可以说没有几项是相符合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理论全无是处,而是说他们对于中国了解不够,国内学者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为丰富与发展人类学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作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上述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重新系统地进行一番有关这项课题的理论与其资料使用方法的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新认识,是有必要的。以下,即是我们经过认真研究以后,所得出的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基本观点:
1.中国前国家社会曾经经历了由平等的氏族社会向不平等的(或曰有阶等的)氏族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不平等的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就是现代人类学者所称的酋邦。酋邦的基本精神不过就是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的结合[6](P52),它可以对应于我国传说中“五帝”时期“天下万邦”的“邦”,也可以对应于考古发现的我国自仰韶中晚期至龙山时期各地出现的由若干聚落结成的二级或三级聚落群结构。我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即源自这种不平等的氏族社会组织。
2.我国古代最早产生的国家应属于现代人类学者所称的早期国家。之所以称其为早期国家,主要是因为这种性质的国家仍普遍存在着各种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成的社会组织,酋邦这种不平等的氏族组织作为基本政治单位也仍然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所谓早期国家就其组织形式而言,不过是由某一势力超群的大邦作为“共主”对其他众邦的统治。因此,判定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就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人们常说的“公共权力”和“地区组织”的建立这两个标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地区组织的建立,应是国家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事情。
3.与此相应,我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途径,也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有所不同。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另一条路径,即氏族社会各个组织的首领因其权力的集中与其“独立化”倾向由“社会公仆”转变为“社会的主人”,从而结成一个统治者阶级,促使社会转化为阶级社会的路径[7](P218~219)。这种权力来源于他们对氏族共同体(即酋邦、酋邦联盟)面临的各种事务(治水、对外战争、宗教事务、内部纠纷等)的管理。这种国家形成的道路在古代社会应更普遍。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应是其典型。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家天下”,即是由众酋邦联合而成的酋邦联盟的首领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可以推论出,由这条道路产生的国家,自然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其原有的氏族组织内部的结构,它的基本阶级结构暨社会形态也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
4.我国上古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即是由以夏后氏、有商和有周三个酋邦为首的势力集团分别建立的国家。这三个国家虽然前后迭相兴起,并其统治的地域也前后相互继承,但它们一开始却各自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并均是在这个地区众多酋邦组成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均属于早期国家的性质。
5.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人是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的建立者。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主要包含了夏的同姓和姻亲酋邦。由于气候环境的变迁,古河济之间自龙山时期以来已逐渐成为四方辐辏、聚落繁庶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聚落和人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成了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发祥地。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就是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城,这已由最近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二里头遗址是夏晚期的都城)。至于夏代国家的建立,无疑与禹作为夏后氏酋邦暨整个古河济地区酋邦联合体的首领,领导这一地区的民众治理洪水有关。所谓大禹治水实是由古河济一带居民发展与保障低地农业衍生出的故事,从古河济一带的地理环境看,它应当是可信的。由于治水之事需要组织各邦民众的广泛参与,需要人力物力的集中,这就促使禹在领导治水的过程中加强了自己的权威,以至最终建立起自己“家天下”的统治。
6.商族与周族均发祥于我国北方,由于气候变迁逐渐南徙。其中,商族作为农耕民族最早居住在晋中地区,约当夏代前期移居至今豫北冀南的太行山前一带,并与相邻的东夷族及原夏族部分成员建立了婚姻关系,从而发展成一支强大的与夏相对立的地方势力。周人则最早居住在今陕西北部临近黄河一带地区,属于奉黄帝为祖先的白狄族的一支,后来逐渐南徙,约当商末移居至今渭水流域中部一带,并与原居于这一地区的姜姓族人结成稳固的婚姻联盟,从而也形成为一支与商抗衡的地方势力。商、周的两个国家均是在与原来的共主夏(或商)的抗衡中建立起来的,而当它们发展得更加强大时,才最终灭掉了前面的王朝。
7.与中原夏、商国家产生的时间相差无几,在我国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曾崛起过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三星堆国家。这个国家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产生的,尽管它也受到周围地区文明的影响,但却能将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融汇为一炉,并从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三星堆国家亦属早期国家,其最终形成,显然也是由一个大的酋邦对其他众邦的统一的结果。三星堆文明的被发现表明,我国早期国家并非只局限产生在中原地区。
8.早期国家的产生并非意味着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过程的结束。这一过程是要待其过渡到成熟国家才算了结的。成熟国家与早期国家的分野主要表现在它不再保有原始氏族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某些残余。其中最主要的是它的统治不再是建立在由血缘亲属关系结成的各种族的组织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按地区划分的行政组织基础之上。在我国,由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过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转型是通过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实现的。
以上观点,我们自知有许多是与目前学界同行,甚至一些主流学者的意见相左的,也难免有错误。但我们想,既然是搞研究,就应当不怕有意见分歧,不怕犯错误,只有通过各种意见的切磋琢磨,才可望求得最终的真理性的结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愿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