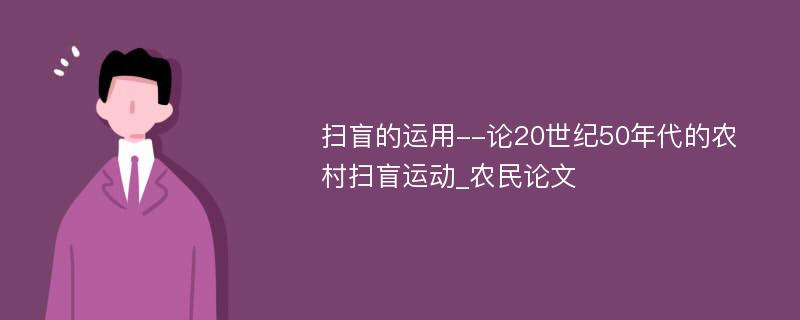
识字的用途——论19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途论文,年代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7-0176-09 一、“文字下乡”与武训的难题 晚清以来,劣绅泛滥,基层社会的士绅结构越发败落,频繁战乱和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乡村,导致地租收入降低,农民生活日益恶化;传统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1930年代围绕“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教育救国派将乡村的症结归为农民的“愚”、“穷”、“弱”、“私”,他们输送新知识、改良农业技术、组织乡村自治,希望重振基层社会。而反对者认为,如果仅依存现成的乡村社会政治机构,无视乡村封建势力和殖民侵略,甚至试图借助军阀势力,依然依托乡村精英重建乡村秩序,这样的乡村建设“退一步说,即使农民识得字,能够看书读报了,也不能解除他们底痛苦;即使农民们能够相当改良技术,使农民的每亩田能够多产一石谷,多结几十斤棉花,然而帝国主义的一场倾销,就可以使你的农产物跌去一半价钱,两次兵差一派,就可以吞噬了你的全部收入”①。梁漱溟就曾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分野,外来者不应该“在乡村社会内起一种分化的功夫”,主张“整个乡村”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可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乡村内部一方卖儿鬻女,一方放高利贷,如何能让经济地位不同的农民组成和谐的“整个”乡村呢?在土豪劣绅统治的乡村,任何送进来的利益只会又一次输送到乡村权贵手中,何谈“自治”?乡村工作者无不感到进入乡村之难,办识字教育往往“穷人不来富人来,好人不来地痞流氓来,不识字人不来识字人来”②。因此,不改变社会结构的乡建,只会复制和巩固这个不平等结构,即便个别穷人有条件学习,最后也只是脱离自身阶层变成新的食利者。乡村教育的挫折感,梁漱溟体会最深,他毕生致力于乡建,创办农校,倡导“社会学校化”,可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我们动,农民不动”。他一方面想组织起乡村,一方面又认为如果“乡民愚昧而有组织”危害性极大③。由于农民消极应对,国民党最后干脆搞成了“强迫识字运动”④,“被迫着去识字的人往往这样问:‘识了字有饭吃吗?’”⑤。 也只有在社会性质论战的视野中,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意义及局限,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调查,回应了这次论战。针对中华职教社认为乡村的病源是“愚、弱、贫、私”,费孝通则认为农民其实并不“愚”,他们有着和城里人不一样的“知识”,只不过不是文字而已。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他指出乡土社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没有产生文字的实际“需要”,所以文字能否下乡就成问题。费孝通沿用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需要”论,从实用角度指出了乡村教育派识字运动不切实际,可谓打中了要害,但也将农民的“不需要”本质化了,这里的“不需要”更应该历史地理解为农民丧失了“需要”的经济条件,而不是农民天生反感文字。但费孝通至少提醒了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改造中,如何既创造出农民识字的物质前提,又创造出农民内心对文化的自发的“需要”,让文字顺利地进入“乡村”?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建国之初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那些梦想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文化下乡运动,将改良乡村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善行和仁义上。《武训传》的初衷是为配合建国初期全国学文化高潮,电影在叙事上以南下干部——冬学女教师(黄宗英饰)在农村夜晚冬学课堂上讲故事开场,中间以女教师的画外音为线索讲解武训兴学故事,意在说明乡村变化今非昔比。尽管如此,导演孙瑜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结果拍成了大杂烩。武训建起“崇贤义塾”后,只能将其托付给柳林镇上有文化的乡绅来主持,这是无奈之举。历史上“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⑥!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依然是卫道传经,而且也并非真的为穷人开门办学: 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武训历史调查记》) 退一步说,即便穷孩子上了学又怎么样?电影结尾通过武训对办学的最终目的很困惑自问:“学而优则仕怎么办?”学好,就脱离了穷人去当官,这其实意识到穷人和仕人是两个世界。武训其实不必杞人忧天,所谓的“经学”和“蒙学”之分早就将穷人家通过读书而升官发财的上升渠道堵住了,18世纪以后由于社会贫富分化带来了教育不平等,富家子弟往往不屑与“贫贱者为伍”,各“延师于庭”,搞私立贵族教育,办起了贵族学校,造成“乡塾党痒不能行于今日”。由此晚明以后在中国乡村已经存在教育双轨制:为慈善的、无关仕途的“义学”,和为培养高级管理人才而承办的“社学”。“义学”虽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识几个字的机会,但并不是为“俊秀之士”登科准备的,只有从小就一路接受经学教育,从开蒙起就享受精英教育,来自“社学”的富家子弟才有科举晋升的机会⑦。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早期科举的确为寒门子弟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公平机会,但到晚明后,尤其清朝,由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捐纳制盛行,寒门通过科举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最为严重⑧。梁漱溟所谓中国社会是伦理性质,穷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地位,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可是“职业分途”又在哪里?晚清的简字运动,也同样强调简古两种文化的区别,“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⑨,同时认为真正有学问的还是小学和古文,小民只需认几个简字俗字,士大夫垄断了上层文化,教育不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生产着不平等。武训对旧官府绝望,可又不能给有了知识后的穷孩子指出一条出路。 二、新簿记与新生产:记工识字课本的兴起 应该说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者都十分真诚地想为农民办点事情,就成人识字课本来说,民国时期最流行的是青年协会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和《农民千字课》⑩,“平民”主要指城市平民,也包括农民。也有专门为农村成人识字编的《农民识字课本》,如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定县公理会福音堂的识字教材。这些课本都强调为强国而必先培养民的“自治”能力,而为民治须先培养“独立的个人”。注意到教育要适合平民,并且提出了“教育农民化”,教育社会化,这是一大进步。课本选材已经注意贴近平民日常生活,叶圣陶更提出“教育即生活”等先进理念。教材内容除了百家姓、三民主义、唱歌、珠算,还有平民应酬和文契等,目的是为了“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但对于农民千字课,当时除了有人批评课本价格太贵和生字太多,“不合平民智力”(11)外,更多读者则批评平民识字课本对象不清晰(12)。教材是工农混编的,民国时一个识字班里学生年龄会有8—60岁的跨度,造成成人课本儿童化现象,当时就引起批评:比如“‘何九买鸡蛋,放在瓶子里,鸡蛋打破了……’没有一处不是属于小孩子的故事”(13),本来在“人的发现”的五四新文化主题下,讲究童趣和滑稽笑话,即是开明本、商务本和世界书局儿童国语教材的一大特点,丰子恺的配图更强化了这一特征。学习应用写作往往学怎么收帐,如何写地契,如何养生。即便是流行很广的陶行知和朱经农千字课本,都很难脱离城市文化的“市民”性。当时饱受批评(14),并没有真正走入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15)。 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新中国彻底改造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在新的乡村社会中,通过文化诉苦,农民意识到没文化的害处;通过合作化中新农具改良、记账、借贷、读报和劳动工分手册等形式,将识字真正嵌入到了生产劳动环节中,改变了费孝通断言的农民“不需要”文字的状况,重新激发出了农民对文字的“需要”,进而自发地产生了学文化的愿望,识字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这既和不问“农事”的儒家经学文化有根本不同,也和中国精英文化中的“耕读”生活方式有区别,所谓的耕读文化和第一线的劳动生产并不相关,因此作为“传家”的“耕”和“读”的分离就是生产和管理分离,“耕”越来越无关生计,成为优雅生活的点缀。 识字如何走近农民日常生活?那就先得让农民认与他生活有关的身边的字。50年代的农民识字课本首先立足于地方性知识,并始终围绕生产为中心。合作化运动,在身体、时间、空间上对农民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改造,现代生活因素嵌入到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并因其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魅力引起农民参与的兴趣,在这个形式下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合作社有了全新的管理方式,有了集体,有事需要请假;上工看钟点;有了合作社,缺钱少物可以打免息的借条预支;有了信用社,可以储蓄和贷款,从此告别了高利贷。这些无不说明文字在新社会成为农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识字也就水到渠成。为培养合作社记分员,各县都因地制宜编写识字课本,开设“记工学习班”,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高度评价了高家柳沟村自编农民记工识字课本的事迹,称之为“了不起的创造”。莒南县的高家柳沟村,在成立生产合作社过程中,由于全村文化水平低,找不到记账员。记账员识字太少,“连人名、农活的名称(指耕地、收割、庄稼等)都写不出来,就只好用画圈、画杠的办法来记账。当画圈、画杠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就只好找记忆力较好的人当‘心记员’了”,结账时靠召集大家回忆凑工分,常常熬到半夜也凑不准,闹得不团结。后来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夜校识字,将学习内容和当前合作社的记账需要结合起来,“先从社员姓名学起,然后逐步地学到土地座落、各种农活和农具的名称,再学各种数码和记账格式等。学习的具体方法,是把社员姓名、土地座落、各种农具等所要用的字,分类排列起来,先学相同的字,后学不同的字”(16),终于解决了难题。 各地地名、农作物、农活、农具都不尽相同。各地农民迫切需要认识哪些字,首先需做调查研究,这也是学文化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创举。根据《星火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编写组交代,本教材入选的都是农民记工和写便条常用的字:“经过向村会计员、记工员和老农调查了农活名、作物名,向社主任调查了人名和地名,向保管员调查了农具名,又向会计员要了各种常用的便条、生产定额表和劳动手册。”根据这些信息入选了九百个字,再进行深入调查,选定社员最需要的328字。(17)选定后即围绕这328字编写课本,这些生字对农民来说音熟字不熟。如一、二课学习记账用的基本数字后;第三、四、五课从全部生字中选出33个笔画简单的基础字,如“上下、大小、土地”等,按照记忆和认知规律成对出现,便于记忆;第七、八课就是农民劳动手册,教农民认识劳动手册和借支记录;九至十是该县旱地和园田的二十种农作物名;十一到十八是各个季节的农活名;十九课是该地最常用的八种农具;第二十课是星火社所在乡乡长、党支部书记和社主任的姓名;第二十一课学习地名,二十二到二十五就是社员常用的五种便条。 50年代农村识字课本的最大特点是现编现学,课文有些句子预留下括号或方框,供各地方教学时自行填写真实名物。首先要认同村人的名字,先认姓,再认辈份和全名。乡村虽然是熟人社会,但名字却一直很“陌生”。认人、认地、认农活,目的是将熟人、熟地、熟物转化为文字,建立新的关系;也是将名和物、声音与符号通过再认重新对应起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地方性知识(方言、方音)翻译为普遍性的文字。通过学习同村人的名字,“熟人”获得了再认识。在中华文明语境中,姓名意义重大,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姓名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志向,寄寓着父辈的理想和对后代的期许,代表着价值观念,姓名还意味着名所对应的主体隶属何种共同体,传统文化秩序中对姓名的管理有严格的分类和谱系秩序。因此对农村人来说,姓名其实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阿尔都塞所言的召唤结构。但是因为生活艰辛和生存无望,底层人对姓名失去了兴致,又因为和文字隔离,作为一个农民,在乡土社会中仅仅以绰号或“小名”或贱名被相互传唤,其“学名”(姓名)因无书写的需要而无法流行在村里和熟人社会中,时间长了就被遗忘,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中寓言性地交代了书写底层农民之难,不仅在于作为现代农村“多余人”无法进入传统书写秩序中,还在于首先就是无法为其命名。阿Q、祥林嫂、孔乙己这些贱民的大名叫啥早已没人关心,在《阿Q正传》中,所有底层人的“学名”都已被遗忘,甚至被宗法社会强迫取消了族权和“姓权”——不配姓赵,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意义。如今将“阿Q”被遗忘的大名激活(“赵××”?),姓名的意义在认字过程中显露出来,穿过姓名这一符号,农民重新获得了全新的形象,一个大写的人站了出来,即便传统文化下的命名和对应的新人依然充满着张力。课文中同村人名单改变了传统宗族姓氏和族谱的排列秩序,在课文中平等地排列:“这样排队的结果:姓高的二十九人的名字中,有三十三个不同的字,姓沈的十三个人的名字中,有十七个不同的字,姓吴的十五个人的名字中,有十四个不同的字,姓褚的两个人的名字中,有两个不同的字,独姓一人,连个不同的字,共计六十八个不同的字”,在这个有别于宗法秩序的名单中,大户和独姓得到平等对待。课本教姓氏时有意打破《百家姓》的四字句顺序,如“高白于金王,丁安田牛方”,要农民认识到“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从姓中培养阶级意识(18)。记工识字课本中对农民“学名”的强调,还表明在新时代,农民地位和身份的提升,他成了生产队集体中堂堂正正的“公家人”:他可以请假,可以无利息借钱借物,想想因高利贷而四处躲债,最终被迫“按指印”画押卖女儿的“杨白劳”,这在农村就是破天荒的新鲜事(19)。第十课的课文则是一个介绍“我”的开放性文本,“我是下思乐村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名叫( )( )( ),社长的名字叫王骏林”,北京星火农业合作社识字课本的编排也是如此,空格里要求社员填上自己的姓名(20)。书写社名和社长名字,不仅因为社员很多时候要找社长办事,打交道,更是一个象征性行为,既是对个体的强调,也是对共同体的皈依。正是通过“文字”这一抽象符号,每个合作社的社员通过各自记工账本,进入了互助组和合作社,一个集体实实在在建立了起来。借助文字的“陌生”符号,社员进入拉康所言“象征界秩序”,每个社员都会在这枚“镜子”中再认出一个全新的自我,并经由符号对自我的再认而获得自豪感。 合作化后农村劳动方式发生的显著变化,就是每天用工分计量农民劳动,月底或年底结算分红,农民的劳动首次有了文字记载,劳动首次和数字建立了联系。工分的出现,表明农民的劳动受到社会承认,第一次被认真地铭记,这是实实在在的翻身解放,每个人每天工分多少根据劳力大小,适当照顾贫弱和按劳分配原则,由村民主会议共同评定。在识字课本中,课文多使用“施事者+施事动作+施事对象”简单句式,这一最朴素句式最容易为农民接受,课文中每个句子都以人名开头,作为句子的主语,作为动作的施事者,劳动者的主体得到了强调。同样,记工工分表也是按照“主——谓——宾”分为三栏来记录工分,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乡村劳动叙事。如第四课课文只有一句话“王丕里担粪八回,记工十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王丕里已经不再是为自家而是为集体担粪,其次还告诉我们王丕里执行着生产队分配的任务,并且他的劳动获得了大家的承认。 八课和九课,是用簿记的形式总结一个农民劳动所得、花销,以及最终的结余。结余让农民看得见收成,积蓄和增收。一目了然的簿记记录了劳动与日常生活收支,这种日常生活的档案化管理,可追溯、可积累,和鲁滨逊簿记账本中专门算计“好处”“坏处”,并求得最大剩余价值的经济个人主义相比,记分手册叙述了新社会农民生活的计划性,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集体性。账簿分栏的语法形式也是饶有意味的,形式上它用分栏和数字。将劳动者和劳动方式以及劳动成果数字化,记工分既是劳动实际需要,又是象征性的仪式,劳动在这里只有分工,没有贵贱差别,每一种劳动形式都获得了承认,也保证劳动计量的平等。工分是劳动成果的数字化,是对劳动的抽象,也是将劳动者和劳动成果暂时分离的过程,这种抽象对于教育一个小生产者来说是必须的,在新的共同体中,工分制也是通过劳动产品和人的分离,让农民重新理解人和物、人和世界的关系,有利于培养更远大的世界观。工分制是劳动日制,劳动者的报酬取决于本人集体生产的劳动工分和工分值,能为农民积极认同。 和农活相关的认字学习主要按“耕”“种”“锄”“割”的季节性劳动顺序展开,因地方差异,在各地的记工识字课本中有不同的劳动,莒南县共排了二十九种农活,运用“做什么,学什么”,真正将知识与生产劳动建立起了最直接的结合。“例如初春的时候,各社正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习‘耕地’和‘送粪’等字。”这样下来,在识字学习过程中,农村记账员也培养起来了。通过记工带动认字学习,也从中培养了农村记账员,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改善了,如前文所引莒南县的材料所言: 以前那种夜里熬眼,账目紊乱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改变。青年满意,群众赞扬。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不但大大提高了青年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而且也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办社信心。副社长吴常桂说,“成立了合作社,文化也提高得快了”。王守敬的父亲,看见他儿子能记账,又被选上了记账员,欢喜地说:“咱也算睁开眼了,以后你好好的学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买。”许多家长,看到了学习管用,都积极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加,并且给买石板、钢笔等学习用具。 识字运动还贯彻了文化创造的群众路线,记工识字课本创造了一种新的编课本方式,课本由各地方农民自己编。山西省昔阳县下思乐村编的记工识字课本经验受到推广,《中国青年报》在社论中鼓励每个合作社每个村子动手编教材。以县为单位的教材编写活动迅速展开:“在一个县范围之内,农活名,农具名是大致相同的,加上年月日、数码和各地大致相同的其它用语,那么各村各社只要再加上人名和地方就可以迅速编出书来。”(21)毛泽东亲自为高家柳沟村通过记工识字课本扫盲这篇通讯写了长长的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 农民识字图快、图用。因此编书时要从农民的“热”字编起。“要从本乡本村的事物和语言学起”,第一册的300多个字的课本由村来编。“编第二本,第三本时,就加上县的,专区的、省的和全国的市区和语言。”(22)对地名来说,也有一个由言语的熟悉化经由文字的陌生化而将“地方”普遍化的过程,这些“熟地”不是作为风景的“自然”,而是进入公家统计并成为改造的对象:“全社地名代‘墩’字的五处,有八个不同的字,带‘坪’字的两处,有三个不同的字,带‘岭’字的五处,有六个不同的字,带‘河’字的两处,有三个不同的字,带‘崖’字的三处,有四个不同的字。其他地名十九处,有二十八个不同的字,总计三十九个地名,带有五十二个不同的字。教学的时候,先学会‘墩’、‘坪’、‘岭’、‘河’、‘崖’等字,再学和这些字有联系的字,如墩‘前’、墩‘后’,‘南’坪、‘大’坪等。”(23)首先,通过学习认识土地的“名字”,旧貌换新颜,农民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中重新来认识自己最熟悉不过的一块块土地。其次,通过对这些土地的“汉字”符码化和再指认,以及通过土地与“命名”者的关联,为农民重新认识土地与土地拥有者(人民)的关系,为认识个人与共同体关联开启了契机。 三、识字的用途 在《语言与国家》中,佛洛里安·克鲁马斯指出乡村识字运动的全球性难题,因为“作为缺乏教育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自己缺乏教育,要是提出帮助他摆脱这一状态,这种要求也未必受到对方欢迎,因为果真如此,随之而来的牺牲是相当惨重的,他必须要上四百小时的课。即便按照识字计划接受了教育,也并不意味着成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24)。在此,识字运动不仅要创造出“需要”,还有赖于乡村生活的整体改变,首先它面对的难题是乡村的分化。“因为文字的难,学校的少,我们的作家里面,恐怕未必有村姑变成的才女,牧童化出的文豪。古时候听说有过一面看牛牧羊,一面读经,终于成了学者的人的,但现在恐怕未有……”鲁迅因此感慨在近代中国,读书是有钱人世袭的事业,也因这样的阶层固化,他对三十年代的识字运动非常悲观。悲观之一是识字帮不了穷人,下等人可能永远是下等人;悲观之二是穷人即便读了富人的“经”,脱离了自己的阶层,农民作家不再是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也不再去写平民“一生的喜怒哀乐”(25)。和旧中国的教育救国派不同,识字运动不是对农民的恩赐,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认为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将来到,反映了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对人的发展的高瞻远瞩。在50年代文化革命实践中,教育农民成为工作重点,文化部要求“把农村文化工作放在首要地位”。50年代人大北大复旦等各地高校开门办学,为工农兵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出了工人作家胡万春,军队作家高玉宝,也培养出了许多既能拿锄头,又能拿笔头的农民作家,此后的全民写作运动如58年的新民歌运动,都是识字运动的开花结果,这是新中国的平等观和人民观,也体现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要由生产者来办的理念,这来自于他青年时代发现的教育与生产的脱节:乡村的文化领导人——乡村教师“基本独立与乡村社会,他们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也不会有意识地参与乡村事物”(26),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他这样写道: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一向是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27)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50年代发明了由农民自己办学的创举,从合作社中找农民教师,不完全脱离合作社生产,让农民自己教自己(28),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这使得与生产相关的知识不再是纯粹技术性知识,也不再因为其实用而受到轻视,知识的等级被打破了。这和旧文化以培养个人慎独、克己、束性为特征的“私德”教育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正是在雅俗意义上将教育和知识的实用和非实用对立起来,从而将教育和社会等级化,将劳动分为生产者与管理者。与知识实用主义相反,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指出17—19世纪主张人文教育的教育专家用“实用主义”来取代实际用处,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或分层教育的同时,也用所谓的“人文经典”教育否定了知识的使用价值。在这些专家看来,高雅的人文主义或古典主义教育似乎不是为职业准备的,而是为了培育个人的“修养”;而那些人人都能平等进入的劳动相关的职业教育却享受不到这种高雅的尊严(29)。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通过对工人文化的人类学调查,揭示了在此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下,工人下一代识字的歧路和困境(30)。 五十年代识字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试图让下层人民拥有平等享受文化的权利,所谓文艺的人民性,就是为人民大众争夺美学和艺术的权力。语言会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平等的共同体,但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文字的诞生却逐步背离其初衷,成为区隔和切割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造成文化与文明的二分,“文明”只用来指代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用以表明资产阶级的身份,而文化则是粗俗的大众文化,是非艺术性的。因此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代表艾略特才会说“工人接受教育也无法改变他们没有文化的本质”。以培养个人修养为旨归的启蒙,是否释放出了“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31)。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打破的就是这一不平等的结构性安排,将旧文化所排斥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放归生活世界中,通过识字运动将排除在政治和历史之外的底层人重新纳入到历史进程之中,通过让文化重新回归劳动人民,通过给乡村日常生活重新赋魅,创造出新的高级文化、一个平等拥有文化权利和文明权利的新世界。如果说教育是人类为摆脱愚昧,进入成熟状态,将个人上升为主体的必然手段,如果说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小农在历史进程中是没有主体的,50年代的文化政治则是要将农业社会主义的农民塑造为新社会的主人,一种非个人主体,一种超越了主奴结构的新主人。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按照意大利的实际状况,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或曰城市知识分子。城市型知识分子诞生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分工而出现,“他们并不主动去指定建设计划。他们的工作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工作的基层,保证及时完成工业高级人员所指定的生产计划”。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乡村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乡村教士、律师等)“总体上比一般农民具有较高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同的生活水平,因此他们代表着农民希望摆脱或改善其处境时所参照的社会典范。农民总想着至少有一个儿子能成为知识分子,作为一名绅士通过与其他绅士取得联系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从而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农民对乡村知识分子是既恨又爱的,“他羡慕(传统)知识分子和一般意义上国家官员的社会地位,但有时又蔑视这种地位”(32)。也就是说,现代城市型知识分子应该脑力和体力劳动是平衡一体的,而乡村知识分子不仅脑力和体力分离,而且成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即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才招致农民的爱恨交加,而农民改变痛恨的方式是取而代之。50年代针对中国的落后现实条件,毛泽东在整体性改造“知识”,改造“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既要改造五四以来的传统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农民。而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社会、农民,与生产关系分离的意义上,恰恰仍然是封建的绅士性知识分子。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同时也要将农民改造为知识分子。就农村来说,也就是要致力于培养新的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再让知识分子成为农民的“他者”,让农民自身成为一种新型的我称之为“农民型知识分子”或农民作家,或许即是三十年代鲁迅呼唤的“农工出身的作家”(33),从而真正实现农民自己书写自己,由自然人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由此我们方能理解,识字就是要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让人人都是哲学家、作家。毕竟,葛兰西说过,“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人人又同时是劳动者。在毛泽东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同样发现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耕读传统,更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传统,但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这一实践也是对葛兰西的“乡村知识分子”概念的改写,而不是按照经典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只能成为现代社会的自然史,这也体现了在农业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在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将落后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34)底层世界的文化信仰是最模糊的地带,正是认识了字,消除了迷信谣言、流言蜚语、谎话偏见,真正开始了移风易俗,生活世界才变得清晰起来。将文化和政治两个世界的分离这一现代性的世界大难题对焦、转变为同一体,以催生新世界。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识字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它试图在落后的中国,最大限度调动生产关系的力量,让文化变成物质力量,主动地促成生产力发展。它试图打破劳动分工;打破文化神秘主义,将文字还给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掌握理论,激活他们批评和创造的能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50年代识字运动如何成功地将农民动员起来,让农民从自然人成为走进政治之内的“政治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什么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此后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探索新的文化与教育革命,以期探索一个整体性的,统一的新世界。 ①孙冶方:《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五期(1936年)。 ②西超:《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印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 ③千家驹:《中国的歧路》,《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第262页。 ④当时国民党学习美国,实行强迫成人识字运动。出台了强迫识字的方案,如闾长负责登记不识字人姓名,以1931-1937为时间段分步实行强迫教育,每个学员须四个月学成。到1937年1月1日起,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一律不得用十八岁以上不识字者。参见马宗荣编《识字运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另外在乡村实行不识字罚款和入学摊派,不识字者不得为选民等政策,“一年以后不识字的人要处罚”等规定,《反对国民党识字运动》,上海档案馆,档案号D2-0-7。陈景汉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五章中也以数据说明,因教育税均摊,识字运动不受农民欢迎。 ⑤叶圣陶:《谈识字课本的编辑》,《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1936年11月1日)。 ⑥武训历史调查团:《武训历史调查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 ⑦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的蒙学》,载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55页。 ⑧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 ⑨劳乃宣:《进呈〈简字谱录〉摺》,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81页, ⑩根据当时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调查,当时全国各处所用的识字课本主要有:《农民千字课》、青年协会之《平民千字课》、《六百字编》、《由浅入深》、《慕道经验问答》、《主日学课单》及画片、《国语教科书》、《市民千字课》、《民众千字课》、《福音千字课》(汉口圣教书会)、世界书局之《平民千字课》。可见不少地方的识字运动都是由宗教慈善机关发起。 (11)基督教识字运动研究会对定县平教会的调查,民众反映当时最流行的两本成人识字教材青年协会的《平民千字课》和《农民千字课》教材价格太贵,“不合平民经济力”,平教会的晏阳初陈筑山现场解释“至于价格太贵,此乃受了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的限制,不能自行定价”。上海档案馆《全国基督教识字运动会研究报告书》,档案号U123-0-156。 (12)解放后为工人农民和军队的识字课本则更加细化,甚至工人中还进一步包括《煤矿工人识字课本》,等等。 (13)(15)马存宣:《对于平民千字课的批评》,《时事新报·学灯》七卷四册第一号。 (14)冯国华:《平民教育谈与平民千字课的批判》,《时事新报·学灯》六卷一册第十七号。 (16)《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9、510页。 (17)《我们编写星火农业社记工识字课本的经过》,载星火农业合作社编《星火农业合作社记工识字课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 (18)《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四十课有新“百家姓”:“高白于金王,丁安田牛方,毛宋徐林姜,陈吴李刘黄,周朱杨孙赵,胡郑何马张。同是一个姓,阶级不一样……”参见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晏阳初批评民国时地主高利贷月利30%,而他们平教会当时给农民以物做抵押贷款物价的70%,即便如此,月利仍高达8%。这对农民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20)第六课课文是:北京市东郊区辛庄乡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21)《快把识字课本编出来》(中国青年报社论),载《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22)项南:(中央青年团宣传部部长)《编“记工识字课本”》,载《怎样编记工识字课本》。 (23)《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0页。 (24)转引自(日)藤井明《中国的文字改革》,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25)鲁迅:《文坛三户》,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26)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2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0页。 (28)这样的教师后来叫“民师”,民师是学校教员,但是报酬由所在生产队以工分等形式支付,新中国后来形成了庞大的民师队伍。 (29)[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第二部分:一、教育与英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163页。 (30)Richard Hoggart,Use of Literacy,Chatto and Windus Press,1957. (31)[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导论部分,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2)[意大利]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33)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34)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载《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