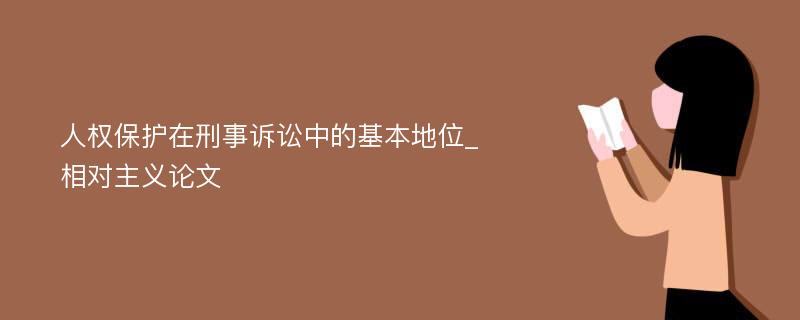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事诉讼论文,人权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33条规定,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亦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无论这些规定的具体含义如何,其目的均旨在加强人权保护应属毫无疑问。在研究领域,不仅理论法学在人权问题上的阐述已经汗牛充栋,而且各个部门法在人权问题上也泼墨不惜。但在刑事诉讼中,究竟什么是人权,保障谁的人权,怎样保障人权,迄今仍然模糊不清,甚至还存在许多错误认识。其原因则在于,刑事诉讼法学对于人权的呐喊虽然持续多年,但对人权理论中的各种学派观点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梳理,对自己所主张的人权概念谈不上有清晰的理解,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核心价值也没有清醒的意识。事实上,人权的概念是变动不居的,有关人权的理论是丰富多样的。对人权理论的不同阐释,必然影响到刑事诉讼人权概念的界定,也直接决定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本文的目标,就是在变动不居且丰富多样的人权概念和人权理论中,确定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界分刑事诉讼人权概念的基本内涵,厘清刑事诉讼人权的具体内容,并阐述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特征。 一、人权概念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 施特劳斯认为,人权渊源于自然权利;在“自然”贬值之后,才演变为“人的权利(human rights)”,就是人权[1](P.47)。自然权利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的霍布斯、洛克,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法国的卢梭等哲学家。无一例外,这些哲学家都是自然法论者。因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都必然建立在假想的“自然状态”的基础上。例如,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生活在没有被共同权力压服的时候,因此他仍是在所谓战争的状态中;这种战争乃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2](P.72)。在这种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享有通过运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自然权利[2](P.75)。洛克亦以自然法为基础来阐述自然权利。洛克指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按照各自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各自的行动和处理各自的财产和人身,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3](P.5)。在此基础上,洛克明确主张:平等、生命、自由和财产都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谁的自然权利受到侵犯,谁就有报复、惩罚与反抗的权利,并引用圣经上的名言:“谁使人流血的,人亦必使他流血。”[3](P.9) 在欧洲大陆,荷兰的斯宾诺莎是“天赋人权”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斯宾诺莎认为,天赋之权就是为欲望和力量所决定的权利;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把自己的天赋之权交付给社会的大多数,从而组成政治社会[4](P.213-219)。荷兰的另一位思想家格老秀斯也是自然权利论的重要代表者。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权利就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由于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自然权利也永恒不变。他指出:“自然法是如此不可改变,甚至连上帝自己也不能对它加以任何改变。”[5](P.24)法国的卢梭则接受并改造了霍布斯的自然权利理论,他赞同霍布斯关于自然法的根据存在于理性原则当中的观点,也赞同霍布斯关于每个人都是何谓自我保全的恰当手段的唯一裁判者的论断。卢梭指出:“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起成为自己的主人。”[6](P.9) 自然权利论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段时期内获得普遍认同。英国于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以及1701年颁布的《人身保护令法》,都是17-18世纪社会契约理论、自然权利理论讨论的基石和对象,也是之后英美及其他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起源。美国《独立宣言》也是深受自然权利论的影响,其开篇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显然认为,所有人生而平等地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建立的目的,就是保障这些权利和自由;因此,当政府丧失了保障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功能,而是走向其反面,成为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专制暴政的工具时,人民就有推翻它的权利。只要社会摆脱政府广泛的干预,人权就得到确立并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这是典型的现代自然主义人权观。 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炮声中隆重登场。该人权文件开篇宣布:“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其第二条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这看上去就像是卢梭、霍布斯、洛克等人社会契约论的立法化。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第一个以“人权”为标题和内容的制定法文件。该文件宣称,文件所列的权利都属于“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序言)。法国革命虽然在后世为人所诟病,《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却成为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自然权利论的式微与功利主义人权理论 自然权利理论曾经盛极一时。但是,这一理论也由于其明显的问题而饱受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激烈批判者伯克指出:“政府并不是由于天然权利而建立的,天然权利可以,而且确实是完全独立于它而存在的;并且是以更大得多的明晰性和以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抽象完美性却是它们实际上的缺点。”[7](P.78-79)法国大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和他的前任一样成为压迫者,自然权利理论的声望自然江河日下。 在自然权利理论之后,功利主义曾经盛极一时。虽然该理论随后也受到不少批判,但是其影响却不容小觑。诚如边沁自己所言:“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公主——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一个人在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8](P.7)我们也可以说,功利主义哲学正是因为迎合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习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分析方法,所以获得了较为持久的生命力。不过,尽管功利主义拥护者众,其对于人权的保障却存在天然的理论缺陷。按照功利主义理论,国家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应当谋求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从而,当牺牲个人权益所产生的社会利益明显大于个人利益时,国家就可以限制人权,以照顾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在这一前提下,假设一个人身体强壮、个性木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若牺牲他的自由,让他全天候为大家服务,完全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那么,根据功利主义原理,剥夺他的自由就是完全适当的了[9](P.8-9)。也就是说,如果奴隶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则这一制度就是值得嘉许的。很显然,如此理论,已经完全偏离了人权保护的方向。 其实,边沁的理论也是为了界定社会可以干预个人自由的界限,甚至其出发点也仍然在于提升个人自由。根据功利主义哲学,当一个政府要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时,必须要对限制自由能够对社会公众达成好处这样的观点进行论证,才能使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获得正当性。功利主义者的目的,仍然是通过其哲学主张,对政府限制或剥夺个人自由的做法加以限制。边沁之后,约翰·密尔提出,个人自由的边界就是“不妨碍他人自由”。密尔说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一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际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10](P.2)密尔的这段话,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格言:“自由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界限。”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个人享有绝对的自由。如学者所言,在这个绝对自由的范围内,“我要躺着睡还是趴着睡”[9](P.7),是完全不受他人干涉的。 (三)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与国际人权法 尽管自然权利理论的确存在明显的缺陷,但是人权的观念却无论如何被保存了下来,只不过从一种形式走向另一种形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权逐渐成为一场国际化的运动。二战中纳粹德国针对平民的暴行、对犹太人的迫害,日本军人对中国平民的屠杀,均激起了国际公愤。法西斯的暴行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思,并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观念:人类不能对其同类遭受的虐待和痛苦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人类的虐待和施加痛苦的行为是一种违反普遍道德的行为,因此所有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团体或机构的一员,都在道德上有义务为消除这种违反普遍道德的行为而努力;所有的政府都应当参加到消除这种虐待和造成痛苦的行为的努力当中,即便这种事情发生在他国也不例外。①所有这些观念都形成了对一个共同概念的支持,那就是“人权”。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向议会发表的咨文中提出了包括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在内的“四大自由”的观点,并且在各种场合表明同盟国在二战中的目标以及战后的计划,就是实现并推广这四种自由。②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完整地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具体包括反暴行的权利(rights against atrocities),例如反对酷刑、反对种族灭绝、反奴役、反对恣意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主要包括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免受政治迫害以及寻求政治庇护的自由,以及思想、良心、宗教、言论、集会、结社、选举等方面的自由;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具体包括自由选择工作权、休息和闲暇权、享有健康和福利所必需的生活资源权、免费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③自此,人权终于成为一个获得普遍接受的概念。 二、当代西方主流人权观及其理论基础 (一)主流人权观之人权概念的特征 西方主流人权观的基本特征是人权的反抗性、消极性、个体性和普遍性。 《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界定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普遍接受的成功标准。”在这个概念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权的普遍性特征。1993年于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最终宣言指出:“所有人权都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④在世界人权大会上,即便是亚洲的中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其外长也都无一例外地宣称人权“当然”是普遍性的。⑤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断言:“所有人都渴望从暴力、饥饿、疾病、酷刑、歧视等的恐惧中得到解放。人权对于任何文化、所有国家而言都不是外来者,都是内生的。它们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属于所有人民。正是这一普遍性特征赋予了人权超越任何国界和一切藩篱的力量。”⑥对此,一位学者声称:人权要么是普遍性的,要么就什么都不是;根本不存在人权是否普遍人权的问题,只能说人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普遍的。⑦ 人权的普遍性直接渊源于人权的反抗性和消极性。反抗性是说人权是作为公民/居民反抗政府压迫的概念而产生的。保护人权的观念虽然兴起并获得承认,但是侵犯人权的实践却不断上演。因此,人权的观念就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约束,它处理的是政府与人民、公民、居民之间的关系,它基本上不涉及公民与公民、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传统上,它也不涉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位学者所言:“与自然权利不一样,只有官方的侵犯才能称得上是对人权的侵犯。”⑧从人权国际公约的功能来看,所有公约实际上就是各国政府承诺不侵犯人权的一种宣示,是政府同意对自己进行约束所作的承诺。与人权的反抗性相承接,西方主流人权哲学主要表现为消极人权观。也就是说,人权主要是权利个体反抗国家及其政府压迫的权利;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看,国家只需要不去做某些事情,就可以实现保障人权的目标。 主流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个人性质的。虽然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也使用了“人民”这样的字眼,但在西方主流人权哲学家们看来,人权应当而且只能是个体性的,不应当而且也不存在所谓的集体人权(collective human rights or group human rights)。在人权国际公约当中,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其他所有权利几乎都是个体性的,其关于权利主体所使用的措辞,几乎都充满了个体性。“任何人(every human being)”、“每个人有权(every one has the right)”、“任何人都不得……”(no one shall be)等字眼,都是在个体的意义上规定人权。即使在那些人们本来有理由期望被表述为集体人权的地方,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被表述为个人人权。杰克·多纳利认为,既然人权是只要作为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也只有人才享有的权利,那么,一个主体如果不是人(human being),就不享有人权;同时,因为只有个人才是人,因此只有个人才享有人权;集体可以享有各种权利,但是不能称这些权利为人权,除非重新界定什么是人权。⑨ 基于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西方主流人权理论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两个公约的母公约,其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重要性方面则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对缔约国违反公约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禁止要求以及相应的程序;后者则仅仅是提出了愿望性的标准(aspirational standard)。后者仅仅是对理想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描述,它希望所有的缔约国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却并没有说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至于说它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则由他们自行决定。按照前一个公约,至少缔约国要受其约束;但按照后一个公约,则什么是遵守公约什么是违反公约都是不确定的,每一个缔约国都是不受挑战的,当然也不会因为违反公约而受到制裁。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直被认为“有牙齿”,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则“没有牙齿”。⑩ 另外,从权利的等级来看,很多主流人权理论家都认为反暴行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才是更基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则是次级的。因为,反暴行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都属于消极权利,它们的保障只需要政府不去做特定的事情,例如虐待、迫害其公民、恣意杀害其人民、对其人民实行种族灭绝等,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则属于积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有待于政府积极的作为,因为只有积极作为才能满足这些条件。保障反暴行的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只需要政府约束自己不去做某些事情即可,因此是可以立即实现的,是可以马上兑现的;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则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它们需要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因此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均持这种立场。(11)事实上,美国一直没有批准也没有加入《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主要理由一是美国认为这些权利与他们固有的观念不符,二是认为这些权利独占性属于政府所有,国际公约对这些事项加以规定会侵犯到一个国家的主权。(12) (二)当代主流人权观的理论基础 尽管关于人权的论述五花八门,有些观点甚至相互冲突,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二战以来的人权运动及其背后的人权理念,主要体现了国际范围内的自由主义传统。(13)有的学者干脆将人权视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遗产,其中包括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14)笔者认为,当代主流人权毫无疑问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产物。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又主要受罗尔斯等平等自由主义哲学理论的影响。学术界一致认为,罗尔斯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路易斯·亨金指出:罗尔斯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15)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被推崇为西方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最伟大的成就”[11](P.456)。罗尔斯的理论既在政治哲学上广受崇拜,其对人权的论述也得到广泛接受。可以说,当代西方主流人权观,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基础之上。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权从诞生之初就是罗尔斯理论的产物,而是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哲学为当代西方主流人权理论提供了更多的精神养分。因此,了解当代主流人权观,离不开罗尔斯的哲学理论。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主要建立在“无知之幕”、“反思均衡”等方法论的基础上。罗尔斯以其独特的方法,在古典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出自己的理论(新社会契约论),以此取代了功利主义哲学对自由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述。根据罗尔斯的论述,所谓“无知之幕”(vein of ignorance),就是在一个假想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中,所有人都必须忘掉自己是谁,从而在达成社会契约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性别、年龄、能力、自己的财富、自然资源、社会地位等信息;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例如是喜欢冒险,还是倾向于保守,是积极乐观,还是消极悲观等;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文明或文化水平。(16)不过,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也并非全然无知。相反,他们还是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的原则,了解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类的一般心理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在无知之幕背后,人们对于一般性事物都全然了解,对于特殊事物则一无所知。 所谓“反思均衡”,就是假设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基于他们的背景知识,建构出若干他们认为公正或不公正的见解。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这种并非基于一时冲动或情绪武断,而是在一个人心境澄澈、良知光明之时,在对人生进行反省思考得到的信念或价值观,就是罗尔斯所称的“慎思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17)罗尔斯的方法,就是要人们由这个原初的判断出发,去建构和推演自己的道德原则再由这个道德原则回头去正当化原初的判断。罗尔斯强调,这个原初的判断或者信念,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固定点;在推演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理论与信念不一致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对未完成的理论的信心大于我们已经秉持的信念,那就修改我们的信念;如果对已经秉持的信念的信心大于未完成的理论,那就修改未完成的理论;我们需要在理论判断和直觉信念判断之间反复来回思考,直至达到两者之间最合适的吻合,这种状态就是“反思均衡”(reflective equilibility)。(18) 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只能保护平等而不能选择平等;在原初状态下,每一个人,无论其特点或兴趣如何,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借助于与其他人的不同来保证自己得到更好的处境。在这一前提下,人们进入无知之幕中探讨人类社会的组织和分配原则,将得出两个基本结论:(1)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与所有人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2)社会或经济的不平等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些不平等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弱势者得到最大照顾;二是所有的机会或职位应当向所有人平等开放。(19)在罗尔斯看来,第一个原则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这一优先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不能因为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受到违反;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以及权力的等级制度,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20) 罗尔斯的理论得到法理学家德沃金的有力支持。德沃金认为,基本权利就像是扑克游戏中的王牌,无论其他砖块花色,见到王牌都必须自动认输;不过,王牌虽然能打败所有其他砖块花色,却也不是天下无敌。当王牌对上王牌,二者就可以厮杀一番,决定胜负。只有王牌能够对抗王牌,只有人权能够对抗人权。除人权以外,其他任何考量,都不能作为侵犯人权的依据。(21)这就是德沃金的“王牌对王牌”原则。德沃金强调,这一理论是把个人放在中心地位,把个人的决定或行为看做具有根本性的东西;它与以目标为基础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尽管它们也计算政治决定对不同个人的影响,并从这个角度关系个人的福利,但是它们把这些影响淹没在了整体或普遍之中,并且把整体和普遍的改善看做是理想,完全不考虑任何个人对于理想的选择。(22)德沃金明确指出:个人权利就是个人享有的政治王牌。当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而享有权利时,任何集体的目标都不足以否定个人作为个人行使那些权利;也不足以正当化那些使个人遭受损失或伤害的行为。(23)正是对个人为中心的强调,使罗尔斯、德沃金与功利主义区别开来。因此之故,罗尔斯德沃金的理论,又被称为“平等自由主义”理论。本文将其理论中对于人权的命题,称为“平等自由主义人权观”。 (三)主流人权观面临的批评 尽管主流人权观主宰着西方人权理论,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平等自由主义哲学也在西方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主流人权观的批评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显然,普遍人权观这种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不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尤其是不为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列强欺凌,以及正在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以及民族自强的国家反对。针对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这些国家纷纷抛出了主权高于人权的观点,从而形成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权领域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实质性主张,就是文化才是道德权利的基础;既然如此,基于文化的多样性而导致的制度多样性是不受任何外来声音的批评的。(24)对文化相对主义而言,没有任何事情对于所有人都一定是好事,也没有任何事情对所有人都一定是坏事。(25)在文化相对主义中,又存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所有道德权利都只能渊源于文化,因此文化才是道德权利的唯一来源;强烈的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文化是权利或规则有效性的首要来源;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则承认文化是权利和规则有效性的次级来源。(26) 相对主义对人权的批评各有不同,其批评的重点却基本一致。首先,在人权观念的起源和内容上,相对主义认为现代人权概念起源于西方,甚至主要体现了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如同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粗读便知,(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这些权利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与制度。”[12](P.2)那些主张普遍人权主义的学者中,也有很大一部分认为,人权概念不仅起源于西方,而且体现的也是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验;非西方社会不仅缺乏人权的实践,而且完全没有人权的概念。(27)这种知识论上的傲慢和自负,更加助长了极端文化相对主义对人权概念的敌视。其次,文化相对主义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人权的相对性:普遍人权必然以共同人性为假设前提;但是,由于人性实际上是被文化塑造的,如果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取决于文化,则人性就是变幻莫测的;从而普遍人权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28)最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人性源于文化的观点,文化相对主义对于普遍道德、普遍规则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相反,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权利和规则的有效性都渊源于文化;如果将本不具有普遍性的规则强加给那些不接受这些规则的群体,实际上就是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完全不具有正当性。(29) 在人权的消极性方面,有学者指出,主流人权观声称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是消极的,是不需要政府作为的,因而是更容易实现的;但实际上,有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是需要政府积极地作为才可能实现;例如游行示威的权利,它不是政府完全无所作为就可以实现的权利;相反,它需要政府派出警力维持秩序,否则反对派就有可能对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进行冲击,导致游行示威活动受到破坏。又如公正审判的权利,它要求政府必须提供公正而无偏倚的法院,必须培训法官、检察官,甚至提供免费的律师帮助;因此,尽管乍一看这些权利似乎具有消极性,但实际上这些权利的实现仍然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30) 对于人权的个体性,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现代哲学家试图对人的个体性进行解构,认为抽象的个人都是不存在的,人权理论中的个体纯粹是乌托邦式的想象。一般认为,人权理论中的权利主体被视为一个没有历史或传统、性别、肤色或宗教信仰、需要和欲望的人;天赋权利就是鼓励的个人合法的应得的权利,这位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道德的权利与义务有许多实现不受妨碍的自我的途径;批评者们则认为人权理论剥夺了人同他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之间的联系,这种观点同样是凶恶且不切实际的[13](P.108-110)。另一方面,一些人权学者批评主流人权观将人权的主体限定为个人的做法使很多“第三代人权”被排斥在人权的范围之外,这显然不符合人权概念发展的趋势。这种观点实际上并不否认个体人权的存在,他们只是强调人权不应仅限于个体人权,诸如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等集体性权利,也应当属于人权的范畴。(31) 面对这些批评,自由主义者也进行了丰富、热烈而充分的回应。(32) 三、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立场 本文赞成平等自由主义关于人权的论述,主张人权应当是一种所有人平等享有的反抗性权利,因此它应当是个体人权、消极人权和普遍人权。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对人权应当具有的基本立场,也是确定刑事诉讼人权涵义的基本原则。 (一)刑事诉讼人权理论应当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观 所谓具有普适价值的人权,就是说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是指人权不因文化、地域、国别、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变化。本文主张人权具有普遍性,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从人权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人权是一个反抗性概念,其功能和作用是建构一个客观的道德观念体系,以此作为批评现行法律及政府行为的武器。夏勇指出:“在观念上,人权要求反映了人们反抗特权、反抗社会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在现实中,法律权利逐步增长乃至进化为人权,是人们反抗人身依附、政治专制和精神压迫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结果。”[14](P.163)可以说,人权及其依赖的观念体系乃是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道德体系而产生,其目的和作用就是对具有主观性的法律进行批判和改良。因此,各国法律虽有不同,人权却不能有异。因为,普遍性正是人权具有批判性的基本前提。失去了这个前提,各国政府都可以主张不同的人权,人权的内容将随着文化、地域、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人权也就失去了客观性,变成和制定法一样,成为完全主观的了。主观的观念不能用来当做批评主观的法律和制度的依据。因此不具有普遍性的人权概念也就不具有批判性,也将失去其反抗性特征,人权概念将毫无意义。 其次,普遍人权理论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人权的反抗功能,先哲们竭尽所能地将人权建立在普遍道德的基础上,以便使人权的内容具有客观性,从而具有批判性。如同杜兹纳所言,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认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所有人都完全一样;因此,通过人权得到认可的政治渴望给予各种身份以平等的保护[13](P.49-50)。人权的普遍性体现的是人类需求的普遍性,是人类本性的同一性。但是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不可能所有的需要都是相同的。中国古代哲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就是承认人既有普遍性,也有多样性。英国理论家米尔恩认为:作为最低限度标准的人权,本身就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这种人权标准为多样性的范围设立了道德限制,但却绝不否认多样性的存在[15](P.7)。任何过于极端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因此,本文所持的普遍性立场,乃是一种相对折中的普遍性立场,它承认人的多样性,但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抹杀人的普遍性。它承认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但是它认为所有人在不希望遭受某些待遇方面,绝对是一致的。 再次,普遍人权是平等人权的理论前提,不承认普遍人权必然导致人权问题上的不平等对待。罗尔斯认为,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应当是由合作各方的人们所达成的协议决定。罗尔斯说:“在理性多元论的假设是既定的情况下,公民无法一致赞同任何道德权威,比如说一种圣经、一种宗教机构或一种宗教传统。他们既无法对价值的道德秩序达成一致意见,也无法对某些人视为自然法的东西的旨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比在对所有人都公平的条件下公民自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更好的选择吗?”[16](P.23)也就是说,人权作为公平合作的条件之一,仍然是缔结社会契约的结果。只不过,罗尔斯所说的社会契约,并不同于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在古典社会契约论者看来,社会契约的达成是基于自然状态;而在罗尔斯看来,社会契约不是基于自然状态,而是在承认所有人都平等的前提下,由这些理性的人在一个假设的原初状态中经过反思均衡而达成的协议。这种在原初状态中达成的协议既是假设的,又是非历史的。由于它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所以它一方面避免了自然状态不存在这样的诟病,另一方面却另辟蹊径实现了自然权利论没有达成的目标:为普遍道德权利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途径。因为这样的协议已经足以成为理性多元的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从而为评价现实中存在的法律制度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 毋庸讳言,从宏观视野来看,普遍性概念在两个方向发生过作用:一方面是在国际的层面上,普遍人权理论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殖民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冷战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普遍人权观念也为有限政府理论提供了坚定的理论支持。洛克、霍布斯等人的国家权理论、有限政府理论均源于其对于自然权利意义上的人权的界定。罗尔斯曾明确指出:“在人民的法律的理性中,人权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限制了对战争及其行为的合理化推论,并且为一种体制的内部自治性设置了限制。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反映了自二战以来孕育的关于主权权力行使的两个基本的历史性的深远变化:首先,战争不再仅限于推行政府的政策才被允许,或者仅仅出于自卫或者在严重案件中为保障人权而进行干预才可被正当化;其次,一个政府的内部自治已经受到限制。”(33) 最后,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可以也应当确立普遍人权观。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从传统上看,我国传统观念虽然没有人权的概念,但是却也没有哪种观念与人权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恰恰相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观念完全兼容。狄百瑞指出,儒家思想尽管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存在明显的不同,但在儒家思想中也存在与自由主义价值观要素相对应的要素[17](P.150)。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不能兼容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普遍价值,只是在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把这些价值与制度进行了有效配置的情况下,儒家却未能把其内在价值彰显为现代制度[18](P.58)。这实际上是说儒家传统也是包含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只是欠缺将这些价值予以制度化保障的机制。更有论者明确指出:“‘人权’或‘权利’的概念或名词虽然是西方的,但人权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9](P.12)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在二战期间为人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理应在普遍人权观念上继续做出贡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1年提出了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四大自由”之后,美、英、中、苏等国家就于1942年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声明为四大自由而战,该宣言为战后联合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P.71)。1945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通过了包含人权内容的《联合国宪章》,中国也是该会议的主要参与国。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这一人权法律文件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并领导了该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构建国际人权保护体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文本投票,中国投了赞成票[19](P.84、94)。第三,从国家发展的未来来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更应该承认并宣扬普遍人权观念。一个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念的国家,永远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要对外输出价值观念,首先必须要承认价值观念的普遍性,至少要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核心价值的普遍性。一个完全不承认普遍价值的国家,既不能输出价值观念,也不能为普遍价值做出贡献,当然也就难以在国际问题上担当起领导的责任,而只能日益被边缘化。在很多场合,人权都被视为是“西方人赠给剩余人的礼物(a gift of the west to the rest)”。(34)从前述人权发展的历史及中国在此过程中的贡献而言,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公正的。但是中国过去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说法,又的确为这种说法提供了论证。中国要改变这种局面,不想成为“剩下的(the rest)”,就应当而且必须扛起普遍人权这面大旗。我们可以在人权的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人权普遍性问题上则应当当仁不让。 (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应当是消极人权而不是积极人权 从经验上看,人权概念的功能是公民个人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恣意侵犯。人权概念的起源与政府对公民个人的压迫息息相关。如同杜兹纳所言:人权获得成功并且不断被编入法典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民一直受到他们自己政府的残酷对待[13](P.26)。马克思指出,“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解除其无权的痛苦就“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20](P.466)。因此,人权具有解放的概念。在历史上,人权就是对抗政府压迫的一种手段。它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得到界定的,它强调的是:政府不得任意侵犯公民的各种基本自由。政府必须尊重人权,正是这一意义的另一表述。如今,政府压迫公民这一现象在世界上仍然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政府总是要压迫公民的,无论是西方的政府还是东方的政府均无例外;对公民个人自由而言,政府的管束永远都是一种必要的恶。正是由于政府权力容易造成对公民自由的任意侵犯,才存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需要。人权就是这个笼子的钢筋,它是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的基本武器。因此,强调人权的消极性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人权被作为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权利来看待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消极的意义上,人权中的生命权就是指生命不受恣意剥夺的权利;自由权就是指自由不受恣意干预的权利。失去了这个特征,人权必然丧失其普遍性。因为,如果不将人权限定为消极性权利,人权概念的边界必然被模糊化,从而任何权利都可能在人权的名义下提出,人权概念也就失去了其普遍性特征,也就丧失了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权利所能够发挥的功能。 从宏观层面看,也就是从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保障消极人权也远较保障积极人权重要。如果我们将消极人权界定为真正的人权,则积极人权不过是人类的一些需要而已。(35)究竟是保障基本的人权更重要,还是保障无边际的需要更重要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克兰斯顿指出:常识告诉我们,救火车和救护车都属于关键的设施,然而游乐园和度假帐篷却不属于;慷慨宽容和仁慈友好都属于美德,但是这些美德所要求的道德义务与拯救一个落水儿童的道德义务完全不属于一个层次。(36) 综上所述,人权乃是最低标准,它的目的是防止最恐怖的事情,而不是追求最好的结局。因此它提出的目标是“必须做”而不是“最好去做”。(37)人权如果不是最低标准,如果不是为了防止最恶劣的情况,其重要性就必然降低。在这个意义上,“不受奴役”、“不被施以酷刑”的权利,显然比“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远为重要。坚持人权属于最低标准,因而应当具有消极性,也是为了给各国制定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人权事务的国际干预已成必然,如果将人权界定为积极的权利,就会导致各国在内政事务方面的空间受到压缩。那些一方面坚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属于人权,另一方面又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理论,实际上是想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差异性,同时打压消极人权的普遍性。 (三)刑事诉讼人权是个人人权而非集体人权 从人权概念发展的历史来看,最早的人权是指个人人权,是以个人为载体的自由主义理念生发出的人权,其载体自然也就属于个人而不是集体。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人权观中的人权主要是指个人应从国家权力的侵害下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但在现代乃至当代人权观念体系中,例如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都出现了例如自决权在内的集体人权。因此,当代人权观中的人权不仅是指从国家权力的侵害下受到保护的个人权利,而且也包括民族从殖民主义侵害下解放出来的权利等。应当说,民族自决权等集体人权的确与人权概念相关,并且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权概念的鼓舞。但是,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人权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个体人权,它无法也不应当容纳诸如民族自决权这样的人权概念。 这是因为,首先,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刑事诉讼中,通常都是只有当民族国家已经不成为问题时,其正常的刑事诉讼才成为可能。如果一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处于混战之中,或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处于战争的状态,此时正常的刑事诉讼通常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有战争的法则,而刑事诉讼则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理性形式。如果一个地区存在着正常的刑事诉讼,存在着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典并且大体上能够依照该法典解决刑事争端,则通常说明这个地区也存在着正常的民族国家。其次,即使民族之间仍然存在冲突乃至战争,人权也并非民族自决权的前提,民族自决权也不必然属于人权概念的范畴。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各民族享有自决权,而是要在维护人权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功能的前提下,维护人权的传统概念。如果将自决权作为人权,将使人权的个人性质丧失,其保护个体利益的出发点由此受到转移,其保障个体利益的功能亦将受到损害。自决权、不受盘剥的权利等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没有必要以人权概念来包容。最后,无论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在公民个人自由的优先地位尚未得到确立,从而个人自由仍然可能遭致政府的无限侵害的时候,人权这一概念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个人如何对抗政府的问题。政府仍然是个人人权的最大威胁,因此人权概念的个体性仍然有必要予以强调甚至加强。 四、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涵义与内容 既然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应当坚持普遍人权观,坚持人权的消极性、个体性,那么,一般意义上人权的内容究竟应如何界定?刑事诉讼保障的人权是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刑事诉讼人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本文认为,一般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平等权,刑事诉讼人权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权的一部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仅指正当程序权的保障。 (一)人权清单应在平等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确定 如前所述,当代西方主流人权理论认为,人权主要是指反暴行的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环境权、发展权等均不属于人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主要代表的罗尔斯对人权范围的界定却更为保守。罗尔斯认为,人权的内容应仅限于作为生存与安全之手段的生命权、在免受奴役、强迫占领以及保证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良心自由等意义上的自由权、财产权和相同情形相同对待意义上的平等权。(38)由于罗尔斯对人权内容的界定范围非常狭窄,其理论通常被称为“最终最小主义”理论。(39)如前所述,西方主流人权理论家主要将人权界定为反暴行的权利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同时排斥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很明显,罗尔斯关于人权内容的界定与西方主流人权理论家对人权内容的界定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罗尔斯将政治权利剔除出人权的范围。当然,这并不表明一个不将政治权利当做基本权利来保障的社会就是罗尔斯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人权仅仅是国际范围内相互之间可以容忍的最低限度。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可以不是自由民主社会,但是一定必须是体面的社会;只要尊重上面罗列的基本自由,一个社会就应当被认为是一个体面的社会,即使这个社会没有民主选举、没有身份平等,甚至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连这些最基本的自由都不能保障,就构成国际社会对这样的国家进行武力干预的正当化基础。(40)可见,罗尔斯是在容忍的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对人权内容所做的界定。 人权范围界定过于狭窄,自然容易引起其他自由主义者的不满。尼克尔指出,罗尔斯将人权简单地理解为国际之间武力干预的标准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人权在国际上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一些角色与武力干预完全没有关系;例如,人权同时也服务于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说服的国际标准,它意味着国际社会认可的一种关于什么是好政府的标准,并且希望和鼓励各国政府以此为标准践行其责任;人权还可以作为一种国内理想和抱负的标准,被用于作为一个国家内部追求或批评辩论的依据;此外,人权还可以作为国家自愿接受的国际条约的操作性规范,以及用于作为说服和批评的国际准则。(41) 本文同意尼克尔的分析,即人权应当具有多方位的功能。在国际上,人权除了作为武装干预的最低限度容忍标准,也可以而且应当作为国家间道德、舆论论战的依据和和平协商、劝说、相互影响的规范标准;在国内,人权应当作为所有人争取平等、自由、享受政治权利乃至提升生活水准和提出相应要求的基本依据。因此,人权应当包括反暴行的权利,可以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不妨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乃至居住权、环境权、知识产权等。但本文更赞成罗尔斯的观点,主张人权应当仅限于作为生存和安全之手段的生命权,在免受奴役、强制占领、良心自由等意义上的自由权,财产权以及相同情况相同对待意义上的平等权。从人权的普遍性立场来看,只有将人权范围界定得比较狭窄时,对人权的普遍接受才更有可能成为事实,而并不总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类理想。毫无疑问,西方社会所尊崇的民主选举、自由结社、出版自由乃至社会福利等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由于它们的出身的确很容易让人将它们贴上“西方”的标签,从而也很容易使它们遭到“非西方”的攻击。因此,将公民权和政治权纳入人权的范围,无疑会增加人权概念在非西方社会获得普遍接受的难度。若退一步,仅仅将人权界定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平等权,反而为人权问题上的东西对话提供了基础,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温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的赞同(当然,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善罢甘休的)。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对人权的界定破除了人权是西方社会专利的神话,并将人权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体面的标准。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退无可退、少得不能再少的人权清单。一个社会如果连这样的基本自由都不承认,必然是一个极端专制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 即使不考虑以上因素,在刑事诉讼中,罗尔斯所主张的最低限度人权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刑事诉讼基本上不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般也不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虽然从更加宽泛的角度而言,一个人由于遭受刑事追诉而也可能被剥夺政治权利,但是相较于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而言,政治权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时,对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人权,如果这些权利也属于人权的话,它也应当由国家立法部门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法律与政策,以及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律,对这些权利进行保障。刑事诉讼作为一个追究被指控人刑事责任的程序机制,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皆毫无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这些权利与刑事诉讼人权无关,不属于刑事诉讼人权。 (二)刑事诉讼人权特指正当程序权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一般意义上的人权界定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平等权。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均不属于人权。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应当比这个范围还要狭窄。一般意义上的基本人权既有其实体部分,也有其程序部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当仅包括其中的程序部分。从程序的角度而言,前述三项基本人权又可以分别表述为不被任意剥夺生命的权利、不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权利和不被任意侵犯财产的权利。刑事诉讼人权就是指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任意剥夺和侵犯的权利。其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对应着正当程序权;其在历史上,与英国1215年大宪章、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美国1789年权利法案中规定的程序性权利一脉相承。无论正当程序的内涵是什么,人权都是其基本内涵。也就是说,人权是正当程序的最低界限。一个刑事诉讼程序,无论其设计多么精美,如果不保障人权,就不是一个正当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权是正当程序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内核。 在西方,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就是指正当程序权的保障,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争议。但是正当程序权的内容,却因各国而异。如同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如何界定刑事诉讼程序语境中我们心意所属的人权,实在并非易事……也许所有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莫过于定罪量刑后被告知详尽理由的权利;如果这是基本人权,则所有本书考察的程序都拒绝了这一权利。(42)在美国,正当程序这一概念,本就几经变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正当程序观念一直被理解为“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也就是只要符合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就是正当程序;之后,正当程序观念又被界定为权利法案规定的程序;有时候被界定为以事实真相为基础的程序;直至最后被界定为“基本的公正(fundamental fairness)”。(43)在加拿大,刑事诉讼人权的内容,基本上根据《加拿大人权宪章》的规定来确定。(44)在欧洲,欧盟国家刑事诉讼人权的内容,基本上依据《欧洲人权宪章》的规定来确定[21][22]。英语国家的其他著作中,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内容也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人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而且应当参照国际人权公约来确定。这是因为,首先,国际公约是在经过各国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的,其对于人权范围的界定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又综合了人权哲学家的各种意见,还协调了不同国家关于人权问题的不同意见,以它作为标准,更容易获得正当性。其次,从人权国际公约获得签署和批准的程度来看,人权国际公约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同,并逐渐成为各国人民在国际国内争取人权的有力武器,可以说,国际人权公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一致性,它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各国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的承诺。再次,人权国际公约规定的有些部分虽然存有重大争议,但是,这些权利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线索;它是全人类在通往文明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的结晶;即使我们不能将其中的全部都视为人权,也可以对其中规定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从而免去毫无根据的闭门造车。最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人权国际公约中的《世界人权宣言》虽然不是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渊源,但是其中的许多规范频繁地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获得引用,其中的多数规范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为具有国际范围内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45)因此,人权国际公约应当作为我们确定刑事诉讼人权内容的基本指引。 当然,参照并不是依照。对于人权公约中规定的具体程序性权利,也要在平等自由主义原则下进行审视、分析和鉴别。本文拟将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十二项权利作为刑事诉讼应当保障的基本权利。第一项,无罪推定的权利,这是通行于世界各国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二项,不受任意逮捕拘禁的权利,这是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的基本要求。第三项,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这是住宅权、财产权和私生活秘密权的核心内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表述为“私生活秘密不受任意侵犯的权利”。第四项,由依法设立且独立无偏的法庭审判的权利,这是所有人权得以保障和得到救济的制度基础。第五项,公开审判的权利,这是防止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恣意剥夺的有效保障。第六项,被告知指控性质及原因的权利(含获得免费译员帮助的权利),这是遭受刑事追诉者有效地准备辩护的前提。第七项,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主要是指按照自己意愿选聘律师的权利。第八项,迅速审判的权利,这是防止无限期关押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基本保障。第九项,对质权,这是公平审判的基本要素。第十项,强制程序取证权,这是被告人有权举证自证清白的有效手段。第十一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这是对刑事被追诉人人格尊重的基本体现。第十二项,不受双重归罪的权利,这是防止政府以不断起诉的方式迫害公民、侵犯人权的基本设置。 除以上权利以外,《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规定了获得免费译员帮助的权利,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申请上一级法院复审的权利,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适于未成年人诉讼的权利,以及冤案赔偿的权利。对于获得免费译员帮助的权利,本文认为可以纳入被告知指控性质及原因的权利,没有必要单独列出。对于获得免费律师帮助的权利,本文认为属于积极权利,不符合人权的基本定义。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适用适于未成年诉讼程序的权利,本文认为,未成年人案件虽然有一些特殊要求,但是其基本原理和成年人案件是一样的;如果成年人犯罪的诉讼程序权利得到了保障,未成年人正当程序权自然也会得到保障;如果成年人诉讼程序设计都不合理不正当,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也很难正当。因此,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障应当是所有刑事被追诉人正当程序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后进一步发展的事项。另外,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适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权利本身也体现在公正审判权等权利的规定中,将其单独拿出来讨论并无特别的必要。最后,《世界人权宣言》也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适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权利,原因就是该权利已经包含在其他有关正当程序权的规定当中。 本文也没有列入冤案赔偿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从人权的消极性角度来看,冤案赔偿的权利虽然重要,但它在性质上主要是一项积极的请求,而不是消极的主张。人权应当是最重要的权利,决定一项权利是否人权的标准之一就是其无比重要性。一个人在被政府冤枉后当然应当有权要求赔偿,但是这项权利没有必要提到人权的高度。最后,关于上诉权,本文也不将其当做人权来对待,因为上诉主要是解决刑事裁判的正当性和终局性问题并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个不允许上诉的司法制度固然让人不爽,却不一定是最坏的制度;一个允许不断上诉的制度固然让人觉得这个司法制度重视被告人的上诉请求,但是却不一定是好的司法制度。例如,英美陪审团审判一直不允许就事实问题上诉,但是该制度一直运转良好;中国古代实行所谓逐级审转复核制,杨乃武案件前前后后上诉三次,审转六次,(46)只能说明该制度从第一审就没有设计好。因此,从极端重要性的角度来看,上诉权并不满足这一条件。 五、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 (一)刑事诉讼人权的主体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刑事诉讼人权是所有人均享有的人权。任何人,只要受到刑事追究,都需要这些人权。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刑事诉讼人权的持有主体是所有人,任何人,每个人。这也与人权的初始意义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权就是指只要是人就应当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人权既然也属于人权,那么,只要是人就享有正当程序权。但同时,当人们说正当程序权应当为所有人享有时,是在平等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说所有人都享有正当程序权,它的意义在于排除不平等。也就是,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因素,一律平等地享有正当程序权。值得指出的是,正当程序权通常只有在受到政府刑事追究的场合才发挥作用;一般人在一般场合基本上用不到正当程序权。这是因为,正当程序权从其性质而言,就是一项与程序有关的人权;因此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下,这些权利才显示出其意义。例如不受任意逮捕与拘禁的权利,对于任何一个视逮捕与拘禁为刑事处分或者意在施加刑事处分的国家,它都意味着一个刑事诉讼的开始。又如无罪推定的权利,迅速审判的权利,公开审判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所使用的措词本身,已经限定了其发挥作用的语境,它们天然地属于刑事诉讼中特有的权利。只有在刑事诉讼开始或发生之后,这些权利才发挥作用,才有其意义。 自然地,刑事诉讼人权的主体也应限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是因为,正当程序权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不受政府恣意追究的权利;它是施加于政府权力之上的一种限制。在刑事诉讼这一特定的语境下,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是刑事诉讼的被追诉人,他们才是“逮捕拘禁”、“秘密审讯”、“有罪推定”、“无限期羁押”等政府行为的侵犯对象,所以他们才需要“不被任意逮捕拘禁”、“不被秘密审讯”、“无罪推定”、“迅速审判”等权利。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就其作为被害人而言,是用不到这些权利的。因此,当我们说到刑事诉讼中的保障人权时,指的就是保障刑事被追诉人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通常不包括所谓“被害人人权”,也不包括所谓证人的人权。这并不是说被害人、证人作为人不享有人权,而是说被害人、证人作为刑事诉讼语境中的被害人、证人这一特定身份,不是刑事诉讼人权的持有主体,因为他们不是政府追究的对象。一旦政府对他们施加了逮捕拘禁、公开或秘密的审讯等行为,他们也就从被害人、证人的身份变成了刑事被追诉人,此时,他们作为一般人而言,作为所有人的一份子而言,同样享有刑事诉讼人权。但此时,他们在刑事诉讼语境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永远都不存在保障所谓被害人人权的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在被害人人权和被告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既然被害人人权都不存在,何谈所谓在被害人人权与被告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呢?那些主张既要保障被告人人权,又要保障被害人人权的说法,虽然表面上看很容易获得支持,但实际上是根本经不住分析的。另外,保障被害人人权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权主要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涉及公民与公民的关系问题,而且是因为,如果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护,被害人人权也不可能得到保护。因为被告人的权利才充分体现了政府如何对待其公民的态度,政府如果可以找借口侵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它侵犯被害人的权利也就毫无心理障碍。 (二)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不受被害人利益之权衡 既然刑事诉讼人权就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被害人就其作为被害人而言并不是刑事诉讼人权的主体,那么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既要保障被告人人权,也要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问题,更不存在“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的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被害人就其作为被害人而言,不存在基本权利被“任意侵犯”的问题,或者说其所面对的情形,往往不是实体权利面临任意侵犯的问题,而是已经遭受了侵犯之后,如何对他的权利和利益予以恢复、救济的问题。如果被害人就其作为一般人也遭到政府的任意侵犯,则他当然也面临人权保障的问题,但此时他的对手乃是政府而不是其他人也不是被告人,因此仍然不存在被告人人权与被害人人权发生冲突的问题。这是前文得出不需要在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的基本前提。 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与刑事被追诉人在人权问题上永远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不错,在反对政府任意侵犯的问题上,被害人、刑事被迫诉人在多数场合立场都是一致的。但是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语境下,刑事被害人和刑事被追诉人的利益,又往往是不一致的。二者一致的场合,也许仅仅存在于当无辜的被告人被冤枉的情形下,被害人报复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但即便如此,如果被害人真诚地相信被告人就是加害人,则尽管被告人是被冤枉的,对其施加惩罚也会使被害人的心灵得到抚慰)。在刑事被迫诉人就是事实上的加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也可能会寻求正常途径之外的惩戒,有时候甚至会超过文明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另外,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如果被告人就是加害他的人,迅速将他定罪判刑以解心头之恨也是符合他的诉求的。从立法上、司法上看,是满足被害人“从重从快”的需求,还是也要充分地、尽可能地保护刑事被追诉人在一个文明社会所应当享有的正当程序权,也需要立法者和法律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作出选择。因此,仍然存在着如何在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利益之间进行协调的问题。 笔者认为,不应当在被害人权利和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这不是因为被害人的权利不重要,而是因为被害人的权利不如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重要。对此,本文提供如下论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刑事司法制度中,无罪推定原则之所以如此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辜者被冤枉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在这一前提下,正当程序权往往是防止无辜者被冤枉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允许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怜悯而突破正当程序机制的限制,放弃对刑事被迫诉人正当程序权的保障,则无辜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将烟消云散,这将大大增加无辜者被冤枉的可能性。其次,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不能说刑事被追诉人永远都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但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被追诉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法治程度如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拥有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拥有搜查、扣押公民住宅、财产的权力;拥有对公民的邮件、电报进行查询、扣押的权力;拥有对公民的存款、汇款进行查封、冻结的权力;等等。在这些权力面前,人权保障的立场只要求:政府不要恣意地侵犯这些权利——前文已将人权界定为“不受恣意侵犯”的消极性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刑事被追诉人与被害人的利益权衡问题上,对刑事被追诉人的保障已经充分考虑了刑事被害人的诉求,刑事被追诉人的利益已经退无可退,再继续对其权利进行权衡已经根本没有可能。换句话说,无论是基于被害人什么样的利益,被追诉人“不被任意地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总是不能被剥夺的。如果连最后这点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就真的成为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任人宰割的牲口。他们就不再成其为人了。他们就不具备基本的人格了。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都不应为了一个其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的人,就剥夺另外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尊严。第三,也是经常面对的,同时也是本文必然要涉及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在血腥的暴行的情况下,当存在令人发指的暴行的时候,也不能假被害人之名,侵犯被迫诉人的所谓人权吗?本文的回答是:不能。因为如何界定“令人发指的罪行”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人权要想获得尊重,就必须永远获得尊重;一旦在某处决口,将有可能导致人权保障的整个大堤崩溃。 以上观念过去很长时期都难以获得认可。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刑事被迫诉人人权相对于其他人权利或利益的优先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比较而言,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该款的规定没有特别提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特别提到辩护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在原条文的基础上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主体,并特别提到辩护权这一权利。传统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当事人,同时也是诉讼参与人。诉讼参与人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被害人、证人、鉴定人、辩护人、翻译人员等均属于诉讼参与人。法律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都需要给予保护。法律不会做无意义的事。立法在此处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单独拿出来予以强调,表明立法者希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予以重点保护;这与本文所持平等自由主义人权观的立场不谋而合,也印证了人权保障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观点。同时,该规定还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单独拿出来予以强调,也表明立法者认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中,要对辩护权给于重点保护。这也是因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人权,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诉讼权利均以辩护权为基础。所以,保障辩护权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强调基本人权。这一规定也表明了立法上对于基本人权保护的优先性。换句话说,上述规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指导司法实践时应当侧重两个方面:首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与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其次,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尤其应当优先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这一基本权利。 (三)刑事诉讼人权不受“公共利益”权衡 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除了主张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权衡以外,还普遍存在着要在保障人权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例如,有论者认为:“刑事司法制度不应只考虑被告人或已决犯的宪法权利,而应同样考虑到犯罪被害人的宪法权利和人权。”并主张刑事诉讼人权应以被告人、被害人人权保障为主,兼顾其他诉讼参与人人权保障的原则[23]。这种主张实际上认为,人权是可受限制、可受剥夺的,限制或剥夺的理由则不外公共利益、社会安全、案情重大复杂、取证困难等等。其实,在欧洲人权法院,上述所有对人权进行限制的理由都曾经为欧盟国家所主张过;同时,在欧洲人权法院内部,各法官的主张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有些案件中,人权法院的裁决并且还隐约透露出人权可受权衡的意思。(47)可见权衡论者在世界各地都有广阔的市场。 笔者认为,应当在保障人权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当人们以所谓“公共利益”来平衡或削减对人权的保障时,实际上是假定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必然是两个相冲突的概念:公共利益是公共利益,保障人权是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必然削减公共利益,加强公共利益必然削减保障人权。这显然是对公共利益的一个偏见,因为它假定保障人权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但是这一假定显然不正确。事实上,公共利益有很多方面,保障人权可能与其中的某些部分相冲突,但不能说保障人权与公共利益就一定是冲突的,因为保障人权也是公共利益中的一部分。路易斯·亨金指出:一个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个人权利得到蓬勃发展,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不断促进被视为公共善的社会。(48)因此,我们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公共利益,其中一种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公共利益,另一种是以追求其他公共善为目标的公共利益。真正冲突的是两种不同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保障人权和公共利益。当两种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存在哪一种公共利益必然优先的问题,因此也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当保障人权所体现的公共利益与体现其他公共善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就一定要败下阵来。可见,当人们以“公共利益”为由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时候,实际上是将“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单向度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论证的基础: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公共利益被普遍接受为惩罚犯罪所带来的利益。这种看法忽略了人们对于保护基本权利的需要也是公共利益的一个方面:不仅惩罚犯罪是公共利益的要求,保护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同样是公共利益的要求。当我们承认“公共利益”并非一个简单的、单向度的概念所能概括的时候,人们将不难发现,以“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人权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当人们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对人权进行限制或削减时,实际上是以多数人或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考量依据。但是,人权是一个不受多数人利益考量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表明,多数并不总是正确的;多数的意志也应当受到少数的约束;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能由多数表决加以限制或剥夺。正如阿伦特所言:“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组织和机制都高度发达的人类将非常民主地——亦即根据大多数人的决定——得出结论,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最好清除掉其中的某些部分。”[13]如果允许多数限制或剥夺少数的人权,种族灭绝必将死灰复燃并且获得其正当性。第二,当我们将一项权利定义为人权时,就是说这项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它对于人的尊严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它是保证人之为人所必须的根本条件,它是退无可退、少的不能再少的权利请求。正因为如此,人权是一个可以用来抗衡多数的制度,是一个反功利主义的制度。无论是从人权概念的起源还是人们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对它的使用来看,人权都是代表了一种基本的权利,都被赋予了某种特别的期待,从而也是一种在被其他利益考量时必然具有某种优先性的权利,至少不是可以通过功利主义的利益衡量而予以削减、限制或剥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民主的;它是经过理性的反思之后对少数人的保护,它反对多数的暴政,反对以多数人利益之名侵犯或剥夺少数人的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易斯·亨金认为,人权是个人用来抗衡社会的权利,社会不能以更大的善或者更多的善以及所有人的一般的善为由要求个人牺牲其人权。(49)但同时,人权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民主的。因为:第一,几乎所有的人权法案都是经民主的程序才产生的;第二,在民主国家中,只有保护人权才能使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加强;第三,保障人权也是民主政府的一个基本义务。(50) 最后,说人权不受公共利益权衡,是指人权不受公共利益中其他公共善的目标权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权就完全不受任何利益衡量。实际上,根据德沃金的“王牌对王牌”理论,还是可以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只不过能够限制人权的只有人权而已。德沃金指出:“我最多只能想到三个可以使限定某项权利的措施具有一贯性的根据。第一,政府可能证明,在这个特殊案件中,原初权利所保护的价值并不真正处于危险状态,或者只是存在某种被稀释了的危险。第二,政府可能证明,如果这项权利的内容包括这一边缘案件,那么,我在前面所论述的强硬意义上的与之对立的权利就可能受到削减。第三,政府可能证明,如果权利是如此定义的,那么社会的代价不仅会越来越多,而且可能超过最初承认的权利时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达到足以证明任何侵犯人的尊严和平等为合理的程度。”(51)德沃金的意思就是:人权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如果一定要限制,政府一定要将限制人权的做法予以正当化论证;而其论证的角度只能从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除此以外,任何限制人权、削减人权的做法都是不能容忍的。 综上所述,既然多数并不拥有任意处分少数之利益的权力,那么,当然也不能以“案情重大复杂、取证困难”等为理由,作为限制人权的正当化途径。因为,无论如何界定“案情重大复杂”,其目标都是要镇压犯罪。而如果公共利益本身已经包含保障基本人权这一内容,那么,镇压犯罪本身单独并不构成“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在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惩罚犯罪才具有正当性。 从历史上看,人权概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概念。在任何国家,当一个政府想要压迫其人民时,刑事诉讼总是最称手的武器。也因此,人权从一开始就与刑事诉讼息息相关。也正是在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呐喊来的格外热烈。当然,人权概念最开始也是一个不平等的概念,甚至刚开始还渗透着种族歧视、女性歧视等因素,但无论是后来的黑人解放,还是妇女平权,也都是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得到灵感和受到鼓舞。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人权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污点,就把它的作用抹杀掉,而是应该从人权起源的历史环境,从它曾经具有而且应当具有的功能出发,来解释和界定人权。事实上,西方国家的人民在历史上主张人权的时候,是用人权的概念来反对政府的压迫,而政府的压迫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对人权的需求仍然强烈。可以说,人权的历史既给了我们经验,也给了我们教训。经验就是人权应当限定在消极权利的范围以内,这样它才能抵抗其他的利益衡量;教训就是人权不能只是一部分人的权利,所以本文主张平等自由主义人权观。在这个基础上,笔者主张刑事诉讼人权就是刑事被追诉人享有的正当程序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消极性、个体性的特征。刑事诉讼人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他性地享有,被害人等不存在人权保障的问题。那种认为需要在被害人人权和被告人人权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完全是混淆是非的。认为应当在公共利益和人权保障之间进行权衡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刑事诉讼人权是不受权衡的。只有当人权历史得到系统的梳理,人权理论得到完整的考察,人权概念得到很好的界定,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论才有坚实的基础,刑事诉讼法学也才会有理论的自觉和立场的自信。 ①Louis Henkin,The Age of Right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13(1990). ②See Micheline R.Ishay,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Globalization Er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13(2007). ③Id.p.213(2007). ④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pp.525-563(1994).See from,Peter R Baehr,Human Rights:Universality in Practice,Palgrave,p.10(2001). ⑤Peter R Baehr,supra note 17,p.10. ⑥Kirsten Hastrup,ed.,Human Rights on Common Grounds:The Quest for Universalit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p.21(2001). ⑦id,p.1(2001).. ⑧Robert D.Sloane,Outrelativizing Relativism:A Liberal Defense Of The Universalit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34 Vand.J.Transnat 1 L.527,p.543(2001). ⑨Jack Donnelly,Universal Human Righ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2d Edi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25. ⑩Joy Gordon,The Concept of Human Rights: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Its Politicization,in 23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705.(1998) (11)See from,Joy Gordon,supra note 23,p.16. (12)Philip Alston,U.S.Ratification of the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The Need for an Entirely New Strategy,84 Am.J.Intl L.365,pp.366-367(1990). (13)Makau Wa Mutua,The Ideology Of Human Rights,36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592(1996). (14)Robert D.Sloane,supra note 21,p.542. (15)Louis Henkin,et el,Human Rights,second edition,Foundation Press,p.145(2009). (1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p.136(1971). (17)John Rawls,supra note,p.47. (18)John Rawls,supra note,p.48. (19)John Rawls,supra note,p.60. (20)John Rawls,supra note,p.61. (21)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Duckworth,London,p.194(2000). (22)Ronald Dworkin,supra note,p.172. (23)Ronald Dworkin,supra note,p.200. (24)Jack Donnelly,supra note,p.89. (25)Michael J.Perry,The Idea of Human Rights:Four Inqui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1(1998). (26)Jack Donnelly,supra note,pp.89-90. (27)Jack Donnelly,supra note,p.71. (28)Jack Donnelly,supra note,p.91. (29)Robert D.Sloane,supra note,p.560. (30)Peter R.Baehr,supra note 26,p.5; Joy Gordon,supra note 24,p.15,脚注69及相应正文。 (31)Louis B.Sohn,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States,32 Am.U.L.Rev.1 pp.48-62(1982). (32)James W.Nickel,Making sense of Human Rights,second edition,Blackwell Publishing,2007; Jack Donnelly,supra note 22; Kirsten Hastrup,ed.,supra note 19; Michael J.Perry,supra note 39; Joy Gordon,supra note 23; Robert D.Sloane,supra note 21. (33)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With "The Idea of Public Resons Revisite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79(1999). (34)Upendra Baxi,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p.24(2002). (35)关于人的基本需要与人的基本权利的区分以及相关讨论,可参见:Michael A.Santoro,Human Rights And Human Needs:Diverse Moral Principles Justifying Third World Access To Affordable Hiv/Aids Drugs,31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 Regulation,2006,p.923 and infra; Melanie Beth Oliviero,Human Needs And Human Rights:Which Are More Fundamental? 40 Emory Law Journal,p.911(1991); Ann I.Park,Human Rights And Basic Needs:Us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To Inform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34 UCLA Law Review,1987,p.1195 and infra. (36)Maurice William Cranston,What are Human Rights? Taplinger Pub.Co,66,67(1973). (37)James W.Nickel,supra note 48,p.37. (38)John Rawls,supra note 53,p.65. (39)James W.Nickel,supra note 48,p.98. (40)James W.Nickel,supra note 48,at 11,93.John Rawls,supra note 53,pp.79-80 (41)James W.Nickel,supra note 48,at 11,93. (42)J A Anderews,ed.,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A Comparative Study,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p.11(1982). (43)Ronald Jay Allen,et al.,Criminal Procedure:Investigation and Right to Counsel,second edition,Wolters Kluwer,p.89(2011). (44)Keith B Jobson,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Canada,in J A Anderews,supra note 69,pp.332-348. (45)Kirsten Hastrup,ed.,supra note 19,p.41. (46)William P Alford,Of Arsenic and Old Laws:Looking Anew at Criminal Justice in Late Imperial China,72 Calif.L.Rev.,1180,pp.1180-1255(1984). (47)Andrew Ashworth Q C.,Human Rights,Serious Crime and Criminal Procedure,Sweet & Maxwell,at 64,67,69(2002). (48)Louis Henkin,The Rights of Man Today,Westview Press,p.2(1978). (49)Louis Henkin,The Rights of Man Today,Westview Press,p.2(1978). (50)Andrew Ashworth Q C.,supra note 76,pp.72-73. (51)Ronald Dworkin,supra note,p.200.标签:相对主义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文化相对主义论文; 人权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刑事诉讼论文; 经济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