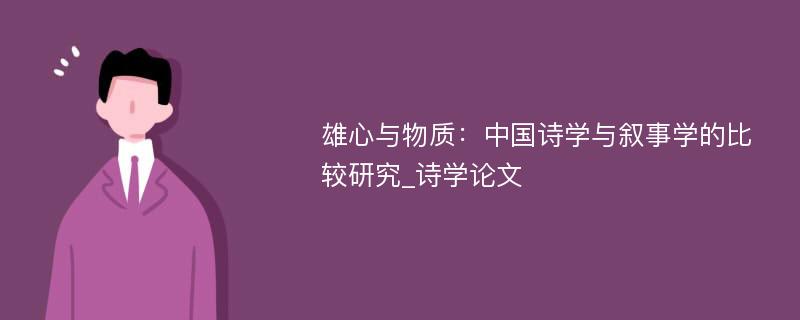
志与事:中国诗学与叙事学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诗学以志为本体,中国叙事学以事为本体。如果说“诗言志”是诗学的开山纲领的话,那么“叙言事”则是叙事学隐含的第一原理。在本体论上的这个根本差别,决定了诗学与叙事学的基本面貌。
一
据现有文献,“诗言志”是由帝舜首先提出来的。《尚书·尧典》记帝舜对其乐官夔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于这个记载,今人多认为并不可靠,一者,今文《尚书》多出于战国甚或西汉,一者,声律观念的出现是晚近才有的事①。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作为诗学开山纲领的权威地位。一方面,“诗言志”被当作为帝舜的话语并收入《尚书》之中,说明它自有其非同寻常之处,另一方面,从接受的角度看,从汉代开始它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书》曰,诗言志,歌咏言”的引用,郑玄《诗谱序》也称引道:“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诗之道放于此乎?”②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开篇即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诗大序》关于“诗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著名的论述,也只是在字面上有所出入。可见,“诗言志”之说,并非无稽的片言只语,而是一个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主流诗学观念。它早已超越了真假的拘限。
事实上,“诗言志”不仅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同时,也是贯穿整个中国诗学的命脉。借助经学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诗言志”居高临下地流播到了整个诗国时空的各个角落。汉唐宋明,历朝历代,朝廷草野,凡是有诗的地方,就有“诗言志”声音的存在。《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张戒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③ 沈德潜曰:“诗不本乎言志,非诗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④纪昀《冰瓯草序》曰:“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都是对“诗言志”说的回应。这种不断的回应与诠释构成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发展。
叙事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本来就没有诗学那么繁荣与显赫,叙事理论中也很难找到一条象“诗言志”那样声名显赫的纲领,然而,在诸多叙事论述中仍然不难发现“事”的本体地位。这在叙事学的逻辑起点——史传处体现得最为明显。史的本义是一种以记事为务的职官,《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就是对史的极好概括。《周礼·天官》曰:“小史,掌邦国之志。”《礼记·王制》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在此后的发展中,“史”的意义发生偏转,由史官变成史传。毫无疑问,对于史传来说,事就是它的本原。史,事也。没有事也就不成史传,甚至也就没有史官这个职位的存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史家为了真实地记录下某一事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故事,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事在史传中的不言而喻的本体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条傍史而生,一条继史而起⑤,然而,两种小说都与史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作者角度看,史家常常与小说家混为一体。以志怪小说《搜神记》闻名的干宝,时称良史,另有史传《晋纪》。唐传奇作家王度、韩愈、沈既济、陈鸿等都是史官。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小说之来源于史传及受史传影响自不待言,即史传受小说影响以致取材于小说者,也不在少数。《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不少材料就是来源于《管子》、《晏子春秋》,《魏晋世语》、《异同杂语》、《曹瞒传》、《赵云别传》则不时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出现。《晋书》更有不少材料照录《世说新语》。欧阳修等人撰修的《新唐书》卷191《忠义传》中的“吴保安”、卷205《列女传》“段居贞妻”的记载,也是分别以牛肃的《纪闻·吴保安》和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作为根据,甚至连文字也大致相近。既然如此,小说也象史传一样以事为本就不在话下。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即使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小说,也同样是以事实为本原。正如吕思勉所说:“凡小说,必有其所根据之材料,其材料,必非能臆造者,特取天然之事实,而加之以选择变化耳。”⑥
需要指出的是,诗学与叙事学分别以志与事为本体,并非只是说志或事乃是作品的来源。本体的意味是在与语辞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志与事之为诗学与叙事学的本体,乃是指它们对语词的决定作用,指在志或事与文辞的关系中,志或事总是处于先导地位,志事为体,语辞为用,志事是语辞的本原、归宿和深层存在。
对于这点,“诗言志”这个短语虽然没有非常清楚地阐明,但《诗大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却是对此最为经典的表述。此后对“诗言志”的不绝如缕的诠释、发挥和回应中,此意更是屡屡明白无误地一遍遍重复出来。刘攽说: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⑦ 袁宗道说:“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⑧所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钟嵘《诗品序》云:“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王若虚引其舅周昂论诗语曰:“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⑨ 袁枚说:“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⑩ 更从反方向重申了情志对文辞的决定作用。他们对辞盛欺志的警醒,深切地体现了诗学的本体自尊意识。
在诗论者看来,诗学既然以情志为本,那么,语辞就得以呈现情志作为自己的目的,如果过分地放纵,势必对诗本体和诗造成伤害,至而使诗不成其为诗。只允许情志大于文辞,绝不容许文辞大于情志。意盛辞乱者,不唯不会受到批评,有时反而能得到高度的评价。叶梦得就以欣赏的口吻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11) 相反,对于文辞大于情志,则认为是对诗的倾轧,甚至将之视为非诗而欲驱逐出诗国。张戒就批评苏轼、黄庭坚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12) 同样的,王夫之也批评韩愈的诗作说:“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短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黄鲁直、米元章益堕此障中。”(13) 至于诗学史中那些有词无志的应酬、应试之作,更是常常受到深切的批判。朱彝尊在《陈叟诗集序》中也说那些宴游赠酬诗,“于心本无欲言”,“其辞多近于勉强”,“以是而称之曰诗,未见其可也”。朱庭珍则说此类诗乃是“词坛干进之媒,雅道趋炎之径”(14)。从表面看来,论者对情志与文辞的态度似失偏颇,实际上这种偏颇却正是“诗言志”的本义所在。
叙事学的本体观对语词与实在的关系的认识,也同样具有决定论的色彩,章学诚所谓“史文千变万化……记言记事,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记言之法,增损无常,惟作者之所以欲,然必推言当日意中之所有,虽增千百言而不为多……推言者当日意中所本无,虽一字之增,亦造伪也”(15)。就是史传叙事事本体论的简明表述。小说叙事学的决定论色彩虽然没有史传那样明确,他们对语辞的态度要更为宽松和放纵,然而,总体说来,这一切仍然是以事本体作为前提,而没有对它形成挑战,他们同样认为文乃事的表象,强调事对于文的先在地位。怀林在欣赏《水浒传》时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16) 徐如翰在《云合奇踪序》中说:“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17)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批评:“有此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稗官者构思之所不能到也。”(18) 当然不只是从材料来源的角度立论,而是具有强烈的体用色彩。他们对事与文的关系的认识,与诗学本体论对此关系的讨论可谓异曲而同工。当然,这也不奇怪,诗学与叙事学虽然各有本体,但在泛文学的层面上,它们还是可以联结起来,两种不同的本体观都可溯源于质文关系。换句话说,诗学本体论与叙事学本体论中对文辞与实在关系的认识,乃是质文关系的同源之异流。
二
乍看“诗言志”,很容易将其中的“志”读为“志气”之“志”,因为今天之“志”主要就是“志气”的意思了。当然,这只是望文生义之谈。作为诗学本体之“志”,自然也包涵了今天之所谓志气,但是,志气只是其中多种义项的一种。在“诗言志”的时代,“志”乃是一个具有深刻包容性的混沌概念,大凡志、情、意、性、知等诸种情感与心理,都包含其中。
郑玄注《尧典》“诗言志”时,将“志”释为“志意”(“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19),同是郑玄,在注《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时,又将“志”释为“心意所趋向”(“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趋向也”)(20)。孔颖达在解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太叔答赵简子语:“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时,将“志”与“情”等同,他说:“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21) 可见,在古人的诠释中,志就已经不只是“志向抱负”方向的意义,而是包括了多种心理内容的混合体。尽管在先秦时候,志已经有“志向抱负”一类的用法,《论语》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等行”(《学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就是如此。闻一多《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意,二、记录,三、怀抱”,也仍然是从多义的角度来对“志”诠释的。
其实,在古代典籍中,在作为诗的本体的论说中,“志”本来就是与其他心理情感因素杂合一起来陈述的。在屈原《九章·惜诵》中志与情就相通,其篇首既云“惜诵以臻愍兮,发愤以抒情”,篇中又多“志”之称,如说“忠何罪以遇罚兮,说非余之所志也”,“固烦言不可结而诒矣兮,愿陈志而无路。”《诗大序》既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与“志”也可互换。当然,如果考虑到以“诗言志”作为诗学的本体论,本来就是一个带有象征意味的简明提法。那么,“志”的多义性就更为明显。诗学论著中大量与“诗言志”相同结构论述的存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国语·鲁语下》曰:“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广雅·释言》曰:“诗,意也。”白居易《与元九书》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魏了翁说:“诗以吟咏性情为主,不以声韵为工。”(22) 王夫之曰:“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23) 袁枚说:“且夫诗者由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朽之诗。”(24) 都是与“诗言志”主语相同而宾语略异的结构,它们可以说都是对诗的本体的论述,这些不同的宾语,其实都是诗的本体意义的不同方面,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作为诗之本体的“志”的丰富内涵。
应该说,志的这种杂多性与混沌性,乃是与“诗言志”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对于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足够发展的人们来说,要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活动作出精微的分辨,并为之命名,当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古代的难题,今人和未来人也同样要面对。就是认识水平与科学水平已经获得了相当发展的今天,在志情意性方面的认识也并不一致。好在无论“诗言志”的“志”是志、是意、是情、是性、是兴,它们最终又都可以统一于一个字:心。《说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无论是志、意、情,还是性与兴,它们都是心的属性,都在身之中,都是对外物的映照和感动。
与“志”一样,“事”的含义也相当复杂和丰富。正如前述,在最早的时候,“事”与“史”都是以手执笔在某物上作记载,都是指称史官。后又经过“史官(传)之所记”这个环节,向其现实来源即“事情”转变。大凡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物及其行为的构成,天文地理、河海山川、花鸟虫鱼、王侯将相、军事政治、柴米油盐都可说是事。然而,细细体察,还是不难发现论者所称“事情”,实隐含了种种不同的认识角度,有未进入作品之事,有进入作品之事。进入作品之事,也有虚实不分之事,有实录之事,有或然之事,有虚构之事,有文生之事种种(25)。
应该说,在“事”最初出现之时,人们头脑中尚没有什么虚实之分,“事”的唯一依据就是耳闻目见。从一些史传记载可以知道,古代的记事史官常常是跟随在诸侯身边,将他们的言行随时记录下来。《左传》昭公元年载,郑伯与诸大夫盟于公孙段氏,“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大史书其名,且曰七子”(26),史官所记录的就是身边的活生生事实。其职能有类于今天的新闻记者。对于他们不能确定之事,也将尽可能地保持原样,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7),“著以传著,疑以传疑”(28)。史传所记之事,基本上都是这个意义。长期以来,小说是以稗史的身份出现的,本来就是史传的一种,所谓“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29)。因而论者要求小说所叙之事应该实有也就不奇怪。罗烨已经指出,讲史应“谨按史书”,“皆有所据”(30),而不能是随心所欲的信口开河。在章炳麟看来,所谓演义,无非是“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31)。蔡元放等以一种值得夸耀的口吻陈述说,《东周列国志》的创作“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32),其实也是将叙事之事理解为实有之事,实在之事。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事情的存在总是与人的认识相关联的,纯粹的客观事实只能是一种理论状态。事既依赖于人与人们的记录才能进入成为另一文本中的事,那么,这事也就自然地加入了主观与想象。事实上,即使以实事作为自己生命的史传,也难免没有虚构的色彩,对此,前人已经多有指出。至于小说,虚构更是其题中必然之义,“凡世界所有之事,小说中无不备有之,即世界所无之事,小说中亦无不包有之”(33)。
尽管如此,这些在虚实之轴上处于不同位置上的诸种“事”,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与物及其行为构成,归结为与作者相对立同时又被他所感觉到的外部存在。实事本来就是来源于现实世界,虚构之事虽然并不是现成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说乃是作者想象的产物,然而,这也不改变它深层的客观性质。正如吕思勉所说:“小说为美的制作,义主创造,不尚传述,然所谓制作云者,不过以天然之美的现象,未能尽符吾人之美的欲望,因而选择之,变化之,去其不美之部分,而增益之以他之美点,以成一纯美之物耳。”(34) 想象初看起来是一种与志情相类似的内部属性,其实却只是联结作者与对象世界的一座桥梁,其目的与归宿也是在外而不在内,与情志的方向正好相反。
志是作者的内心世界,事是与作者对面的外部世界,这就是诗学与叙事学的本体所在。它们的内外对立,将中国文学划成了畛域分明的两个世界,将这两个世界合起来,中国文学又构成了一个完满的世界。志与事的基本规定性,使得诗学与叙事学具有了自己一贯的特点,而其丰富含义及其可诠释性,又使中国诗学与叙事学充满了无限的活力,时时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
诗以志为本,叙以事为本,而志、事又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品性,这不同本体的赋予,使得诗学与叙事学之间表现出了强烈的区别意识或曰主体自我意识。《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见,诗叙的区别意识在先秦时候已然产生。诗与叙独立分流之后,相互区别更是衍变为相互排斥,诗归诗,叙归叙,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各自固守着自身的特点。王夫之说:“诗有诗笔,犹史有史笔。”(35)“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36)
诗学对叙事的排斥,在古代诗歌类型上得到了清楚的反映。在西方文学传统里,诗不仅有抒情有叙事,叙事诗还是诗坛的主流。然而,在古代中国,叙事诗章既少,就是有少量叙事性质的诗篇,也很少能进入诗论者的理论视野。《文心雕龙》的论诗篇章中很少提及叙事的诗篇,钟嵘的《诗品》也同样未将《孔雀东南飞》、蔡琰的《悲愤诗》等叙事成分较重的诗歌纳入自己的品评范围。在不少诗论者看来,诗学既然是以情志为本,叙事对于诗学就是非法的,只有将是拒之门外,而对那些悄然步入诗歌殿堂的叙事之作,也只能视为诗之伪体而予以别裁。即使是一代诗圣杜甫的“诗史”之作,也同样受到强烈的排斥。杨慎就认为,宋人以“诗史”称杜甫的叙事之作,是将杜诗中的“下乘末脚”,“拾以为己宝”,如此“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37)。王夫之也批评杜甫《石壕吏》一类叙事之作,“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38)。以叙事歌行著名的吴梅村也受到了同样的批判,王夫之、钱陆灿都将其与里巷盲词并称。这其中都体现出了叙事乃“诗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39) 的诗学观念,吴乔说得很清楚:“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40)
比之叙事,诗学对写物的态度要更为宽容和温和,古诗之中以物为对象的诗作可以说不在少数。然而,细读一番,仍然可以发现,真正纯粹的写物诗同样很少存在,同样受到诗学本体的排斥。张戒说得明白:“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41) 王昌龄也说:“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42) 诗中的物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是存在的,一种是作为情感的触媒,一种是经过作者情感的浸染、加工和改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者情志的表现形式。纯粹的物事在诗中是空洞和无意义的。王国维之所谓“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只不过是情感的两种不同表现方式的结果,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都是有情之境。杜甫《江村》诗曰:“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自去自来”、“相亲相近”显然是作者情态在燕鸥身上的投影。杜甫《曲江对酒》诗曰:“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也经过了作者情感的改造。纯粹的自然物事,应不存在桃花杨花的追逐,即使有追逐,也应是杨花追桃花,而非桃花追杨花,何者?桃花重而杨花轻,桃花在前而杨花在后。如果定要把诗中的物事当真,那就必然会闹出诸如以杜甫《偪侧行赠毕四曜》诗句“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来求唐时酒价的笑话(43),产生诸如杜诗《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中的尺寸是如何计算之类的无聊争论(44)。
正如诗学对叙事的排斥一样,叙事学也坚守着自己的事本体,而拒绝情志的进入。诗学在表达上要求自我灌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这方面,诗学之所近,恰成了叙事学之所远,诗学之所亲,恰是叙事学之所忌。史传实录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让事情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再现出来,而不加入作者的主观情志。史传写作的最大美德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45)。与此相应,最大的恶行当然也应是因个人的主观而使事实改变。史传之中虽然允许作者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是,它们必须严格地与事实区分开来,而不容混淆。早期史传中的论断与叙事已经有一定的分界,“载事之文,有先事而断以起事也,有后事而断以尽事也”(46)。两者不易混淆。《史记》之后,这种区别就更为严格,作者的论断只能以“论赞”的形式置于叙事的正文之后,两者分立,壁垒森严。
史传的实录其实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内容为现实中所有,非作者的虚造;一是在叙事时,作者与其对象保持距离,互不相渗,所谓“述而不作”是也。《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都表明了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冷静的记录员,而不是历史的创作者,而这也正是史传作者的理想品格。小说叙事在虚实的层面上与史传叙事有着质的不同,然而,在情感的介入方面,却继续保持着冷静的特色。唐代小说之作,往往由人物姓名、身份、籍贯、生平起笔,如《李娃传》开首云:“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霍小玉传》第一句曰:“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进士及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宫。”就是一种史笔。黑格尔曾经指出,叙事诗人“因为他所叙述的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外表形式上都应该显得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现实世界,和作为主体的诵诗人隔着很远,所以诵诗人无论就内容本身来说,还是就诵的方式来说,都不应主观地使自己和所诵的独立自足的世界统一(混同)起来。”(47) 我国古代叙事学恰恰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显然,这种感受不到作者存在、对象仿佛是自我凸现出来的叙事方式,对于作者的情感介入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这样一种写法,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做到,然而,卓越的小说却总是在以客观的态度将作品叙述出来。《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说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金瓶梅》的叙写,“作者于有意无意之间,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性情,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于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是在明眼人之识之而已”(48)。《儒林外史》更是通篇“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卧闲草堂称其为“绘风绘水手段”(49)。小说史上自然也有作者禁不住站出来抒情议论的作品,它们甚至还一度大量涌现,然而,这类作品归根到底只是小说发展史上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是小说中的偏体,即使是当时作者也已感觉到它们“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50)。
需要说明的是,叙事学以事为本体,而事本是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叙事学不仅不排斥,而且十分欢迎和需要情感描写。诸如才子佳人小说等叙事作品,甚至还是以情感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并没有消解叙事学对情志的排斥。叙事学对情志的排斥,指的是作者的写作应该不掺入自己的情感,叙事学对情感的需求,乃是指作为叙写对象的情感。《红楼梦》既是一部伟大的情感小说,作者的写作同时又是恪守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第一回)的写作原则,以至脂砚斋说:“《石头记》不是作出来的。”两者并不矛盾。
诗以志为本,叙事学以事为本,它们不仅坚持自守自己的本体,而且还对对方的特点予以排斥,这就使中国文学形成了诗学与叙事学分流并立的基本布局。另外,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长期以来诗学与叙事学发展都不平衡,诗学占据文学的中心,而小说叙事学则只能在其边缘默默前行,应该也与诗学与叙事学的相互排斥有很大关系。
四
诗学与叙事学的分流与并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事实,这在西方文学的比照下会更加显明。西方之所谓诗,虽然也包含了近似于中国诗的抒情诗,但史诗与叙事诗却一直是西方诗歌的主流,在许多时候,“诗”所指的乃是整个文学,以至“诗学”成了文学理论的另一种称呼。可以说,从一开始起,西方的诗学与叙事学就常交叉与合一,这与中国文学的布局大异其趣。亚里斯多德《诗学》以悲剧和叙事文学作为对象,钟嵘《诗品》只以“吟咏性情”之作作为对象,在对方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并非说中国古代诗学与叙事学就没有任何的交流。诗学与叙事学的相互排斥,已经说明它们之间有所交流与融合。没有交流,何须自守?没有融合,何须排斥?
事实上,在诗叙获得各自的本体而独立之前,在人们的意识尚未完全从自然的怀抱之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志与事两者本来就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在初民们的简单作品中,很难辨别出他们是在描述世界,还是在对世界感叹。他们的情感与对象还是这样紧密地依附在一起,难以分开。这是一个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叙事的时代。那些流传下来的较为可靠的上古诗歌,如出自《吴越春秋》的相传为黄帝时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显然有浓厚的叙事色彩,而被认为是叙事之祖的神话,则常常是诗意盎然。这种情况与“志”的另外一个前面没有指出的义项也正相吻合。闻一多作于1939年的《歌与诗》指出,在“志”的所有义项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即“记忆”与“记载”,“记忆之记又孳乳为记载之记。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古时几乎一切文字记载皆曰志”(51)。
即使是到了孔子的时代,志与事、诗与叙也仍然常常粘合在一起,很难分开。《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以周朝先祖事迹为对象的作品,与其说是“诗言志”的“诗”,还不如说是以事为本的叙事。钱谦益更说:“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52) 这种说法应该说有其偏激之处,然而,其中所表达的“诗史同源”,仍然有其合理之处。不然,“六经皆史”何以会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
诗学与叙事学在获得了自己的本体,真正独立之后,志与事也仍然存在交融与关联,虽然有不少论者在顽强地维护着各自体性的纯洁。从理论上说,心志并非是一个实在之物,而是对物的一种反映,情志的产生与表现本来就离不开物与事。《礼记·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53) 钟嵘也说,性情乃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结果,它们要么是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之四候所感,要么是为嘉会离群、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之类生活境遇所激(54)。不仅如此,情志要在诗中表现出来,也常常需要借助于事物,依附于事物,它无法单独直接抒发。否则,诗便很可能不成其为诗,而只能是口号了。可见,情志与物事在本性上就有其相通之处,物事之进入诗境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必须。
同样的,叙事学也难以离开作者的情志而单独存在。事物本来就是依待人的意识而存在,没有被人认识的事物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就不成其为事物,而进入作品中的事物则更是作者创造的结果,在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作者的情志。即使是最为客观的作者,在叙事之时也很难完全避免情志渗入叙事之中。从创作动力的角度看,叙事之作也同样是作者情志冲动的结果,无冲动就无创作,有冲动就有寄托、有情志。从《春秋》、《史记》到《聊斋志异》、《红楼梦》,几乎所有的叙事之作都不能例外。
正因为如此,诗中之叙与叙中之诗一直就无法避免。在整个诗学史上,叙事诗数量虽然有限,却也不绝如缕,如白居易、吴梅村等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叙事作品中的诗歌衔入,也是叙事学史上的不断的景观,甚至还出现了《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诗意小说。中唐以后,志与事的交流与合作还出现了分工合作的新形式,比如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的相配,元稹《莺莺传》与李绅《莺莺歌》的相配。陈寅恪《长恨歌笺》就说《长恨歌传》与《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结构”,“《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之内,《歌》中自不可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这种珠联璧合的配合,也从一个角度见证了志与事、诗与叙的交流与互补。由于诗中之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它也引起了批评者的重视。贺贻孙就对诗中叙事进行了艺术总结,他说:“叙事长篇动人啼笑处,全在点缀生活,如一本杂剧,插科打诨,皆在净丑。《焦仲卿》篇,形容阿母之虐,阿兄之横,亲母之依违,太守之强暴,丞吏、主簿、一班媒人张皇趋附,无不绝倒,所以入情。若只写府吏、兰芝两人痴态,虽刻画逼肖,决不能引人涕泗纵横至此也。文姬《悲愤篇》,苦处在胡儿抱颈数语,与同时相送相慕者一番牵别,令人欲泣。……《木兰诗》有阿姊理妆,小弟磨刀一段,便不寂寞。而‘出门见火伴’,又是绝妙团圆剧本也。”(55) 这样的总结当是对诗叙交融的一种特别肯定。
尽管诗学与叙事学的交流与融合,比之它们之间的自守与互斥来说,还显得非常的柔弱,这种交流与融合,只是在分流与并立的基础上的交流与融合,它们还无法改变诗叙分流与并立的基本格局,也没法改变诗叙发展的不平衡,然而,诗的叙事化追求与叙事的诗意追求,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起了特别的作用。诗学史上由以诗为诗向以文为诗、由诗向词、由词向曲的发展,叙事追求应是其重要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小说发展史上的几次关键性转折,更与叙事的诗性追求有关。唐传奇的诞生与小说的文体的独立,可以说正是诗笔对史笔点化的结果,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奇书的兴起,也得益于诗性对评书的改造。至于最伟大的叙事之作《红楼梦》,则更是志与事、诗与叙交融的产物。叙事学如果没有诗学的点化,它很可能会长时间困守在史传叙事的胡同中而无出头之日。正是有了诗意的追求,叙事才有了史实之外的意想,有了飞扬的文采,才避免了堕落。
注释: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36页。
② 《诗谱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2页。
③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0页。
④ 沈德潜《徐元叹诗序》,《初学集》卷32。
⑤ 参阅罗书华《章回小说源流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
⑥ 吕思勉《小说丛话》,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页。
⑦ 刘攽《中山诗话》,《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
⑧ 袁宗道《论文》上,《白苏斋类稿》卷20。
⑨ 王若虚《滹南诗话》卷1,《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06页。
⑩ 袁枚《续诗品·崇意》,《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029页。
(11)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7页。
(12)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2页。
(13)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4)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4,《清诗话续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6页。
(15) 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章氏遗书》卷14。
(16) 怀林《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容与堂本《水浒传》卷首。
(17) 徐如翰《云合奇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3页。
(18) 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第48回总评,《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9页。
(19) 《诗谱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2页。
(20) 《礼记正义》卷36,《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2页。
(21) 《春秋左传正义》昭公25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08页。
(22) 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2。
(23)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24) 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小仓山房诗文续集》卷30。
(25) 关于中国叙事学的事体,本课题另有专章论述。
(26) 《春秋左氏传》昭公元年,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3页。
(27) 《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74页。
(28) 《春秋谷梁传》庄公七年,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82页。
(29) 雉衡山人《东西两晋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9页。
(30) 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31) 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32) 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33) 无名氏《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34) 吕思勉《小说丛话》,《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35) 王夫之《明诗评选》卷5,《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410页。
(36) 王夫之《姜斋诗话》卷1,《四溟诗话·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37) 杨慎《升庵诗话》卷11,《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8页。
(38) 王夫之《古诗评选》卷4,《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51页。
(39) 王廷相《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王氏家藏集》卷28。
(40) 吴乔《围炉诗话》卷3,《清诗话续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8页。
(41)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0页。
(42) 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43) 刘攽《中山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都有此尝试,并得出唐时酒价每斗三百钱的结论。王夫之嘲笑他们说,与杜甫同时的崔国辅《杂诗》所载的当时酒价是:“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如果“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见王夫之《姜斋诗话》卷2。
(44)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讥刺说:“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耶?”王得臣《麈史》卷中《辩误》认为“两手指合而环之,适周一尺”,算起来古柏“是大四丈”。黄朝英说四十围是指直径,而非周长,如此,“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8)对于这些离奇之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6、范温《潜溪诗眼》已有批评。
(45)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38页。
(46) 陈骙《文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47)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页。
(48) 文龙批评《金瓶梅》第77回回评。
(49) 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第4回评。
(50)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丁锡根《中国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9页。
(51) 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6页。
(52)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有学集》卷18。
(53) 《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27页。
(54) 钟嵘《诗品总论》,《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55) 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