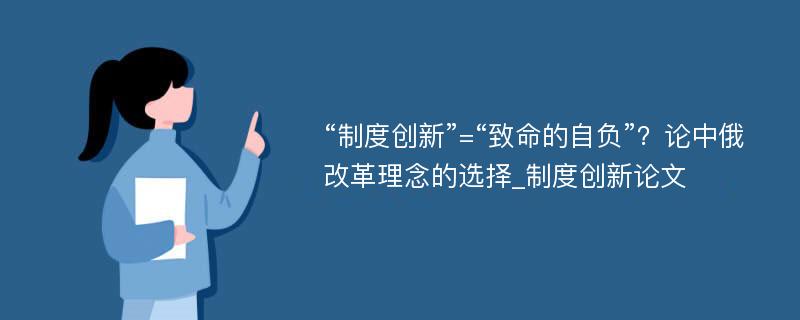
“制度创新”=“致命的自负”?——兼谈中俄改革思路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 (1999)03—0140—(3)
近读韦森先生“注意哈耶克 慎思诺思”一文及给编辑先生的信(注:参见《经济学消息报》1999.1.8及1998.11.27),深感畅快。因为,结合中国改革的思路选择将两位大师放在一起进行如此深入的比较,据我所知尚不多见。不过,畅快之余,对“制度创新”的深思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制度创新”等于什么或不等于什么。
为避免歧义,先约定,这里的“制度”是大制度(Regimen )而非小制度(Institution)。 这也暗含着我们将把关于制度的政治艺术存而不论。
先说“苏联范式”的计划经济制度。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据我所知,源出俄国——列宁第一个鲜明地提出了“计划经济”,继后由斯大林推到极致。“自负”到“僭越”,是这次制度“创新”或设计的鲜明特点:以有限理性取代“终极真理”,以局部理性取代整体理性,以过渡理性取代过程理性,以个体理性取代类的理性……对于苏俄的这种“自负”,高尔基的批判和预见特别深刻:“这些人在政治上非常内行,各种各样的知识相当丰富,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知识并不妨碍他们充当反犹太主义者、反民主主义者,甚至充当基于压迫人民群众、压迫个性自由的国家制度的真诚捍卫者……把人们像牲口一样往监狱里赶。”“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高尔基甚至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的最终解体。在这个意义上,士绅精英的自由、不平等的自由、无平民的自由、无民主的自由的“制度创新”,就只能是“制度创新”等于“致命的自负”。这里的“致命”,是彻底丢掉了一个“阵营”。不过,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致命”未必不是制度“自然”演进过程中的一站。
苏东国家的改革在几十年时间里历经反复曲折,始终未能走出“统死放乱”的怪圈。正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说:在一元化的国家所有制框架内,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苏东“激进式”的走向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历史的选择。舍此,它别无出路。可是,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中国,从“工业六十条”到“联产承包”,从“放权让利”到“搞活国有企业”,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我们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它同样是历史的选择。
再说“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制度。
这是中国人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虽然是“学”,但也是一种“创新”一种设计,好在中国人的“学”还未到“致命”的程度——我们有很多人、地方、部门似乎还没有那么“理性”——“道法自然”多少是这个“制度”的内生变量。不管怎么说,20来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自然演进,多少都有些类似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从实行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到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支持农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性改革,到鼓励、推动农民兴办乡镇企业的产业创新……比较起“休克疗法”来,今日中国改革的思路选择可以说更多的是对哈耶克的“注意”。这种“理性”地抛弃,是否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算得上一种制度的设计或创新?从人类“理性”历史的发展看,应该说资本主义(平民的自由)比封建主义(贵族的自由)更“自负”。据罗炤先生考证,1949年以前的中国,其资本主义成份要超过1917年以前的俄国(注:参见《经济学消息报》1998.10.30)——小岗村的“大包干血手印”字据或许可为一例。以如此的历史底蕴来对比分析中俄改革思路的选择,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些新的启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创新”不等于“致命的自负”。
谈到制度变迁、改革思路的选择,德国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对象。远的如李斯特不说了。近的可以看一看二战后的艾哈德。正是这个艾哈德,以其独特的“自负”为德国“设计”了一条复兴之路并取得了成功——来自竞争的繁荣。
这样看来,制度的设计或创新,从技术的角度讲,或许是一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然有可能“错”得“致命”),而作为主流思想的现象形态,制度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有“自负”这个人的“基因”——按诺思的说法,“制序”是经由人们发明、创造、设计制造出来的。但是,“自负”会不会是“致命”的,关键又是它在制度的设计或创新中的“权重”如何,而这个“权重”的决定,恐怕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问题了(诺思明确地把“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石之一)。日前广东有人说,“三个一点”(即邓小平讲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对广东目前的困境负有一定责任,实在是还没有弄明白“制序”的形成机制。这多少也可算是一种局部的“致命的自负”吧?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马克思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达: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意味着,人(类)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有限理性也即“自负”去逼近那个“终极真理”。作为一种存在,这是人的一种类本能,它是如此地自然自发,又是那样地自在自为。因此,不管“制度创新”是不是等于或会不会等于“致命的自负”,那都与哈耶克和诺思无关,也与马克思无关,而在于当事人这一代或几代是否“意识”到了“自负”的“权重”并如何来决定这个“权重”。进一步的,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本身又成了人们自己设计、选择、创新的内容和必须由自己来承担的结果。因此,虽然哈耶克与诺思有知识论基础的不同,但两位大师的理论思想来源在如下意义又可以说相同:哈耶克倾向于“制序”演进的自然自发形成机制,诺思倾向于“制序”变迁的自在自为形成机制——这实在是“两极相通”。换言之,制度的形成及其创新,从来就是以人为轴心的,从来就是自然自发与自在自为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无法将其分开也不可能将其分开;人们的“意识”可以决定人们的“自负”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权重”,这当然就成了一种“制序”的选择。
其实,布坎南(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把经济学定位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说的“美国精神”或“美国人的历史经验”,未必不是一种制度创新或一种制度的发明和设计。美国历史不长,但进展神速,依我看,就确实离不开这种制度创新或制度“设计”。如果说这是美国学界的一种“精神自负”,那么它恰好是证实而不是证伪了诺思。相应的,“民主在美国”(注:参见《读书》1999.1,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的自由意识传统又较好地决定了这种“自负”在其制度形成过程中的“权重”,因此它又恰好证实而不是证伪了哈耶克。我想,这也许会是今后“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案例;当然,几十年前“理性地整体设计计划经济”的历史性错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案例。窃以为,如果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和“政治企业家”们能够从这两个案例中确立自己的“意识”并把它自由化为主体(主流?)的“意识”,则中国改革的思路选择可能会更有效率。比如,原定于1999年1月1日出台的“燃油税改革方案”之所以流产,原因就在于其制定者自以为这是一项大的“帕累托增进”(实际上顶多是帕累托次优),这当然又是一个局部的“致命的自负”。
这是一个信号:纯粹帕累托增进也许可以是“自发”的(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为什么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就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一阶段改革的受益者),但次优帕累托增进也许就得靠“自为”了(为什么90年代以来的改革愈来愈有“攻坚”的性质?就是因为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已经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已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这是一个隐忧:现实中国的每一项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都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寻租”并力图把新制度引向旧制度的“自负”。所以,在这里,无论是哈耶克的“保守”还是诺思的“激进”,都不再是唯一的一“极”。“演进”与“变迁”交织在一起了。
在过去数千年中,社会(人)的世界虽然是由有意识的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但却一直是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这种无意识的“自负”,使当今人类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跨地域、跨意识形态的全球性问题,并日益成为对“类”的“致命”威胁。要应对这些问题,就需要一个“整合”,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当然也就需要一个更新的有意识的“类”的“自负”(譬如《21世纪议程》、世界经贸组织,等等)。中国仅仅有孔夫子、老子是不够的,仅仅有“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新增长经济学”也是不够的,中国改革的思路选择,还需要像哈耶克、诺思那样的思想家,尤其需要像“总设计师”那样能够进行“综合”的思想家。这种“综合”,就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以“顺之以治”。因为从理论上讲,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出现“真空”“摩擦”“失序”总是不可避免的,这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制度创新”必须支付的成本;而从长远的发展过程看,只要(意识)方向正确(比如中国于1999年3 月修宪,正式确认私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措施得当,假以时日,转型时期出现的“混乱”就迟早会得到克服。确实,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而言,俄罗斯在不少方面目前还不及中国,但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以极大的(甚至是“国破家亡”的)代价所实现的社会结构转变看,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除了技术性选择的限制外,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可言。中国则不然。中国还必须围绕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这个“中心”做文章。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历史的经验提醒我们,如果仅仅只围绕这个“中心”兜圈子,那它就是一个“死结”。简言之,只有在一场更深刻、更广泛、更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问题,才有可能化解并超越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巨大矛盾。
海德格尔不信任群氓似的民主制度,但他也承认,只要有伟大的思想就必有伟大的失误。这是否意味着“学者只能是学者”?这也许还是一个暗示:作为思者的学者,如果一旦幼稚地进入到那个他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经济领域,其结局多半就是自己先被革了命。
中庸之道,止于至善。
理性基于本能,本能美于理性。哈耶克和诺思两位大师分别站在“制度”的N与S,并各自以其独特的理论洞见、“分析理路”和“思径取向”,为人们描绘了制度形成的“思想史”;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边界,在更深刻的思想传统上,从人的“自负”本性的角度说,这就是伟大的自由(主义?)精神——平民的自由,民主的自由,平等的自由。
收稿时间:1999—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