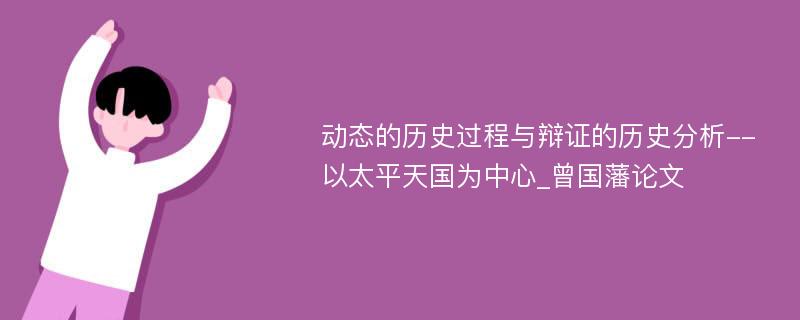
动态的历史过程与辩证的历史分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历史论文,过程论文,动态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农民起义史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倘若始终如一地站在起义领导者的正义立场来评判历史,分辨是非,是否就能确保站在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否就能得出颇有说服力的科学结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正确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关键所在。
一
不少论著在总结太平天国起义军最终前功尽弃的主要原因时,既充分注意到了洪杨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所造成的致命伤,也如实地指出洪杨一班人早在杀出广西之前就迫不及待寻求享乐、在定鼎南京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个中信息无异于表明:小农出身的旧式农民起义领导者只能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选择区间和创造区间中有所作为。既然旧式农民起义领导者在起义成功或相对成功之后,便由昔日的贫苦农民或别的社会底层摇身一变而成了同自己的起义对象并无本质差别的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由被压迫者变成新的压迫者,由自己所属的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变成了自己所新属的压迫阶级的代表,那么,只有用辩证法的动态眼光来看待这种合乎历史逻辑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审视这种变化的阶级实质,分别研究各变化阶段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保证史学工作者始终站在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立场来主持历史的公正裁判,才有可能始终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倘若一成不变地站在农民起义领导者的立场来判断历史,就会不知不觉地随着这些农民起义领导者的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发生阶级立场的移位,不知不觉地被起义领导者的阶级地位的变化牵着鼻子走,动机与效果的背离也就开始了。
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集团都是动态中的社会集团,“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线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2 〕如果史学工作者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所得结论就难免失之偏颇。对于旧式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不可能创造“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不可能为着这个进步而重新设计有助于“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的政治方案和经济方案,但他们的造反功业能使原有的阶级对比关系发生相应的变化,能或迟或早地制定一系列反映自己今非昔比的“阶级面貌”和政治利益的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成者为王”之后,他们自身的政治要求不外乎重建专制王朝秩序,享受人间富贵,充其量还能像刘邦或朱元璋那样尽快医治战乱创伤,尽快恢复广大农民的家园和生产生活秩序。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起义追随者或胁从者仍然是社会底层的基本成分,他们所获得的最佳回报除了朝政开明和轻徭薄赋外,就所剩无几了。广大劳苦农民并不指望新的主宰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东西,旧式农民起义也不可能给他们给历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我们在研究近代农民起义领导者洪杨集团与太平天国的实际操作过程,评价其历史作用时,不应当机械地站在洪秀全一班人的政治立场来说话,不应当采取尽量挖掘甚至夸大其正面效应,尽量为其负面效应辩护或轻描淡写的态度,而应当始终站在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立场,运用历史辩证法来冷静分析和区别对待之。〔3 〕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的正义性,又要充分注意洪杨集团攻占南京之后以军功贵族和劣质主宰身分日益疏远自己曾经置身其中的下层劳苦大众这一客观事实。既要估计到洪杨起义军之于清朝的致命打击有助于晚清“洋务运动”之发生,有助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瓦解等方面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正视洪家王朝与清军双方借助于历时10余年的战争拼杀与搜括富庶江南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关于太平天国之于近代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是一个“进步作用”或“倒退作用”之类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或十分省事的“功过分成”之类结论所能说明的。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性,舍具体分析无他法。否则,历史就毫无复杂性可言了。
在近年来出现的曾国藩研究热中,如何冷静地看待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曾氏倡导“洋务运动”等其他事功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在困扰不少研究者。新近的有关学术讨论与研究状况表明,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学术争论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第一,有的研究者为了充分肯定曾国藩之于开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先河的洋务运动的某些历史作用,试图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历史作用;有的则强调清皇朝已经腐败透顶,只能彻底推翻。而曾氏率领湘军人马助纣为虐,维护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把太平天国将士残酷镇压下去,这就无异于开历史的倒车,是为研究和评价曾国藩一生事功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点上不容含糊。
第二,受上述争论的制约,在关于曾国藩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所谓盖棺定论上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争论者都想说服对方,又都说服不了对方。
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4〕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广大农民往往是在自身的生存都已受到威胁时才铤而走险的,洪秀全一班人振臂高呼之后的四方景从完全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被压迫者的造反权利是历史所赋予的,不是哪个后世研究者所能任意赐给或取消的,史学工作者没有理由淡视甚至怀疑洪秀全等人擎旗金田的历史正当性和必要性。至于农民起义者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或者洪秀全一班人能否在王袍加身之后履行自己的宗教诺言,尽可能为广大劳苦大众带来甜头,那是另一回事。曾经去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一书中也提到:“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为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至于这场起义的历史作用,也许它并不直接体现在同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联系上,而是体现在同“洋务运动”即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之发生的历史联系上,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因为,如果不是洪杨起义军横扫东南半壁江山的雄姿彻底揭露了清朝八旗、绿营等经制之师的腐朽和无能,打乱了原有的中央集权制与民族歧视的统治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曾国藩和他身后一批汉人督抚的迅速崛起,因而也谈不上“师夷之长技”方案的尽快到位。如果不是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带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异军突起,欲期力排众议“师夷智”,其阻力必将更大。
太平天国将士们十数年浴血奋战之于清朝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冲击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据《清文宗实录》记载,仅在咸丰元年至咸丰六年(1851—1856年)间,亦即洪杨起义军兴师之后的前6年内, 骁骑校等正六品以上的八旗武官死亡共260人, 其中副都统等正二品以上者36人,占八旗死亡官员总数的14%。另外,因师糜饷、贻误战机而受各类处分者68人次,其中副都统以上军官占55人次。绿营军遭受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其中死于战阵的把总、千总、守备、都司等中下级武官不计其数, 游击等正三品以上的中高级将领死亡者即达204人,其中提、镇大员18人,占全国水陆提、镇总人数的67%;总兵83人,占全国总兵人数的47%。 另有遭受处分的正三品以上绿营将领达223人次,其中提、镇大员占114人次。在此期间, 文官七品以上死亡者达429人,其中藩、臬、抚、督等正三品以上者共63人。 至于被起义军镇压、“殉节”、非自然病故以及遭受革职处分的地方知县共达415 人次,其中安徽、江西、广西三省的知县变动人数在70%以上,〔5 〕许多新任命的知县、知府等官还不敢前往赴任。广西巡抚劳崇光于咸丰五年十一月上奏即称:“盐法、左江二道悬缺均已三年,平乐、柳州二府悬缺各已二年,丞倅州县佐杂悬缺数年者更不可胜计”,上年“奏明咨取大挑知县来粤计有十员,迄今并无一员前来”。〔6 〕太平军以偏师约2万人自扬州和六合拔队北征时,朝野震颤,清廷在河南、 山东一带和京畿附近调集近20万军队防守,而且“粮道不通,京师震动,部内部外官僚送回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京城一空”。〔7 〕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武器批判下,清皇朝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空前的冲击和破坏,以汉人为主体的湘军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冒出来,并迫使清廷倚为长城。曾国藩不仅使一向疑忌重重的满族贵族们委以统辖江南4省军务之大权,而且将地方督抚权限轻而易举地扩展之, 从地方政务扩展至军权和财权,可以不听中央六部的使唤和藩司的牵制,有意无意地削弱着由满族贵族所独揽的清朝中央集权统治,其影响可谓久远。越来越为后世史学工作者所看重所称道的“洋务运动”,就是在有头有面、有权有势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督抚大员的竭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启动的。因而可以说,是金田起义后的时势造就了湘军统帅曾国藩,洪杨起义军有功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洋务运动”之间具有某种因果联系。洪杨起义军之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轫的那一份历史功绩理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与相互作用。列宁在《论国家》中强调:“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8〕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们既没有必要为了适当肯定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而贬低被曾氏所剿杀的太平天国起义者的那一份历史作用,也没有必要把曾氏倡导的“洋务运动”同他双手镇压农民起义之举对立起来研究之。在肯定曾国藩之于洋务运动的开拓之功或批判其残酷镇压天国将士的阶级罪恶时,只有适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才有可能确保历史描述与逻辑思维的连贯性。
二
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一班人起兵镇压太平军固然属于无可争辩的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如同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和君主专制统治进行武器批判一样,都是阶级的本能所驱使。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的阶级罪恶,似不应成为研究和评价他的其他历史活动的障碍或前提条件,否则,全面研究和公正评价云云,就有可能成为空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9 〕对曾国藩的研究与评价亦当如此。倘若曾国藩不去镇压太平天国,不去维护由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阶级关系”,那才不符合历史的常规,至少算是曾国藩的失职,清朝最高当局饶不了他,他也当不了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从而力排众议,在“师夷之长技”的筚路蓝缕中有所作为。这大概也算是历史无情的一种表现吧。
至于洪杨集团高高兴兴地在南京城为自己营造天国之后,他们就过早地同广大劳苦大众疏远、隔离甚至对立起来,前者就以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的姿态明显区别于后者,曾国藩之辈的阶级罪恶与洪杨集团的阶级面貌之间也就难分轩轾了。此时时刻,“兄弟”“姊妹”之类甜蜜的称呼和《天朝田亩制度》之类鼓动性的承诺对于广大劳苦大众究竟有何实际意义?互相拼杀的新式贵族同清朝贵族之间究竟有何本质的区别?也许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对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纲领和洪仁玕向洪秀全提供的改革方案,我们不妨听听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告诫:“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10〕
更无情的历史景观在于:自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侵略者破门而入,中外民族矛盾日形尖锐。在太平天国将士同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在内的清朝兵勇殊死搏斗期间,俄国侵略者就趁火打劫,强占我国东北地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英、法联军则悍然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我国。既然内战本身是由国内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的,战争双方还不可能像帝制推翻之后的国共双方那样从民族大义出发,停止内战,携手对外,历史的法则就只能是通过较量,尽快结束内战,由胜利者去扮演中国早期现代化之领导者的角色,走“师夷之长技”之路。
就历史研究而言,在相对客观描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清理其来龙去脉,这比我国学术界流行的“功过分成论”以及“正面或反面”,“肯定或否定”(或曰“是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之类非此即彼的整体性盖棺定论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个产生于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历史人物,至少当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还没有适当拉开距离之前,似乎还没有必要急于寻找一个十分简单的整体性结论。这样的整体性结论也许很省事,但不一定科学,还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为好。在具体分析之后,有时仍很难也没有必要综合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来。
如果断定曾国藩或别的历史人物“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或主张“三七开”、“四六开”等等,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颇具科学特征,实际上均属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时空,而且内容、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与事件是无法通过加减计算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往往是互相联系着的,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过之间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害的。
应该说,研究历史人物不必急于得出一个简单结论,然后确定褒贬的基调。通过具体研究,史学工作者如果能切实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大概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力量与科学精神完全可以在回答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却无法指望貌似准确而实属主观臆断的所谓“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之类的简单结论去体现。当然,这并不排除具体研究之后,人们各自对历史人物形成某种整体印象,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出某种整体估价的可能性。
如果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看作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那么,何谓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最高峰”的标志何在?是因为它克服“流寇主义”所建霸业的时空范围超过了以往的同类先行者,还是因为起义领导者引进了上帝观念而摆出了学习西方的姿态?是因为洪秀全颁发了集唐末黄巢起义以来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之大成的一纸空文《天朝田亩制度》,或者因为匆匆赶来的洪仁玕提出了既能体现其个人游历香港数年之后的思想与见识又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历史发展趋势相吻合的《资政新篇》,还是因为这场起义打击两千年来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与小农经济结构的广度和深度与众不同?还是因为它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番弟”或“洋兄弟”有什么惊人之举?等等这些线索,似乎还可进一步讨论。而对于广大受苦受难的社会下层民众来说,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也许并不是基于那些空头许诺所展示的想象力或系统性和鼓动性,也不是后世研究者所看重所欣赏的战争空间之广袤与战争时间之长久,而是揭竿而起的军功贵族们在“成者为王”之后能尽快打扫战场,以廉洁开明和轻徭薄赋回报农民,尽可能让嗷嗷待哺的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或者就是把秦朝末年的陈胜起自垄亩前那句朴实无华的承诺付诸实践——“苟富贵,毋相忘”。
不是因为我们偏爱揭前人之短,喜欢同洪秀全等人的历史形象过不去,只是试图区分并且具体说明作为阶级整体的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与作为个体的洪秀全一班人自身的缺陷与失误,试图说明洪秀全一班人的真实言行与近代政治革命之间的历史鸿沟,我们才不得不抖出一些系于洪秀全一班人之身的诸多缺陷,并无存心苛求或贬低之意。如果一定要将历史的天平无条件地偏向洪杨一班人,无需用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和适当区分当年以劳苦大众的代表身分揭竿而起者与时过境迁后的军功贵族或新式地主之间的明显差异,那就另当别论了。毛泽东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作近代民主革命的一个基本内容甚至是重要内容或革命高潮之说,至少就不是“正规”的说法了。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2〕《列宁全集》第12卷,第393页。
〔3〕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 吴承明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吴承明先生还指出:“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4 页)吴承明先生的上述见解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如果我们用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洪秀全一班人所作用的历史演变过程,也许可以跳出某种思维误区,关于农民政权的性质与转化等问题的学术争端也就迎刃而解。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0—501页。
〔5 〕以上统计数字参见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70页。
〔6〕《宫中档》(清咸丰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李汝昭:《镜山野史》。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9页。
〔8〕《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20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页。
标签:曾国藩论文; 洪秀全论文; 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