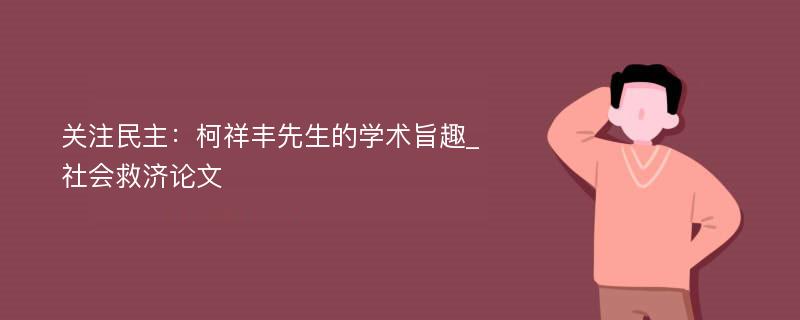
关注民主——柯象峰先生的学术主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民主论文,学术论文,柯象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象峰(1900-1983年),安徽贵池(今池州)人,著名社会学家。1912年求学于金陵中学,192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7-1930年于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0年获法国里昂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历任教授、系主任、金陵大学教务长。1943年当选中国社会学社理事长。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照搬苏联高教模式,撤消社会学,转任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1978年,南京大学恢复、重建经济学系,先生转任该系教授,以垂暮之年为中国经济社会学之发展尽最后之力。1980年,经小平同志指示,中国社会学得以恢复,先生已退休矣。但其一生最后几年,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进程。
柯象峰先生的社会学研究,重点突出,倾向明显,关注民生,匡济天下乃其学术主旨。在人口问题、贫困问题(先生称为贫穷问题)、社会救济诸领域,取得突出学术成就。1934年,发表第一部专著《现代人口问题》;1935年,出版《中国贫穷问题》专著,是社会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贫困问题的著述;1937年,发表《贫穷问题》著作,是为前书的扩展、深化与补充。前书专论中国,此书已论及一般、普遍。1943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先生身居课堂书斋,心怀天下民众,成就《社会救济》专著,亦乃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社会救济的著述。在此书“自叙”中,他说:“作者于十年前曾写成《中国贫穷问题》一书,其中多为贫穷之分析,而对于救济方面,仅涉端倪,未及详论,常引以为憾。今兹专论社会救济,以赎前愆。”(注:柯象峰:《社会救济·自叙》,正中书局1943年版(民国三十二年版)。)此外,先生还有译著《欧文选集》等发表。
一
柯象峰关注民生是从研究人口问题开始的。其动因有三:其一,“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已渐得一般人士的认识。”其二,“惟至今介绍人口问题之基本理论与事态的著作,尚不多见,除非是利用一些外国教科书。”其三,“西洋学者对于此项研究虽有很多阐精抉微的材料发表,亦可算为权威的著作。但是其中也有些难免入主出奴之见,或者是材料偏颇,文字结构亦有欠整饬的。要寻觅一本适合中国人士作初步研究的完善书本,是不容易的。”(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自序》,世界书局1934年版(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08页。)所以他利用“三年来教授此项问题”的资料积累与学术储备,写成《现代人口问题》一书,以贡献给中国学术界。上述动因,可概括为对民族之民生关怀和争取人口问题研究方面的话语权,以打破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话语霸权。
柯先生认为,人口问题之严重性表现,首先是人口分布不均,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不均,而且在一国内亦分布不均。其次,生活资料分布亦不均且严重不足。生活资料丰裕的国家人口却较少,生活资料匮乏的国家人口却较多。再次,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问题亦渐次突出。特别是贫穷国家,因男性为劳动力,所以以各种手段控制女性如溺女婴等等,导致男多女少。各年龄段人口,也多为不均。第四,出生率分布不均。经济发达人口文化素质较高的国家,出生率较低,落后国家则相反。而落后国家的死亡率则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为弥补人口死亡,又大大提高了出生率,恶性循环。这种不均又强化了以上的不均。其五,人口素质问题,先天缺陷人口问题(即优生问题)也日益突出。人口众多及教育的不普及或无法普及乃此问题之要津。其六,迫于人口压力,大量人口涌入都市寻求工作,导致极端都市化的发展,使都市在经济、文化、卫生诸方面难以应付。最后,欧美白人殖民主义者凭籍武力占据了本为全世界共有的广大区域及殖民地,并实行歧视性移民法,阻止世界人民尤其是东方有色人种移民,加剧了诸多不均,加剧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针对以上问题,柯先生提出“适中人口”范畴,以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目标。“适中人口是在某种环境内的一个理想的人口数量,他不是绝对的。”今日,“应以经济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唯物的观点来决定适中人口”,那就是“在有某种自然资源及存在某种生产制度或社会及经济的组织下,能使每一个人口均能获得充量的经济收入或经济物”的人口数量。所以,最适当的人口政策的实施,是应当以此为标准为终结的。”(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17-418页。)为实现此目标,他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条途径:世界人口分布合理化;各国之产业合理化(即据比较成本比较优势,充分发展各国之经济);各国人口增加之合理化(提倡、推行生育节制并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优生的合理化、法制化(以法律约束有先天重大缺陷及遗传缺陷者的生育)。后三条,已为当世人类之共识。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条,如何才能实现世界人口分布的合理化呢?柯先生认为,日本屡屡挑起战端,侵占别国领土,其深层动机之一,即为地狭人多导致的人口压力,加之军国主义因素。因此,对外侵略扩张乃日本的本性。对此,中国应有足够的警惕与注意。以战争手段为人口谋空间谋出路的方法柯先生认为是很坏的,不足取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中国因政治不良、经济落后(人均资源稀缺;资本与技术短缺)、科教落后、武力不强,更不可能用此道。用其原话:“在最近期内,决无妨害世界和平之可能。”(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4年版,401页。)奈何?柯先生是否留下了一点意味深长的考虑给人们思考呢?否!他说:“学者中当然也有主张用合理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冲突的:他们主张有土地甚多而不能利用的国家可以把这些土地善意的让渡于需要的国家。不过这种意见,终究是书生之见。在今日,人类方在文明途中的初段,充满着自私与短视,而国家主义的思想又弥漫着人间,加上一班贪狠的自私的资本家,尔虞我诈的政治家,狡猾的外交家的拨弄是非,这合理化的君子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目前人类一大部分,根本就缺乏这高尚的理智。”“除非是人类有了彻底觉悟,社会制度及人类文化有了彻底的改进。”(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4年版,413-414页。)换言之,他认为人口问题的彻底解决在于分布均匀的适中人口。而实现此点的前提之一,是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的成比例、相协调。因此人多地少与人少地多的国家可以善意协调让渡。这在目前,做不到。因此应寄希望于整个人类文化与制度的进步。所以他又写道:“目前世界人口与资源是有一种失调的现象为国际纠纷之源。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人口过庶的国家当然应尽先利用本国的资源,如增加耕地,利用尚未耕种的可耕地,以及移民支边等;一方面应有国际合作,凡是一国不能利用的土地,可以从协议或让渡的方式让人口过庶的国家去开发利用。”(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4年版,422页。)最起码西洋发达国家所占之广阔土地及殖民地,应准许世界各国人民移民。人类近代史都是西方列强到处侵略扩张的历史,柯先生却代表人口众多的东方落后国家向其要地,而且是通过和平的、理性的、人类文化获取进步了的方式。这究竟是柯先生过于天真、可爱,以书生之见与虎谋皮呢,还是彻底解决全球人口问题的一种先知先觉(当然要结合其他三条途径)?令人深思。
柯先生疾呼,人口过庶之问题能自我感觉到就有办法。最令人担忧的是人口已过庶,但因文化落后,对此危害浑然不觉。因此他强调改进文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之道。上述四条途径,皆以文化进步为基础,孙本文先生评价柯先生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时说:“自来人口论者大抵不出马尔萨斯之窠臼,注重纯粹生物的与经济的因果之探讨。”“而人口问题之重心,在文化而不在人口与食品”,这二者的关系仅为人口问题之表象,文化才是深层原因。“故研究吾国人口问题者,其注重之点应在如何改进文化环境。……柯象峰教授此书,其所持论,大率近是。”(注:孙本文:“柯象峰先生《现代人口问题》序”,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1页。)
从本国人口问题出发,将其置于宽泛、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讨论,将其视作社会大文化系统之一部分加以考察,并以世界性、人类性之眼光来寻求解决之道,即在今天,也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研究理路,可谓历久弥新。当今研究此问题的学者,有此恢宏精深理路者,亦不多见。
二
人口问题之严重性,集中于贫困问题的产生。柯先生随即将其对民生的关注转向贫困问题。
贫困问题虽乃人口问题的直接后果,但其成因则具多重性。所以贫困问题并非某一单纯因子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柯先生认为中国贫穷问题成因有三方面:其一,地理因子即地理环境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矿藏资源不丰、森林资源荒废、温度(气温)在地域、时间上分布不均匀、旱灾水灾频仍等。其二,生物因子,指生物环境的弱点。包括蝗灾频仍、各种病虫害多发,恶化了农业生产环境。各种疾病频发、流行,恶化了人的生存环境。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及设施又极度落后,两者交相作用,恶性循环。其三,人口过庶。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百年来人均寿命不足35岁。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还追求多子多生,又是一种交相作用,恶性循环。(注:参见柯象峰《贫穷问题·第2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二十六年版)。)他并未论及政治不良乃贫穷原因之一,这表明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立场。但他在论及贫穷之影响时,也并未迥避社会政治不良的问题。
贫穷的社会影响,柯象峰高度概括为“循环性”,即恶性循环。从微观言,贫穷导致无力求学读书,导致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做苦工为生,导致低工资,导致贫穷;贫穷导致无能力移往别处,导致失去许多良机,导致贫穷;贫穷导致情绪恶化,导致工作效能低就业机会少,导致贫穷;贫穷导致无知,导致不知节制导致过多生育,导致贫穷;贫穷导致自暴自弃,导致无志放纵堕落,导致贫穷(此论述远远早于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关于贫困文化呈现内在循环性特征的分析)。从宏观言,贫穷导致人类维护、改造地理环境的能力不足,导致地理环境恶化,导致贫穷;贫穷导致人类防治病虫害抵御疾病侵袭的能力不足,导致疾病与病虫害肆虐,导致贫穷;贫穷导致人的健康状况恶化,导致人的工作学习能力下降或不足,导致贫穷;贫穷导致社会病激增,如卖淫嫖娼、自杀犯罪等等,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人们悲观失望,导致贫穷;贫穷还导致社会人文环境恶化包括兵匪一家、贪污受贿、苛捐杂税、以权势欺凌弱小等腐朽现象遍布天下;还导致无力发展生产、经济落后、国力不强、外患不断、交通闭塞、科教不振;这一切又进一步导致贫穷。对贫穷后果如此系统、全面、辩证之分析,在今人之研究中亦属罕见。柯象峰忧心忡忡地写道:“贫穷多方面地引起社会的横逆淘汰,使社会日趋退化,这是实堪注目的。”(注:柯象峰《贫穷问题·第3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12页。)因此对贫穷问题必须予以积极的防治。
防治贫穷之途径有二,其一为预防,又分为两方面:改善自然环境与改善社会环境。改善自然环境包括改善自然之不足之处,以“文化克服自然”之不足,即以科技改善之。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推行少生优生的教育与政策,改善人口状况,尤其是要注意纠正人口的横逆淘汰现象。改善社会环境包括改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思想文化诸多方面。其二即为发展社会救济事业。预防乃治本,但须假以时日;救济为治标,可立竿见影。诸多贫穷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救济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以预防作基础,行救济之实践,二者齐头并进,标本兼治,贫穷问题可解决矣。(注:柯象峰《贫穷问题·第4章》,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二十六年版)。)
本着社会改良主义之宗旨,柯象峰此后对预防问题论及较少,而将学术研究之重点转向社会救济方面。
三
柯象峰对于社会救济之研究,突出贡献有三。其一,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社会救济的理论。他首先阐发了社会救济的概念:“社会救济,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缘(相对于血缘而言的人的社会关系)因某种疏忽、脱节、失调或冲突,而发生不幸、不良、不平或不安之状态时,而加以援助、纠正、调整或改善的一种社会工作及现象。”(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第1页。)显然,社会救济属社会工作范畴,且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社会救济呢?从社会的责任立场而言,人生的遭遇难得一帆风顺,而个人的种种不幸遭遇往往并非个人责任所致。如贫者不一定是能力薄弱、荒嬉颓废之徒。而能力薄弱、荒嬉颓废者,则不一定贫困,其间且有不少富有者。“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不平,社会的不公道。这种社会的不公道是由于好多因素造成的:自然的、遗传的(继承的)、尤其特别的是社会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酿成的。”“如果这是社会所造成的病态,这责任自应由社会来负起一大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社会救济,因为这是社会的责任。”(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3-4页。)从“社会关系和连带”即社会关联主义或社会连带主义的立场而言(社会关联—连带主义乃法国经济学家季特所创),“社会关联精神或连带主义,应该变成人们行为的准则,一种应尽的责任。其理由乃因每一个人的行为一定对于每一个其他人士以及彼此间要发生某种影响,也许是祸,也许是福。因此,我们彼此相对间的义务及损害,也随之而剧增。”“因此我们应当把人类的社会组成一个互助的大社会。在社会中根据善意的指导,使这关联的精神,变为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每一个人应分担别人的艰难与痛苦,而同时也可以分享别人的康乐与幸福。”(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6-7页。)从发扬我国社会道德的立场说,“我国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在人的方面,尤其是在社会伦理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因为我国文化根本就是一个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所以注重人伦或社会伦理;重视人与人相处的行为准则,所以重视道德;着眼于人世间的生活,所以重视现实;这是我国文化的特色,而为别的国家所不及的。”他继而阐发儒家伦理的最高境界,并非“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而“己所欲,施于人”和“人所不欲施于己”方为儒学伦理的理想境界。(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9页。)因此,利天下从利人做起,利人才是利天下之起点。“据以上三方面的理论,社会救济实在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工作了。”(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10页。)柯象峰还将社会救济作为实现其理想社会的途径之一,“社会救济以实现大同思想为终极”。“试观‘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206页。)柯先生赋予、寄托于社会救济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实用价值。
其二,结合中国实际,引入并发展了可行性现代救济理念。单纯之救济不可取,救济应以培育、恢复被救济者的能力、使其能够自立为要旨。当然,不可能达成此者,仍应予以单纯救济。科学的救济观与方法论就此确立。柯象峰写道,救济应恰到好处,太过则长其依赖性,不足则不足以令其自立;救济应当同时改造其心理、人格,“教”“养”兼施;救济事业应重预防,预防式治贫事半而功倍;救济要有科学头脑,要变妇人之仁为积极的爱护,虽必须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手段则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总之,救济的目的,是要使不能生产者能得着适当的生活,使无力生产者养成生产能力,已经失去生产能力以及暂时失去生产机会者,均各得适当之救济,能培植及恢复生产能力。”(注:柯象峰:《贫穷问题》,商务印务馆1937年版,第123、134页。)“教”“养”并重,救济与助其自立相结合,被动式救济与主动式救济相联系,至今仍是社会救济事业的要旨。
其三,科学预见了社会救济事业的未来发展与变化,显示了其学术研究的高度前瞻性。他认为,社会救济作为社会工作之一部分,偏重于事态之矫正,稍带消极办法之色彩。但在不久的将来,在社会制度未臻合理化之前,仍有不可缺少之贡献。即使将来因整个社会之日臻完善,仍有其地位(如病疾、残废之助理等),不过或须变换其形式——由社会救济发展为社会保险,更由社会保险发展为社会(经济生活)安全制度,即社会福利制度。虽然达此,需社会诸多条件的配合进行,方能成就。(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210-211页。)这不仅是他的预见,而且是他的理想。因为“社会福利可以说是社会的保健,相当于吾人日常生活之卫生或保健,是比较广义的、积极的、预防的、治本的。”(注: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3年版“绪言”第2页。)
柯象峰先生立足于社会实际,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救济范围、对象,并对之作了科学分类(长时期的和临时的、全部的和部分的等等),研习了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救济模式,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必须由政府和社会(民间组织)共同进行,共同发展,才能趋于完善,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救济功能的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之道。他还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措施与对策建议,包括树立正确观念、筹措资金制度、培养专业人才等等,完整地架构了当时条件下中国救济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及制度框架。
四
柯象峰先生的学术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毕生研究,关注民生,乃其最大最基本特色。
非常重视实证性资料,是其学术研究的又一特色。这与其接受过严格西学训练及承传了社会学的实证性传统直接相关。为取得实证性资料,柯先生重视并常常自行调查研究。如在论述中国的人口问题时,他即仔细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的人口密度。“其中人口密度最高者为江苏(813人/1平方英里——1928年),较当时欧洲人口密度最高之比利时尤高;其次还有浙江(554人),河北(583人),山东(552人),河南(454人),均呈人口过庶现象。”(注:柯象峰:《现代人口问题·自序》,世界书局1934年版(民国二十三年版),第308页。)
柯先生学术研究特色之三,非常关注西学相关理论及其进展,并常介绍引用之,将其内化于并丰富自己的学术探讨。如他分析贫穷原因时,分别介绍了吉宁(Gillin)、庞慕利(Parmelee)、德克氏特(Dexter)等人的见解,进而食洋而化,得出自己的分析。
柯先生学术研究特色之四,擅长于分析—综合之中有所创新。柯先生每研究一问题,首先是分析,条分缕析,步步深入,然后精辟综合,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于分析—综合之中,旁征博引,理论实证,阐发出自己的见解,常有创新独到之处,如文化问题乃人口问题之深层原因;贫穷问题的恶果在于贫穷所致的恶性循环;科学救济观的完整论述等等等等,莫不如此。
柯先生学术研究特色之五,即重应用。学以致用,研以致用,经世致用,救济民生。所以他对人口问题、贫困问题、社会救济之研究,均以解决之道为结论。其研究的问题,均乃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其研究结论,多为可行性对策(当然也有少部分非可行的书生理想主义之见)。于此,其学术宗旨可见一斑,社会关怀、造福社会乃其底蕴。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老一辈社会学家多为高度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者,柯象峰先生亦然。他对民生问题如此系统、深刻的关注,使其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必据一席之地。
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有两种思路。一为经论,一为策论。经论者追求制度的革命,近代中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必先解决民族民权问题,解决此二者乃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为经论。策论者寻求制度的改良,即并未对现行社会制度作根本价值研判,而是寻求面对既定现实,如何一步步改良社会,推进发展。概括之,策论者论述应该如何;经论者诉求为什么必须如何。柯先生据社会改良主义立场,为策论者。
当代经济学发展的主潮之一,乃制度经济学的再度崛起。科斯、诺斯、福格尔、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当属制度学派。该学派认为,制度成本的高低,是社会能否发展之关键。社会的一切进步,均依赖于制度成本之低下;反之亦然。制度学派通过分析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正相关性,指出了制度对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追求制度的变革。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具巨大影响的观点吻合,不过更加具像和经济学化而已。近代中国之贫困,归根结底乃制度之贫困。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成本太高,社会制度与发展不协调、不相容;社会制度并不支持、甚至阻滞了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缺乏现代化的、先进的、优良的制度,制度贫困乃近代中国贫困之源。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无论是经论者,还是第二类的策论者,都追求中国社会制度的改良、进步,都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值得后人尊重、景仰。柯象峰先生当在此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