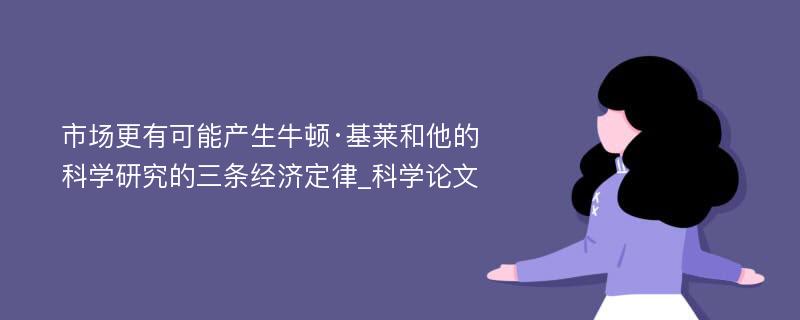
市场更能产生牛顿——基莱和他的科学研究的经济三定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更能论文,定律论文,科学研究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百多年前的英国,牛顿用力学三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物体运动规律统一起来,标志着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最后完成。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英国,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学者,基莱,在其《科学研究的经济定律》一书中,也提出三个“定律”——“科学研究的经济三定律”,试图揭示对科学研究投入的经济规律,并大有引发关于科研投入的“经济学革命”之势。他的努力在科技政策研究者和一些经济学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反响。
基莱所说的科学研究是指所有的研究与开发(R&D)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基莱之前,有很多学者研究过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他们大都认定或默认,虽然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大部分基础研究、部分应用研究和少量的技术开发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主要是因为这类研究成果的公有性或对经济作用间接性等等,使研究者无法独占创新收益,因而企业或私人缺乏投入的兴趣,亦即单纯的自由放任政策会导致“市场失效”。基莱则对政府介入任何R&D活动表示怀疑, 而这又与他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的分析相关。
传统上,涉及科技对经济作用时,人们习惯于沿用的“培根模式”。这种模式把纯科学作为源头,认为应用科学或技术产生于纯科学,经济增长则由技术进步所推动。基莱指出,这是一种单向线性模式。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技术是更基本的力量,新技术要么从原有的技术中产生,要么是科学和原有技术相互作用而产生。科学又是由技术上的需要所推动,其发展离不开技术手段。这个论点使我们想起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技术上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总的来说,科学是由技术“内生”的。所以,他认为科学和技术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创新过程是在市场中进行的,科学又能由技术“内生”,因此科学和技术都是市场内生的。
如果我们同意基莱的上述“内生”观点,那么我们就会主张,政府应当尽量少介入科学研究,因为国家介入就等于“集权”和“计划”。基莱把“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推广到科学研究领域,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不可以计划,也不可能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和“计划”大都使其偏离市场,走向低效。把科学当成独立于市场之外同时又能推动技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过分夸大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他还考察了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历史,认为是市场经济推动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就是说,不是由国家垄断的“学术研究”推动了前者。
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基莱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一些经济指标,主要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和R&D投入的数据作了一定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三个“经济定律”:
第一定律:各个国家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增加。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需要增加R&D的投入, 因为发达国家在科技进步停止的情况下,会出现收益递减。要么创新,要么落后,已是市场经济的铁的规律。 而技术发展程度越高, 进一步创新所要求R&D投入比例越高。市场经济使不断的科技创新、不断增加的R&D投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发展中国家则可利用技术引进或仿创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其R&D投入占GDP比例可以低一些。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R&D 投入比例不能太低:引进或仿创也是一个创新过程,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点,否则就很可能是无效的引进或仿创:或者无法打破先行者已经形成的市场优势,或者不能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要设法形成自己的首创之点。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如此。因为,由于贸易壁垒的减少,国内市场的开放,单纯的技术引进的效用也随之减弱。
第二定律:对R&D 的公共投入(主要指国家)和私人投入(企业等)的数量之间,存在相互消减和替换的关系:国家投入多了,私人投入就会减少;私人投入多了,国家投入就会减少。这是因为,国家和企业对R&D的投入都是利用企业所创造的利税中的一部分来进行的, 一方占用资金多些,另一方占用资金就会少些。这里隐含一个判断:如果国家不进行“效绩低下”的投入,企业会作相应的、更加合理的投入,因此,国家和企业的投入不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更多的研究者看来,国家投入的科学研究的探索性和开拓性的特点,为企业的投入开辟了更多的可能空间,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的投入会引起企业投入的增加。
第三定律:上述消减和替换是不对等的:国家投入导致私人投入的减少,大于国家投入本身。 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抽取企业的收入从事R&D活动,削减了企业的投资能力。同时,国家对某一领域的投入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投入同一领域的壁垒,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总的投资成本——至少就市场交易成本而言。因此,国家对R&D的投入导致企业和私人R&D投入的减少,大于国家投入本身。总之,国家投入的负面作用大于其促进作用,这似乎又进一步说明了科学技术应是市场内生的。
这些观点引起了较大争议。人们对第一定律异议较少。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定律。基莱的反对者如鲍·戴维、本·马丁等人认为国家资助部分R&D(尤其是基础研究)活动是必要的,如前面所述, 企业因无法独占这类研究的收益,从而很少介入。一些大的综合性研究(如历史上的曼哈顿工程、航天工程)也需要国家来主持,事实也证明这些研究在以后产生了商业效应。而市场自身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介入科学研究,形成了探索性研究和实用定向研究之间的互补,使企业回避风险并节省社会的总研究费用,如果基莱所说的国家的投入导致私人投入的更多的减少是正确的,也只能从这种意义来理解。一些人还认为,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国家权力对科技和教育的忽视,是造成某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科技和经济衰落的原因。
基莱则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介入,企业有必要而且会愿意资助纯科学或基础研究。科学及某些技术尽管具有公共性(非排它性)和探索性的特点,但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现象。(1 )率先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企业或其它机构,虽然不能独占其研究成果(公共性),但能作为“第一行动者”对市场形成独占和垄断,这种垄断地位只会在以后的技术扩散中逐渐失去。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2 )只想“搭便车”的“第二行动者”尽管可以回避“探索性研究”固有的风险,但也并非不花费成本。纯科学并非免费的午餐。这可作如下比喻:法律知识是公共的,但人们到了打官司的时候,还是要花钱聘请律师以利用其多年积累的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第二行动者,要花一定代价去打破第一行动者业已形成的垄断地位。此外,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的联合也使市场自身能进行大的综合性研究的可能。如果说市场因“短视”不能产生这类研究的从事者,那么,国家的“长期战略目标”的依据又何在呢?凭什么说它比市场、企业更高明呢?他以日本政府主持第五代计算机研究计划的失败来说明这种来自政府长期战略目标的不可靠性。因此,市场更能够让牛顿们产生。
的确,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其建制化;并且随着其逐渐完善及科技自身发展的特点,如某些领域从科学到技术的距离缩短,甚至在某些方面一体化,都使得R&D 研究越来越企业内部化和市场化。但是,市场能否成熟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能把所有技术和科学(尤其是纯科学)直接纳入其中,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环节,是需要审慎研究的。至少,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在企业规模都不大的情况下,政府介入部分R&D活动是必要的。
但是,人们已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应主要在市场之中进行。同时,由于某些科学和技术的直接和紧密联系,使得很多企业也直接从事或资助基础研究,这表明基莱的观点的某些合理性。除了基莱的分析以外,市场本身还存在其它支持基础研究的因素,如企业规模的扩大、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直接支持基础研究的多元效应等等。这意味着我们起码应充分研究并有效利用市场本身的上述因素,完善市场机制。虽然科学研究完全市场化仍是值得怀疑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由于大部分技术创新和部分基础研究能在市场中有效进行,政府似应把主要力量用于其它需要支持的基础研究之中,如果政府也介入市场本身能够有效支持的R&D活动,一方面, 可能会真的出现基莱所说的“替换和消减”;另一方面,也很难真正做到“稳住一头,放开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