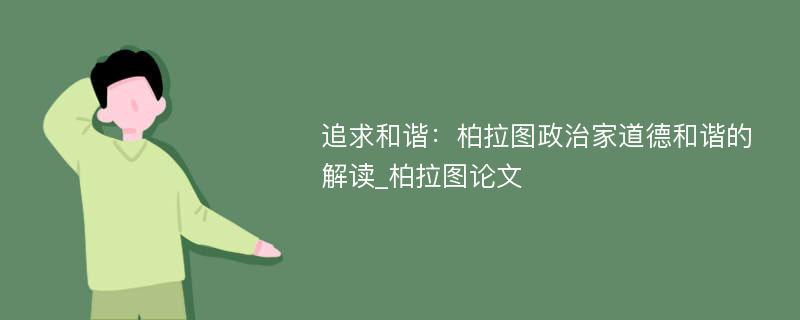
和谐的追寻:柏拉图《政治家》中的德性和谐思想演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和谐论文,德性论文,政治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3)10-0008-05
一、思想渊源和理论发展
柏拉图哲学是毕达哥拉思、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德性和谐思想无疑也受他们和谐思想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主张,世界万事万物从形式上讲都仿效了“数”的自身和谐性,和谐是最重要的一种“数”的规定性。灵魂是毕氏的核心概念之一,“灵魂是一种和谐”(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魂的和谐既是灵魂和肉体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和谐,又是灵魂内部各种不同因素之间的和谐;净化灵魂的目的是使灵魂处于和谐状态。柏拉图吸收了毕氏灵魂和谐思想,但是反对毕氏把数学比例和谐同灵魂和谐两种不同意义的和谐无原则的地加以混淆。他在《政治家》中对此作了明确划分,认为数学量度和道德评价是不同的,二者不应混同。
巴门尼德认为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自身等同性,即存在等于存在自身;存在的和谐即符合同一律的自身同一反复性。柏拉图吸收了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合理思想,将巴氏赋予存在的稳定、恒久和绝对品质移用于理念之上,但是他反对巴氏对感性事物无原则放弃。他认为感性事物作为辅助事物和理性分不开,同名的理性和感性事物暗寓一种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善的理念对于各种感性事物起着价值上的导引作用,就像一个国家中国王的统治离不开其他阶层的辅助一样。
苏格拉底认为和谐的基点在于善。就善本身而言,它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和谐原则;当一个人在从某种特殊的善行时,他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感性事物和具体环境的影响,这些感性因素和环境都带有特殊性;于是,善的动机和善的行为之间便产生了距离,即便把所有人的善行加起来也不可能等于善本身。柏拉图继承了苏氏对善的高扬精神,并以此为核心作了理念论的梳理和阐释,将善所统领的众理念形成和谐的理念结构。
以上是对柏拉图和谐思想传承关系的简单回顾,下面对柏拉图的德性作一简单的界定。现代意义上的“德性”主要侧重道德性质和个人性质。而古代的“德性”概念意义要更加宽广,不仅指称道德,而且指称非道德;不仅用于个人,而且用于制度。德性是古代伦理学的中心概念,甚至成为传统伦理学的一种主要形态。柏拉图哲学中的“德性”概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并不纯然局限于道德领域的美德因素。就狭义而言,德性与道德品质关系较为密切;就广义而言,德性指的是过好生活或做善事的卓越艺术,是一切技艺中最高尚的技艺和规范。本文所讲的德性总体上包括技艺和美德两个方面,尤重技艺层面。
我们不仅要看到柏拉图对前人的思想承继,而且也要注意到他自身思想的发展过程。
柏拉图思想主要奠基于理念论之上。柏拉图认为先有理念,后才产生出具体事物;个别具体事物都不是如实的存在,而本有的实存只有理念;个别事物是以理念为型范而铸成,它们摹仿或分有理念,但不能完全和理念相似,终不及原来的理念那么完满。同样,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那些理念并非一一处于平等地位,而是有高下之分。不同的理念随高下之分层层递进,形成一个阶梯体系。居于这个体系顶端的是“善”,这个理念处于众理念之上,好像其下的那些理念都以它为目标,向它而趋。因而善的理念是最完美的、最圆满的,是理念世界中唯一君王。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具有浓浓的伦理色彩和理想氛围。
理念论在柏拉图那里最直接、最出色的运用,是他以此为基点,根据他心目中的国家理念构建了“理想国”的治世蓝图。这个理想国散发出一种整体善的光彩,是善的理念的最完美的再现。理想国在世上也许并不存在,但是作为理想具有永恒的魅力,可以说每一个人心目中都藏着一个理想国,向善而趋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恒久冲动。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他的德性和谐思想。柏拉图认为个人和国家在德性上是同构的。在个人方面,他认为人的灵魂分为3部分:理性、意志和欲望,灵魂是这3部分的和谐统一体。理性的德性是智慧,意志的德性是勇敢,欲望的德性是节制,若能实现三者的和谐,其中涵蕴的美德是正义(公正)。在国家方面,柏拉图将全体公民分为3部分:统治者、军人和手工业者、商人、农夫等自由民。统治国家的哲学王应是善的体现者,其德性是智慧;军人的德性是勇敢;而手工业者、商人和农夫的德性是节制;当3者各安其事,各得其所时,就会体现出正义(公正),也就是国家的和谐状态。在这里,和谐和正义在内涵上相类,由此柏拉图的德性和谐不仅是对各阶层的要求,也是对个人的道德要求。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家完全按照理性的抽象要求,遵循形式上的和谐原则进行,凸显了他的重德思想。同时柏拉图也认为,现实国家和理想国家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有必要研究使治理国家的现实政治达到相对完善状态的有效手段。
以上是对柏拉图德性和谐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作了一个简单回顾。
二、德性和谐的标准是“中”
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承继以前的思想,并作了相应的修正和发展。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蓝图是作为国家的模型而提出来的,毕竟这种理想状态和现实政治有一定差距,它的实现是不大可能的,从而哲学王出现的可能性也不大。人们与其拘泥于现实政治的绝对完善主题,不如研究使现实政治达到相对完善的有效手段和技艺。柏拉图认为,个人德性和国家德性的关系是大字母和小字母的关系;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个人是缩小了的国家;存在于二者中的最高德性就是正义,也就是德性的和谐状态。寻找理想的国家便等于寻找理想的哲学王及其理想的辅佐者,理想的国家便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反之亦然;那么,寻找现实的国家便等于寻找现实的政治家及其辅佐者,现实的政体(国家)便是政治家统治的政体(国家),反之亦然。正如善的理念是唯一的,理想国也是唯一的;正如其他理念由于分有或摹仿善的理念的程度不一而有差异,各现实政体会因摹仿理想政体(国家)的程度不一而出现不同名的政体(国家),从而各现实政治家会因摹仿真正的政治家技艺程度不同而出现不同名的政治家。因此,柏拉图的德性和谐思想包括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
柏拉图的德性和谐是以价值向度为依归,以政治伦理为特色,以向善而趋为方向。在《政治家》中,他探讨政治家真正的治国技艺,追求国家和个人的整体和谐状态,这就涉及到如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技艺以及怎样实施的标准问题。欲探究柏拉图的德性和谐思想,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标准问题。柏拉图提出德性和谐的标准是“中”。
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客观存在的现存物仅因分有或摹仿理念而获得存在的权利和合理性。现存物存在的依据在于理念,由是只有理念才是永恒的、绝对的,也只有理念才是现存物存在的标准。尽管在诸理念组成的理念世界中,善居于最高地位,但就各理念相对于各相应的同名存在物而言,它是这些存在物的极致和圆满状态,丝毫也不因这些存在物对理念的分有或摹仿程度的差异和高下而有所贬损。譬如,工匠制造各种人造物所依据的就是各种理念,同样,评价这种人造物的标准也只能是理念,以各人造物对理念的分有或摹仿程度而品评高下与否。各制造物的理念是工匠有意识要全力趋赴的,但各制造物终究是理念的近似样式,不可能达到极致状态。各理念作为向善的召唤,对工匠起着一种“应然”的导引作用。由之可以从对制造物的尽善尽美的追求过渡到对工匠制造技艺的尽善尽美的追求。
显然,仅以善的理念作为众理念乃至各种具体制造物的应然追求还较为笼统。当柏拉图用现实眼光探究政治家技艺时,他特地提出了“中”的标准,并以此开启了亚里士多德求中庸的理路。当然,不仅政治家技艺以之然,各种技艺也为之然。在此,可将善视为事物的终极价值目标,“中”可视为由善到事物的辐射线的中间层面。如将善视为普照光的话,那么“中”则是滤光镜,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善的理念,下启具体事物(包括制造物,并尤以制造物可体现出“中”的作用)。就“中”为所有技艺所遵循的依据而言,它有共性的一面,并以此保其价值性;就“中”在不同技艺中有着不同的具体的意蕴而言,它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并以此保其操作性。正因为这样,“中”才可能起标准之用。
柏拉图认为所有技艺共通地存在较大与较小的测定问题;易言之,所有技艺都可被看作量度技艺问题,大小即量度。较大与较小甚或量度的勘定标准有两个:①比较标准:相互比勘,较大只比小大,不比其他任何大,而较小只比大小,不比任何小。这种比较没有某种绝对的标准作为参照。所谓的较大与较小,只在相比较而言的意义上成立,一旦脱离二者的比照关系,则二者的大小关系便不复存在。因此,二者仅具有相对意义,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指归意义,它们随着不同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这种较大较小仅具有名称意义,不具有实质意义。②“中”的标准:“中”的标准决定着比较标准,“如果这一标准存在,它们(较大与较小——笔者注)也存在;如果它们存在,则这一标准也存在;但如果其中之一不存在,则两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1-1]当衡之以“中”的标准的时候,较大与较小都是与“中”相比较而得出的,较大不仅比小大,而且比中大;较小不仅比大小,而且比中小。不仅大小如此,而且健全的人与有缺陷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合乎“中”。“不管在口头上还是在实际上,都真实地存在着超过中和不及中”,[1-2]过犹不及,都是不合“中”的状态。当有些技艺发生超过“中”或者不及“中”的情形时,那么会出现“现实实践中的真正困难”;而“当它们保持了中的标准时,它们的所有成果才会又美又好”,[1-3]由此“中”的标准的价值指归意义立显。由两种标准出发,柏拉图将“量度技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所有测量、数目、长度、宽度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对立面的技艺,另一部分包括那些与适度、恰当、恰好、必要以及所有其他位于两端之间的‘中’的标准相关的技艺。”[1-4]
柏拉图认为比较标准更重差别方面,二物的相互比勘以差异为基础;“中”的标准更重统一方面,它是所有过与不及的契合处。两种标准应结合起来以臻和谐,而不是“草率地把那些迥然不同的关系纳入同一个范畴”,[1-5]应在众多对象不同处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同时亦应在众多事物统一处看到事物的所有差别。柏拉图在探求政治家技艺时所应运用的一分为二的方法中,就依循了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原则,此不赘述。
包括政治家技艺在内的所有技艺都要依“中”的标准加以审视自己的价值,合乎“中”的标准成果又美又好,但在实际状况中,达到“中”的标准少之又少,过与不及恰恰是常态,我们也只能从过与不及中得以窥得“中”之一斑。合乎“中”的标准的政治家技艺是理想国里的合乎理念状态的技艺,只有理想的哲学王能为之,现实中尽管心向往之,但连柏拉图本人也认为实不能至。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偏离“中”的标准的政治家技艺是常态,柏拉图列举了政体作为例证。在个人的品德问题上,合乎“中”的标准的才是美德。有的美德要素在类别上是对立的,但因皆合乎“中”的标准,所以都能名之以美德。如勇敢便是对动作敏捷、敏锐的称赞,但这并不妨碍用节制(得体)表达对动作平稳、舒缓的表征。但当不合乎“中”的标准时,同样的美德要素其意蕴发生变化,动作快到超乎正当理由的激烈时,会被称作凶暴、疯狂;如若动作慢到超乎正当理由的沉稳时,会被称作怯懦、迟钝。可见,不管是政治家技艺还是个人美德,都须要合乎“中”的标准。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曾将“中道”视为至高美德,主张两端之间用其中,比如说勇敢就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鲁莽和怯懦就是两极状态;前者失之过,后者失之不及,过犹不及,两者都没有达到理想的中道状态——勇敢。从中可以看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的师承关系。学生的理论继承就是老师的理论影响之所在,尽管继承的要旨是在超越。
三、德性和谐的要义在于“编织”
柏拉图着力于政治家专门技艺的探求,无非是要找一种合乎“中”的标准的最伟大、最崇高的治国技艺。理想虽好,实际不可得,那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能做到的便是要求政治家应该追求对这种理想的治国技艺的无限接近。政治家技艺与士兵、法官以及通过利用口才以“劝人”为名的传道士的技艺有区别。政治家的任务不在说服或打赢战争,而是决定应该采取说服还是强制手段,以及是否进行战争。所以他的任务不是执行法律,而是制订法庭必须执行的法律。政治家的作用就是控制和协调所有人的种种活动,他的任务就是在一国之内把所有的阶级像织布一样“编织”起来,成为一种最壮丽、最美好的织物;当编织完成时,和谐便在其中了。柏拉图通过“编织”的隐喻对现实的个人和国家的社会关系以及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作了深刻的揭示。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以人的本性为依据,将社会成员作了各种划分,从而构成他的以纵向制约为特色的编织(统治)结构。正如编织衣物的主要技艺包括一些辅助技艺一样,政治家技艺也需要各种社会成员的辅助,但这种辅助是由政治家来单向推动的,是他“编织”的结果。正像一匹编织物中较硬的经线和较软的纬线交织成那样,国民的生活或特性也具有相似的组成成因,其构成因素既有较为坚强刚硬的气质,也有比较柔和阴弱的气质。柏拉图列举了两种主要气质:刚勇雄健的气质以及平和文雅的气质。这两种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一类的德性是勇敢,另一类的德性是节制,二者就其各自依中而成其为德性而言,它们无冲突。当二者各自走向极端而不经另一方的调和,都会走向美德的反面。一类退化成粗暴和疯狂,另一类要变成怯懦和迟钝。一个社会分别各依一种德性,后果都会堪虞。倘若一个社会生活的基调是持久的节制,起初是无防人之心、爱好和平,但因实际上它没有勇敢作为调节,最终会衍化成怯懦,以被侵略者奴役而告终;反之,一个社会假如选择勇敢作为占优势的基调,会由于过分好战而陷入与许多强有力对手的敌对状态中,同样会导致被奴役的结果。真正的政治家在于以和谐之道化之,即要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德性灵活而妥善地“编织”在一起。他会监督教育家训练年轻人的性格,培育不同德性的以供“编织”之用的经纬线,为防止不和谐的性格变成不利于编织的因素,应用死刑或流放排除之。当编织材料具备后,政治家开始加以编织他的经纬线——勇敢和节制的人,当他把具有勇敢性格的人视为经线,把具有节制性格的人视为纬线,把二者“编织”起来,从而达到一种公民各安其事、各从其职的和谐状态。政治家的技艺也需要其他各阶层公民技艺作为伴随技艺共同起作用,公民技艺的外现无非是本职活动而已。因此,技艺方面的德性和谐就是各个阶层公民按其本性外化其技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本职工作)时表现出来的和谐状态。
每个公民应学会双重“编织”,一方面每个人的德性不仅作为经纬线以供政治家施以从上而下的编织之用;另一方面他又要对自身德性要素加以协调性的编织。公民灵魂中勇敢和节制等永恒部分要用神的结合力加以结合,兽性部分要用人类的结合力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勇敢和节制德性同样需要对方的补充和调节,每个人都热切寻找相类似的品质,后果却是有危害的。具有勇敢品质的人在行动的大胆方面优于节制的人,具有节制品质的人一般异常谨慎、公正和稳健。勇敢的品质如不与节制相互协调,显得公正与谨慎不足,终会衍变为完全的疯狂;节制如没有勇敢的搀杂,会缺乏敏锐和某种迅捷而主动的胆气,终会变得过于呆滞而最终完全丧失活力。所以,个人自身的品质也同样需要编织,即“决不允许自制的品质与勇敢分开,而且凭着共同的信仰、荣誉、耻辱、见解以及誓约的交换把它们编织在一起,从而把他们编制成意见平滑的、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织得很好的织物。”[1-6]
概言之,当个人自身勇敢和节制的品质得到协调的编织,同时,节制和勇敢的人被君主(现代社会就是各种公共机构以及具体制度)编入共同的生活中,各个部门都由两种类别的人组成,一个国家才会在公共和私人事物方面都取得完全的成功,整个社会的和谐便会到来。换言之,一个各安其所、各得其命、得其所哉、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关系便得以建构完成。
四、德性和谐的基点在于理性
柏拉图的德性和谐观是以其理念论(即理性论)为基础的。他认为理念是本,摹本是末。不论是在个人的砥砺方面,还是在国家德性的建构方面,实际上都是以理性(理念)作为指导。理想政治家不过是理性的化身而已,他同样也遵循理性的指引,并以获得理性(理念)为最大的美德。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德性各构成要素协调一致时,个人德性和国家德性才会实现和谐。在这里笔者将理性、智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作等同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提出“四主德”说,国家正义在于3阶层(统治者、武士及手工业者、农夫和商人)的和谐一致,个人的正义在于灵魂3要素(理性、意志和情欲)的和谐一致。统治者具有理性的德性智慧,武士具有意志的德性勇敢,工农商人具有情欲的德性节制。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是靠理性(智慧)来统合武士和工农商阶层的,因此,智慧是最基本的美德,勇敢和节制皆离不开智慧。
在《政治家》中柏拉图仍延续了《理想国》中的对理性作用的强调,并加之以现实的改造。柏拉图探讨政治家技艺无非是寻找一种理想的、可供各类不同名政治家摹仿的技艺原型,合乎“中”的标准的真正政治家技艺称得上是“最伟大和最崇高的非物质的东西,只能借助于理性来展示”。[1-7]柏拉图是在共通的意义上谈论政治家技艺及与其相应的政体形式,无论什么样的现实政体都是和相应的政治家一一对应,政治家表征着所在国家的政体形式,各种政体本身即政治家通过不同的方法编织公民所致。真正政治家技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家技艺,同样,按照真正政治家技艺施以统治的政体是唯一正确的政体形式。政体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对真正政治家技艺的摹仿程度的不同而已,只不过有的摹仿得好一些,有的坏一些。政治家的技艺与其说是实践性的,不如说是理性的要来得好一些。政治家“必定是依据某一技艺或知识来行使他们的统治的”,“并总是尽可能凭借才智和技艺施予公民以绝对的公正,从而保护他们而使他们境况更好”。[1-8]只有拥有政治家技艺知识的明智而且赋有国王本性的人将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由此政治家总是凭自身的智慧去施行统治,完成编织臣民的工作,去引导国家臻于和谐状态,而不管其统治是否是出于臣民意愿,是否有成文法。真正的政治家应根据“知识”(理性)而非法律去施行统治,而立法本身是政治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政治家既然能制订法律,当然也能发布与已有法律相分离的其它法律,一切唯“中”是从。法律有过于凝固化、狭隘化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考虑到任何人,在人们制订的法律和自身的活动之间更应该以什么为本,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最理想的事情是政治家体现为纯智慧(理性)的权力而非受法律约束的权力,那么,正确的政府就是“把专门技艺的权威置于法律之上”的政府。[1-9]政治家唯一恰当的品格是他的智慧和美德,他就是凭他的智慧和美德为国家领航。假定政治家强迫人们做比他们以往所做的更公正、更高尚、更好的事,却与法律和传统相反,应不受谴责,恰恰在这个时候,他更显得像本真意义上的政治家,正在以其政治家智慧运用政治家技艺来管理国家,令人心仪的各阶层各从其事的和谐状态无非是这种管理自然而然的结果。
柏拉图一直未能忘情于从演绎的角度尽力于他的理想国家的建构。但经验事实告诉他,正如真正的政治家技艺是所有技艺中最高技艺一样,真正掌握这种技艺的人一定少之又少(一两个人)以至于无;由理想的政治家统治的政体是唯一正确的政体,可是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多元政体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距离,因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理想政体中,政治家凭真正的政治家技艺在理性指导下实行符合“中”的标准的统治,这是最完美的形式;可在现实的多元政体中人们不得不做次好的选择,他们选择法律作为施政的某种标准,毕竟法律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客观可能,最起码对于政治家自身不可避免的人性限制对施政的不良影响作了有益的补充。柏拉图以统治者数量的多寡和法律的有无为基准划分了几种政体,并一一做了必要的价值评价。有法律的君主统治是现实各政体中最好的,排斥法律的君主政体是最坏的;民主政体是有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好的,而又是无法律的政府中最不坏的。
柏拉图探讨政治家技艺是有现实考虑的,他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资摹仿的真正治国之道。显然,柏拉图心目中最真的政治家技艺便是理念形态的政治家技艺,而现实的政治家是政治家理念的程度不同的摹仿。政治家行使“编织”式的统治智能,是力求找出适合“中”的标准的内部秩序井然的理想政体,这种政体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最大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家是君主制国家,这是和他的唯一的最高至善理念统领一切的理论体系是契合无间的。
收稿日期:2003-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