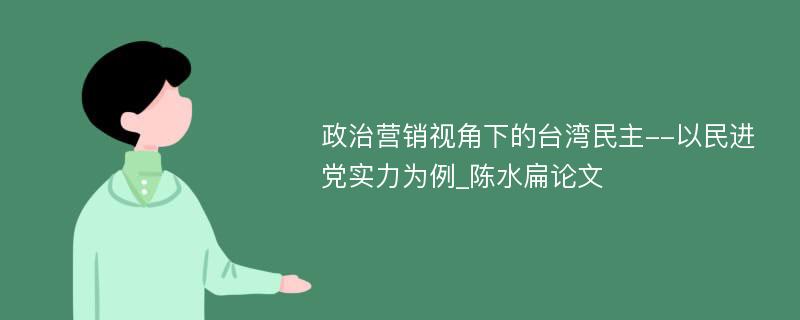
从政治营销的视角看台湾民主:以民进党的实力消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进党论文,为例论文,看台论文,视角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4)04-0061-08 在台湾的政治发展中,经由解严、党禁报禁的开放、两次政党轮替,逐步使台湾实现了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其中,民进党的成立和成长推动了台湾政治转型进程,使台湾民众“获得了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实现了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公职人员直接选举”。①许多学者也把民进党的成立和成长所带来的台湾政治转型称为“较成功的样板”,认为“台湾是第一个成功地从安定的威权体制直接转变为稳定的民主政体的典范”。② 然而,台湾民主的“异化”发展也是有目共睹:“民众认同出现混乱,省籍、族群对立与统‘独’对抗交织在一起,台湾社会被严重撕裂”,“民众的正当民主权利诉求被引向危险的‘台独’方向”,“具有浓厚分离倾向的‘台湾主体意识’在岛内恶性膨胀”,“权钱交易、黑金政治、暴力事件、选举‘奥步’层出不穷”,“民众一人一票选出的领导人也会无视法律与道德贪腐成性”,严重伤害了台湾的民主品质。③结果是,台湾社会“民粹主义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势力张狂、政客道德沦丧”,④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的精神,偏离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轨道。 对于台湾民主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异化”现象,已有很多学者从民进党反商、暴力、街头运动、“台独”等诸多“负面基因”方面进行过多重角度的剖析,但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运用政治营销的相关概念来解析者尚不多见。事实上,在政治转型发生之后的台湾,“选举已成为规模最广大、影响最深远、重复最频繁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⑤而大众媒体的发达又使政治营销成为选举中增强政党实力、获取选票的最有力武器之一。民进党是较早较自觉地运用政治营销增强其政治实力,从而推动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政党。但是,民进党在运用政治营销克服其诸多“负面基因”并增强其政党实力时,也通过掺杂政治欺骗和利用台湾民众的集体非理性,把陈水扁和“台独”等“伪劣产品”推销给了台湾人民,以挟持“人民的选择”⑥来获取政治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民主的“异化”。本文拟从这一新的视角,以民进党的实力消长为例,通过解析其实力消长的原因,说明民进党如何挟持“人民的选择”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民主的“异化”,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台湾民主的另一面。 一、锁定营销对象形成和巩固“基本盘” 政治营销是政治组织推销其政治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政治产品,以换取公众支持,发挥政治影响力并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活动。⑦在政治营销过程中,政治组织把政治视为一个市场。政治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市场交易关系,政治组织是销售者,民众是消费者。所交易的对象是政治产品,包括政治主张和公共政策,所获得的交易货币则是民众的支持态度,比如选票或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支持。由于政治组织把政治视为一个市场,那么,政治组织在进行政治营销的过程中,主要是运用市场营销理念和手段,以“建立、维护和加强与社会的长期政治关系,以实现相关政治角色和政治组织的目的”。⑧政治营销的第一步是市场细分,即把社会民众分为不同部分(群体),便于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⑨根据市场细分结果,政治营销者确定主要的消费者群体,锁定营销对象,打造最能打动营销对象的主题,以推销其政治产品,获取相应群体的政治支持。 民进党之所以在成立后十多年就取得政权,其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它追求权力和推销其政治产品时,比其政治对手更自觉地运用了市场细分理论,较为精准地锁定其营销对象。首先,民进党把台湾民众按族群划分为“本省人”和“外省人”、“台湾人”和“中国人”等。⑩通过炒作族群政治和族群矛盾,把其政治营销对象锁定为“本省人”和“台湾人”。在民进党看来,“本省人”和“台湾人”是占台湾地区人口多数的族群,只要能够在这部分台湾民众中成功推销其政治主张,就等于把民进党推销给了整个台湾地区。其次,根据经济地位,民进党把台湾地区的中产阶级锁定为营销对象。这些中产阶级包括中小企业主和知识分子,在人口上占有绝对优势,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再次,根据地域标准,民进党把台湾南部县市锁定为票仓。通过利用南北方的发展差异,甚至采用传谣、耳语、小道消息、“台湾人出头天”、“福佬沙文主义”等等手段,民进党努力煽动南方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使其支持民进党,而形成其南台湾“基本盘”。 民进党的上述策略在2000年和2004年“大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清楚地揭示了南北投票行为的差异性,形成典型的‘北蓝南绿’的政治地域格局。从浊水溪北岸的彰化县往南,陈水扁在9个县市的得票率都是第一,且均在40%以上,在台南县更高达53.8%。陈水扁在南部9县市的总得票数(包括连江、马祖与澎湖)为2,237,899万张,9县市的得票贡献率为44.9%。(11)民进党在南部占有较大优势的同时,在北部的得票率与“泛蓝”阵营的得票率差异较小,因此陈水扁在“相对多数”选举制度下以39.3%的得票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其取胜的关键在南台湾,形成了其“基本盘”。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进一步强化南北对立,在所谓“南北平衡”的口号下,采取“遏北扬南”的战略,有意将台湾经济、文化建设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以获取南部选民的更大支持。(12)2004年“大选”,陈水扁的得票率上升为50.11%,其中南部9县市得票贡献率为43.4%,(13)南台湾的“基本盘”地位得到巩固。 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大选”中,虽然民进党“基本盘”因选情影响受到稍微冲击,但南部选民仍然显示出强烈的政党认同倾向,“选党不选人”,成为民进党的“铁票”,(14)民进党“基本盘”的总体稳定性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因此,民进党通过锁定营销对象,形成并巩固其“基本盘”的营销策略是成功的,“基本盘”体现出民进党的实力所在。 二、隐形宣传说服和争取中间选民 政治营销是媒体政治时代(15)政治传播转型的结果,是传统政治宣传的华丽变身。政治传播者逐渐把自身的“政治宣传者”角色转变为“政治营销者”角色,把政治传播活动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变为以受众中心,从心理上祛除了政治传播的强制性,增强了说服性,并注重受众的认同性。这样,政治传播者不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赤裸裸的宣传和灌输,而是更多地通过各种营销手段进行政治观念和主张从形式到内容的隐形宣传。一般来说,现代政治营销的隐形宣传包括采用政治新闻、政治广告、政治主题的包装等基本形式。从政治传播的心理机制上来看,政治营销的隐形宣传可以增强政治传播的效果,变“我(政治传播者)要你(受众)相信这是正确的”为“我(政治消费者)相信这是正确的”,从而隐去了政治传播的真实利益导向,即把表面上以政治传播者为利益导向转变为表面上以受众为利益导向。就像在市场销售上一样,一个推销员想推销产品,最好的方式是把该产品说成是顾客的生活需求,而不是销售者的利益需求。因此,政治营销正是通过这种以“顾客是上帝”的市场营销原理,把民众当做政治市场上的“上帝”,说服民众“购买”政治营销者的政治产品,即支持政治营销者的政治立场和公共政策。从政党选战的实际情况来看,政治营销的隐形宣传主要是针对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是“对任何政党都没有特定立场的选民”,他们“既不靠左,也不靠右”,(16)但他们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是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的,甚至在政党“基本盘”势均力敌的状态下会决定选举结果。所以,政党往往通过隐形宣传,在选战中说服和争取中间选民,以获取尽可能多的选票。 在台湾地区,“蓝绿营基本盘一般固定不变,但选票开出以后,常常会出现与基本盘比例不相符合的结果,这就是中间选民转了向,造成巨大的‘板块移动’。因此,国民党与民进党都意识得到,要在一对一的‘总统’选举对决中取胜,要斩获超过半数的选民支持,要争取的不是蓝或绿营的基本盘,而是处在中间的两成选民。谁能获得中间选民的青睐,谁就能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笃定胜出。”(17) 2000年之前,民进党在其实力迅速增长的时期,充分利用政治营销的隐形宣传手段,说服中间选民支持其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民进党成立之初,由于民进党并不掌握充分的媒体资源,不可能像国民党那样以政治宣传的形式完成政治传播。于是,民进党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媒体环境,努力通过制造新闻,比如街头暴力运动、抗议示威和游行等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并博得不少民众的同情和支持。20世纪90年代,民进党通过参与台湾地区各种类型的选举,进行选举营销,进一步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特别是2000年“大选”期间,陈水扁聘请“广告鬼才”范可钦推出了最具杀伤力和最具代表性的“平安篇”和“铁汉柔情篇”政治广告。在“平安篇”这则政治广告中,民进党把陈水扁打造成“台湾之子”,以“台湾平安”为主打诉求,塑造了“贫苦”、“奋斗”、“清廉”的政治形象,“表达”出台湾基层民众的“心声”,使他们产生共鸣,吸引他们的选票。(18) 民进党“执政”之后,利用执政资源和执政优势进行政治置入性营销,扩大其政治主张、政治路线、政治势力的市场占有率。正如国民党人士邱毅指出,民进党“执政”时期,政治置入性行销最为严重,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从谈话性的“大话新闻”到民视的“亲戚不计较”都有,并首创把置入性行销渗透到戏剧节目,通过置入性政治营销对台湾民众进行“政治洗脑”,(19)从而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 同时,民进党在政治主题上,提出“走新中间路线”,努力采用“民主化”和“本土化”政治诉求包装其权力欲望和“台独”意识形态,长期炒作“台湾主体意识”,操作“台湾VS.中国”、“爱台VS.卖台”、“本土VS.外来”的二元对立选战主轴,把“3·19枪击案”耳语成“陈扁帮台湾人民挡子弹”,借此煽动悲情、鼓动民粹,(20)成功地把其追求权力所需要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其“基本盘”和中间选民的诉求。这样,民进党不但通过“民主化”和“本土化”成功说服了一部分“本省人”成为其基本盘,而且通过炒作“台湾主体性”,吸引了更多“本省”和“外省”中间选民的支持,扩大了其选战实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大选”中,民进党不但稳操其“基本盘”,而且拿下了当时处于“北蓝南绿”对峙中间地带、中间选民较多的台中县,(21)显示了民进党通过隐形宣传说服和争取中间选民的成效。 三、建构职业化竞选团队弥补组织力量不足 媒介政治时代,政治组织或政治人物必须依靠职业化的政治传播专家,才能实现他们的政治愿望。这些职业化的政治传播专家,要么是政治组织内部的新闻机构、新闻秘书、新闻官、新闻发言人,要么是政治组织外部的媒介顾问、民意测验机构、政治公关公司和游说机构等政治竞选团队。(22)特别是在政治竞选中,候选人必须建立强大的竞选团队,“候选人必须保证竞选团队的名单上出现一些头牌顾问的名字,否则将很难得到选民的认真对待。”(23)于是,职业化的竞选团队在政治选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工作核心就是推销政治组织及其政治人物,辅助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获取竞选胜利。 在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民进党是首先运用竞选团队辅助选战的政党。受其前身“党外势力”的影响,民进党成立之后,积极参与台湾地区各市县选举,党内各派系也都逐渐认同选举总路线。为了选举胜利,民进党极为重视辅选机制的建设,强化辅选机能。“在辅选组织上,民进党中央成立了选举对策委员会,全面负责制订选战纲领和文宣主轴,遴选精干选战操盘的人士,成立选战指挥中心和助选团。在地方上由县市党部主导成立助选组织。”“在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时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陈文茜推出了‘酷哥辣妹助选团’。在竞选的最后一周,民进党中央展开‘决胜大行动’车队大游行,”并组成了“历史上最美丽的助选团”。(24) 在1996年之后的历次“总统”大选中,民进党均有整齐的竞选团队。以2004年陈水扁竞选连任为例,陈水扁成立了一个组织严密,富有效率的竞选团队。其中,“总统府秘书长”邱义仁任指挥官,负责选举战略的制定并掌控选举节奏;“行政院长”游锡堃负责执行陈水扁的政策及选举资源的分配工作;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负责协调内部分歧,整合内部意见;“总统府秘书”马永成直接秉承陈水扁的意志,是陈对外关系的窗口;“总统府秘书”林锦昌是陈水扁的文旦,负责撰写重要文稿与选战口号、基调;陈水扁的亲信与子弟兵罗文嘉是选举的具体推动者;企业界人士黄维生是陈水扁的大掌柜,负责选举时的资金调度。如此有组织、运行有序的阵营为陈水扁的“总统”竞选提供了强大的后盾。(25) 民进党建构职业化的竞选团队,一方面是因应媒体政治时代政治选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弥补了民进党组织力量不足的缺陷。建构职业化的竞选团队,由政治精英对选举进行导演与设计,对候选人进行形象定位,使政治诉求不能有明显的瑕疵,避免犯愚蠢性错误,并通过操盘手左右风评和公共舆论,成功地把陈水扁推销给台湾选民。比如,民进党颇有成效的选举造势活动,就是由职业化的竞选团队负责策划和实施,使民进党获取了大量政治资源和台湾民众的政治支持。如果没有职业化的竞选团队,民进党很难在组织力量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提高其政治知名度,并两度击败国民党而成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因此,正是民进党职业化的竞选团队,弥补了其政党组织力量的不足,成功地推销了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从而增强了民进党的政治实力。 四、“包装政治”取代“实质政治”满足选民“新政”愿景 形象包装是政治营销的关键步骤之一,也是媒体政治时代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只有在民众中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没有良好动人的政治形象,很难在民众中获得支持,也就很难获得或巩固政治权力。事实上,在现代媒体立体化发展的时代,借助电视、互联网视频等图文媒体,“包装政治”已经取代了“实质政治”而成为政治过程的核心。特别是在西方式的政治竞选活动中,“候选人取胜不再是依靠政治经验和治国智慧,而是‘形象制胜’”。“形象制胜”已经成为现代政党和政治人物获取竞选胜利,提升政治实力的重要法宝。“这使政治过程趋向于‘表演化’发展,而非着重考虑和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只要给公众留下一下好印象,是否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则属于次要,能力好不如形象好。”(26) 在民进党实力增长的过程中,熟练把握和运用“包装政治”,满足选民的“新政”愿景,增强了民进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比如,民进党把其“反商”形象包装成“替穷人奋斗”,把其“街头暴力”形象包装成“为正义斗争”,把其“台独”形象包装成“走中间路线”等等。更重要的是,民进党通过包装,鲜明地表演出了其“被迫害、民主、本土和清廉”的政治形象,助力其历次选战。 早在“美丽岛事件”后的“增额立委”选举时,“被迫害”形象就已经开始被党外势力加以包装和利用,使“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以“代夫出征”为名,在竞选时用悲情的眼泪换来了许多选票,高票当选“增额立委”。“陈水扁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推着妻子吴淑珍的轮椅竞选,把吴在一次选举的意外事故说成是政治事件,吴的受迫害形象为陈水扁拉来了不少的同情票,尤其是一些妇女选票。”(27)。 民进党成立之初,“为了凸显自身的存在,争取民众的认知、同情和支持,开拓社会基础,”民进党采取了反体制的斗争路线。“由于热衷于街头政治、群众运动和强烈的反体制色彩,早期民进党给人一种‘暴力党’和‘激进党’的政治形象。”(28)进入20世纪90年代,岛内政治转型的逐渐深入,使民进党通过选举路线实现政治目标的期望变成现实。这样,民进党调整了形象定位,开始包装自身“民主、改革、理性”的新形象,成为国民党的新型反对党,纳入到台湾政治体制之内。 同时,民进党还从整体上打造自己的本土形象和清廉形象。毕竟,民进党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本省人”,即使开始有一些“外省人”,最后也在包装本土形象的过程中使他们被迫离开。在民进党清廉形象的包装方面,把党的清廉形象与其领袖的清廉形象进行捆绑销售,即主要通过塑造陈水扁的清廉形象来塑造民进党的清廉形象。在台湾地区2000年“大选”中,“陈水扁以台南贫苦农家子弟出身为切入点,以‘台湾之子’自诩,把自己包装成来自民间下层,最爱台湾,能够维护台湾民众利益的‘骄子’。攻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是公子哥,好讲排场,不知民间疾苦。同时,民进党不遗余力地以党产不清、党库通‘国库’、金权结合、与黑道挂钩、治安混乱等来攻击国民党贪污、腐化、颟顸无能。”(29)民进党及陈水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极力妖魔化国民党,精心包装自己“本土”和“清廉”政治形象的做法,收到了很大效果,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综上所述,民进党通过政治营销手段形成并巩固了其“基本盘”,说服和争取了中间选民,弥补了组织力量的不足,“满足”了选民的“新政”愿景,从而连续两次获得了台湾地区的“执政”地位,实现了民进党政治实力的增长。 然而,政治营销毕竟只是一种推销政治产品和获取选战胜利的工具,民进党能够利用,国民党也能够利用。民进党实力的上升固然有赖于它比国民党更早更自觉地运用了政治营销工具,但后来国民党也学会并掌握了这一工具,且于2008年卷土重来,2012年连续“执政”。比如,国民党通过锁定营销对象开拓南部选民,一度进入到民进党的传统票仓,缩小了民进党的势力范围;(30)国民党运用政治广告和政治主题的转换等隐形宣传,策略性地收起“统一”大旗,坚持两岸政策上的“不统、不独、不武”主张,成功地吸引了大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国民党同样建立了强有力的竞选团队,充分发挥其组织力量和政治大佬的影响力;国民党推出了善于演讲、风格清新、政治清廉的马英九作为其“总统”候选人,重新包装起“民主”、“本土”、“清廉”的“新国民党”形象,并利用陈水扁及民进党高层的“贪腐”把“陈水扁由原来的‘人气天王’变成了选举的‘票房毒药’”,(31)最终削弱了民进党的政治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决定政党生命力的关键并不在于政治营销的“工具”效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容否认的是,民进党的成立与成长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使“台湾逐步实现了从威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民主政治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步”。(32)民进党通过政治营销也推销了诸多较好的政治产品,比如要求民主选举,要求保障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要求保护台湾弱势群体的利益,号召人民“爱台湾”,反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等。 但是,民进党在成长过程中,展现出的许多“负面基因”,包括其反商、暴力、街头运动、“台独”等“政治包袱”本来与民主的价值(自由、平等、正义、宽容、进步)相背离,与台湾民主的发展方向和进步要求相冲突,压得民进党本应有“发展瓶颈”,但民进党利用政治营销掩盖了其“负面基因”,摆脱掉了“政治包袱”对其成长的不利影响,使其从成立到“执政”的短短十四年间迅速壮大,并连续两次成为“执政党”。 退一步讲,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民进党利用政治营销掩盖其“负面基因”,摆脱其“政治包袱”,增强政党实力也无可非议。但其不择手段地兜售“伪劣产品”,把陈水扁包装成“台湾之子”,把“台独党”、“江湖党”(33)转换成“民主正义的化身”,以达到单纯为获取权力而获取权力的目的,则与民主政治的价值相背离,严重伤害了台湾民主的品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民主的“异化”。就像不良商家把“伪劣产品”或“水货”包装成“正品”、“行货”进行销售,只为获取利润而不顾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一样不可取。 比如,在锁定营销对象并形成其基本盘的过程中,民进党主要是利用南部选民教育水平低下、“政治无知”、社会经济结构弱点、乡土意识、对国民党的不满、“恐共”意识和南北矛盾,采用地下电台、恶质民粹、传谣、耳语、桩脚、抹黑等手段宣传“台湾人出头天”、“福佬沙文主义”,扩大南北对立和族群矛盾,以“买票”、“宗族人情”、“走透透”、“博感情”等方式获取南部选民的非理性支持。(34)但事实证明,民进党的执政并没有使南台湾民众的生活质量因选举而向上提升,反而差距愈来愈大。(35)在隐形宣传方面,民进党一方面攻击国民党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宣传,硬性灌输意识形态,一方面又利用政治广告和置入性营销包装“台湾主体意识”,标榜自己是民主的化身,“台湾人”的代表,实际上仍然是对选民进行“政治洗脑”,向选民灌输“台独”意识形态。而竞选团队只不过是民进党用来导演群众大戏和操弄民意的选举机器,以策划和实施各种“悲情”、“正义”、“民主”的表演,利用媒体上演一场场的闹剧。最后就看谁的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唱的热闹,吸引眼球,谁就能获取更多选票。民众只是充当群众演员,是被欺骗的对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进党不顾台湾人民的真实利益而把陈水扁包装成“台湾之子”,但结果证明陈水扁只不过是“台湾之耻”。(36)陈水扁及民进党高层的贪腐、黑金政治,不折不扣地把民进党宣扬为“新政”愿景的“伪劣产品”昭示于天下。可以说,在政治营销的作用下,台湾民主简化成了选举,(37)选举简化成了选票,选票简化成了“拉票”,民主正义简化成了“拉票”正义,民主的权力转移变成了单纯的竞选团队比拼,“人民当家作主”的期待变成了人民只是群众演员。 总之,从民进党的实力消长可以看出,过度依赖政治营销只能导致台湾民主的“异化”,导致民主价值的边缘化。民进党不择手段推销其“伪劣产品”,单纯为追求权力而追求权力的政治行为,与正义无关,与民主的价值无关。其采用“有人支持——我正义——争取更多人支持——我更加正义”的循环论证挟持了“人民的选择”,只是以“人民的选择”来证明民进党推销“伪劣产品”的“正当性”,是一种恶质的民粹主义。事实证明,所谓的“民主游戏”不是简单的“人民当家作主”,所谓“人民的选择”只是政治精英操控的结果,“人民也有可能犯错误”,(38)民进党的“执政”并非台湾人民的神圣福音。相反,通过不择手段的政治营销制造悲情、仇恨和族群分裂,制造“蓝绿”对垒,非理性地“反共”、“反中”的假民主,只能导致台湾社会更加动荡;坚持“台独”意识形态和分裂国家的民进党只是台湾民主“饮鸩止渴”的药引,背离了台湾人民期待中的民主愿景。可惜的是,商品营销中的“伪劣产品”还可以退货,而政治营销中的“伪劣产品”不能“退货”。不择手段的政治营销在台湾民主游戏中的作用越大,离“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正义就会越来越远,台湾民主的“异化”程度就会越来越深。 ①余克礼,石勇:《化异求同,培植共同价值认同,携手推进民族复兴》,《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②刘国深:《台湾政治概论》,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③余克礼,石勇:《化异求同,培植共同价值认同,携手推进民族复兴》,《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④李兵:《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⑤黄嘉树:《台湾选举纵横谈》,《两岸关系》2002年4月。 ⑥黄嘉树:《大棋局》,中国评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⑦Stephan C.M.Henneberg,"Understanding Political Marketing",in Nicholas J.O'Shaughnessy and Stephan C.M.Henneberg,The Idea of Political Marketing,(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2),p103. ⑧Stephan C.M.Henneberg,“Understanding Political Marketing”,in Nicholas J.O'Shaughnessy and Stephan C.M.Henneberg,The Idea of Political Marketing,(Westport,Connecticut and London:Praeger,2002),p103. ⑨[美]布鲁斯·埃·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张哲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第10页。 ⑩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1)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2000年中国民国总统选举”和“2004年中国民国总统选举”的选票统计资料,并根据两次“大选”中南部“基本盘”得票总数分别占陈水扁两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得票总数的比率,计算出南部“基本盘”的得票贡献率。 (12)王建民:《台“大选”活动中的“南北问题”》,人民网http://tw.people.com.cn/GB/14811/14869/2097386.html. (13)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2000年中国民国总统选举”和“2004年中国民国总统选举”的选票统计资料,并根据两次“大选”中南部“基本盘”得票总数分别占陈水扁两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得票总数的比率,计算出南部“基本盘”的得票贡献率。 (14)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40页。 (15)Neil Washbouren,"Mediating Politics:Newspapers,Radio,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Open University Press,2010),p1. (16)张华:《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 (17)严泉:《中间选民与台湾选举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台湾研究》2012年第4期。 (18)阿扁的超级化妆师范可钦用广告打动五百万张选票,凤凰网http://tw.ifeng.com/special/jingxuanguanggao/detail_2011_10/16/9890369_0.shtml. (19)邱毅:《民进党首创政治置入媒体是“政治洗脑”》,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0/12-29/2753667.shtml. (20)张华:《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 (21)谢郁,曾润梅,赵会可,吴宜:《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 (22)Jay G.Blumler and Dennis Kavanagh,"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Influences and Features,in Denis McQuail,"Mass Communication:II",Sage Publication,2007,pp46-48. (23)[美]布鲁斯·埃·纽曼:《营销总统:选战中的政治营销》,张哲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第10页。 (24)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40页。 (25)王建民:《陈水扁竞选连任“战略战术”之分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3/Apr/304439.htm. (26)刘文科,张文静:《第三代政治传播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10月。 (27)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40页。 (28)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40页。 (29)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第134-135页,第135页、第138页、第140页。 (30)《台媒:台南部已非铁票仓,民进党方面唇焦舌敝》,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7-27/3213657.shtml. (31)陈星:《民进党结构和行为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32)余克礼,石勇:《化异求同,培植共同价值认同,携手推进民族复兴》,《台湾研究》2012年第3期。 (33)《民进党在台湾20年:从楼起到楼倾》,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200610/1009_25_15706_3.shtml. (34)谢郁,曾润梅,赵会可,吴宜:《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 (35)《台大学教授:南北台湾社会经济差距愈来愈大》,中国台湾网http://www.taiwan.cn/xwzx/tw/twcj/200612/t20061223_332372.htm. (36)《民进党在台湾20年:从楼起到楼倾》,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200610/1009_25_15706_3.shtml. (37)许开轶:《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38)黄嘉树:《大棋局》,中国评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标签:陈水扁论文; 台海时事论文; 台湾地区选举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台湾媒体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形象包装论文; 台湾民进党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国民党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