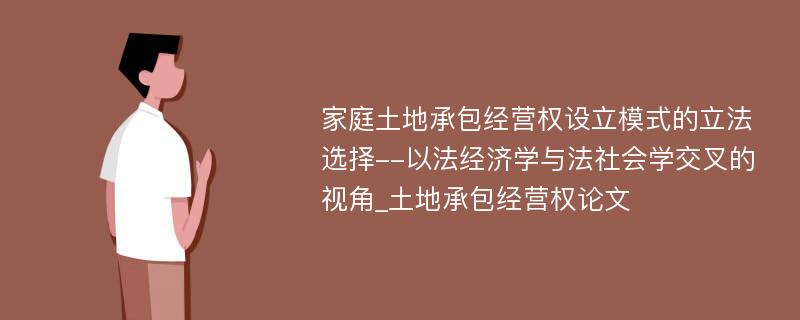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立法选择——以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交叉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营权论文,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土地承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1-0136-08
一、引言:问题与争议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将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下简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规定为“合同生效设立”,第49条将经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规定为“登记设立”。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规定为“登记设立”,学者并无异议,故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对于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规定为“合同生效设立”,部分学者表示支持,但也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我国《物权法》第127条沿袭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综观我国《物权法》艰难的立法历程,不难发现,《物权法》的沿袭做法并不意味着学者之间的分歧已经消除,而仅仅是急于出台《物权法》的无奈之举。那么,我国未来农地立法在该问题上应该如何抉择?
针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问题,“支持派”学者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成员权密切联系,且农地承包合同是以公开方式订立的,已起到了如同登记那样的公示效果,故无登记的必要;① 而“反对派”学者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制度既可以借助登记的程序功能使其权利内容获得公众的认可来增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公信力,② 又可以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设立模式相衔接。③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也都存在考虑不周的地方。“支持派”的观点虽然比较切合中国农村的现状,具有法律实施的亲和力,但即使以公开方式订立农地承包合同,果真起到了他们所言的公示效果,也只具备了“合同生效设立”这种设立模式立法选择的必要条件,并不因此具备了如此选择的充分条件。因此,此种建议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确如“反对派”所言,“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确实能与不动产的登记设立模式在逻辑上保持一致。此外,当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生在“陌生”的当事人之间时,“登记设立”的公示效力远非“合同生效设立”所能比拟的。然而,这种建议忽视了对农地法律制度的适用语境的考量,似乎有过于超前立法的嫌疑,其实施效果令人怀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在权衡两者之间的公示效果及实施成本的基础上作出,而这种权衡必须考量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具体适用语境。
二、何种设立模式更具有公示效果:登记设立抑或合同生效设立
(一)对潜在受让人产生公示效果:不动产物权设立模式的实然效果
依经济学原理,交易往往可以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若要真正实现不动产物权的交易,潜在的交易当事人除了具有交易意愿外,权利的潜在受让方还应能充分获取不动产物权权属状况的相关信息,以便判断这种交易能否使其利益最大化。然而,在市民社会不动产物权的交易中,“陌生”的双方当事人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即“物权的受让方对权属的了解,处于弱势地位,而物权的出让方则处于优势地位”。④ 因此,“权利的受让人为防止不测的损害之故,在任何交易里,均非详细地调查真正的权利人,以确定权利的实像,方开始交易不可,如斯一来,受让人为确定权利关系的实像裹足不前,对于现代活泼迅速交易行为自然会受到严重影响”。⑤ 为了扭转当事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促进交易的正常进行,现代民法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设立模式,以便潜在的受让方能以较低的信息成本获取标的物的权属状况,据此判断能否交易。另外,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即使交易双方据以成交的设立登记有误,只要受让方不知道或不应知道其实际权属状况,法律也赋予了其物权变动的效力,此即为物权登记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设立所具有的公示效果虽然面向的是市民社会的全体成员,但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往往只为潜在的受让方所知晓。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了解交易标的物权属状况的内在冲动,而对于压根就没有受让意愿的人来说,并无白白花费一笔费用去查阅对己并无用处的相关登记的必要。因此,登记的公示效果仅对不动产物权潜在的受让方具有实然意义。由此可见,法律所欲创设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模式只需对潜在的受让人产生公示效果即可,而无须“自作多情”地对市民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公示效果。但是基于市民社会交易的开放性的考量,其所有成员均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不动产物权的受让人,这就使得立法者不得不选择能够对市民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公示效果的登记制度作为其设立模式。如果我们能具体圈定某种不动产物权潜在受让人大致范围的话,只要某种设立模式能够对其潜在的受让人产生公示效果,即可判断这种设立模式具有公示效果,而无须“过高”地要求其对市民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公示效果。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不动产物权,其设立模式自然也不例外。
(二)乡土社会的内部成员: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潜在受让人
一如前述,判断某种设立模式是否具备公示效果,首先必须圈定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潜在受让人的大致范围。笔者认为,经济利益最大化和人情网络的羁绊是影响家庭承包地流转对象选择的两个主要因素。
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与乡土社会的外部成员相比,其内部成员更容易成为家庭承包地流转的潜在受让人。其理由为:其一,以“细碎化”为特征的“均田制”的实施,每个农户一般(并不尽然)可供给的农地数量较少,⑥ 使得意愿供地的农户一般会预期到缺少跨地区流入的受让人,也就缺乏到乡土社会之外去寻求流转对象的动机。另外,缘于乡土社会天然封闭性的考量,对于外部成员而言,搜寻内部意愿供地的潜在出让方的成本较高。这样就很难形成乡土社会内外成员意愿供给和意愿受让信息之间的“对接”,也就不具备流转的可能性。反观乡土社会内部,其成员之间对彼此的个性、品行、脾气、家境以及以前的履约情况都非常了解,达到知根知底的程度,其搜集信息成本极低。这也为乡土社会成员在其内部搜寻潜在的交易方提供了便利。因此,出于搜集成本之考虑,意愿供给与受让农地的农户将家庭承包地的流转对象的选择范围往往锁定在乡土社会内部。⑦ 其二,在耕作技术近乎同质的情况下,基于耕种所获得的净收益的多少几乎完全取决于成本支出的高低。与内部成员相比,外来人员若耕种乡土社会成员流转的承包地,平添了耕种地与居住地之间的往返成本(包括往返时间和费用的支出)。特别是,由于“强龙不压地头蛇”,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与内部成员相比,外来人员在抢灌抢排方面又增加了几分艰辛与酸楚。此外,内部成员接受的承包地,或许可以与其承包地连成一片,在劳动力禀赋未达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并取得更为可观的规模效益。因此,与外来人员相比,乡土社会的内部成员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具有更高的价值评价。依法律经济学原理,将资源转移到价值评价更高的用途上,能带来更多的合作剩余,也使得交易双方在分享合作剩余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和余地,其交易成功的可能性更大。⑧ 因此,对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具有更高价值评价的内部成员更容易成为家庭承包地的受让方。其三,由于人情网络的约束和重复博弈等原因,与外部成员相比较,内部成员之间更不愿意轻言违约,⑨ 降低了违约的可能性,减少了惩罚成本支出的可能。即使存在少之又少的违约,其受害方往往既可以借助重复博弈的机会进行私人惩罚,还可以借助乡土社会内在惩罚机制进行集体惩罚,⑩ 从而减少对法律惩罚的依赖,(11) 降低了惩罚成本的支出。而对于外部成员的违约,受害方往往只能诉诸法律惩罚,此种违约惩罚成本极高。基于上述几点经济原因,就一般意义而言,对于意愿承包地流转的农户选择内部成员作为其流转对象,无疑是最佳的。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选择流转对象的唯一标准,农户选择农地流转对象的行为还受到乡土社会特有的人情网络的约束和羁绊。(12) 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里,由于农业生产中的土地不能移、乡村生活中的聚族而居和家庭伦理中的血缘亲情等原因,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情网络。乡土社会人情网络的约束使其成员之间的土地流转不能仅仅基于利益的计算,还须进行人情的考量,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法理论关于市民社会“经济人”的预设前提,呈现出些许“伦理人”的特征。据此可知,农地流转的潜在出让人为了加固相当倚重的“人情链条”,在内部成员愿意支付相同甚至略低“对价”的情况下,即使心有不愿也不得不选择其作为农地流转的受让人,以免“人情链条”出现裂痕甚或断裂。也就是说,在人情网络的羁绊和约束下,乡土社会内部成员一般享有农地流转的“优先受让权”。
综上所述,基于经济利益和人情约束的双重考量,家庭承包地流转的受让方绝大多数为乡土社会的内部成员。这一点也为相关的统计数据所证实。根据调查,即使是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江苏省,77%的农地流转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13%的流转发生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仅有10%的流转是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的。(13)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的10%市场化的农地流转还包括很大一部分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若单就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论,市场化的比例将会远远低于这个比例。另外,根据访谈得知,在少量市场化的家庭承包地流转中,其受让人也未必全为乡土社会的外部成员。即使其部分受让人为外部成员,其交易往往也是通过乡土社会内部“关系人”的中介作用而达成的,因此,由于乡土社会内部成员的勾连作用,他们已成为熟悉乡土社会内部情况的“陌生人”。
(三)“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更具有公示效果:基于农地法律的适用语境之考量
众所周知,我国农地承包合同往往是通过集会方式由发包方与承包方公开订立的。在乡土社会特有的制度语境下,这种农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方式实然地发生了面向农地流转的潜在受让人,具备了物权设立模式所必须具备的公示效果。其理由为:其一,“乡土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共享的优越性,由于人际关系无间隙、稀薄和简单,某些信息的传播会有着‘长波’效应,能够以较小的失真度而迅速传遍生活圈子”。(14) 这就使得各户集会分配的家庭承包地的相关情况能够通过乡党邻里的话语、村头巷尾的议论迅速而又准确地传遍全村。其二,由于“历世不移的结果,人(指乡土社会成员)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15) 致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成员对村落里的每块土地的四至都“了然于胸”。因此,熟人社会信息传播的“长波”效应及内部成员心中的“活地图”之间的“合力”无形中使集会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起到了“公示”的效果。
那么,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数的逐年增加,这种“公示”效果是否会减弱甚至消失呢?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农村的实际状况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此种担心纯属多余。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进城打工的农民达到1139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其中举家进城打工的农民2430万人,占全部进城打工农民总数的21.3%。(16) 由此统计可知,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不足农村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举家外出打工的农民更是不到农村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何况,农村土地的承包是以“户”为基本单位进行的,故每户只要有一个“613871部队”(17) 的留守人员,就意味着此户外出人员实际上也能通过家庭的留守人员知晓村里每块土地的四至及权属状况,其“公示”效果并未因其外出而减弱。另外,对于举家外出打工人员,只要还心系土地,他们也能利用原先建立的人情关系网络了解到与之切身利益相关的土地的四至及权属状况,其“公示”效果依然存在。即使存在少之又少的“单门独户”并“毫无人缘”的举家外出人员,他们无法了解与之相关土地的四至及权属状况,也不影响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依合同生效而设立的制度规定的实施效果。因为,法律上的“知道”有时只是依据一定的制度背景推定当事人“应该知道”而不管当事人实际是否知道。也就是说,此种“应然性的知道”并不完全等同于当事人“实然性的知道”。诚如英国法学家杰弗里·塞缪尔所言,法律并不是在“真正的事实”基础上运作,而是在一种“虚拟事实”基础上运作。这种“虚拟事实”的构造取决于客观事实被如何观察,有哪些特定方面被强调,而哪些方面又被忽略。(18)
一如前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因登记而设立,具有面向市民社会全体成员的“公示效果”,而合同生效设立仅对乡土社会内部成员具有“公示效果”。就应然层面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设立模式似乎更具有“公示效果”。然而,物权设立模式的公示效果仅对潜在的受让方具有法律意义,而对无心交易的其他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由于合同生效设立模式能够对土地流转的潜在受让方产生公示效果,因此,在此等意义层面上,合同生效设立模式并不比登记设立模式的公示效果差。就实然层面而言,若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状况相一致时,绝大多数农民,要么由于欠缺物权法知识,没有查阅登记簿的意识,要么基于人际信任的考量,没有查阅登记簿的动机。据此可知,绝大多数潜在的受让人并没有因登记设立增加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状况的了解。更有甚者,若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状况不相一致,当乡土社会内部成员查阅登记簿并据此进行了交易,法律又不能依据登记簿的相关记载赋予此种交易有效性时,便造成了“查了也白查”的尴尬局面。因为,据此交易的受让方,虽然因“生于斯、长于斯”而实际知道或应该知道交易标的物权属的真实状况,但并不具备赋予其交易公信力的法律基础。由此可见,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设立制度不仅不能起到明晰法律关系的作用,有时反而徒增法律适用的混乱。因此,登记设立的公示效果反而不如合同生效设立模式所起到的公示效果。
三、何种设立模式具有较低的实施成本:登记设立抑或合同生效设立
依科斯定律,“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19) 由此可见,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立法取舍,不能仅仅局限于权衡两者的公示效果,还应权衡两者对交易成本的影响。
依法律经济学原理,根据交易的不同阶段可将交易成本分为三种形式:搜寻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及执行成本。(20) 在熟人社会的语境下,无论登记设立,抑或合同生效设立,对讨价还价成本的影响几近相同,而影响之不同主要表现在搜寻成本及执行成本两方面。
交易的搜寻成本主要包括两方面,即搜寻潜在的交易相对方的成本和查询标的物权属状况的成本。由于乡土社会成员彼此之间非常了解,达到了知根知底的程度,故无论选择上述哪一种设立模式,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方交易人都会非常便利地利用这些地方性的知识,选择乡土社会的内部成员作为潜在的交易相对方,其搜寻潜在的交易方所需的成本几近相同。但是,在上述两种不同设立模式的制度背景下,搜寻意欲流转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状况所需的成本却相差甚远。基于市民社会的交易双方处于“陌生”状态之考量,我国《物权法》第9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登记设立模式。确实如周林彬教授所言,“如果无需登记,当事人则免除了信息公布的成本负担。从微观上看,似乎交易者的信息成本降低了,但从宏观上看,由于缺少了‘登记’这种权属状况的外观,交易者为了了解标的物的权属,需要花费更多的信息收集费用。因此,减少的信息公布成本又以信息收集成本的形式回到了交易者身上。而且,物权主体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对权属有比潜在交易者更为清楚的了解,也就是说,信息的公布成本小于收集成本。……‘登记’的公示制度都将交易必须的信息成本,交由公布环节承担,从整体上降低了信息成本,也就降低了物权变动的成本”(21)。然而,在乡土社会里,基于“熟人社会”的语境,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设立的信息公布成本是否低于信息收集成本,不无疑问。
如前所述,由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封闭性,由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交易双方对于乡土社会每块土地的四至情况都了然于胸,也由于乡土社会特有的居住方式决定了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共享性,(22) 乡土社会成员之间对于彼此承包地的权属状况都知根知底。即使有少数常年举家在外的务工人员对其不甚了解,也能很轻易地通过原本建立的人情网络了解到意欲交易的家庭承包地的权属状况,其搜集信息成本极低。故我国立法若选择“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其交易双方不仅不要承担信息公布成本,而且搜寻成本极低。
那么,与“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所产生的极低的搜集信息成本相比,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所产生的信息公布成本如何呢?若采纳某些学者的建议,在乡镇一级建立土地登记派出所,(23) 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统计,截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乡镇43735个,若按每个乡镇的土地登记派出所至少应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来计算,全国将净增从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工作人员43735人之多,即使不算土地登记派出所硬件设施的成本支出,按每人每年的工资、办公经费加总3万元计算,全国每年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的工资、办公经费的总开支就达13.1205亿之多。另外,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登记属民事设权登记,应秉承自愿登记原则,土地登记派出所既无上门登记的义务,也无强制登记的权力,故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登记应由农民主动上门登记。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统计,截至2000年底,我国共有2.41487亿个农户,即使对其实行免费登记,每户登记的旅途往返费用按5元计算,总共需花费12.07435亿元。更何况,家庭承包地调整后须重新设立登记。我国现行法律虽将农用耕地的承包期限规定为30年,但由于农地承载着社会保障功能,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会根据农户人口变化的情况适时地调整其承包地。据国务院发展中心对浙江、江西、河南、吉林四省的调查,在1989年~1993年的5年期间内,四省每年平均调整次数为0.13次。(24) 若按此计算,农民每年平均用于登记设立的费用达1.57亿之多。因此,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登记设立模式,每年用于公布信息的成本就达14.7亿之多,这还不包括土地登记派出所的硬件设施的开支和潜在受让人查阅登记簿的往返成本。而且可以预计,未来的几十年,随着我国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及承包地的进一步细碎化,这种设立模式的信息公布成本还会大幅度增加。(25) 据此可以认为,采用登记设立的信息公布成本远远高于采用合同生效设立的信息搜集成本。
执行成本一般包括监督成本及惩罚违约行为成本两个方面。(26) 一般情况下,无论采用哪种设立模式,交易双方都能利用乡土社会特有的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共享性,及时地监督对方当事人的履约行为,其监督成本并无二致。而在违约行为的惩罚成本方面,两种设立模式却相差甚远。若采用依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并赋予其公信力,交易当事人进行交易及法律维护其安全的依据是交易标的物的真实权属状况。由于交易及法律维护其安全的依据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从而能够得到乡土社会所有成员的心理认可,大大提高交易的履约率,降低了违约行为的惩罚成本支出的可能性。其理由为:其一,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通过对社会文化心理的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当某种行为是以最少的迟疑和最小的努力达到的,这种行为最能为成员个体所愿意接受,其实施成本最低。(27) 其二,即使存在少量“冒乡土社会之大不韪”的违约行为,也会受到乡土社会内在惩罚机制的严惩,降低了对法律惩罚的需求,从而减少了惩罚成本。因为,违反了所有成员心理认可的约定的失信行为意味着很可能失去所有成员的信任,失去所有层面的重复博弈的可能性。(28) 若采纳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并赋予其法律上的公信力,那么,交易当事人进行交易及法律维护其交易安全的依据是土地登记簿记载的交易标的物的权属状况,即使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的权属状况不相符合,只要交易人在交易时“不知情”或“不应知情”亦应如此,这是登记设立模式应具有公信力所使然。(29) 若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的权属状况相一致,其违约行为的惩罚成本与依合同生效设立模式背景下的惩罚成本几近相同。然而,一旦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的状况发生了偏差,就会大大增加惩罚成本。惩罚成本的增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方一旦发现其交易标的物的真实权属状况与登记簿记载的情况不相一致,常常因不懂深奥的物权法及出于生活经验而心存狐疑,影响其履约的积极性,履约率会因此而降低,从而增加了违约惩罚成本支出的可能性;其二,一旦交易当事人因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与真实状况发生偏差而违约,法律为维护交易的安全,依据登记簿记载的权属状况惩罚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时,由于其依据与民间习惯的内在机理相差甚远,其惩罚行为可能会受到强有力的抵抗而陡增成本。(30) 据此可以认为,在执行成本方面,登记设立模式高于合同生效设立模式。
综上所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虽然与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在讨价还价成本方面大致相同,但在搜寻成本及执行成本两方面均超过了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
四、合同生效设立: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应然选择
一如前述,基于乡土农村熟人社会的制度语境,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生效设立模式实际所产生的公示效果超过了登记设立模式所产生的公示效果,并且其制度的实施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登记设立模式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就构成了我国将来的立法仍然应选择合同生效设立模式作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的充要条件。
除此以外,“路径依赖”是我国将来立法应选择合同生效设立作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又一理由。法律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使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制度化,因此,法律“是以它的‘老规矩’‘萧规曹随’来满足社会多数人对可预期生活的需求”。(31)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32) 当然,法律并不是一味地墨守成规,只不过是,法律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其调整对象,即“只有当社会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生活的实际规则都发生变化时,法律的变化才‘千呼万唤始出来’”。(33) 据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已确立了“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在农村特有的制度语境未发生根本性嬗变的情况下,不宜改“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为“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否则会徒增法律适用混乱之烦恼。
最后,农地法律适用需要农地法律适用之对象的配合,也是选择“合同生效设立”设立模式的理由之一。法律制度固然可以制约着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并由此而发生一定的嬗变,但行为主体进行过长期的博弈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固有的行为模式也无时不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和构建。缘于此,我们在选择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时,完全有必要考量此制度的规范对象即农民的固有的行为模式对该制度构建的影响。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在实践中,农民不但不会主动去登记,(34) 而且对地方政府发放的各种土地确权证书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因此,出于经济理性之考虑和传统惯习之做法,绝大多数农民没有登记的意识和动机。鉴于此,不符合乡土社会民间习惯内在机理的登记设立的制度设计即使出台,也会被村民“束之高阁”的,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需要的产物”。(35)
综上所述,权衡各方面因素,我国未来农地立法仍应沿袭现行做法,继续采用“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作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合同生效设立”永远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模式的较佳选择。一旦中国农村特有的制约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家庭承包地的流转具有了开放性,我国农地立法就应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变更为“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
五、余论:农地法律制度设计的法律逻辑与生活理由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并不完全属于西方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制度。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制度是以市民社会“陌生人”为预设前提而进行设计的。然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适用语境为熟人社会,其制度设计有时不能不受到熟人社会特质的影响而呈现出与西方用益物权制度不同的面向。一如前述,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设立”的设立模式,不仅公示效果不如“合同生效设立”的设立模式,而且还徒增家庭承包地的流转成本。其个中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熟人社会特质的影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制度的设计乃至所有的农地法律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根据西方法律逻辑(如不动产物权登记要件主义)任意地裁剪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当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农地法律制度的设计应注重对生活理由的关注,而不应拘泥于西方法律逻辑。
然而,这并不意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设计完全不能借鉴西方法律逻辑尤其是西方物权法的内在机理。问题的关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设计如何实现生活理由与法律逻辑的协调和融合。立法者应在凸显生活理由的基础上并兼容法律逻辑来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达到“超越法律”的理想状态。诚如苏力先生所说,“社会生活并不服从逻辑,相反,逻辑倒是常常要服从社会生活”。(36)
注释:
①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
② 孙宪忠:《物权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③ 韩芳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47页。
④ 周林彬:《物权法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
⑤ 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第246页。
⑥ 截至2004年底,我国耕地只有18.37亿亩,人均耕地仅1.41亩。然而,根据十省实地调研,黑龙江省的人均耕地高达7.7亩。参见袁铖《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一个产权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⑦ 刘克春、朱红根:《农户要素禀赋、交易费用与农户农地供给行为关系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75~179页。
⑧ [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6~68页。
⑨ 林聚任:《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⑩ [美]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4~224页。
(11) 桑木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0~151页。
(12) 钟涨宝、王萍:《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中国农地观察》2003年第6期,第55~64页。
(13) 杜培华、欧名豪:《农地土地流转行为因素的实证研究》,《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8年第1期,第54页。
(14) 刘雷:《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9页。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括号里的注系笔者所加。
(16) 袁铖:《二元结构转型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页。
(17) 此为农村用来戏称留守的儿童、妇女及老人。61指儿童、38指妇女、71指老人。
(18) 方孔:《实在法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5~26页。
(19)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文版译者序言》,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20) [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第77页。
(21) 周林彬:《物权法新论》,第246页。
(22)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0页。
(23) 孙宪忠:《物权法》,第271页。
(24) 姚洋:《集体决策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演化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第12页。
(25) 按目前城市化速度,每年只能吸收800万人口。至2030年之前,我国每年新增人口为1000万。由此可以预见,至2030年,我国仍将有农村人口8亿多,与目前基本持平,甚至略有增加。而且,城市化比例的提高还将征用大批土地,在将来的几十年里,家庭承包地还将进一步“细碎化”。参见《2004土地风暴》,新浪网2004年12月31日,载《南方周末》。
(26) [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第77页。
(27) [美]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于闽梅、陈学晶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28) 桑本谦:《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第38~62页。
(29) 史尚宽:《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50页。
(30) 徐勇:《“法律下乡”:乡土社会的双重法律制度整合》,《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第25页。
(31)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32)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33)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第155页。
(34) 此处登记指行政登记,而非民事登记。即使是免费的、主动登门的行政登记,农民尚且如此,费时费钱的民事登记,农民的行为偏好可想而知。
(35) [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36)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