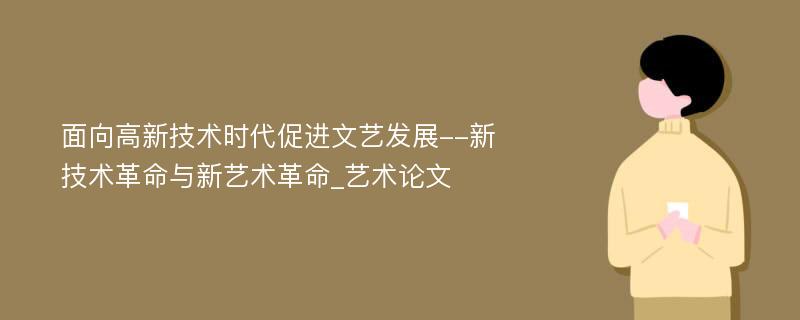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 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新技术革命与新艺术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艺术论文,科技时代论文,新技术革命论文,新艺术论文,高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性交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在19世纪,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表现出人类认识宇宙的两个概念,一是运动,二是进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理解为各种“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视生命形态为生物体与环境间动态演进的结果。运动和进化两个概念为19世纪人类理解世界建立了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都力图证明历史内涵即参与历史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抗、逆反、替代的过程。这种力的相互运动形成了事物的终极形态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艺术家对人生的感悟之中。诸多现实主义大师都写过关于年轻主人公与生存环境艰难斗争最终达成美好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譬如《浮士德》,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进化”的史诗。
进入20世纪后,物理学转向对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研究。“基本粒子”和“结构”这两个概念支撑着技术。物质世界的状貌被认为是由一些微小的元素按一定结构模型组合起来的。科学家们力图精确客观地描述这些元素和模型,于是出现了技术与情感、意志对抗的现象。美国学者格里芬讽刺这一时期的科学倾向时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了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注:〔美〕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第204页。)这种基本粒子加结构的技术观念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感,他们力图保卫自己那块自由想象的天地,天是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一种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其真实意图在于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观念对感性生命的压制。
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技术与艺术的对抗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了格里芬称赞的“后现代科学”时代。量子力学和微电子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学说形成了生物工程技术,这两种高新技术使后现代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杰姆逊曾写道:“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所取代,这一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注:〔美〕F·杰姆逊(F.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7,第293页。)后现代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感悟方式的革命,也带来了艺术的革命。
支撑着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观念是基因和代码。生物工程技术把生命当作隐含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螺旋式构成的23个碱基对的表征,人的生命也是这些遗传密码代代相传的结果。电子信息技术将一种非物质化的代码交流方式赋予人类社会,以计算机网络的形式把人们由身体或物品的交流带入代码的交流之中。基因和代码的观念使当代社会文化从物品到理解方式上认可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生物工程可以制作虚拟的生命(如转基因生物),网络则让人们进行虚拟交流(如“网恋”)。所以,杰姆逊讨论的后现代“幻象”、鲍德里亚描述的“仿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界定的“非物质社会”,其实都源于现代高新技术中的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
以基因学说来理解生命,则我们传统思想中用社会历史因素来界说人的生命表征的做法就必然解体。比如过去的批评家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眯缝眼睛是要表现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生命力的压抑,而按基因学说,这只是安娜家族遗传的一种习性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生物工程技术用嫁接碱基对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在外表上与真实的自然无二,但却是一个人工制作的虚假的真实。非物质社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生物工程技术为人们开启的以代码制作实在幻象的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出的网络产业使后现代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种超越身体和物品的“通讯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造成了人与物质世界距离的远化,让人进入了一个无指涉性的代码世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话语参与权力。网络交流是一种“互动化”的交流,完全不同于麦克鲁汉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交流。大众传媒时代,言说者把他的话语通过阻隔式的交流模式“霸权化”地推向大众。言说者(比如借印刷品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作家)用宣言式话语向芸芸众生发布真理。而网络则彻底推毁了个人话语霸权,同时也消解了宣言式话语,因为网络交流是一种言说者之间互动的、可逆的交流,它排斥一切独语。
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和广播电视作为主要的交流传播形式,固然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为人类获取信息拓展了视界,但这些传播方式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色彩。信息发送者像发布皇家文告一样面对大众,而作为交流一方的接受者只能认可交流对象的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交流体制使他们能够把个人话语推向大众,而大众则被分离成孤独的个体,被动地承受着印刷品和电视画面的统治。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的神话,因为互联网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听演讲”的场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言说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交流,都不会被剥夺话语权。而且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即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都是在与交流对象相互间进行着一种话语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方面先在话语权力的取消意味着宣言式话语中包含的整体性深度模式的消遁,另一方面互动把交流行为本身的价值凸现出来,解构了宣言式话语对所指的意识整合,于是先前充斥媒体的宣言式话语被网络聚会中的游戏话语取代。我们在网上见到的大都是一些无指涉对象的“巧言”,网络交流的快乐在于交流行为本身,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游戏。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交流方式的互动游戏特点肯定将改变印刷出版时代以载道缘情为原则的文学范式。互动游戏的文学是消解了指涉物的能指游戏,它以“策略”的态度对待言词,并在其中体验交流的快感。所以,在我们告别印刷品主导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即将告别背负着人类解放之重任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正如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教授阿兰·芬基尔克罗所言:“我们都是以前的进步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怀旧含有某种反动的意味;不过这里所说的怀旧是对现代本身的怀念,是对印刷品的怀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文化摆脱束缚的怀念。”(注:〔法〕R·舍普编:《技术帝国》,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197页。)
互动游戏的文学在摆脱叙述真理的重负时,允许每一个交流者成为言说者。印刷品文学时代,作为交流一方的读者,其言说地位受到压制。而文学成为互动游戏后,读者作为言说者才真正出场。法国Ecole Nat-ionale d' Art de Cergy教授Fred Forest认为,技术时代的空间是一种“建立在通讯交流媒介上的‘遭遇性’空间”,他预言:“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使大家相互接触’,这样一种作为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标志的关键观念,将变成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观念……”(注:〔法〕马可·第亚尼(Marco Diani)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第161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这样的:几十个不知名的作者,一大堆新奇绝妙的话语。
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都观察到一种现象:当代生活中,文化成了渗透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种物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我们发现,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消费的是技术物品的功能,而高新技术时代里人们除消费物品功能外还消费技术行为。这就使得消费活动染上了一层非物质的精神色彩。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对R.K·默顿在1942年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加以补充修正,为科技活动制订了五个原则:公开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科技活动给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确的数据和机械程序,它同样也使人体会到一种美学激情。高新技术把每一个当代人卷入技术行为之中,它让每个人体会到了一种艺术的韵味。
因此,在高新技术左右生活的后现代文化中,出现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现象。费瑟斯通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造成了艺术与实际生活界限的模糊,知识分子力图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符号和影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审美内涵(注:〔英〕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文版,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第96-98页。)。在当代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艺术终结的感叹,但我们又鲜明地感到日常生活更像符号、更多独创性。实际上我们感叹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纯艺术的消亡,而我们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日益靠近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是一种审美“收集”的工作,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收集在纯艺术中以保卫艺术在技术理性、消费文化面前的独立性,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后现代艺术则是在进行着一种审美“散播”的工作,它把审美因素从纯艺术中析离出来分派给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言:“经济与科学的后现代发展导致艺术脉搏与生活现实性强烈一致。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现实中,都直接地体现着某种艺术与创造性的精神。后现代社会是创造性的社会,是创造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成为创造性地、艺术性地从事自己职业活动的人。”(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5页。)我们把艺术走下神坛的现象称作为“审美散播”。审美散播也许意味着纯艺术的消亡,但审美因素被散播到职业活动、生活行为、日常物品的过程又使我们的审美感受更加丰富了。
当然“审美散播”之所以可能与技术将职业艺术家的技艺训练简化也有关系,比如用电脑合成的手段来构图,普通人稍加训练即可掌握。这在技术上为审美散播提供了条件。
我们在这里论述的“互动游戏”、“审美散播”等当代艺术现象,也许不能涵盖新技术革命下的新艺术革命的全部内容,但这些现象可以使我们找到一条艺术的变迁与技术的变迁之间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