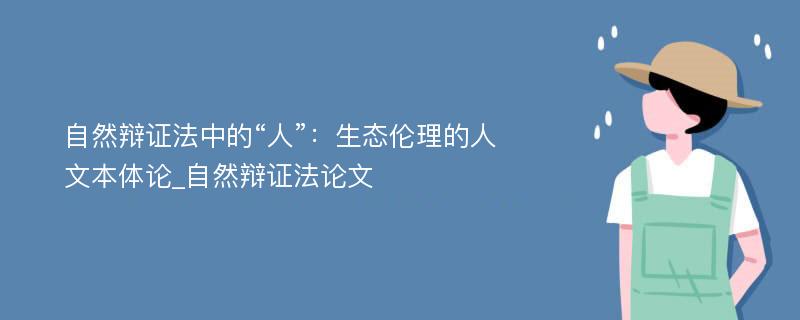
《自然辩证法》的“人”: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伦理学论文,辩证法论文,人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7)02-0005-06
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立,取决于人类是否应该给自然以伦理关怀;而人类是否应该给自然以伦理关怀,又取决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取决于“人究竟是什么”这个古老的人学本体论问题。正如杨通进所说,就生态伦理问题而言,人究竟对哪些存在物负有义务的问题,与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形象设定”和“存在认同”密不可分。换言之,生态伦理学离不开某种人学本体论。[1]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人”作了自然的和历史的考察:从自然维度看,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人的生成就是自然的自我生成,因此,人必须敬重自然之“母”,给自然以伦理关怀;另一方面,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的生成就是对象化活动中的自我生成,因此,为了维持自身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他也必须呵护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给自然以伦理关切。
一、从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到道德走出对人的“固恋”
恩格斯认为,从生命的起源看,所有的生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2] 284。人类也好,非人类也罢,都只是蛋白体在量上的不同组合,都可以还原为蛋白体。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的结构也是基本一致的;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也有同样的体现。“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2] 328因此,无论从人体的结构看,还是从人的基本特征看,人和非人类的生命都是一样的——都具有同质性。
与人和非人类的同质性相对应,在进化论问题上,人的进化和非人类一样,也是自然的自我生成与自我“分化”。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一章的“导言”中,恩格斯继承了19世纪中叶赫胥黎、海克尔、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理论,详细说明了自然界的自我演变、生物的进化和人的产生过程。其中,关于人的生成过程,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人是由最初没有定型的蛋白质通过核和膜的形成而发展为细胞,然后发展到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再由原生生物发展到动物和植物,最后由动物中的古猿发展而成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2] 17这就是说,人的形成,并不是上帝因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捏造,而不过是自然“自组织”的结果,是自然自我分化的产物。
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对自然予以呵护的必要性。自然是人类进行“物料交换”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是人类“必要的存在条件”,因为人作为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其本质契机在于和它置身于其中的外部自然界进行不间断的物料交换,这种物料交换一旦停止,人的生命就会如蛋白质的分解一样而随之消失。在《自然辩证法》第284页的注脚中,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物料交换”对于人作为有机体生命的决定性作用:“在无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破坏了它们,而在有机体的情形下,物料交换是它们必要的存在条件。”[2] 284既然物料交换是人类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由于物料交换的对象是自然、物料交换的空间也是自然,所以,人类要珍惜自身的存在就应该珍惜自然的存在,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像呵护自己的手和脚一样去呵护自然。这是自然界自我进化、自我发展的逻辑,也是自然“自组织”的逻辑。
人的自然性及其与自然进行物料交换的必要性,决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对待自然“怎么都行”的方法论的荒谬。自然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物料交换的中介,存在着普遍而广泛的相互联系与交互作用,这种普遍联系与交互作用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除了“绝对的斗争”,还有“和谐的共存”。“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交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据此,恩格斯认为,达尔文把自然界化约为绝对的“生存斗争”、霍布斯把人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人与人之间如狼的斗争”,二者都把自然的“生存斗争”加以扩大化或绝对化了,都是对自然界物料交换的普遍性及其有机性的反动。“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乱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生存斗争’这样一个干瘪而片面的词句中,这是完全幼稚的。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2] 291因此,如果我们的哲学都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一味地怂恿人们战天斗地,那么,早晚有一天,不仅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将一点一点地消失,而且地球也将和月球一样,成为“冰冷的”和“死寂的”球体。
恩格斯从自然维度对人的本质的解读,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中世纪神学的人学观认为,人,作为天地之秀、万物之灵,是上帝的唯一代表,是大自然的合法性主宰;所有的非人类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其价值大小完全取决于它能满足人类需要多少及其程度。在恩格斯看来,既然生物学、进化论、地质学等都已经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同质性,那么,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只不过是人类自作多情或一厢情愿的产物,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正如他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写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2] 328
恩格斯在自然维度上对人的本质的解读,为“生态中心主义”从“是”到“应该”的跨越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大家知道,生态中心主义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例如,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就是根据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和“人不过是一些运动中的物质”来说明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的;奥尔多·利奥波德也是根据“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来佐证他的“大地伦理学”的。既然“人也是由自然分化出来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2] 17-18,因此,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并没有超越于非人类之上的道德特权;非人类和人类一样,理应是道德大家庭中的平等的一员;人作为“道德代理人”与非人类作为“道德顾客”之间并没有价值地位上的高低。正是根据人的自然性这一事实,恩格斯逻辑地提出了人类应该呵护自然的伦理学主张。例如,在《古代人的自然观》一章中,针对毕达哥拉斯为了庆祝他发现“毕达哥拉斯定理”而举行的“百牛大祭”,恩格斯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牛的同情:“这是精神(知识)的快乐和高兴——然而牛付出了代价。”[2] 38
二、从人是“劳动的产物”到呵护“大地”的逻辑必然性
恩格斯不仅把人理解为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把人理解为劳动的存在物。在恩格斯看来,尽管从生理结构看,人与自然是同质的,但是,人的生活决不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吃喝自然”或“享受对象的生活”;人,作为地球上唯一的“思维的花朵”,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如果只见人的自在性而不见人的自为性,只见人的物质性而不见人的精神性,就势必在人学问题上陷入“客观的自然主义”的窠臼。
那么,恩格斯视野中的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劳动”。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章中,恩格斯对此给予了系统性的阐发。他认为,劳动是人自我塑造、自我确证和自我生成的唯一方式,是使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而成为真正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的过程。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或用自己的本能的方式引起自然界的简单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2] 304正是劳动在人与非人类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人日益摆脱动物的规定而朝向人的本性的方向生成。动物虽然也进行“生产”,但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近乎为零。只有人才做到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通过劳动,人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改变了其周围环境的面貌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它们活动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
相对于语言、意识而言,劳动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人的生成既是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个历史的过程。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是劳动的作品,劳动对人之为人的形成与完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古猿采集水果,到手和脚的区分(直立行走),到语言与工具的出现,再到脑(意识)的形成,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2] 299透过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尽管人的本质问题,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是哲学界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语言的,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意识的,但是,人的本质从发生学层面上看只能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为意识和语言的产生,并最终通过头和手的结合,创造出非人类所不能创造的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帕格尼尼的音乐等。
恩格斯在历史维度上对人的解读,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提供了“本体论证明”。依照恩格斯的逻辑,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而劳动又是人作为主体作用于自然作为客体的活动,那么,由于主客体的“场依存性”,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人类非但不能对自然恣意妄为,反而更应该悉心保护自然,并把对自然的伦理关怀作为人类主体性得以发挥的要件。他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 295这里的“人”是主体的人,这里的“自然”是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是“自然界”创造了人本身的人类学延伸;只有以自然界作为人的劳动对象,人们才能够透过它“直观自身”,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因此,人类呵护自然的价值诉求不过是人的劳动本性在伦理学领域中的自然拓展,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的逻辑的展开。
恩格斯在历史维度上对人的解读,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科学的方法论,即“有所不为”的方法论。由于劳动决不是人类单纯而抽象的精神性活动,而是客观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劳动的客观实在性构成了劳动的“外在尺度”,这个外在尺度总是以“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被控制的力量”等制约着人类的劳动实践,造成“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还首先由未被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并且经常得多的是恰恰相反的结果,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2] 19。因此,劳动决不能消灭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只能服从它、利用它,表现为“理性的狡猾”,而不是感性的胡为。“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2] 303这里,“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就含有理性地对待“理性”、科学地对待“科学”、谨慎地服从自然规律、在自然的承受力之内从事对自然的改造的蕴含;也说明了只有服从自然规律的劳动才是真正的人的劳动,也只有真正的人的劳动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劳动。“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305
三、从《自然辩证法》的“人”到生态伦理学本体论的超越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既是蛋白体的人,又是劳动的人;既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它对于克服生态伦理学在“人学本体论”上的形而上学对立,使之从“分殊”走向“统一”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就非人类中心主义而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本体论基础便是人与自然的同质性。为了论证人与非人类的价值平等性、诉求人类“顺从自然”、“敬畏生命”的伦理实践,非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纯的自然性,理解为人与非人类的同质性。例如,通过使地球“尘埃”化,内在价值论者罗尔斯顿把自为的人“渺小”到了纯粹自在的“物质”层次;通过遗传学证明,动物解放论者辛格把人与黑猩猩的智商相提并论;通过拟人化的文学手法,刘湘溶教授把人的理性与长颈鹿的脖子、飞鸟的翅膀同日而语等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客观自然主义”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全正确的。它只看到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人的劳动性,只看到人的自在性而忽视了人的自为性。它似乎忘记了正是人的自然性与生物性决定了人必须劳动,必须以自然界作为“物料交换”的对象来获取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进而决定了人把自然作为“道德顾客”的伦理应然性,决定了人类在生态伦理实践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虽然“紧紧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是,在它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话”。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只是“抽象的人”、“感性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不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人学空场”,使得非人类中心主义蜕变成了“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和“无主体的伦理拓展主义”,蜕变成了价值论上的客观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肉体性、自然性出发呼吁人类呵护自然,这个逻辑起点是对的,但它不明白“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3]。这个“人”就是劳动的人、“经过思考的”和“有计划的”人、现实的人、既改造自然又尊重自然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充当“大自然最敏感的神经”,并自觉承担起呵护自然的伦理重任。
其次,就人类中心主义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一个重要的本体论基础便是人的“理性”。为了论证人类相对于非人类的价值优越性,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纯的理性的存在,理解为自为性的精神性存在。例如康德就把理性、精神看成是人的本质,认为正是理性决定人必须首先保持自己和自己的种类,决定了人只能把自己视为“目的”。黑格尔也认为,由于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因此只有人才能超出他的自然的存在。既然人是唯一能思考的“狡猾”的动物,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人给自然立法”而不是“自然给人立法”。人类中心主义把理性看成人的本质,这是部分合理的,但是它不应该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甚至把理性的作用加以神化或绝对化,因为根据恩格斯的理解,理性、意识、思想等归根结底都只是劳动的产物,是人在劳动过程中对外部自然的内化与积淀。“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 正是劳动的“物质行动”,即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接触,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为人成为“有目的的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提供了精神准备。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规定劳动,而不是以劳动规定理性;把理性“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而不是把人看作是有理性的个人,这只能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是“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理解“人”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本体论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正是这种名为理性实质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本体论,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上的“三个一切”和方法论上的“人类沙文主义”与“种族灭绝主义”。“劳动是这样一种因素,它既是实现由猿到人的转变,使人从动物界脱离开来和提升出来的根本因素,又是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成为人而存在的根本因素。”[5] 这个“根本因素”既包括人的物质性,又包括人的精神性;既包括人的自然性,又包括人的自为性;既包括人的受动性,又包括人的能动性。只有以这样的人学本体论为基础,我们的生态伦理学才能既照顾到自然的“神性”,又照顾到人的“人性”;既能指导人们科学地改造自然,又能提醒人们理性地保护自然,在“改造”与“保护”、“发展”与“环境”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
总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研究出发,到生态伦理学价值论的逻辑回归,整个“行程”说理充分、推理严密,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人学本体论基础。在环境持续恶化、生态危机加剧的今天,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重新解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