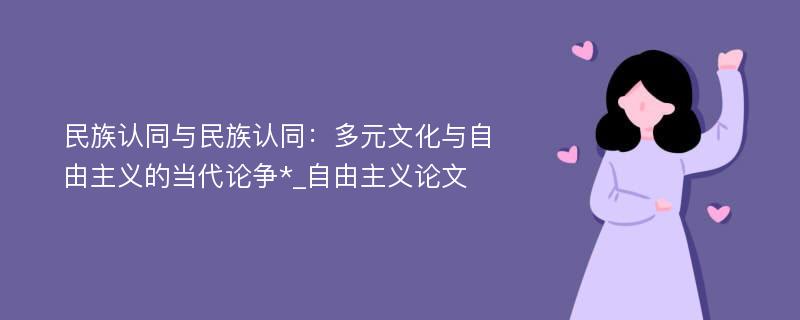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族群论文,当代论文,身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化互动的增强以及社会自身能力的提高,族群意识、文化认同与少数权利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西方多族群国家不得不面临日益增长的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和文化主张的压力。这些恰是多元文化主义所要思考和解决的。在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政治论争中,多元文化主义在族群身份、族群认同、族群差异与族群文化权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与策略,而这一切均是围绕族群与国家尤其是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一、个殊还是普遍: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
族群身份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与60年代的新移民运动,使少数族群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迅速提升,对族群身份的吁求也愈加强烈,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如果说少数族群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主体的话,那么,族群身份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动力。①
少数族群基于特定的族群与族群意识而形成的文化成员身份,就是族群身份。②这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者最为关注的一个概念,而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关系问题更是当代西方理论论争的焦点。③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对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弱势群体以及移民群体,要承认他们的差异性、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的平等参政权和社会经济权,在此基础上,解构传统的话语权力,对正统和主流的话语体系进行修正。换言之,承认、平等和解构是族群身份的三大价值取向。
西方多族群国家在处理族群与国家关系时,多年来大体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统一模式”,也被称为“盎格鲁化”模式,④政府对少数族群和移民群体实行同化政策,使他们逐渐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并融入主流文化。⑤第二种是“熔炉模式”,也称“同化模式”,政府在不干预的情况下,使不同的文化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如果可能,主流文化可以起主导作用。⑥第三种是“马赛克模式”,也称“文化多元模式”,主张不同文化和平共处,平等存在,保留各自的特色。⑦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第一种模式绝对是不能接受的。第二种模式承认文化共存,但对各种文化之间是从属还是平等关系,没有明确界定,美国版的“熔炉说”甚至提出要将各种文化溶化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主料的“大锅”里,也是让人难以接受。比较温和的是第三种模式,它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价值,并给予所有社会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
多元文化主义极力倡导“承认”,显然代表着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在他们看来,尽管一些国家历来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价值及与主流文化的差异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充其量只能称其为多元文化社会,却绝不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因为只有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各民族、族群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地位状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的“承认”具有双层含义:既承认族群差异,还要承认差异平等。
在解构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以美国为例,以盎格鲁-撒克逊为核心的白人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主宰着美国的话语霸权,但事实却是:黑人奴隶、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等少数族群,同样也是美国历史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应拥有部分话语权利。因此,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重新解读传统文本,用新的话语理论解构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同时,积极构建亚文化群体的话语体系,以建立族群身份的自信,培育族群身份的自主意识,进而争取社会的承认和平等的话语权。
从承认存在,到追求平等,再到解构霸权,族群身份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与角色。理解族群身份的价值内涵,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
随着族群身份概念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有学者开始担心这一身份可能会冲击传统意义的公民身份。因为“公民身份”强调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活方式的所有人,拥有一致的国家认同和政治信念,承担平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义务,显然具有一种整合的力量,而“族群身份”强调族群差异,关注族群特权,督促族群有意识强化其内在的文化特征,自然会冲击公民身份所内含的公共精神,甚至危及社会团结。
罗伯特·H.威布(Robert H.Wiebe)详细分析了族群身份带来的变化:引发公民身份危机;更改传统的政治主题,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选举如何影响文化差异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差异如何影响选举的问题”;⑧扩展公民身份内涵的同时,也引发社会无序状态,“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公民资格,除非有人来教他——教给他公民的习惯,教给他公民的语言。”⑨
对此,杰夫·斯宾勒(Jeff Spinner-Halev)主张应对各类族群区别对待。一些激进的族群,由于强烈希望拥有与主流文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将主流文化作为竞争对手看待。但一些相对温和的族群,由于各种原因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只是希望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多元社会中的一部分,并不想争取特殊的文化认同。还有一些游离的族群,对政治生活和共同体的事业持冷漠态度,对国家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和期望,他们虽然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不属于优良公民,但至少不会危及其他公民的权益。⑩斯宾勒认为,除了激进的族群外,后两类族群身份都不会对公民身份构成实质的威胁和挑战。(11)
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观点与之相近,他承认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不过他也认为,如果过度强调族群身份,也不排除部分族群放弃主流社会的公民身份,从主流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走向边缘状态的可能,这种“族群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极易导致社会分化。(12)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某一族群身份强调的是语言权或族群代表权,对公民身份就不会构成什么挑战,但如果更多强调的是自治权,就会对公民身份有所冲击,因为前者是让少数族群参与和融入主流社会,而后者则是要族群脱离主流社会,削弱与政治社会的联系。金里卡试图在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中寻找一个和谐的节点,使后者合理地“包容”前者,从而缓解两者间的冲突的努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的。
在关于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的争论中,坚持一元文化的自由主义与坚持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多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倡导自由主义的公民观。按照这一思想,个人权利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起点和归宿,公共权力要保护个人权利,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意味着,国家应对个人的权利不加任何区别地给予平等的保护。这种平等的权力分享将人从群体的归属中拉出来,置于平等的法律呵护之下。正如罗尔斯所说,“政治权力乃是公共的权力,即是说,它是作为集体性实体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按照规则强加在作为个体和作为联合体成员的公民头上的”。(13)
这种主张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在多元主义者看来,这种主张实质意味着基于个人权利的公民身份可以拥有高于族群身份的地位。如此一来,国家完全可以借保护个人权利之名,否定群体的权利。即便是基于保护个人权利的目的对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进行国家干预,也是本着主流文化的一厢情愿。艾丽斯·杨(Iris Marion Young)认为:“族群的需求是不同且多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的单一认同,不能满足族群的多元需求,结果会造成族群间彼此矛盾、紧张、冲突的产生。”(14)菲利克斯·格罗斯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这必然会影响到种族上的少数民族,歧视和迫害政策就会变成‘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意义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15)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提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族群,而非公民个人。自由主义只关注社会生活中公民和国家这两极,却忽视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由多元群体构成的中间地带。在现实政治中,个人往往通过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和社会与国家发生关系。个人既是国家的公民,也是某个特定族群的成员;既拥有公民身份,也拥有族群身份。因此,绝不能将社会简单化约为个人的集合体,否认族群的存在,甚至将公民身份掩盖或抵消族群身份。然而当前的社会现实却是,弱势的族群无时无刻不在主流社会和正统文化的包围和冲击之下,后者内在的“同质化”趋势使这些族群无时无刻不在面临一个两难命运:要么被同化,要么奋起对抗。
为了缓解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差异公民”(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概念。(16)这意味着,政府在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平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认和包容少数族群的身份和权益,赋予其特殊的“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此时的族群身份成为一种与公民身份有所“差异”的独特的公民身份。这种族群身份对于共同体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金里卡所说:“在文化多元的社会中,需要不同的公民权来保护文化共同体免受不必要的解体。”(17)泰勒也赞同差异公民的主张。在他看来,文化族群是构成社会的一个独立的单位,需要承认其独特的认同。平等的承认政治,应该将文化族群的集体目标纳入政治领域,承认族群的特殊性和价值。
既承认公民身份中的公共价值取向,又拥有族群身份的“差异性”,这就是“差异公民”的实质。文化多元主义的“差异公民”以及形成的“差异政治”确实可以为我们思考族群与国家关系提供一个不错的思路。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族群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差异并非是全面的,应仅限于文化差异,族群的自治权也应限于文化自治而止,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而言十分关键。如果走上激进立场,就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
二、一致还是冲突: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中,共同体成员往往拥有多重身份。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不同,因为“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存在,正是在各自的文化和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当代社会的认同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家认同,强调政治上的归属;另一种是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侧重文化上的归属。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前者一直为人们所强调,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族群权利观念对此提出了挑战。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过分强调国家认同,会使少数族群的权益陷入困境。族群认同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国家认同存在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这是下文即将探讨的问题。
一般来说,族群认同与态度、价值观等有密切的关系,涉及个体对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看法,更涉及个体对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类属关系的看法。正如W.伯里所说,族群认同往往通过四种形式进行,即整合、分离、同化、边缘。(19)由于族群与文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族群的发展只有凭藉文化认同,才能自觉且有选择地与其他文化交流,维持自己主体性的地位,反之,若一族群失去了自身文化认同,而任由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对一个族群的发展,将是致命的打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具有同质性。因此,大多数多元文化主义者在谈论族群认同时,就是指族群的文化认同。
当今社会是多元的社会,基于文化认同的族群认同需要各族群相互承认,这是建构自我尊重意识的必要条件,也是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正如泰勒所说,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具有对话特征的,个人的自我认同是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的,族群成员的自我认同是需要其它族群承认的,“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20)
基于以上考虑,如何理解族群认同的性质、构成要素及产生模式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关系着族群的归属与承认及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由于产生模式不同,族群认同的性质也不同,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不尽相同。(21)
一些学者主张“原生模式”(primordialist model)。根据这一模式的观点,族群归属感是族群认同的根基。这种归属感往往来自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或某种共同的信仰等原生的文化因素和情感纽带。共同血缘、语言概念以及宗教感情是族群认同的基本要素。原生论模式主张族群认同应高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没有资格同化或凌驾于族群认同之上;诉求国家认同必须以尊重族群认同为前提。
一些学者则主张“场景模式”(circumstantialist model)。这一模式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和层次性。如巴斯(Frederick Barth)认为,虽然多元社会中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由此引起的族群互动并不必然导致同化现象的产生。一些族群处于一些经常性的互动当中,不仅没有被同化,还可以和平共存。换言之,人们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中转换其语言和族群认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国家可以运用族群认同达到经济、社会、政治目的,同样,族群认同可以借助国家认同实现合作与双赢。为了适应多元社会中的经济环境,一个群体可能强调共享的国家认同作为增强协作的手段,将族群认同视为不同利益和地位群体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
一些持相近立场的学者甚至认为,族群认同具有如此的流动性和情境性,它们终将消失。由于族群认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具有不良功能,就需要在多元社会中实行基于同化目标的政策,族群认同应置于国家认同之下。国家可以为促进特定的文化实践和价值观念以消除族群认同,并将少数群体融入单一文化之中。显然,他们的主张有推销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
无论是原生论所强调的认同的血缘关系,还是场景论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甚至是一些学者提出的人为的建构,都只描述了族群认同部分层面的构成。实质上,只有血缘或文化因素,是不会产生认同的;同样,没有文化的互动与共处,认同也无从谈起。这样一来,国家或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族群精英所进行的动员,就成为维持、强化、削弱甚至消灭族群认同的中介变量。毫无疑问,多元文化主义所强调的上述因素与环节,恰是现代多民族社会处理族群与国家关系时必须关注的重要变量。
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目标,既不是建构个人的文化认同,也不是建构民族的文化认同或国家认同,而是建构所谓的族群认同。(22)对于游离于边缘的少数族群而言,这种基于差异而产生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完美的契合点,以维护多元社会中族群差异与少数权利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正如艾丽斯·杨所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非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两者兼容的。”(23)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族群认同属于文化范畴,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范畴,两者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首先,族群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族群的群体意识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微妙;往往先有政治国家,然后由国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24)换句话说,国家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是后天由国家树立起来的,而不是形成于国家之前。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权威有意识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塑力量,各种局部的、游离的族群认同虽并不先于国家层面的国家认同而存在,但却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有学者所言,“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象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25)其次,国家认同以族群文化认同为根基。对于国家认同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往往强调血缘、语言和地域特征等标识族群特征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能够缩小各族群间的心理距离,增强各族群的亲和性,有效地体现国家一体的观念。这些同样是国家认同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命运相同。日益扩张的全球化不仅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更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威胁族群认同的合理层面。正如萨林斯所说,全球化威胁着族群认同,也威胁着国家认同。(26)
显而易见,为了论证族群差异的合理性,减少少数权利实现的阻力,在论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时,多元文化主义更偏重于强调两者的一致性。但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揭露和挖掘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这些批判者看来,从国家的角度讲,国家的政治统一和认同情感,需要共同的民族性发挥至关重要的合法化作用。(27)这样,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族群特性,使族群文化边缘化。这些因素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从族群的角度讲,每个族群都有独特的权利要求。这些权利要求的实现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治,对少数族群实行制度或法律上的倾斜。一旦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少数族群就会产生背弃感或歧视感,就有可能对国家权威和政府合法性提出质疑。结果只能是,族群认同过度强化,促使族群中心主义产生,进而威胁国家认同。
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28)族群认同固然重要,但它关注的只是个别群体的存在价值。族群权利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个别群体,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同样不能指望少数族群来维护。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必须要上升为一种与基于国家主权的国家认同,才能真正解决少数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29)
三、多元还是一体:族群差异与政治认同
国家应以何种态度对待族群差异,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关系如何,这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自由主义认为,公民身份应以“无差异”的普遍原则对待每一位公民。而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看似公平,实质却在执行“一人一票”的简单多数原则,这一原则可以确保多数人的利益,却会危及少数族群的生存,更对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构成潜在的威胁。
批判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倡导族群差异的合法性,一直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课题。艾丽斯·杨认为,自由主义倡导以相同的标准和原则对待每一个公民,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质是想将社会建构成一个同质同构的公民共同体。(30)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式平等不仅没有削弱族群差异,反而将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推向更为不利的处境。而且,自由主义的“平等参与”实际上是将一个两难选择推给少数族群:要么选择认同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要么选择走向自我抛弃。对这一观点,多数多元文化主义者表示赞同。(31)
马里昂批判了自由主义所谓的政府中立性。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用民族的语言来处理本国的政治和法律事务的。行政和教育体系也是以特定语言和民族利益为优先地位。正如安东尼·阿巴拉斯特所说:“要所有社会能够一代又一代地在抚育孩子和实施教育的整个领域保持中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32)杰夫·斯宾勒也认为,政府往往由某一个特定的文化族群所掌控,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生存的少数族群往往成为弱势文化,甚至沦为备受主流社会歧视的牺牲者。(33)
针对这一现状,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对策是:国家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证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国家不应对少数族群权利备受主流文化侵犯的现状袖手旁观,而应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同时入手,建立少数族群利益表达的渠道,确立维护少数权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不应只扮演消极的角色,而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保障所有公民尤其是少数族群团体中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多元文化态势。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批判了自由主义所谓的文化中立性。自由主义将所有差异都界定在非公共领域,族群文化与宗教信仰一样,不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意义。正如格雷所说,自由主义所谓的“多元”,实质是个人价值观的一个延伸,是一种被稀释了的“个体式”的多元,而文化多元主义恰恰要将这些差异界定于政治领域,并且将“文化的差异当成是政治领域所要处理的素材”。(34)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自由主义表面上仿佛在坚持一种中立的文化观,除了公共领域的权力运作外,在私人领域奉行自由而宽松的文化政策,政府更是以“小政府”和“弱政府”的姿态出现。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对人性的预设、对个体价值的推崇、对公私的界分,无不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价值取向。既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就不可能做到文化中立。(35)
如果认定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是一种特殊主义,那么就有理由将族群的认同与差异归属于公共领域,将族群差异不简单化约为个人差异。因此,必须对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那些由不同族群构成的特殊团体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这些团体的认同,它们就有可能走向同化和消失的危险;而忽略这些团体的差异,它们同样也会被压制甚至边缘化。
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者倡导的“差异公民”概念,就是要强调族群差异的公共性,个人在具有公民身份和权利的同时,也具有族群的身份和权利。(36)此时的自由主义政府不但基于个人立场,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而且为了承认和包容少数族群的特殊认同和需求,还要赋予它们以集体为单位的少数权利。(37)由此看来,在多元文化主义看来,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并不矛盾,承认族群的差异并不会直接威胁国家认同的存在。
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争论,是关于差异政治和少数权利会不会危及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问题。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拥有特殊权利的少数族群为了维持其非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确保其文化特性不受自由主义制度的影响,必然会阻止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运作,但这些族群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同样也妨碍了他们内部的平等。沙切尔(Ayelet Shachar)的研究表明:当政府采取包容政策以减少族群间权力的差异时,反而造成族群内部的权力阶层的形成,某些族群成员因此而易于受到不当的对待。(38)他具体分析了两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指出族群内部之所以有压迫现象发生,主要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只关注族群的整体认同,却忽略甚至牺牲了族群内部分成员的个体经验和认同。(39)
而多数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则认为,族群差异与自由主义理论并不矛盾。金里卡认为,以前人们之所以对少数权利充满戒心,是因为人们认为过分强调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少数权利相对于公民大众而言是不公平的,但现实政治已经证明,包容文化差异、推行差异原则,不仅没有带来不公平,反而带来了少数族群原有不利处境的改善和公平与正义的提升。金里卡告诫人们,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权益,如认同、语言、文化成员身份等,而这些恰恰是多元文化主义所关注的重要因素。(40)
关于族群差异与少数权利问题,当前争议最大的是族群内子女的教育权问题。少数族群内的儿童作为未来的公民,如果其父母的教育倡导族群差异,就有可能影响甚至削弱国家认同。(41)虽然大多数支持文化权利的学者认为,儿童有权选择不同于父母的生活方式,但也有人担心,如果少数族群的父母不让其子女充分暴露在主流文化当中,政府将无所适从。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少数族群对其子女的权利是有限的,族群不能以族群认同为理由阻止其离开。正如盖尔斯敦对两个经典案例的分析。(42)当个人权利和族群权利产生冲突时,前者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包容差异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公共制度,对部分相对弱小的文化社群的某些支持和包容,并不会危及公民身份和国家的认同。(43)
这一争论鲜明地表现了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的微妙关系。忽视或漠视族群差异,以国家认同去消融少数族群的差异,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过分肯定和认可族群差异,如果寻求差异的族群越来越多,社会的稳定与政治的参与就可能受到威胁。(44)文化多元主义为了少数族群的权利与利益,诉诸“族群身份”和“族群差异”,但这些理念所引发的相应的问题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回应显然力不从心。
确保国家与族群间的和谐与稳定是对的,追求各族群间的平等、共存与相互承认也是对的,但这一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做到“多元共存、政治一体”。具体而言,对于多民族国家,族群差异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需要处理好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族群差异与国家认同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
一方面,国家认同是族群差异的精神基础和前提条件,族群差异应该是在国家完整性和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没有国家认同的“差异”缺乏内在的凝聚力。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文化不可能各自处于孤立封闭的状态,它们或基于天然的地理条件,或缘于长期的政治统一和经济生活的共生和互补,或因为现代化国家的高度社会化沟通,而自然地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国家认同和共同价值也以族群差异为前提,国家文化是吸纳和融合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文化,而各种文化只有在一个社会中具有平等和合法的权利,才会自然地对国家产生认同,并融合到国家主流文化中。国内有学者提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原则,(45)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政治抉择。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研究”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公民文化的起源与形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④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4、158~160页。
②(12)威尔·金里卡:《自由主义、社群与文化》,应奇、葛水林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54~171、162页。
③(45)常士訚:《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载《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2期,第117~178、118页。
⑤Madison Grant,The Pashing of the Great Race: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21,pp.107-145.
⑥Robert W.Hodge and Patricia Hdge,Occupational Assimilation as a Competitive Proces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71,1965,pp.249-264.
⑦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p.120-145.
⑧⑨罗伯特·H.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李振广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1、202页。
⑩(11)(41)(43)Jeff Spinner-Halev,Cultural Pluralism and Partial Citizenshi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65-68,p.68,p.77,p.83.
(13)刘东、黄平:《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4页。
(14)Iris Marion Young,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in Ronald Beiner ed.,Theorizing Citizenship,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386-408.
(15)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王建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16)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Citizenship in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Issues,Contexts,Concepts,in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ed.,Citizenship in Diverse Socie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1.
(17)贝斯·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8)常士訚:《多元文化与民族共治——凯米利卡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载《天津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13页。
(19)John W Berry,Ethnic Identity in Plural Societies,in Herbert W.Harris.Howard C.Blue&Ezra E.H.Griffith ed.,Racialand Ethnic Identity: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Expression,New York:Routlege,1995,pp.20-38.
(20)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21)Clarry Lay & Maykel Verkuyten,Ethnic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 to Personal Self-Esteem:A comparison of Canadian-bom and Forein-born Chinese Adolescents,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3,1999
(22)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载陈明主编《原道》(第三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23)(36)Iris Marion Young,Polity and Difference: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1994,pp.386-408.
(24)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99页。
(25)Tan Chee-Beng,Ethnic Ident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Some Examples From Malaysia,in Identities,Vol.6,No.4,2000,p.441.
(26)Sahlins,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m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Modem History,Vol.65,1988,pp.1-25.
(27)奇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28)吴燕和:《族群意识·认同·文化》,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44页。
(29)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页。
(30)(31)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06.
(32)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9页。
(33)Jeff Spinner,The Boundaries of Citizenship,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10.
(34)John Gray,Enlightenment’s Wake,New York:Routledge,1995,pp.136-138.
(35)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60-64.
(37)(40)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Citizenship in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Issues,Contexts,Concepts,in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 ed.,Citizenship in Diverse Socie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 1-41,pp.3-5.
(38)(44)Ronald Beiner,Why Citizenship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Ronald Beiner,ed.,Theorizing Citizenship,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p.22-25,p.3.
(39)Ayelet Shachar,On Citizenship and Multicultural Vulnerability,in Political Theory,Vol.28,No.65,2000,pp.68-69.
(42)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佟德志、庞金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1。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化认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