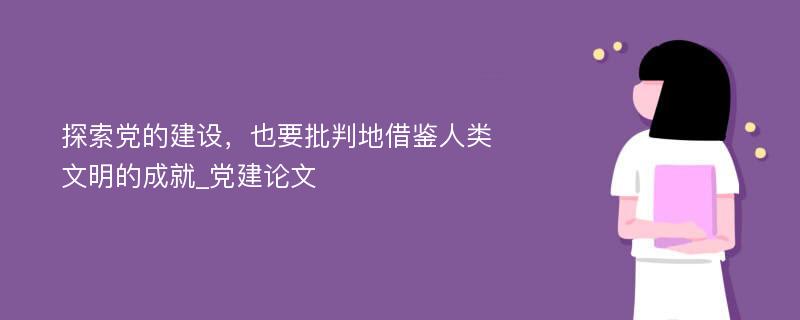
探索党的建设也要批判地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要论文,党的建设论文,人类文明论文,成果论文,批判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发展,就必须善于学习、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时代特征,就是它有宽广的眼界,善于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鼓励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党的十五大再次突出强调了这一思想。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应当有这样一种眼界和高度。因为毫无疑问,所谓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即包括人类在发展经济、文化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应包括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创造的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政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党作为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工具,其活动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又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党的运作也是可以吸取他党教训、借鉴他党经验的。
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领袖对这个问题早已作过明确而肯定的论述。例如,周恩来在一次论及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1〕刘少奇在1956 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之后回家当平民,艾森豪威尔当了总司令、总统,退职后又去当大学校长等作为例子,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2〕。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像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实质上是承认,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合理的东西。领袖们的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态度。
政党和政党体制之间可以比较、借鉴,是因为政党活动除了各有自己的特点外,还遵循共同的规律。比较、借鉴的目的,就是要探索和把握这些规律。例如,政党都毫无例外是要干预政治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但是,干预的效果如何,要看其干预的途径、方式是否科学。西方政党对政治的干预,往往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在保证国家政权按自身规律运作的前提下进行。所以,尽管政党的影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甚至经常引起民众的反感和抗议,但总体上看,其干预没有超出政党活动的范围,因而西方民众很少把由此产生的弊端归结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上。以苏联为代表的政党领导体制(我们也长期受这种体制的影响)则不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通常都是十分明显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党组织总是被作为一个权力组织不科学地外加在政府的运作之上,甚至用对政党的要求来规范政权的活动,结果使政府的权力来源、授权关系都发生了混乱,造成了长期党政关系不顺,实际上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研究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无疑能够大大促进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遗憾的是,5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之间也可以相互比较和借鉴的重要思想,在后来我们党的建设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从50年代末以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当然此外还有大量复杂的客观原因),我们对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缺乏具体分析,很多都简单地采取了批判、排斥、否定的态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执政党建设理论是我们的任务。而要发展,就一定要有比较,有借鉴。我们讲要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包括要有开放的观念和务实的态度,要有大胆开拓进取、又面对各种风险岿然不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需要我们清除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封闭的、狭隘的和排他性的观念。否则,党的建设就很难正确地接受他人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往往会重复别人的错误。
把不同政党、不同政党体制之间的比较、借鉴引入党的建设研究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课题。必须有正确的原则作指导,才能保证其正确方向。为此,特别需要强调以下四点。
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党的建设领域开展政党之间的比较研究,必须进一步摆脱“左”的观念的束缚。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敢谈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比较和借鉴,似乎一谈借鉴,就是要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就是主张多党制、议会政治。这种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以致直到今天,都不能说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其实,政党活动的相互借鉴,正像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西方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基督教民主党与其他世俗政党之间,都有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一些本来属于一党发明的理论、观念、主张,常常逐渐为另一些党所吸收和利用。诸如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福利国家的政策,国家和平变革的道路,党内民主制约机制等等,都曾经为一党所独有,如今却成为许多政党的共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应当看到,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连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无”之分的共性的东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性质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共性的东西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那就等于缩小了自己的理论空间,封闭了自己,让出了本不该让出的阵地,这是很可惜的。在这方面,过去的沉痛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
其次,绝对不能以学习、借鉴为名,照搬照抄别国党的模式。在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对本国政治和社会进程有影响的政党,或长期存在、有相当稳定性的政党体制,都是在不断适应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尽管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弊端,有的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却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对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然而,这绝不等于说,可以把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模式全盘搬用到我们国家来。一种政党和政党体制之所以长期为该国人民所容忍和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对于本国国情的适应。离开了国情,它就很难生存。例如,西方国家特有的社会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产生了两党制和多党制。但是,如果把这套政党体制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那就只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动乱,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实践已经表明,任何照搬照抄别国政党或政党体制模式的做法,都是不会成功的。邓小平很早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这一点:“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3 〕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深刻结论。
再次,政党比较要贯彻尊重别国党、别国人民历史选择的原则。要借鉴,就要有比较。在政党比较中,有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是需要澄清的。因为,我们进行政党比较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此外,我们用来进行政党比较、用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根本思想武器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不应当有任何含糊。所谓“批判地吸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要通过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中有数,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因此,它和过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开展大批判、开展意识形态论战是根本不同的。历史早已证明,对别国党、别国人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除了造成国际、党际关系紧张之外,不会取得任何积极效果。所以,就像邓小平再三强调的那样,党不论大小,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这是研究、比较政党和政党体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最后,要把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作为政党比较和借鉴的落脚点。为我所用,这是我们倡导进行政党比较的目的所在。离开了这一点,研究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当前,在我们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确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但是,放眼世界,遇到问题的并不只是我们党,也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久经考验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已经发生了危机。这说明,政党政治从总体上看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变革阶段既充满困难,又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只要适应这种变革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建设必定能够得到加强。开展对各类政党的比较研究,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把这一研究的根牢牢地扎在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上,这个课题就肯定会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课题。
党的十五大已经在用更加宽广的眼界看待党的建设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例如,十五大报告不再简单地把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归结为只是思想问题,而强调标本兼治,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把制度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强调党的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等。这里面都反映出对以往(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吸取。尤其重要的是,党的十五大倡导的探索精神,为更加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在党的建设中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沿着党的十五大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把探讨引向深入,是党建理论工作者的庄严责任。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
〔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7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