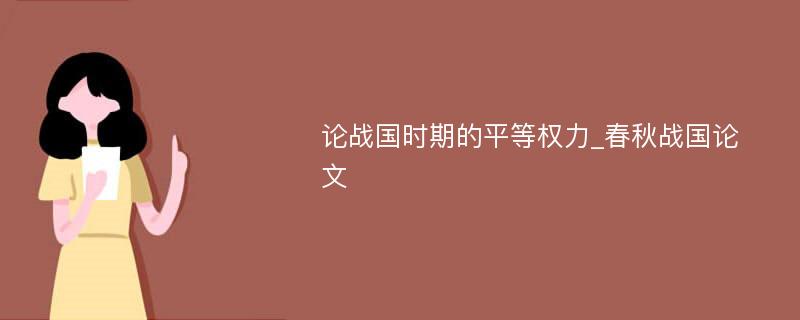
论战国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国相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先秦时代社会政治的演变过程中,由各级宗法贵族统治进而到分层次的中央与地方官僚统治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战国时期,从周代卿权到战国相权的变迁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关键所在。战国时期列国相权强大,当时有不同类型的相,主要是,1.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布衣之相,2.作为旧传统旧制度遗存的贵族之相,3.衔负外交使命的特殊之相。这几类相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君主统治工具的布衣之相。这类相,其与春秋时期卿的重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出身寒微,不会对君权造成威胁。这类相即孟子所说的能够“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良臣”(注:《孟子·告子下》。),虽然孟子从民本主义的观点出发不赞成这样的臣,但“良臣”只对君主负责并为富国强兵做出贡献,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在迅速变革的战国时期,相权的发展演变颇富时代特色,它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变化的面貌。
一、相的历史发展
春秋时人曾将相的起源追溯到很早,鲁国的太史克谓舜受天下拥戴,“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注:《左传》文公十八年。),把辅佐舜的“八恺”、“八元”称为“十六相”。春秋中期晋卿魏绛述夏代事,谓伯明氏的不肖子弟寒浞,“夷羿收之,信而从之,以为己相”(注:《左传》襄公四年。),认为夏代已有“相”。春秋后期宋臣仲几谓“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注:《左传》定公元年。),墨子说“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注:《墨子·尚贤中》。),此为春秋时人以为商代有相之例。究其实际而言,舜至夏商时期,不大可能设置后世那样的相职,春秋时人只是将古代起到辅佐君主之责的大臣比附而称其为相。
相的本义为辅佐、襄助。春秋时期的相如果按其身份地位高低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辅佐君主治国或完成各种礼仪的卿,一是各种赞礼或进行辅助事务工作的小臣。就前者而言,春秋时期的相多为辅佐国君或高级贵族完成各种礼仪者,他们一方面相礼,另一方面也主持国政,究其身份应当说还是卿,所以春秋时期的相权实即卿权,属于宗法贵族政治范畴。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这在春秋时期多称之为“相”。行“相”之事者亦被称为相(注:据《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谓“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左传》宣公十二年),将楚国令尹子玉称为“国相”,在这里,“相”已由动词转化为名词。列国执政之卿似乎都可以被称之为相。秦国医生名和者曾经对晋国正卿赵文子说:“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左传》昭公元年),即将卿的执政之事称为“相”。鲁国的季文子执政历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三世,故谓其“相三君矣”,亦与医和之语为同例。周的单襄公“为卿士以相王室”,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子产被视为“善相小国”,他在铸刑书的时候,晋国的叔向写信反对,信中说“今吾子相郑国”(《左传》昭公六年),亦将子产所执行的正卿之事称为“相”。这类相,逐渐演变为一种职官。春秋时期,可能以齐国设置相职为最早。史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齐臣崔杼弑齐庄公以后,立齐灵公为君,“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既称“左相”,则崔杼本人当为“右相”,可以推测当时齐国已有左、右相的职官设置。)。春秋前期,齐国的鲍叔力谏齐桓公,欲使管仲治理齐国,他说:“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注:《左传》庄公九年。)齐桓公不念旧恶,“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不是使管仲相礼,而是使他辅助自己治理齐国。晋公子重耳率臣流亡途中到达曹国时,有人即谓“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意即重耳手下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而是可以辅助君治国的大臣。在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卿权向君权转化的时候,有些卿士自己也设置相,或称为“相室”,意即卿族家室之相。《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载,赵襄子的时候,其“相室”曾经进谏任命人才之事。这种“相室”虽然并非国家的“相”,但其已有了这类相的影子。
终春秋之世,可以说列国担任治理国家重任的“相”者,皆属于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策国家军政大事,实质上都是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春秋中期鄢陵之战后,晋臣郤至告庆于周的时候,周臣即认为他“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当时郤至还不是晋国上卿,所以周臣谋划“导晋侯使升郤至以为上卿”(注:见《国语·周语中》及韦注。)。属于三桓的鲁国季文子在鲁宣公、成公时执鲁政,有人即谓“季孙于鲁,相二君矣”(注:《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相国——即辅佐君主治国——之事实为卿的职守,晋国正卿范宣子“以相晋国”、赵文子以正卿身份执政事,“相晋国”(注:《国语·晋语八》。),皆为其例。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卿、相连用混用的情况多有所见,但仔细分析起来,两者的区别还是存在的。卿的称谓于春秋时期居多,除了职官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贵族身份的标识;相的称谓于战国时期居多,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并不是传统的那种贵族身份的标识。战国时期列国之相又被称之为“卿相”,只是出于对任相者的尊崇。
战国时期相权是春秋时期卿权的蜕变。孟子曾子向齐宣王谈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问题。《孟子·万章》下篇载: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由春秋时期的卿向战国时期的相的转变,契机在于强化君权的需要,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即将其赶下台——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春秋战国之际,强宗大族日益解体,代表这些强宗大族势力的“贵族之卿”的权势趋于没落是必然趋势,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又为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孟子所说的“异姓之卿”跟“贵戚之卿”相比,其主要区别即在于他们没有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布衣卿相之局的嚆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二、布衣卿相的先河
由出身于卿族以外的人担任相,这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出现。晋国卿族擅权的时候,各自已经设置相。史载“三卿宴于兰台,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这位段规就是魏桓子之相,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智襄子侮辱段规事为“耻人之君相”,认为“君相”有相当影响,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注:《国语·晋语九》。)。段规并非晋国卿族,也不是晋君之相,而是日益显示出新君形象的晋卿之相。段规一类的人物实为战国时期治国之相的先驱。到了战国时期,许多出身寒微的术士奔走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以谋取相位为最高荣光。曾出任赵、燕等国相职的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注:《战国策·秦策一》。)。秦国的商鞅虽然始终没有正式的“相”的名号,而只任大良造之职,但其职守实即为相,所以战国时人谓“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注:《战国策·秦策一》。),其出身虽然为卫国公族,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但商鞅本人地位并不高,只是魏相公叔座手下的一名“中庶子”(注:见《史记·商君列传》。)。著名术士张仪在任相之前,被人视为“贫无行”者,随楚相饮酒时楚相丢了玉璧,张仪首先被怀疑偷璧,被“掠笞数百”(注:《史记·张仪列传》。)。秦相范睢曾经向秦王这样讲述自己的出身:“臣东鄙之贱人也,开罪于楚、魏,遁逃来奔。臣无诸侯之援,亲习之故,王举臣于羁旅之中,使职事,天下皆闻臣之身与王之举也。”(注:《战国策·秦策三》。)以范睢这样的“东鄙之贱人”的出身,若觑觎君位,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之,战国时期,一批出身并不高贵的人担任相职,实开秦汉时代布衣卿相之先河。
这些出身寒微的士人一旦为相,自觉没有什么根基,所以他们所努力的目标只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取君主的信任与欢心,从而巩固自己的相位。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士人出身的相有的可以犯颜直谏,例如赵肃侯不顾农事而率众出游的时候,赵相大戊午即“扣马”而谏,谓“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遂使“肃侯下车谢”(注:《史记·赵世家》。),停止了出游。这里提到的大戊午,《战国策·韩策一》作大成午,曾与申不害联合引外援而固己之相位,盖为其出身低微的缘故。这样出身的相可以因国君的好恶而随时任免,他们皆有益于国而无害于君。春申君黄歇担任楚相20多年,“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从历史记载看,黄歇“游学博闻”,写得一手好文章,似为士人出身。他担任楚相如日中天而权力甚大的时候,曾经有人劝他“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注:《史记·春申君列传》。)。黄歇终不行此事,关键原因在于他在楚国贵族中并无根基,所以在楚国政变中被杀身死。齐相宋燕被斥逐,“罢归之舍,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注:宋燕,《战国策·齐策四》作“管燕”。),无一人肯随之另谋出路。宋燕没有贵族出身的履历,所以士人皆不相随,这与大贵族出身的齐相孟尝君罢相之后,鸡鸣狗盗之徒皆随的情况大异其趣。
普通士人或低级贵族出身的人往往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靠自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来谋取相位。周的王室贵族周最曾经对术士吕礼说:“子何不以秦攻齐?臣请令齐相子。”(注:《战国策·东周策》。)按照周最的设想,吕礼可以先让秦攻齐,则齐便任命吕礼为相以免遭秦攻。卫国人吴起,曾经就学于曾子,可见其社会地位并不高贵,他从魏至楚的时候,“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不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注: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为人臣,尽忠致功”(注:《战国策·秦策三》。)。他尽忠于楚悼王,为楚国变法富强立下卓著功勋。这类士人出身之相虽然得君主青睐而可以平步青云,显赫一时,生活优裕,“结驷列骑,食方丈于前”,但若失去相位,则地位一落千丈,只能“织屦为食,食粥”为生(注:《韩诗外传》卷九。)。他们的利益附着于君权,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为君主效忠尽力。这样的相,不仅要随时察言观色以求君主欢心,而且要入乡随俗,取得国人支持,以稳固自己的地位。《战国策·赵策三》载,有一位从魏国赴赵任相的张相国于“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未尝不言赵俗之善者也”,其目的即在于讨得赵人欢心。
在复杂激烈的竞争当中,相往往处于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特别是出身低贱之相,更由于没有牢固根基而常常遭人攻讦,因此更要时刻警惕,以免遭人暗算。《战国策·东周策》载,东周君免相工师藉之后,任命周仓为相,周仓引见外来的术士往拜东周君的时候,“前相工师藉恐客之伤己,因令人谓周君曰:‘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以此来避免伤害自己。术士往往利用置相之事作为攻击政敌的手段。张仪欲谮害秦国权臣樗里疾的时候,便设法让樗里疾出使楚国,“因令楚王为之请相于秦”,然后张仪对秦王说楚王请秦任樗里疾为相,“今王诚听之,彼必以国事楚王”。此事引起秦王大怒,樗里疾不得不出走避难。《战国策·秦策一》所载此事或当出于术士假托,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术士的心目中,揭露某人引外援而谋相位,确是攻击政敌的有效手段。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
甘茂相秦。秦王爱公孙衍,与之间有所立。因自谓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闻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见王曰:“王得贤相,敢再拜贺。”王曰:“寡人托国于子,焉更得贤相?”对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得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于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甘茂采取捏造事实进行诬陷的手段将公孙衍击败,反映出术士间为争夺相位而进行的斗争的残酷。在秦相应侯范睢失势的时候,术士蔡泽采取直言不讳的办法直接引起范睢的重视,他先扬言于范睢说“燕客蔡泽,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夺君位”,然后在见到范睢时条分缕析其利害,终于使范睢“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笃,因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注:《战国策·秦策三》。)。蔡泽因势利导,既没有得罪范睢,又为自己谋得了相位。《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为了谋害其政敌陈轸,遂“令魏王召而相之,来将梏之”(注:《战国策·魏策一》。),将相位作为诱饵,引诱陈轸上钩。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争夺相位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战国时期布衣卿相之局的发轫,对于自周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有很大影响,后世封建专制中的官僚系统实开端于此。这种政治格局标识着宗法贵族已经比较迅速地退出社会政治舞台的核心地位。在西周春秋时期多层次的宗法贵族统治下,普通民众之上的直接权威即宗法贵族,而非诸侯王。从本质上说,普通民众只对本宗族的贵族负责,而不受国家的干预和支使。可是在布衣卿相格局下面,民众却听命于相及其以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受控于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布衣卿相之局正是在大量自耕农民涌现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的结果,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变动。
三、战国时期一类特殊的“相”
战国时期所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相”,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列国间激烈竞争和权力下移的时代特点。这类任相职者有许多出身于术士,他们与国家内部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相有不少区别。在各国纵横捭阖、外交斗争十分频繁的时候,一些为国君倚重的大臣可到别国为相,还有一人而挂多国相印者。这类“相”与作为国君股肱的相不同,他们实际上是一些高级别的外交官,与本国的真正掌权大臣有一定区别。这些“相”与当时的客卿相似。《战国策·楚策一》谓苏秦“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史记·苏秦列传》载此事谓“佯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王以为客卿”。可见《楚策》之相即《史记·苏秦列传》之客卿。除了纵横家之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有被别国召去任相者,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尝君相魏。魏国的公孙衍曾向魏襄王建议说:“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注:《战国策·魏策二》。)这个建议为魏襄王所赞赏,不久即召孟尝君田文至魏为相。显而易见,魏之所以召孟尝君为相,目的是为了加强与强齐的联系。这样的类于外交官的相,与本国实际上的相可以同时并列。
这种专司外交事务的诸国之相位,吸引了诸多纵横家参与竞争。《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张仪先后为秦、魏之相的时候,在楚国的术士史厌对赵献说:“公何不以楚佐仪求相之于魏,韩恐亡,必南走楚。仪兼相秦、魏则公亦必相楚、韩也。”他劝赵献利用诸国间复杂的利害关系以谋求兼相楚、韩两国。以情理度之,赵献当是楚国专司外交的大臣,可能和张仪类似,也属于纵横家之类。战国时期,不仅许多术士参加相位的角逐,而且术士还往往为贵族大臣出谋划策以射取相位。楚国术士名献则者曾经对秦国大臣公孙消说:“公,大臣之尊者也,数伐有功。所以不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他为公孙消谋划如何取得太后的欢心,最后达到“太后必悦公,公相必矣”(注:《战国策·秦策五》。)的目的。战国中期,魏相田需死后,由谁继任相职一时间成为列国统治者和术士们关注的焦点,楚相昭鱼担心由张仪、薛公孟尝君或犀首公孙衍中的某一人为相,术士苏代便拟往说魏王,请魏让太子任相。苏代所拟说辞如下:“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自相也。’”(注:《战国策·魏策二》。)从这段说辞里面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置相对于他国的外交甚有影响,所以楚相昭鱼担心跟楚关系不好的人担任魏相。第二,在一般术士的心目中,一些担任过相职的著名术士,其政治倾向可谓尽人皆知。第三,相位对于术士是很有吸引力的诱饵,所以若魏太子为相,术士们便会认为定非长久之计,魏国定会任用他人为相,因而在魏国的“丞相之玺”吸引下靠近魏国。
战国时期这类特殊的“相”,以张仪最为典型。秦惠王后元三年(前322年)张仪为秦国利益而相魏,即《史记·张仪传》所谓“相魏以为秦”。论者或以为张仪是主持魏国大政的“相”,其实不然。魏国不会那么傻,让一个秦国间谍担任掌握国家大权的相。魏以张仪为相,固然是看中了张仪的外交经验,但也是迫于秦的压力而向秦作出的友好姿态,是魏国试图通过张仪而跟强秦联络的一种方式。《史记·张仪传》谓:张仪相魏之后,“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其间的原因就在于魏惠王心中很清楚张仪的作为,并没有把他当心腹大臣看待。后来,魏国“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由此可见,魏王很了解张仪的背景和他到魏国的目的。《战国策·魏策一》谓“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指出魏任用张仪是为了联合秦国而使魏取韩国之地。魏人雍沮就很清楚张仪相魏的个中缘由。请看相关记载:
张子仪以秦相魏,齐、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谓张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则国家安,而百姓无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计过也。齐、楚攻魏,公必危矣。”张子曰:“然则奈何?”雍沮曰:“请令齐、楚解攻。”雍沮谓齐、楚之君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张仪于魏,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魏矣;若不胜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敝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结也。今仪相魏而攻之,是使仪计当于秦也。非所以穷仪之道也。”齐、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于魏。
从这个记载里可以知道,张仪“与秦王阴相结”,并不是太秘密的事情,雍沮就对此了如指掌(注:如果不明此类相的特点便公造成一些误解。林春溥《战国纪年》认为“薛侯会魏王之明年,齐与魏会,韩以兵合於三晋,因使孟尝君入秦,即齐策所谓孟尝君为从,先观秦王之谋也。及秦觉其谋,孟尝君几不免”。林氏此说不妥,钱穆先生指出“孟尝君合从固非一日,然谓其入秦在诈观秦王,则恐未必”(《先秦诸子系年》第399页)。钱说甚是。外交与特务固然不可截然区分,但也不是没有区别。孟尝君被免相,根本原因在于秦国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不是发觉孟尝君之谋的结果。因为孟尝君相秦的目的,依照战国时期这类外交人员的相的特点,应当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不需要特别的发现。),和张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孙衍也知晓“张仪以合秦、魏”(注:《战国策·魏策一》。)而为魏相的真正目的。张仪为秦而相魏,魏为拉拢秦国而使张仪为相,这就是事情的实质。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把张仪所任之“相”作为高级别的外交官来理解,那么,可以说张仪实际上是“并相秦、魏”(注:《战国策·魏策一》。)的。他任魏相,实际上是负责魏与秦的外交联络工作。张仪在魏国时,曾就魏与楚联合以伐齐的事情发表意见,但“魏王弗听”(注:《战国策·魏策一》。),在涉及魏国对于秦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张仪的意见并不受重视。各国君主对于这一类担任相职的外国人员很不放心。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手下的小吏司空马到赵国担任“守相”,即代理之相。当秦军攻赵的时候,司空马曾经请缨于赵王,谓“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请为大王悉赵兵以遇”(注:《战国策·秦策五》。)。赵王不信任司空马,终不使其率兵,司空马只得讪讪离赵。
在列国争雄的时候,强国能派重臣(特别是那些纵横家)到其它国家为相,弱国为了某种原因也能派臣到强国为相。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前318年)赵国的“乐池相秦”(注:《史记·秦本纪》。)就是一例。关于乐池其人,另有两处史载亦提及。一是《韩非子·内储说上》载“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一是《赵世家》载燕王哙之乱时,赵武灵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和索隐皆谓纪年说与此同。可能这三个乐池为一人。他为赵臣,被赵派为中山相,后又至秦为相。乐氏为赵国大族,乐池盖为赵国重臣,其为秦相,表示赵欲与秦交好。此年齐韩魏赵燕五国攻秦,但五国各自心怀鬼胎,貌合神离,赵派乐池到秦,应该是为了表明赵并非秦国的主要敌人。假若对于本国不利的人至大国为相,则其国往往想方设法使大国免其相位。秦昭王七年(前300年)赵人楼缓相秦,于赵不利,赵便派术士机郝到秦活动,“请相魏冉”(注:《战国策·赵策三》。)。在机郝周旋下,“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注:《史记·穰侯列传》。)。
这种派人到别国任相职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联络和外交斗争的手段。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欲通过置相的办法来影响别国外交政策。例如,战国后期魏国欲与秦联合的时候,赵国相当恐慌,术士即建议赵国资助以反秦著称的周最到魏国为相,认为“资周最,而请相之于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虚矣”(注:《战国策·赵策三》。),将此视为釜底抽薪的办法。战国中期,秦、魏两国君主约定会见的时候,魏国缺相,术士便劝魏王任命亲齐者为相。其辞谓:
遇而无相,秦必置相。不听,则交恶秦;听之,则后王之臣,将皆务事诸侯之能令于王之上者。且遇于秦而相秦者,是无齐也,秦必轻王之强矣。有齐者不若相之,齐必喜,是以有齐者与秦遇,秦必重王矣。(注:《战国策·魏策四》。)
所谓“秦必置相”,指秦将派人到缺相的魏国任相。就当时的形势看,魏置相之事,实为决定其外交是倾向于秦,抑或是倾向于齐的表态。依术士的分析,魏应置亲齐之相,这样魏便会与齐交好,从而秦也不敢小觑于魏。置相与外交的关系于此十分明确。为了扩展自己的影响,有的大国甚至可以为某人求取两国相位。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年)五国攻秦以后,秦昭王即“欲为成阳君求相韩、魏,韩、魏弗听”(注:《战国策·秦策三》。)。其事显然是秦为增强对于韩、魏两国的影响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其次,置相于别国是增强本国外交地位的重要手段。魏相翟强去世时,术士曾劝楚利用这个机会联合齐国一起让魏国任甘茂为相;其理由是“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雠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注:《战国策·楚策二》。)术士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甘茂相魏对于楚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所在。战国时期术士曾经指出,“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注:《战国策·韩策三》。),显然,将亲秦的人物置为韩相,正是秦国增强自己对于韩的外交地位的措施。
再次,有时候,弱国欲通过置相的办法试图给强国造成麻烦。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战国中期,楚怀王曾经与术士范环讨论派谁至秦国为相的问题,楚怀王以为甘茂可以,范环认为甘茂为贤才,而“秦之有贤相也,非楚国之利也”,并且建议“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孙郝者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注:这里所提到的“公孙郝”,《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作“向寿”,《韩非子·内储说下》作“共立”,并谓“共立少见爱幸,长为贵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环,以听于朝,且利以乱秦也”。)。在相互竞争的时代,强国的贤相于弱国不利,范环深明此理,所以才建议楚力主让与秦王亲昵的人为相。《战国策·韩策三》载,术士在为楚国利益而讨论韩、楚关系时谓“韩之父兄得众者毋相,韩不能独立,势必善楚”,认为楚应当支持在韩国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为韩相,楚怀王则必定推荐名韩珉者为相,谓“吾欲以国辅韩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恶珉,珉必以国保楚”(注:《战国策·韩策三》。)。后来,韩果然以韩珉为相,这与楚国奉行不使敌国有贤相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复次,将置相作为加强国家间联系的手段。例如战国前期,魏一度灭中山,不久,中山复国,魏即用“中山君相魏”的办法加强魏与中山的关系(注:《战国策·魏策二》。)。前324年术士公孙衍在发动燕、赵、魏、韩、中山等五国相王之前,曾经“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注:《战国策·魏策二》。)。将列国相位的安排作为联络诸国的重要办法。他曾对魏王说:“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注:《战国策·魏策二》。)认为魏若任命孟尝君为相,必将加强魏、齐两国关系。战国中期,赵国为了对付楚、齐、魏三国的联合,便“结秦,连〔赵〕、宋之交”,加强与秦、宋两国的联系,其措施就是“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注:《战国策·赵策四》的“魏败楚于径山”章所述此事原作“结秦,连楚、宋之交”,姚本去“宋”字,但于文义未安。《战国策·东周策》“谓周最曰仇赫之相宋”章亦载此事,由文义看,此“楚”字当为“赵”字之误。关于仇郝(即仇赫)相宋的目的,是章载“仇赫之相宋,将以观帮之应赵、宋,败三国。三国不败,将兴赵、宋合于东方以孤秦,亦将观韩、魏之于齐也”,可见赵国实将置相于宋作为其外交政策十分重要的一步棋。)。
第五,置相是本国外交倾向的一种表达方式。秦国推行连横政策时曾经“内韩珉于齐,内成阳君于韩,相魏怀于魏”(注:《战国策·赵策四》。),将置相于别国视为重要的外交方式,表示秦与齐、韩、魏等国的交好。战国末年秦贬斥文信侯吕不韦的时候,吕不韦之臣“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注:《战国策·秦策五》。)。任命司空马为赵国守相,表明赵国与秦交恶,所以为秦所忌恨,遂即发兵攻赵。《战国策·韩策一》载:“楚昭献相韩,秦且攻韩,韩废昭献。昭献令人谓公叔曰:‘不如贵献以固楚,秦必曰楚、韩合矣。’”依这里所载,韩依然用昭献为相,即表明韩与楚国交好,使秦不敢小觑于韩。
就总的情况而言,这种专司外交职责的相位的设置,是战国时期频繁外交与列国间尖锐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小国受大国的压力而任命某人为相,实际上是对于大国的屈从,是并不光彩的事情。战国时期的术士对于这一点很明白,曾谓“韩求相工陈籍而周不听;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听,何以也?周曰是列县畜我也”(注:《战国策·楚策一》。)。周虽然十分弱小,但却在有的时候为了本国的面子问题而敢于顶住大国压力,不按照大国的意愿而置相,其目的就在于以此表示周并不是大国属下的“县”,而是独立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些国家任用一些其它国家有影响的人物为相,往往有保护本国利益或振兴自己国家的用意在内。术士曾拟孟尝君到楚为相,谓“小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注:《战国策·齐策三》。)。孟尝君是战国中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其为各国所重并委之以相位,实出于各国自己的目的。在孟尝君一度被齐王放逐的时候,术士冯谖曾对魏惠王说:“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魏惠王为了利用孟尝君的影响,于是“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注:《战国策·齐策四》。)。齐、秦两国争取著名术士甘茂之事,亦为这方面的典型。甘茂离秦赴齐的时候,术士曾经对秦王说:“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明白了个中利害,“即赐之以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而齐国也“位之上卿而处之”(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欲以更优裕的条件以求甘茂留在齐国。
术士之类的人物被派往别国为相,虽然是很风光的事情,但有时候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特别是一些负有间谍使命的术士更是时刻面临杀身之祸。著名的术士苏秦被“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注:《战国策·楚策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传秦相吕不韦为了达到攻赵以扩展自己私邑的目的,便请张唐到燕国为相。张唐推辞说:“燕者必径于赵,赵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注:《战国策·秦策五》。)原来张唐与赵有隙,赵曾悬赏捉他,而从秦到燕须经赵国之地,张唐视其为危途,所以不愿到燕国为相。魏国的范座任相职期间曾经不从赵命而拒绝实行合纵政策,所以范座在魏被免相以后,赵王便“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魏王许诺”(注:《战国策·赵策四》。)。虽然后来范座得免一死,但任相职而带来的危险则还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四、旧传统的遗存——战国时期的贵族之相
还应当提到的是,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和社会结构中旧贵族还有不小的势力,所以战国时期诸国亦有高级贵族任相职者。赵相平原君为赵王诸公子之一,曾经“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注:《史记·平原君列传》。),在赵国很有影响。术士公孙龙曾经当面说他“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注:《战国策·赵策三》。)。可见平原君是依靠贵族亲缘关系而占据相位的典型人物。这样的相虽然有的赁借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而为君主作出贡献(注:例如战国初期,魏相魏成子系魏文侯之弟,他“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魏成子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魏招纳贤士,做出了贡献。),但在许多情况下却往往给君主造成威胁。例如,秦昭王时相魏冉,虽非秦国王族,但他是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故能干预朝政,称穰侯。史载“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穰侯之富,富于王室”(注:《史记·穰侯列传》。)。在秦国东进与东方六国斗争的时候,魏冉使富庶的陶为其私邑,实为秦国的一支分裂势力。应侯曾经对秦昭王说:“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国无事,则已;国有事,臣必闻见王独立于庭也。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王子孙也。”(注:《战国策·秦策三》。)秦相魏冉影响之巨于此可见。
战国时人有“千乘之君与万乘之相”(注:战国策·齐策三》。)的说法。列国的贵族之相往往对于君主造成很大威胁。齐国的大贵族田婴任相职时,“与故人久语,则故人富;怀左右刷,则左右重”(注:《韩非子·内储说下》。),跟故人多说一些话,赏赐左右一些布巾之类的小东西,都可以使他们贵富起来,可见其相位的重要。其子孟尝君为相的时候,“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注:《荀子·强国》。),“以人臣之势,假人主之术”,使得臣下奔走于其麾下,对于齐国政局带来颇大影响,其势比田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国的情况与此相类似。贵戚穰侯魏冉为相的时候,秦国大权一度旁落。术士范睢向秦昭王进言时谓“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明言秦国政治局势中相权已经危害到君权,使秦昭王下决心驱逐穰侯,废其相位,并且“拜范睢为相,收穰侯之印”(注:《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战国策·赵策二》载赵王之语谓:“先王之时,奉阳君相,专权擅势,蔽晦先王,独制官事。寡人宫居,属于师傅,不能与国谋。”相的权力如果达到了“独制官事”的地步,君主自然不能不感到恐惧。赵武灵王传位于赵惠文王以后,其晚年赵国发生内乱,其叔父公子成为相,与司寇李兑共掌大权,“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注:《史记·赵世家》。),使赵武灵王饿死于沙丘宫中。战国时人评论此事谓“武灵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兑为相,武灵王不以身躬亲杀生之柄,故劫于李兑”(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赵武灵王之死乃是大权旁落的恶果。战国时期的术士讲楚国白公发动叛乱的时候,楚王左右都说没有此事,其原因就在于“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矣”(注:《战国策·楚策一》。《韩非子·内储说下》载此事谓:“州侯相荆,贵重而主断,荆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所载与此略同。)。楚王左右之臣的众口一词,原因即在于其相的贵重主断。这种贵族之相有时候甚至可以攫取君主之位,宋相司城子罕就曾经“劫宋君而专其政”(注:《韩诗外传》卷七。其所提到的司城子罕,为春秋时期宋国司城子罕的后人,古本《纪年》称其为“易城罕”,谓“宋易城罕废其君辟而自立”,“君辟”当即宋桓侯璧兵。如宋司城子罕之类的“相”,实即春秋时期卿权发展、蜕变的结果。对此,作者曾
在《论周代卿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一文加以讨论,敬请参阅,这里不再赘述。)。可见相权对于君权的威胁。
五、简短的结语
相的普遍设置和相权影响的增强,是战国时期极富时代特色的事情,它是由宗法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纵横捭阖、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各国的相实处于政治与社会运转漩涡的中心。在各国的政治体制中,相是职官系统的核心权位,许多士人对于“贵重主断”的相位趋之若鹜应当是情理中事。一般说来,战国时期凡是由旧贵族任相职者,其政治多陷于腐败没落的境地;而由那些有杰出才能的士人担任相职者,则政治往往比较清明,国势蒸蒸日上。士人的平步青云而任相职,实开秦汉时代布衣卿相之局的端倪,是社会政治结构变迁中不可小觑的变化。
标签:春秋战国论文; 张仪论文; 战国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战国策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魏国论文; 田文论文; 楚国论文; 儒家论文; 君主论文; 左传论文; 战国时期论文; 西汉论文; 秦朝论文; 东汉论文; 隋朝论文; 东周论文; 周朝论文; 唐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汉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