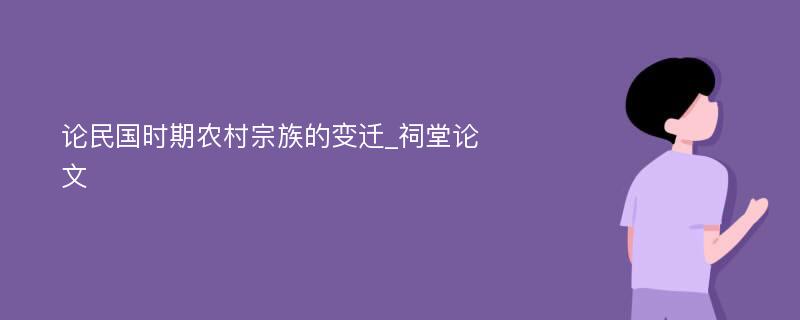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试论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2-0083-06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剧变时期。农村的宗族制度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宗族的根基在民国时期并没有被动摇,因此,尽管它在总体上不断消弱,但并不妨碍其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和变异。本文主要探讨民国时期农村宗族衰落与变异的表现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
一般认为中国的宗族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式的宗族、殷商时期的宗法式宗族、魏晋以降到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宗族和宋以后到清末的近代封建宗族组织。它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衰落和变异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革命中基本被消灭。在80年代,特别是在南方某些地区又有所复苏。
民国时期的宗族制度在体制上依然维持着宋明以来所形成的近代封建宗族制度的模式,即个体小家庭组成的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和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并以前者为主。宗族在内容上依然包括族产、族权、祠堂和族谱。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宗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宗族势力在总体上却走向衰落。其原因可以从经济形态转变和社会政治变革中去寻找。
首先,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宗族制度形成巨大的冲击。清末民初以来,在内部商品萌芽与外来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作用下,以市场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对自然经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而宗族制度是以自然经济为前提的。自然经济的衰落使宗族的根基有所动摇。随着资本主义侵蚀农村,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涌向城市,使宗族人口迅速减少,严重动摇了宗族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农村的发展,引起了宗族成员的迅速分化,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宗族内部的两部分族众愈来愈对立,使宗族的统治愈来愈难以维持。
其次,宗族制度能够延续两千年是因为它与政治上的宗法一体化互为依存,因此政治变革对宗族的冲击更为有力。1911年民国的成立使传统的封建政体崩溃,传统的社会关系开始松动,旧式宗族制度也受到影响,尤其是民国新法律的制定直接宣布了传统家庭关系的解体。民法废除了传统的宗祧继承制度,同时规定一夫一妻制、男女经济地位平等,否定了几千年中国家庭社会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观念,使宗族制度失去了旧有的法律保护与政府庇护。
第三,人民民主革命沉重打击了宗族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宗族制度、宗法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封建的宗族制度进行了系统、尖锐的批判。他们看到了宗族制度的种种罪恶,如破坏人们的独立人格,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剥夺人们的平等权利,养成人们的娇情习惯等。指出要改变中国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必须摧毁他们称之为“家族本位主义”的宗族制度(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订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也领导了批判和消灭宗族制度的斗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政权、族权、神权、大权是束缚农民的四条绳索的论点。指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族权则是维持封建统治的辅助力量,要消灭封建族权,首先要消灭封建政权(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1926年到1927年上半年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对封建宗族制度开展了有史以来的最猛烈的冲击。这次农村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革命的矛头对准农村封建政权、土豪劣绅的同时,也把宗族制度和族权当作主要打击目标之一。许多作恶多端的族长族绅被批判或镇压,祠堂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处,族谱族规被农民踩在脚下,妇女和族中贫苦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村的封建宗法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倒转乾坤”的变化(注:彭述之:“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页。)。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第一次提出了消灭族田公田,并将它分配归农民的纲领,这说明中共对于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宗族制度有了十分明确的认识(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六大以前》,第830~832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一时期对宗族的打击主要体现为各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中没收宗族祠堂的土地和打击宗族中地主豪绅的斗争,这样在根据地内就从根本上推倒了宗族制度的基础,消灭了宗族势力的统治。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共对族产族田的政策从没收改变为暂时保留。解放战争开始后,党的农村政策转变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时,对于族产族田也相应改为统统没收的政策了。
尽管以上原因导致了宗族在民国时期的衰落,但只要小农经济未被根除,宗族仍会复苏。因此1949年前,中国农村宗族总体上的衰落速度仍十分缓慢。1952年全国土地改革和农村民主政权建设完成后,宗族才遭到致命打击。
二
衰落是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主要特点,也代表了宗族在近代社会的总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国民政府中央控制区的衰落慢于革命根据地,内陆地区慢于沿海地区,农村地区慢于城镇地区。农村宗族总体上处于缓慢解体的状态,这可以从宗族的四个要素——族产、族权、祠堂和族谱的衰落过程中体现出来。
族产是宗族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宗族实现聚宗合族目的的条件。族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族田,族田的来源有三种:一是祖上分家时所保留的部分公田;二是由公田的收租谷购买的田地;三是由同宗后裔所捐献或绝嗣者的土地。族田的数量、质量及其管理直接影响到宗族的盛衰,反之亦然。因此,民国时期族田的破坏既是此时期宗族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宗族步入强弩之末的一个表现形式。
族田的被破坏主要表现为族田被侵吞以及自由买卖族田。族田的设置,作用在于“收族”,名义上属全体族人共同所有,但实际上常为族中富人所把持,他们往往利用宗族职权侵吞族田。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更为猖獗,如在族产较为发达的江苏省,有人曾调查了上海附近的一个叫黄渡的村子,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族,有公田200多亩,这些族田已逐渐沦入族长手中,残存的不过8亩而已。而这8亩土地本来应该并吞绝尽,只为了装饰祠堂和每年祭祖费用而得以苟延残喘(注: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版,第44页。)。除了直接侵吞族田,族长们还侵占田租,使得实际用于族众的田租大大减少,基本只够支付每年的祭祀费用,更无从谈起救济族中贫困的农户。以族产最为发达的广东省为例,“凡族中可以收到的塘租、房租、利息,特别是田租,统归理事支配,除掉纳税、祭祀、修理族产、津贴教育外,族产即被他们保管,或支或存。他们普遍是要舞弊的,许多理事始终就没有详细帐目公开的报告出来,有的甚至拿太公田的田租暗中支付他们私家的田赋。虽然太公田是不能被人自由的买卖,实际太公田的收入已为主管人任意支配,这样族有田产便成为变相的家庭或个人所有的田产。”(注:陈翰笙编:《广东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版,第60页。)侵吞族产直接影响到救济族众目标的实现,使宗族合族敬宗的功能无法发挥。
与此同时,族田在一定限度内的自由买卖也显示了这一时期宗族的衰退。如在华北地区,黄宗智曾调查过河北省沙井村,民国以前的沙井村也恪守同族和同村人有优先买地权的惯例,但到了近几十年,旧日的传统被以土地为商品的新现实所取代。经济压力迫使贫农首先照顾自己的需要,他们不顾宗族内部成员的反对,将土地或坟地卖给或典给外人。在这样的压力下,部分宗族已无法维持宗族的习俗——准许最穷的族人耕种祖坟地上的几亩可耕地。沙井村七个较大的族中,只有三个宗族在调查时仍然把祖坟地租给最穷困的族人(注: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276页。)。土地卖给外人,不仅反映出村庄共同体解散的趋势,也更深刻揭示了宗族关系全面崩溃的事实。而在南方族田较多的省份,除了宗族首领侵占族田,成为实际上的大地主外,更有一些驻防当地的军队没收或出卖族田,使族田数量日益缩减。如四川人民曾呈请国民政府,禁止各地驻防军队没收、典卖族田。
从以上所举事例不难看出,族田的衰落在民国时期愈演愈烈。族田的衰落必然导致族产的日薄西山之势,而宗族一旦被掐断经济命脉,衰落之迅速是必然的结果。
祠堂是宗族活动最主要的场所,它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是族长向族众灌输封建礼教的课堂,是族众讨论族中事务的会场,还是宗族的法庭。祠堂作为宗族的物化象征和中心机构,代表着宗族的利益和宗族的团聚。由于族田的衰落而必然导致宗族公费的不足,1928年中华民国教育促进会对河北省定县农村宗族公费的调查显示,全县154个宗族中有145个全年经费不足40元(注:李景汉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发行,1933年版,第170页。)。祠产的衰竭和公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宗族日常活动的展开,以至于合族祭祖这样的大事都得不到保证。在河北省沙井村,到1940年,“要拜神的各自去。而过去全村一年一度的聚宴,也只有几个交费的村民参加了。”(注: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7页。)祠堂作为宗族活动的公共场所,其作用日益削弱。同时由于战乱频仍,大批宗祠毁于战火或遭抢掠。而在革命根据地,祠堂几乎完全失去了固有的宗族意义。祠堂被改作农会场所、医院、学校。在江西瑞金县保留的85处中央机关和著名领导人的旧居中,仅宗祠即达27座,占三分之一(注:参见《江西遂川县工农兵旧址陈列解说词》(未刊稿)。)。祠堂由宗法礼教的课堂和族长族权的法庭转变为各级革命政府的办公场所和文化娱乐之地,打破了祠堂在宗族组织中的中心地位,而宗族一旦失去了祠堂的依托作用,必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族谱作为维持宗族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民国时期也受到很大程度破坏。在动荡的环境下,广大农民生存尚为艰难,更无从谈起保存族谱,大量族谱流失毁灭,而幸存的族谱也无法得到定期修订。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宗族意识的淡化,族产的流失和族众凝聚力的减弱,族谱已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族产的分崩离析意味着祠堂、族长、族权统治的经济基础正日趋消弱,而祠堂、族谱的毁灭则击碎了族长族权“代祖先立言”的神圣光环。族权的衰落一方面表现在族长权力的相对弱化、族长在宗族事务中的决策性地位受到日益猛烈的冲击、族长类型日益多元化、族务处理也趋向民主化;另一方面,族权对族众的控制力也明显下降。这源于族产的破坏导致了宗族内部阶级分化加剧,随着贫农、雇农、半自耕农人数的增加,他们对族产日益丧失宗族性关怀感到失望,以至于宗族感情日渐疏淡。另外,祠堂族谱的毁坏,族规的逐渐松驰,分解了广大族人的凝集力。族人可集中力量挑衅族权,而族长亦无计可施,族长族权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三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宗族制度从本质上讲,它反映出一种经济形态,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宗族的产生、发展、嬗变与衰亡都源于斯。民国时期,在内部商品经济萌芽和外部资本主义渗透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结构分崩离析,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局面。但只要小农经济这条根依然存在,这条根总会产生宗族制的客观要求和主观愿望。20世纪20年代,闽粤赣边区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农村宗族势力,“族长及祠款经营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族款。坏的族长、经管已经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人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注:《毛泽东选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但是一旦革命根据地势力削弱,宗族制又卷土重来,迅速恢复了旧有状态。这充分表明,革命运动只能摧毁宗族制的外延形态,却无法动摇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内部机制与基本功能。只有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发展取代了自然经济的存在,宗族制才会真正走向消亡。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宗族制即继续存在,也已经是变异与更新,不再是简单的重复,海外华人社会中的宗亲组织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其次,民国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宗族势力的进一步蔓延,但这种冲击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例,30年代初南京政府曾致力推动农村建设以实现所谓“民权”政治,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如在武汉地区,“整理保甲,选经省府定有方案……究其实际,各项章则,上级政府之设计,苦心焦虑,制成大观,不过低级机关档案上添一陈列物耳。……省府有令到县,县府即以之转区,区长再令而下之,则如石沉大海,有去而无返。区长逼无可逼,只得闭门造车,敷衍上令。任保甲职务者……垄断一切。其主任保长之权力,决不肯放弃,于是优秀者皆退避三舍,而不与为伍。……有劣迹之主任保长,虽欲去之而不能”。(注:《武汉日报》1936年6月19日。)即使在备受国人称赞的山西地区,直接民权的实现也是微乎其微的,而“能够有直接民权,才算是真正民权”。(注:悲茄著:“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和农村”,载《中国农村月刊》第二卷第6期。)可见,所谓的乡村政治建设徒具其表,只不过是南京政府的一驾播音机而已。
民国政府深知宗族制度对推行资产阶级宪政的巨大障碍作用,但统治者对迅疾推行宗制改革心怀戒备,他们担心羸弱的社会结构无法承受宗法组织消亡后的混乱局面。在外患未除,军阀纷争的解构力量的冲击下,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国共之争的威胁下,民国政府无心、无力也无意于进一步削弱摇摇欲坠的政权基础,为其他政治力量造成可乘之机。相反,在国内分裂倾向日趋严重的巨大压力下,民国政府转向于扶植、收买基层宗族势力,寻求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蒋介石曾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明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古来建筑国家的程序,自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而社,则合之以互动。由乡社以至县与省,以构成我们国家大一统的组织。故我们建设的基层实在乡社。”“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政权与族权的结合集中体现在宗族官员承担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各种职能。宗族的头面人物既是族田的收租人,同时又扮演着当地政府收税官员的角色。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农村选举村长,大多数地区只不过将旧首领改为村长。1931年政府提倡实行五户一组的邻闾制度,以后又推行保甲制度,这在实际上非但未建立起统治者所鼓吹的“乡村民主政治”,(注:陈洪进著:“民权政治与乡村建设”,载《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247页。)反而形成“保甲为经,宗族为纬”的社会格局。(注:何有良:“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载《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宗族的演进还受到自身内部规律的制约。首先,它的发展体现出一种惯性特征。这表现在明清以来自然经济的解体并没有导致宗族组织的迅速崩溃,中国农村宗族势力虽然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它仍是农村地区的基本组织系统。意识形态以经济基础为依托,但它有自身的独立性,其消亡还需以自身内部机制和基本结构的解体为前提,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次,部分地区尤以海外移民社会为主,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自然经济的依托,演化为纯血缘、地缘的各种宗亲组织、同乡会馆等。即使在城镇地区也广泛存在。这些组织已丧失了传统宗族的宗法性特征,从本质上讲,它们扮演着华人社团的、凝聚华人社会的角色。在这里,宗族的根本属性已经变异,沿另一个方向发展,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不再对宗族产生任何作用。
民国时期宗族的变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宗族的组织原则趋向民主化。在一些宗族中出现了宗族议事会,这就削弱了族长的权力和宗族的宗法色彩,使宗族的管理有一些民主化倾向。例如广西容县陈氏宗族,其宗祠管理机构由以下设置组成:董事一人,主祭一人,执事一人。(注:《容县陈氏族谱》(民国)。)在这样的体制下,族长的权力受到其他宗族官员的制约,权限相对较少,族务处理较具民主性,族长权力与地位向“名誉型”发展。
二、族规族约中添设新内容。民国时期撰写或修订的族谱除包含传统的内容以外,又纳入了一些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成分。如工农商皆本的思想开始在族约族规中体现。湖南益阳熊氏在《家训》中声称:“子孙或读书,或务家,或商贾技巧,诚能奋发有为,则无有读不成的书,粪不肥的田,作不得的生意,学不就的技艺。所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注:《湖南益阳熊氏家谱》(家训)。)荥阳郑氏在族规中自称:“内以正心齐家,外以农商富国”(注:《荥阳郑氏大宗族谱》,卷八。),同时族谱中也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想开始与宗族意识碰撞、协调并接轨。
三、血缘原则的突破与社会功能的强化。民国时期,血缘原则的突破主要发生在移民社会,集中体现在台湾移民的宗族社群中,有的宗族任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员为族长,地缘关系也成为形成各种宗亲组织的条件。同时随着封建王朝的颠覆,宗族的政治功能日益弱化,社会功能成为宗族活动的主要领域。宗族功能的社会化是近代中国农村宗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宗族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它的发展演变深深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各方面。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衰落与变异反映了整个农村社会走向破产的事实,同时也促使农村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全国土地改革和农村民主政权建设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