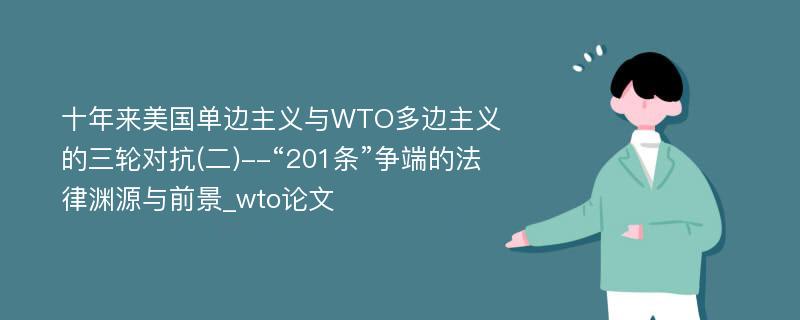
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下)——“201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三大论文,法理论文,美国论文,争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美国政府外贸国策的主要顾问之一,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当时曾亲身经历这场全国性大辩论,并于1994年3月和6月先后两度出席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举办的公听坐,发表“证词”。据他事后撰文评介,当时这场辩论的缘由和要点大体如下:
1994,《WTO协定》的缔约各方在总结GATT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达成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DSU),其中规定设立“争端解决机构”(DSB),它实际上是WTO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以不同名义召开的会议,由它全权处断争端。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暂停适用有关协定项下的关税减让和其他义务”。(注:《谅解书》,第2条第1款。) 尤其重要的是,在DSB中,彻底改变了GATT实行多年的“协商一致”(注:在《WTO协定》第9条的一项注解中,就“协商一致”一词的特定含义作了专门解释:“某事项提交会议审议时,如果与会成员无人正式表示反对,就视为该有关机构已经以协商一致同意(consensus)作出决定”。这种议事和决策程序,充分尊重了各成员的自主权利,但如果事无大小一律采取此种决策程序,事事都要求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才能决定通过,就会在实际上造成“一票否决”的后果,从而导致有关机制的低效和软弱。《GATT 1947》中有关争端解决程序的原有规定,即具有此种缺失,被称为“先天性缺陷”(birthdefect)。) 的程序,转而采取“反向协商一致”(negative consensus)的决策原则,即“一致反对,才能否决”,其实际效果就是:只要受害的申诉方或潜在的胜诉方在DSB会议上坚持经过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正式认定的正当请求,就会实现“一票赞成,即可通过”的结局。
由此可见,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远较GATT的原有机制强硬和高效,这种争端解决机制如能确保正常地运作,对于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缔约成员,特别是其中的超级大国,无疑是一种比较有力的约束。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中,往往因“财大”而“气粗”,按民族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事,造成对弱国贸易利益的重大损害;而实施上述争端解决新机制之后,一旦再遇到受害方依法投诉,DSB依法审断,则像美国这样的超级贸易大国,就难以再依仗其经济强势和借助于过去实行的“协商一致”原则,随心所欲地阻挠和逃避任何制裁。
上述这种新的争端解决机制乃是整个《WTO协定》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994年4月15日美国谈判代表在该“一揽子”协定上签署,在这前后,美国政府主管部门将它呈交美国国会审议和批准。美国国会两院针对《WTO协定》的全套规定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和全会。许多议员对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果横加指责,认为批准接受该《协定》就是“违宪”行为,因为它“侵害了美国的主权”,其主要论据之一,就在于担忧接受其中的新争端解决机制之后,势必会“毁损、剥夺美国的主权”。另一些议员针对上述观点加以反驳,认为接受WTO体制,包括其中不可分割的争端解决机制,完全无损于美国自己的主权。国会内两派议员的激烈争论,经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炒作,遂形成全国性的论战,杰克逊教授称之为“1994年主权大辩论”(" the Great 1994 Sovereignty Debate" )。(注:See:supra, J.Jackson, Sovereignty Debate, pp.169-170.)
杰克逊坦言:“参加或接受一项条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缩小了国家政府行动自由的范围。至少,某些行动如不符合条约规定的准则,就会导致触犯国际法”;(注:Id., p.172.) 美国国会中不少议员之所以反对接受《WTO协定》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就因为它相当强硬严峻,不再允许单一国家 (贸易大国)对专家小组的处断报告自由地实行抵制,拒不接受。(注:See:Id., p.177.) 因此,日后它势必对美国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对美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及其有关立法措施,产生约束作用和不利影响。“许多反对此项条约的人断言:WTO会危及美国的主权,因为许多决定可由WTO作出,并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注:Id., p.173.) 据此,杰克逊反复强调指出:1994年美国这场有关维护本国“主权”的全国性大辩论,其实质和关键就在于权力分配问题(questions about the allocation of power):即决策权力如何在国际机构与美国政府之间恰如其份地分配的问题。(注:See:Id., pp.160, 179, 182, 187-188.)
在这场全国性的主权问题大辩论中,杰克逊教授曾于1994年3月23日以美国“对外贸易代表公署”总顾问的身份,出席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公听会发表证词。除缕述WTO体制的来龙去脉之外,他还针对美国国内有关“接受WTO体制会损害美国主权”的“WTO反对派”见解,作了如下的解释和“澄清”:
“关于WTO体制的效果及其对美国法律的各种影响作用,存在着某些思想混乱。几乎可以肯定:就象美国国会处理最近几项贸易协定的情况一样,WTO和乌拉圭回合订立的各项条约并不会自行贯彻在美国法律之中,因此,它们不能自动地变成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同理,WTO专家小组争端解决程序作出的结论也不能自动地变成美国法律的一部分。相反,通常是经过美国国会正式立法,美国才必须履行各种国际义务或执行专家小组报告书作出的结论。一旦美国认为问题十分重要,以致明知自己的某种行为可能不符合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却仍然有意地违背有关的国际性规范准则(international norms),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体制,美国政府仍然享有如此行事的权力。这种权力能够成为事态发生严重错误时的重要抑制力量。”(注:J.Jackson,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March 23, 1994,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3rd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5, p.305.)
杰克逊教授上述这段“证词”给当时的议员们以及其后的所有读者们至少提供了以下信息,证实了以下几条“美国信念”:
1.美国在参加缔结任何国际条约时,一贯把本国利益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美国“主权”,和美国法律,放在首要地位。
2.美国参加缔结的国际条约,其中所规定的各种国际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通常都必须通过体现美国“主权”的主要机构——美国国会加以审议、批准和立法,才能转变成为美国国内法律的一部分,才能在美国贯彻实施。
3.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行动来“维护”本国的重大利益,它就“有权”不受国际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有权”违背自己依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自行其是,我行我素。这种权力,就是美国的“主权”,就是美国在任何国际“权力分配”过程中始终保留在自己手中的美国“主权”!
一言以蔽之,根据以上“美国信念”来签署和批准《WTO协定》,美国在接受和参加WTO这一全球性多边主义的贸易体制之后,仍然“有权”继续推行其单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
杰克逊教授所论证的这种美国“主权”信念,在当时美国的“WTO赞成派”中具有代表性。经过数月的全国性“主权大辩论”,这种“主权”信念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占了上风,终于促使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在1994年11月29日和12月1日分别以288票:146票和76票:24票相继批准了《WTO协定》。
回顾和揣摩美国这场“主权大辩论”的前前后后,人们不难领悟到以下两点:
第一,汉金教授的主权观与杰克逊教授的主权观,貌似相反,实则相成:原来两位教授的用词遣句是各有所指:汉金教授主张应予“废弃”的主权,乃是专指不愿臣服于超级大国的弱小民族的主权,因为它们总是带着主权这面义旗,抵制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杰克逊教授主张应予保护的“主权”,乃是专指超级大国美国自身的“主权”,因为打起“主权”这面堂皇的大旗,恰恰可以用来遮盖和掩护美国既得的霸权,从而抵制国际条约义务、国际行为规范和国际行为准则对美国的约束。一句话,两位美国教授对“主权”一词的看法确实是一对矛盾:汉金的“废弃论”,乃是针对弱小民族主权的进攻之“矛”,而杰克逊教授的“保护论”,则是遮掩美国“主权”即既得霸权的护卫之“盾”,真可谓功能不同,各有妙用。看来,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事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于此又是一大例证。
第二,由杰克逊加以阐释论证的上述美国式主权“信念”,即参加WTO这一全球性多边体制之后,美国仍然“有权”不受多边主义的约束,仍然“有权”继续推行其单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云云,乃是美国国会当初终于批准《WTO协定》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乃是:美国参加WTO之初就已确立的既定方针和行动指南。可见,贯穿于上述这场“主权大辩论”全过程的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首度大交锋的结局,乃是前者的胜利,后者的败北!美国参加WTO之后,之所以不断地用美国的单边主义阻挠、冲击和破坏WTO的多边主义,其最主要和最新的思想理论根源,盖在乎此!
三、美国单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的第二次大冲击:“301条款”争端(1998~2000)
“301条款”一词屡屡见于中外报端,人们耳熟能详,这是“美国贸易代表”频频挥舞的一根用以威胁和压服外国政府贸易对手的“狼牙棒”,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经济霸权。它原是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Section 301),其后几经修订,扩充了内容,共计10条,习惯上仍统称为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以下沿用此习惯统称),其文字相当冗长,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确认外国的某项立法或政策措施,违反了该国与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或虽未违反有关协定,但却被美国单方认为定“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以致损害或限制了美国的商业利益,美国贸易代表便有权不顾国内其他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准则作何规定,径自依照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凭借美国经济实力上的强势,采取各种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以迫使对方取消上述立法或政策措施,消除其对美国商业造成的损害或限制,或提供能令美国官方和有关经济部门感到满意的赔偿。(注:See:Trade Act of 1974 § 301, 19 U.S.C.§ 2411-2420(1994);并参见张玉卿、关越:《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载于《国际贸易》,1992年第6—9期;杨国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7页。)
比较起来,“301条款”与前述“201条款”有迥然相异的法律功能,却又有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的立法特色。一方面,就其法律功能而言,“201条款”的主旨和效应,在于充分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及其国内市场的“高度安全”,使其免受外国进口产品的强劲竞争;“301条款”的主旨和效应,则在于保证美国产品能够长驱直入和充分占领其他国家和国内市场;前者是用以保障美国本国市场的坚壁和高垒;后者则是用以攻入他国市场的坦克和大炮。另一方面,就其立法特色而言,“301条款”与“201条款”相同,在实质上和实践中,都是在维护美国国家经济“主权”这一大纛下在全球推行美国经济霸权,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置美国已经承担的多边主义国际义务于不顾。
1995年1月《WTO协定》正式生效后,美国果然按其在“主权大辩论”中得出的上述“结论”行事:既参加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享受其他成员给予美国的各种权利和优惠;又继续推行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和法律,享受其自私自利、损人肥己的特权。实践证明:美国的这种做法,在某些场合,确实达到了它“左右逢源”的预期目的。
但是,在另一些场合,美国上述左右逢源的盘算却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商战和论战,使美国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其典型之一,就是1996年至2000年绵延长达四五年之久的“美欧香蕉贸易争端”(注:See:Reports of the Panel.European Communities-Regime for the Importation.Sale and Distribution of Bananas-Recourse to Article 21.5 ( Separately) by Ecuador & by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T/DS27/RW/ECU; WT/DS27/RW/EEC.) 案以及由此导致的“欧美‘301条款’争端”案。(注:See:Report of the Panel, United States-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ereinafter " ROP" /DS152) , WT/ DS152/R, 22 December, 1999.(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dispu-e./wtds152r.doc) .)
鉴于美国在《WTO协定》正式生效,DSU/DSB多边性争端解决机制正式开始运作之后,仍然继续依据其国内立法“301条款”,一再对WTO的其他成员实行单边主义的威胁和报复,并且屡屡得逞或“奏效”,欧共体决定针锋相对,予以反击。1998年11月25日,即在美国动用“301条款”单方宣布即将对欧共体采取报复制裁措施以迫使欧共体让步之后十余日,欧共体向DSB提出要求与美国磋商谈判,以解决《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问题。接着,又在1999年1月26日要求DSB正式成立专家组,审理此案。显而易见,欧共体此举乃是“开辟第二战场”,反守为攻,从“美欧香蕉案”中的“被告”,变为“301条款案”中的“原告”,把原案中气势汹汹的美国推上了新案的被告席。
如所周知,不少国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吃过美国“301条款”的苦头。此次由欧共体牵头,一呼多应:巴西、喀麦隆、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中国的香港地区、印度、以色列、牙买加、日本、韩国、圣卢西亚以及泰国,先后纷纷要求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身份,参与本案的磋商谈判和专家组的审理程序。如果欧共体以其15个成员国计算,则连同诸多第三方,使本案审理过程实际上形成30多个WTO成员共同“声讨”美国“301条款”的局面。
这场由《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引发的WTO众多成员间的对垒和论战,突出地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国经济主权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新争斗;其中既主要体现了全球经济霸主与其他经济强国(注:含本案“原告”欧共体成员德、英、法、意四强国以及“第三方”日、加两强国。) 之间在经济主权问题上的大火拼,也涵盖了众多经济弱国与全球经济霸主在经济主权问题上的新较量。
从双方实力对比上说,似可称之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这种局面,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审理本案的专家组,则可称之为“处于两大之间”。
本案专家组在1999年3月31日组建成立之后,经过长达约9个月的审理,于1999年12月22日向各方当事人签发了冗长的审结报告书,并呈交DSB审批。其中主要认定内容和裁断结论是:(注:See:ROP/DS152.pars.7.37—7.33; 7.109—7.112; 7.126, 8.1, supra, WT/DS152/R.22 December, 1999.)
1.《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法律措词用语(statutory language),虽未强制美国贸易代表必须在DSU多边审理程序终结以前单边地作出美国权益已经受损的断定,却也并不排除美国贸易代表在上述审理程序终结以前作出上述断定。换言之,这些法律措词为美国保留了(reserves)径自采取单边主义措施的权利。因此,这些措词用语至少可以作为“初步证据”(prima facie),证明美国的“301条款”违背了DSU第23条关于“加强多边体制”的规定。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专家组基本上赞同和接受了欧共体方对美国“301条款”的指控,批驳和拒绝了美国方作出的抗辩。
2.但是,专家组又认为:仅凭初步证据,还不足以最终确认美国已经背弃了《WTO协定》的各项国际义务。除了上述法律文字措词外,还应当综合考察美国国内的“体制因素和行政因素”(i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elements),才能作出全面的认定。
专家组所称的“体制因素和行政因素”,主要是指1994年9月间“主权大辩论”之际由美国总统提交美国国会的《政府行政声明》(Stat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简称SAA)。专家组认为:(1)该SAA是由美国总统连同美国实施《WTO协定》的国内立法即《乌拉圭回合协定法》草案,一并提交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的,它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2)该SAA中明确规定和承诺:美国贸易代表“将会”(will)(注:在英文法律用语中," will" (将会)一词是个软性的、任意性的、模棱两可的助动词(auxiliary verb)。它迥异于 " shall" (应当、必须)这个硬性的、强性的、必须遵照执行的助动词。因此,对美国贸易代表说来,SAA中列举的4点做法并非必须遵照执行的指令,并非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并无任何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本案专家组成员谅必都是既精通法学、又精通英语的饱学之士,他们把美国AAA中所声称“将会”做的含糊表态解释为美国当局作出了“保证”,显然并非出于对英文中" will" 一词的误解,而是有意加以曲解。——详见下引陈安论文《世纪之交围绕经济主权的新“攻防战”》,第120—124页。) 依据DSB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庭的认定结论,断定美国的有关权益受损,这就意味着在DSB审议通过上述认定结论以及DSU审理程序终结以前,美国贸易代表径自断定美国权益已经受损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已被“取消”了(curtailed)。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专家组完全赞同和接受了美国代表就“301条款”争讼问题提出的抗辩,拒绝和驳回了欧共体代表提出的指控。
3.基于以上理由,本案专家组在其审理结论中认定:欧共体指控的《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各点,并不违反WTO体制中DSU以及GATT1994的有关规定。
4.以上结论,是以美国政府当局在前述SAA声明中针对WTO/DSU体制所作的各点“承诺”和“保证”(undertakings, guarantees)作为基础的。因此,一旦美国政府当局或美国政府的分支机构背弃了(repudiate)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取消了这些承诺和保证,则上述结论中作出的各项认定就不再继续有效。相应地,《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现行规定就违背了DSU第23条关于遵循多边体制的国际义务,从而会(would)使美国因此承担“国家责任”(State responsibility)。
综观本案专家组在其审结报告中作出的冗长论证以及上述认定和裁断要点,可以看出:专家组不但未能切实遵照DSU第11条规定的职能和职责,认真审查美国“301条款”这一霸权立法,追究美国在1995年1月WTO体制正式运作之后仍然多次对WTO其他成员采取单边主义威胁的霸权实践,鲜明地裁断其中的大是大非;反而把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内容充满自相矛盾、毫无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前述“SAA”行政声明,任意“拔高”,美化为美国作出的“承诺和保证”,并鼓吹什么对于美国总统在其中作出含糊其词的空言约许,“可予以信赖”。简言之,这份审结报告的论证“特色”是:在“两大”之间,依违两可,双方讨好,八面玲珑;对美国“301条款”这一霸权立法及其霸权实践,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曲为辩解,加以袒护宽纵。因而漏洞和疑窦甚多,留下隐患不小。)(注:对本案审结报告的评析,详见陈安:《世纪之交围绕经济主权的新“攻防战”》(全文约4万7千字),第四至第八部分,载于《国际经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难怪国际上已有学者对这份审结报告作出了这样的总体评价:“它讨好了双方,至少给双方都保全了面子”;“‘美国301条款案’专家组的审结报告在政治上是很精明圆滑的(astute),但其法律根基的某些方面,却是破绽百出的(flawed)。对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今后的发展说来,这份审结报告所具有的政策方针性含义,令人产生了严重的关切和忧虑。”(注:Seung Wha Chang ( Korean) :Taming Unilateralism under the Trading System:Unfinished Job in the WTO Panel Ruling on United States Sections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ereinafter " Taming Unilateralism" ) ,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l.31, No.4, 2000, pp.1156, 1185.)
专家组的审结报告在1999年12月22日发布之后,“原告方”欧共体与“被告方”美国均表示不再上诉,但其各自的“说词”却体现了“各取所需”和不同的“精神胜利法”。
美国贸易代表公署抢先在12月22日当天即发布号外“新闻公告”,宣称美国已经“胜诉”:“WTO的解决争端专家组已经驳回欧盟提出的指控,确认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301条款’完全符合WTO体制”;并且得意洋洋、霸气十足地扬言:美国的“301条款过去一向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强制实现美国国际贸易权益的基石(cornerstone)”。(注:Press Release by the Office of the U.S, Representafiv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ress Release No.99-102, WTO Panel Upholds Section 301, par.1 ( Dec.22, 1999) .http://www.ustr.gov/releases/1999/12/19-102.html.) 但是,美国的“胜利”说词避而不谈上述认定的前提条件和保留条件(即上述认定的第4点),显然有随意“阉割”之嫌。
紧接美国上述《新闻公告》之后,欧盟贸易专员帕斯科·拉梅(Pascal Lamy)于翌日即12月23日也发布了号外“新闻公告”,宣称:“欧盟满意地注意到WTO专家组现已公布‘301条款案件’的审结报告”,它“对欧盟、对多边体制都是上好的结果”;“总的说来,这是多边体制的胜利。……任合一方都不能自称凯旋班师,因为,尽管‘301条款’这一立法仍可在卷未废,但本案专家组已予澄清:它只能在严格遵循WTO体制规则的条件下才可以用来对付WTO的其他成员。令我高兴的是美国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必要的承诺(the necessary commitments)”。(注:Press Release by the EC, No.86/99, WTO Report on U.S.Section 301 Law:A Good Result for the EU and the Multilater al System ( Dec.23, 1999) , ( http://www.insidetrade.com) .) 但是,这一“胜利”说词却避而不谈欧共体一方原先的主要诉求,即通过DSB的处断从根本上否定美国“301条款”这一霸权立法,远未实现。(注:由于本案双方均未上诉,DSB遂于2001年1月27日正式通过了本案专家组的审结报告。但欧共体依据《WTO协定》第16条第4款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每一成员(在本案中特指美国)应确保其本国的一切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完全符合WTO各项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则显然被搪塞、绕开和搁置了。) 因此,所称“多边体制的胜利”,在颇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甚至只是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301条款”案争讼双方最终打成“平手”,似乎不分胜负,美国的单边主义与WTO的多边主义,似乎可以在WTO体制中“和平共处”,(注:See:supra, Taming Unilateralism..., pp.1224-1226.
韩国学者Seung Wha Chang在上述论文中指出:本案专家组所作的裁断,不认真审查1994年美国当局在SAA中表述的自相矛盾的立场,不认真审查1995年《WTO协定》生效后美国在若干具体案件中背弃WTO义务的所作所为,却完全采信了美国的抵赖说词;完全信赖美国代表在审理过程中的“保证”表态。所有这些,都将给WTO/ DSU的争端解决机制带来危险。这些评论,确实颇有见地。但是,作者在文末却特地声明:他撰写该文的目的,不是代表美国贸易对手指责美国的“301条款”,而只是敦劝美国今后不要再滥用“301条款”。作者声称美国的“301条款”与WTO的多边贸易体系可以“同时并存、和平共处”(coexist);WTO需要美国充当“领袖(leader)”才能保持其多边贸易体系,等等。这些“善良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某种糊涂与天真:希望通过规劝,让虎狼改荤吃素;期待以薄荷甘草,根治霸权顽症。)但是,从深层次的本质上看,WTO/DSB在本案裁断中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301条款”霸权立法,竟然显得如此软弱、姑息和无奈,则不妨说实际上乃是WTO多边主义的一次大挫败。因此,随后在WTO体制内美国经济霸权与各国经济主权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美国单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的冲击,以及两者之间的较量,不可能就此止息。
果然,就在“欧美‘301条款’争端案”的轩然大波于2000年1月底平息之后,不到十五个月,即2002年3月初,美国又挑起了前文所述的“欧美‘201条款’争端案”。
四、几点结论
如果把前文所述2002~2003年的“201条款”争端,与美国1994年的“主权大辩论”以及1998~2000年的“301条款”争端,联系起来,加以宏观的综合考察,则可以说,2003年11月结案的上述“201条款”钢铁进口争端,乃是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的第三次大冲击,乃是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第三个大回合。尽管在这第三回合的交锋中,美国的单边主义以“败诉”告终,但美国在2003年12月4日发表的“总统声明”中,不但对其已经实行了21个月单边主义“保障措施”给其他国家从事钢铁生产和钢铁贸易的对手造成重大损失,装聋作哑,不作任何检讨,反而进一步公开宣称:美国今后仍将继续“执行我们自己的贸易法律”,并且将进一步强化针对外国进口产品的“监督措施”。(注:See:President' s Statement on Steel, at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12/20031204-5.html;并参阅:《美国取消保护性钢材进口关税,同时实施预警系统》,2003年12月5日,中国日报网站,http://www.sina.com.cn;《商务部发言人崇泉就美国撤销钢铁保障措施发表谈话》,2003年12月5日,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 gov.cn/atricle/2003 12.) 其语调、语意与当年“301条款”争端案审结后美国贸易代表在1999年12月22日发表的前述公告,同出一辙,足见美国在此次“败诉”后,对受到全球诟病的本国单边主义霸权立法,毫无改弦更张、弃旧图新之意。
综上,不难看出:第一,十年来上述三大回合交锋的具体时间、地点和表现形态虽各有差异,但其中的法理冲突,则是同出一源的,即都是美国经济霸权与他国群体经济主权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也都是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之间的原则大碰撞。
第二,上述“201条款”争端案中WTO多边主义的“初度小胜”,其影响力和效果显然只是相当有限和不稳定的,因为祸根仍在,病根未除,美国基于其特有的“主权”信念在参加WTO之初就已确立的既定方针和行动指南,始终如一;美国的霸权积习及其单边主义霸权立法依然“健在如恒”,并未受到丝毫损伤,从而,任意挥舞“301条款”、“201条款”之类大棒为所欲为的霸权顽症,仍然可能随时复发。今后在WTO体制内美国经济霸权与各国群体经济主权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仍将时伏时起,难以止息。套用一句中国古谚,可谓“庆父不去,鲁难未己”。因此,善良的人们不能不经常保持清醒,增强忧患意识,随时谨防美国单边主义大棒之卷土重来的再度肆虐。
第三,“201条款”争端案中WTO多边主义之初度小胜,端赖与美国对垒的22个主权国家,敢于和善于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经济主权,及时开列“报复清单”、采取报复措施,并且及时联合起来共同把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推向WTO/DSB的被告席等等,通过诸如此类的反击措施,对经济霸权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注:参阅:《中美钢铁贸易战中方胜诉》,《贸易争端:政府力量不可忽视》,载于《深圳商报》2003年11月12日,第B2版。) 反之,如果不坚持经济主权,或忽视经济主权以及群体经济主权这一武器的充分运用,则面对经济霸权的横行与肆虐,经济实力上的弱者势必无以自卫、自保,即使是小胜也不可得,更遑论积小胜为大胜,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由此可见,国内外一度相当“时髦”的理论,即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经济联合国”WTO正式运转之后,有关国家经济主权的原则和概念应当日益“淡化”、“弱化”云云,此类说词,至少是不够清醒的,也是很不可取的;至于经济主权“过时”论云云,则显然是居心叵测的理论陷阱,对此,不能不倍加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