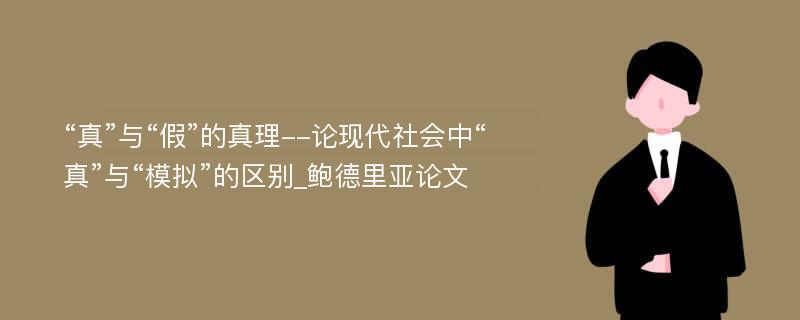
“真”的真实与“假”的真实——论现代社会中“本真”与“仿真”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实论文,本真论文,现代社会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是西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不仅有诸如启蒙、审美、时间、历史、信仰、现代化、现代主义等宏大主题,还包括许多像速度、日常生活、怀旧、真实、距离等与现代人的世俗生活非常切近的微观主题。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标志是个体的生成,现代性的主体是人。因此,研究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种种体验、感觉、情绪、心理、价值等问题,通过研究这些问题来探究现代性的实质和后果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上述诸多与现代性相关的主题,我们或许可以确定“真实”这个概念是至关重要的。真实是人类的生存依据,也是人类精神领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等方面合法可信的前提。然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人们对于“真实”的认识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并且这一变革也引发了现代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
我们知道,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有两个与“真实”观息息相关的概念:一为本真性(authenticity),一为仿真(simulation)。这两个概念的核心词都是“真实”。真实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异或变形恰恰是通过从本真向仿真的转折而实现的。那么,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又是什么?
一、原创的与摹仿的
本真性的提法最初是出现在音乐领域中的。19世纪之前,除圣乐演奏之外很少有其他的音乐演奏,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音乐篇章的概念被作品(work)的概念所取代,自律、完整和包容性的艺术作品开始形成,音乐演奏也变得丰富起来。本真性的问题也由此开始引起了音乐理论家们的关注。所谓本真性,其最原初的意思就是指对作品的表演要符合作者的本意,它是介于原作和表演实践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主要针对古典音乐、芭蕾和交响乐,而不适用于爵士乐和戏剧。迄今为止,讨论本真性要考虑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本真性是否可能?第二,是否必须要用到作品形成时的特殊乐器进行演奏才能达到本真的效果?第三,是否必须遵循作者所处时代的习俗惯例?第四,如何跨越作者的指导建议和演奏者的实际表演之间的鸿沟?第五,当原作缺失时,怎么处理原作、表演和表演的表演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六,音乐作品的风格、流派对本真性的形成确定有何影响?第七,作品本身能否被独立考虑?它在作者和表演者之间扮演了何种角色?第八,本真性是否值得发扬?第九,表演者的动机在本真性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等等①。
从音乐对本真性概念的阐释来看,本真性是一个非常类似于作者身份的问题,而用解释学的理论来分析它,又可以牵涉到真实(客体真实和主体真实)、意图和意图谬误之间的复杂关系,这说明本真性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理论的弹性。如果把它的原初意义扩大到文学艺术的范围,或许可以笼统地说,本真的就是原创的,与仿造的或摹仿的相对。在现代艺术史上,无论是音乐、绘画、建筑、舞蹈、雕塑,还是戏曲或影视文学等别的艺术种类,都要涉及到对摹仿、表现甚或对赝品的争论,这些都足以说明本真性是艺术理论中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仿真则不同。这个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用以分析后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一个术语。它不是的德里亚的首创,却被鲍德里亚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鲍德里亚在重述博尔赫斯那个关于地图和国土的寓言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地图在先”的原则,他说:
今天的抽象之物不再是地图、副本、镜子或概念了。仿真的对象也不再是国土、指涉物或某种物质。现在是用模型生成一种没有本源或现实的真实:超现实。国土不再先于地图,已经没有国土,所以是地图先于国土,亦即拟像在先,地图生成国土。如果今天重述那个寓言,就是国土的碎片在地图上慢慢腐烂了。遗迹斑斑的是国土,而不是地图,在沙漠里的不是帝国的遗墟,而是我们自己的遗墟。真实自身的沙漠。②
这其中就谈到关键的概念——拟像(simulacrum)和仿真。
在鲍德里亚的理论系统中,仿真与拟像是一组互文的概念。仿真(也可译作模拟)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是控制现实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目前历史阶段的主要生产方式,意味着符号(或象征)对另一对象的模拟仿造,“一切现实都被符号仿真的超现实所吞噬”③;而拟像是个名词,也可译作仿像,是仿真的产物,是代替原本及其再现客体而组成社会的形象和符号系统。这两个概念反映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后现代文化的“表征危机”(赵一凡语)。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或形象要经过四个发展阶段:
形象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
形象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
形象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席。
形象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是其自身纯粹的类像。
……在第四个阶段,形象不再从属于外表序列,而是进入了仿真序列。④
显然,这里的仿真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富有自主性的生产逻辑,它可以不与现实或真实发生联系,而是自我复制与自主生产,它纯粹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行为,用以实施摹仿“真”的真实与“假”的真实。
粗略地比较本真与仿真,前者的中心是“真”,而后者的中心是“仿”。从本真性到摹仿,再到机械复制,最后发展到符号现实,借用鲍德里亚自己的说法,其变异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⑤。
二、现实的与符号的
从关于本真性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真实性是本真性最基本的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真实性决不等于本真性。相对而言,真实性是一个古已有之、较多适用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词,本真性的内涵在人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和美学等领域的扩展却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才得以完成的,而恰恰是后者才真正构成了本真性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所独具的理论张力。所以,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重谈本真性才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
本真性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态大概包括四种。
第一,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本真的也即完整的和原生态的,与被遮蔽的、被表现的、被想象的或被主观理解的,或片面的和派生的不同。拿《红高粱》来说,本真性的东西是唯一的,即自行放置在遥远的时间之流中的历史本身,莫言的小说原创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都是非本真的,无论其中揭示或印证了多少与切实发生的历史完全吻合的内容,它们都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文本”,是被想象和表现出来的某一部分历史内容。尽管“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⑥。
根据历史学家萨林(Sahlins)的说法,“文化的每一项复制都是一次改变,把当前世界和谐地组织起来的各种范畴在实践中总会吸收一些新的经验的内容”⑦,无论是小说家以文字的方式“复制”历史,还是影视艺术家以图像的方式“复制”历史,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彼时彼刻的历史真实,这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历史与历史理解之间的差距。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的,“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开来”⑧。一方面,一向被视为真实客观的传统史学观念已遭到了来自文学和修辞学最猛烈的质疑和颠覆,因为文字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有所选择、有所裁定的主观行为,“历史学家远非依赖他们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的自我以外权威的陈述,他们是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思想相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⑨正是在此基础上,新历史主义学家才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就是把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描述为对事实的“文本建构”,认为前者与小说家、诗人一样从事的都是虚构故事的工作,也要遵循一定的流派和文体规则,是“历史文学作品”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小说和电影本身也一样包括社会记忆和历史重构的双重内涵。因为艺术创作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行为,它不可避免地要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等多种因素发生关联,当艺术家以个体的身份进入历史、解读历史和开放历史的同时,也意味着原本复杂和完整的历史真相被遮蔽、被筛选了,我们所见证到的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
第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本真的也即本土的和民族的,与异域的相对。在早期人类学中,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本真,其主要标准就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受到了外国的殖民统治或传教士的影响,假如这个社会还处于一种太古的、未受玷污的状态,那么它就是本真的。詹姆斯·科林伍德称之为“人种学的现在”,意指一种静止的、凝固在时间中的社会图像,主要用来与始终变化的西方文化形成对照。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当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实践标准之后,本真性就更被当成了人类学家的一个关键目标,以求找寻到对外国文化的一种真实的理解。
再借电影《红高粱》来谈。在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文本”的基础上,外国影评专家对它的理解就要比张艺谋本人的理解较少本真化,因为对前者而言,《红高粱》所揭示的世俗风情、社会习俗、传统惯例和文化精神都是一种异己的东西,他们本身是与这种异己的东西深深隔阂的,他们只有把自我的生存体验和本民族的文化阅历参与合并到异己文化的本真性中,才有可能获得对异己文化的理解。使此理解活动顺利进行下去的前提条件是:被理解的事物与被表现的文化内容之间有某种相容性。而即使这种理解能够达成,其实质也是在一个虚设的语境中本土民族精神的“异域投射”,已经和必然的是一种“二手”的本真性。换句话说,本土意义上的本真性必然存在着“意图谬误”,必然是一种“影响的误读”。值得我们特殊关注的是,异域情调在现代性语境下不仅指对另一种异质文化的本真感受,还包括在同种文化形态下对熟悉但却遥远的事物的陌生化体验,而后一种异域情调实际就是传统的复兴。比如《红高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原始生命力和黄土高原上颠轿、酿酒、祭天等民俗,不只是对外国人,对生长在远离黄土高原的其他中国地区、深受都市文明浸润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也是极其陌生和充满神秘魅力的,他们观看《红高粱》也是以一种“他者”的身份,也要超越时间对历史的蒙蔽,也要经历两种异类的地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和磨合融会。又如《花样年华》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克制而隐忍的爱与忠诚,以及女主人公在一部影片中连换28身旗袍,同样激发了现代人的怀旧之情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向往。道理是一样的,在现代人的理解范围内,两部影片都是现代文明下的“异类”,因而它们所象征的文化也就是本真的。
第三,从哲学的角度看,本真的也是存在的澄明状态,它的对立面是异化的、沉沦的和不自明的状态。这种提法主要取自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分析。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我们的地位、家庭、文化等方面获得一个身份,我们的生活价值和目标就取决于对此身份的定位、认同、反思和批判,“本真的个体,已经从他们的日常关注中被唤醒,对他们的生命负有责任,因而也选择自己的身份”,而本真性就是这些人“理解自己生命的存在结构”的状态。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在此在宿命的沉沦与被抛状态中,人只能作为常人而存在。常人是以非自立状态存在的,因而此在也以非本真状态存在。此在被异化了,这使得某种程度上的非本真性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海德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对价值的批判性估价是以非批判地接受它们为先决条件的,实际的生命的必要条件使非反思性的行为优于批判性的深思熟虑”,因此,本真性成了一种不可能实现也无法通过“堕落的”个体的自身努力来争取的状况。海德格尔最后指出,我们只能在过去和历史中寻找自我存在的根据,回到我们自身,通过对存在的回顾保持一种本真生存的可能性。
第四,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本真的也是本能的、自然的和和谐的,与冲突的和文明的相对。这一点不仅在第二和第三点中已经有所显露,而且正是从本土到异域、从本真到异化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本真性一词在美学领域内形成对立范畴的原因,即异域和异化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在众多美学理论中,对本真性的讨论体现在对自然界的热爱、对以古希腊精神和艺术为象征的美的理想的尊崇、对以艺术为代表的感性世界和美的张扬、对以童年为代表的人的本原状态的留恋,等等。
相比而言,仿真作为一种逻辑或行为,对其内涵的界定则要简单得多。还是看回鲍德里亚的解释。在鲍德里亚看来,运用仿真原则制造拟像,有别于以任何形态出现在历史上的摹仿及表征(或再现)。归纳起来,差别有两点。
第一,参照物不同。摹仿是对原本的摹仿,不但必然存在着一个原本,而且摹本与原本之间的相似性(尤其是外形的相似性)是衡量摹本价值大小的关键依据。甚至在柏拉图看来,摹本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通过观看摹本获知任何有关原件的新知识,相似性既是再现艺术唯一的手段,也是它获得合法性存在的唯一理由。詹姆逊在比较摹本和仿像之不同的时候也说:“摹本的价值是从属性的,而且摹本帮助你获得现实感,使你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⑩也即摹本与原本的相似性永远也无法取消二者之间的地位差距,由于原本的独一无二性,原本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
而仿真却截然不同。仿真就是把没有的东西假装成有,把不在场的呈现为在场的,它实际暗示的是被模拟之物的缺席状态,也即摹仿没有原本的东西。看起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缺失就意味着每个拟像都是新的,都能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新信息和新知识,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惯常拥有的对原本的实体性想象已被纯粹的、无从取证也无可驳斥的理念取而代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未始不是对柏拉图建基于理念之上的摹仿说的“戏仿”。所不同的是,这种戏仿已经完全由一种显现和再现变成了一种策略性的操作。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或译为超真实),它既非实存的客体,也非再现的客体,而是自身无限重复和复制的东西;它既非现实或现实的对照物,也不根源于现实,而是自我指涉的符号世界和形象系统,是一种新的真实。
第二,生产方式不同。虽然摹仿强调摹本和原本在视觉外观上的相似性,但只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对原本的再现。尼尔森·古德曼认为,相似只是“对一幅画的视觉经验和物体/对象之间的相似”,而不是“所画之物与原物体之间的相似”(11),意即在从原本到摹本的过程中还必须有艺术家个体的视觉经验参与,从而使图画不是看起来像自然的样子,而是像自然被画家通常所画出来的样子。绘画及观画就是一个“画画家看到的东西”与“看画家画出的东西”的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主观精神和人格化活动,是选择和呈现而不是接受和复制的过程。
仿真与此相反,因为仿真没有可以信奉和依据的真理源头,因此拟像本身既是形象,也是幻象,它与任何现实无关,也与任何对现实的观念无关,它只是某种符号系统而已。这一符号系统是先于其自身的指涉物而存在的,鲍德里亚称之为“仿像的先在性”,实质上它不过“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即是说,是借助其操作性的双重性来延宕任何现实的运作,是一种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描述的机器,它提供了现实物的一切符号,阻止了一切变动”(12),逃避了想象物及其与现实物之间的区别,彻底颠覆了指涉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才会宣称,海湾战争不过是一场新闻事件,也许它并未真正发生过。沃尔夫冈·威尔什声称:“‘你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但你从未看到你不应看到的东西。你不可能确定你看到的东西是现实的馈赠,还是电视频道的礼物。”(13)鲍曼也不得不承认:“‘新闻’、戏剧和游戏之间的区分界线已变得日趋模糊,在这个过程中,现实正演变成诸多形象之一。”(14)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知,仿真与摹仿之间最重大的差异就是前者改变了我们对真实性的定义。真实不再是客观事实或心理事实,它也不等于真理,它只是一种“可以被对等地再现的东西”,“可以被复制的东西”,或根本就是“总是已经被复制出来的东西”(15)。“真实已经与理性无关,因为不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否定的事例来衡量真实。它只是一种操作的东西。
三、危机与救赎
通过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真性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昭示了现代文明的代价,与现代人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但问题恰恰在于,本真性只是现代人精神栖息的乌托邦,在现代社会中,它是必然缺席的。取而代之的甚至不是真实,而是“仿真”,是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现代人类生存的无奈的真相。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论逻辑来推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真实不再包裹在想象之中,它就根本不再是真实了。它是一种超现实。”(16)作为超现实的真实是依据人的记忆和指令模型得以创造的,它依据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这种突飞猛进带来的生活世界的扩张和人类感性经验的增殖。这必然会导致真实的不确定性和虚幻性。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但事实上,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是“具体可感”的。还拿海湾战争的例子来说。战争的缘起、进行过程乃至双方的战略战策都是媒介传导给我们的,当我们从屏幕上看到浓烟、士兵、枪炮和被战火吞噬的大海,听到有关战况的精确报道和战争专家对胜负伤亡的数量估计,我们无法不相信这场战争的真实性,即使没有亲眼看到它,我们也能够确定它发生在世界的另外一个地方。但是,鲍德里亚的真实观就是要让我们对此产生怀疑。
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海湾战争作为一个电视事件是真实的,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甚至电视报道也有可能是媒体的运作,持不同立场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完全可能使海湾战争的面目各异。即便我们确信海湾战争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我们看到听到的也已经成了被媒介再现、复制或操作的海湾战争。生活也是如此,通过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生活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拟像,通过抹去现实和想象、真与假、物质与观念等的分界来证实自身。生活也成了屏幕上的一个事件,人们凭借这一事件的吸引力、愉悦感、快感和美感来对待生活,媒介是唯一的操纵者和设计者,而媒介也充满了虚拟性和游戏性。它更像是一场审美的幻境,与其说这是把“生活向艺术学习”的唯美主义信条推进到安迪·沃霍尔的交换艺术符号的极致,把人变成机器的超现实主义戒律,不如说它已经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生活发挥到了超艺术的极致。
既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能把握的呢?本真性的消解已经使“真”的真实变得不可能了,而仿真术无懈可击的狡黠又令我们难以信任“假”的真实。当人类生存的基本依据——也即对于真实的基本诉求——被技术、媒介甚至理论作弄得歧义丛生时,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必然要陷入巨大的危机。自我的界定或定位都成了问题,因此难以保证自我身份的完整感和自身历史的连续性。这是传统的真实观被颠覆所带给现代人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创伤。
仿真世界对我们的视听冲击和真实信念的彻底颠覆不但使语言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败(这大概是20世纪后期以降“视觉文化转向”取代占据20世纪主流的“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马丁·杰伊称后现代主义是“视觉物的神圣化”(17),显然一语中的),而且也使怀旧承担起再度体验真实的使命蓬勃发展起来。鲍德里亚如是说:“当真实不再是以前的样子,怀旧便展现出充分的意义。关于现实的起源和符号的神话以及关于二手真理、客观性和确切性的神话大量繁殖。真理得到了攀升,生活体验得到了攀升,客体和实质已经消失的形象语言得到了复活。”(18)一厢情愿的怀旧就是要借助真实的回忆和虚幻的想象,赋予我们一种“似真似幻”的连续性和完整感,使我们的生活世界重新得以平衡。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拟像盛行的后现代语境中,怀旧也成了一种仿真行为,怀旧主体所消费的同样是关于过去的符号和拟像,怀旧的实质就是怀旧需求的具体化和这种需求的自我满足。这其中所蕴涵的最大深意就是“‘思考’的缺席”和“对自身视角的缺席”(19),即反思的缺席。它不仅使怀旧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对“旧”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的消费活动,而且通过消费趣味和消费趣味的符号及拟像膨胀了怀旧工业的可能性,说到底,怀旧也只是可能性之一而已,拟像的无穷无尽本身就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
仿真对本真的僭越既意味着危机(传统真实观的颠覆),又暗藏了救赎的可能性(仿真成为一种新的真实)。拯救来自于危险所在之处,当历史不能返身回转时,我们只能从危险处进入。也许正是它这种暧昧而复杂的特质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了新的活力。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动力所在。
注释:
①See Michael Kelly etc,eds.,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③⑤(12)(15)(16)(18)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66,p.120,p.167,p.167,pp.145-146,p.167,p.171.
④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70.译文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页。
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⑦转引于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⑧⑨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⑩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11)See Michael Kelly,eds.,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37.
(13)Wolfgang Welsch,Undoing Aesthetics,London:Sage,1997,p.85.
(14)Zygmunt Bauman,Life in Fragments,Cambridge:Blackwell,1995,p.150.
(17)See Martin Jay,Downcast Eyes: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French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p.544.
(19)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