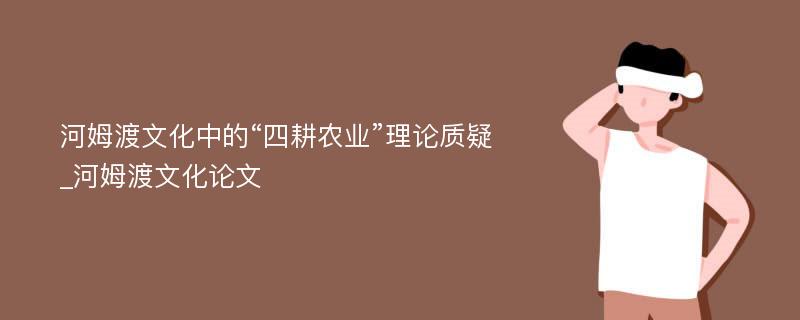
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河姆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及“河姆渡文化”的命名,不但证明了中华文明多源论的正确性,而且也使稻作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热点。前人研究认为:河姆渡遗址大量骨耜和栽培稻谷的出土以及大片房屋建筑遗迹的揭示,使“河姆渡文化”农业发展已经进入锄(耜)耕阶段的论点得到普遍接受,“河姆渡遗址的先民过着以耜耕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1]
而笔者参加“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发掘(1996年9-12月)以及田螺山遗址的部分发掘工作时(2004年5月),在田野注意到一些考古现象,遂对“河姆渡文化”骨耜是否作为稻田翻土工具、水稻是否达到成熟栽培阶段、定居是不是非要以农业为主等产生怀疑,并形成不同于前人的认识。
前人对“河姆渡文化”稻作的研究均集中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约7000-6500年前,原因是绝大部分稻谷和占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总数79.4%的骨耜均出土于该层,故本文对“河姆渡文化”稻作发展阶段的探讨也仅限定在第四文化层,这样可以避免用同一遗址的晚期发现物来解释早期考古材料。
一、“骨耜”用途新认识
“骨耜”由游修龄先生依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物而定名,它是由动物的肩胛骨制成,认为类似后来的木耜。[2] 从骨耜正中留有自上而下的浅槽及两侧各一长方孔与绑扎痕迹可知,河姆渡骨耜安有直向柄是不容置疑的。[1] 对河姆渡“骨耜”用途的认识,是阐释河姆渡文化稻作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所以探讨的人不少,众说不一。
以生产工具为依据,农业发展一般分为刀耕(踏耕)农业、锄耕农业、犁耕农业三个阶段。游修龄认为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骨耜”是插入土中作为发土翻地的工具,因此提出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处于犁耕之前,相当于“锄耕”阶段,然在河姆渡没有锄具,不称作“锄耕农业”,而是有了自己的发展形态,其耕地农具为骨耜,所以称“耜耕农业”。[2] 华泉认为把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耕具全部定名为“骨耜”是值得商榷的,因之,把我国农业的早期形态叫做“耜耕农业”也就失去了实际依据。[3] 汪宁生否认河姆渡“骨耜”为翻土工具,认为只能用于土壤表面,故认为是一种刀耕火种农业。[4] 黄渭金据骨耜加工使用痕迹提出已有翻耕农田、修整水田和平整农田等不同分工,其耕作方式为“踏耕”和“耜耕”并存。[5] 至今最流行的是“耜耕农业”说。
对“骨耜”用途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河姆渡文化”稻作发展阶段的认识。然而这个问题已讨论30年尚无定论,仍停留在推测阶段,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重要原因是没有获得考古学的支持,没有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研究史前工具的用途时,出土状况往往是重要的信息和线索。[6] 如河姆渡骨耜骨柄处所凿的横穿方孔,是否穿过一根小木棒以供足踏,开始也是议论纷纷[1][2][7],后因1977年河姆渡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时在第四文化层出土一件“骨耜”(T224④:175),其耜面正中保存有一段木柄的末端,横穿方孔部位则以十多圈藤条紧缚着木柄的末端,这一重要发现消除了横穿方孔用来安插脚踏横木的疑虑。[8] 至此,“骨耜”装柄的复原才得到大家的一致认识,这说明考古发掘出土的证据是最直接的。再如河姆渡的磨制石器,石斧是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材的,石锛用来刳木,石楔用来开裁原木,石凿用来挖凿木物件的凹槽和卯眼,这些工具的用途如此明了是它们都能依据石器刃缘的大小在木制器物上找到砍、削、凿的痕迹,因此它们的用途就不单单是推测而已,而是建立在事实证据的层面上,令人信服。那么,能不能找到“骨耜”使用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呢?
1996年我们在鲻山遗址发掘时,有一个现象让人费解,即发掘到具有干栏式建筑的文化层8层下时出现大量的灰坑、柱洞。[9] 它们不仅打破第9、10层,而且深入生土层(遗址发掘完毕,340平方米中共有120多个到达生土层,平均不到3平方米即有一个)。灰坑和柱洞坑口有圆形、方形,坑壁直而陡,许多深70-110厘米,有些灰坑四壁保留挖掘时工具留下的痕迹,如位于T3的H62呈长方形,开口8层下,打破9、10层和生土,长75厘米、宽50厘米、坑深110厘米,四壁陡直,坑壁留有明显的11-12.5厘米宽的工具印痕;位于T5的灰坑H61开口8层下,打破9、10层和生土,坑口方形折角,长86厘米、宽64厘米、深90厘米,坑底有明显工具印痕;位于T1的灰坑H71开口于9层下,呈圆角方口,四壁平直,深68厘米,四壁遗留工具痕迹。
这些印痕是何种工具所为?从灰坑四壁陡直、坑深可达110厘米来看,河姆渡人手臂没那么长,用手拿石器直接挖掘不可能达到如此之深,即使人趴在地面也够不着,必须借助长直柄工具才能挖成如此之深且四壁笔直的坑。河姆渡遗址第四层的工具中,石斧、石锛等都是安装钩状柄的,而且绝大多数石斧刃部宽小于7厘米、只有极少数大于7厘米,最大宽9.5厘米;石锛刃宽均小于5.2厘米;石斧和石锛刃部宽度与坑壁的工具痕迹不一致。只有“骨耜”(包括木耜和木铲)是安装直向柄的,而且坑壁痕迹的宽度落在“骨耜”刃部宽的变化范围内。
故目前有直接考古证据的,“骨耜”是用来深掘灰坑和柱洞的,和干栏式建筑密不可分。至于第四文化层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骨耜”?这说明地处沼泽区的河姆渡人要避免高温湿热,构筑房屋的需求比稻作还要高,同时我们看到了房屋建筑面积如此之大,柱洞、灰坑数量如此之多,需要大量直向柄的取土工具,“骨耜”的数量当然就多了。
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还分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相当或略早于河姆渡文化的出土材料,并把相关因子列成表1。从表中可知,骨耜仅分布在有干栏式建筑遗迹的宁绍平原,确实与干栏式建筑密不可分;属于半地穴式建筑的河南贾湖遗址则是以安有直向柄的石铲代替骨耜,作为半地穴式建筑挖土工具;而含有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的彭头山遗址,由于骨、木器的保存条件差,情况不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淮河流域有地面建筑的遗址均没有发现骨耜;杭嘉湖平原的罗家角遗址虽也发现四件由肩胛骨做成的“骨耜”,然其肩臼部中央没有穿孔,器身也没有一对穿孔,无法制成直向柄工具,与河姆渡的骨耜有明显的区别,显然定为骨耜不合适。
表1 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骨耜—水稻—建筑”关系分析表
遗址骨器保存水稻 建筑 年代
地区骨耜 北纬海拔(米)
名称 状况 特征 形式 (BP)
河姆渡[10-11]
好籼、粳、野稻干栏式 大量 7000-6500
29°58′ 1.1
(第4层)
长 罗家角[12] 好 籼、粳 地面少量(特殊) 7000-6100
30°37′ 5
江 (3-4层)
下 马家浜[13] 好 地面
无 6500-6000
30°43′
草鞋山[14] 好 粳、籼
?
无 6200-5900
30°22′ 3.4
游 (8-10层)
崧 泽[15] 不好粳多籼少地面
无 6000-5000
31°13′ 3
长 彭头山[16] 差?
地面、 ? 8200-7800
29°38′ 45
江 半地穴式 (相对5米)
中 33
游 八十垱[17-18] 较好
籼、粳、野稻 地面
无 8000 29°53′(相对2米)
淮河
贾湖[19-20]较好
粳、籼、野稻
半地穴式(石铲)
8300-7500
33°36′ 68
流域
龙虬庄[21] 好
粳稻 地面
无 6600-5000
32°50′ 2.4
那么“骨耜”能否用来翻土深耕、种植水稻?由于河姆渡遗址一带当时为沼泽区,遗址周围多为淤泥,土壤松软,砂砾石含量极少,我认为有可能做到,然目前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
二、稻谷综合研究结果与耜耕农业认识相矛盾
要分析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必须先搞清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关系以及对栽培稻内部分化的认识,这是本质问题,但以前被忽略了。研究表明,亚洲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在形态上可分为多年生型和一年生型两个生态型及存在着偏粳到偏籼稻的广泛变异类型(地理变异)。从遗传学角度,用44个RFLP(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标记对普野和栽培稻样品的研究后,也证实在核DNA分化上中国普通野生稻可分为原始普野型、偏籼型和偏粳型三种。普野的叶绿体DNA和线粒体DNA同样存在籼粳两种类型。[22] 对亚洲现生普通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同功酶研究比较后可以发现,中国和南亚普通野生稻在悠久的系统发育过程中均发生了籼粳分化。[23]
毫无疑问,亚洲栽培稻是由亚洲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那么野生稻与栽培稻之间的差别是否如多数人认为的已经达到生物种级分类水平?亚洲的普通野生稻(Oryza rufipogon)和栽培稻(Oryza sativa)虽在形态和生态上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作为分开的两个生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它们之间达到生殖隔离,不能杂交并繁育后代。可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分布于同一区域,能够杂交并繁育后代,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生殖隔离,故它们应属同一生物种[24],不符合另立物种的条件,栽培稻最多只能是野生稻种中的一个亚种。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栽培稻内籼稻和粳稻之分是不是亚种间的差别。日本学者加藤1928年把亚洲的栽培稻Oryza sativa,细分为印度亚种Oryza sativa indica和日本亚种Oryza sativa japonica。中国学者丁颖1949年把亚洲的栽培稻,定为籼稻亚种Oryza sativa hsien(相当于印度亚种)和粳稻亚种Oryza sativa keng(相当于日本亚种)。[25] 根据生物学命名优先法则,应该取消Oryza sativa hsien和Oryza sativa keng两个拉丁文名称,考虑到籼稻和粳稻的传统称呼,可以沿用中文名称。
对栽培稻这两个亚种的命名似乎已经承认两者是亚种间的差别,其实不然。亚种是种内个体在地理上和生殖上充分隔离后所形成的群体,它有一定的形态生理、遗传特征和地理分布,所以也称“地理亚种”。[26] 可我们看到的现代籼稻主要分布于热带平地和亚热带低地及其高温季节,粳稻主要分布于热带高地和亚热带的夏秋季节以及高纬地带。在云南高原区,可以观察到籼、粳的垂直地带分布特点:海拔1200-1750米以下为籼稻,海拔1900-2000米以上为粳稻,介于两者之间为混杂过渡区。[27]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陕西汉中现为亚热带北界的秦岭南坡,海拔800米以下为籼稻,而1000米以上为粳稻,800-1000米间为过渡带。显然籼稻和粳稻的制约因素是气候尤其是气温,它们在地理上出现重迭,没有发生地理隔离也就没有发生生殖隔离;它们之间仅仅出现垂直地带性分异,适应于不同的生态,属于气候生态型的差别;所以两个亚种的划分不太合适,应该是栽培稻的品种分化(籼稻和粳稻类型),或称栽培稻的两个变种更准确。当然,受气温的影响,纬度越高其粳稻的含量也越大。
基于这些认识,我们来考察河姆渡遗址稻谷的认定问题。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稻谷最先由游修龄根据形态特点定为栽培稻的籼稻稻谷[2],周季维判断为籼粳并存、以籼为主的原始籼粳混合群体。[28] 自那以后大家都在引用,似乎全是栽培稻。一直到汤圣祥等从河姆渡的81粒碳化稻中检出4粒具有普通野生稻特征(占5%),才知道当时的普通野生稻与原始栽培稻混生或近生,这表明河姆渡人也进行野生稻及其他可食植物的采集。[29]
植物硅酸体分析技术的应用,扩大了稻作研究的视野,然籼稻和粳稻鉴定的判别标准直到十多年前才取得突破,1996年才引进并应用于中国。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稻叶堆积物和土壤所做的植物硅酸体分析较早[30],故其得出的结论与谷粒米粒鉴定相反,即植物硅酸体鉴定出籼型21.6%-22.6%、粳型73.1%-74.4%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稻谷外稃双峰乳突的电镜观察和谷粒长宽比的研究均表明,河姆渡水稻处于“正在分化”的非籼非粳时期。[31]
以上从稻谷形态、植物硅酸体到外稃双峰乳突的鉴定结果,其共同点是河姆渡遗址稻谷存在籼稻、粳稻混合状态并有野生稻。从表1也可以看出早于河姆渡的河南贾湖、湖南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都是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混合,籼稻、粳稻分异的重要控制因素是气候(温度)而非人工驯化。我认为这些正是野生稻或原始栽培稻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以采集经济为主的体现。从生态上看,河姆渡遗址周围为沼泽地,只能适合于种植籼稻,用栽培观点无法解释当时河姆渡人跑到地貌部位较高、气温较低的山区种植粳稻,故只有采集才能把生长于不同地貌生态部位的稻谷聚集到居住地。因此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即使确定为栽培稻,它也只能处于驯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阶段,这与处于相当成熟的“耜耕农业”发展阶段的认定是矛盾的。
三、稻谷数量被夸大了
原始发掘报告明确“第一次考古发掘在十多个探方面积达400多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一层乃至多层,以芦苇类茎叶、稻草、稻谷、秕谷、谷壳、木屑碎渣及禾本科植物与少量动物遗骸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层,层中以木屑、秕谷、谷壳及植物茎叶最多,层层迭压,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不等,最厚者达70-80厘米。出土时稻秆、稻叶和稻谷与秕谷壳色泽如新,外形完好,有的连稻谷颖壳上的隆脉、稃毛仍清晰可辨,个别地方还出土有稻谷与茎叶连在一起的稻穗”。[1]
可有人依此推断“原先的厚度当在1米以上,假定平均厚度只有1米,其中平均有1/4为稻谷和谷壳,换算成稻谷当在120吨以上,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32] 我认为这一推断过于夸大,因为压实后的混杂堆积物厚度10-40厘米,最厚者才70-80厘米,怎么能都以1米厚度计算?
作为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的参加者,劳伯敏先生明确指出:“这些‘稻谷堆积’的成分,主要是一些仅有空壳的秕谷;完整的炭化稻谷数量较少,有些是烧焦了的;它们和稻杆、稻叶碎片以及大批尘屑等杂质混杂在一起,其底部还有大批以碎木片为主的木屑,组成了这层‘稻谷堆积’。”[33] 混杂堆积物中稻谷只占一小部分,这是发掘人员亲眼目睹的,绝不可能达到1/4的分量。
笔者在鲻山遗址发掘时也见到同样情况:该遗址1996年掘340平方米,共分10层,第9文化层总体特点为暗灰色粘土质细砂、细砂,植物枝叶含量高,并有木炭、木板、陶片、木器、骨器等,仅在探方T1、T4、T6、T11的第9层的局部部位见到已成黑色的稻谷混杂在木屑、稻草和芦苇中,数量不多,肉眼能挑出一部分,花半天时间用分析筛水选后从中挑出数百粒炭化稻谷和脱壳炭化米。[9]
显然,河姆渡和鲻山两遗址均未发现保存稻谷的窑藏或灰坑,稻谷都是与稻草和其他植物的枝叶呈层状、似层状共存,稻谷的含量仅是一小部分。故对河姆渡遗址第3-4文化层中稻谷含量应该有个客观的认识,不要用局部状况去估算整体,以致夸大了事实。
另外,河姆渡遗址前后两期共发掘2630平方米,可面积如此之大,仅在第四层发现9件用动物肋骨片制作成的收割工具——骨镰形器,没有石刀和石镰。再者,谷物是通过碾和捣去壳碎粒的,相应的工具是石磨和杵臼,可逐件考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收藏的砾石后,却没有发现专门的石磨盘[34];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中仅2件被定为木杵,有人推论有木杵肯定有木臼,只是木臼易腐烂,以致未能发现遗物。[35] 这种推论与事实不符,因为河姆渡第四层的埋藏环境极为优越,器物保存几乎达到完好无损的程度,出土时稻壳、葫芦都是金黄色的,木臼怎么会烂掉呢!显然是不存在或目前尚未发现木臼。收割和加工谷物工具的缺乏虽不能反映栽培稻或野生稻问题,但从侧面反映了稻谷作为食物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大。
四、稻作不是主要经济形态
河姆渡遗址两期考古发掘,在第四文化层中发现大量食余的果实,如橡子、南酸枣、菱角、芡实,尤以前两者为多,它们储存于灰坑中,保存完好,有的灰坑可见底铺芦苇席,内存成堆的橡子,其上再盖苇席,功能类同于窑藏。[8][10] 这些都是采集品,遗址中没有找到成堆稻谷的储藏坑,说明采集野果等数量不亚于稻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河姆渡遗址第4文化层出土有骨镞1079件、木矛42件,足见河姆渡人狩猎活动的频繁。狩猎的鸟类8种,主要是生活于沼泽芦苇地带的鹈鹕、鸬鹚、鹭、鹤、鸭、雁等;哺乳类达31种,如大型动物亚洲象、圣水牛、苏门犀、爪哇犀,凶猛动物如貉、豺、虎、黑熊等;遗骨遍布第3、4文化层各个探方,据不完全统计,仅鹿类下颌骨标本就有700余件,角的件数达1400多件。[8][10]
渔捞对象主要是淡水鱼类(鲫鱼、黄颡鱼、乌鳢、鲤鱼)、淡水蚌类和龟鳖类,尤以鲫鱼和乌龟最多,能区分出的乌龟个体达1570个。[8][10]生产工具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骨制、角制工具无论数量还是品种较之石器都占明显优势,这些都说明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文化遗物中缺乏捕鱼工具如鱼叉、鱼钩、网坠之类,原因很简单,河姆渡人面对的不是河流、池塘,而是沼泽地、芦苇荡,水体很浅,可以用带柄的骨镞射鱼、用徒手围捕。
6500-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与今日华南相似,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很难迫使河姆渡人从事复杂的作物栽培活动。当然,不可否认,人们在采集过程中对植物的习性和特点非常熟悉的情况下,也会自然演变成栽培植物,但这个过程相对会慢些。根据最佳觅食模式原理,人们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获,所以,大型动物在人类食谱中总是处于最高的档次,不管其数量多少,它们是狩猎采集者钟爱的食物;而植物特别是采集加工费时费力的稻谷,无论怎么丰富,营养价值如何高,在食谱中的档次就很低;只要有档次高的食物可以果腹,它们就不愿意去利用。有例子证明,中美洲人类对栽培作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的时间。[36]
因此,笔者认为当时河姆渡人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稻作农业为辅,在采集、狩猎、渔捞和稻作等多种经济并存中,稻作至多占经济比例的1/4。
河姆渡人无疑过着定居的生活,有一种认识是“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满足”定居条件,那么河姆渡文化稻作应该达到相当高的发展阶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认为食物供给是否充足是定居的必要条件,而要实现这一条件不一定非要发达的农业或以农业为主,攫取性经济社会在良好环境下也能做到这一点,其条件是有丰富的、取之不尽的狩猎采集和渔业资源。河姆渡具备了这个条件,河姆渡人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不能证明河姆渡人以稻作为主要经济形态。
上述表明,对河姆渡文化骨耜用途的新认识使得“耜耕农业”发展阶段说难于成立。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稻谷出现籼、粳和普通野稻组合,这是原始栽培稻的特征;河姆渡人采集、狩猎、渔捞和稻作并重,这是当时农业处于原始状态的特点;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高估了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