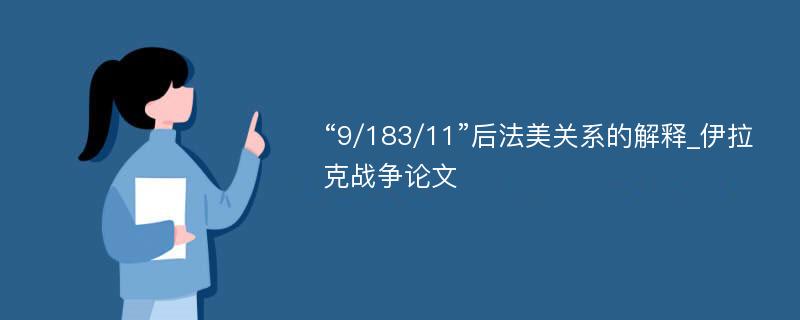
解读“9#183;11”后的法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美分歧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就开始在北约内部与美国闹独立。法国的这种对美离心倾向在戴高乐时代发展到顶峰。其时,法国不顾美国的压制和阻挠,执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发展独立核力量,改善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作为开时代风气之先者,戴高乐为法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以后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不管政治观点如何,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戴高乐的政策遗产,向美国的主导地位挑战。
时间并未弥合二者之间业已形成的裂隙。冷战结束后,法美非但没有尽释前嫌,反而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二者赖以结盟的战略基础也发生了动摇。迄至“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施,成型于二战后的美欧同盟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对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一重大问题上,以法德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公开了它们与美国的分歧。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大西洋两岸的根本文化和制度基础的动摇,美欧同盟关系开始走向死亡。(注: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Policy Review,Summer 2002.)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分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美欧之间仍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注:Philip H.Gorden,“Bridg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p.70—83.)如何解读这些矛盾的观点和看法?本文试图以“9·11”后法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例,探讨在当前美国反恐特殊时期,法美之间裂痕的产生与弥合过程,进而阐释美欧在“9·11”之后关系的新变化。
一、“9·11”后的法美关系:从弥合到裂隙再到修复
美国总统布什2001年夏首次访问欧洲时曾遭到大规模抗议,这不仅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布什是一个知识贫乏的牛仔,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国家看来,布什的当选代表了与欧洲价值观有着很大差异的“美国化”观念。此后,美国因不愿接受一些多边机构的约束而采取的单边主义行动,如拒绝参加国际刑事法院、退出《京都议定书》、不接受《禁止杀伤地雷国际公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更是加深了欧洲认为美国只顾自己利益的坏印象。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却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广泛同情,欧洲更是迅速表达了对传统盟友的支持。作为欧洲大国,法国率先垂范,希拉克是在“9·11”后第一位飞往华盛顿,向美国表示支持的西方国家元首。接着,布什在阿富汗耐心、谨慎的军事行动使得欧洲人对他刮目相看,欧洲国家因之一反先前的疏离态度,对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行动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宣称他们与美国“无限团结”,北约盟国还援引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即共同防御条款,认定对美国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对全体北约国家的攻击,因此将被给予集体还击。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
然而,在亲近的背后也蕴藏着又一次的关系危机。以法国为首,欧洲人开始对美国将一切事情都简单地归结到反恐战争并将其扩大化的做法表示不满;而巴以之间频频发生的相互暴力事件也使他们对华盛顿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政策提出批评。美国人则抱怨法国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拉克这样的敌对国家采取行动,并指责法国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威胁说:“美国必须以任务决定联盟,而不是以联盟决定任务。”(注: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s”,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2,p.54.)虽然英国首相布莱尔反复警告说法国和美国分裂会造成危险,但法国总统希拉克仍坚持“多极世界的必要性”,希望欧盟能够说服美国。两种观点在欧洲都有各自的支持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同美英意见一致,大多数中欧国家及意大利、荷兰、丹麦也倾向于大西洋主义;法国则希望至少欧洲可以宣布和美国分道扬镳,其立场得到了德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左冀力量的支持。
随后,更具震撼力的事件发生了:法美之间就是否对伊拉克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公开走上对立。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可谓由来已久。法国外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曾说,透过伊拉克危机,人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一种是崇尚权力和武力,相信民主有可能从外部强加;另一种是强调国际合法性和捍卫国家安全利益,希望尽量避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注:德维尔潘3月27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的讲话:“权利、武力和公正”[N],[法]《世界报》2003年3月2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3年4月15日。)法德等国普遍认为布什政府所偏爱的“先发制人”战略同主权原则是对立的。两国指出,根据主权原则,只有在抵抗侵略或受到袭击时战争才是合法的,同时相信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仍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为阻止美国武力攻伊,法国和德国宣布将在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这是没有先例的。法德的态度最终导致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三国要求联合国授权动武的提案流产。不仅如此,法德还广泛开展反对美国对伊政策的外交游说活动,这些游说活动打破了大西洋联盟半个世纪来的关键时刻“一致对外”的传统。“伊拉克战争以及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所作所为已经使美欧关系处于1945年以来最糟境地之中。”(注:Elaine Sciolino,“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
对美国来说,美欧关系中的部分裂隙根本无法抑制它主导中东事务的战略意图。在盟友的反对声中,美国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法国人及其欧洲盟友们竭尽全力的和平努力,随着“斩首行动”的实施而宣告彻底失败。尽管法国的右冀报纸《费加罗报》称赞希拉克是“和平的捍卫者,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斗士”,但是巴黎那些明智的顾问还是提醒总统不要陶醉于这种假象之中。设在巴黎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多米尼克·莫伊西撰文称,“喀土穆或的黎波里街头的喝彩并不表明法国取得外交胜利”。(注:Dominique Moyse,“From Suez to Baghdad:The Iraq crisis may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Eropean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The Economists,March 22,2003.)虽然法国在中东的利益只有寻求联合国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但一旦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开战,就不能不使法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对法国来说,欧盟是无可替代的;对于大部分欧盟国家来说,和美国持续对抗下去是无法想象的。用“幡然醒悟”来形容法国人随后回头的心路历程,大概再合适不过了。
随着美伊战争的全面展开,围绕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产生对立的法美两国,开始出现了修复关系的迹象。法国首先着手弥合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欧洲分裂,并把它当作寻找与美共同点的第一步。法国外长德维尔潘2003年3月3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意见一致的领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与英国的关系,然后再设法修复与美国的关系。”(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爱丽舍宫已下令法国官员不要对美国加以批评。法国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4月1日在议会说:“必须警惕一切形式的反美行动。反美行动是不可接受的。”(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前夕,法国希望搭乘“胜利者之车”的动机非常明显,比如拉法兰强调指出:“我们不希望独裁者获胜,而是希望民主主义取胜。”(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西洋盟友的示好言行作出了回应。国务卿鲍威尔在4月3日与欧洲23国外长举行的会议上说,双方已就联合国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上应起到的“显著”作用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注:Steven R.Weisman,“Powell and Europeans See U.N.Role in Postwar Iraq”,The New York Times,April 4,2003.)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国有关外交人士认为,战争比当初预想的时间要长,在布什政府内部作为温和派的国务卿鲍威尔的发言权将增强,这将有助于法美之间在日后的合作。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拉克和德维尔潘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了下述态度:巴黎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暂时的。德维尔潘说:“我并不对分歧能否消除感到担忧,因为我们是朋友和盟友,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是(任何国家)不能替代的。”(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
二、法美关系演变的原因
法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尤其是“9·11”后种种戏剧性变化是有着其独特的深层原因和现实原因的。
就深层原因来看,首先,从根本上说,法美关系的变化源于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促使欧美一致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在无政府的世界中,实力超群的美国更倾向于将武力当作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段,而不再顾及相对弱小的欧洲伙伴的意见,两者的利益关系也随之失去了协调的基础。欧洲不再是世界的唯一重心。今天的国际热点所在,是从中东到中亚、再到印支次大陆的广阔天地。这里不仅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的最大储存地和运输线,而且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和欧洲对各自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及其重要性的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在彼此再也找不到相互妥协的理由时,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变得无法避免。最早把美国称为“超大国(hyperpower)”、也是最早公开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思潮,正在美国愈演愈烈。这种心态使美国自认为“别人都应该向我们学习”。对阿富汗军事打击的速胜,助长了某些美国人对武力的崇尚和“单边独行”的观念。特别是美国一些所谓的“鹰派”人物,在维护美国利益时那种咄咄逼人、排斥异己的态度和家长式作风,更是让欧洲人不能接受。
其次,法德等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也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和地缘考虑因素。欧洲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德法曾是主战场。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要尽力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欧洲各国在这一问题上高涨不落的大众反战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地理位置上,欧洲与中东毗邻,如果伊拉克战争导致伊分裂,进而使中东局势动荡不已,本已高度紧张的巴以局势将更加恶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中东引发难民潮,欧洲国家自然首当其冲。基于此,法美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就不是偶然的。
再次,历史、文化和外交传统等因素,在法美关系的演变中也相当重要。欧洲曾经诞生过许多世界级的强国,如今却只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二流角色,现实的反差令其中的心犹不甘者越加对现状不满,对美国试图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充满了疑问和否定。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欧洲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谈论“欧洲特性”、“欧洲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表现出对美国霸权的厌恶和排斥。欧洲各国普遍珍视本国的历史文化,鄙视美国文化的浅薄和商业化。法国人更是顽强地捍卫法语的地位和纯洁,努力抵制美式大众文化。而美国人看法国,也充满了轻蔑和不信任:动辄游行罢工、中央高度集权、效率低下、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福利要求却越来越多等等。就外交传统而言,比起美国来,欧洲各国更愿意重申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平等”、“公正”、“主权”等传统价值观,视自己为其最“正宗”和最坚决的捍卫者。对于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强大实力的前世界强国,运用自如的当然是外交上的娴熟谋略和传统智慧。法国尤其如此,自戴高乐时代传接下来的适时与美国对着干的做法已成为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屡试不爽的外交技巧之一。
不难看出,美欧之间不和谐的这些深层原因是长期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此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美关系在“9·11”后的演变轨迹。首先,在中东问题上,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地区派驻了大量兵力并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战略上已基本控制了沙特、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和运输,美国需要在伊拉克彻底消灭萨达姆政权,扶持亲美政府,实现将整个中东产油国完全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并进而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战略目标。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性控制以及压倒性的政治军事存在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欧盟的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法国和伊拉克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密切。法国一直是伊拉克的重要武器供应国。法国也与中东地区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法国石油只有5%自给,高达52%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中东。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不仅不愿看到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且还希望早日解除对伊拉克的国际制裁,以便从中渔利。30多年来,法国在伊石油勘探和开采方面大量投资,在这个石油探明储量世界第二大国里拥有了相当的开采权,这对能源资源缺乏的法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自1980年代以来,伊拉克国内进口量的25%来自法国。直到前不久法国国家石油巨头还在与萨达姆当局就价值达400—600亿美元的伊南部油田开发合同进行谈判。(注:Kenneth R.Timmermau,“French Twist”,The New Republics,March 17,2003,p.10.)法国担心美国对伊动武将导致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并严重影响法国的经济发展,危及法国长远利益。从整体来看,美国对伊动武,无论是失利还是获胜,对欧洲来说都是弊多利少:如果美国开战不利,势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目前疲软的欧洲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美国攻下伊拉克,无疑美国将完全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欧洲将在能源上受制于美国,阻碍其经济、政治一体化,制约其综合实力的增强。因此,保护石油供给安全以及加强在中东事务上的发言权,成为法国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所首先要顾及的。
其次,自科索沃战争以来,经济上、政治上日益强大的欧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却尚不具备直接向美国挑战的能力。“9·11”后,欧盟在国际政治上面临着不断被美国“单边主义”边缘化的危险。阿富汗战争后,美国更是打着反恐的旗号,忽视盟友意见,在诸多事务上一意孤行。这样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加深了巴黎的忧虑。一旦有一天,当欧洲既不能配合美国的行动,又没有能力维持现状或为美国的干涉行为“买单”时,不难想象美国人将会怎样对待欧洲人。到那时,作为对美国“犯上”次数最多、程度最重的法国的处境,就更可堪忧。所以,法国就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及早让美国人明白:单边主义已使美国变得格外危险,最终有可能毁了美国乃至世界。同时,法国也看到,欧盟正面临这样的政治现实:支持美国动武的欧盟国家除了西班牙、意大利等传统欧盟国家外,还有即将加入欧盟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它们在美国的推动下,极有可能摆脱法德的传统影响,不断向美国靠拢。甚至有消息说,波兰准备要取代德国成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兵站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意味着法德两国作为欧盟核心的地位正遭受着严重冲击,更加使法国和德国不能不尽其所能缓解美国一家坐大对欧洲产生的分化作用。
再次,从法国国内因素看,它地处地中海北岸,在地缘政治上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国拥有数百万阿拉伯后裔或侨民,1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在处理伊拉克危机的过程中,希拉克与阿拉伯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并与他们采取了共同的反战立场,这显然是为了保证法国社会安全的长远利益,希拉克也因为坚持此立场而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好评与尊重。
此外,法美冲突还有着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1995年当选、2002年连任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是法国政坛上的常青树,也是世界政坛上资历颇深、影响较大的一位政治家,素有“戴高乐主义的传人”之称。希拉克曾说其雄心是“遵循戴高乐将军的教导,寻求法国在世界事务中应有的突出地位。”(注:[法]《世界报》1995年4月7日。转引自王毅:“法国总统大选及今后政策走向”[J],《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第3期。)多年来,希拉克不仅在国内出色地经营了自己的传统右翼阵线,而且也在世界舞台上为法国的大国地位纵横捭阖,活跃异常。面对锋芒毕露、甚至公开把法德称为“老欧洲”的布什安全班子,希拉克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前辈”、“长者”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时下法美关系紧张的个人原因之一。
法美争锋也是欧盟成长壮大、意欲扮演更加积极的国际角色的集中体现。1990年代以来欧盟的发展令人瞩目。随着欧元迅速成长为能向美元挑战的国际货币和欧盟向东欧地区的进一步扩展,欧盟最终将形成一个囊括整个欧洲地区、人口超过4亿、经济总量与北美相当的强大的发达经济体。伴随着欧盟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在国际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更加明确地维护其政治独立、经济自主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遭遇美国一超独霸强力阻击的形势下,欧盟作为一支上升的力量,正在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同时也应看到,尽管欧美之间矛盾摩擦在增多,欧美联盟凝聚力在下降,欧美关系的裂痕在扩大加深,但毕竟双方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欧美关系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人们必须冷静地对待局势的发展。
三、伊拉克战争后法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判断伊拉克战后法美关系的未来走向问题,首先可以从战争本身的原因进行分析。石油可谓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战争过程中,油田可能遭到破坏,但一般估计这种破坏程度将远远小于当年海湾战争中的科威特油田被破坏的程度,战争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因而,对于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石油资源的争夺将会是影响战后法美关系走向的因素之一。
其次,关于伊拉克战后的重建问题,显然也会在大国之间引起激烈争论。在美国看来,“坦克开到哪里,就在哪里划分势力范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逻辑,美英在战争中所承担的主要责任应该成为其主导伊拉克战后事务的最大资本。而法国等国认为美英开战是违背了联合国宗旨所采取的单边行动,这一行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带来的破坏只能在其后由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行动才有权利、有能力来加以纠正和弥补。双方在联合国将在“多广泛”的范围内发挥“细节性作用”上仍有分歧。(注:“Powell and Europeans See U.N.Role in Postwar Iraq”,The New York Times,April 4,2003.)正如一位欧洲高级官员所说的:“如果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起到主导作用的话,跨大西洋关系将能够得到修复。如果只把联合国看作是美国主导的行动的幌子的话,则(这种修复)不会发生。”(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
再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更深一层动因,显然还有战略考虑。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得手,无疑将直接加大美国对中东和阿拉伯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掌握了海湾地区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整个欧亚大陆。至少在能源方面,美国可能对法国等传统欧洲大国进行制约。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伊战后法美的战略利益与观念形态的重大分歧将会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透过法美关系,主张多边合作还是坚持单边“独行”的这一对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事实上,在战争尚未结束时,美国就有舆论开始鼓吹要对法国进行报复性惩罚,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抵制法货的运动,新奥尔良州的一些政治家更是对希拉克等法国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虽然这些不友好行为并没有阻碍法国当局修复与美国关系的步伐,但事态的发展,如不久前法国驻美大使指责五角大楼授意新闻媒体攻击法国及美对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进行变相抵制等行为不能不对法国此后的外交主动性产生影响。也许,最具说服力的范例莫过于6月初的埃维昂八国峰会了。由于双方心存芥蒂,美法首脑会晤的气氛是不很融洽的,在表面热情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勉强甚至冷漠。《华盛顿邮报》对此解释道,白宫对美法单独会谈没有什么兴趣,只称这是一次“礼貌的会面”。这说明两国在世界秩序观和国际战略上的分歧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当然,由于弱者一方的回归,业已产生的裂隙似乎有所弥合,但问题是机体的损害一旦转化为心灵的创伤,就会在双方之间留下抹不去的阴影。这也是为什么诸多评论家都说这次法美分歧是“分水岭”式的,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以来最严重的美欧关系危机”。(注:“Europe Assess Damage To Western Relationships And Takes Steps to Rebuild”,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2003.)因此,法美关系要修复到以前那种“斗而不破、和好如初”的惯常模式的前景不容乐观。
法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欧关系的发展框架。“一个地位上升的欧盟将肯定会尝试挑战美国,尤其如果美国不放弃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嗜好的话,曾经团结一致的西方世界可能一分为二,成为竞争对手。”(注:[美]查尔斯·A·库普钱:“谁是美国的终结者?”[J],《编译参考》2003年第1期。)查尔斯·A·库普钱的这一论断,可以认为是对当前欧美关系症结的实质性表述和今后走向的大胆预测,但这决不意味着时下的必然结果。
尽管舆论一直在谈论“9·11”后大西洋两岸的分歧,但将这种分歧上升到欧美关系分水岭或试金石的地步,还为时尚早。现实是美国和欧洲的基本价值观和利益并没有背离,欧洲民主国家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朋友。据有关研究显示,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司在欧洲的收益占它们全球总收益的一半。(注:Chris Patten and Pascal Lamy,“Let's Put Away the Megaphones:a trans-Atlantic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April 9,2003.)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与欧洲都受欧洲启蒙运动的熏陶,并且有着广泛的种族文化联系。过去的半个世纪,它们携手创立国际法律体系,内容不仅涵盖贸易和安全,还包括人权和基本自由。可见其基本世界观非常相似,尽管行为方式有时不同。
国际事态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战前大多数人没有料到美英会在攻伊战事进行到一半时发生分歧;现在法德俄三个反战国家的立场转变和向华盛顿示好也同样出人意料。欧洲国家目前依然无法承受北约分裂的代价,因此,断言跨大西洋关系将就此分裂、西方世界重组将会展开,恐怕言过其实。美欧双方各自对其关系的评估、对萨达姆政权的深层共识及仅在战争手段上的表层分歧,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一框架下,我们便可以理解法国由硬到软的立场转变过程。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衬托出美欧关系的现实利益基础和理性考虑。至少在中、短期内,双方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纽带仍将继续维持,而两者之间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综合实力的悬殊差距也使得双方无法分裂成真正的对手。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对伊拉克战后世界格局的展望将可能出现重大偏差。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美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