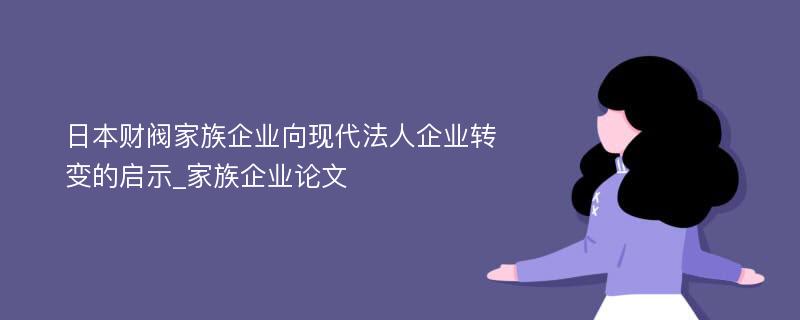
日本财阀式家族制企业向现代法人企业形态变迁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阀论文,企业论文,日本论文,形态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财阀式家族制企业的历史与变迁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为止,主导日本经济的主角是财阀企业。二战结束后,日本财阀企业被强制解散,财阀家族持有的股份被卖给了公众。但不久之后财阀很快又重新回到了日本经济的中心。
1.明治时期对财阀式家族制企业的大力扶持
明治政府为日本的传统家族企业和新兴的家族企业成长为大型的财阀企业集团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出资兴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1880年明治政府大规模低廉地出售“国有企业”。三井、三菱、住友等当时已经有一定实力的家族企业都从中购买了一些重要企业,从而各自掌握了一些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等。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认为,这是日本财阀的真正“起点”。正是这些产业,尤其是矿山,为这些家族企业的扩张、进入其他领域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支撑。财阀家族与明治政府也发展出了类似的一种互相支撑、互相利用的互惠关系。三井家族通过在最初几年的困难时期里大力支持了明治维新运动而得到政府的信任,承担明治政府的金库代理业务。这使其发展出了庞大的全国性的分支网络。三井物产,获得了日本国有煤矿优质煤出口业务的垄断经营权。
业务扩张导致这些家族企业开始以组建新形式的企业——公司来吸收家族之外的股权资本,包括公众资本,但是家族保持控股地位。这样逐渐形成了最上层是家族,家族持有绝大多数股权的财阀总公司(本社),往下是一层、二层、三层,并构成了层层控股的企业。
2.财阀式家族制企业向现代法人企业形态的渐变
到了20世纪之后,在不放弃家族对企业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日本家族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外部股权融资。1936年,日本公司的股票市值总额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6%。即使今天,也只有美国和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公司股票价值总额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除了股权集中度相对还是比较高之外,总体上可以说一种股东至上和股东所有权主导的公司治理文化。
财阀家族除了对本社(就是控制财阀集团企业的总公司)和重要的第一层子公司保持着很高的股权比例之外,财阀整体对下属企业的控股比例下降趋势十分明显。1929-1943年之间,除安田之外,四大财阀中的三井、三菱和住友,财阀整体持有下属企业股权的平均比例基本都从50%左右降到30%多一点。安田对下属企业的持股比例保持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因为安田在这一期间没有像其他三大财阀那样大踏步地发展,其下属企业数增加很少。不过从四大财阀1928年时对其第一层子公司的控股比例来看,安田已经是最低的,只有48.1%,而三井、三菱和住友对其一级子公司的控股比例分别是90.6%、77.6%和80.5%。
1945年,财阀被解散时,四大财阀企业集团中,三井和三菱的本社——母公司也都已经不是100%的财阀持有。从被解散后的日本财阀企业集团的所有权变化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已经呈现出其逐渐开放股权的趋势。三菱、三井等财阀企业集团也已经开始在母公司层面上扩大所有权开放程度,而对子公司保持着较高程度的股权控制,逐步向现代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模式方向转变。
3.财阀式家族制企业间由于交叉持股形成的特殊渊源
战争和解散财阀作为“外部冲击”,隔断了日本的家族财阀企业按照其本来很强的股东主权主义的逻辑和逐步分散股权的路径,使其未能完成其向现代国际化企业制度模式自然演变的过程,但财阀还是为战后日本新形成的“企业集团”——系列企业,提供了重要并不可或缺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战后日本企业的交叉持股本身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就是财阀的“遗产”。在主要靠自我融资,资本相对短缺而又要保持控制的情况下,财阀下属企业之间已经存在着大量的相互持股现象。可以说,交叉持股是战后日本企业在其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和历史条件约束下所“生成”出来的一种在股权分散条件下,保持企业控制权的做法。为什么面对股权分散和并购威胁,日本企业走上了交叉持股,而不是像美国企业那样采取一系列的反并购措施?这除了前财阀企业的交叉持股遗产及前财阀成员企业之间的情感联系等软性因素之外,法规方面的硬性因素,尤其是战后《反垄断法》的法人持股比例限制以及《公司法》的禁止企业回购自身股票(1998年修改)等起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财阀式家族制企业向现代法人企业形态的转化对公司治理模式变迁的启示
1.家族制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虽然是一种很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但家族制企业未必是过时、低效率的。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只要催生家族制企业的特定社会环境还存在,家族制治理模式就仍有其合理性。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家族制企业一般都是企业的主要组织形态,并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市场不成熟、规则不健全、信息不完备,特别是信任制度欠缺时,家族关系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能较好地弥补市场缺陷。家族制企业治理模式可以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实现创业所需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集中,家族成员之间比较容易建立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从而更易进行合作,达到更高的决策效率,在社会上通常也有更高的信誉优势(尤其对于定位为区域化发展的企业而言)。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由家族成员为主要管理人员的家族企业强调关系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非正式的治理机制”代替“正式的契约式治理机制”,这使得家族企业在特殊的条件下可发展出正式契约关系所不具有的忠诚与效率。简而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一种企业制度总是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的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联系,更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企业产品和所在产业性质、企业规模与效率密切相关。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成长阶段下企业所需的生产要素的特征不同,企业既定规模边界和最优制度选择也应不同。所以,企业制度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应与否之别。对企业制度适合与否的评价,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现代化”的公司架构,而是看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分工合作所需的交易成本,是否有利于对企业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家——提供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是否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保证。
2.以社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家族制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向历史证明,家族制企业最终必须向公众化方向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发展,在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半径加长、经营管理活动更为复杂和专业化的条件下,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变得突出,这时如果继续沿用家族治理模式,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和家族成员管理能力不高便会导致内部交易成本增大、容易导致高昂的“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造成竞争力下降,此时家族制企业的治理模式就是不合理的和低效的。这就要求家族企业必须突破自身的界限,以家族资本去有效融合社会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网络资本和文化资本,需要与非家族成员共享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经营控制权。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现,在家族企业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家族成员间因产权不清造成激励不足的问题。加之亲情关系的纠缠,家族规则往往不能或难以抑制家族成员的违规行为和内讧,因而造成企业的衰亡。因此,一般普遍认为,家族制治理结构有利于创业,而不利于发展。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指出: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因此,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应当实现企业治理制度的变迁。
3.企业制度变迁的国别条件差异。从世界范围看,虽然现代企业制度存在共性,但社会经济制度、科技水平、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的不同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走上不同的路径,并各具特点。即使同为发达国家,不同国家的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演变的路径与结果也不相同。演变的过程不仅受一般经济规律的支配,也要受到具体的历史;地理、制度、传统文化和伦理规范的约束。因为任何制度变迁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要受到其他相关制度(如文化传统、社会法律环境)的影响,如果一项新的制度安排与这些制度相矛盾,新制度就难以推行。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要根据各个国家自身不同的特点,尤其要重视一个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因此,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不可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在引进制度的同时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通过制度创新摸索出一套与自身国家体制、文化传统、国民意识和特定环境相融合的企业制度,这是建立起来的企业治理模式得以有效运作的最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