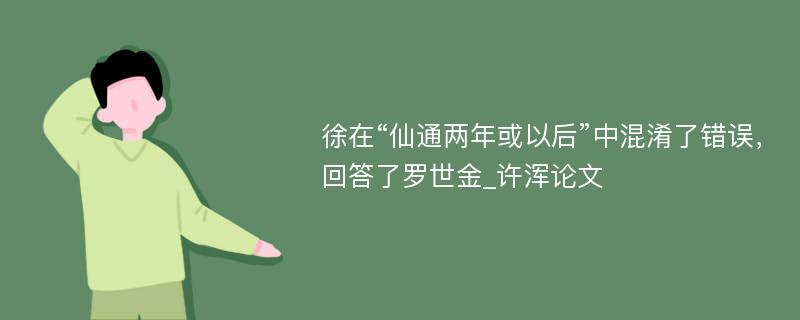
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辨误——兼答罗时进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年论文,稍后论文,卒于论文,兼答罗时进君论文,说辨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207-05
我们在《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下简称《新说考辨》)①中论辨了罗时进《唐诗演进论·许浑年谱稿》(下简称《年谱稿》)②等文所主张的许浑贞元四年生,咸通二年或稍后卒,与顾陶《唐诗类选后序》(下简称《后序》)约咸通三年前后撰为误,并涉及他因误读某些诗文、史载而导致的论证疏失。此后罗时进君又发表《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与吴在庆、高玮商榷》(下简称《如何考订》)③,坚持其大多数观点,并重申:“我在《许浑年谱稿》将其卒年订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得略为宽泛些,是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在其自辩及批评我们时,存在所批非我原意而自树靶子的情况。今谨就若干分歧再做考论。
顾陶编《唐诗类选》,并撰《唐诗类选序》(下简称《前序》和《后序》),两序均是考订许浑等一批作家卒年的关键文献。《后序》云:“近则杜舍人牧、许鄂(庆按:‘鄂’,应为‘郢’之讹)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别为卷轴,附于二十卷之外,冀无见恨。若须待见全本,则撰集必无成功。……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备,兴比之间,独与前辈相近。亡殁虽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④据此,如知《后序》撰时,则可知上述诸人的大致卒年。但《后序》未署作年,仅知《前序》于大中十年撰。《后序》作年,缪钺《杜牧卒年再考辨——与罗时进同志书》⑤,梁超然《唐才子传校笺·李敬方笺证》⑥早就认为撰于大中十年。我们在《新说考辨》也论证《后序》和《前序》均大中十年撰,并以此为许浑非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佐证之一。对此《如何考订》却认为是“先预立《后序》作于大中十年”,再“来订他们的卒年”,是“应当摈弃”的“先验的观念”。读者只要阅读上述诸人的相关论著,自可判断此言的真实性,无庸再辩。
《如何考订》判定《后序》大中十二年之后作的“重要依据”是《唐诗纪事·杨牢》提及《后序》中有“删定之初,如杨牢等十数公,时犹在世”语,而《千唐志斋藏石》收有《杨牢墓志》,其中记杨牢卒于“大中十二年正月二日”,据此认为“《后序》作于大中十二年之后当是不争的事实。”可惜“事实”是建立在《唐诗纪事》引文有误的基础上,而且此误早就被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杨牢传》的《校笺》所纠正,谓《后序》中原有“‘杨茂卿’,无‘杨牢’。……则计氏以杨牢为茂卿,实误。”⑦此后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也指出:“计有功以杨牢为茂卿,实误,故不足为凭。”⑧
《如何考订》提出:“如果出现了杜、许、张、赵、顾等人(甚至哪怕其中一两位,但最好不要以孤证定论)确实卒于大中七、八年的过硬证明,那……《后序》与《前序》同作于大中十年之说便能成立。”其实在《新说考辨》中对于相关人卒年的考证虽限于篇幅较为简要,但诸人卒年的考证并不仅依靠《后序》作年立论,也非孤证。现仅就杜牧、张祜卒年做一简要,却非孤证的考证。
杜牧大中六年卒,缪钺等先生已有充分的反复论证,为省篇幅,容不多赘,请读者参读吴在庆等人的《杜牧咸通元年卒说辨误》(《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此文足以证明杜牧确实卒于大中六年,而非咸通元年。
再简要论证张祜卒年。张祜卒于大中八年事,笔者之一在《张祜卒年考辨》一文中即有论证⑨,今容不详述,仅略引典籍以证。《新唐书·艺文志》四:张祜“大中中卒。”⑩《唐诗纪事·张祜》:“大中中,果卒于丹阳隐舍。”(1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张祜“大中中,果终于丹阳隐舍,人以为谶。”(12)《唐才子传·张祜》:“大中中,果卒于丹阳隐居,人以为谶云。”(13)以上记载均谓张祜大中中卒。大中(847-860)乃宣宗年号,凡十四年。则称大中中,最宜时间应是大中六至九年间。前已论张祜卒于大中八年,则与上述四则记载谓其大中中卒相符合,以此亦可合证张祜非大中十年后卒。
又,《全唐诗》卷六二六陆龟蒙《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并序》(下简称《诗序》)略云:“(张祜)死未二十年,而故姬遗孕,冻馁不暇……友人颜弘至……访其庐,作诗吊而序之,属余应和。余汩没者……邀袭美同作。”又《全唐诗》卷六一四有皮日休《鲁望悯承吉之孤为诗序邀予属和……用塞良友》诗(14)。从上引知道,陆、皮之序、诗当为同时先后之作,而作《诗序》距张祜之卒“未二十年”。据《杜牧咸通元年卒说辨误》所考,皮、陆此次酬和约于咸通十一至咸通十三年春。今以张祜卒于大中八年算,则至咸通十一、十三年,分别为十七、十九年,这与陆龟蒙所说此时距张祜之卒“未二十年”恰合。
从张祜卒至陆龟蒙《诗序》撰时,其“死未二十年”。今设《后序》即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而张祜等人之卒,到《后序》撰时“才二、三年”。则即以前三年论,则张祜之卒约在大中十三年(859),如至咸通十一年(870)才十二年虚,到咸通十三年才十四年虚,均远不能称“未二十年”。此即可证《后序》非“咸通三年前后”撰,反之可证张祜大中八年卒可信。张祜既卒大中八年、杜牧大中六年底卒(顾陶得知杜牧之卒可能在大中七年了),均在大中十年前,而《后序》谓包括两人在内诸人之卒至《后序》撰时“才二、三年”,则《后序》大中十年作又再得确证。
《新说考辨》指出并论证《年谱稿》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一些论据以及论证之非,而《如何考订》除对个别极为明显的失误保持缄默外,其余多坚持己说,并多有发挥与反驳,这就不得不就其中的某些主要问题再事辨析。
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以下简称“许浑新说”)的重要依据是《吴越备史》卷一的记载:“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赉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厌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据此,“许浑新说”认为所谓“王者气”事指“大中十三年以裘甫为首的浙东起义”,并将侍御史许浑前往“厌之”事定在咸通元年,据此证诗人许浑必卒咸通元年后。
我们在《新说考辨》据有关史籍指出“王者气”是指吴越王钱鏐事,而非裘甫。还指出《吴越备史》所记为“咸通中”,而“许浑新说”为牵合其许浑卒年以及《后序》作年说法,却将其硬系在咸通元年。对此我们委婉指出:“以上据以考论诗人许浑的资料与论述疑窦颇多,难于凭信。”又具体指出其三点疑窦。但“许浑新说”依然将《吴越备史》的“咸通中”硬系于咸通元年,并作为“许浑新说”的坚证。其实,仅就这点而言,“许浑新说”以及《后序》作于咸通三年前后说就存在矛盾。咸通凡十五年,于末年十一月改元乾符元年。因此最宽泛称“咸通中”的适合年头应是约咸通五至十一年间,而以咸通七、八年为确当,而决不能如“许浑新说”那样硬将咸通元年视为咸通中。那么即以咸通七年侍御史许浑出差钱塘厌胜而论,如又坚持把此许浑视为诗人许浑、固持《后序》作于咸通三年前后、许浑咸通二年或稍后卒,并认同也《后序》作时诗人许浑等人之卒“才二、三年”,那么其间几个观点结论间的左支右绌,不是显而易见吗?这就表明这些观点论述多有失误。
既然坚持侍御史许浑即诗人许浑,而侍御史许浑咸通中(以七年论,下同)尚出差钱塘厌胜,则与诗人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许浑新说”矛盾。既然固持《后序》作于咸通三年前后,而认同作《后序》时杜牧、许浑等人之卒“才二、三年”,那么其一,所认定的诗人许浑卒年距《后序》作年仅一年,与《后序》“才二、三年”有所不合;其二,许浑等人既卒于撰于咸通三年前后的《后序》之前,而尊文又认为咸通中诗人许浑(即所认为的侍御史许浑)尚出差钱塘,这岂非活见神仙!换个说法,如以尊文《后序》作于咸通三年前后为基点考虑,那么所认为是诗人许浑的侍御史许浑,在咸通中就不能返魂奉命去钱塘厌胜,多年前他已去世了。也许上面将“咸通中”定在咸通七年显得太精准了些,那么就以最宽泛的咸通五年,甚至咸通四年来检验上述“许浑新说”等几个结论,不巧的是也同样都不能自圆其说。
如前述最近已经有学者以不同的资料与角度论证《后序》确实作于大中十年,再加上上述以“咸通中”侍御史许浑出差事检验罗君的上述诸说,以证罗君诸说之矛盾不通,其实已经无可怀疑地论证了诗人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他即是侍御史许浑,以及相关论说(如我们认为许浑卒于大中八年,故疑要么《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诗非许浑诗,要么《新唐书·宣宗纪》记刘皋被杀事于大中十二年三月有误,但罗君认为两者均不可怀疑)的失误与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之无济于事。不过为了回答围绕罗君所坚持的“许浑新说”而做的辩解与反驳,我们还是得再费点笔墨将相关的主要问题说明一下。
《如何考订》对我们指出《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许浑不是诗人许浑颇不以为然,坚持二者同为诗人许浑,并做了种种辩解。以下,我们抉出其几处辩解加以分析。
《如何考订》说:“至于《新说》认为许浑已历官至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我认为,这涉及唐代重视京官而产生的官场文化现象。许浑在大中末郢州刺史任满后,并不能排除特授侍御史的可能性。正如晚唐崔嘏《授裴谂司封郎中依前充职制》所说:‘台郎望美,词苑地高。’一般来说,唐代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诰决定。但御史、拾遗、补阙、郎中、员外郎等台省官员,虽然只有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但都须上报,由皇帝亲自任命。且此类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授。”接着以韦应物、许浑等多人由州刺史升任郎中或员外郎之例为证:“他们的京职品秩皆低于地方郡守,但京官‘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如果认为这样的现象是‘降职’而不是擢升的话,是有违唐代官制常识的。”
唐代一般有重视京官的现象,这是从事唐代文史研究者的常识,不过说成“唐代重视京官”却也太绝对了。实际上,这只是大多数时期如此,而此现象在盛唐张九龄建言后的一段时期就开始有所转变,特别是肃宗、代宗以后,晚唐的宣宗时期就反而有“外重内轻”的时风。如清人赵翼即指出“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15)唐宣宗大中改元,为了改变内重外轻的风气,下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亲人之官,急为政之本。自浇风久扇,此道稍消,颉颃清途,便臻显贵。治人之术,未尝经心,欲使究百姓艰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为政之始,思厚儒风,轩墀近臣,盖备顾问,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未曾任刺史、县令,或在任有赃累者,宰臣不得拟议。”(16)顾炎武《日知录·京官必用守令》亦据此有所说明(17)。除此之外,上引的这段强调要懂得常识的话,还有些也是不妥的,今析论之如下:
1.我们提出的疑问原本是“诗人许浑大中七八年已任虞部员外郎、郢州刺史……诗人许浑的历官已如此,他在大中八年任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后又无贬官的记录,则为何至咸通元年反被降为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呢?”引文去掉许浑已任虞部员外郎这句话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但去掉它就造成了原意的改变。我们当然也知道品级高的刺史也常入任品级稍低的朝中郎官,如虞部员外郎、郎中之类。但虞部员外郎和侍御史同为朝官,而前者品秩高于后者。这样假设如《如何考订》所说的许浑果由四品下的郢州刺史入任从六品下的侍御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到他之前就担任从六品上的虞部员外郎京官,那么以他这种任官资历,又非贬官,又为何反任较之前已任的虞部员外郎品级低的同为京官的侍御史呢?这难道能让人无惑?
2.《如何考订》所要说明的是侍御史一职乃“望美”、“要职”,但所引用作为论据的例子却对不上榫。所引用的那道制诰“台郎望美,词苑地高”两句并不包含侍御史在内。这道制诰原有如下内容:“敕:台郎望美,词苑地高……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裴谂,袭庆于门,腾芳载席……自擢居文囿,参伺瑶墀……是宜仍金鸾之旧职,荣粉署之新恩……可依前件。”(18)可见,裴谂是由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擢授司封郎中、依前充翰林学士的。因此这里“台郎望美,词苑地高”两句是分别就郎官和翰林学士而说的,并不包括侍御史而言。可见,《如何考订》所引对其所要论述者而言,实在离题了。
3.《如何考订》说:“但御史、拾遗、补阙、郎中、员外郎等台省官员,虽然只有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但……此类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授。”这样的说法也是存在问题的。第一,据《旧唐书·职官志》,拾遗的品级为从八品上;补阙的品级为从七品上;郎中的品级为从五品上;员外郎的品级从六品上;“御史”,唐代一般乃是御史台三职之称呼:即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可见《如何考订》上引五官名都非“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最多只有员外郎和侍御史这分别为从六品上、下的官员可泛称“六品这一层级的品秩”。第二,《如何考订》说上述“此类台省官员往往正是由州刺史迁授”,这话也不对。比如其中的御史(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在正常情况下(如《如何考订》所说的“而且只有循吏方获此荣”)难道真会由州刺史“迁授”?如能这样,那就请各自举出几个事例来证明。
4.《如何考订》接着以多人由品级高的刺史入任品级稍低的郎中、员外郎之例,说明尽管侍御史的品秩不如刺史高,但因它是“京官‘班望颇重,中外要职,多由是迁’”,以此证明诗人许浑可由郢州刺史“擢升”侍御史。这样的证明也是有问题的。郎官在唐代确实是“望美”之职,确实多有由刺史而迁授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京官都是郎官,都是“望美”,如有刺史入任任何京官的情况,都可视为“擢升”。比如你所举出的拾遗、补阙,御史,尽管都是京官,但谁会愿意由刺史入任它,并认为是“擢升”呢?能找出这样的几个事例吗?
我们认为,诗人许浑和咸通中的侍御史许浑是不同的两人;而《如何考订》坚持认为同属一人,其反驳的主要理由是:1.“当然,我更倾向于许浑此次被派遣浙东,其‘侍御史’并非实授,只是因为许浑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一台省职位,便借以称呼,这正是唐人尊称京职的习惯。”2.“关于这个问题要特别提出一条材料,即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南海非》关于许浑赴南海幕府与诗人方千里交往的记载:‘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具诺焉……’需要说明的是,许浑南海之行在开成元年(836),其时尚未任监察御史,也就是说,‘侍御’并非许浑赴南海时所带京职。正因为如此,《南海非》中的‘许浑侍御’之谓就特具参考价值了。……这里范摅对许浑以‘侍御’称之,无论是尊称,或者是对其最后特授官职的记录,都说明咸通年间出现‘侍御史许浑’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活动的客观反映。”
关于咸通年间的侍御史许浑决非诗人许浑的问题,我们上文所再次论述的《后序》作于大中十年,杜牧、张祜、诗人许浑等人均卒于是年之前,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否定《如何考订》将这两个“遥不相干的”许浑混为一人的所有论说了。不过上述的罗君之说实在令人难于赞同,真如罗君所说“在进行晚唐诗坛人物研究时,这个同姓同名现象其实进不了话题”(引号乃《如何考订》语),故不得不稍再论析。其显然的矛盾、失误如下:
首先,认为“其‘侍御史’并非实授,只是因为许浑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一台省职位,便借以称呼”。上文罗君为了论证的需要,极力证明诗人许浑确实有可能由郢州刺史“特授”侍御史,而今又反转说“并非实授”,前后之说矛盾,截然不同。
其次,监察御史与侍御史品级相差很远,称呼也不同:后者“众呼为端公”,前者如同殿中侍御史“众呼亦为侍御”(19)。怎能因许浑曾任过监察御史,就将其与侍御史等同,“便借以称呼”?能这样以“尊称京职的习惯”而改易称呼吗?
最后,所特地提出的《南海非》的许浑侍御以及其事在开成元年等论说,这在《年谱稿》中早就有相同的更为详细的考论,可惜均实在远离历史事实。此事不在开成元年,许浑出差南海时也并不是未任监察御史等等,其详细论证可参见由巴蜀书社出版于1987年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续编·许浑行年考》会昌四年条,是书第148—150页;还可参考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李立朴的《许浑研究》第83—84页,以及将许浑南海之行事系于会昌四年的第93页。尽管上述二书尚未对“弘农公”云云有确实的解释,但其他的论述则大致可信。
我们欢迎对于《新说考辨》的反批评,但《如何考订》对我们的批评却存在所批非我原意而自树靶子的情况。此不一一指出,只就几点稍加论析。
第一,我们在《新说考辨》中说《东观奏记》虽然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述,又以具体事例论证并强调无论是全书或是下卷,并非每条记事均严格地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事,也存在不少不按时间顺序记录的情况。这意在表明不能认为记在某事之后的事件,其时间就一定在某事之后,并据此说:“可疑的是《新唐书》对杨玄价杀刘皋的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系年。我们知道唐武宗以后的实录等史料多亡缺,正如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裴庭裕《东观奏记》三卷条下所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因此正如田廷柱先生在其点校的《东观奏记·点校说明》中所指出,欧阳修在撰《新唐书》时多据《东观奏记》‘补充了许多不见于《旧唐书》的资料。’又引清人王鸣盛之说以证实云:‘《新书·李珏传》多取《东观奏记》。他又说:‘《旧书》所无,《新书》增入者多取《东观奏记》。’在其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传中,都或多或少地据此补充了若干事实’。可见,《新唐书》关于杨玄价杀刘皋的记载乃取资于《东观奏记》。《东观奏记》关于此事的记载并未记年月。”应该说,《东观奏记》的记载是较为严谨可靠的,因此在其明了所记事件的具体时间时,作者在许多条目的记载中,多有具体的年月记载,而未知道具体确年的,则未记年月。杨玄价杀刘皋的这一条就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新唐书》何以将未有年月的此事记在大中十二年三月呢?察其缘由,大概乃在于如《许浑卒年再考辨》(笔者今按,此文亦罗君文)一文所认为的此书‘大致以年代先后为次’,这样,杨玄价杀刘皋之事,《东观奏记》既然记在第65条的‘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之事后的第67条中,那么也就按时间先后推断此事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了。”《如何考订》节引了上文后说:“这里存在两个需要辨析的问题:第一,《东观奏记》对刘皋被杀事件有没有可靠的依据?第二,《新唐书》的记载是否肯定取材于《东观奏记》?……《新说》在质疑《东观奏记》的同时……再猜疑《东观奏记》事件编年的不可信”云云。从上引我们的“《东观奏记》的记载是较为严谨可靠的”等等论说中,《如何考订》怎么会提出“需要辨析的”第一个问题?怎么得出说我们“在质疑《东观奏记》的同时……再猜疑《东观奏记》事件编年的不可信”?这是我们文中的观点吗?至于问我们:“《新唐书》的记载是否肯定取材于《东观奏记》?”我们说过“肯定取材”这样的话吗?我们所说的“乃取资于”,怎么就变成“肯定取材”了!再则,谁能确定《新唐书》的这一记载就完全没有取资于《东观奏记》?
第二,《如何考订》说:“《新说》在质疑《东观奏记》的同时,又顺势提出《新唐书》关于这一事件‘时间记载只是根据上述情况(按,指《东观奏记》下卷记载)推测出來的,其实并不可靠’。这似乎有些强加于《新唐书》了。要知道,《东观奏记》下卷记载刘皋被杀事,是未记月份的,而《新唐书》却确切记载为大中十二年‘三月’。难道《新唐书》的作者会先从《东观奏记》中得到一个‘大中十二年’的大致时间,再编造一个‘三月’的具体月份吗?如果这样想象,对欧阳修和《新唐书》都太不严肃,太不尊重了。”我们说过或冒出过欧阳修在“编造”的词语与念头吗?“对欧阳修和《新唐书》都太不严肃,太不尊重了”,我们决不会这样。又,所说的“要知道,《东观奏记》下卷记载刘皋被杀事,是未记月份的”,事实上是《东观奏记》既未记刘皋被杀的具体年份,也未记月份。至于所认为的欧阳修负责《新唐书》“本纪、志、表的修撰,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宋敏求的六朝实录的;也只有按照实录的体例,历史事件才会精确到年月。”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一“得助”情况,但为欧阳修所利用的宋敏求的记在大中十二年三月的刘皋被杀事的《实录》,谁又能否认它也有取资于包括《东观奏记》在内的史料,谁又能肯定它的这一年月的来源不仅有可能取自于《东观奏记》外的有明确年月记载的资料,或也有可能据《东观奏记》的记载,同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而得出的呢?但不管如何得出这精确的年月,尽管《新唐书》较为严谨而为人取信,可它千虑一失之处还是难免的,此前人多有指出,故宋吴缜有《新唐书纠谬》,后有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罗振玉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等,近年傅璇琮先生《唐翰林学士传论》对《新唐书》亦多有纠谬补充。因此在我们发现《新唐书》这一“大中十二年三月”的记载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其他事件的时间确实存在矛盾时,就如上文所说,现在已有学者如我们一样也考订《后序》确实撰于大中十年,这也就是说,诗人许浑、杜牧等人在大中前数年已经去世了,那么尊文又坚持《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诗为许浑作不能怀疑,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就不能对刘皋被杀的时间记在“大中十二年”提出怀疑吗?尊文小标题所提出的“《闻边将刘皋无辜被戮》作于大中十二年的事实能够否定吗?”这又有多大的合理性?
第三,在《新说考辨》中,我们考证了许浑大中八年还有诗作,并论证《后序》撰于大中十年,故许浑应卒于大中八年。因此在此文第二节之末说:“《后序》既然提到许浑、杜牧、张祜、赵嘏、顾非熊等人‘身没才二三年’,则许浑等上述诸人之卒,据《后序》而论,就不可能卒于大中十年之后,而只能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又在全文末说:“据我们前考许浑卒于顾陶撰《唐诗类选后序》的大中十年前的二三年间的论断,如果《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为许浑诗无疑,则刘皋被杀事,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人许浑去世之前。”但这样两段话却被《如何考订》概括得走了样:“在全文第二节末说:(许浑)‘只能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全文结尾在考辨《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后再一次表达了这个意见,并将‘只能’一词换成‘必’字,意在强调这一结论的不可动摇。”又在之后干脆改成这样:“说‘大中十年前三年’许浑就去世,是和现存史料相悖的”。对照上下文,将我们的“许浑等上述诸人之卒……”改为“(许浑)‘只能卒于……”;将“则刘皋被杀事,必在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的诗人许浑去世之前”改为是针对许浑之卒年而说的;最后又干脆将“大中十年前二三年间”改为“大中十年前三年”,这样的概括符合我们的原意吗?根据这样的概括而批评我们“这在逻辑上实在自相矛盾,让人很难理解《新说》的文理所在”,也就失去了它的针对性。
注释:
①吴在庆、高玮:《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中州学刊》2007年第6期。下引此文以及它文均在首次出注,之后则不具注。
②罗时进:《唐诗演进论·许浑年谱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4—273页。下引此文均见此,不具注。
③罗时进:《晚唐诗人许浑卒年应如何考订——与吴在庆、高玮商榷》,《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下引此文均见此,不具注。
④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3687页。
⑤《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186页。
⑥(13)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230、180页。
⑦(11)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第1473—1474、1420页。
⑧陈才智:《元白诗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⑨吴在庆:《张祜卒年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
⑩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2页。
(12)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许逸民、常国武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992页。
(14)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15)赵翼:《陔余丛考·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315页。
(16)《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16页。按,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岳麓书社,1994年,第332—333页。
(17)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岳麓书社,1994年,第332—333页。
(18)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八四,中华书局,1966年,第1959页。
(19)赵琳:《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1—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