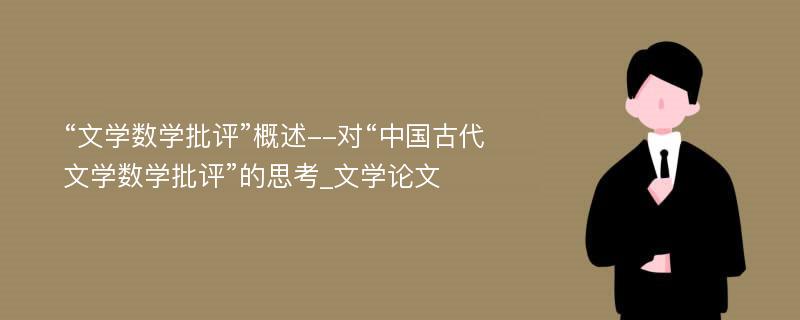
“文学数理批评”论纲——以“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为中心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理论文,批评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1-0003-09
一、“文学数理批评”的提出
已故著名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以下简称“程文”)的结论中说:
我们认为,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的方法来。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论家从过去的及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论以丰富理论宝库并指导当时及后来创作的传统做法,似乎被忽略了。于是,尽管蕴藏在古代作品中的理论原则和艺术方法是无比地丰富,可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这就使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免局限于再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既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所发现,也就不能使今天的文学创作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这种用一条腿走路的办法,似乎应当改变;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也似乎应当重新使用,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1](P25-26)
他还说,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作了这样一次尝试。对一与多在古典诗歌中存在诸形态”[1](P26)作了探索。
程文写于1981年10月,至今已经20多年了。应当说,“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这种用一条腿走路的办法”,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虽然本人并不想评论“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局限于一种再认识”的结果,是否一定如程先生所说的那样前景暗淡,但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界一时很热的“话语转换”讨论所显示突围的努力,至少说明这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正遭遇“山重水复”的困惑。即使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并不存在这种困惑,而一直处在“柳暗花明”良好状态,那也不过“一手硬,一手软”,“重新使用”“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也就是“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的工作,仍然是当务之急。基于这种认识,近几年以来,笔者在学习、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概括“古代文学的理论”,希望能有些微的创获。先是从我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入手,研究古代“数”在文学中的应用,逐渐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数传统”的认识,进一步提出并尝试“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并通过对鲁迅小说的解读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所应用,因此有对“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思考。(注:拙作有关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若干结构模式》,《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天道”与“人文”》,《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虽然这些个案的探索和理论的思考还很不成熟,甚至可能是失败的尝试。但是,本人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之下,企图“再开采新矿”的动机,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解,也希望本人所谓“文学数理批评”的提法,能够得到认真的批评和热心的赐正。
二、“文学数理批评”试定义
我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所谓“数理”是指文学文本中数字作为应用于计算之“数”同时又作为哲学的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因时代、民族、地域与作家的不同而异,但是都因其作用于文学形象体系的建构,而形成文本建构的数理逻辑。这种逻辑在文本的存在状态,有隐有显,或隐或显,从根本上决定形象体系的意义指向与基本风格,是文学研究中与形象并重不可忽视的另一半。文学数理批评就是从文本所应用“数”的理念与具体“数”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考察作品的数理机制,分析其在文本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形象意蕴的渗透与制约。
因此,文学数理批评不仅是形式美的批评,也必然达至形象内涵即文本思想意义的探讨。我在拙作《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一文的结尾,曾就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可能性展望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不单纯是文学形式的探讨,而将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有时本身就是这种阐释。它不排斥任何其他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却不是任何其他理念与方法的附庸或补充,而是相对于传统“象”或“形象”批评的另一翼,与象或形象的批评相得益彰。但在当今古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形象中心的批评理论多借自西方,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而结合了象或形象的数理批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却有“那把钥匙开那把锁”的根本之用,所以格外值得重视和提倡。著者相信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引入数理批评的原则,将有助于建立写人与叙述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的新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模式。[2]
在坚持这样一种基本认识的前提下,我把“中国古代文学”扩大到“(全部)文学”的理由,及其在东西方文学范围内“数理”一词的根据,还需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把“中国古代文学”扩大到“(全部)文学”,虽然已经有了对中国古今文学所作初步考察的基础,但是对外国文学的缺乏研究,仍然使这一提法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来说,早就有学者对数理批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过论证,并得出结论,例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要人物之一波里克勒特认为:
(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3](P388)
亚里士多德认为:
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4](P265-266)
胡世华曾著文引马克思的话:
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5]
因此,尽管本文“文学数理批评”的提法好像自我作古,但是,在对中国文学的考察和参考西方古近代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笔者相信“文学数理批评”在古今中外文学中都有根据,是可以成立的一种认识。
(二)从以上引文还大略可知,西方自古就重视自然与人文的“数理”关系。这在波里克勒特是指“数的关系”及其“意义”;在亚里士多德是指“数理诸学”与“美”的关系,即把美的研究纳入以数学、物理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范围;而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得出文学批评也应该可以“运用数学”,并且“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换言之,文学数理批评不仅是文学批评题中之义,而且是其“真正发展”的标志。三种说法虽因历史语境的区别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有后先相承的联系即共同性,也就是认为“数”、“数理”或“数学”的研究,是艺术与美与包括艺术与美在内的一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之点,甚至是其高级的形态。
由于人类的共同性和民族的差异性,我国作为哲学概念的“数理”的内涵(详后)与西方互有异同,并且东西方古今“数理”之义也自有异同,从而形成文学数理批评在世界范围的的普适性与在各国家民族范围的特殊性,乃至对具体文学现象做具体分析,是文学数理批评的根本原则与灵魂。而作为一种理论,“文学数理批评”的内容及其实现的方式也当随在有异,表现为适合各自不同对象的具体的原则与方法。换言之,“文学数理批评”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它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才能得到验证和体现,特别是在当今初始的阶段,我们并不想也不大可能很多地注意其作为理论体系的特征。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文学数理批评”仍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包括(1)因“文”知“数”,(2)即“数”求“理”,(3)因“理”论“文”。这就是说,文学数理批评的对象是“文”即文本;批评者的任务是从文本发现其各种“数”和“数的关系”,经由这各种“数”和“数的关系”进入文本思想与艺术之“理”的探讨;因“数”之“理”而对文本做出相应的说明与评价。
已如上述,这种批评必须结合了文学的“象”或“形象”的研究才便于进行;反之,理想的“象”或“形象”中心的批评也需要结合了“数理”的批评才有可能完成。因此,与中国哲学传统“象数”一体之学的理论相应,“数理”与“形象”的批评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而相对于“形象”中心的批评,“数理”批评优越性在于,只有它才能充分说明文本即形象体系的逻辑性及其意义。因此,文学数理批评是通过深入揭示文本的数理机制及其作用、价值与意义。而达至对包括形象在内的全部文本意义的说明,与形象中心的批评殊途而同归。
“文学数理批评”就形式而言,有似于西方“原型”或“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但是,它特指从“数理”角度所作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数理批评”不排斥“原型”、“结构主义”或社会历史的、形象的等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却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批评。虽然它的理论与方法还有待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进一步确立与完善,但是,笔者相信其是一项大有希望的学术事业。但是,鉴于古今中外文学的多样性和可以想见的文学数理批评的复杂性,以及目前文学数理批评初创的阶段,笔者对此课题的探讨又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文学入手,本文以下将主要说明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有关问题。
三、“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释义
由于中国上古文献——文学的自然传承关系,这里所指“中国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史哲各种文献与后世各体文学作品。而所谓“数理”之“数”与“理”,则是《周易》所称“天地之数”、“万物之数”和“天下之理”(《系辞上传》)、“性命之理”(《说卦传》),原属古代哲学的概念。
“天下之理”、“性命之理”即“道”,而“天地之数”、“万物之数”又无非“天下之理”、“性命之理”即“道”的体现。《说苑》卷六《复恩》引孔子曰:“物之难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这就是说,“数”中有“理”,“理”因“数”见。而“数”因此能有沟通天人的作用。《国语·周语下》说:“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世人行事则当“举措以数,取与遵理”[6](论人),“修其数行其理”[6](君守);临事则当“察数而知理”[7](兵法),“推数循理”[8](平津侯主父列传)。因此,“数理”一词虽然晚至《三家注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句下《集解》引干宝曰“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才正式出现,但是,早在上古就已经是先民知行的一大原则,百世不替。《张载集·横渠易说·系辞上》:
天浑然一物,终始首尾,其中何数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渐尔。理须先数天,又必须先言一,次乃至于十也。
这句话说明为什么古人以“数”明天道之理,即今所谓自然数之序正合于人想像中天地自然之序,所以数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天地万物之理无可见,则因数见之;无可知,则以数推之。明何孟春《余冬序录》卷二记洪武末钦天监博士元统之言说得明白:
盖天道无端,惟数可以推其机。天道至妙,因数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数显,数从理出。故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也。
这也就是说,数是沟通人天,以人知天、合天的凭据,数之理即天理——天道。从而天之道可以用数表示。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模式的两种经典表述,一是《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易传·系辞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云云,就都是用数作为世界生成变化的代式。至今日常生活中“凡事要心中有数”的说法,根本上也是古人这种“惟数可以推其机”思想传统的曲折体现。但是,这种古代哲学以至体现于当今日常生活的重数传统并没有引起学者更进一步的注意,所以,现代哲学家虽然看到了所谓中国古代“宇宙代数学”的发明,却没能更进一步发现“数”在中国古代以至今天作为哲学地把握世界的工具,有无可忽略、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至今哲学研究中几乎见不到有关“数理”的论述,是非常遗憾的。
而同样遗憾的是在文学研究中,也几乎完全忽略了上古在“举措以数,取与遵理”生活原则影响下形成的我国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
《易经》是我国今见最早“倚数”编撰的文献。《汉书·律历志》云:“伏牺作八卦,由数起。”《易传·系辞上》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又说:“……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而《易传·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这些论述综合表明,八卦——《易经》是我国最早“倚数”编撰之作,而《易传》是最早带有数理批评内容的文学批评论著,是中国文学数理批评的萌芽,实际开启了中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先河。
四、“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与方法都因其对象而存在,并主要因其自身的积累而发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基本依据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批评对象即古代文学文本的依据
如上所述及,以《易经》打头,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形成“倚数”编撰的传统,从而其文本能以成为数理批评的对象。
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对此,笔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说明,基本的看法如该文提要所说:
中国上古重数,以数为宇宙化生的关键与万象联络的枢纽。先民由卜筮之数创为八卦——《易经》,开创我国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包括《易经》产生的商周之际,文献——文学中重数用数的传统经六次变迁而贯穿始终,表现由文献而文学,由诗文而小说、戏曲,由外及内,由明转暗,由粗转精等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久被忽略而显得隐晦。其隐晦之故有社会、哲学及文学批评诸方面的原因。从作品的不同层面看,这一传统表现为编撰“倚数”称名和布局谋篇,“倚数”行文的模式与技巧等,综合而成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机制,表现出数理美的特点。[2]
此种机制与特点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基本内容,也是其成立的根本依据。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倚数”编撰传统的久被忽略,当今欲揭示它并使之得到专家学者的承认,以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当务之急仍是要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数传统及其所形成文本数理机制与特点的关注,然后才可能有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真正的讨论。
(二)古代文学研究的依据
1.古人有关“文学数理”的认识与揭示
古代的文学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中并非没有涉及文学数理批评的文字,然而不多;又因其往往有数术的色彩,所以也不大受人注意。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说:
天、地、阴、阳、木、火、金、水、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毕数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此也。
这是说古人篇籍有取天数特别是以“十”为编撰之法的原则。又王充《论衡·正说篇》曾经批评的汉代经师之说:
《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共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又:
经传篇数,皆有所法。
王充对这些说法的批评未必不有正确的成份。但是,考之《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大史公书。
又考之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
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司马迁自道《史记》尚且“倚数”编撰,汉儒“经传篇数,皆有所法”之说,也就未必全无根据。而晚至萧梁时代精研文学的刘勰著书尚且标榜倚用“大易之数”,则后世可知。所以,我们对古代篇籍有“倚数”编撰的传统完全可以抱有信心,作实事求是的探讨,恰如其分的估量。又,《孟子注疏·题辞解》“正义”曰:
此叙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数也。……然而篇所以七者,盖天以七纪璇玑运度,七政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于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已。
又,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批》说:
《西游记》称为四大奇书之一。观其……西天十万八千里,觔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卷之数终,真奇想也。
《西游记》第59回黄周星批评说:
小说演义,不问何事,动辄以三为断,几成稗官陋格。
陈士斌诠解《绘图增像西游记》第100回批云:
三藏历叙三徒出迹,来往功程,正是传经之的旨,连去连来恰在八日之内,言只在三五妙道运用之内也。篇中来东已五日,则归西止三日。来五回三,已分明指示,人自不悟耳。读者谓此等处,俱不可思拟,奈何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耶。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文体作品的批评,也都显示或揭示了古代文学“倚数”结撰现象的存在,可以视为“文学数理批评”早期的萌芽。虽然极为零星而且粗浅,但是,至少已足证明我国古代并非完全没有人注意到文学“倚数”编撰传统,而文学数理批评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也是有基础和根据的。
2.今人具有“文学数理批评”实质性内容的研究
近今学者涉及文学数理批评内容或带有文学数理批评色彩的论著时有问世,然而大都因人类文化学对神秘数字关注而涉及文学,不是真正的文学数理批评。笔者阅读所及,近今具文学数理批评实质性内容的研究论著,美国学者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与《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值得特别重视。前者的第二章《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神话与原型》之三《中国传统的对偶美学》与第三章《奇书体的结构诸型》,后者有关“四大奇书”百回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西游记》“运用数字构思”[9](P160)特点的揭示具有数理批评的意义。但是,作者似乎不曾注意中国上古即有“倚数”编撰的传统,加以其西方文化的立场,便很轻易地把这一现象纳入到了“原型”批评的视野[10](P48),与文学数理批评擦肩而过。
除此之外,近今也有一些具文学数理批评实质性内容的论文发表,最值得注意的是杨希枚先生《再论古代某些数字和古籍编撰型式的神秘性》与《古籍神秘性编撰型式补证》(以下合并简称“杨文”),以及上引程文等3篇,接近于我们所称的“文学数理批评”。
杨文揭示先秦及汉代若干古籍“倚数”编撰的特征,指出:
古籍或具神秘编撰型式原是至迟东汉以前的旧说。虽然,王充曾著说驳斥,却认为经传篇数都是据事意而作,决不该有所谓“尚书二十九篇法日斗七宿”之类的“法象之义”的。此外,著者曾推想,如魏刘劭撰的《都官考课》七十二条,仲昌统撰的《昌言》二十四卷,说不定也是具神秘性的编撰型式。……近半年来,著者……发现不唯若干古籍确具神秘性编撰型式,篇卷章句之数都与神秘数字信仰有关,且整个社会社会生活的生活事物无一不与神秘数字信仰有关,而实为一盛行神秘数字的社会了。这就是说,著者前此近乎空想的想法不仅原是先儒的旧说,且实为前代的史实。[11](P116-117)
按作者所谓“前此近乎空想的想法”即:
中国古代对于某些数字或有某种神秘的信仰,影响所及,古籍的句数也就常采取了某些固定的数字,从而使得编撰型式也就具有某种神秘意义。”[11](P717)
杨文具体论证了先秦两汉古籍如《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泰山刻石铭》、杨雄《太玄经》等,各为“篇卷或句数符合神秘数字之数,因而成为象征天地的一种神秘性的编撰型式”,另有《史记》等“其他可能是神秘编撰型式的古籍”数种。从而说明“一项古代书论编撰的情况,就是古籍除了基于义穷理竟的通则而决定其编撰型式,即其篇卷或句数,甚至音韵的变化以外,也由于神秘数字的信仰而采取某些固定的型式”,“古籍具有神秘性编撰型式的无疑是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11]。
杨文的探讨带有文学数理批评实践的性质,对本人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有过重要启发作用。不过杨文作者不曾或者也不想把他的工作说成是“文学数理批评”,而且其所论述限于西汉以前,又主要是就“篇卷”数的考察而未深入到文本叙事与描写的分析。同时,他考察的目的主要是文献学的,即认为有关“神秘性编撰型式”的研究有利于“古籍的鉴定”、“解释和勘正”[11]。所以,杨文作者主观上完全不涉及我们所谓的文学数理批评,因而在我们看来,也还只能算作文学数理批评的初步的不自觉的实践。
程文从“一与多”的对立统一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描写与结构”,他的结论包括五个方面:“一多对立(对比、并举)不仅作为哲学的范畴而被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且也作为美学范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达成一种更巧妙的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在一与多这对矛盾中,一往往是主要矛盾面,诗人们往往借以表达其所要突出的事物”;“一与多虽然仅是数量上的对立,但也每在其中同时包含着其他一对或数对矛盾,因而能够表现更为丰富的内容”;“一与多对比或并举……运用得合适,也能使不相干的事物发生连系,表达了诗人丰富的联想,也同样能给人以艺术的满足”。[1](P24-25)
程文虽然只限于“古典诗歌的描写与结构”中“一与多”现象的研究,但其实质是深刻的文学数理批评之作。其与杨文的不同之处在于:
1.杨文用古代神秘数字说明“古籍编撰型式”,是以古释古;程文从现代哲学角度讨论古典诗歌中的“一与多”,是以今释古。
2.杨文以古籍“篇卷”“句数”等较为外在的“编撰”形式为研究对象,而程文关注的是“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等更为内在的艺术个性。
3.杨文的研究以“古籍鉴定”等为目的,程文则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艺术的批评。
总之,杨文是文献学的研究而带有文学数理批评的意义,程文是文学的研究并实际深入到了文学数理的批评。不过,程文是“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的“一次尝试”,所以也不曾想到古代文学中尚有更广泛的数理问题和提出文学的数理批评。但是,程文与杨文互补,加以浦安迪先生的研究,构成近今我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研究中“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的典范,也构成了我们所说“文学数理批评”事实上的开端。
上述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和古今学者有关这一传统的揭示,是我们提出并尝试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对象基础和学术背景。笔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之上开展工作的。
五、“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解剖
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可大致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作品命意批评,即“数”作为天命、天道观念在文本中作用、意义的研究,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中的“天数”、“气数”等往往指“天命”、“性命”之数。这种“数”本是对所写人事生灭兴衰宿命的解释,无可称道,所以从来为研究者忽视,却决定着作品总体构思包括对题材处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使作品深蒙神秘气氛。例如,《三国演义》描写各种场合中“天数”一词出现17次,“气数”一词出现10次,多半用于说明汉朝衰亡之象,而终卷诗“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一联无疑代表了作者宿命的历史观,是《三国演义》总体构思的基本思想依据。《三国演义》研究如果不顾及书中频繁出现的这种“套语”和“俗套”的意义和作用,必将忽略天命论对作者创作的重要影响,而作品无可奈何的悲剧意味也将不能得到深入的解释。
(二)编撰体式批评,即古代文献——文学“倚数”为篇卷乃至字句之数规律性的探讨,如上引杨文所举证各书,以及诗之连章、律体,赋之“七”体、“九”体,古文、时文章法,小说、传奇文体所依据数理的研究。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民族特点的进一步发现和切实深入的探讨,其中蕴涵各自特定数理的发掘,必将导致对这些文体性质、意义的新的认识。例如,熊笃《诗词曲艺术通论》认为,近体诗律起源因于南齐永明间沈约“四声八病”说的发明,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形成五、七言律绝的定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初直接受到了《周易》四象八卦观念的影响,而实践中能广为文坛大众所接受,“也正与集体无意识中对于‘八’、‘四’这些数象所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的长久积淀有关”[12](第2章《近体诗源流论》),实际是从数理角度说明“五、七言律绝的定式”形成的原因,显然是很深刻的看法。
(三)框架结构批评,即对文本总体构思所依据数理的研究,如有关诗文之起结布局、小说戏曲叙事框架等所依据数理的研究,包括诗文运笔之“起承转合”,小说、戏曲叙事之“谪世升仙”、“轮回报应”以及各种“善报”、“恶报”和“大团圆”结局等等,这类研究将深入探讨文本内部的框架结构与“天人合一”思想的普遍而深刻的联系。笔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一文中曾经指出: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苏轼《赤壁赋》……大致各抒作者一己之情,却也要说到宇宙万物,以天地悠悠、人生恨短的雄阔悲慨之境打动人心。王羲之《兰亭集序》在感慨宇宙无穷而人生恨短之后说“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就总结出了中国抒情文学的这一特点。至于各种轮回报应、谪世升仙或悲欢离合故事的小说戏曲更是如此。总之,无论作者情趣雅俗、手眼高低,把笔往往就有“究天人之际”的倾向,结果抒情之作每充满今所谓终极关怀,叙事文本的结构框架则很象一个圆。“文学是人学”为文论家共识,但笔者每感慨中国古代文学之为“人学”常常是“天人之学”。[2]
(四)情节及语言模式批评,即对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连章方式、细节描写以至语言运用等方面依据各种数理形成的叙事、抒情模式的研究。如抒情之“叠韵”、“叠章”,叙事之“三复情节”、“三事话语”、“三极建构”、“七复”、“九复”以及各种错综数字行文的样式,[13]基本上都是一些“俗套”或“套语”。其在古代文学中应用的广泛,远非一般想象所能测,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有关的研究将结合我国古代社会习俗等情况,系统揭示其各自的数理依据和表现特点,深窥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理。例如以《三国演义》“三顾草庐”为代表的“三复情节”,实际是至晚从《左传》就已经开始形成,并累世有广泛运用的一种“俗套”。它的思想渊源在于先民对数字“三”的认识和“礼以三为成”即后世“事不过三”的习俗,[14]等等。
(五)时序批评,即对古代文学文本以季节月令时日等历数为结构素或象征的研究,拙文《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曾经指出:
《红楼梦》第1回说:“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而作为宝玉及贾府命运象征的甄士隐的破家和悟道正由于元宵节一场大火,可知“元宵节”是原本叙事大转折处,惜今本描写已不够明确。这大概可经由《金瓶梅》溯源于《水浒传》的影响。《水浒传》集中写了四次元宵节,分别在第33回、第66回、第72回、第90回,各都为关键处。[2]
补充地说,三书中“元宵节”大约还有象征的意义。这类有关时序在文本中作用、意义的研究,将有助于说明古代文学作历时性叙述的数理依据及其技巧和特点。
(六)空间批评,即对文本中以“四至”、“五方”、“八方”等方位之数为叙述次序的研究,如拙文《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所指出的:
早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至汉乐府有“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等古辞,《木兰诗》乃有“东市买骏马”以下四句,都不曾标明而实际有四方之数存为内在的联络。[2]
这类叙述模式在描写战争的小说中应用最为广泛,《三国演义》所写“八阵图”是典型的体现,《水浒传》第76回回目即“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而在《西游记》中演为“东土”“西天”、“四大部洲”、“四海龙王”等。有关的研究将能揭示古代文学的空间与环境描写的数理依据及其特有的文学意蕴。
(七)比例批评,即对古代文学文本中的各种对偶、对比、序列关系的研究,如诗文辞赋中常见的数字阶、数字对、数字串,以及小说、戏曲中常见的人物群类等。[2]有关的研究将能揭示文本因此呈现的序列美、错综美、对称美等等特点。上引程文“对一与多在古典诗歌中存在诸形态”的研究,可以看作此类批评中“数字对”考察的范例。
(八)节奏批评,即对文本叙事或抒情发展变化所依据数理的研究,如诗词字节、音节与韵律共同组成的节律变化,小说戏曲情节发展张弛缓急等等,其实都依据并包含一定的数理。前人论文常言之“一唱三叹”、“一波三折”,毛宗岗评《三国演义》叙事所谓“笙箫夹鼓,琴瑟间钟”、“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以及笔者所称“三变节律”[15]等,都是文学叙事或抒情节奏中数理的表现。有关的研究将能揭示古代文学叙事抒情节奏变化所依据的数理原则及其形成的特殊美感。
上列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各类研究,肯定不够全面。其称名述义也未必十分妥贴,但是,笔者相信其基本的方向是正确的。唯是在具体应用中将因文体文本的不同而随在有异,但是,一般说来对经典文本全面的数理批评,都很可能是多角度的考察,并且还可能有特殊的数理表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是从古代文学重数和“倚数”编撰实际出发的文学研究,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即就有处说有,而决不无中生有。但是,比较外在已成为“俗套”的表现,古代文学的数理机制更多深隐的富于灵性的存在。因此,研究者必须有充分的敏感发现、发明那些深藏不露的数理现象,例如《儒林外史》写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三复情节”就是典型一例[15]。
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又是从古代数理哲学入手的文学研究,因此必须尊重古人把握、表现或再现世界与艺术接受的方式与特点,在承认其历史合理性的前提下论其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今用,而不应仅仅绳以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标准对古代文学妄行褒贬。例如以现代的标准,很容易把古代文学的数理表现视为思想的“糟粕”和艺术的“俗套”而轻视、轻弃之。百年来学者没能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和自觉开展数理批评,部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又必须借鉴吸纳现代哲学与文学研究各种有益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全部)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数理机制有很大不同,也许现在还不能肯定中外当代的文学中还有这样一种机制,但是,至少“三角恋爱”原理是文学的通则,其他更多的东西只有通过研究才能发现。
然而,即使我们抱有文学数理批评一定成立的信心,它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与方法,在目前还只能说是想象中或实验中的事业。因此,本论纲总体上也还只是一个构想,难免浅薄和谬误。但是,本人从考察古代数字“三”在小说中的应用入手,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文学数理批评”,自以为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之认真的理论概括过程,纵然不免浅薄和谬误的成份,却只是识见、能力所限,或不必被责以好为“体系”之过。而在当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还需要大力“开采新矿”,现代文论又多是“拿来主义”改造之成果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界真正缺少的还正是中国人自己的“体系”;加以对学术界日渐宽容的信任,所以,本人敢于标新立异,以图千虑之一得。是耶,非耶?盼专家读者有以赐正。
2003年10月24日星期五初稿
2003年12月19日星期五改定
收稿日期:2003-11-25
标签:文学论文; 数理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易经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杨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