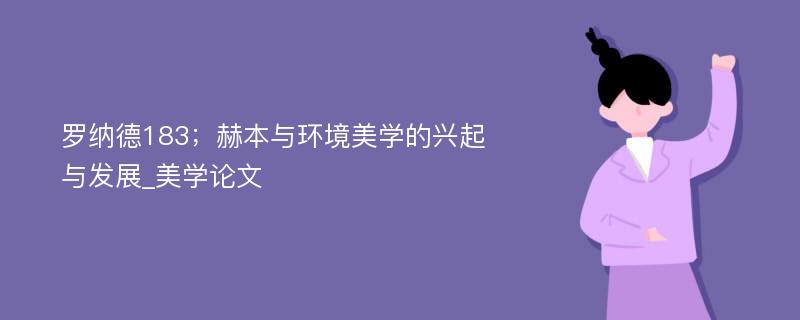
罗纳德#183;赫伯恩与环境美学的兴起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美学论文,环境论文,罗纳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4.2 环境美学的兴起是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环境保护运动合力产生的结果,但其直接的渊源与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纲领性论文《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有关。尽管现在环境美学已发展出各种迥异的学术立场,但若溯其根源,这些立场大多可直接或间接追溯至赫伯恩当初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赫伯恩继续扩展和完善了其中某些重要的主题,对环境审美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作了重要的揭示,并激发了环境美学领域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析。赫伯恩在环境美学研究中引发的持续效应值得我们关注。本文试从“自然与艺术”、“严肃与琐碎”、“形而上想象”和“融合的途径”四个方面对此稍作评析。 一 自然与艺术 根据赫伯恩的研究,自然美曾经是18世纪美学关注的首要内容,对艺术的关注在当时反而是第二位的和派生性的。但是现在,美学基本上只关心艺术,很少真正关注自然美。美学甚至被定义为“艺术哲学”或“批评哲学”,研究艺术在描述和评价艺术对象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①美学理论对艺术美的偏爱和对自然美的忽视导致了在传统的自然美学中“如画性欣赏范式”(picturesque paradigm)几乎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该范式根据艺术欣赏所需要的特定视角、距离、观者心境和作品形式特征来衡量自然美的优劣,例如,艺术欣赏需要一个确定的、有边界和形状的人造物,并假设该造物背后有一人类作者的存在,而自然美却很难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前者而言,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起乔治·桑塔亚那关于自然美的描述,即“自然风景是一种无定形的东西;它几乎时时都是气象万千”②;至于后者,我们也知道哲学和美学史上的有神论或泛神论的看法,认为自然背后的作者实际上是“神”而不是“人”)。因此,根据“如画性欣赏范式”,自然美在其感知和形式特征以及体现人类意志方面是无法与艺术品相媲美的,这导致旧的自然美学几乎不假思索地判定自然美低于艺术美的结果。 但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并没有严肃地探讨自然本身的美学性质,也没有充分理解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欣赏的复杂经验。而赫伯恩对自然美的理解正是从自然与艺术各自不同的特性开始的。从审美经验上看,赫伯恩认为艺术欣赏所要求的远距离静观并不适合自然欣赏:在自然欣赏中,观者“可能会作为一个静态的、分离的观察者面对自然对象;但更典型的是对象从各个方向包围着他。在一片森林中,树木包围着他;他被群山环绕着,或者就伫立在平原之中。如果景色在运动,那么观察者本身也可能处在运动中,并且他的运动可能是其审美经验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试想一个滑翔机飞行员。在气流把他托在高空的平衡中,他在漂浮中感到快乐”③。这意味着在自然欣赏中观赏者介入自然环境的程度要远高于艺术欣赏——在艺术欣赏中我们需要和作品维持一定的距离,但在自然欣赏中我们不是站在欣赏对象之外,而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从审美对象来看,赫伯恩用“有框架”与“无框架”来区分艺术对象与自然对象。艺术作品一般都是有“框架”的,这种“框架”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绘画或雕塑的物理边界,也包括宽泛意义上的将艺术对象和其背景区分开来的设置,比如剧院中舞台和观众的分离。通常来说,在艺术品框架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我们对该作品的审美经验中,例如,观众席中偶然传来的咳嗽声是不能进入正在演奏的弦乐四重奏中并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的,它只能被视为对艺术欣赏的干扰。艺术框架的存在保证了所有感知要素都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和确定的范围内,为艺术家的创作和观赏者的欣赏提供可以控制的稳定性。相较而言,自然对象则是“无框架”的,在自然欣赏中各种不可控制的声音或视觉等因素会不断侵入并试图整合进我们的整体经验中。一方面,当我们欣赏一片开满郁金香的田野,鸟儿的啾啾、昆虫的和鸣还有不时闯入我们视野的小动物,这些背景因素并不像在艺术品中那样容易被排除;另一方面,观赏者自身的运动也带来了自然对象的不确定性,比如当我们从几十公里外来看这片郁金香田野时,它可能只是我们所见的背景中的一个色块,此时它所引起的审美反应也就完全不同。 赫伯恩认为,自然的“无框架”特点在审美上有其不利之处:各种因素会不断挑战我们的整体经验并试图修正它;不断侵入的因素会造成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熟悉的欣赏模式上;甚至还要冒着无法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审美经验的危险。但赫伯恩强调,“如果‘框架’的缺席排除了自然审美对象所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那么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可预知的感知惊奇;并且它们的可能性为自然的凝视提供了一种冒险的开放性”④。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自然对我们感知力的挑战并适应自然对象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我们就能经验到想象力的突然扩张。赫伯恩因此驳斥了如画性旧范式的那种带有等级性的审美观,认为“在自然对象和艺术对象之间的某些重要区别不应使我们认为前者在审美的重要性方面不如后者,而应看到其中有些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和颇有价值的自然审美经验。这类经验在艺术那里并不能达到自然所能提供的程度,在一些情况下艺术甚至根本没有提供这类经验”⑤。 赫伯恩对自然审美经验的动态性以及自然审美对象“无框架”的分析已是环境美学中的经典论述,但在笔者看来,该论述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启发了自然审美的一种新思路,即“按自然所是”(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而不是按艺术的欣赏范式来对自然进行欣赏。例如,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为艺术欣赏需要观赏者掌握一定的艺术传统和艺术风格的相关知识,正如我们要正确欣赏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就需要有立体主义的背景知识那样,要正确地欣赏自然环境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等知识。这相当于在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的类比中凸显自然欣赏自身的特征,认为自然欣赏需要根据自然的相关知识而不是艺术的知识来定义。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则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自然自身的审美特征。他不仅倡导观赏者对自然环境的全方位、多感官的参与和沉浸,甚至将参与和沉浸同样视为艺术欣赏的根本特征,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与艺术在内并以审美参与为核心的更普遍的美学体系。在这一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和卡尔松相比,伯林特更强调自然欣赏的参与特点。 相较而言,赫伯恩本人关于艺术和自然的看法则更持中一些。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根据艺术考察的自然》中,赫伯恩一方面认为艺术经验能为自然欣赏提供丰富的新视角,另一方面又强调“一些限制条件是必需的,我并没有宣称自然只能根据艺术来被审美地思量,或者说艺术经验对自然经验的每一种影响都必定是有益的。对于一个贝壳、一个洞穴或一棵蕨类植物这样的自然事物来说,去除它们和人类智巧的各种关系,而只是根据产生它们或者维系它们生存的自然过程来进行观赏,就审美而言是有好处的。审美愉悦可以从了解到那些过程与艺术家行为之间的遥远距离中产生”⑥。赫伯恩主张的是艺术经验和自然经验之间的相互借鉴、促进和修订,而不是不加批评地“根据艺术对自然形式的同化作用来看自然和艺术之间的关系”⑦。 但也有学者怀疑这种艺术和自然间的区分是否恰当,如迪菲(T.J.Diffey)提出:“‘自然美’意味着那些非艺术美的美,那些既非人像也非美德也非任何其他的美。这让‘自然美’看上去好似某种残余的范畴,只是那些不能塞进其他类型的美的垃圾倾泻场。”⑧在艺术和自然之间进行区分是否站得住脚,它们之间是否还有更为复杂的关系,恐怕还需要更多哲学和美学上的检阅。但较之于用艺术欣赏范式来同化自然欣赏的如画性欣赏范式传统,这种区分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其最大的贡献是为自然环境谋得了审美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用赫伯恩的话来说就是根据与“自然有关的标准来评价自然美”⑨,即“按自然之所是”来欣赏自然美和评价自然美。这对于20世纪囿于艺术欣赏范式的传统自然美学向环境美学的过渡无疑起了奠基的作用。 二 严肃与琐碎 卡尔松和伯林特曾经描述环境美学中两种重要途径的起源:“哲学上的对自然美学的研究更加和赫伯恩的洞见有关。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最初的发展,每一种都涉及那种对感知和形式特性的远距离静观旧范式的回应,并且每一种的先兆都出自于赫伯恩那篇开创性论文的中心主题。一方面是对旧范式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在感知和形式特征的拒绝,并追求赫伯恩所说的对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必须得到我们对它的真实本质的认识的引导;另一方面是对无功利、远距离静观的审美欣赏的传统观念的反对,并认可赫伯恩关于自然环境有助于一种开放的、参与性的和创造性的欣赏模式的建议。”⑩其中第一种倾向即是以卡尔松为代表的强调科学知识在自然欣赏中地位的科学认知途径,而第二种倾向则是以伯林特为代表的强调审美参与、情感和想象的涉入等特点的途径。 这两种途径的兴起都可追溯至赫伯恩,很大程度上和赫伯恩思想的复杂性有关。在描述自然审美经验的特征时,赫伯恩认为,因为不受艺术史传统、固定视角和背景知识等“框架”的束缚,自然审美更容易实现一种开放的、参与性的和创造性的欣赏模式;同时他又强调“框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自然界的审美缺陷,它实际上构成一种和艺术欣赏不同但同样值得严肃对待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来源,因此我们需要按照“自然之所是”而不是根据艺术来认识自然真实的审美本质。赫伯恩因此强调了自然欣赏两方面的特征:它的感知特征的开放性和对它的真实本质的认识。在后来的《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琐碎和严肃》一文中,赫伯恩用“琐碎”和“严肃”概括了自然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并深化了该主题。 赫伯恩认为:“我们需要承认在大多数自然的审美欣赏中存在二元性,即感知的成分(sensuous component)和思想的成分(thought component)。首先,它有感知的直接性:例如,最纯粹的例子就是人们对天空的颜色或景观中云雾的翻腾感到惊讶。但是,更通常的情况是,当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实际的和可能的、现在和过去进行暗中比较时,就会有一种思想的成分在里面。”(11)以秋天的落叶为例,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着它落下而没有任何想法,这就只是一种感知的直接体验;但如果我们在一种更加复杂和深刻的经验中沉思一片落叶,那么,在其感知形式中可能会夹杂着对时光易逝的感伤,对四时更迭的了解,对生命和人类命运的感契,甚至是对宗教静谧和空无观念的透悟。赫伯恩认为,自然的审美经验实际上存在一个宽广的渐变范围,其一端是以感知的直接性为特征的琐碎而容易的美,另一端则是存在思想成分的严肃和困难的美。在艺术中,艺术史知识的存在使我们可以很好地把琐碎性从严肃性中区分出来,比如我们可以说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艺术批评是琐碎并且未中肯綮的;但在自然欣赏中,严肃性和琐碎性之间的区分则缺乏明确的引导。尽管如此,赫伯恩认为两者的区分仍是必要的,要使自然欣赏具备和艺术欣赏同等的重要性,就有必要实现前者从琐碎性到严肃性的上升。赫伯恩说:“假设积雨云的轮廓类似一篮子洗涤物,而我们在思量这种相似性时感到愉悦。假设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思量的不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或者柯勒律治式的‘幻想’)方面,而是尝试去认识云层内的紊乱状态,以及从它中间或旁边掠过的气流,它们决定着云层的结构和可见的形式。难道我们不应该说,与其他经验相比,这后一种经验没那么肤浅或做作吗?难道对自然来说它不是更加真实并因此更值得拥有吗?……如果在艺术中存在着从容易的美到困难且更严肃的美的过渡,那么在对自然的审美观照中也存在这样的过渡。”(12) 赫伯恩关于“自然美的观照应从感性的琐碎走向严肃的思想”这一观点对卡尔松影响甚大,后者于1977年发表的《论量化景观美的可能性》是其关于环境美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卡尔松引用了赫伯恩的例子和思想,并指出:“关于环境批评的基本事实就是:这种作用像艺术批评的作用一样,同时要求具有关于所欣赏者的知识和为欣赏它而应有的敏感性。……只有知识不能产生审美欣赏,只有敏感性则只能产生很贫乏的欣赏。……因此,一个人没有有关环境的许多知识,仅仅具有感知方面的敏感性,也许能够发现一处山景的平衡;但是,要感受这座山坡上所生长树木表达的坚决和顽强,除敏感性之外,还需要有关这些树木和这些树木所生存环境的知识。”(13)正如赫伯恩将自然欣赏分成感知的成分和思想的成分那样,卡尔松认为自然欣赏包括敏感性和知识,而要实现赫伯恩所说的从琐碎向严肃的上升,就要在自然欣赏中强调知识的作用。对于自然欣赏中较少认知维度的因素,如审美参与、情感、想象和直觉等,卡尔松认为对它们的关注无疑是偏向琐碎那一端,因为它们仍主要关注审美当下的感知特征与形式属性,因此需要“深入探究赫伯恩所认为的这种审美欣赏,即自然欣赏尽管是开敞的、参与式的和创造性的,但如果要使得对其的审美欣赏更加严肃而非琐碎的话,这种欣赏必须被知识与理解所指引”(14)。 但卡尔松对赫伯恩的思想显然作了过度的阐发。虽然赫伯恩说自然欣赏要实现由琐碎向严肃的上升,但他所谓的“严肃性”并非就等于科学知识。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第一,赫伯恩所讲的“严肃性”是科学知识所不能完全容纳的。赫伯恩明确表示他“会反对一种单方面地以科学为主导的自然欣赏”(15),认为科学可以实现一种客观化的欣赏,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允许科学取代感知经验。因此,赫伯恩只同意自然的科学知识与审美有关并且可能会加强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但不同意“它们有一种权力去取代其他要素”(16)。第二,赫伯恩强调的是“琐碎性”与“严肃性”的平衡与融会。他认为两者并没有完全取代对方的能力——流行的感知惯例和简单化需要抵制,但反思性的成分也可能是老套的、不成熟的或没有活力的。因此,琐碎(感知的成分)和严肃(思想的成分)构成了自然审美的两极(extremes),只有“在这两个极点之间,我们会发现一种可以接受的理想,甚至在这里严肃的审美感知鼓励我们自己去加强思想的成分,使之无限靠近这个极点但又不会超越它,甚至因为这个极点失去了具体感知的那种活泼性”(17)。 可见,赫伯恩意在取得琐碎性与严肃性的平衡。在他看来,严肃性的获得既不是非得落实在科学知识之上,也不是非要排除审美参与、情感、想象和直觉等因素。同理,赫伯恩也不同意审美参与等因素能够压倒甚至取代自然审美中的严肃性。他批评伯林特道:“审美欣赏是艰苦的,并且会涉及许多感觉的作用;我们会参与、沉浸在我们审美欣赏的事件中。但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概念方式来标志我们的非审美的、实用倾向的感知和关注的非连续性。因为只有充分的分离,我们才能将反思性的和感知的成分综合为一个复杂的个人经验的整体。它是既/也的关系而不是或此/或彼的关系。”(18) 三 形而上想象 赫伯恩关于“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到严肃”的主张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提出的“形而上想象”这个概念上。想象对于艺术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艺术作为一种人造物,本身就是人类意志的体现,艺术品的框架、材质、线条、造型等,都通过瞬间界定欣赏者注意力的边界而有意地引导他们的想象。但是,想象在自然欣赏中的位置则仍未明确:一方面,如赫伯恩所说,和艺术品相比自然对象的特征就是无框架,那么这种本质上无法框住、无法限制的审美对象将对我们的想象力造成挑战,为自然审美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提供了某种冒险的开放性——用赫伯恩的话说即“自然世界的形式为想象的训练提供了空间”(19)——如果我们能够适应这种变化,最终很可能会经验到难忘的想象力的突然扩张;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对象本身并非人造之物,自然欣赏中的想象力又极易被认作人为“附加”在自然之上的,故如果要实现按照“自然之所是”来欣赏自然,那么这种附加在自然对象上的想象力就不仅会被视为琐碎的和偶然的,甚至还会被视为不恰当的。 在《景观与形而上想象》一文中,赫伯恩提出“形而上想象”这个概念,试图通过提升想象的严肃性来解决上述矛盾。所谓“形而上想象”是指在自然的形式特征中阅读出某种“高层次的意义”,即我们的想象能够将自然界解释为“揭示了某种形而上的洞见”,例如,从自然的形式中洞悉生命意义、人类状况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形而上真理。在赫伯恩看来,自然景观的审美经验是多层次的,纯粹的感知成分如颜色、形状、声音、触觉、味觉等,就算有也很少会独立存在。更通常的情况是我们会在感知成分上添加某些反思性的关联,比如,看到地平线上黑暗的云层,我们不会只将它看成纯粹的某种形式,还可能会将它视为一种不祥的预兆,又或者在极地风光中看到某些包藏终极意义的宇宙论真理。这种我们无法用语词和概念清晰表达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先验真理就是赫伯恩所说的“形而上想象”。赫伯恩认为,这种有关形而上真理的想象具有相当的严肃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与自然同一”的观念——在欣赏自然时,我们有时会感到主客消融于无间,人与自然分享着共同的连续性:分叉的叶脉就是我们的血管,波浪冲刷岸边的节拍宛若我们呼吸的节奏……在这里,“与自然同一”是自我与自然的协调、共鸣和一致。通过这种我们与自然的连续性的意识,一种强烈的接受或者顺从的观念将被置于自然审美经验的核心,即相信如果不遵从自然或宇宙的规律人类将遭受巨大的灾难,因为自然的破坏也代表着我们自身生命形式的崩坏。 赫伯恩这种形而上想象的思想至少从两个方面对那种割裂琐碎性与严肃性的主张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对于那种只专注于自然欣赏的感知特征如审美参与、情感、直觉等的主张,赫伯恩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自然审美经验中确实存在思想的成分,并应该严肃地将之视为对某种事实或真理的揭示。因此,他认为不应“去催促一种摆脱形而上学的自然审美经验,因为那会是非常肤浅的,还不如去鼓励承认它的无尽的多样性”(20)。另一方面,赫伯恩又不赞同卡尔松那种科学认知途径。原因之一我们在上文已提及,即赫伯恩认为提升自然欣赏的严肃性并不一定就非得落实在科学知识上,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是超出科学的界限的,在自然欣赏中我们能够获得某种形而上的理解,足以让自然欣赏从琐碎的感知升华为某种严肃的体悟;原因之二是自然欣赏中的思想成分扎根于感知经验中,因此它不是抽象的科学宇宙论或形而上理论的命题,而是通过我们的愉悦经验所揭示出的关于某种真理的洞见。我们可以发现,赫伯恩的“形而上想象”概念得益于一种灵活的解释策略,在他看来,“很明显在景观的审美反应的两极之间存在一个变化的范围。在其中一极,我们对于瞬间辨认出来的富有表现力的性质感到满意;而在另一极,我们运用预设的形而上理论的想象图式,在一个宽广的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中描述世界的特性。在这两极之间有着各种可能性”(21)。意思即说,单纯的当下感知和单纯的理论预设构成了自然欣赏“琐碎”和“严肃”的两极,但是这两个极点在真实的自然欣赏中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这两极之间各种可能的组合,即感知与思想、琐碎性和严肃性、想象力与形而上洞见的组合。 赫伯恩关于想象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的看法也在环境美学中引发了相关的争论。艾米丽·布雷迪(Emily Brady)很明显接受了赫伯恩关于自然审美更加自由和灵活,并因此更加倚重欣赏者的感知和想象的思想,反对以卡尔松为代表的那种重视科学基础的认知模式,提出要以感知和想象作为自然审美的核心。为了展示想象在自然审美中的作用,她区分了四种和自然对象有关的想象模式:探索型、投射型、扩展型和启示型。探索型想象即在感知对象形式的时候展开的自由沉思,比如看到一棵年龄久远的树而联想到人生经验丰富的老人;投射型想象是在感知之上添加或覆盖一个投射的意象,典型的例子是夜晚仰望星空时我们可能会把几何形状投射其上,将其视为各种动物或其他东西;扩展型想象则扩展了感知所给予的东西并因此超出了仅仅是把意象投射到事物上的想象方式,比如看到海边的卵石我们可能会想象它在被海水冲刷而磨光前的样子;当扩展型想象启发了对一种审美真理的发现,这种想象行为就是布雷迪所说的启示型想象,比如对河谷、冰川的沉思常常揭示了自然界的巨大力量。我们可以发现,在布雷迪划分的四种想象模式中,启示型想象与赫伯恩提出的形而上想象最为接近。但布雷迪并没有给予启示型想象特别的重视,她只是对自然欣赏中的想象力的普遍模式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并未真正留意到赫伯恩的“形而上想象”这个概念更重要也更深远的意义。 玛西娅·伊顿(Marcia M.Eaton)不同意布雷迪的看法。在她看来,创造性的想象和虚构确实有很多优势,但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限制,则常常会发展出不利于自然生态的观念,因为想象和虚构经常带有“感伤化”和“妖魔化”的倾向。例如,奥地利作家菲利克斯·撒尔顿于1923年创造了小鹿斑比这个形象,将鹿塑造成天真无邪的可爱动物,结果导致一些地区鹿的过量繁殖并由此引发生态危机;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的食火鸟是超过一百种热带雨林植物的种子传播者,但因其形状过于恐怖怪异,当地民间故事和传说常常把它描述为妖魔般的怪物,这使得这种鸟的数量因滥杀而锐减,最终导致大量树种的消失。基于这种考虑,伊顿认为“如果可持续性环境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虚构必须服务于事实”(22),而她所谓的“事实”则主要是卡尔松所提倡的那种生态学知识和环境科学知识。在她看来,即使这样的知识确实剥夺了某些审美的乐趣也是值得的,因为只有知识才能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践。伊顿强调想象要以坚实的知识为基础,在提升想象的严肃性上她与赫伯恩的观点相似。但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赫伯恩并不认为自然欣赏的严肃性就只能落实在科学知识上,他认为在琐碎性与严肃性的两极中充满了无数可能的组合,科学知识在其中有自己的位置,但不能取代其他资源的作用。由此来看,伊顿的主张仍显得有些狭隘。自然欣赏中的想象和认知之间的矛盾,最终要放在赫伯恩所说的琐碎性和严肃性的更宽广的范围中去解决,并且要回到赫伯恩所说的维持两者合理的比例并保持两者无数可能的组合上去。 四 融合的途径 赫伯恩对于环境美学之兴起的贡献无可否认。作为环境美学实质性的起点,赫伯恩富于原创性和启发性的观点为后来环境美学的一些重要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激发了这个领域中不同立场之间持续的争论。但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赫伯恩对于环境审美经验宽广的、复杂的特征描述倾向于达成某种多元的融合,可以将分化出来的各种环境美学立场融合为一种灵活而具体的策略,在其中,无论是审美参与、想象、情感还是科学知识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此意义上,赫伯恩的思想不仅是环境美学的起点,也构成了环境美学的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分化出各种重要的环境美学立场,同时也预示着分化之后的一种可能的回归,即回到原初最具孕育性的各种分叉边界融合的阶段。 这种融合正逐渐成为环境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上面提到的玛西娅·伊顿,我们还可以在雪莉·福斯特(Cheryl Foster)、罗纳德·摩尔(Ronald Moore)和卡尔松最近的主张里看到这种趋势。福斯特认为,在当代自然美学的认知途径和注重感知因素的途径之间出现了“分裂”。尽管她宣称主要捍卫的是后者,但她同时也强调两种途径之间结合的必要性,即“没有哪一种途径可以单独充分地解释自然经验如何产生我们所知道的审美价值”(23)。与福斯特一样,罗纳德·摩尔也认为,当代环境美学出现了各种立场的分化,然而他注意到了“赫伯恩坚持认为自然是无框架的,但他否认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结合想象和明智的视角来恢复与自然的友好关系”(24)。依据这种“结合想象和明智的视角”的主张,摩尔提出一种“融合的美学”(syncretic aesthetics),试图以此调和各种立场:一方面强调科学知识能够给予我们很多有关自然的信息,但并不至于主导我们对于自然的审美欣赏;另一方面则强调在自然欣赏中想象是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也不能将自然完全交付给不受限制的想象。他认为,“应该可以建立一种关于自然对象的审美价值的视角,这种视角融合了自然科学和想象,又不会使其中某一方占据压倒性的地位”(25)。摩尔依据的理由是,对象置身于性质的集合中,其中一些是审美的,一些是科学的,一些是政治的,等等,我们无法将对象截然分成单一性质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其实是在一种综合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语境中认识审美对象的,并且每种因素在审美欣赏中都起到或重要或次要但却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融合的美学也成为卡尔松最近的主张,在深入考察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和他自己主张的科学认知途径之后,卡尔松认为两者各有千秋,因为“参与美学在非人类中心和环境聚焦方面特别突出,而科学认知主义在严肃性和客观性要求方面更为突出,可能还要加上伦理参与要求。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将这两种主张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单一、统一的方法”(26)。 本文认为,融合的途径不应被理解为某种既定模式。其关键不在于强调科学和想象、感知和思想、审美价值与道德判断之间的硬性结合,而在于赫伯恩所说的“在琐碎和严肃的两极之间保持着结合的无数可能性”。其具体的结合则要视当下的审美语境和欣赏者自身情况而定。很多时候赫伯恩给出的答案是开放甚至是模糊的,他强调艺术和自然的区分但又认为艺术经验和自然经验之间可以实现相互借鉴;他主张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但又认为两者应相互蕴含;他肯定形而上想象的重要性但又指出两者的结合具有无限可能性——这多半是因为他更倾向于提出灵活的模式而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未来的环境美学研究必定会寻求更加广泛的学科交叉和更深层次的视域交融,在此意义上赫伯恩的融合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的起点。 综上所述,罗纳德·赫伯恩在环境美学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且持续不断的影响。他于1966年发表的论文《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是环境美学兴起的实质性起点,在这篇论文及后续研究中提出的多个主题对环境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关于艺术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启发了“按自然所是”来阐发自然审美特征的新原则,突破了用艺术同化自然的那种如画性景观欣赏旧范式,从而推动了20世纪中叶传统自然美学向环境美学的过渡;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后来环境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重要的立场,即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科学认知途径和以伯林特为代表的审美参与途径;但赫伯恩更倾向于通过融合的途径来模糊环境美学中各种立场之间的边界,他提出的“形而上想象”这个概念试图通过想象力和形而上洞见的结合来解决自然欣赏中想象力的迸发与思想的深度之间的矛盾。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环境美学各种立场之间的持续分化和争鸣,这种融合的途径已成为该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赫伯恩的思想无疑也为未来的环境美学提供了某种新的指引。 注释: ①③④⑤(12)(19)Ronald Hepburn,“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43,p.45,p.47,p.48,p.57,p.47. ②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255页。 ⑥⑦⑨Ronald Hepburn,“Nature in the Light of Art”,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Lectures,6,1972,p.253,p.244,p.254. ⑧T.J.Diffey,“Natural Beauty without Metaphysics”,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eds.,Landscape,Natural Beauty and the A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0. ⑩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Introduction:The Aesthetics of Nature”,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p.15~16. (11)(17)Ronald Hepburn,“Trivial and Serious 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Salim Kemal and Ivan Gaskell,eds.,Landscape,Natural Beauty and the A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66~67,p.73. (13)(26)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20页;第296页。 (14)艾伦·卡尔松:《自然与景观》,陈李波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第8页。 (15)(16)(20)(21) Ronald Hepburn,“Landscape and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Ali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130,p.130,p.129,p.132. (18)Ronald Hepburn,“Review of Living in the Landscape:Towards an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by Arnold Berlean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56(3),p.303. (22)Marcia Muelder Eaton,“Fact and Fiction i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178. (23)Cheryl Foster,“The Narrative and the Ambient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197. (24)(25)Ronald Moore,“Appreciating Natural Beauty as Natural”,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eds.,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Broadview Press,2004,p.223,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