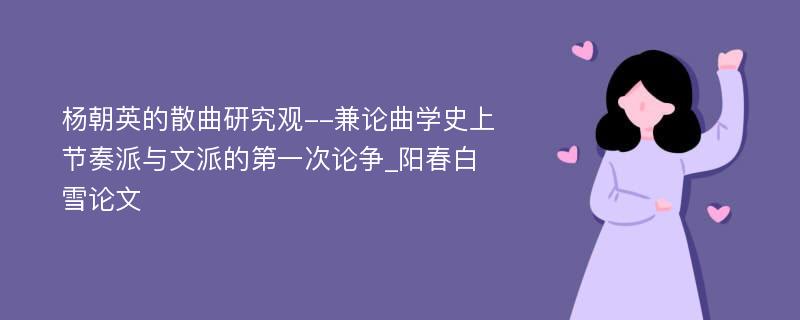
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格律论文,史上论文,试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2-0081-05
杨朝英是一位散曲作家兼编选家。他首开元人选元曲之风,先后编刊了《阳春白雪》与《太平乐府》二书,现存全元散曲的半数赖之以传,杨氏也作为保存元曲的第一功臣而著名于散曲学史。为了全面而确切地理解和把握杨氏的曲学理念及其成就,首先有必要对他的年里、活动以及编刊曲选的时地等有关背景情况略作考述。
一、关于杨氏年里和《阳春白雪》的编刊时间与地点
杨朝英号淡斋,青城人。元代县名有二青城,一在山东,一在四川;此外宋代汴梁城外还有祭祀天地的南北二青城。故杨氏究竟是山东人还是四川人,抑或是河南人,目前曲学界已存在三说,但未见有人提出判断的根据。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杨氏曲学特点的确认,故须预为澄清。我们认为杨氏系南方人,为四川青城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列举理由如下。其一,杨氏闭口韵与开口韵不分,所作【水仙子】“寿阳宫额得魁名”小令,韵脚用“名清印今英寻村”七字,被周德清讥为“开合同押,用了三韵,大可笑焉”[1]。一般说,开口韵与闭口韵混淆是南方人的语音特点,北方人不大容易犯这类错误。无独有偶,明代大词曲家杨慎的曲作中也不乏这类开合同押的毛病。例如他的小令【北正宫·醉太平】《新愁厮禁》和【南商调·黄莺儿】《秋夕忆别》皆用闭口的“侵寻”部韵字,中间却杂入开口的“真文”韵“印”、“恨”、“烬”等字。王世贞《曲藻》曾批评说:“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杨朝英在散曲用韵方面发生的毛病如果不是与杨慎偶然巧合,那他就该是蜀人。其二,以入声作曲,不熟悉北曲“入派三声”的语音规则。他有五首【殿前欢】小令,起句皆作“白云窝”,以求与此调首句“仄平平”的格律相合。这是由于他不懂“白”字在北曲中已经入派平声,不能再当仄声字来用而发生的错误。因此也被周德清抓住,当作“句中用入声,不能歌者”之例予以嘲讽。“入派三声”的实质就是以中原音系为代表的北方语音消失了入声一调,原中古音入声字分别转化为平、上、去三声。根据对元曲家尤其是北方籍曲家的调查统计,其作品用韵都严守着入派三声的规则,几无例外。表明北方人制曲一般不会发生像杨朝英那样把“白”字仍读入声,并计入仄声类的错误。其三,为杨氏《太平乐府》作序的邓子晋自署“巴西”,是为蜀人。邓氏既非曲家又非名人,杨氏请他为自己的曲选作序,有可能是因了同乡关系。此条单独本不成其为理由,但有了以上两条,则可作为一条参考证据。根据以上情况推断,杨氏里籍应为四川之青城,而非山东之青城县,更不可能是“中原音韵”的故乡河南地区。
近人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据周巽《怡情集》卷五《上欧阳玄》诗序,推测杨氏系“青城人而家于龙兴(今南昌)者”;另据张之翰《杨英甫郎中淡斋》一诗,认为英甫当为杨氏之字。可以信从。此外,从他的散曲作品和所编《阳春白雪》透露的信息看,如同钟嗣成、贯云石等众多元曲家一样,他于1324年前后曾流寓江南,而那里恰恰是元代中后期曲家们的集散地和活动中心。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下面对《阳春白雪》编刊时地的考辨再加说明。
《阳春白雪》是元人散曲的第一部选集,开创了曲学编纂学的新学科,影响很大,流布特广,历有多种传本。关于其编刊时地,这是互有关联的两个问题。确定杨选的编刊时间,贯云石序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志。此序虽未署年月,但可推断作期。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说“皇庆(1312-1313)中贯酸斋序之”;杨镰等《贯云石作品辑佚》135页说得更具体:“这篇序写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这无疑是说贯序写于作者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期间,杨选亦编刊于此时此地。孙说的根据可能就是贯序中的“年来职使稍稍暇顿”一句,杨镰等解此句为“今年我任职使官,公务不那么繁忙。皇庆二年二月拜翰林学士”。其实此句还可解作近来退职之后,有了闲暇。那么就是贯氏于延元年(1314)“称疾还江南”之后。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由《阳春白雪》所收贯氏的许多隐逸曲子得到内证。下面只列举他的【双调·清江引】三段,见于各刊本与抄本:
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竞功名有如下坡车,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入安乐窝。
避风波走入安乐窝,就里乾坤大。醒了醉还醒,卧了重还卧。似这般得清闲的谁似我。
弃功名如敝履的“昨日玉堂臣”,明显是作者辞却翰林学士,称疾还江南之后的夫子自道;“似这般得清闲的谁似我”正是序中“年来职使稍稍暇顿”的具体注脚。据此可认定贯序作于元仁宗元年(1314)贯氏退隐江南之后。另外,贯序中还有“北来徐子芳滑雅,杨西庵平熟”之句(注:“北来”据元刊本,九卷抄作本“比来”,与下句“近代”在时间上矛盾,“比”当为“北”之误。),也流露出写于南方的口气,可以作为旁证。至于贯序写作的下限,则容易确定,就是泰定元年(1324)五月,这是贯氏逝世的时间。据此可以推定《阳春白雪》的编定时间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到泰定元年(1324)五月之间,并且能够进一步推断其编刊地点是江南。选中描述苏杭风景的曲作特多,这一内容特征也与上述推断吻合。我们还可再找证据进一步缩小时间范围。《阳春白雪》九卷抄本和十卷刊本中皆选收无名氏【双调·新水令】《大明开放九重天》一套,中有“庆吾皇泰定年”之句,应为泰定改元朝臣颂圣之作。此套可能是选中作期最晚的,如果不是重编本后来增人,那就可以确指《阳春白雪》的编定必在泰定元年之初,贯云石序也作于此时,而不可能再晚。这不仅因为贯氏于本年五月逝世,而且周德清在同年九月已对刊刻流行的杨选作出了反映。从刊出到周氏看见,总需要一定时间。
二、杨氏二选所体现的进步曲学观
一个优秀的作品选集家,必是一个对创作本身有着全面研究和深刻认识的理论家。不过,他的学术成果不是呈现为理论形态,而是落实到了实践层面,体现于对作品的选择去取和编排分类等具体工作之中。杨朝英就是这样一位以曲选家身份、面目出现的曲学家。他虽然没有专门的曲学论著,但是表现在杨氏二选中的曲学观念比起那些古典曲学家的论述显得更为严肃、切实而明智开放。这里先提出最突出的两点予以论析。
(一)崭新的乐府观 作为第一个散曲选集家,面对元人曲坛遗音与新声交奏、剧曲与散曲杂陈的繁乱局面,选什么不选什么,怎样在混沌中给定秩序,建立一个合理的分类编排体例,对于杨朝英来说是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他的《阳春白雪》首先刊载了燕南芝庵《唱论》,表明他的散曲观和分类体例确是受了《唱论》的启发和影响。芝庵是曲学史上第一个对散曲进行分类的学者,不仅杨氏所采用的“乐府”、“小令”、“套数”等术语概念皆为芝庵所创,即是称词乐为“大乐”,在《阳春白雪》中选录苏东坡等宋金人十首词的做法也是承自《唱论》。然而,杨氏并不甘做芝庵的奴隶,亦步亦趋地被动消极接受前人的成说,而是积极大胆地予以修正、改造和提高,消除了芝庵乐府观和分类法中存在的局限和矛盾,从而创造出一套较为科学的散曲文体分类体系。《唱论》采取乐府、小令和套数的三分法,不仅未能提出一个与散曲相当的综合概念,且有分类标准不统一之嫌。他用是否“成文章”即有无文采作为乐府与小令的分界,同时又以篇章体制的长短来区别令与套,造成严重的逻辑层次混乱。杨氏则首先把“乐府”提取出来,使之包含小令与套数两类,升格为一个相当于今日所说散曲的综合性概念,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乐府之下再分小令与套数的散曲二分法。杨氏二选皆名之为“乐府”,说明这是一个总称。在《阳春白雪》中,乐府之下除了小令与套数,还包括一个“大乐”,即宋金人的十首词。这是由于《唱论》对“乐府”的定义不严或语焉不详而导致的误会。杨氏后来觉察到这一失误,所以到他的第二部曲选《太平乐府》中,就彻底把旧词乐剔了出去。由此可见,杨氏乐府观的形成,也有一个不断提炼与完善的发展过程。
在杨氏的新思路中,对“小令”和“套数”两个术语的涵义和性质也做了调整修正。芝庵又称小令为“叶儿”,把它严格局限于“街市小令”或“时行小令”的市井俗曲范围。杨氏则拿来指称所有的散曲小令,在散曲二选中,凡非套数的单章、联章和带过曲均归入小令类,无论其有无文采,也无论其是文人的还是市井的。这与我们今天的认识相一致。至于以谐俗为特征的套数,芝庵虽然指出其形式标志是“有尾声”,这一点大致不错,但还是有两个更为急迫的问题没能说清说透。首先,杂剧剧套算不算套数?其次,他强调“乐府不可似套数,套数当有乐府气味”,如果套数有了乐府气味是否就可以进入乐府的圣殿?这些问题是他的三分法未能或无法回答的。杨朝英在这里表现出十分清醒的头脑。他首先排除了剧套,把套数严格规定在散套的范围之内,然后又不问其文俚,一律归于乐府之下,以与小令相对。这就从外延方面厘清了“套数”的边界,从而避免了不同文体的混乱牵扯。杨氏二分法比芝庵三分法显得明智通达,不仅消解了原来的文人贵族意识或保守成分,而且坚持以篇章体制为分类的惟一标准,严格遵守了逻辑划分的正确规则,因此显得明辨透辟,超越了其前其后常见的词曲不辨、剧曲与散曲不分的思考习惯,代表着元人曲学的较高水准。后来的曲论家和曲选家大多接受了杨氏的乐府观,如现存的另一部元人曲选《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其编排体例就全仿杨氏二选;钟嗣成的《录鬼簿》把散曲家单列,称为“乐府”家,以与“传奇”杂剧家相对,自然也是受了杨氏的启迪。明清曲选和曲论多有称“乐府”者,实则散曲与戏曲杂糅,那是把杨氏早已澄清了的问题又搅乱了,属于学术的倒退现象。
(二)开放性的选曲原则 如果仅仅从杨氏二选的书名和《阳春白雪》选张可久曲最多等表面现象着眼,容易使人想像两书所收必为典雅藻丽和歌功颂德之作,并误认为选集家一定是文采派曲家的代表,近代以来不少散曲论著正是以此为据将杨氏划入乔、张文采派一流的。实际并非如此简单。明曹安《谰言长语》记载:“予家有《阳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刘时中、关汉卿诸人之作尤多。”说明杨选还有多收关汉卿等本色派之作的另一种传本。即使就杨选今本多收文采派作品的事实,也可理解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反映散曲创作的全貌,另一方面也与文采派作家数量多,时代较近,其作品容易收集有关。当然,杨氏作为第三代散曲家,生活在文采派风气弥漫曲坛的时代,要完全摆脱精神氛围的影响,那也是不容易的。《阳春白雪》今本选曲数以张可久为第一,或者就是上述诸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对杨氏二选的认真考察,我们认为他的选曲标准具有开放性,并不囿于一家一派。选中同时大量选入俚俗本色的曲作,尤其是那些不被人作为乐府来看的以谐俗为特征的套数,就说明了问题。杨氏之选之所以命名为《阳春白雪》或《太平乐府》,主要是为了对抗鄙视新兴散曲的世俗舆论,出于为其争身价争地位的考虑。如邓子晋在《太平乐府序》中所说,只不过是为了“重其名”罢了。所谓“阳春白雪”,仅言其曲好。至于“阳春白雪”的具体标准,则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贯云石序就只承认关汉卿等六人的曲作,对于其他人则拒绝批评,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回避态度,实质上是委婉地表达了否定的意见。“客笑,淡斋亦笑”一句颇有深味,说明杨氏作为散曲作家和美学家,是站在贯氏一边的;而作为曲选家的他,又不能与贯氏完全认同,仅仅局限于本色一派,而是还必须兼顾其他。正是杨氏的双重身份,造成杨氏之选的如下三个特点:
其一,坚持开放性原则,尽量揽入作家作品,力图从数量上反映元散曲创作的完貌。综合杨氏二选现存各种版本进行统计,《阳春白雪》选曲达70余家,收录小令533首,套数93篇;《太平乐府》选曲80余家,收小令1067首,套数131篇。二书合计之,汰其重复,共得作家115人,小令1600首,套数230余篇,占了现存全元散曲的二分之一。这些数据说明,杨氏二选在容量上具有一种全集式的气势与规模,几乎涵盖了杨氏当时和前代所有散曲家的绝大多数作品。相形之下,后来的曲选、曲录著作都望尘莫及。钟嗣成《录鬼簿》著录“有乐府传于世”的专门散曲家仅有46人,再加上那些散曲与戏曲兼作者也不过60余人。今日传存的《乐府群玉》和《乐府新声》,是后出于杨书的另外两部元人曲选,虽对杨书有所补充,但终属有限。近人隋树森编辑《全元散曲》,加上杨氏二选之后的元末作家,也仅收集到200余人;而所收散曲前三代作家的作品,除去张养浩、张可久等个别人的专集之外,其余十之八九不出《阳春白雪》,则来于《太平乐府》。我们今天能够直接看到金元散曲繁荣兴盛时期如此多的实物标本,就多亏了杨氏二选。杨氏作为元人选元曲的开创者,在当时收集信息资料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够网罗这样多的作家作品,与坚持了一条全面开放的编纂原则肯定是分不开的。
其二,基本上囊括了元人散曲的优秀作品,尤其是那些名篇精品,从质量上体现出元曲创作的艺术水平。近人赵景深曾批评明末陈所闻编选的《南北宫词纪》说:“北曲部分选得并不怎么好。像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刘致中的《上高监司》、冯惟敏的《骷髅诉冤》这些当时比较进步的作品就都不曾入选。”[2]睢、刘二作是元散套中最著名的篇目,也是中国诗史上少有的奇作。选元曲者如果遗漏了这些作品,当然就可以断定他“选得并不怎么好”。而这两篇套曲恰为杨氏首先收录,前者见于《太平乐府》,后者见于《阳春白雪》。这表明杨氏的审美眼光非同一般,具有时间的超越性。除了上举二篇,还有杜仁杰的《庄家不识构阑》、马致远的《借马》、关汉卿的《杭州景》、《赠朱帘秀》、钟嗣成的《自序丑斋》等名套以及白无咎的【鹦鹉曲】等小令绝唱,也都是在元人文献中仅见于杨书者。我们虽然不能断言杨书已将当时的优秀曲作网罗殆尽,但可以肯定,遗漏的数量绝不会大于收录的数量。杨氏遗漏名篇的例子是有的。如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和【赵调·天净沙】《秋思》,均载于《中原音韵》的“定格”40首,被周德清分别评为“万中无一”和“秋思之祖”。【天净沙】小令还见于元人笔记《庶斋老学丛谈》,并有序云:“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说明在当时文人圈子中流传还是比较广的,元末无名氏的《乐府新声》也收录了此曲。但是杨氏二选今传本均无此一令一套。从时间上看,《庶斋老学丛谈》与《中原音韵》都比《太平乐府》刊行在前,杨氏极可能是未看到这些材料。综合明清两代保存元散曲的各种曲选、曲论以及曲谱著作予以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杨氏二选遗漏名篇的例子乃属个别或偶然,而不是大量的或普遍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它基本上保存了元散曲的精华。
其三,综赅百家,不避亲仇。元人散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本色、清丽、骚雅及格律四派。本色派以关汉卿、王和卿为代表,清丽派以白朴、马致远为代表,都属于散曲的主流、正体。骚雅派以张可久、乔吉为代表,追求典雅藻丽,以作词法而制曲,是散曲的变体。格律派则以周德清为代表,讲究格律声韵,与骚雅派有一致之处。这是大致的区别,就主要倾向而言。具体到某一个别作家,尤其是大作家则并不如此单一纯粹,而往往表现为多种风格并存一身的复杂情况。杨氏二选突破了一般选家全凭个人喜好抉择去取的习惯,自觉坚持了一条兼容并包、综赅百家的选曲原则,因而能够使元散曲各家各派的各种风格之作都得到了反映和保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对那些轻视自己或反对自己的曲家,也同样报以论曲不论人,平等相待的宽容态度。这里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钟嗣成作《录鬼簿》,未收杨朝英;周德清曾对《阳春白雪》公开点名批判。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杨氏初选行世之后,而且周、钟、杨三人都同时活动于当时的元曲创作中心——苏杭江南地区,要说杨氏对周、钟二人的意见、态度一无所知,似乎是不容易解释的。但他在编辑第二部曲选时,不但把二人的名字列入《太平乐府姓氏》表,而且选录钟氏小令20首,套数一篇;收录周氏小令25首,套数三篇。这充分显示了杨氏的宽容大度和论曲不论人的学者风范。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杨氏收录自己和朋友作品的情况。杨氏在二选中计收个人作品27首,而且在《阳春白雪》受到周德清等格律派批评之后还在新编本中主动进行了删除。杨氏虽非大曲家,但一生制作决非仅止此数。贯云石是他的好朋友,既是名曲家,又是社会名流,今存散曲98篇,实际创作肯定要超过此数。而杨书统共收贯曲70篇,与其他相比并不是最多的。这说明杨氏对己对人,无论亲仇,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并不因为关系亲疏而改变根本的选曲原则。
三、周德清格律派对杨朝英的批评
《阳春白雪》问世伊始,立即遭到以周德清为首的江西格律派的激烈抨击。周氏公开点出杨书之名进行指摘,再加上萧存存、罗宗信、琐非复初等江西诸“同志”彼此呼应,一时造成对杨氏的群起围攻之势。这些材料散见于《中原音韵》及其诸序,所提问题达十数条之多。江西派的批评由于过多地充斥着门户偏见和主观意气,因此即使抓住了一些事实,也往往带有粗暴武断与强加罪名之嫌。透过表面的意气之争,埋藏于深层的则是两种曲学观、审美观的对立冲突,是音乐文学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反映,而这才是周、杨矛盾的实质。正是从江西派的批评中,我们得以了解杨朝英关于散曲的一些基本论点,从而对他的曲学观有了更深刻更明确的理解。周、杨的对立分歧首先从最基本的乐府观上就发生了。两人的乐府观都来源于芝庵《唱论》,但杨氏表现出一种不拘成说,大胆革新的开放态度,把通俗的小令与套数都包容于乐府,从而突破了芝庵“成文章曰乐府”的藩篱。而周德清则死守芝庵命题,甚至不顾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发生的矛盾混乱,仍在一力维护旧说。他一会儿说“套数能摘为乐府者有几”,一会儿又指着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套说“此方是乐府”;他甚至为了找一条“六字三韵语”,竟不惜牵扯王实甫《西厢记》剧曲“忽听一声猛惊”为例。这就不仅违背了他所维护的乐府与套数、小令三分的旧标准,而且连散曲与剧曲的界限也弄混了。周氏从这样一种保守的乐府观出发来非难杨朝英及其《阳春白雪》,以其所见,杨氏开放革新的乐府观自然就是“务取媚于市井之徒”,不足以识辨美丑“妍媸”。从江西派的批评中可以反推以曲为曲,以本色俚俗为美是杨氏曲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本色俚俗,就不能不用方言口语,就不能排除衬字,也不一定非要像诗词的文言或书面语那样,拘泥于“逢双必对”的语言形式。这又与“成文章曰乐府”的命题不能相容,故此被周德清讥讽为“不遵而增衬字,名乐府者,自名之也”。
由于杨、周乐府观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格律论的分歧。从江西派的批评中,得以知道杨朝英主张“也唱得”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也唱得”不是唱不得,也不同于唱得好,而是一种灵活、宽松的格律标准。就音乐文学中字调线条与旋律线条的配合规则而言,唱得好是高严标准,“也唱得”则属于宽松标准,过此以下方为唱不得。杨氏主张的实质是以文学为主,以格律为辅,兼而顾之,能唱就行的曲文本位论思想。与此不同,周德清坚持的则是一条唱得好的高严标准,所取为词、乐配合形式中最佳的自然也是惟一的选择。这一主张的本质则是以格律为主,以文学为辅的曲乐本位论观念。作为视角不同的两种曲学理论,本来各有道理及其价值意义,并不存在此是彼非,互不相容的问题。因此,当周德清硬要否定杨氏标准的时候,就不能不采用粗暴武断、强加横扯的批评手段,终致把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真理也推到了片面绝对的地步。他这样责难杨氏“也唱得”之主张:
不思前辈某字某韵必用某声,却云“也唱得”,乃文过之词,非作者之言也。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谚云“钮折嗓子”是也,其如歌姬之喉咽何?
也唱得”不是唱不得,怎么会钮折歌姬嗓子?“也唱得”是否杨氏的文过之言,即杨氏的作品是否“也唱得”,那是另外一回事,怎么能说就是“非作者之言”?即使亦步亦趋地严守“前辈某字某韵必用某声”,马致远的【四块玉】“彩扇歌,青楼饮”不也遭到江西派的非议?可见周氏所追求的格律准则属于那种极端严格的、完美无缺的典范性准则。既然是典范,是完美无缺,就只有少数人的少数作品方能达到。相比之下,杨氏所持的宽松标准则具有普及性、群众性和现实性,尤其是作为编辑曲选的指导方针,明显具有宽容、圆通与开放的特点,无疑是十分正确而且适用的。如果以周德清的高严标准作为选曲原则,那么只能像他所做的那样,除去“定格”40首,就再也无曲可选了。
“也唱得”并不是要取消曲律形式。事实证明,杨朝英也并非格律否定论者。他在第二部曲选《太平乐府》卷首刊载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且加按语云:“海宇盛治,朔南同音。中州小乐府今之学词者辄用其调,音歌者即按其声。然或押韵未通出入变换,调音未合其平仄转切,此燕山卓氏韵编所以作也。是以录刊予乐府之前,庶使作者、歌者皆有所本,而识音韵之奇,合律度之正。虽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之曲,亦当有取于厮焉。”卓氏《音韵类编》同周德清《中原音韵》属于同一音系,韵部相同,表明杨氏和周氏一样,也是主张北曲应当用北韵,应以“合律度之正”为合作,只是不像周氏那样把格律视为曲之本体,强调得那样绝对罢了。
杨、周之争,是曲学史上文学派与格律派的第一次交锋,争论的结果,是两派观点的互相促进、补充与交融,而不是像后来吴江派和临川派那样,都采用“宁可……也不”的语言逻辑把两种不同的观点推向水火不能相容的极端。杨朝英的学者态度和风范尤其值得称道,他不但虚心接受了论敌的不少合理意见,而且不计个人恩怨,在自己编选的第二部曲集中收录了周德清的近30篇作品,体现了一个真正学术家的气度、胸怀和修养境界。
收稿日期:2001-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