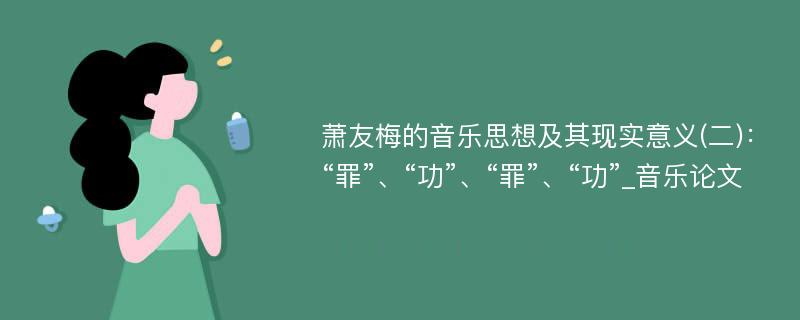
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下)——有“罪”还是有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音乐论文,萧友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萧友梅理论表述中的问题 ——关于三个观点的讨论
尽管怀有某种苛求前人之嫌的担心,我还是想从严格的理论表述角度,对萧友梅的三个观点,提出讨论。
第一,当年他怀着“爱之深,责之切”(注:《萧友梅音乐文集》381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心情力陈中国旧乐落后,确有振聋发聩之效。而与此同时,对于旧乐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继承旧乐传统,虽然也有所述、有所为,但他还是没有给予如同阐述旧乐落后那种程度的关注。换言之,他在旧乐的落后性与不可替代的宝贵性之间,尚未在理论上将二者更恰当地结合起来。我以为还是稍后的赵元任将中西音乐概括为“不及的不同”与“不同的不同”(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261页。)更全面。前者,是指音乐文化发展程度;后者,是指永远要区别于西乐的独特性。而这独特性的深厚根基,就在旧乐之中。所以,必须给予旧乐以至少不低于如同学习西乐那样的重视程度。尽管当时侧重强调旧乐落后有可以理解的理由,但萧友梅在理论表述上,我以为还是有欠完整。
第二,关于“乐器为工具”的观点。由于萧友梅视乐器为工具,便“只求其精良利便,不必严分国界”。他还以交通工具、战争武器为例,证明可以直接采用西方的。这只道出了一面的道理,但还缺少另一面的道理:乐器还有非工具性,即特定的音色、演奏法及其与特定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密切联系。乐器这方面的特性,使它与物质生产、科技领域的工具有所区别。乐器的工具性,是中国音乐可以使用西方乐器的根据,这已为历史与现产所证实;乐器的非工具性,是中国固有乐器不可舍弃的原因,这同样为历史与现实所证实。只看到工具性,会出现取消中国固有乐器的倾向;只看到非工具性,会导致拒绝西方乐器。60年代对“民族化”的片面理解曾在相当大规模上这样实行过,然而那已是历史的插曲。因此,如何对待中西乐器的问题,从理论认识上,我以为应当既看到工具性,也看到非工具性,才更全面,也更符合实际。
第三,在有关“什么是国乐”的讨论中,萧友梅将音乐分成三个要素:一为音乐的内容;二为音乐的形式,即躯干,“即节奏、旋律、和声与曲体等”;三为音乐的演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音乐之生命绝对不寄系于音乐之形式及演出,而仅寄系于其内容”。“国乐与非国乐之分,应以内容为唯一之标准”。什么是国乐应有的内容?即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感。他坚决反对“以为凡用我国旧有之乐器及技术所表演之旧调”便是国乐,说“此种观念实属谬误,且足为复兴国乐之障碍”。他说那种“仅抄袭昔人残余之腔调及乐器,与中国之国运毫无关涉”的,“则仅可名之为‘旧乐’,不配称为国乐也”(注:《萧友梅音乐文集》539-540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我曾将这种观点概括为国乐的“内容决定论”。
从音乐的有益社会功能和道德伦理价值角度定义国乐,有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意义。然而,这里几乎完全忽视了形式方面在确定音乐性质上的作用。实际上,萧友梅在这里触到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一音乐美学界至今仍未理清的“麻烦”问题。萧友梅并未从音乐美学角度就此详述,本文也不能在此展开专论,但还是想提出,“内容决定论”把内容与形式的复杂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了。因为,音乐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形式又是什么,在不同范畴内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又有什么不同所指,在什么意义上二者可以分得开,在什么意义上二者分不开,在什么情况下二者各居于音乐艺术中的什么地位,这些问题,均远非一个“内容决定”即可解决的。比如,就按形式是指“节奏、旋律、和声与曲体”的说法,这已经是音乐本身了!这岂非说,只要内容是现代中国人的,音乐本身什么样似乎是无所谓的。很难说这是符合音乐实践的实际情况的。再说萧友梅指出的那种音乐内容,在那时代中国人身上也并不难得到。而将这内容如何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音乐本身,或者,何种样态的音响躯干才能完美地容纳进并显现出理想的音乐内容,可就谈何容易了。这既需要理论上的切实研究,更赖于创作实践上的反复探索。在我看来,一定意义上,创造中国新音乐的关键、症结、困难,更多的恰在于音乐的形式、躯干方面。因此,我以为在强调内容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指出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依存性,形式对内容的制约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讨论,并不针对萧友梅的实践。一旦涉及到实际工作,纵观他整个一生,有关音乐的任何方面,凡有益于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没有他不支持的。他明确反对的只有他称之为“西乐中的不良好者”JaZZ音乐和中国的“有伤风化和有颓废性或消极性的音乐”(注:《萧友梅音乐文集》345-346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但是,他在理论表述时毕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所承担的使命,是在学习西乐之必要这方面。这也正是他的主要历史功绩之所在。其次,历史每前进一步,或许就要付出某种代价?当学习西乐经验首次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性迫切课题时,就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忽视旧乐?这都是没有答案的假设性问题。好在,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并不是为单纯的评判是非,更不是要求前人事事完善,而是为吸取有益于今天的历史经验。
由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都联系着他的专业音乐教育实践,下面两节,就从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角度,针对两点我以为是最重要的而又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经验予以研讨。
六、中国传统音乐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经验之一
近代以来,历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建设需要两大基石:一个是借鉴西乐文化成果;另一个是继承根植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的中国音乐传统。二者不可缺一(注:参见魏廷格《当代音乐创作的立足点》,载《文艺研究》1988年1期。)。否则,不是消除不了“不及的不同”,就是保持不好“不同的不同”。这就是无论我们主观意愿如何都无法改变的最近一个世纪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客观存在。
在借鉴西乐文化成果这个基石上,萧友梅从开创专业音乐教育入手,再经几代人的努力,业已基本确立。但是,中国传统音乐这个基石怎么样呢?不能说萧友梅无此愿,无所为;或者无论认为他本该做得更多,还是说他已尽力而为;客观言之,在实践上,他终究未能解决好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问题。
问题的解决,首先要有理论上的正确认识。赵元任兼顾“不及的不同”与“不同的不同”,比只讲“落后”前进了一步。但是更完善、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则是萧友梅逝世两年后,杨荫浏发表了《国乐前途及其研究》(注:连载于1942-1944年的《乐风》,《中国音乐学》重新发表于1989年4期。)一文,才真正完成的。遗憾的是,这篇极有见地的论文,几乎被我国音乐界所遗忘(注:参见魏廷格《反思中国现代音乐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关于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国音乐学》1989年4期)和《再议杨荫浏的国乐观》(《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在现代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有必要重温杨荫浏的基本观点。
针对中西音乐关系中的国乐问题,杨荫浏写道:“国乐的独到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合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他说,拒绝中西音乐交融。“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国乐前途充分发展的障碍”。
这是以很有远见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对待中西音乐交融的。这使他区别于(实为高出于)有的带有排外倾向的中国传统音乐提倡者。但同时他又指出:中西音乐交融前各因素“独立基础的强弱”,“准备工夫的充分与否”,会“形成种种不同的交流结果”。他认为当时中国音乐的情形恰恰是尚未充分准备,而“世界音乐的力量却已非常强大”。他担心“我们若再不准备,便只有让整个世界音乐逐渐地来淘汰或排挤了这仅存的一些国乐成份”。这样,他在看到不必拒绝中西交融同时,又指出了无条件地、不做准备地交融可能存在的危险性。这使他又区别于(实为清醒于)有的只看到中西交融的必要性,而对中国传统音乐问题缺乏深入思考的观点。
可见,杨荫浏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既看到了“不及的不同”(世界音乐力量已非常强大),也看到了“不同的不同”(这是他毕生的事业)。那么,一方面不必拒绝中西交融,另方面又存在着西乐可能淘汰了国乐成分的态势,怎么办?文章提出:必须“特殊、过度注意国乐”,即特殊、过度地加强传统音乐的“准备工夫”,造成强大的独立基础。唯此才能在与已有充分准备的西乐的交融当中,产生出合理的、良好的结果来。文章围绕特殊、过度注意国乐,阐述了“国乐的事实”、“国乐将来地位的前瞻”、“国乐研究多方面的准备”、“国乐基础的深度”、“国乐基础的广度”、国乐资料“去取的审慎”、“国乐园地中的工作”、“各人的责任”等等。不仅要充分挖掘、全面收集全部国乐资料,而且要系统整理、深入研究,直到“形成清楚而具体的结构”,能“提纲挈领地令人一望而知”。如此才能为创作提供丰富的材料,才便于纳入系统、有效的教学体系里。为此,杨荫浏设想了一个“伟大而合理的计划”,其中列举了15种(后面还加了省略号)不同学科、专业背景(其中有音乐的也有非专业音乐领域)的人,都可为国乐准备工作做出贡献。文章读来,深感高瞻远瞩、视野广阔、眼光锐利。
这样,杨荫浏就首次同时阐明了中西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国乐准备工作的优先性和艰难复杂性。我认为,这不仅达到了此前中国音乐界对有关问题认识的最高点,而且也为后人多所不及。因为,我们往往不是偏向于忽视传统音乐,就是偏向于排除西方音乐,或者一般性的谈论中西结合。总之,有关发展中国现代音乐两大基石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认识问题,就由杨荫浏于40年代初基本解决了。
但是,理论认识问题的解决,不等于具体实践上的解决。自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实践上究竟如何?
我们历来的专业音乐教育,主观上,可说没有不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然而,也应当说,我们也没有按照类似杨荫浏设想的“伟大而合理的计划”,实行过“特殊、过度注意”中国传统音乐。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音乐教学,却是基本实现了系统化、规范化、便于教、易于学、乐于听。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音乐院校里实际所学到知识的总体情况(抛开个别专业及个别情况),不能不说,依然是西方音乐知识多于中国传统音乐知识。这确为至今犹在、恐怕无须论证就能得到共识的现实。这种情形,对整个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建设,都有直接、间接的不利影响。
在专业领域,首先是学习作曲专业的学生,若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不够,便不可能深刻领悟和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精神,那将断然无法创作出继承并发展了中国音乐传统的作品。而作曲专业学生及其作品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中国现代音乐的未来。其次是西方乐器表演专业,也并非与此无关。因为,只有真能深刻理解本民族音乐,才能深刻理解他民族音乐。如果中国人仅只试图用外国人的心态去理解外国音乐,那将永远达不到外国人的水平。任何演奏家都要有审美支点,否则就难免某种空虚。中国演奏家第一个审美支点,应当、也只能来自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这一点,从著名钢琴家傅聪的演奏艺术成就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傅雷影响下,傅聪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是相当深厚的,这是他能跻身国际钢琴乐坛的审美支柱之一。这个领域不是常有中国学派之说吗?除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前提外,只有真正熟谙中国传统音乐精神的演奏家,才能在西方音乐表演艺术中创造出中国学派来。其实,即便是学习中国传统乐器的学生,也存在着如何学、怎么学才能真正将中国音乐气质、神韵融入自己灵魂的问题。每当看到个别学生热衷于在中国传统乐器上演奏西方乐曲,就不免使人疑心是否“心态西移”?
由于专业音乐教育领域里中国传统音乐知识传授不足,在非专业音乐教育领域,将会更难以选择、充实进适当的教学材料。进而再从业余音乐界波及到更广大的社会范围。于是渐渐地,在社会公众的音乐审美心理中,就会缺少更自觉、更稳固的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意识,削弱、淡化民族音乐文化上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从精神、心理上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见,中国传统音乐在现代音乐教育中的应有地位问题,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怎样解决?这是个重大题目。在此可以提出的是,应该明确地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既然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建设需要两大基石,那么中国的音乐院校的基本责任就应当是并举并重地传授中西音乐知识。所谓并举并重,是说加强中国传统音乐分量时并不以削弱西方音乐学习为代价。反之亦然。既不厚此薄彼,也不厚彼薄此,而是要双双丰厚。这是历史赋予的特殊责任,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西方专业音乐教育最主要的区别,也是这个领域里中国特色的最主要标志。因此,传授西方音乐知识多于中国传统音乐知识,应当只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初创期这可能是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既然应当只是一个阶段,就不该长期(比如七十余年)停留于此,就要在条件允许时,积极主动、不失时机地向着中西音乐知识并举并重的目标逐步实现战略性转变。能转变一步就转变一步,能转变两步就转变两步,直到实现中西音乐知识传授双双丰厚的平衡。
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之一,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准备工夫”,即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本世纪中,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几代中国音乐学家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多种学科的重大成果和多种开拓性、突破性的进步。尽管仍然不能说都已“形成清楚而具体的结构”,尚不能“提纲挈领地令人一望而知”,但仅就“准备工夫”已经取得的成果中,若将应当和可能纳入教学体系的同已经被纳入教学体系的做一比较的话,恐怕还是前者多于后者。这是应当得到改变的。如果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界和教育界能共同持有更明确的战略眼光,将“准备工夫”的成果成熟一个就在教学体系里纳入一个,成熟两个就纳入两个,使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也成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便于教、易于学、乐于听的教学,进一步改变缺少足够有说服力的音响材料的情况,那么,中国传统音乐一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切实进入各专业音乐学生的知识结构之中。
当中国传统音乐知识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里得到更充分、有效地传授后,就会在非专业音乐教育领域里产生相应的良好影响,进而再从业余音乐界波及到更广大的社会范围。于是渐渐地,在社会公众的音乐审美心理中,就会逐步形成更自觉、更稳固的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意识,增强、浓化民族音乐文化上的认同感,使之成为从精神、心理上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我们不应当满足于现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的状态。在21世纪临近之时,我们有必要从专业音乐教育的全局到各个具体专业的局部,对其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和要求等等,给予全面回顾、总结。以便尽快完成向着中西音乐知识并举并重、双双丰厚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战略目标的转变。这是萧友梅想做而不能做、今人已有可能实施的。
当我们回顾作为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音乐思想时,我以为这是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经验之一。
七、创作人才培养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历史经验之二
没有民间的、专业的及所有类型的音乐创作,就没有音乐艺术,也就没有缘音乐而生的以及与音乐二字有关的一切事物。没有各种类音乐创作的发展,就没有音乐艺术的发展,也就没有缘音乐而生的以及与音乐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因此,各种类音乐创作的发展,是音乐艺术得以产生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也是缘音乐而生的以及与音乐有关的一切事物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动力。
这段话,似属常理范畴。然而,当依此观察中国现代音乐创作问题时,却在音乐学者中间多有争议。例如1986年召开的一次音乐学术会议,讨论“当代中国音乐的紧迫问题”。当时我提出,最紧迫的莫过于“我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多种形式风格的、声震国际乐坛的、伟大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由此,音乐理论界应当“为创造高度发展的各种形式风格的当代中国音乐,提供全面的理论根据和理论指导而开展研究”。(注:《艺术美学文选》(1979-1989)244页,重庆出版社1996年。)对此,许多学者朋友都不以为然(注:参见魏廷格《现代中国音乐前途之所系——关于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关系》,载《音乐研究》1987年1期。)。直到多年后,还有位学者朋友揶揄创造伟大的中国现代音乐的观点是“心理失衡后的功利冲动”和“情绪化的非理智冲动”(注:《寻求自立——谈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意义》,载《人民音乐》1990年2期。顺便说,这位很有才华的作者最近发表的几篇评论,表明他已开始关注中国现代音乐创作问题。我认为,着眼于宏观,音乐学者的理论关注,是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意思是只有失去理智者才能把中国音乐创作看得如此重要。看来,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在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中的地位,还是个不得不先予讨论的问题。
诚然,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不仅是指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它还有更宽泛的内容。但在其中占有主导、决定性意义的,却只能是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因为,本质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应当是直接表现现代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反映他们新的音乐审美好尚和审美需求的音乐。只有高水平各种类中国现代音乐创作,才是这种音乐。优秀的外国音乐和中国过去的音乐虽然是现代中国人音乐精神食粮的一部分,但却并不具备中国现代音乐的典型属性,故不能说这两种音乐是本质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音乐。试想,若无本世纪以来各种类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概念,还凭何撑起呢?显然,没有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音乐文化。没有这种创作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因此,轻视、或无视发展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重要性,实为否认发展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必要性。
这种否认,有违事物发展规律。中国音乐从她诞生起,就象一条永无尽头的长河,注定要不停地流淌、发展下去。她既不会因外国音乐流入而消失,也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时独自滞留在中世纪。实质上,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不是发展与否的问题,而是发展得快些或慢些、好些或差些、多些或少些的问题。
本世纪以来,各种类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已有不可小视的成果,这是几代中国作曲家怀着对中国现代音乐的理想和使命感,发挥他们杰出才能创造出来的。有了这种成果,才有了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之存在。否认这种成果和文化的存在,那是不顾事实。
但是,中国现代音乐创作迄今仍未达到理想境地,这也为众所公认。这就直接、间接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试举几例:
一个突出现象是,在专业音乐舞台,由于中国曲目不足,只好任由外来音乐文化充满于自己的音乐空间。某些外国音乐具有人类文化财富性质,也应当是现代中国人音乐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本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外国音乐“占领”了过大的音乐空间。在中国举办的所有西方乐器演奏比赛,其中的中国曲目都少得不成比例(甚至全无中国曲目)。长期如此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在音乐教育上,由于没有足够数量高水平中国现代音乐作品作为教材,我们的音乐院校、系科,不可避免地都是以传授西方音乐知识为主的。这不正是现实存在着的现象吗?中国的西方音乐表演艺术,由于没有足够数量高水平中国作品为凭借,所谓“中国学派”,还不近乎空谈?遍及全中国的“钢琴热”,由于受到中国作品不足的限制,近百万中国业余钢琴学生,不也是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接受相对系统的西方音乐教育吗?(注:关于这一点,虽然也存在中国钢琴曲作品不足的问题,但“责任”并不全在曲目不足上。)倘若我们有时忧虑西方音乐排挤掉中国音乐的话,那也必须提倡继承并发展了中国音乐传统的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因为这是抗拒这种“排挤”的强大力量之一。仅赖中国旧乐是不够的,虽然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同样应当是现代中国人音乐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中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战略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创作问题。创作问题不解决,中国现代音乐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解决。没有现代创作的真正繁荣,哪怕有再多的音乐院校,再多的音乐人才,再优的音乐设施,再大的资金投入,也无法使中国现代音乐文化这一概念,获得其应有的充实、丰满的内容。
另外,站在国际性立场上看,中国音乐应当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贡献。这贡献不能仅限于中国既有旧乐,而更应在于现代音乐创作。至于某些西方人士希望中国只有旧乐,那是我们不该接受的“博物院”的中国观念。
大凡能够做出国际性贡献的音乐文化,首要的是该文化本身要有深厚广博的传统,这是在广袤地域上生成的又经悠远历史考验的独特价值的保证。其次要有现代性的音乐思维方法,这是专业化、现代性、国际性所必需的。可否说,中国是欧洲“文化圈”以外的为数不多的具备(或可能具备)以上条件的国度之一。我想,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早在1923年,王光祈就说他从事研究的“最后目的”是为产生“有资格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成一个对立形势”的中国新音乐(注:《王光祈音乐论文选》49页,成都王光祈学术讨论会筹备处1984年。)。1927年我国第一所音乐学院成立时,首任院长蔡元培就提出:新的中国音乐创作“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亦非绝不可能”(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载《音乐杂志》,1928年1卷2期。)。至于稍后些的所有有成就的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几乎无不将创造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的中国音乐作为他们的理想,这实为近代以来几代中国音乐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音乐界的历史夙愿。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尚处起步阶段,当时中国文化、音乐界人士就有这种可感可敬的历史感和自信力。当前,中国现代音乐创作已有长足进步,我们后人何以反而称其为“情绪化的非理智冲动”?
历史的时针已经指向世纪之末,而我们仍不能说中国音乐界的历史夙愿已经实现。因此而生的种种不利影响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消极作用。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曲人才的培养。因此,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将作曲人才的培养置于突出地位,就有战略性意义了。
回顾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史,在一般性标准上,对作曲人才的培养都很重视。但在特殊的战略性高度上要求,则多有欠缺。例如,从观念上,似乎我们还从未明确地将培养作曲家作为专业音乐教育最重要的战略性目标并采取相应措施。我们也没有有意识地将最优秀的音乐人才集中到作曲专业上来。对于怎样的知识结构、课程设置、教学手段才能培养出将要承担历史重任的中国作曲家。似乎我们也没有做过专门研究。至少,仅就作曲学生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来看,按现有的有关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还相当薄弱,远不能构成坚实、深厚的创作基础。还有,我们是否为已经显露出创造才能的作曲人才提供了可能提供的最佳创作环境?须知,相当数量成功的中国作品,是由“业余身份”的作曲家写就的。需要研究的问题肯定不止这些。
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当我们不着意于培养作曲人才时,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西方乐器表演艺术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因为欧洲音乐已经为这门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学生在领悟西方音乐的美学趣味、掌握表演技巧上,又表现出很高的才能。在这个领域取得成果,对于天才的中国学生,相对而言,并非特别困难。而另一方面,在中西融合中间踏出一条中国现代音乐创作之路,那是十分艰难的事业。这要装备尽可能多的中西音乐知识以构成“两大基石”。但“基石”还只是基础,并不是、也不能自动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大厦。“大厦”的建成,还需要解决融合中西两大音乐元素中的全部复杂问题。其中不可避免的要有探索、试验、失败,再探索、再试验、再失败。这需要才能、敏感,需要勇气、信念,更需要百折不回、矢志不渝的毅力等等。总之,在创作专业获得成功,相对而言,比较困难。另外,西方音乐表演艺术的成功(特别是国际比赛中的成功),还特别容易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也可能情不自禁地从中产生对教育成果的满足感(可以有所满足,但却不应仅满足于此)。长此以往,这多少又会模糊培养高水平作曲家的战略意识。不是说应当削弱西方乐器表演艺术,在中国发展这门艺术具有无庸置疑的多方面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推动、促进中国乐曲创作)。只是说,在高质量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真正繁荣之前,从战略上,应当对作曲人才的培养给予特殊关注。
在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中,对中国新音乐创作人才的培养是十分重视的。他那篇写于1916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用下面的话作结束的:“我个人的愿望是……应该更多地注意音乐的,特别是系统的理论和作曲学在中国的人才的培养。”(注:《萧友梅音乐文集》133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以此表明了他写作博士论文的最高宗旨。后来当他说中国国民乐派在世纪内能否实现,全看“吾国新近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时,更说明他深知中国现代音乐的命运是由现代音乐创作决定着的。但他也深知,在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初创时期,还不具备提出将培养作曲家作为最重要战略目标并采取相应措施的条件。并非不想,实为不能。今天,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已经度过了七十个春秋,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提出并实行前人可想而不可为之专业音乐教育战略观念。
当我们回顾作为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音乐思想时,我以为这是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又一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萧友梅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有大功劳于中国现代音乐文化。但他不可能解决极其复杂的中国现代音乐的全部问题。我们后人的责任,应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他不可能解决而今有可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