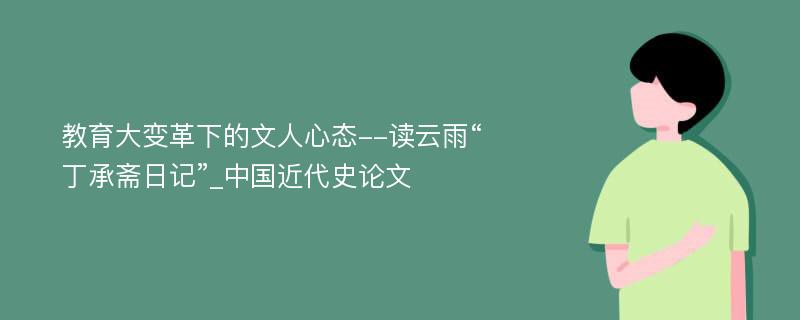
教育大变革下的士人心态——《恽毓鼎澄斋日记》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斋日论文,士人论文,札记论文,心态论文,大变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教育而言,实在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1901年,清政府颁布“变法”上谕,改革教育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朝野的极大关注;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越一年,《癸卯学制》在全国颁行;1905年,清政府明令废止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1907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女子学堂章程……一系列旷古未有的重大变革,震撼着千百万旧教育体制下穷年累月孜孜以求的士人心灵,关系到他们的前途与命运。面对这些巨变,士人们作何感想?他们的心态如何?这些问题在官方档案文献中很难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史研究中也很少注意及此。这是因为人们真实思想和感情的流露,往往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见之于公开的文字。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通过“日记”这种传统士人惯用的形式,记下了彼时彼地的真实感受,“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1]解读这些日记,将日记中的记载与有关史料文献进行对比互证,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一个世纪前那场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加深对历史全貌的认识。
《恽毓鼎澄斋日记》[2]就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的日记。[3]日记的主人恽毓鼎(1862-1917年)原籍江苏常州,河北大兴人(今北京大兴区)。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咸安宫总裁等职,特别是担任起居注官十余年,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可以说见证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业余从医,在京、津一带颇有名气。1901年,清政府设立宪政研究所,恽被任命为总办,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1903年3月,恽“奉旨派充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考官”[4],与孙家鼐、荣庆等一起主持了中国科举史上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的会试阅卷工作。1904年后,恽在京师创办和参与创办多所各类新式学堂并亲自为学生授课。辛亥革命前的1911年4月,恽辞去清政府的一切任职,虽一再声称“顿觉无官一身轻,天空海阔,任我游翔,可为人生至乐”[5],但始终不忘情于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后,作为清朝遗老,恽一直活跃于文化教育界直至去世。那么,这位20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点翰林,并曾随侍光绪皇帝,熟悉晚清中央政情的士人,对20世纪初的教育大变革持什么态度?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实际行动?一部百万余言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和鲜活的材料。
一、王朝利益的考量:对改革科举与停废科举的矛盾心态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不仅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用人制度和仕进渠道的改变。严复曾经断言:“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6]把科举停废比之为秦始皇的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实在是一种深刻的见解。无独有偶,作为旁观者,时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亦把此举称之为“一项革命性的法令”[7]。众所周知,晚清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维新变法时期即已拉开帷幕,进入20世纪,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改革步伐加快。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戊戌与新政两个阶段,前一段的主角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改革以废八股、改试策论为目标;后一段的主角则是袁世凯、张之洞、陶模等清廷封疆大吏,旨在全面停废。[8]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与存废作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考量着从身居庙堂到躬耕于穷乡僻壤的每一位士人。早在1898年初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后不久,恽毓鼎即上《经济特科敬陈管见折》,在赞同严修主张的同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建议在保荐和试以策论的基础上,对录用人员根据其专长,分配至中央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一年,“言行相符而后大用”;二是建议被推荐人员必须既要有“才”、更要有“德”,“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充荐牍,斯人品正而才皆有用之才矣。”[9]折上,光绪帝在上谕中对恽提出的第二点给予充分肯定。很显然,这一时期的恽毓鼎是站在支持对科举取士做局部改革的一面。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恽有如下记载:“本日奉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臣谨按:时文之弊,至今已极。……若改为论体,……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10]这段日记表达了作者的两层意思,一是积极拥护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称之为是“善制”;二是对“义理之学”前途的忧虑,他担心科举考试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会影响到“义理之学”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晚清科举改革的第一阶段,恽毓鼎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支持开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完全赞成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主张。但是,无论是人才选拔方法的改革还是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他都认为不能动摇“义理之学”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人品正”、“趋向端”是最重要的一条。
进入20世纪,改革科举的步伐加快,陶模、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清廷重臣多次奏请停废科举取士制度。恽毓鼎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导致其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最关注的“义理之学”和“学术人心”日益受到冲击。1903年旧历二月初一至三月初一的整整一个月,恽毓鼎作为同考官,与孙家鼐、荣庆等一起主持了中国科举史上倒数第二次科举考试的会试阅卷工作。他工作认真,经常是“日上而起,更深而寝,目不停览,手不停挥,无一刻可以暇逸,心力真交瘁矣。”[11]但心情却很郁闷,因为许多考卷让他看了感到痛心和愤懑。1903年4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枕上思之,不胜愤懑。”[12]同月27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束之高阁……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亦如此,岂不可痛哉!”[13]恽毓鼎虽是皇帝近臣,但毕竟只是一个侍读学士,一介词臣,并无实权,当然无法与张之洞、袁世凯等封疆大吏抗衡,但在日记里却可以宣泄。在这里,他担心的是科举的停废将导致圣贤义理之学的“弃若弁髦”。1904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心情:“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倡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梵坑之祸。南皮总督真吾道罪人也。”[14]在这里,他把义理之学的沦丧与清王朝的存亡联系在一起,直指主张停废科举的张之洞为名教罪人。
1905年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5]恽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16]科举的废止是由皇帝谕旨宣布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日记中也不便说三道四,流露真实的感受,只好无可奈何地写下“科举在今日诚可罢”一句,但笔锋一转,在学堂章程上大做文章。仍是抓住圣贤经传、义理之学这一主题,担心十年之后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
查阅恽毓鼎的日记,直至其去世,再没有对晚清停废科举一事说过好话,在以后十几年的日记中,每一提及此事,总是痛心疾首。
1906年8月19日:科举既废,科甲出身人不堪用,而学堂学生则又知其不足恃而不敢用,然则将以何取士乎?所用者唯捐纳耳,贵游子弟耳,善走门路以求速化飞行之人耳。……毓鼎一腔悲愤,万行血泪,无日不盼中国强,大清永,万民安。往往从梦中痛哭而醒,泪痕犹渍枕函也。[17]
1910年4月27日:访陈松山前辈,畅论时局,共痛心于南皮故相之误人家国,为名教罪人(故相生平行事无一足取,而废科举以绝寒畯登进之途,崇东学以亡圣贤文学之绪,铸铜元以乱国计而股民生,致今日上下交困,不可收拾,尤其罪之大者,而一般无行无识之徒,乃奉以山斗之名,言之齿冷)。[18]
1910年10月30日:余与李石府痛论今日学术人心之害,石府愤激不欲生。噫!谁生厉阶,不能不归咎于南北二张也。[19]
1911年7月22日:悲哉,悲哉!废科举,立学堂,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南皮、长沙二张矣。[20]
1911年8月23日:评阅医学堂毕业国文课卷,吾以见中国文字之将亡矣,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创议废科举、立学堂之大老也。[21]
辛亥革命后,其言词之激烈直欲把张之洞追削官谥不可。
1911年11月27日: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22]
从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科举,到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前后十余年间,作为亲身经历者,恽毓鼎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拥护到激烈反对的重大转变。其源盖出于他把科举取士制度的改革停废与清王朝的兴衰存亡自觉地联系在一起。前期的拥护改革,是因为在他看来,设置经济特科,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巩固封建王朝;而后期的反对废止,则是担心科举制度的废止将导致这一制度所承载的圣贤经传、义理之学会随之消亡。科举取士制度废止后的第六个年头,清王朝在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中崩溃。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不会仅仅是由于科举制度的被停废。但是,作为一名信守传统文化理念的知识分子,恽毓鼎却把“科举——学术——人心——大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在科举制被废止后一个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研读这段历史,不能不说当事者的这段刻骨铭心的体认自有其道理。但是,他真的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即将倾复的封建王朝大厦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吗?其实未必。随着形势的发展,恽毓鼎将面临新的矛盾和困境,他必须做出新的选择。
二、家族利益的考量:对新式学堂的矛盾心态
进入20世纪,清政府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始终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改革整个教育体制的重要一环,迭令各地兴办学堂。1901年9月14日的“兴学诏”明确要求:“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著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23]同年11月25日,清廷谕政务处将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通行各省,仿照办理。三个月后,再次谕令各省督抚奏报兴学情况,语词严峻:“该督抚等身膺重寄,目击时艰,当知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如再观望迁延,敷衍塞责,咎有攸归,不能为该督抚等宽也。”[24]以后,在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以及宣布递减科举中额和立停科举的历次谕旨中,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反复强调“时事多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责成各督抚“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建设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25]
那么,作为皇帝近臣的恽毓鼎,对清廷的这一重大举措抱什么态度、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翻阅这一时期的日记,随处可以看到恽毓鼎对各地新式学堂的不满与批评:“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官定学堂课程,有所谓修身学、伦理学。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其背戾不通,一至于此!”[26]“阅报纸,载湖南学生滋事情节颇详,麇聚全班,无理取闹,逼死监督,詈辱官长……从前科举之法固不善,然行之三百年,曾有此等暴动乎?在此中求人才,恐牛毛而麟角耳。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27]“目下学堂之法,将二十一行省之少年俱教成不通中文、不能写中国字而后止。祖龙焚坑,其祸不如此之烈也。”[28]有对课程设置的批评,有对学堂管理的不满,更有对教学内容的愤懑。然而,批评归批评,愤懑归愤懑,出于家族利益和个人前程的考量,恽毓鼎不仅适时地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新教育,而且,自己也主动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活动。
就在清廷宣布立停科举的第二天,1905年9月3日,恽在日记里写下如下一段话:“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命宝惠(恽之长子——引者注)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专就经济上着意,如法律、食货之类,皆宜贯穿本末,穷究利弊,一切琐碎异同可置之。”[29]恽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停废科举的谕旨才颁布了一天,他就果断地决定,让长子改弦更张,“一切琐碎异同可置之”,研习政法学,以“为他日致用之道”。恽毓鼎出身科举世家。其祖父恽光宸,道光戊戌进士,历官至江西巡抚。其父恽彦碹,同治丁卯举人,内阁候补侍读。恽本人20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点翰林。可以说,恽的一家,从祖父到他本人,都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受惠者。1898年长子恽宝惠14岁时,恽毓鼎就让他回原籍大兴参加县学考试,并在日记里郑重其事记下一笔:“成儿取入大兴县学第二十五名。”[30]查这一年的日记,共有近20处提及此事,可见恽本人对儿子的期许和厚望。现在,儿子已从14岁的少年变成21岁的青年,而科举制度却无可奈何地被废止了,路断桥横,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延续家族的地位和荣耀,必需另辟蹊径。进学堂、学法政,正是20世纪初从旧学转向新学的传统士人最愿意选择的一条捷径。日记中关于送子侄入法政学堂读书的记载还有多条,如,1908年5月19日:“宝铭(恽之侄子——引者注)在法律学堂肄业,夜坐询考课程,验其勤惰。以屠雨航自日本寄来新译出之《政法述义》十余种授之,督其逐次研究。”[31]1909年10月15日:“发常州电,命隽侄来京,考贵胄法政学堂。”[32]1910年1月7日:“贵胄法政学堂出榜,橼侄取三十七名,骏侄取四十名,铭侄不录。”[33]年纪大些的子侄都送入学堂,年纪小的则在家设塾。1904年2月23日:“未刻为儿女开学,赞儿仍从程先生,丙女、柔儿、酉儿改请袁锡三先生。率儿辈在至圣先师前行礼,又拜先生,送入塾。”[34]1907年2月28日:“未刻,以车迎袁先生,命儿女开学。”[35]1909年2月16日:“延江西鲁夫人督课九女,一侄女,一孙女。晚,设席请师。”[36]从1910年春节过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时恽家设有两塾,一塾用来教育第三代,一塾用来教育第二代。1910年2月28日:“午后陈鹤年先生先到,衣冠率汀、振、闰、樱四孩拜圣行开学礼。未刻,范俊丞先生到,复率赞、柔、酉三儿拜圣行开学礼。”[37]直至1916年2月19日的日记中还留下为三个儿子请塾师的记载:“为汀、振、闰别延同邑陈隐隆先生(栋)授读,下关书请柬,择二十日开学。”[38]恽毓鼎共有8个儿子,9个女儿,10个孙子,2个孙女。儿女辈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初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到了读书年龄,这让他大费周折。日记中也时时流露出这方面的苦恼。1910年4月4日:“因宝襄(恽之第二个儿子——引者注)不率教,愤恨终日,中气因而下坠,腹胀不能偃仰。甚矣,为父者期望儿子之心如是其切也。”[39]1911年1月18日:“因宝襄不率教,大动气恼。吾家累代清门,子弟皆恪守规矩。……今乃生此不肖子,岂余行止多亏,天以此示罚耶?若终不就范,毓鼎何面目以见祖先?”[40]究竟这个恽宝襄是如何“不率教”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把一位饱读诗书、温文尔雅的侍讲学士气得中气下坠、腹胀不能偃仰,甚至感到无颜面去见祖先,大概是相当出格了。当然,更多的是成功的喜悦。他一心培养的长子宝惠确也为恽家争得荣耀:据日记记载,恽宝惠22岁“以主事分兵部学习行走”[41];23岁“调承政厅(陆军部——引者注)行走,充秘书科一等科员”[42];25岁“派充禁卫军一等书记官”,“奖四品衔”;[43]26岁“升一等执事官,月薪百金”;[44]27岁“升补郎中”,“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并赏加三品衔”,[45]一年之内再次擢升,“以副都统记名简放”。[46]27岁做到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作为一个汉人,这样快速的升迁,连恽毓鼎也深感不安:“汉人任旗籍,乃近十年之破格,吾家科第虽盛,而此官则初创为之。宝惠由任子纳赀为主事,甫六年,历补郎官,遽跻二品,不可谓非乘时之缴幸也。”[47]大儿子乘了什么“时”,恽毓鼎没有接着讲,但是,在日记的其他地方却透露了有关信息。1904年6月6日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吏部具奏: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之子宝惠,请给予荫生。奉旨:知道了。钦此。”[48]此时科举取士制度尚未废止,宝惠赶上了末班车,靠着老子的身份赚了个“荫生”头衔。在恽毓鼎看来,“荫生”头衔的获得为宝惠日后快速升迁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换言之,恽宝惠既有科举体制下的功名身份,又有新学知识,在其父的指导下“专一研究政法学”,这是他短期内仕途畅达的重要条件。
就个人而言,恽毓鼎在清廷宣布废止科举制度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了。1904年3月23日日记:“午刻至畿辅小学堂,陪中西五教习开学酒席。”[49]畿辅学堂是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堂,前后经营十数年,直至去世。日记中有关畿辅学堂的记载有近百条,有的一个月内就记下多条,如,1906年2月记有4条,3月记有5条;而创办之初1904年5月的最后一周内,居然有三天的日记中记有关于该学堂的事情。检阅这些有关日记可以看出,大至学堂教师聘任、经费筹措、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的拟订、教员的考核、教学方法的研讨、开除学生的决定,小至随堂听课、课后观操、批改作业、检查学生缺席情况,等等,恽无不一一亲自过问。而且,从1906年4月14日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记中留下了恽每周一次给学生上课的记录。1906年3月16日:“午后至畿辅学堂,听教习讲论,看学生体操。”[50]4月14日:“未刻至畿辅学堂登讲台,为学生演说《论语》第一章,此后,每值休沐前一日则登台讲四书或经书一章,使学生有所启悟。”[51]5月10日:“至畿辅学堂……与郑、宋、侯、王、白五教习面论,请其每日散学后在揭石馆中会谈一小时,彼此研究讲授之学,互换知识,精益求精,以收教学相长之益。”[52]1910年9月3日,畿辅学堂举行首届高等小学毕业生毕业典礼:“辰刻至畿辅学堂,率高等小学诸生行毕业礼,发文凭,共二十一人,学部考取十八人,奏充廪增附生,余三人给佾生留习。”[53]辛亥革命后畿辅学堂继续开办,直至他去世前不久的日记中还有关于该学堂的记载。恽毓鼎致力较多的另一所学堂是顺直学堂。顺直学堂从1905年底开始筹备,一年后在金台书院原址开办,至1913年9月因筹款无着而解散,前后七年,用恽毓鼎自己的话来讲是“顺直学校以无款停办。……余掌校七年,备历艰苦,成就甲、乙、丙三班学生八十余人。”[54]七年间他不仅“以校长而兼尽教员之义务……每星期二、五上历史两堂”[55],而且,为筹款、教员聘请、学生管理等事付出了大量心血。第三所学堂是1908年创办的医学学堂,1912年也因经费不济而停办,前后四年。此外,民国前恽毓鼎在京参与创办或参与主持的新式教育机构还有(旅京)江苏学堂(1905年)、龙泉寺小学(1906年)、顺天二十四属中学堂(1908年)、辅仁改良私塾(1909年),民国初年参与创办或参与主持的新式教育机构尚有利仁义塾(1912年)、农业学校(1913年)、甲种农业学校(1916年)等,总数达十余所,日记中都留下了相关记载。
恽毓鼎以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史馆总纂、咸安宫总裁等身份所从事的上述办学活动,使他在体制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和新的身份认同。晚清至民初的十几年间,各种民间的、官方或半官方的学术团体、政治团体,新旧杂陈,如雨后春笋。由于上述活动带来的社会声誉,恽毓鼎先后被推举担任了多种会社团体的会长、副会长。据日记记载:
1908年10月4日:未刻至湖广馆,赴教育会特别会,投票公举会长。余及李嗣香前辈得票最多,且数目相同,遂同充正会长。[56]
1909年7月29日:酉初一刻往良氏愚园赴世界教育会,各国学界有名者皆充会员,中国唯余及江伉甫二人。[57]
1910年10月2日:申初刻至蜀学堂旅京教育会……余充会长一年,轮应更换,由会员投票公举,余得票仍在多数,连任一年。[58]
1912年4月15日:未刻赴社政进行会公举会长……全会一致推(余)为会长。[59]
1912年6月29日:午刻赴湖南馆教育统一大会,会员一百十一人。余登台演说教育原理,众多拍掌。旋投票公举理事四人(即会长),余得103票当选。[60]
1912年10月20日:西珠市口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开会……余登台演说……语次众屡拍掌,其声如雷。会中议公推余为评议总长。[61]
1912年10月21日:昨日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开会……投票,余得次多数,为副会长。[62]
1913年4月27日:未刻至湖广馆赴孔社成立大会,入社者一千三百余人。……嗣投票选举,余以四百十四票得副社长。社长为徐花农前辈。[63]
1914年3月31日:孔道会送敦请书来,公推余任名誉会长。[64]
1914年7月19日:饭后赴社政会改选正副会长。会员到四十五人,全体起立,坚请余及李丈连任,无庸写票改举。余力辞不获,拍掌之声如雷。[65]
从上述日记摘录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会长”、“副会长”之类的新的身份,不管其倾向是“趋新”,还是“守旧”,恽毓鼎都是非常认同且颇为得意,日记中有意无意记下的“众屡拍掌”、“其声如雷”、“力辞不获”等词汇,表达的正是这种心情。特别在教育统一大会的选举会上,恽与汤化龙、王金绶、章炳麟等叱咤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共同当选,真有点让他感到受宠若惊。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汤君(指汤化龙——引者)为当代闻人,余则旧人也,乃票数几与相埒,亦奇事也。(恽以103票当选,汤以105票当选,二人仅差两票——引者)。”[66]“奇事”二字,包含了恽毓鼎难以言说的感受和遐想!
在20世纪初的教育大变革中,如果说,恽毓鼎对科举改革与废止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话,那么,他对新式学堂的态度,至少从表面上看,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言行的错位。日记中处处流露出对新式学堂的不满和批评,但实际行动中却不仅送子侄进学堂、读法政,给他们指示学习新学的门径和方法,而且投身学堂的创办,亲手经营的各类新式学堂不下十余所。上述言行的错位何以会产生——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家族利益和自身利益的考量。揆之常理,恽毓鼎作为一个传统封建教育体制下的士子,少年得志,举人、进士、翰林,一路顺风,获得了那么多在常人看来求之不得的荣衔,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他的感受是所有头衔,说到底仅是一名封建王朝的“词臣”、“史官”而已,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几年,不仅没有什么实权,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连经济上也带不来更多的利益。日记中多有流露:“通籍几二十载,仍埋头龟于故纸堆中,冷局生涯固可笑,亦殊有味耳。”[67]“殊有味耳”只是一种自我解嘲,“冷局生涯可笑”才是真实心情的表白。在参加了1903年的会试阅卷之后,恽毓鼎企盼着1904年的阅卷工作也会有自己的份,这是因为,试学的差事会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阅卷大臣名单公布后他榜上无名,在这天的日记中恽写道:“分房揭晓。一日闷闷不出门。……予为家事累,不能无望于试学差,乃并会房而亦失之,郁郁殊甚。”倒是他的妻子较为通达,劝他说:“年甫四十,官至九卿,不为贱;家计虽不丰,然日用幸可支柱,不为贫;儿孙绕膝,大小安适,不无无聊。春秋佳日,饮酒看花,一门雍容,尽可寻乐,何怏怏于一差得失为!”恽听了之后“愧其意,念其诚,为之一笑。”[68]一段夫妻间的对话恽居然如实地记入日记,是用以自我安慰还是一种凄凉心情的宣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正是这种切身利益的考虑,使恽毓鼎在清廷还未被推翻之前即决意辞去一切政府职务,另谋出路。投身新式学堂的创办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符合潮流的时髦之举,作为一名传统士子,也更符合他的身份。
一部120万字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为我们留下了认识、理解一个世纪前那场教育大变革中士人心态的生动记录和鲜活材料。恽毓鼎只是身处变革大潮中千百万士人中的一个。他的认知和行动,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个人成长、文化传承所给予的深刻影响,对封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崩溃感到痛心、无奈和愤懑;另一方面,家族和个人切身利益的考量,又促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跻身于这场变革之中。他的言论、行动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和悖论,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复杂面相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剧变时代知识分子普遍面对的一种文化困境。这是我们重新认识这段教育大变革、评骘历史人物时应该充分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