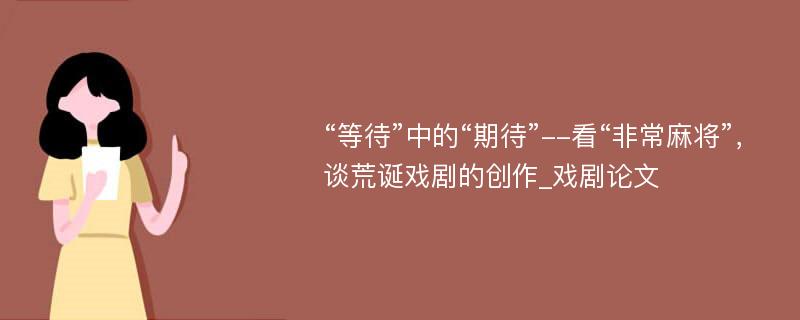
“等待”中的“期望”——看话剧《非常麻将》兼谈荒诞派戏剧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派论文,话剧论文,麻将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出吸引人的戏
在目前戏剧演出的淡季,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的话剧《非常麻将》吸引了很多观众,尽管观众的反映不一,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还有人说看不懂。但我认为这是一部能够吸引你看下去的戏,尽管它在剧本创作上并非完美无缺。
首先,这个戏的演出是完整的,流畅的。三位演员的表演非常到位,使得剧中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可以说,这个戏为演员提供了“用武”之地,而演员的创造也“保”了这个戏。舞美设计很简练,灯光、音响的配合非常默契。
其次,作品中所展示的社会人生及其寓意性,台词的精练与生活化,也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剧的剧情并不复杂,一天,因麻将而结拜的“竹林四闲”,在老二来到场的情况下,另外哥仁作出决定:在打完最后一晚上的麻将后,便金盆洗手,退出麻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然而,就在相约的那天晚上,老二始终没有到场。戏就是从“等”老二开始的。在“等”的过程中展示了哥仨的复杂心态。他们似乎在等老二,又似乎不是在等,因为他们最焦虑的是“告别麻坛”以后能干什么。老二为什么迟迟不来,原来老二已经死了,他们哥仨都参与了杀害老二这件事,但他们还然有介事地、一本正经地在“等”二哥。
就戏的内容说,似乎并不难理解。那么,为什么会让一些观众产生观赏障碍——看不懂呢?看戏后一些观众提出了疑问:这些麻坛高手要“告别麻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真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为什么要杀掉二哥……?
这显然不是创作者想听到的效果。作为编剧和导演的李六乙说,其实二哥在戏里并不重要,只是为了让观众留下来所设置的一个悬念。这个戏只提供一个过程,讲述一种生存状态,让观众去思考。比如说,戏中讲了一个打麻将三缺一的故事,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缺什么?
“缺什么?”导演的提示更让观众费思量。有嘴快的便说,“缺钱,缺房子,缺汽车,缺……”这,跟这个戏能联系得起来吗?
“你们不能以传统的眼光去看这个戏,应该从戏中去感受它的寓意。比如说,大哥往电话机上缠电线,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大哥是想把二哥‘拽’出来!”“我认为是反映大哥内心的复杂……”
然而,这似乎也不是创作者所要的效果。
创作与欣赏之间的误差
很显然,创作者在《非常麻将》中,是想把麻将与人生联系起来,以麻将寓示人生,让观众去感受更深一层的寓意。只是,导演在舞台演出中并没有很好地利用“麻将”这个载体,用独特的舞台语汇把自己的创作构思充分地、准确地、完全地表达出来。以致发生了创作者与观众在创作与欣赏之间的思维误差。
综观全剧,我感到创作者在戏中要表达的立意仍停留在表面层次。按照戏中的展示,观众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竹林四闲”决定“告别麻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二是在“等”二哥的过程中看出了哥三个内心的阴暗、虚伪和狡诈,尤其是杀死二哥,更表现了他们的残忍。然而按照这样的逻辑,观众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告别麻坛”与杀死二哥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导演认为没有必要去追究这样的细节真实,因为二哥在戏里并不重要。我认为这样说是不确切的。二哥虽然没有出场,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他始终生活在这个戏里,去掉了老二,这个戏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认为,也许只有把杀死二哥的动机揭示出来,才能通过打麻将这样一个载体,展示出一个古老民族的意识积淀,一种历史背景和一种文化现象,从而把麻将与人生、与社会联系起来,引发观众的思考。也就是说,通过他们杀害二哥的动机使观众看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说明他们的残忍,而是要达到他们嘴上说要“告别麻坛”,而行动上并不想“告别麻坛”,不想结束麻将生活的目的。二哥不来,“三缺一”怎么打?只有“等”,“等待”中存在着一种”期望”。而这种“期望”与他们告别麻坛的“决心”是相反的,即通过“等待”延长麻将生活使它不会马上结束,“期望”着重新开始(打麻将)。而他们此前的信誓旦旦,不过是装装样子给别人看看,或者聊以自慰而已。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杀死二哥,才会找到“不结束麻局”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哥三个才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去“杀”老二这样的“主意”。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说明“麻将是一种灾难,一种恐惧,一种死亡”的主题,而且也可以回答导演让观众思考的“我们的生活中缺什么”的问题。并由此使观众产生一些联想,如现实生活中的那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他们喜欢说大话,却并不付诸于行动;也可以联想到那种以“三缺一”来拆台的人,并有可能对我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意识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
“荒诞”不是“荒谬”
当然,因为小剧场戏剧的特点是注重探索性与实验性,不论是表现的形式,还是叙述的过程,都与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观赏现实主义戏剧的思维习惯去看实验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不过,这首先应取决于小剧场实验戏剧的创作与演出风格。比如,《非常麻将》的创作者也曾反复强调这是一出实验戏剧,要求观众不要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看它。可是,该剧呈现在舞台上的故事、人物、画面及台词却是非常现实的——喝茶有水,吸烟冒烟,电视有声音图像,故事有时间地点,有逻辑有推理,人物是活生生的,语言是生活化的,除往电话上缠电线和几次开门多少使人感到有些神秘外,整个演出风格与现实主义的戏剧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观众按照你的演出逻辑去思考并没有错。之所以会出现创作与欣赏之间的误差,我认为主要还是创作者创作观念方面存在着问题。
很多观众在着真正的实验戏剧——荒诞派戏剧的时候没有欣赏障碍,如尤涅斯库的《椅子》,结局是满台的“椅子”把主人“挤”下了台;高行健的 《车站》中的人物转眼之间由男女青年变成了满脸胡须、满头白发的老头儿老太太;别役实的《可以睡觉》的女主人公正在给一个个缺胳膊少腿的布娃娃寻找合适的胳膊和腿,她说这些“孩子”是30年前在一次大爆炸中受的伤。如果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看,这些戏的情节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但这种荒诞的形式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与思考。而《非常麻将》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风格,从这一点说,它的创作远不如《雨过天晴》更具有实验性——荒诞派戏剧的味道。
前年,看了日本别役实的两个荒诞派戏剧——《厕所应这儿》和《可以睡觉》,顿时使我生出一番感慨:中国缺少好的荒诞派戏剧作品,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对荒诞派戏剧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创作者缺乏思想。
在有些人看来,所谓“荒诞派”就是让人 “看不懂”,有人甚至把“荒诞”与“荒谬”划成等号,荒诞派戏剧在他们的手里就像是一个大垃圾袋,所以什么都可以入戏,什么手法都可以使用,观众越是看不憧,他们越是自鸣得意。这无疑是对荒诞派戏剧的误读。实际上,即使是产生于西方的荒诞派戏剧,尽管表现形式是怪诞离奇的,但内容上却反映了当时西方社会的现实矛盾,每个戏都有一个明确的主旨。荒诞派戏剧是以荒诞的形式反映了社会真实,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从这一点说,它比现实主义戏剧有着更大的创作难度。没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没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是不可能创作出好的荒诞派戏剧来的。
观众在“等待”,也在“期望”着有更多更好的实验戏剧作品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