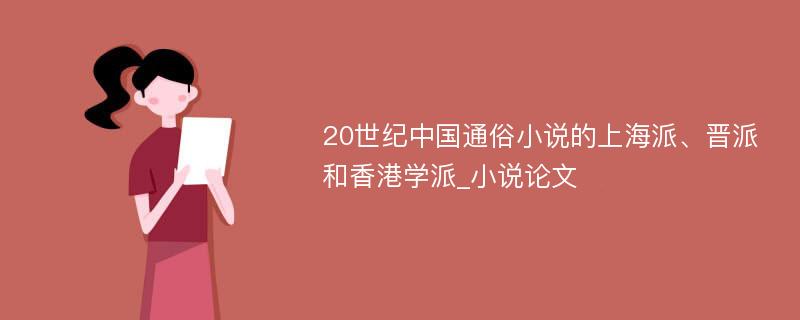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海派、津派和港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中国论文,通俗论文,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2-0063-(05)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作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和天津、香港。由于地域的特点,作家的创作风格很多方面显示出一致性,因此他们分别被称为海派、津派和港派。这三个流派的作家不仅作品众多,而且此起彼伏地成为引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排头兵,因此,了解了这三个流派,也就了解了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发展变化的总体特点。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是从清末民初的上海开始的。最早是吴趼人等人的具有新闻体色彩的“谴责小说”流行于上海,之后,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登上文坛,其中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作家最有名,这五个人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他们的创作构成了海派通俗小说的风格。
在“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时候,这些作家作品曾经受到严厉地批判,新文学作家将其斥之为“守旧”的、“封建”的文学。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严格地说,他们应该是一批继承着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显示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在新时期的延续。这些作家大多是在科举场上爬滚过多年的中国传统文人。他们小说中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是他们所恪守的做人的标准;小说风格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笔记体”或者“话本小说体”。如果不是简单地排斥中国的文化、文学传统,而是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学看作为与“五四”新文学引进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风格并行的文化、文学类型,这些通俗小说的“海派”作家应该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海派”通俗小说作家对中国文学创作的生产体系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在中国,文学创作从来就是一种闲暇之事,是作者抒发理想抱负、遣愁抒怀的工具。“海派”通俗小说作家将文学创作改造成一种事业,并且走进了市场。这些“海派”作家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小说家,又是中国最早的报人。新闻工作的经历和操作方式对他们文学创作生产体系的改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刊登在报刊上,小说也刊登在报刊上;新闻写作有稿费,小说写作当然也有稿费;新闻写作需要“读者效应”,读者多,报纸销路广,记者就成为了名记者,小说创作同样需要“读者效应”,读者多,报刊的销路广,作家就成为了名作家。既然记者是一种工作,新闻是一种事业;作家自然成为一种工作,写作自然成为一种事业。根据现有资料,当作家在当时经济效益还不错。更何况这些作家都笔耕不辍,同时为数份报纸、刊物写稿,其收入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创作文学作品的收入不菲,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作家也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中国的职业作家就出现了。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职业作家。他们不同于鲁迅等人将市场作为生存的手段进行社会启蒙和思想启蒙,而是完全将市场视为能否生存的生命线。他们也进行社会批评,依赖的是市场所提供的现代传媒。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职业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清末,通俗小说作家们对官场的腐败嬉笑怒骂;民初,通俗小说作家们反对袁世凯复辟;1920、1930年代,通俗小说作家们抨击社会乱象,嘲讽军阀政府。“海派”通俗小说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空间根本不可能。他们把文学创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为了活得更好,他们就必须使其创作服从于市场(尽管有些不甘心)。他们的文学作品有着更多的“市场气”。在市场地逼迫下,作家们很容易使得文学创作跟风走、庸俗化;但是它又促使着作家们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他们要拼命地写好,也拼命地花样翻新,道理很简单,写得不好,总是老花样,就没人看,没人看就没有人请你写,也就没有了钱。于是,我们看见了“海派”通俗小说在受到新文学批评之后,不但没有衰竭,反而在1920、1930年代走向全面繁荣。从民初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全面地扩展至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滑稽小说各种文类。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批判明显加强。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的中心,还是新文学创作的中心。在上海创作小说,要想得到市场,没有“新”的气息就不行。举个例子说明,早期的张恨水以创作社会言情小说为主,他创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前两部创作发表在北京,后一部创作发表在上海。《啼笑因缘》不同于前两部的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写了社会压迫,二是建立了人物中心。小说所展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沈凤喜等人的性格悲剧。这两点正是新文学的特征,张恨水将之纳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之中,将中国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张恨水自己的努力,也是上海创作气氛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到我写《啼笑因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1] (P254)通俗小说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来自作家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动,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的需求和市场的动力。
1920、1930年代京津地区也有一些通俗小说作家作品,如张恨水1920年代在《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上连载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等小说。但是和上海地区的通俗小说相比京津地区始终形成不了气候,因为京津地区始终缺少一个作家群。这种状况到1930年代后期才有很大的改变,一个通俗小说作家群在京津地区形成,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通俗小说的“津派小说”。① 津派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特点展示它的特色。
燕赵之地多豪气。武侠小说是津派小说的强项。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可称为此时武侠小说五大家,也是“津派”作家群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中国武侠小说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1930年代后期他们将武侠小说从“江山意识”拉入了“江湖世界”。小说价值取向的转变给武侠小说带来的最大好处是拓展了小说的传奇空间。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以传奇取胜,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的传奇性只表现在武侠人物的行为动作上。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的传奇性不仅是行为动作,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神秘的深山古刹、险峻的丛山老林、荒凉的戈壁沙漠、古怪的水中小岛,这些是武侠人物生长的地方,也是他们打斗的场所。传奇环境的拓展,明显地加强了武侠小说的纵深感。同样,在“江山意识”的要求下,武侠人物再神奇,也是次要人物。当武侠小说转向“江湖世界”后,武侠人物就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世界、心理变化、性格脾气成为了小说不可缺少的描述内容。朱贞木1940年代发表小说《七杀碑》,又将武侠小说与历史故事结合了起来,使得武侠小说历史化,又将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武侠小说在江湖世界里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但故事有一种缥缈之感,以历史事件作为背景,不管武侠故事如何传奇,它都有了“根”,给人以真实之感和厚重之感;武侠小说的历史化,实际上是从江山之中写江湖,江湖故事围绕着江山的更替来写,不管故事是如何散乱,它都有了一条稳定的线索,犹如一根藤上的瓜,不管瓜结在何处,它们都是这根藤上的;以江山为背景写江湖故事,江湖故事也就有了廓大的表现空间,它可以由于政治家的阴谋将江湖故事写到宫廷里去,可以由于结党结社将江湖故事写到高山野林之中,当然,也可以根据民族矛盾将江湖故事写到边区异域里去。武侠人物走入江湖,确立了武侠小说的文体特征;武侠小说与历史“攀亲结故”,武侠故事有了更多的“根据”,武侠小说也就有了无穷的生命力。
津派小说中,与武侠小说同样繁荣的还有社会小说。与南方的社会小说相比,北方的社会小说很少写新旧矛盾的交替和争斗,商业气氛和金钱的欲望也很淡漠,爱国小说和“国难小说”几乎没有。它的特色在于描写政治黑幕、码头文化和小知识分子的卑琐人生。北派社会小说主要的作家作品有:陈慎言的《故都秘录》等;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耿小的的《滑稽侠客》、《时代英雄》等;刘云若的《小扬州志》、《粉墨筝琶》等。
陈慎言在《故都秘录》第一回中,从衣服的角度写了这样一些人物:“有戴珊瑚顶穿国龙马褂的王公贝勒,有朝珠马褂小辫子的遗老,有挂数珠穿黄马甲红长袍的嘉章佛,有戴顶帽佩荷包的宫门太监,有光头黄衣的广济寺的和尚,有蓄发长颈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有宽袍阔袖拿大皱折扇的名流,有礼服勋章的总次长,有高冠佩剑戎装纠纠的师旅长,有西装革履八字髭的官僚……”这里面有旧有新,有文有武,有老有少,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北派人物”,正是这些人构成北京、天津的上层社会。这些人不仅要钱,还要权。他们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内心肮脏、生活腐败。从张恨水开始,北派的社会小说写的就是这些政治黑幕以及这些政治人物的家庭黑幕。
码头文化是指天津的流行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特殊韵味。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聚集着众多的三教九流的人物,有着更多的亚文化的积淀,也为流行小说提供了无穷的题材。对天津的码头文化写得最生动的是刘云若的《小扬州志》和李燃犀的《津门艳迹》。天津有“小扬州”之称,是说明它虽是北方城市,却有扬州那样的喧闹和繁华。刘云若的《小扬州志》写的是破落的士家子弟秦士虎与几位女性的爱情纠葛和起伏的人生命运。小说中的这条情节主线在其他作家的同类小说中也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围绕着这条情节主线描写的天津特有“码头文化”使人大开眼界。作者为了说明天津为什么被称为“小扬州”,就竭力地写天津的喧闹和繁华,小说“津味”十足。如小说开始时对天津城市的描写、秦虎士眼中的“南市”、江湖戏班子的生活实态……这些土里土气、原汁原味的描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天津的地域特色就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混混”。写天津“混混”最出色的作品是李燃犀的《津门艳迹》。“混混”并不像人们所想像中的地痞流氓,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乡邻排忧解难,热心于公益工作;也有些人讲义气,不怕死,敢出头,平时多吃多占,关键时候也敢为民办事;当然还有为数众多的依靠官府,欺行霸市,滋扰乡里的“混混”,他们是地方的黑势力。这部小说就写了这些不同的“混混”不同的行为以及他们互相的争斗。小说在写现实生活的同时将一些历史、掌故、轶闻、趣事穿插其中,处处透现出地域的韵味。
“北派小说”也有“市民小说”。与上海的“市民小说”善写城市的店员、家庭妇女、小商小贩以及妓女略有不同,北派的流行小说写城市的小知识分子形象特别生动。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出色的是耿小的。耿小的肄业于北京师大,长期担任职员或者教师工作。他在1940年代以小职员和中小学教师为主人公在报纸上连载了30多部流行小说。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那些“小衙门”和“小学校”的乌烟瘴气的黑幕以及混迹于其中的那些小知识分子的卑琐的人生。正如他在《行云流水》开头所说:“我写小说的意思,以是暴露官场上的一点黑暗,而这点黑暗仅今写了万分之一而已。……这部《行云流水》仍旧是写机关的女职员们,自然故事没有影射,起始仍要写位科长……实际上也许是局长,也许是会长,也许是校长……”科长、局长、会长、校长以及他们周围的各色人等如何地骗人骗钱、投机钻营、虚伪弄巧、不学有术就构成了耿小的笔下的一个个灰色的人生故事。
自张恨水在上海发表《啼笑因缘》之后,他的创作中心就开始了南移。1940年代京津地区写言情小说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刘云若和梅娘。与张恨水一样,刘云若也是报人出身。他创作的言情小说也和张恨水相同,将社会和言情结合在一起,走的是社会言情小说的路子,因此刘云若也就有了“小张恨水”之称。与张恨水小说不同的是,他缺少张恨水小说的社会广阔性和政治敏感性。他的小说描写的一般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故事性很强,生活气息很浓。人物描写更为细腻,在“小处”见工夫。梅娘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女作家。1940年代中期她在北京创作了很多有关女性婚恋生活的小说,其走红的时间与上海的张爱玲相同,因此也就有了“南张北梅”之称。与张爱玲的小说比较起来,无论是小说的社会性、文化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梅娘与张爱玲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女性特有的心理描写上却胜张爱玲一筹。她特别善于细腻地描写婚恋中的女性心理,哀哀怨怨、款款曲曲,十足家庭少妇情调。因此,她的小说可称为“闺怨小说”。
“津派”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地域小说”。作家们就生长在他们所描述的环境之中,地域的色彩渗透于作品的每一个字中,韵味十足。
“港派”文化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在中国大陆一时甚嚣尘上;“我的中国心”等香港歌曲几乎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人的时尚小调;粤语班一时林立,很多人满嘴“啾啾”。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作家为代表的“港派”通俗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大陆。
香港是背靠中国大陆的世界城市,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世界流行文化混杂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香港都市文化,这样的都市文化很鲜明地体现在“港派”通俗小说中。“港派”小说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孤独的英雄、伤感的人生、苦涩的爱情、戏谑的弄臣,“港派”小说的这些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我们可以在大仲马的小说、莎士比亚的宫廷戏以及美国的“硬汉派小说”、英法的“伤感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等众多的世界流行小说中找到其源泉。忠孝观念、因果报应、恪守人格、发乎情止乎礼等,这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中夹杂着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无论是悲情还是喜剧总是夹杂着自怜自悼的伤感、愤世嫉俗的孤独和或浓或淡人生宿命等世界性人生情绪。“港派”通俗小说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引领到世界流行文化的潮流之中去。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中将“做人”和“个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似乎“做人”就是要坚持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个性”发展的枷锁,要想“个性”发展就要冲破“做人”要求的束缚。这种二元对抗的价值观念在“五四”文学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港派”通俗小说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再是将两者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是将两者处于认同的状态,并从中展示人物形象和性格。例如金庸的小说是以人物成长为线索写人的形象和性格,人物的成长过程是人格逐步健全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升华的过程。“做人”和“个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圆满。“港派”通俗小说的成绩实际上解决了长期困扰通俗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小说创作如何既保持中国特色,而又人物生动,对1990年代以来大陆的通俗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家们都有意地接受外国小说的影响,丰富自己小说的内涵,通俗小说的“港派”作家同样也走这条路。但是,与某些精英小说家不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小说结构、情节、话语等方面完全进行“西方化”变革,而是在保持着中国化的基础上接受外国小说的影响。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将中国传统小说与世界文学沟通起来的作家。
金庸、倪匡、李碧华、亦舒等“港派”通俗小说成名作家毫无例外地都是小说、影视双栖作家,他们作品的红火与影视的推动密不可分。影视创作技巧渗透于这些“港派”作家的作品内。影视创作技巧对通俗小说的创作是把双刃剑,它对小说创作中的时空调度、动作语言、环境描述等都起了积极作用,因此现在的通俗小说情节更为紧凑,故事更加好看;但是情节内涵、语言表述、心理刻画却越来越弱化,语言艺术正在丧失语言的优势,使得当今通俗小说“快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港派”作品的模式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市场上正在强劲地发酵,一部影视剧的热播带来一部文学作品的热销已经是中国当今文坛的惯例。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促使着当代作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向影视媒体靠拢,说现在中国的通俗小说就是影像小说也未尝不可。
“海派”、“津派”、“港派”是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三个流派,也是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发展链中的三个环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通俗小说具有怎样的特色,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传统型”走向了“现代型”。
注释:
①之所以称为“津派”,而不是“京派”,是因为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家主要集中在天津,发表的阵地也主要是天津的报纸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