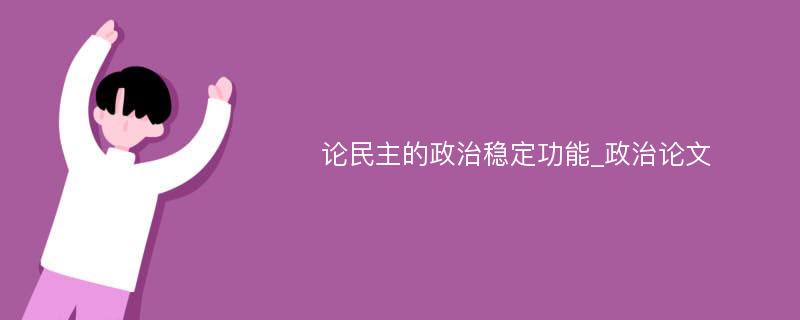
论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体论文,民主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稳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权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而如何在社会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则是各国政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不断探索和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动,面临诸多挑战与考验,政治稳定问题自然倍受关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稳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关因素,学术界围绕二者关系有诸多讨论。本文拟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与运行机制——即从政治体制的层面上,梳理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探讨民主的政治体制是否具备政治稳定的功能、能否产生政治稳定的效应。
一.两种政治体制的结构与功能比较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权力结构即政治权力主体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形式,表现为对权力主体权限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运作方式即行使权力的程序。集权与民主是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
集权政体的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型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支配——服从的方式进行;民主政体的权力机构内部为平等型的政治关系,权力运行以博奕方式进行。集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各具特点,二者有十分明显的差别。
在现代社会,从长期来看,集权政体的稳定性是十分脆弱的,它要么具有绝对的稳定性,要么处于绝对的不稳定状态。集权政体的自稳功能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集权政体的等级结构产生了政治行为的高度一致性和政治组织的高度单一化,上层政治角色的意图决定下层角色的行为,下层的行动满足上层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压力——稳定”机制。集权政体稳定性的前提是政治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的上层角色具有权威性,否则权力结构就难以稳定。这一前提条件决定了政治权力(机构)必须不断防止可能对其权威权成挑战的社会团体的成长;必须不断压制来自体制内外的不同意见。换言之,“压力——稳定”机制具有使集权政体下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积累起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方面看,集权政体下社会重大矛盾的解决只能以否定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为前提,终究会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
民主政体常常处于相对稳定和相对不稳定之间的平衡状态。民主政体的内部结构中的平等型政治关系决定了权力角色行为的异质性,这是该体制的相对不稳定性的原因所在。但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权力精英间平等的政治关系,即政治角色之间具有形式上相等的影响力以及平等的法律地位,政治权力又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平衡意味着稳定,民主政体内在的“平衡——稳定”机制决定了它的政治稳定功能。进一步讲,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民主政体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有着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参政程度的提高又加强了政府的统治基础和权威;其次,高度的制度化使民主政体可以敏捷灵活地对民众诉求做出反应,并有能力及时、有效地做出相应调整,使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遵循一定的规则达致妥协;第三,历史地动态地来考察这一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益集团的兴衰消长变化十分激烈,而民主政体可以在政权的合法性、连续性不中断的前提下,及时地在政治过程中体现这些变化,不致于因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脱节而使国家的发展受阻。
民主政体的“平衡——稳定”机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印度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极其艰难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社会结构复杂、社会矛盾尖锐,这些都构成了印度社会发展的障碍,孕育着现代化道路上的危机。但是,令世人惊奇的是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累赘的印度,在独立后五十多年中始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稳定。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民主政体,1950年印度宪法生效,此后这部宪法经过了80次的修正案的补充和修正。1952年至1997年的45年间印度进行了12次大选,成立了12届民选政府。在民主政体下,印度社会并非风平浪静,民族、种姓、阶级、地区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然而,在频繁的宪法、法律修改和政府变动条件下,在政治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印度的政治结构却又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充分表现了民主政体对于社会矛盾的适应、调节和整合能力。
在政治系统建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因需要解决的矛盾的性质及任务不同,政治体制的稳定功能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因而,对于不同体制的政治稳定功能的评价亦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来说,在确立新的政治秩序过程中,集权体制往往更有效率,因为它能在短期内迅速动员社会资源,彻底地调整社会阶级关系。而对于追求发展、完善的国家来说,政治框架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民主体制就应当成为人们明智的政治抉择。而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时机、方式往往成为国家完成现代化飞跃的关键。
二.“东亚模式”的反思
在对民主政体的政治稳定功能进行一番理论分析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广泛建立,使政治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实践也为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于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即认为民主政体对于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而似乎集权体制更合乎发展的需要。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曾提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注: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20、516页。)此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威权主义”的发展理论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曾引发过热烈的讨论。亨廷顿的“威权主义”在实践中是以所谓“东亚模式”为支撑的,这一模式被认为是集权政体的发展模式的成功范例。
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集权政体似乎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所谓的“东亚模式”却发生了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韩国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1997年年中以来蓄积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从7月份泰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一连串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大部分东亚国家。其中韩国,这个80年代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奇迹”,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打击,导致了自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1月,韩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高达5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实际上宣布了国家财政、国民经济的破产,“东亚模式”向世界亮起了红灯。
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意识到了“东亚模式”的弱点。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模式”,韩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者。在这种模式下,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阿姆斯登在总结韩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时写道:“在韩国,并不是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对私有企业进行指导,而是由政府作出投资决策,每个企业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运行,而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市场里运行。”(注:艾丽斯·阿姆斯登,“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南朝鲜和后起工业化”,《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0页。)台湾知名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在分析“东亚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关系时也指出:“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这些工作在经济进步的国家,都是为眼光远大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所担任的”。(注:李国鼎,《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在这种模式带来一些为人们所反复论及的好处的同时,也埋藏了隐患,积累了弊端,这次席卷亚洲的危机正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与隐患的大爆发。
首先,政府强行干预机制造成了经济集团化与垄断。在集权政体之下,政府必然要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而集中与控制的有效途径即是扶植并左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政府强行干预机制的推动下,韩国历届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特别是通过政府主导型的间接融资为主的投资体制,将经济资源集中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由家族管理的大型“财团”(CHAEBOL)的手中。目前,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的财产占了该国国民财富的1/3。这些财团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实行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使韩国经济具有很强垄断性。这样,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运转缺乏灵活性;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之间激烈竞争造成了经济规模的极度膨胀,形成“泡沫经济”。只要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快速扩张的条件被削弱,这种“泡沫经济”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韩国的这次危机就是由于财团经济的过度膨胀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而引发的。苏黎世肯帕财务公司的经济分析家黑尔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的问题是一个经济模式失灵的问题”。(注:“韩元的损失——韩国以往的政策无法医治今天的经济疾病”,《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4日。)而韩国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则在于集权政体下的政府强行干预机制。
其次,集权政体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亚洲的集权政体在工业化过程中利用政权力量强制实现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地积累、加深和加剧。1961年5月18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后称“国家再建最高会议”的名义)宣布禁止一切工会活动。此后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均遭到了强行压制。1971年12月颁布了《关于国家保卫特别措施法》,1972年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韩国政府对社会的统制达到了顶点,政府对工会、各类政治团体及普通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以暴力为基础的严格的社会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公开表现,但绝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反而在不断地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韩国在长达25年的专制集权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以致终于爆发了“光州起义”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反独裁运动。
再次,集权政体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完善,引发严重的政治性腐败。集权政体一方面没有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的缓释和解决;另一方面制造了一个与经济界联系密切的庞大的官僚体制,成为严重的权力腐败的温床。在集权政体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政、企关系密切,进而造成了经济运行中的二元调节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两种性质、方法和目标均不相同的调节机制的左右,即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普遍发生在集权政体国家中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并非偶然,它正是这种“二元调节”的直接后果。“二元调节”模式曾受到许多赞誉,被认为是“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但人们却不应忽视其与腐败的密切联系。在二元调节的模式下,两种调节机制在配置资源的目的和方法上存在着矛盾,腐败便从这些矛盾中产生而成为一种经济需要。其典型的表现即是企业运用寻租行为通过政府而不是市场即可获取资源与利润。应当说,较为单纯的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或较为单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都是较少的和可控的,都不易发展为严重的政治性腐败。而唯独政府与市场两种调节机制大面积交叉和并存则容易造成大范围的腐败。
韩国的集权政体下出现的普遍、持久而严重的腐败现象为上述理论分析模式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韩国的三星、现代、乐喜金星、大宇、鲜京、双龙和韩国火药等七大财团中,出身于政界、军界的经营管理人员占其副经理以上的主要经营者总数的近17%。有资料表明,韩国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退职后几乎都有在财团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经历(注:贲贵春、尹传学,《南朝鲜企业集团》,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3页。)。官、商人事结合化解了对经济活动的种种监督制约机制,废弛了法律,使腐败大行其道。腐败强化了发展的盲目性,从总体上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经济扩张时期,韩国众多的财团和企业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广施贿赂,大搞人情贷款、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了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埋下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腐败对经济及社会的危害暴露无余。
在这次韩国的危机中表现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的双误现象,充分说明了集权政体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弊端。从长远来讲,集权政体既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利于政治稳定。
东亚模式的危机已经在提醒人们:应当重新考虑政治体制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到底是集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人们应该作出新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