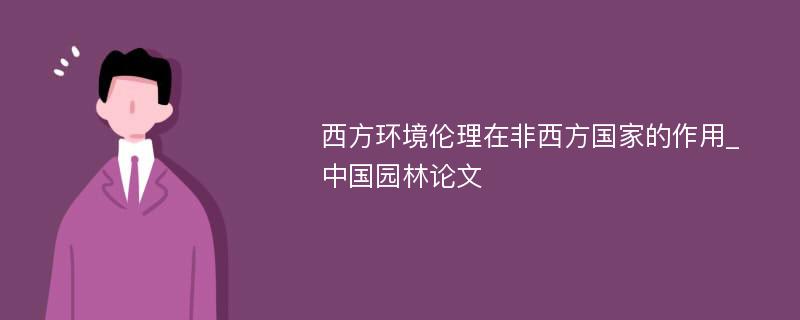
西方环境伦理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西方国家论文,作用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哲学领域,西方环境伦理学是19世纪70年代主要从英语国家开始的学术研究的产物。不过,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主题,尤其是风景绘画、景观园林、博物学,以及自然诗歌和散文。[1](P87-112)它的基础并不特别源于现代哲学之中,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哲学或多或少是反自然的,而现代哲学延续了这一倾向。古代哲学把实在定义为永恒的、不变的和不可摧毁的,使得人们很难发展出对充满变化的世界的关心,因为变化的世界被认为是虚幻的。在中世纪哲学中,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追随古代哲学的这些趋势,但世界的存在要取决于基督教上帝的意志,从而使得人对自然的关心是狂妄和傲慢的。环境是上帝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人们遵循笛卡尔的主张,决定通过认识论来研究形而上学,这使得世界的存在本身受到了怀疑,而如果连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那就很难谈得上保护它。[1](P14-47)
随着地质学中均变论(uniformitarian)取代灾变论(catastrophism)的发展,自然的非永恒性(impermanence)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自然并非永恒的;但是,如果任其自行发展的话,有理由预期它会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如果受到人类行为的损害或破坏的话,它将是无可替换的,因为造就自然的物理和化学力量,是在使人类的时间框架相形见绌的漫长时期内达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自然存在于一种半永恒(quasi-permanent)的状态中,但它又具有脆弱性,从而使得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t)的关心有了正当理由。[1](P87-112)这种关心之所以是有理由的,是因为随着均变论的提出,对地球的保护就不再被视为上帝的职责。[2](P260-264)上帝并没有隔一段时间就摧毁和重建世界。如果世界由于人类的行为而落入某种状态的话,那么,它就会继续以这种状态无限地存在下去。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首要基础是自然美学(nature aesthetics)。在近代的开始,作为哲学的新领域,美学主要关注自然美学,尤其是“崇高”(sublime)。当时美被定义为是和崇高相对的,因而以崇高来指称自然,以美来指称艺术。这种对立随着人们对一种中间立场,即绘画美(picturesque beauty)的接受而被打破,它认为看起来像山水画一般的山水景观也可以是优美的,它们美得足以入画。景观园林(landscape garden)也发挥了作用。园林起初只是一块圈起来的地方,后来园林的设计者们专注于按照几何图案来布置植物,对它们进行精心修剪,以此对自然加以人工的美化。这些注重形式的园林力求通过给园林加上简单的几何形式和图案,来使自然变得更美丽。渐渐地,这些园林又被非形式的园林所取代,后者没有强加上几何的形式和图案,而且人工操纵的痕迹也尽量隐蔽。这些园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风景绘画创作的影响,也受到博物学,尤其是受引进外国植物的影响。对于从世界其他地方引进的植物,任其自然生长,避免人工的修剪和控制,使得人们可以对处于自然生长条件下的植物进行审美的欣赏。此外,自然诗人和艺术家、园艺师以及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发展一套能够表达对自然美的持续兴趣的术语。
中国园林也对西方的自然美学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尽管这一点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对中国园林的记叙始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的出版。[3]18世纪,在西方园林从形式园林向非形式园林或绘画园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园林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作用。[4]这些最早出现于英国的园林,最初被称为“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或“英国中式园林”(Anglo Chinese Garden),但是,最后只被称为“英国园林”,强调其如绘画般的特点,而淡化(或遗忘)其中国的影响。
中国影响的这种“内化”(internalization)或被遗忘,也许典型地反映了一种有效的相对变化是如何发生,或应当如何发生的。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早期阶段,东方或亚洲的影响也受到很多的关注。在林恩·怀特(Lynn White)提议以新的东方宗教,如禅宗佛教取代基督教之后不久,这种反应就开始出现了。[5](P1203-1207)约翰·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在其《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一书的开始就讨论了林恩·怀特的观点,他反驳说:“伦理并非……那类人们可以简单地决定是否要拥有的东西;‘需要一种伦理’决不像‘需要一件新外套’那样。一种‘新的伦理’只能产生于现存的态度;否则,就绝不会产生出来。”[6](P4)如果帕斯莫尔是对的;那么,发生于中国园林的那类内化,就是一种影响要在另外一种文化中起作用的惟一途径。
类似的情绪在亚洲也能见到。在环境伦理学的文献中,印度学者拉马禅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的第三世界批评也许是最著名的例子。[7](P71-83)从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西方环境伦理学是基础主义的(foundationalist)、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殖民化的(colonizing),以及总体化的(totalizing),不是东方所应接受的那类哲学或伦理学。[8](P117-134)关于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亚洲和非洲的一般负面影响,人们最常见的抱怨是国家公园的理想性。[9](P147-158)要求自然公园摆脱人类的使用,导致了当地居民的迁移,以及对传统的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这会造成经济的困难,有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结果,这样的自然保护活动通常被人视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残留。本内特(Burnet)和康格斯(Kang'ethe)就非洲的情形这样写道:“假如西方从来没有入侵班图兰(Bantuland),荒野保护的问题最终也会呈现出来。设想一次长老委员会聚集在一起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应该消费,还是应该保护我们现在已经枯竭的黄豆树(weru)?’与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机会提出来的事实相比,长老委员会可能采取的行动显得很苍白。……西方的荒野象征着西方化所产生的灾难,而西方的解决办法,即通过出口关于景观的观点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GNP),对于那些除了在本地存活下去就别无选择的人们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10](P145-160)
显然,避免这类跨文化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形成一种不依赖于文化的国际环境伦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真的懂得如何去做。伦理学不像法律。要制定法律,人们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政府实体来执行既定的立法程序就可以了;但在伦理学的情形中,并没有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无论伦理学家们就伦理学写下了多少论文,一种新的伦理观点只有当普通人开始接受它时,才能发展出来。而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点是无法预测的。当一种观点和文化传统相兼容时,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一旦它被接受,它就成了那种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的结果是,如果要发展出一种在所有文化中都可以被接受的国际环境伦理,它很可能来自于一些试错的尝试,在诸多文化中建立起一些独立的环境伦理。在各种文化的正在兴起的环境伦理中,有可能会独立地出现一些相似的特征。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就可以成为一种不依赖于文化的国际环境伦理的基础。无论这种国际环境伦理是否会形成,这项计划都是有益的,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一些依赖于文化的环境伦理,而这反过来将会使发展出这些伦理的文化受益。
因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进行了近30年,所以,它很可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的研究的出发点。这种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要取决于可资比较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内化到每一种文化之中,就像中国园林被采纳和吸收入西方的自然美学一样。为使这种内化在非西方国家发生,就必须尽量避免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问题的那些特色。而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的划分、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概念,以及权利(rights)的概念似乎是其中最有麻烦的三个。
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的划分在西方环境伦理学自身内部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当环境主义者们开始敦促哲学家们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普遍相信,根本的问题是人类只是按照自然对人类的工具价值来评价自然。结果人们开始错误地把“人类中心的”(anthropocentric)和“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这两个词语视为同义词。“人类中心”这个词语还渐渐被视为一种思维模式。以人类为中心的思考渐渐被认为是工具性的思考,亦即是从人类利益角度的思考。奇怪的是,“非人类中心的”(nonanthropocentric)渐渐被认为是一种不涉及价值判断的思维模式。人类中心的思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或从人类的角度进行的思考。这种二分法鼓励了哲学家们寻求一些不包含人类判断的思维方式,最后意味着在自然之中寻求一些不依赖于人类评价的客观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常常引起很多的争议,而且在作者看来,即使被接受,也是没有道德的价值的,除非它被道德地评价,并重新引进人类的判断。人们设想,按照利奥波德(Leopold)提出的我们应该像山那样思考的思想[11](P129-132),一个人可以非人类中心地思考,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如何像山那样思考,我们所知的任何思考都是像人类那样思考。既然可以预见这个术语最终要从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消失,而且它是造成荒野概念的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就没有必要让它来困扰那些在非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工作的人们。
内在价值的概念问题是和人类中心与非人类中心的区分紧密相连的。让人感兴趣的这种内在价值据说是一种非人类中心的价值,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类的判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价值。“非人类中心的内在价值”这个词语是同义反复的,它把同一个论点说了两遍。“非人类中心”一词是指“不是以人类为中心”。“内在的”一词意指为了事物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与事物有某种联系的,通常是观察它(而非评价它)的人类的利益。
由于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的影响,内在价值也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反对摩尔(G.E.Moore)关于内在价值的观点,费了很多时间试图反驳它们。人们误以为对摩尔观点的批评适用于所有内在价值的观念,并相信接受实用主义就是抛弃内在价值。[12](P321-329)可喜的是,人们终于逐渐认识到,抛弃内在价值,以及采纳一种几乎完全是工具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件意识形态的事情,是对杜威的盲目追随。人们认识到,实用主义者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内在价值当做他们的环境伦理学的一部分来加以接受。[13]既然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内在地评价事物,那么,持人类不能内在地作评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第三个有问题的领域是权利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认定权利的概念会在环境伦理学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位于其核心的是一种动物权利的观点。然而,虽然环境伦理学家们竭力阐发一种自然的权利理论,但他们并没有成功。权利的目的是要保护个体的利益,但不幸的是,环境主义者们想要保护的的东西,如生态系统和物种,并不是一些个体,而是由有着不同利益的个体构成的集体。在许多情况下,对个体有益的东西对系统或种群未必有益。例如,特定个体的死亡可以增进种群的健康,个体的死亡是系统继续存活所必需的,就像动物要捕食才能继续生存一样。(注:关于这场争论的关键论文,参见Eugene C.Hargrove,ed.,The Animal Rights/Environmental Ethics Debate: The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替代权利的方法。权利是西方近代早期的发明物。权利的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确实并不为人所知。如果一个人提出某种道德的行为,然后试图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他并不需要从权利的角度来论证。例如,19世纪初北美和北欧对待动物的行为的变化,可以被解释为制订一种不施加无必要的伤害的义务(义务论伦理学),或被解释为一个道德人格的行为变化(德性伦理学),解释为对非人类有机体的权利的承认,或对人类权利的限制。在这些方法中,对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的承认,在西方仍然是最有争议的。对人类权利的限制也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它和国际上促进人权,比如生育权的运动相冲突。正因为人权常常和环境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相冲突,所以,它们在文献中向来被忽略,尽管随着环境伦理学中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即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发展,它们也许最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参见Laura Westra and Bill E.Lawson,Faces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Confronting Issues of Global Justice,Lanham,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
作者认为,一种环境伦理最终如何被阐述,并不是一个哲学争论的问题。它取决于一种给定文化当中人们自己的决定,而哲学家们最终会发现,人们采纳的某种特定观点开始在政策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作者同意帕斯莫尔的主张,即一种新的伦理将“只能产生于现存的态度,否则就绝不会产生出来”。[6](P56)当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伦理学研究时,出发点是审视环境思想背后的观念的历史。作者尤其想要知道,当作者20世纪70年代初努力保护一个岩洞的水免受污染的时候,为什么作者和对手们会说出我们当时说过的那些话。结果发现,作者的观点来自近代的画家、诗人、园艺家,以及自然博物家们的观点。相反,对手则从日尔曼人的土地使用传统来发言,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和罗马人相遇的早期日尔曼部落。作者和对手对于我们立论所依据的传统都一无所知。这些传统的起源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传统本身还存留下来。或者,人们也许可以说,起源没有被遗忘,只不过它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不再容易被分辨出来罢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遗忘了中国园林,我们还遗忘了许多别的东西。因为严格来说,遗忘之后存留下来的仍然是一种认识。例如,当我努力在密苏里州保护岩洞的时候,我的对手同时从传统和实践来说话。他们无法很好地表达这个传统。他们可以说,“我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别人有什么权利告诉我怎么做?没人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他们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作为辩护。只有对于那些与他们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传统的人,他们的话才是有意义的。同样,作者从自然美学和岩洞的科学用处的角度来谈论,但是,也没能很好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作者的话也只是对那些发展出从科学和审美方面对自然的欣赏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作者不知道自己在结结巴巴地表达着一种已经发展了近四个世纪的自然观,而对手们同样也不知道自己正极力表述一种有着2000年历史的日尔曼的土地使用传统。
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把这种知识称为“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在波兰尼看来,以这种知识而言,我们所知道的,比所能说出来的要多。就艺术和工艺而论,知识的传递常常是通过学习的实践而获得的。因为这种学习是非语言的(non-verbal),因此,“一种技艺如果搁置一代人不使用的话,就会完全失传”。[14](P53)正如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On Certainty)中以自己作小学教师的经验证明,儿童被间接地、以非言语的方式教会很多东西,而这种“知识”形成了经验研究、世界观,以及日常生活和实践——即维特根斯坦所称的我们的“生活样式”(form of life)的无可置疑的基础。正如维特根斯坦强调的,这种知识与其说是“学到的”(learned),不如说是“获得的”(acquired)。[15](P143)
笔者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应包括这种意会的或个人的知识。它来源于本文开始所描述的西方的学科发展——风景绘画、自然诗歌和散文、景观园林(包括中国园林),以及植物博物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环境伦理学仍然是不可言传的、个人性的,因为环境伦理学家们仍然没有发展出一套可接受的术语来表达普通人心里知道而又无法言传的那些东西。
如果笔者的看法不谬,那么,环境伦理学的任务就不仅仅是发展出一种理论,而是要发展出一种和西方文化中的意会知识相容的谈论话语(discourse),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开始根据一套公认的术语来争论,因而有助于创造出一种或一套环境伦理,让人们能够正确地表述他们虽有所知,但除了“感觉到”之外却又无法清楚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当前,环境主义者们表达着一些他们相信是自己零星创造出来的观点,而对一直支持他们观点的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思想一无所知,也很少认识到,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也正是大多数人同样“感觉到”,却无法充分表达出来的东西。
如果作者的看法正确的话,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于非西方文化充其量只能具有比较的价值,因为设想一种从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中产生,致力于表达西方环境传统中的意会知识的文献,将会表达非西方环境传统中关于环境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那是不现实的。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一些“中国园林”,但是,其中多数也许是无用的——它们和非西方环境伦理学所应当立足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并不相容——即使是其中的“中国园林”,也许也要经过“内在化”,或者“亚洲化”,才能真的有用。
虽然作者主编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一本期刊《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已逾25年,而且相信这个杂志所积累的研究资料对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文献只是第一步,因为成年的西方人很少有准备来利用这些资料。一般来说,西方人偏好事实而非价值,他们谈论价值的时候常常觉得不自在。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应该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来谈论问题。他们认为价值只不过是一些感情,通常把它们称为个人偏好。改变这种局面并不能通过写更多的环境哲学论文做到。相信应该重新发现普通人的环境关怀背后的观念的历史,把它们清晰地阐述出来,使人们能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说出或表述这些关怀。这是一项必须从小学就开始的工程,而西方和非西方文化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平行地进行。[16](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