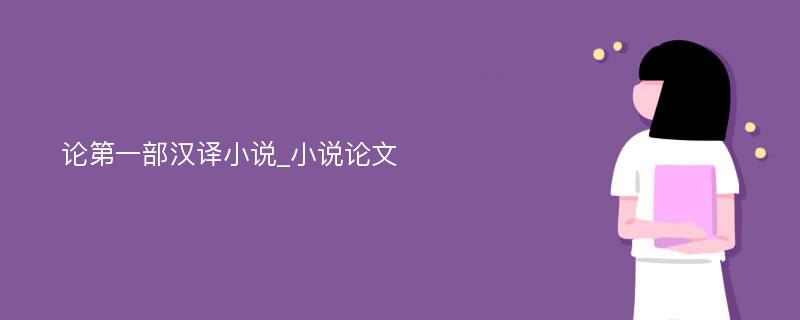
谈第一部汉译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部论文,汉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昕夕闲谈》虽然最早分26期于1873到1875年发表在上海的月刊《瀛寰琐记》上,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因为实际上早在1852年外国的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们就已经开始翻译宗教性质的小说了,尽管如此,就一般人的兴趣而言,它好象仍然被认为是最早的小说译本(注:发表于该月刊1873年1月的第3期至1875年3月的第28期上面。每一期上刊登两节,一共是52节。在28期后,月刊更名,同时形式也做了调整,翻译也就终止了。1875年的晚些时候,增补了三节,以书的形式出版。)。这本小说的英文原名没有被译成中文,而译者也只能通过“蠡勺居士”的笔名来判断。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仅在于确定原著及其译者,而且想谈谈《昕夕闲谈》译本的特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仅有必要了解小说原著的英国文化背景,也有必要了解《昕夕闲谈》的中国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一般比较,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译者自己评论的确认,来推演出译本后面的指导性原则(注:这种方法接近所谓“描述翻译研究”,见基登·托利(Giedeon Toury)《描述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Beyond),阿姆斯特丹,约翰·本杰明出版社,1995年)。)
原著及其作者
这部翻译小说表明是长篇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的前半部,其作者是英国作家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原著最初出版于1841年(注:中译本以利顿小说的第三卷(共五卷)第十章结束,总计只有全书68节中的33节。利顿小说最初出的是三册本,后来是两册本,最后是一册本。译者所用肯定是1851年或更迟的版本,因他已包括了利顿明显为1851年版写的一个脚注。)。这部著作将利顿所喜好的两种次文体联系在一起:即青年成长小说,他自己的小说如《恩内斯特·迈特瓦》(Ernest Maltravers)(正如利顿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注:参见他给《恩内斯特·迈特瓦》(1837年)1840年版写的前言。),这是一部源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古典形象类型的著作),罪犯小说(Newgate Novel)及其受人同情的罪犯,这种类型的人物其实利顿最早在《保尔·克利福》(Paul Clifford)(1830)和《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1832)就已经尝试塑造了,尽管他为此遭到过猛烈的攻击。虽然非利·莫顿(后来的非利·巴福特),《夜与晨》中的英雄,并不是一个象恩内斯特·迈特瓦一样的知识分子,但小说仍然集中表现其在生命经验中所受到的道德教育。题目中的“夜”与“晨”表现出他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书的前半部展现的是其失败与悲伤的一面,后半部则表现了补偿和欢乐的一面(在题目的翻译中,译者没有把这种象征意义表达出来)。犯罪人物加底是一个骗子和伪造者,在书的中途他被巴黎警察枪杀了。作为一个浪漫型的形象,一位现代的评论家称他为“很可能是所有(利顿的)罪犯人物中心理描写最引人注目,艺术表现最成功的形象”(注:参见朱利叶·约翰(Juliet John)所编《被人崇拜的罪犯,罪犯小说,1830-1847》前言(鲁特勒基出版社,伦敦,1998年)。)。
在《夜与晨》1845年版的前言里,利顿称较之对犯罪的关心,小说更加关注法律对罪恶的不当处理。犯了小错误的孩子被野蛮地惩罚,然而那些犯有对社会更大罪恶的人却逃之夭夭。这部小说中罪恶的最主要例子表现在愤世嫉俗、没有道德观念,玩弄权术的林贲爵士身上(利顿自己是一个贵族,但却是一个贵族统治的严厉批评者,不但在其开拓性社会学的研究,如《英国和英国人》(England and the English,1833),而且在其小说里都是这样)。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利顿的说法,所谓受尊敬的人常常具有最卑劣的品质。在《英国和英国人》一书中,他写道:“对财富不适当的关注会产生出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一个人没有值得称道、受人尊敬的美德,但仍然有可能是可敬的。”(注:斯丹第什·麦卡姆(Standish Meacham)所编《英国和英国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1970年),第45页。)这部小说中罗伯特·巴福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正如利顿所暗示的那样,这一形象影响到后来狄更斯在其《马丁·朱士尔威特》(Martin Chuzzlewit)中所塑造的匹克斯里夫(Pecksniff)形象(注:这在利顿1845年所做的前言中已有强烈暗示。)。在《夜与晨》中爱情主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非利在最终与凡尼结婚前和两个女人的恋爱,但与《恩内斯特·迈特瓦》相比,这种作用要小得多。
译者问题
关于译者,唯一已知的确认材料是在1905年的上海报纸《新闻报》上发现的,那上面有一则重译原文英文小说的广告(注:这一点最初是由郭长海在《蠡勺居士和藜床卧读生》(载《明清小说研究》3-4期,1992年,第457-61页)指出的。1905年5月11日到6月1日期间每周刊登一次。)。广告确认从前的译者为县太爷蒋子让。虽然这是在翻译出现三十年后才得出的归属结论,但由于它说得很具体,得承认它有一定分量。于是问题成了:谁是蒋子让?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说出他是谁。
但我们可以从译者在《瀛寰琐记》和《申报》中发现的其它作品得到些东西。正如颜廷亮所指出的,因为蠡勺居士为翻译小说所作的序言写于其上海居所的小吉罗庵,他肯定是小吉罗庵主,而他的文章在《申报》和《瀛寰琐记》中都能找到。而小吉罗庵主和蘅梦庵主的作品,尤其是其诗歌,也可以在报纸和刊物上找到,可以肯定他们肯定是一个人(注:关于这些身份,参见颜廷亮《关于蠡勺居士其人的点滴臆测》,《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106-110页。还可对小吉罗庵主和蘅梦庵主的身份加以证明的是另两个材料:对鹤槎山农(就是江湄)发表在《申报》壬申年(1872)12月11日的诗的介绍,及篆香老人(就是顾敬修)发表在《申报》癸酉年(1873)11月6日上的诗的前言。)。象很多当时的文人一样,译者显然是在同时使用很多的笔名。用蠡勺居士的笔名,他在给《瀛寰琐记》作介绍性的序言时,从其内容和语调来看我们可以判断出他就是刊物的编辑。用小吉罗庵主的笔名,为他自己的翻译作品《昕夕闲谈》写评论以及其他几篇重要文章。1873年末在他替一位朋友的诗作序时,蘅梦庵主的情况才得到些描述,他在杭州参加考试考中举人,是“武林名孝廉”(注:见癸酉年11月6日《申报》(1873年12月25日)。)。同时蘅梦庵主也被认为是《申报》上发表的第一首诗作《观西人斗驰马歌》的作者,此诗描绘了上海的外国人在赛马场上情景(注:见3月25日《申报》(1872年5月2日)。)。他显然是该报的高级编辑。在壬申年(1872)的7月号上刊登了一位日本来宾到报社办公室去看望报社老板美查(Ernest Major)并作诗的消息。在场的四个人也作诗相和,其中第一人就是蘅梦庵主(注:见壬申年7月18日《申报》(1872年8月21日),“东洋槎客诗”。)。显而易见,这位作者倾向于使用自己的笔名:写散文时用小吉罗庵主,写诗时用蘅梦庵主或小吉罗庵主,写通俗小说时用蠡勺居士。有一次,在谈论杭州的犯罪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将所有这三个笔名——甚至还包括第四个西冷下士放在一起。所谓蠡勺居士口述,西冷下士拟稿,蘅梦庵主手录,小吉罗庵主附跋(注:见癸酉年1月14日《申报》(1873年2月11日)。)。
我认为译者很可能是《申报》最早的主编之一,是一个表字叫蒋芷湘的人。在关于申报的研究中,据说在他作为主编的时候还是浙江的举人,他考上进士后就离开了报纸(注:参见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期刊》1934年2.1:220,245页(《上海新闻事业史料辑要》,台北,天一出版社,1977年)。)。我认为蒋的本名应该叫做其章。申报馆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收集了500篇应试文的集子,题名为《文苑菁华》,出版在癸酉年(1873)7月。在报纸的公告上,这本书仅仅被称作为编辑人员所准备的,但很值得思考的是编者的名字署的是蒋其章(注:关于即将出版新书的广告首先登在6月7日(7月30日),称此书为“本馆所编辑之时艺标明文苑菁华”。但关于确切出版书籍的广告则首次刊登在7月1日(8月23日),并延续了一个半月。蒋的名字没有作为编者出现在书中。实际上,在书的第一页没有提到编者的名字,而在前言里也仅仅提到了其笔名,漪生阁主人。但编者的名字被称为蒋其章,请参见《中国丛书综录》第2册,第1563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蒋其章生于1842年,籍贯为浙江钱塘,1870年乡试中举之前是杭州府的廪生。1877年在会试中金榜提名,之后被任命为敦煌县县令(注:这些史实取自于1870年的《浙江乡试录》和1916年的《杭州府志》。)。1876到1889年间浙江的蒋姓考生中唯一在殿试中录取的是蒋其章,所以如果我们关于蒋芷湘的信息正确的话,那么没有疑问他的名字就应该是其章。
小吉罗庵主发表在《申报》和《瀛寰琐记》上的文章告诉一些关于蒋其章的信息。他写过一些关于西方发展的文字,采用了一种幽默的,有时甚至是离奇的笔调,诸如一篇文章讨论过英国布赖顿的新建水族馆,另一篇文章显示了他本人以及他的读者们对于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的驾轻就熟。第三篇文章对“伟大的东方”号轮船的奇特历史作了反思(注:分别参见《鱼乐国记》(第1期),《人身生机灵机论》(第2期),和《记英国他咚巨轮船颠末》(第2期)。)。在壬申年10月还有一篇记录了对长崎的一次短暂访问,显示了对日本风俗的强烈兴趣(注:《长崎岛游记》第2期。)。《申报》上还登过他写的一些传统故事,如寒门出身的妇女为取得贞节而自我牺牲(注:也有一些更加个性化的记载,例如,蘅梦庵主家里藏钱谦益的一本很少见的书。参见壬申年十二月十三日《申报》。)。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1905年公告中所出现的蒋子让的名字呢?子让是不是蒋其章的另一个号?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公告的执笔者错误地将蒋的表字与两位原主编中的另一位的表字,即江西的吴子让,混淆了(注:关于其他编辑的信息,参见胡道静《上海的日报》第244页。吴被聘用于筹办《申报》的那个阶段,蒋被聘用于《申报》将要出版的时候。在对《申报》的研究中,把蒋芷湘的主编任期说成是延续到1884年和1885年为止,就于当时殿试得中并离开了报纸,但日期肯定错了。1884年也没有举行任何殿试。)。
《申报》的老板美查(Ernest Major)和译者(大概是蒋其章)很可能曾一起在《瀛寰琐记》上密切合作。美查的中文很好,他积极参与报纸及其企业的管理。创办一家国际性文学刊物的想法一定起源于他,他无疑参与其运作过程。蠡勺居士在创刊号的前言中即已提到美查(尊闻阁主)的建议。钱徵(钱昕伯)在1878年出版其文选《屑玉丛谈初集》,这是在美查鼓励下编辑和出版的书,他在前言中回忆起四年前,即1874年夏天,当他住在上海的时候:“其时尊闻阁主方蒐辑残编断简,用活字板排印成书,月出一卷,问世初名《瀛寰琐记》”。即使我们承认钱的记载有夸大其词之处,但很显然美查在此月刊的运作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杂志包括诗歌和散文,再加上长篇小说,这很可能是美查的主意。在当时,西方人远比中国人更乐意这么做。将小说连载也很可能是美查的决定;英国小说家通常在他们的小说出书之前都在报刊上进行连载。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假定,很可能是他首先向蒋其章推荐了《夜与晨》这部书,并给他提供了文本。而《申报》和《瀛寰琐记》中所发表的小说的作者都是有名的小说家,他们的书在任何具有良好教养的英国人家庭图书馆里一般都可以找到(注:大约在此时的上海也有一家外文图书馆,即所谓洋文书馆,参见《1874年中国指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1年重印),p.8J.)。美查肯定也帮助解决了翻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提供了多少帮助。例如,是否由他进行口译,然后蒋进行笔头的加工?这样一种双人合作翻译成中文的模式在19世纪末中国相当普遍,直到接近19世纪的时候——所以如果在187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某人自己能全靠个人的力量来翻译一部小说,那将是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尤其是翻译一部要涉及多种领域专业知识的小说。确实,《昕夕闲谈》在顺序上对《夜与晨》做了一些变动,但这些变化可以这样来解释,即作者是在修订和改写初稿后做出的。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就想象出双人合作翻译这种方式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这取决于合作者之间理解掌握对方语言的程度。但我们只假设其中一种可能性,如果《昕夕闲谈》真是双人合作翻译的产品的话,好象说话者(口译者)并没有检查书写者的工作;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那么他肯定会纠正其中偶尔出现的口误。
如果我们假定这的确是一种双人合作翻译的情况的话,即可以把某些文本特征(譬如,一些省略和解释)划归于口译者,而把更多的特征划归于书写者,而其它一些(譬如,口吻)则由两者共同承担。但为了简洁起见,我在本文中不打算做这种划分。根据上下文,“翻译者”这个词既指口译者、书写者,或者兼指两者。
美查为什么会选择利顿的小说作为第一部长篇译成中文不难理解。虽然利顿的声望在20世纪中已急剧下降,但在1870年代他仍然是最著名的英语小说家之一——和狄更斯在一个层次上。他之所以知名,首先是因为虽然有时会故意煽情,却能扣人心弦,他当然还具备其它一些使自己值得推荐的特点。他除了写有很多小说、剧本和诗歌之外,他还写出过象《英国和英国人》这样的著作,在英国政治中他也扮演过引人注目的角色。所以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译成日文的小说——在1879年——也是利顿的小说也就并不令人感到非常惊讶了(注:《恩内斯特·迈特瓦》(1837)及其续篇《爱丽斯》(1838),均由日本人丹羽纯一郎译为《花柳春话》及其附录。参见《明治文学全集》系列中的《明治翻译文学集》(1972)。)。
但我们如何来解释译者恰恰是从利顿为数众多的小说中选中了《夜与晨》呢?它之所以被选中很可能是因为它描述的是现代生活,涉及到英国社会的不同层次,也因为不仅以英国,而且以法国、意大利为背景。在小吉罗庵主给其译本所做的前言中提到该书将通过西方风俗扩大人们的视野,这大概也是美查的部分意图,相同点也更强烈地表现在“上卷总跋”里,在那里指出阅读小说可以改变读者对外国风俗,即外国文化的态度。
为方便起见,我将暂缓讨论翻译的实际接受问题,而留待我谈完其方法和目的后再说。
描述翻译的问题
所有的翻译本身都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之间进行居中调停的工作,如果要对翻译进行满意的描述,两种文化都需要考虑进去。这种调和的本质因翻译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如常用形容词“字面上的”和“自由的”所表明的那样。翻译中的变化可以用一般的术语,说每个译本在两极之间,一极是全方位的保存,另一极则是全方位的同化。关于保存,我是指译者努力尝试进行复制——或者至少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再现——原作的看得出的特征。通常情况下他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即特征对于一种真正欣赏至关重要。关于进行积极同化,我是指作者通过对原作的修改,使之变成一般读者熟悉的形式。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处于两者之间,既非彻底的保存,也非彻底的同化。还有一点要注意,小说的译者很少在整部作品中始终如一。例如,他们在翻译对话时往往采用更多同化的态度,因为为了取得近似于自然话语的效果,他们不得不舍弃词语而更注意场景。
上面提到的差别只能提供一个概念上的框架来描述翻译,它们并不等同于一个程序。一个翻译文本可以就其保存和同化了原文的特点等被分析,而其特点的数量在理论上是无限的。选择那些最有意义的特点需要一种敏锐的眼光,对这些特点进行分析将能发掘出隐藏在译本之后的指导性原则。
就广义而言,《夜与晨》的中译本是一部同化适度的著作,不管是其对话,还是其叙述和说明都是如此。他的翻译修改或除去了小说特色,就如同它补充、裁减或者给文本重排顺序那样。他所进行的修改非常之多,尽管大多数地方只是很小的变动,但仍是不容易将译本和英文原文进行连续几个句子的对比。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缩写,因为它对原文的增加很可能和它对原文的删减一样多。它也没有严重地篡改原文的意思。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主要研究《昕夕闲谈》作为译本的特性,这实际上意味着,检查其积极同化、进行同化的技巧。在我开始这样做之前,请允许我谈一谈有关文化参照的问题。
小说家通常可以通过含蓄的手段来解释不熟悉的东西,但翻译家的权力却有限得多。187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隔绝,两者之间的翻译面临着一大堆涉及如何处置对方作为一种文化独有的问题。主张同化的译者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无关紧要就删除掉,如果是些重要的就予以解释,但常常在寻求某种程度的相似。所有这些方法,尤其是后两种对我们了解译者的思想立场及其翻译目的提供了很多帮助。
还有,所有的翻译,尤其是比较同化的那种,倾向于介绍涉及读者文化的更多专门的东西,从谚语和引用语直到人和事的典故(有些情况的介绍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在一个更高的分析层次上,翻译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化原著中的主题和人物类型,使之符合读者自己的文化。在翻译文本中这些因素的扩散再次衡量了其同化的趋势。
形式,顺序,连续性
如同利顿的很多小说,《夜与晨》用了很多题词——甚至现代的读者都可能认为修饰过度——其五卷书的每卷开头甚至每一章起始都使用。各卷书前的题词引于一首德文诗,“朝圣者(Der Pilgrim)”,作者是席勒(注:利顿出版了一本席勒诗译集,并附传记,《席勒诗歌》(1844年)。),而章前引用的题词则出自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其中有些出处不很有名。使用题词明显是为了显示利顿的博学,象他经常拔高的风格一样也是为了提高小说的文学水平。
译者删除了所有的题词(除了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的一首诗,因为它已放入叙述之中)(注:参见文本的p.103a。加底朗诵一首诗,内容跟克雷布的诗差不多一样。),而在所有章节前都用上中国传统小说回目。他这种做法,产生了贬低小说水平的效果,像平常小说一样,对此我将在下一节中进行讨论。
还有一点很重要,翻译的章节很少和原作的章节相匹配。中文的章节有着统一的篇幅,以符合连载出版和有限空间的要求,但象典型的中国小说的章回一样,它们总是在结尾方式上留下一个悬念,然后再和下一章结合。
不管翻译方法如何使用,有些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时间和焦点的把握总是采取语言上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空间方式,因为中国的标点符号还没有象英文那样提供很多分段的方式。评论的功能则通常通过一些词汇来表示,如“看官”或“原来”。作者在原作中没有标出的评论,在翻译中通过这种方式介绍出来,就象那些被译者插入的话一样,但这可能导致读者思维的混乱,因为他猜不出这是作者的评论还是译者的评论(注:有时译者仅仅是对叙述者加了些评论,所以加深了这种混乱。)。
就方式和时间而言,对人物身份的鉴别常常和原作不一样。18和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喜欢推迟公开人物身份,但这种技巧并不符合中国的习惯。利顿有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道出人物身份。例如,小说重要人物非利,即年轻的非利的爸爸,出现在小说原作的第一章,但直到第二章才明确身份,但在译作中在第一节即表明了身份(虽然它仍然称其为“客”)。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凯瑟琳(中文为爱格)、她的小儿子希尼、林贲爵士和其他人的身上。
类似情况还在背景知识的介绍上,在英文中这常常被压后,而通常在中文里很早就说了出来。这样非利和爱格很早就在译本中确定了身份时,他们的家庭及其处境也就一目了然。原文中留待人们想象的动机问题,在译本中通常也是一清二楚。译本中有两三个例子,一件神秘的事早早就被揭开了谜底,其代价是损坏了一些原作中精心设置的悬念。例如,白尼对加底的秘密监禁——两人都在巴黎制造假币,如果伯尼告发了加底,他既可以得到谅解,也可以得到奖金——在中文里我们很早就得到了解释,由译者道出了原委,他惟恐自己的读者会感到困惑(“此处若不将此情节叙明阅者未免如堕云雾这一节事情后文再行交代”)。在另一个例子里,他解释了加底所受到的巴黎捕员华发的秘密恐吓。虽然这些变化是部分根据读者理解的需要做出的,他们也都符合中国小说的一般趋势。
那么究竟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叙述事件的呢?译者最喜欢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一个很大的例外发生在第二卷的第四节,这里他按照英文一整节的篇幅进行了倒叙。估计他这样做是因为两件事情同时出现的缘故。他没有在两者之间进行来回穿梭,而是选择了一件事的线索进行叙述,这件事牵涉到了非利(康吉),然后再回过头来叙述另一件事,涉及到了他的弟弟希尼。在这种情况下,连续性——尽可能延续同样的焦点人物叙述——被认为比时间顺序更为重要。
总的来说,一种平稳的延续性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利顿则象同时代的其他英语小说家一样,在没有设定场景的前提下,喜欢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上,显然希望获得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在几章的开头他经常这样做,其中好几章用对话开始,尽管读者对这些场景还一无所知,有时甚至连对话人是谁都不知道。但这些跳跃对中国的译者是不适合的(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叙述可以在时间或焦点人物两者之间择一进行跳跃,但不可能同时两者都进行跳跃式的叙述)。作为替代,在事件之间则要有一种简短的连接性的叙述,场景有设定好的,也要有明确的参加者。一个很大的例外出现在第三卷的开首,在英文中开卷是对一位神秘的络弗先生开办的巴黎上流社会婚姻沙龙所作讽刺性精心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中文本没有作任何衔接性叙述便仿效采取了这种排列——但它却立即把络弗先生当成了加底。
译者是怎样将小说在中途截断的?在刊物的最后一期中,他让加底死于警察的乱枪齐发之中,作为小说的部分结尾。但然后,他在承诺用一个不同的题目的续篇给出结局之间问读者康吉出了什么事,“性命如何?看官请掩卷思之这康吉原是卷中第一个人物这一枪来那里就会将他打死?”
风格、声调,语言水平
删除题词和用世俗的回目取而代之是译者最极端的变化方式:他拒绝利顿那种雄伟的风格。
利顿风格的主题给我们带来某些困惑。当写那些非小说类作品如《英国和英国人》、关于席勒的传记、或者自己的自传时,他可以写得很清楚很好;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甚至称赞他的《英国和英国人》作品的优美风格(注:约翰·克里夫,《英国和英国人》的前言。)。
但利顿的小说风格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在近几十年来更是处处被嘲笑和奚落。我认为对于困惑的答案可以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中找到,这部自传可能写于1852和1855年之间(注:参见罗伯特布瓦·利顿,《爱德华·布瓦和利顿爵士的生平、信件及文稿》(伦敦:Kegan,Paul,Trench,1883年),第1册第5页。)。利顿讨论了他的小说所受到的批评,并注意到其早期著作中所接受的莎士比亚和欧里庇得斯的影响(注:参见利顿伯爵所著《爱德华·布瓦·第一爵士利顿的一生》(麦克米兰出版社,伦敦,1913年)。这些引语见第一册88-89页。)。
在《英国和英国人》讨论小说风格的时候,他使用了同样的类比:“小说,还有它的图解式的描绘,要求熟悉的感情,是适合于大众的——因为它是文学的雄辩术。”(注:第298页。)他显然把他的高雅的风格视同于戏剧独白或者雄辩语言。这也是他故意地为了“把读者赶入激情”的做法。
即使在利顿的小说中,《夜与晨》也以“其铺张风格”著称(注:《爱德华·布瓦的一生》第2册第31页。评论是作者的。)。下面这段文章紧跟在爱格的葬礼之后,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葬礼结束了,死者埋葬了。这好象是多么奇特的一件事啊,这个身体,我们小心谨慎地表达着赞颂,我们感受珍贵并小心照料,我们相互拥抱以抵御寒冷,我们甚至希望从她面前搬开石头以不使她被绊倒,而所有这一切一下子突然就消失了——于是产生一种憎恨的东西,地球上看不见——一种可恶的讨厌的事物,但却要被隐藏和遗忘!而这种骨肉相连的成份在昨天还是那样的强烈——男人所尊重的,女人曾经爱过的,孩子们所喜欢的——今天却悲哀得没有力量,不能去保卫或守护那些最亲近的人;其财富受到洗劫,其愿望受到唾弃,其影响也随着最后的叹息而终止。唇上的最后一口呼吸就是“生”“死”之间的巨大的区别。(1.5.72-73)
中国传统的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几乎不会允许这种冗长的吐露感情的叙述方式。译者舍去了整个大段文字,并非对爱格的死亡漠不关心——实际上在译本中这段痛苦描述增加了不少——而是因为这种雄伟叙述的沉思在译者小说的概念中根本没有位置。他经常译出利顿关于人物和事件的言论,却又常常略去其雄伟演说。
利顿的文雅风格并不限于言语夸张的沉思段落。在描绘一些年轻人同情被马撞倒的老人时,他评价道:他们是年轻人并且“还没有被世界的车轮磨成石头”,中译简而言之就是“年纪尚轻良心尚在”。在更具有戏剧性的时刻,利顿甚至在对话中就可以达到他的文雅风格境界。当加底准备对已将他出卖给巴黎警察的伯尼开枪时,他叫道:“我的奴隶身份和所有秘密也完蛋了!”当非利最后意识到加底犯罪的真实本质时,他惊叫道:“不要对我皱眉,嗜血的人!”两次喊叫在中文本里都被省略了。
利顿还有另一种文雅的风格,和他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都有,即调侃的或反讽的委婉文体。钓鱼被描绘作“垂钓弟兄们的最佳运动”,渔翁被称之为“邻居的沃尔顿们”(注:1.1.20,沃尔顿(Izaak Walton)是一部古典钓鱼著作的作者。),中文的表达则减少到很简单明了的语言。有很多像这样的事例。
因为翻译回避了利顿写作时的文雅的风格,其文体范围就远比英文小说狭小得多(注:译者同样也使得利顿所喜爱的突兀多变的对话变得通畅自然。)。
叙事技巧
在翻译中的叙述可以看到一些重要趋势,特别是通过增加的细节描写来扩大场景和将简略叙事改变成场景,还有通过一个人物的视角而不是非人格化视角来观察一个场景。这两种趋势都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征。
场景,尤其是那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场景,通常在翻译中被增加了,有时加上了具体的额外的细节描写,有时加上对话。尤其是那些冗长的讲演和叙述,通常会被插入的感叹词和问题分为对话。这部小说里就有许多表达思想的段落,很大一部分是由译者或者进行补充或者夸大了的,很自然地从概括性叙述变成了场景性叙述,因为中文叙述倾向于将思想当作直接的引语来处理。
英语小说通常从一个超然的视角或观点来描述一幕场景或一个人,中国小说刚从人物的角度开始描绘。例如,林贲爵士参加在米兰举行的迈克格莱哥(MacGregor)的晚会的那幕场景,原文中是从一个非人格化的、超然的视角进行叙述,但在中译里则通过康吉的观察来描述。有一处在英文小说里是以这种方式开头的:“一天早晨,三个人被看见由圣田尼门步行进入巴黎城。这是一个春季里阳光明媚的日子……”译者无法接受非个人化的“被看见”,他改变了顺序以及观察的视角,从日期和天气开始讲述,然后才说“这一日那巴里司守城兵役看见有三个人从田尼门步行进城。”
有一种情况是翻译被迫采用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原文已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的堂弟阿大出现的时候,康吉躲藏起来并在暗中观察。叙述者对这两个男人的外貌和体格进行了比较:“这两个男人就其个人天生的优点而言不好相比;康吉,尽管他经历坎坷,碰到过不少困苦,但现在已经成熟起来,成长为一个在体形和外貌上都少见的完美形象。他胸脯宽阔,气宇轩昂……”小说里没有人物可以把两个人进行比较,但这一段实在是太重要以至于无法省略,所以他让叙述者将读者转移到这个任务上来:“看官你请将他二人比一比。”视角可能不是人物的,但至少在形式上它不是非个人化的。
接受外国文化的参照
我现在使用“外国”这个词来指那些在原文中参照的东西,大概在1870年代,估计当时的中国读者对这样的提法还很不熟悉。正如我曾提到过的,在同化性的翻译中这种特点可能就会被删去,改编或者是加以解释,删去的例子如,banns(结婚预告)个词,在字典里将它定义为“在一所准备举行婚礼的教堂里作口头或书面的公布”,翻译中不得不解释婚姻是在教堂里由一个牧师举行的,还要解释在教堂登记注册的事实。因为真正来解释banns这个词会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这个词就理所当然地被省略了。再举个例子,白拉先生,一个狄更斯式的人物,很喜欢视自己长得象拿破仑的样子,他对非利(康吉)说:“现在把我想象成在圣赫勒那(St.Helena)……”(注:比较英文本1.6.104,St.Helena是拿破仑去世的海岛。)翻译中已经插入了一些有关拿破仑生涯的介绍,但就是忽略了这段情况的介绍。还有很多其它这类情况的例子。
改编一般意味着用广义的不需要解释的词语来代替需要解释的词语。例如,“一个邮递员……来回奔波”变成“一人短衣结束身背包裹”,“野外跳栏赛马”变成了“打猎”,“马槽”变成了“池塘”,“断头台”变成了“法场”,“代数”变成了“算学”等等。有部分改编即使带有一些不合适的内涵,但还是适当的,例如lynx-eyed(象山猫眼光锐利)被译成“千里眼顺风耳”,Good Heavens!(天那!)被译成“阿弥陀佛”。
有几次,译者提到的情况只是在英文原著里涉及到。当康吉对加底解释他为什么决定离开伦敦去巴黎的时候,他说:“我说过,我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我站在那座桥上,从桥的一边你可以看到教会首领的宫殿,另一边是修道院的塔楼,那里面埋葬着我在历史里读到过的人物。”英语读者能够理解,康吉是站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从那里他可能看到在河一边的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官邸,另一边是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译者知道威斯敏斯特大桥并提供了其名字“忽鸣士大桥”,他也知道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以及在英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牌匾。但他没有听说过兰贝斯宫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伦敦宫邸,而把它当作了英国政治大议院(注:p.100b。如果是双人翻译,很可能口述者美查认为解释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官邸太复杂了。)。
当译者愉快地承诺要用简单的术语去扩大读者的知识,介绍欧洲的一些习俗,小说中出现了许多解释的例证。有时他想很含蓄地解释一些东西,通过给名字进行界定,例如上面所谈到的英国议会大厦。他对伊顿、基督教会学院、牛津和拿破仑也都使用了类似的含蓄解释。他没有去解释英国的法律,而只是把“按照英律”的短语放进了译文中。
很清楚的解释,通过“看官”或“原来”作为正规的标志,数量更大。这里所列的是部分利用中国类似情况的例子。公用马车和江南航船的比较;伦敦的公园和在香港新近开放的一家公园的比较;西方葬礼上用的黑色和中国的白色相比较;巴黎的侦探和北京的番子手相比较;外国妇女继承财产的从容和中国所发生的法律争执相比较;西方打牌骗子的技巧和中国打牌作弊者的比较;决斗,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也被拿来与在福建和广东的一般格斗进行比较;护照则和中国所用的照会及工部局的捐票相比;牧师所戴的铲型帽——译者认为是学位帽——被和中国的方巾帽相比;英格兰的“爵士”称号被拿来与授给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头衔相比。
涉及到对没有的中国具体相似物的解释,请允许我首先谈一谈有关接吻的实际问题,这是一个困扰中国和日本译者几十年之久的东西。接吻首先是在康吉请求他的母亲爱格给予一个吻的时候提到,中文本将其省略,没有任何提及。第二次,当非利被他的妻子爱格拥抱时,英文仅仅说他“被她的双臂紧紧抱住”,但中译文却选择了这种妻子吻丈夫的场合来向读者解释这种风俗:“原来外国的礼妇女遇着亲人无论兄弟子侄夫婿均以接唇为礼在人前绝不避忌。”此后,接吻或者被省略了,或者通过几种方式翻译出来。
下面仅仅是其他几件事的例子:西方自由求爱的习惯;牧师可以纳妻;遗嘱;五梁栅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非利正是因为试图纵马跨越其中之一而死);温室;拿破仑;律师职员的穷困;决斗;公墓;莫分(松饼)(因为被盗的松饼的重要性);爆(里面有糖,外面有诗);派对游戏“鞋戏”和“瞎汉戏”;“普德士”(Brutus);专利局;从卢梭到拿破仑的法国革命;触摸自己前额表明某人疯狂的手势;乡村舞蹈;犹太人;英国青年人的欧洲大旅行(没有命名,但直接从上下文中正确的推断);西方刑法;欧洲浴室;德国矿泉疗养地;欧梨舍(爱丽舍宫);裤子口袋;警察的叫子。
只在很少的情况下译者会试图直接去利顿那些长长的明喻中找一个翻译。原本加底正与康吉谈论法国革命后的危险情况,他否认拿破仑主义已经完蛋了,而认为革命的影响刚刚开始感受到。“社会从一头到另一头受到了摧毁,我笑他们想还用小钉子把社会维系在一起。”他继续说:“帝国制度大规模融解后,经过破解产生了大量的生命力,正沿着潮流漂浮,对于国家这首船来说是些可怕的大冰山……”中译没有提到“国家之船”,无论如何也许这在中文里不是一个普通的意象,但它确实是指政府面临的危险“大约有如浮冰山”,还说“那小钉怎能补得大(穴)隙呢”?关于冰山和小钉的比喻肯定让读者感到困惑,所以过了一会在这一节的结尾,译者回到了“所说浮冰山的比喻”,解释北极冰山如何在冰原中松动并向南漂流,给船只夜间航行造成了极大的危险。“所以借作比方哩”。
如果在翻译背后隐藏着任何明确的思想上的动机的话,这是我们期待他们表现出来的地方,即译者对所参照的哪一种外国文化选择做出解释。这些解释将会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对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在以后的日子里,即自1895年开始,对一篇探讨现代欧洲内容小说的翻译将毫无疑问充满了有利于这种或那种文化的对比,但这和这本书的翻译无关。有些比较对西方有利,尤其是在风俗习惯(如求爱和婚姻),法律(如遗产法)和机构(如专利局)等方面,但也有些比较有利于中国。例如,在英国头衔的继承是自动进行的,这就允许堕落的林贲继承贵族的地位,而在中国要取得这种继承则需要官方的正式批准。但这种比较常常要远比通过简单提供情况的解释少很多,从对欧洲风俗习惯有兴趣的几件小事到重要的事实。译者很少让自己发表个人的言论,但他在描绘了派对游戏“鞋戏”和“瞎汉戏”之后,他发表了宽容的看法:“其戏虽然粗鄙然却最喜作此戏法。”
但是,如果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动机的话,他一定显示出了自己的一些兴趣。他将原作中处理得很一般的东西具体化,例如,某些商品,尤其是孩子的玩具就是这样。他更新了加底承认参加的活动,包括“为电线公司传递这些行情机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了两条表示对拿破仑崇敬的评语(注:p.29b及p.108a。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涉及波兰被瓜分的材料,下一代作家肯定高度重视这一主题,在1905年版的广告中,对瓜分波兰和拿破仑的生涯说了不少话。)。总的来说,和他的时代对小说家的期望相比,他给出的道德评判相当之少。
中国文化参照系的传播
翻译里对中国文化的明显参照不限于涉及外国情景的解释上。在任何同化性翻译中,这种需要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渐进的效果,它的出现势在必然。至少在两个层次上可以对他们进行检验,这两个层次分别为语言和主题。
在一个基本的分析层次上,翻译包含了许多的谚语和熟语,其中有一些显然是中国的,它们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翻译西方谚语,而只是作为语言的要素。其中还包括一些中国小说的常见的比喻。最后,还有些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它们可能是无意识中用的,因为它们是深深植入语言之中的,这些参照均包括媒人、缠足、纳妾这样的现象,它们在英国社会是不太适合的。
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中国文化有具体的参照。例如,罗把的非常软弱的妻子,完全在她的丈夫的羽翼之下,被比拟为《红楼梦》中的邢夫人,而林贲,在和加底的决斗中致残,就被比拟为道家仙人李铁拐。有关周昉和杜甫的一个俗语被插入到译者作了大量改写的一封信里。来自李商隐一首“无题”诗的两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引用时称为来自于“古人”,但这两句诗名气太大,甚至可以看作是谚语。爆竹外面的诗句充满了具体的中国文化指称。
有几种情况,可以看出翻译已朝着熟悉的中国主题方向移动。在小说原作中,在前面章节里的威尔斯山庄位于遥远的山谷里,游客踪迹罕至。几乎没有办法“吸引那些更坚定的狂热者前来”。不幸的牧师排士在剑桥虚度了青春之后,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囚禁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地方。但中文翻译却无视小说的讽刺意味,把这座山庄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显得更合适的是,在伦敦之外的房子,那里非利安置了爱格,也在翻译中变成了一座田园式的宫殿,并重新命名为“桃花别境”。
第二个主题有关穷困的文人。排士是位遭受过挫折的牧师,受到过利顿叙述者的冷嘲,在中译里成为受人同情的一个经典人物——一个穷困的知识分子。翻译强调了他处境的痛苦,对文本作了扩写,以告诉大家他无钱娶妻、他的疾病、绝望以及死亡这样一些情节。这和作者十分重视对悲痛场面的描写是一致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悲痛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英文文本经过改编以适应现成的中国主题。例如,在(爱格的哥哥)磨敦身上所体现的惧内型主题,此外还有关于友爱、子女孝行以及因果报应等主题。但最有趣的还是加底所体现的英雄主题。加底,正如我已解释的,是利顿同情的罪犯之一。他发展成为一名罪犯的过程,利顿将其部分归因于其先天性情和客观环境的产物(他被自己的父亲、叔叔和他的奸诈的朋友林贲所误导和出卖)。利顿把他看作低水平的革命者:
(加底)是伟大精神的化身,这种精神是由世界规律培养起来反抗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在宏观上这个世界由于其不公正而受到了惩罚;而在微观上受到蚕食和干扰,就象老鼠在啃大象的蹄子:——在巨大的戏剧舞台上这种精神冉冉升起,硕大无朋,令人崇敬,表现在战争和革命的英雄人物身上,诸如米拉波、马拉和拿破仑;在小型舞台上,它表现为进行煽动的政治家、狂热的哲学家和暴民作家;在被禁演的最小的舞台上,被社会唾弃的人坐在臭气冲天的灯前,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这些人里从没有哪一位象加底扮演的流氓那样更为成功或是带有更多悲剧的尊严。(3.4.322)
译本插入一段提到米拉波、马拉等,等:“此种人物倘或计谋不中则就落于下流不守王制奸法盗窃无所不为计谋若中则反为天下豪杰英雄人皆畏归附。”(p.112b)后来,原作的叙述者说:“法律是人类对付敌人——犯罪者的象征。”(3.5.345)译者改变如此:“法律者朝廷之威权世人即有胆力那有抗拒朝廷威权以自称为英雄豪杰的?”(p.125b)在康吉看来,加底一直是英雄;后来,他又把他看作“英雄好汉子”,在最后的时候,在看到加底身上所表现出感化人的心灵、结交朋友的非凡本事时,他对自己说:“何等的英雄豪杰就是失足做了匪类生涯还望他后来改悔如今都完了。”
很自然中文译者不再提到利顿的“伟大精神”了。他选用他熟悉的好汉题材范围来放置加底,将他塑造成一个既凶狠又豪爽,看得见摸得着的英雄。他还把加底放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叛逆题材领域来描写。这种叛逆不能改朝换代就称为强盗。可以这样说,任何同化性的翻译都将会倾向于走这条路,将不熟悉的主题放进读者的文化圈里,让类似却又远非雷同的主题在一道互相适应。
译者的评论
译者同化的本意通过其评论得以大大增强,这样做首先用中国文学概念保卫了小说这种文体,其次又因为其所谓的中国技巧而对其表示了赞扬。进一步说,译者所选择进行赞扬的技巧,在有些情况下,不是已经插进去的,就是他加强过的。
评论部分包括一个简短的序言,前四节中每节的结尾有总评,第一卷书末的总跋,以及在翻译结束时的一些注释。此外1873年1月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宣布翻译的广告:“新译英国小说”。虽然序言显示了利顿的序言对1845年版本的某种影响,但它主要关心的还是依据传统中国标准来鉴赏这种英国小说。在用熟悉的语言写出了简明小说史之后,它宣称任何小说家都必须遵守道德原则和文化的社会规范。这部小说的积极价值在于它表明“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分别参照康吉和罗伯特·巴福特)小说同时也介绍了很多有关西方风俗的情况,“其所以广中士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读者们应该不至于把这部小说当成是“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
评论者经常指出这部小说里所用的技巧都是属于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小说批评,例如他认为,小说开篇的秘密婚礼是其关键所在,“如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他还争辩说,小说采用迂回方法突出外围人物排士的手法要高于任何非利对爱格求爱的直接描述。而非利和爱格的幸福则通过排士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妻子和其悲惨命运得到了暗示。这种技巧被称之为传统的术语“烘云托月”。我们已经明白译者是怎样为了自己的目的,试图将排士表现为一个可怜人物。这种对比的价值在第二节中提到两封信时再次被显现出来,从非利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心醉神迷的幸运儿,而从排士身上则看到了一个伤心潦倒的人物。译者自己应当对重写第一封信和起草第二封信负责。
在其第一次总评中调用了很多批评技术手段之后,译者终于向读者泄露了他正在做些什么。在赞扬了小说明显采用了中国技巧之后,他调侃道:“作者其得力于芥子园各种才子书耶?”(注:芥子园是17-18世纪的一家书肆,虽然它重印过《六才子书》中的两部小说,但好象没有出过《六才子书》。)这里提到的是金圣叹所选编并评注的《六才子书》。金圣叹是一位最有影响的小说评论家,而提到金圣叹则是对译者同化态度的一种幽默化认可。
我们已经明白译者为了其译作能够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做了多大的努力。但我们究竟能推论出关于这部著作的实际接受情况的什么来?
连载成为世纪之交小说的标准形式(注:例外很少,在1872年五六月《申报》连载了两种中译本(原作是两部英文小说的一部分),《谈瀛小录》(4期)和《乃苏国奇闻》(6期)。),但是一般来说,在《昕夕闲谈》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尝试。正如我说过的,这有点象来自英国的想法,很多小说家,但不包括利顿,通常都在其小说的单行本出版之前进行连载。这本月刊的初版印数为2000份,鉴于它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份文学期刊,所以这已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目。广告声称:“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任剞劂之役”,并且作了不太准确的预测,称译文每个月发表三到四章,全部内容将于一年内完成。广告很关心中国读者可能不太喜欢这种读小说的新方法,因为下面一句就是:“士君子务必逐月购阅庶不失此书之纲领。”《申报》1873年10月27日的一则宣布第一卷完成的通告上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关心,称在第二卷第一部分将收入“上卷总跋”,概述了此前的内容以使可能没有读过前面内容的读者能跟上思路。
1875年9月,《瀛寰琐记》刊出其最后一部分的6个月之后,《申报》上登出了“全帙”的广告。实际上,出版的书让康吉和美费儿夫人相遇并堕入爱河,就象原作者三节所描述的那样(第三卷第11-13回),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将会结婚。而在利顿的小说里,非利(康吉)和美费儿夫人这个女人只有过一段短暂的爱情故事,之后在经历了许多冒险和发现之后,他最终还是与凡尼结婚了。广告对“全帙”的描绘让人觉得好象它是部标准浪漫型的“才子佳人小说”。
对这部小说拦腰截断肯定意味着它没有得到读者们的很多喜爱。不仅翻译从来就没有适当完成,而且也没有带来任何模仿。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这一点就显得非常显著。在日本,《恩内斯特·迈特瓦》和《爱丽斯》1879年的译本非常成功,所以译者很快就接着翻译了很多利顿的其他小说,对大多数人的口味而言,《夜与晨》至少是和《恩内斯特·迈特瓦》一样有趣的小说,而中国的译者除了对文本的处理更为充分以外,就整体而言比日本的同行更加有同化的倾向。中国翻译的相对失败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其连载的方式,中国的读者对此还不适应。在我所引用的《屑玉丛谈初集》的前言里,钱徵接着批评《瀛寰锁记》及其后续期刊所提供的空间太有限。每期只有30页——实际上是24,还得划分成四种不同的材料。这就导致出版物得分成多个部分,引起“阅者病焉”。我想他肯定指的是《昕夕闲谈》,它比《瀛寰琐记》上连载的任何其他作品的时间都要长。不管怎么样,小说进行连载的试验并非一个新潮流的开端。虽然中文小说《野叟曝言》早在1882-1883年期间就在报纸上连载过(注:在《沪报》和(重新命名的)《字林沪报》上。),但直到1892年另一部中国小说《海上花列传》才在一家期刊上发表。但连载出版几乎不可能成为影响小说接受的主要原因。所谓的“全帙”单行本出版于1875年,但在1904年之前还没有其他版本被报道过,这说明单行本不大成功。一个更可能的理由是那时中国喜欢读外国小说的人还不够多。《瀛寰琐记》及其后续性刊物从原来重点描述国际性的内容变得狭窄了,最后成了传统的文学作品园地,表明了这一倾向。等到下一代中国读者成长起来,还要二十年时间,那时在变化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他们开始对外国小说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