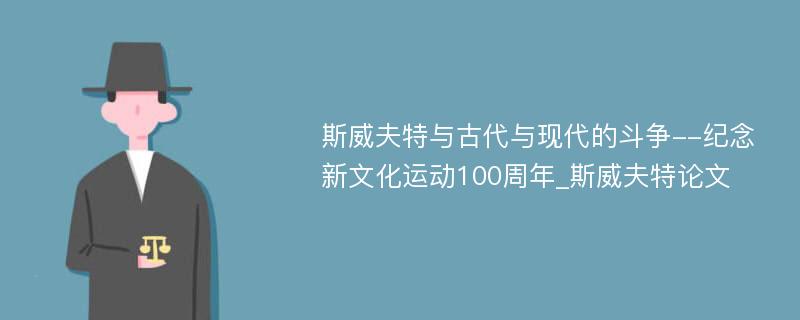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之争论文,古今论文,而作论文,斯威夫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5-0070-07 1690年,出身于伦敦的英国文人、资深政治家坦普尔爵士在伦敦发表了《论古今学问》①一文,对崇今派发起主动攻击,引发了伦敦的古今之争。坦普尔眼力敏锐,他看到崇今派的内在冲动是欧洲新兴王国的崛起,力图摆脱欧洲古典传统和古典德性的规制。他在《论古今学问》中说,西欧的日耳曼诸王国仅仅在近两百年才开始出现自己的学问,与古希腊罗马学问相比——更不用说与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国度的学问相比——只能算是学问上的幼儿:“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西部地区在学问和知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超过了过去那些在学问和知识上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只能证明,我们过去的水平有多低,而不能证明现在的水平有多高。”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就政治制度的优劣而言,欧洲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未必等于英格兰新政制的“水平有多高”。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按孟德斯鸠的说法,这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民主政制。对于坦普尔来说,英国的现代政制创新未必是“巨大进步”,民主政制相比于传统政制未必“水平有多高”。坦普尔在作比较时把我们中国也扯进了论争: 古代中国人就自然哲学写了大量著作;他们伟大而知名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差不多同时代,与苏格拉底一样,他也是开始改变人们对自然无休止、无意义的思考,让他们转到道德思考上来。然而,他们有一点不同,希腊人的重点似乎在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中国人则重视王国或统治的良好状态和幸福,众所周知,这种统治已延续了数千年,完全可以称之为学士的统治,因为其他人无权管理国家。与此相反,崇拜英国新政的崇今派必然会贬低中国的古代政制。1748年,崇英的孟德斯鸠在日内瓦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思想史家伯瑞称之为“启蒙时代”的真正标志。②在比较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大政体类型时,《论法的精神》专门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作为专制政体的样板,一反当时的传教士和智识人把中华帝国视为君主政体的典范和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赞美: 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③ 一般认为,伏尔泰虽然是启蒙文人,但他对古代中国的态度显得较为肯定。其实,在涉及到古今之争时,伏尔泰仍然立场鲜明地贬低古代中国: 中国人在我们通俗纪元前两百多年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道城墙却也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万里长城是一座由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巨大建筑;[埃及的]金字塔是一些虚荣和迷信的遗迹。长城和金字塔都证明人民的巨大耐心,却并不说明任何高等的建筑艺术。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埃及人也好,都不会塑成一件像现今我们的雕塑家所塑造的人像。④ 在我国当今的诸多知识人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式的品评古代中国的姿态仍然时可见到——这仅仅表明,古今之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真正展开而已。 伦敦的古今之争刚刚展开,坦普尔就在1699年元月去世,接替他继续抵抗崇今派的是他年轻的秘书斯威夫特。年仅30岁的斯威夫特写下了题为《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的寓言小品(篇名全题“上周五发生在圣詹姆斯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之战:一份完整的纪实”,通常简称The Battle of the Books[书籍之战]),采用伊索寓言笔法描绘发生在皇家图书馆里的古书与现代书的激烈战斗,隐射当时仍在持续的激烈论战。 不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完成后并未随即出版。1699年元月坦普尔去世后,斯威夫特离开伦敦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帕特里克教堂担任总司铎。1701年,斯威夫特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与争执》。这篇论说文共5章,从讨论古希腊罗马的3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入手,过渡到集中讨论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引发的政争,以及由此引出的僭政问题。在斯威夫特看来,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在任何时代都难免,最好的政制是权力均衡的政制或者说混合政制。在总结古希腊罗马政争的历史经验时,斯威夫特认为首先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是: 国家的权力均衡一旦正式确定,最为危险和愚蠢的作法是对于民众最初的夺权行为做出妥协。这样做通常是为了逃避无理取闹,以获得安宁,或者把妥协当作仅供买卖的商品。这等于拆掉整体去满足一时之需,是江湖庸医的止痛疗法,将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迁就孩子,他会顺从满足;稍微迁就一下恋人,她就会满足,不再有其它要求,于是希望用小小的让步使民众满足。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哪一个公民大会,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它在起初夺权时得到了一点点满足就从此安于现状,假如能找出一条例证,说明公民大会曾经清楚、提出或宣布他们的权限,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通过思考、讨论和辩论调整权力均衡。然而,既然所有事实显而易见均非如此,我认为,在稳定的国家里不必要采取其它措施,那些被托付重权之人应该持之以恒,坚定信念,永远不要让步于民众的无理取闹,不要使国家有一丝的裂痕,否则无数的权力滥用和争夺迟早必定强行涌入。这些话是针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争而言的。论文最后一章直接讨论到英国的当前政制问题,文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民众僭政”这个语词。在斯威夫特眼里,晚近半个世纪的英国政制变革证明的是一个古老的法则:“先是迎来了民众的僭政,然后是单个人的僭政。”这篇论说文看起来与当时的“古今之争”没关系,其实不然。毋宁说,斯威夫特才真正看懂了坦普尔的《论古今学问》。事实上,这篇论说文彻底挑明了《论古今学问》所隐含的论题,而且通篇都在比较古希腊罗马的政争与现代英格兰的政争。议会民主制对西方人来说的确不是现代才有的,古代的雅典和罗马都有平民议会建制。对此斯威夫特的看法是:“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重大议事机构有时抛出无知、鲁莽、错误的决议,常常让我感到诧异。这使我意识到,民众的议会也会犯个人所能犯的所有问题、蠢事和邪恶。”与如今的我们喜欢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优越相反,这篇论说文用古代史例来论证民主政制的品质低劣,并进而证明英国的民主革命品质低劣。虽然这篇论说文以史带论,斯威夫特的论析实际上依傍的是柏拉图的观点:如果城邦不是由有卓越德性的人统治,那么,权力“必然成为你争我夺的东西,这种产生与自己人之间和城邦内部的战争必将毁灭这些人和其余的城邦”。在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中,今人的确找不到对民主政制的颂扬。因此,贬低古典作品,才能更顺当地为现代民主新政提供论证。 1704年,时年36岁的斯威夫特出版了长篇寓言体作品《木桶纪事》(又译《木桶的故事》),一同付梓的还有《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和《圣灵的机械作用》。⑤作为坦普尔的学生,斯威夫特清楚意识到,眼下的古今论战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古今政制之争。在《木桶纪事》的“序言”中,斯威夫特把霍布斯称为“我们时代具有威胁性的才子”——第九节的标题“关于共富国中疯狂的起源、用途及其改进的离题话”,据说针对的就是霍布斯《利维坦》的书名。《木桶纪事》问世20多年以后,斯威夫特又发表了篇幅更大、寓意更为深远的《格利佛游记》(1726)。⑥这部传世的经典之作是斯威夫特对“古今之争”所作的更为透彻的思考,堪称“古今之争”时期最为深刻的政治哲学著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则是最令我们尴尬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我国教育部如今已把这部作品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义务教育部分”推荐书目,印数相当可观。由于这部“世界文学名著”采用的是寓言文体,要概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非常困难。⑦一方面,寓言式的叙述使得这部作品据说看起来像是“深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另一方面,书中大量涉及的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知识,显然又不是“儿童”们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就内容而言,《格利佛游记》与比它晚出22年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属于同类性质,两者都是政制比较之书,差异在于,《论法的精神》推崇现代式民主政制,《格利佛游记》推崇古代式君主政制。不妨说,这两部书是崇今派智识人所推崇的现代式民主政制与崇古派所推崇的古代君主政制的品质对决。 《格利佛游记》中的主角格利佛是英格兰人,按书中所记叙的出海时间推算,他应该出生在“共和革命”之后、“光荣革命”之前,上过剑桥大学。《格利佛游记》以第一人称形式分4卷记叙了格利佛作为外科医生4次出海远行的奇遇。显然,格利佛作为英格兰现代知识人的身份是整个作品的支点,在他身后是被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视为人类理想政制的样本:英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 格利佛第一次出海远航流落的地方是一个名叫Lilliputia(利立浦特)的“小人国”,因为那里的人渺小委琐,政体的品格也渺小委琐。无论是18世纪的读者还是今天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个“小人国”就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如今我们所追慕的两党政制,在格利佛眼里不过是高跟鞋党与低跟鞋党之间委琐的争权夺利,各自都得靠扫街拜票获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种政体中,商业利益是唯一的政治动机,政治生活成了人的自然欲望的玩物。这种新式政体来自于基督教分裂导致的国家内战:为了摆脱宗教内战,英格兰最聪明的智识人(斯威夫特指的是霍布斯和洛克)设想出了一种以实现个人自由而非以实现美德为取向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存自然性命及其私有财产。斯威夫特用“小人国”来指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十分切合现代自由主义政制观念的品质——灵魂的渺小委琐。当然,在一个比如说伏尔泰这样的崇今派眼里,情形并非如此。1733年,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1726-1728)动笔写的《关于英格兰国族的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在伦敦出版。⑧此书仅比《格利佛游记》晚7年,由于伏尔泰是个崇今派(或者说由于他的灵魂类型),他对英国新政的见解与格利佛有天壤之别。 在第2卷里,格利佛记叙的出海流落地是一个名叫Brobdingnagia(布罗丁奈格)的“大人国”,那里的人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心性高尚,民风淳朴。这是一个尚未经历现代革命的古老的君主制王国,“属地之内没有宗教纷争或者战火连绵的历史。他们唯一的政治难题是古老而自然的君主、贵族与民人的冲突,这也已经在很早之前就通过建立一个均衡的政体解决掉了”。显然,格利佛笔下的“小人国”与“大人国”形成的对比,是现代民主政体与古代君主政体的对比。 奇怪的是,格利佛在“小人国”时是个高大的人,他看不惯“小人国”的方方面面,“小人国”中人也看不惯他,甚至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会认为他的行为举止莫名其妙。与此相反,格利佛在“大人国”则是“小人国”的代表,“大人国”的国王把格利佛放在手掌心上与他谈话,询问他属于代表商人和金融贵族以及其他新生资产者上层的辉格党,还是属于代表大地主和门阀贵族利益的托利党。格利佛在书中的这种角色变换,与其说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国度的身份不同,不如说表征的是同一个国家的知识人的分裂。如《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在一开始所说,如今,一个“智识国家”的读书人分裂成了崇今派和崇古派——格利佛表征英国知识人,但英国知识人分裂为两派。于是我们看到,来到“小人国”的格利佛通过描述利立浦特的古代政制向新的君主表明,古代的利立浦特并非“小人国”。这个国家变得渺小委琐,是“光荣革命”的结果。显然,这个格利佛是英国知识人中的崇古派。与此相应,我们在第2卷看到,格利佛向“大人国”的国王介绍自由民主新政(同样是在第6章)。听完格利佛叙说英格兰晚近一个世纪的大事记后,“大人国”的国王对格利佛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一再被人引用: 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 对于英国走向商化民主政制,“大人国”的国王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你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是大自然让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可憎的害虫中最有害的一类。 “大人国”的国王拒绝了“爱自己的国家”的格利佛提出的有利于“大人国”现代化的建议,理由很简单:“爱自己的国家”的含义是“爱”现代式的自由民主政制,不爱这种政制等于不爱国。那样的话,“大人国”就会跟着英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国”。让我们会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格利佛已经描述了如今我们称之为导弹甚至原子弹一类的新式武器,以此证明英格兰的新政制何等先进。但是,这个格利佛清楚地知道,他所代表的新国家与“大人国”的差异最终在于“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他认为,“大人国”的国王闭关自守,满脑子偏见和狭隘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在我国以及欧洲的文明国家却根本不可能产生”,因此他说:“如果把住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的一位君王的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当做全人类的标准,当然很难令人接受。”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很像我们的古代,因为,卷2中的格利佛针对“大人国”说的那些话,与我们如今的一些知识人对自己的国家说的话一模一样。而且,他们也像这个格利佛向“大人国”讲述英格兰近代大事记那样,通过翻译更为详备的英国史向自己的国家推荐英国模式。在把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今天,《格利佛游记》的确不能算作一部极端反动的书。毕竟,第2卷中的格利佛提出了新的“全人类的标准”或者说新的“普世价值”:一个人相信自由和民主就是好品德,不相信这种价值就是坏品德。 如果说《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突显的是读书人的灵魂品质的优劣,那么,《格利佛游记》突显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品质优劣——如布鲁姆所说,在斯威夫特看来,古代政体具有“对秩序的远见”。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说法,灵魂品质的优劣就像大人高过小孩。因此,“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对比,首先是灵魂品质优劣的对比。何况,读书人个体灵魂的品质与国家政制的品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说,有多少灵魂的类型就有多少类型的政体。苏格拉底区分了5种灵魂类型,与此相应也就区分了5种政体。即便不能说《格利佛游记》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仿作,也得说《格利佛游记》延续了《理想国》中的问题。与此相反,无论伏尔泰的《关于英格兰国族的书简》还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抛弃了《理想国》中的问题。 格利佛记叙的第3次出海是在1706年动身的,这次到的地方不止一个,而是5个。首先到的是一个叫做Laputa(拉普塔)的岛屿,由于这个岛屿“似乎能随意升降,或者向前移动”,格利佛称之为“飞岛或者浮岛”。格利佛发现,这个岛的国王是个精通数学的天文学家,国家的主要阶层也是这类人。这个飞岛国的国王对格利佛所到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宗教和习俗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他看来,政治的事情很简单,如果哪个城邦发生动乱或叛乱或剧烈政争,用天文学方式处理易如反掌——“只要国王能说服他的内阁和他合作,他就可以成为宇宙间最专制的君主”。显然,这个飞岛的政制基于现代天文学原理,它表征的是新理性科学废除传统生活方式的雄心和自信。 格利佛随后发现,飞岛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支配好些岛国(都是飞岛),首都是“拉格多”(Lagado,据说隐射伦敦)。格利佛乘坐飞行的拉普塔岛来到首都拉格多的所在地巴尔尼巴比,下降到岛上以后,格利佛在首都停留期间受到殷勤款待。这个城市是设计家的家园,最重要的地方是科学院。当格利佛走进科学院时,发现全是搞各种试验的实验室——其中一间挂满了蜘蛛网,带领格利佛参观的人高声尖叫,要格利佛千万小心别碰乱蜘蛛网,因为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蜘蛛代替蚕抽丝这一古老传统。如果我们事先读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就会知道,这一试验所具有的现代含义是什么。由此来看,通常把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理解为“乌托邦”是错的,毋宁说,格利佛所到的飞岛是崇今派头脑中的王国,它并非乌有之乡,而是崇今派的智性之乡——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看来,斯威夫特的笔法是,通过卷1和卷2比较“小人国”(民主政体)与“大人国”(君主政体)的品质之后,《格利佛游记》进一步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商化民主国这种理想政制是由什么样的头脑设计出来的。换言之,卷3的飞岛之行深化了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的比较:如果说“大人国”政体追求的是常识性的道德德性,那么,“小人国”政体追求的就是技术知识所带来的舒适和快乐。 格利佛还发现,飞岛上的科学家对政治和时事非常关心,讨论国家大事或一个政党的主张时,非常激烈,寸步不让。显然,飞岛上的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才真正懂政治,而且有特殊权利去改造所有传统的政治,因为他们有新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实验理性原则确立了新史学。不用说,对于摧毁“大人国”来说,这门学问比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火力大得多、管用得多。 参观过飞岛京城的科学院后,格利佛本来要去另一个飞岛拉格奈格,在马尔当纳达港转船时,由于一时没有班船,当地一位高贵的绅士建议格利佛去附近一个名叫格勒大锥(Gludubdribb,其含义是“巫人岛”)的小岛看看。到了那里以后,格利佛发觉自己到了一个极为古怪的地方,因为那里经常出没许多古人的魂。原来,这里是现代式的新史学专门处理古人英魂的地方。格利佛用了第7-8两章篇幅来讲述在“巫人岛”的经历和见闻。他首先要求见荷马和亚里士多德,并希望也见见给他们做评注的后人。这种人一来就是好几百,由于惭愧自己对荷马和亚里士多德胡说八道,他们都躲得远远的。荷马和亚里士多德对这些后人大发雷霆,说他们的灵魂缺乏理解高贵精神的品质。格利佛特地还让他们请来笛卡尔和伽桑迪,这两位当着亚里士多德的面承认自己“在自然哲学方面”犯了错。 最让格利佛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现代式新史学家人数太多,他们“像娼妓一样哄骗世人”,颠倒黑白地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写成“最卑鄙的流氓和卖国贼”——反之亦然,把历史上“最卑鄙的流氓和卖国贼”写成了不起的诗人政治家。如今好些学人都惊讶,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利佛能够准确预见到辉格党式史学的出现。甚至我们中国学人也难免惊讶斯威夫特预见到了当今的新史学笔法。不过,最让人觉得斯威夫特的飞岛记具有历史预见性的是,格利佛后来发现,各个飞岛虽然有海洋隔开,从地理上讲其实是一个大陆,它“向东一直延伸到美洲加利福利亚以西的无名地带”,通过拉格奈格岛,这个大陆还与日本“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个飞岛大陆有如“英美”世界,如今的“美日安保条约”就像是拉格奈格岛与日本结成的“亲密同盟”的进一步巩固。 有论者认为,卷3的飞岛记显得松散,故事性不如前两卷。其实,这一卷的古今之争色彩最为明晰。不过,相比之下,格利佛在卷3中的身份比较模糊。一方面,格利佛对飞岛相当鄙视,尤其对飞岛首都的科学院十分厌恶,显得像个崇古派。毕竟,无论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王国学院还是1668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都是崇今派知识人的摇篮。可是,格利佛在飞岛时与岛上的大贵族(大数学家)也相处很好,甚至愉快且秘密地相互交流政见。格利佛对岛上的语文考据家的科研提出意见时,马上被承认有原创性,答应给他署名权。凡此表明,卷3中的格利佛又是个崇今派。即便在“巫人岛”时,格利佛让亚里士多德反驳了笛卡尔,却没有反驳培根。格利佛有可能与同时代的伏尔泰一样,信奉的是培根而非笛卡尔的新科学方法。也许我们可以说,作为英格兰知识人,格利佛有两类:崇古的和崇今的。如果是崇古的,他来到飞岛必然心生厌恶,如果是崇今的,就会在飞岛感到十分愉快,并参与岛上的实验。 这个双重的格利佛形象在卷4得到进一步证明。卷4虽然题为“慧骃国游记”,其实,这次格利佛所流落的地方并没有名字——与此相反,前3卷的标题中都没有出现country(国)这个语词,这次却出现了。还有一个差异值得注意:格利佛记叙的前三次出海,他的身份是外科医生,这次是船长。不过,故事一开始,格利佛就遇到船员造反,他被囚禁起来,然后被扔到一个不知名的岛上——显然,这比喻的是国家政变。我们可以肯定,这段情节是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讲的“国家航船喻”的改写。 格利佛流落这个无名岛国后首先遇到的不是人,而是一群奇怪的动物。然后出现了两匹不同的马,一匹名叫“慧骃”,会说话,善良、高贵、有理性,另一匹名叫Yahoo(雅虎)(张健译本译作“耶胡”),贪婪、凶恶、损人利己。整个卷4的故事仅有4个角色,除了格利佛和无名的马主人外,就是慧骃和雅虎。故事的中心情节来自这样一个问题:格利佛的样子究竟像慧骃还是像雅虎。因此,与前3卷不同,在这一卷里,格利佛谈到了自己,在此之前,他学习马的语言并认识慧骃和雅虎的天性。在无名的马主人要求下,格利佛谈过自己之后又谈到了自己的新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宪政。于是,格利佛的样子究竟像慧骃还是像雅虎就变成了这样的问题:英国宪政究竟像慧骃还是像雅虎?如果我们记得《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在讲过“国家航船”故事后说,这个故事“与城邦和真正的哲人的关系相像”,那么,我们有理由说,斯威夫特的故事要探究的是英国宪政与现代哲人的关系。 通过马主人对英国宪政的评价我们得知,英国宪政属于雅虎一类。可以说,揭示英国宪政的样子像雅虎而非慧骃,是《格利佛游记》的基本意图,否则,斯威夫特不会在《格利佛游记》的前言(“格利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蒲生的一封信”)中大谈雅虎和慧骃。然而,尽管自由民主宪政的样子像雅虎而非慧骃,却并非与慧骃没有关系。飞岛人更像是超级慧骃,除了缺乏高贵,他们并不缺乏善良和理性。在卷4接下来的记叙中,除了辨识慧骃和雅虎这两类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辨识不同的慧骃(因此这一卷题为“慧骃国游记”)。毕竟,当格利佛对马主人说到自己国家的贵族时,这位马主人就断定英国宪政其实更像出自慧骃的头脑。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区分和辨识不同天性的慧骃。斯威夫特要读者注意: “慧骃”中的白马、栗色马、铁青马跟火红马、灰斑马、黑马的样子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才能天生就不一样,也没有变好的可能。所以,白马、栗色马和铁青马永远处在仆人的地位,休想超过自己的同类,如果妄想出人头地,这在这个国家就要被认为是一件可怕而反常的事。 这里列举的各色慧骃其实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白马为代表,一类以黑马为代表。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想起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剖析有爱欲的灵魂时说到的“白马”“黑马”比喻:“白马”要拉着灵魂奔向天上,“黑马”要拉着灵魂冲到地上。布鲁姆认为,“慧骃是从柏拉图刻画的人中推演出来的,而雅虎则是从霍布斯刻画的人中推演出来的”。但斯威夫特把“白马”“黑马”比喻用于区分两类慧骃,而非区分慧骃和雅虎。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宪政的确属于雅虎(霍布斯刻画的人)一类,但这种宪政却出自慧骃中的“黑马”一类的聪明设计。于是,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雅虎式的宪政是黑色慧骃式的灵魂设计出来的——英国宪政是黑色慧骃与雅虎联手让白色慧骃由主人变成仆人的结果。可以肯定,黑色慧骃式灵魂寓意的是崇今派知识人,白色慧骃式灵魂寓意的是崇古派知识人,尽管挑明了这样的寓意会让如今的我们心里很不舒服。 《格利佛游记》以出海探险为基本叙事框架,有人说,这是刻意模仿笛福——顺便说一句,他是英国宪政的鼓吹手——的《鲁滨孙漂游记》。即便这种说法有道理,难道我们不也可以说是在刻意模仿培根的《新大西岛》?要说文学写作的航海经历这一主题类型,鼻祖当然非荷马莫属。读过荷马的我们都知道,奥德修斯的航海经历也是认识自己的灵魂的过程。就此而言,《格利佛游记》模仿的既非培根更非笛福,毕竟,无论在《新大西岛》还是《鲁滨孙漂游记》中,都没有涉及灵魂的自我认识。整个来讲,《格利佛游记》的第4卷就是格利佛对自身灵魂的认识过程,而这个过程基于前3卷的游历多方。只不过,格利佛对自身灵魂的认识在这里聚焦于一个时代的选择:古今之争的选择。所以,格利佛出海探险时“身边总有许多书籍”,一有空闲“就阅读古代的和现代的最好作品”。 已经有悉心的读者注意到,《格利佛游记》寓意的是一个有极高智力热情的人的自我认识过程。⑨格利佛的自我认识从认识自己所在的小人国开始,通过认识小人国,格利佛发现自己有非常强烈甚至极高的智性热情。为了找到让自己的智性热情得以实现的地方,格利佛着手探究过去和现在的最佳政体。接下来他去往大人国。与大人国国王的交谈让格利佛慢慢觉得,自己对家庭和祖国的眷念之情越来越淡薄——这正是我们后来在黑色慧骃身上可以看到的情形。在飞岛的经历让格利佛对自己的智性欲求的性质有了成熟的认识,他从此不再迷恋新科学理性。接下来与慧骃的相遇是格利佛的自我认识最为关键的一课——格利佛发现,慧骃族不仅在好奇心方面与他旗鼓相当,而且追求智性知识的献身精神比他还要强烈。慧骃族献身智性知识的热情受一个伟大的理想支配:打造一个完美的“理性社会”。由于这个理想,慧骃族自己先组成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美德是友谊和仁爱——然而,这两种美德的根基却在自然理性。 按伯柔的识读,小人国人、大人国人和慧骃族的差异让格利佛懂得了人性的差异,这种认识使得格利佛对慧骃族的理想产生了怀疑:自然理性的哲学取代常识非常危险。慧骃族的理想让格利佛深感震撼,认识到这一点后,格利佛就不再看重自己特有的智性热情。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利佛是否得出了伯柔所说的这种自我认识,恐怕见仁见智。毕竟,文本叙事错综复杂,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但笔者可以肯定,伯柔看轻了智识人认识自身灵魂的艰难,他与布鲁姆一样,没有注意到黑色慧骃与白色慧骃的差异。毕竟,格利佛最后回到故土后,他已经不能忍受人味,受不了与妻子和孩子一同生活,“一闻到他们的气味就恶心得受不了”。 可以确定的仅仅是,如《格利佛游记》的“出版者致读者”所言,刊布这篇游记为的是给“青年贵族”提供一部“有趣读物”,免得他们受那些谈论政治和政党的“烂书”毒害。可以断定,这里的所谓“青年贵族”指的是从古至今都会有的慧骃族灵魂。斯威夫特能指望的仅仅是,每个时代凭自然而生的慧骃族灵魂应该好好认清自己,尤其要注意两类慧骃——即便这两类慧骃也还有多种不同颜色:这是灵魂的颜色。毕竟,对于慧骃族灵魂来说,首要的危险是缺乏自我认识。如果没有自知之明,无论慧骃有多高的智性、多奇妙的才华,都有可能沦为雅虎。当然,斯威夫特清楚地知道,不必引导所有人都走向这种自我认识,或者说让雅虎通过自我认识而改变自己不可能。为了让“一般读者广泛接受”,或者说为了掩盖这种灵魂的自我认识,他采用了寓言形式。就此而言,坊间认为此书是“儿童读物”并非不正确。 最后还需提到《格利佛游记》的另一大基本特征——讽刺,这一已经见于《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和《木桶纪事》的特征显然是模仿伊索。我们知道,《伊索寓言》善于通过短小的动物之间的故事来讽刺人性的弱点甚至邪恶,讽刺对象是人性品格等级中低劣和败坏的东西。在雅典时期的阿里斯托芬和古代晚期的路吉阿诺斯那里,这种讽刺诗艺得到极大的提升。他们不仅善于描绘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比如阿里斯托芬的《鸟》)的故事,而且讽刺对象除了人性的弱点和邪恶,还尤其讽刺了慧骃族中的某类灵魂以及民主政制。可以说,《格利佛游记》是阿里斯托芬和路吉阿诺斯作品的现代翻版。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中说,崇今派文人学士渴望嘲笑所有严肃美好的东西,由于自身的灵魂品性像雅虎,他们的作品只能靠嘲笑古传德性为生。斯威夫特参与古今之争的主要作品师法阿里斯托芬和路吉阿诺斯的笔法,使得讽刺叙事这门诗艺本身也陷入了古今之争。 注释: ①这篇论说文是1690年坦普尔出版的文集《杂篇二编》(Miscellanea,The Second Part)中的一篇,1692年,坦普尔对《论古今学问》一文作了修订,次年重印,并被译成法文。坦普尔去世后,被收入4卷本文集(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卷3。中译(斯威夫特:《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附录,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即出)依据这个版本。本文所引均自李春长译文(个别引文略有改动),便于读者核查。 ②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0页。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9页。 ④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0页。 ⑤权威版本见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版中的Jonathan Swift,A Tale of a Tub and Other Works,Marcus Walsh编,Cambridge 2010。《木桶的故事》中译本(主万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没有收入《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和《圣灵的机械作用》。 ⑥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据笔者所见,最为精当的概述见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选编,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438页。 ⑧法文版《关于英国的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nglais)1734年在里昂秘密出版。这部书的中译本名为《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让人误以为谈的是哲学。其实,这是一部宣扬英国清教革命的政治著作,史称“投向旧制度的第一颗炸弹”。 ⑨参见伯柔:《〈格利佛游记〉与矮化哲人》,刘小枫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上卷,李小均、赵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481页。